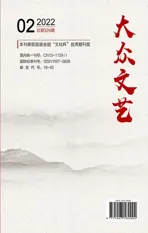从人情汹汹的都市叙事到温情脉脉的故乡叙事*
——论凡一平小说的身份焦虑与身份认同
2021-07-12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桂林 541006)
每位作家都是将自我的问题当成艺术品来进行创造。壮族作家凡一平的小说同样围绕着自我问题来展开自我的探寻,他的小说将个体的生存境遇和心理状态的变化展现得通透且深刻。凡一平出生在广西的一个小山村——上岭,他的作品是由农村到城市后又回到农村的。与尼采的“永劫回归”不同,凡一平的“回归”是主动的,他在城市和乡村中游移和徘徊,然而对于故乡的情怀在其心中永远无法抹去,在他离家之后尤甚,这种故乡的情愫让其实现了身份的认同,也只有在故乡的语境中,个体的身份才能得到最终的认定。
一、出走——身份的困惑与焦虑
个体心理学派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受“向上意志”支配,也就是说人都有着追求优越的天性。这种天性反映在我们的行为之中,那就是每个人都有对自己物质生活和情感生活进行改善和提升的不懈追求。人们总是会选择更好地工作,更好地工作自然意味着更高的要求,相应的,也会给予更丰厚的报酬,人们的物质生活就能得到更好地满足。如果再具体到现实生活中那便像诸如到大城市打拼等形式的生存路径。这个过程就像“打怪升级”一般,人们要不停地提升自己的“等级”,比如从工人到工头、科长到主任、员工到老板。
可以想象,这个过程必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经历困难和挫折后,人会自然产生自卑的情绪,焦虑也会不自觉地浮现。在阿弗雷德·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中提到,人们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三个主要问题:职业、社会和性。在他的理论中,人通过劳动和工作而获得报酬,获得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通过社会活动与社会需要,个体得到成长。人们都需要去逐一解决这些问题对他们的困扰,需要缓解这些问题所带来的焦虑。
面对这些困扰,凡一平小说《请你来爱我》中的草梅与《禁欲》的大学讲师胡光,都试图消解自己身份的焦虑,他们妄图用荒诞刺激的性爱来填补自身精神世界的空虚,渴望在身份的焦虑与错位中获得一种变态的快感。这种行为看似与社会合一,却是一种错位的心理安慰,他们的焦虑无法消除,自身反而坠入深渊。《请你来爱我》中的草梅明知“我”会抛弃她,仍旧偷偷和“我”幽会,在“我”需要的时候就能来为“我”“服务”,并直言“只要你快乐,我甘愿享受你的摧残。”这其实是个体尊严和自我已经被空虚的心灵禁锢而极度焦虑的一种反馈;《禁欲》里,大学讲师胡光第一次与一名陌生女子发生关系时,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种交易,只要占有了女人的肉体就得付钱,他冲动地上了床,却意外发现这名叫谢琳琳的女子,是自己所在学校毕业的大学生,而“老师哪有给自己的学生付钱的”这句话,让胡光颇为震撼。老师和嫖客、学生和妓女这两组身份在此重合,身份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短暂的肉体甚至精神的享受和释放,但这种畸形的思维模式和对自身认同,让身份的焦虑陷入无解的恶性循环。凡一平有意识地把个人置身在社会真实的情景中,在光明和黑暗的二元对立中,把黑暗那面示众。他不直接描述身份的焦虑,但通过身体和心理的细致描写和刻画,让对身份的认同中隐约的不安、躁动和矛盾自然地浮现出来,情理之中,却在意料之外。错乱的性爱是凡一平笔下的角色对于缓解身份焦虑的一种尝试,但这种尝试显然起到的是反作用。不过我们可以看出,纵欲是在试图遗忘,是在创造一个崭新并短暂的情景,以达到片刻脱离社会身份与职业身份的目的。就像是手术前的麻醉,尽管只是片刻,那就尽管“片刻”脱离身份,以图可以脱离焦虑。
但是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麻醉”就只会让人丧失自我,当自我丧失到一定的程度,就必然会产生空白,而这种空白就像是“他人的侵入”,身份的焦虑在此时反而到达了顶峰。凡一平的小说对人的名字尤为关注,《一千零一夜》中的陈宝国通过拨打自己的同名的人的电话以确认自己的身份,他发现同名的人竟然互相都不希望对方的存在。“从其意识到的同情心理和根据他被自身所属社会群体灌输的思维判断模式来进行分析和评判,而对此并没有意识”,这种强加的身份认同必然导致新的冲突。在《同名俱乐部》中,凡一平把同名的人全部聚集在了小说当中,叫陈国军的人组成了一个联盟叫同名俱乐部,记者陈国军看上了酒店经理部的宁静,帮她拉到了客人解决了业务的问题,同时设置了圈套,占有了宁静,记者陈国军开解宁静,暗示宁静同名的人很多,身份却不同,不要把自己看成经理部的宁静,也不要把自己当作记者陈国军,于是宁静把记者陈国军当成了自己所爱的总经理陈国军,亲吻了起来。宁静怀孕了,为了验证哪个陈国军是孩子的父亲,总经理陈国军把所有陈国军叫到了一起,但没人承认,宁静说把孩子生下来再验血就清楚了,这让他们心慌意乱。最后他们决定都改名字,都不叫陈国军了,似乎谁都不用承担这个责任了。这是一个非常啼笑皆非的故事,也是违背基本逻辑的故事。某人犯了错,只需要改了名字就可以不去承担任何的罪责。名字在这里成为一种逃避罪责的杀手锏,但其实名字作为一个固定的符号又是犯事者的铁证。名字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或者代表,对名字的戏谑其实也是对人身份认同的一种戏谑。名字虽然可以一样,但作为代号的名字其实是唯一的,而我们偷换概念的过程其实也反映了个体对于其身份的盲目和无知,正是这种无知造成了人内心的摇摆,像一颗野草,随风飘扬。这些对于名字的揶揄,其实反映了在集体这一环境下对个体意识受到忽视,身份的互换和身份的错乱意味着身份的解体,凡一平在荒唐的故事情节中告诉了我们焦虑对于个体的摧毁。
二、归来——自我的审视与重建
如果说身份的焦虑是“出走”所带来的困境,那么身份的认同则必然与“归来”相连。20世纪末,经济复苏并高速发展,开始往大城市迁徙,人们在出走的过程中不断寻找物质和精神的平衡点,而到了21世纪,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在物质上得到了满足,精神上得到了一定的调和,个体对于精神更高的需求必须得到满足,凡一平在此时的小说也开始了转向,从《上岭村的谋杀》《天等山》《上岭村编年史》《蝉声唱》到《上岭阉牛》等作品都有回归的意识,这种回归是对新时代人们内心转变的细致洞察,也是对身份认定标准以及身份本身的重新审视。
当个体认为自身已经与城市融为一体的时候便是他“回归”的起始,个体所认为的都市身份在认同的那一刻开始瓦解。从《上岭村的谋杀》起,凡一平开始以家乡上岭作为生活背景进行写作,他把上岭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来书写,通过记叙家乡上岭的人和事,试图回到原点,找寻在身份焦虑中丢失的美好。《上岭村的谋杀》围绕着村霸韦三得之死,在寻找凶手的过程中,赤裸裸地揭开村里人的真实样貌。韦三得、苏春葵、蓝彩妹等老村民身上带有“乡村反面人物”或者“留守妇女”的标签,由于他们的固守,他们所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也较少,他们对自身以及对乡村的认同感较强,也很容易获得身份认同感。黄康贤是走出乡村进入城市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但他的内心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父母家庭便是他心中的信念,他尊重甚至会膜拜自己的父亲,血缘关系牵动着他的“归乡”情结,毕业后,他选择回到上岭做一名警察去实现他的价值认同。而唐艳遭受韦三得强暴而离开家乡实属无奈,她想要回归的意念让她不惜为报复韦三得做出巨大牺牲,她在报复中完成了身份的认定。
凡一平的故乡书写不仅是以上岭作为背景的描写,他的笔墨更倾注在上岭人的心灵变化上。他善于挖掘人物在生活中的心灵轨迹,让他们在他所营造的上岭世界里疗伤。《上岭村编年史》中的唐文武从卖茶叶蛋发迹,后来经营一家房地产公司,资产过亿,但因他投资不善,自己欠下很多债务未能偿还,成了老赖。于是他跑回上岭村躲债,他曾经为上岭村捐款建设学校、操场,但村民最终未能抵御金钱的诱惑,将其行踪暴露。而唐文武自己也受够了东躲西藏的生活,决定走出来自己面对这一切。从城市回到乡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倒退,但从动荡不安的城市生活中脱离出来回到乡村,有时身份的认同需要这种倒退,但这种倒退不是退缩,而是智慧地将自身置于一个客观的立场,从而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个体对于身份的认识总是经历着从怀疑到出走最后方才领悟,而随着时间流逝,往往心中那份被唤醒的温情才是获得领悟的根本。《两个世纪的牌友》是一篇未完又续写的小说,小说以时间为线索分为两个部分:20世纪与21世纪。两个世纪的风貌和生活背景以扑克牌为线索串联起来,最终唤起我们对自我认识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在小说中,陈国富原来富得流油,却意外遭遇了经济上的滑铁卢,最终败下阵来,欠款无数;相反,韦春龙经历了坐牢和在屠宰场被“奴役”的磨难,最终成功开了肉联厂。韦春龙对于友情的珍重,对于钱的淡然的态度,是被作者所推崇的,他送了“我”一辆车,把朋友千万的欠款一笔勾销,还帮朋友打听肝源的事情,帮罹患癌症的员工还清了房贷,对于钱财如此大手笔的“挥霍”,一方面是客观上他有这样的资本,他感恩于朋友为他筹款办起来肉联厂,另一方面也说明他逐渐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地位与金钱这些东西的获得离不开身边人的支持和鼓励。两个世纪的牌友,时间的洗涤让个体对自我的身份以及与周围人的关系看得更加透彻和清晰,历久弥坚的感情才是身份认同的真实可靠的依据。
身份认同不仅仅是认识自己,也是在建构自己独立的品格,而在经历了焦虑、欲望和混乱的洗礼之后,面对无可奈何和无路可走的世界,身份认同的结果可能是死亡。山在等,天也在等,等待我们最真实的样子回归。《天等山》中的雷燕,也就是后来的龙茗,为了保证弟弟能上学,被骗到东莞做上了小姐的生意,之后又被富商林伟文包养,这些不光彩的经历让她厌恶,她想通过高考的形式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于是便用龙茗这个名字开启了自己的大学生活,从此隐姓埋名。但是她的从良之路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各种牵绊,从根本上来说,她失去了自由,而这种自由来源于她的过去,她对于自身尊严的一种认同。与林伟文的一纸包养协议看似公平,却无法对等,当她拿着林伟文为她准备的身份证,改名为龙茗、籍贯变成了福建时,她其实也失去了自我。而一起看似天衣无缝的谋杀,也是被逼无奈下做出的选择。最终,层层伪装被自己心爱的人识破,龙茗在天等山顶一跃而下。天等山,代表了龙茗悲情一生的起与落,“只要我上了这山,躺在这草坪上,就能睡得着觉……这草坪的任何地方,包括那悬崖边上,我都能睡得着,而且净做好梦”。她的逝去实质也是其寻求自由、回归自我的一种最悲情的方式。
与其说凡一平在有关上岭的小说是对世界的和解,不如说那是一种对家乡的和解,又不如说是对于家乡的和解让世界得以和解。这种和解体现在他大胆直露而毫不避讳地把上岭推到了中心,把所谓的好的坏的这些二元对立打破,展现出一种对于家乡,对于自身的自信。在小说中,他大量地把自己和自己的名字置身作品其中,把鬼子、东西、李冯、胡红一这些文坛好友的名字植入作品,甚至以他们本人的身份出现,在与这些名字玩笑和他们揶揄的同时,也暗含了作家对于其身份的自信,这是打破身份焦虑的一种方式,也是对自身身份认同的最好体现。
三、码头——故乡的存在与联结
对于故乡上岭,凡一平有着割舍不掉的感情。故乡让人找寻到了身份的源头,故乡的写作成了凡一平写作新的范式,也成了他小说中人物身份认同的精神内核。凡一平对故乡的创作回归也体现着他对身份认同的独特认知。从上岭到都市再到上岭,似乎这样的主动回归是凡一平的情之所至或情之所动,这种情感的联系和联结唯有上岭——故乡可以做到。
从挣脱到回归,这中间的联结点其实是故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于出身以及出身给个体带来的现实的苦难,我们不应该去逃避,而应该直面。不应去回避自己身份可能存在的弱点,或是社会对其不公的评价,而是把这样的劣势转化为自身的优势,从源头去找寻存在于我们内心的柔软的力量。而上岭的优势便在她的温情与她能给所有村民以庇佑,让人无意识间产生了对家乡、故土、家族的心理依赖。在凡一平的小说中,这种庇佑和依赖隐含在文字当中,从而让他的文字传递出与冷峻现实截然相对的脉脉温情。
在《蝉声唱》中凡一平记录着上岭村的苦难。樊家宁终其一生在保守着一个秘密,他倔强地把英勇牺牲战友的骨灰移回上岭,承担着全团只剩他一人活着的流言蜚语。而真相其实是樊家宁为了让战友成为烈士,对世人撒下了善意的谎言,他为此承担了所有,但他内心无愧,将这个秘密守口如瓶。这样的故事是悲怆的,不免让人觉得无奈和凄凉。这个故事是苦难造成的苦难,是一种被动接受的事实,具有自然和不可抗的成分。而上岭村的人淳朴、执着,甚至执拗,他们愿意用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这一切,只是在改变的过程中,他们不得不经受各种阻碍,凡一平的上岭故事讲述的就是他们改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实质上是对苦难的对抗,当然,不是每一次的对抗都能得到现实的成功。
凡一平的很多小说情节都很荒唐,充斥着黑色幽默,深刻地抨击现实,荒唐的情节与幽默的语言能带来更大的反讽的力量。凡一平的文字非常朴实,甚至是直白、直露的,他也是个编故事的好手,但最关键的还是他在作品中情感的注入,能直击人的灵魂中温情的部分。他对父亲、对叔叔、对上岭人的情怀,或者说是对自己生长的土地的一种感恩,这种无法割舍的血浓于水的深情是在每一篇上岭小说中得以充分体现。正是这种深情,让小说的文字更加鲜活,更具感染力,更能打动读者。上岭的天人合一的状态培养了质朴和真诚的作家,作家再用这样的笔触传递给每个受众,这种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
《上岭村的编年史》中的每个部分都是悲剧甚至是悲壮的,但是于当事人而言,却又是幸福的。当蓝能跟把硫酸泼向自己的“老婆”美伶后他感到无比畅快,这不是纯粹的发泄,而是他觉得用这种方式美伶就能和普通人一样过上安稳幸福的生活。韦宝路被改判后似乎如释重负,但当他走出监狱来到社会,发现社会还不如监狱,他没有办法适应人与人之间被钱所阻隔的冷漠,他无法做到用他的简单和淳朴去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所以当他的钱花光了,母亲去世了,亲情的寄托没有了,他又想重新回到监狱。上岭村的生活让上岭人获得了独特生命的体验,而这些体验只有当他们真正踏上上岭的土地时,才能真正体悟到,他们的出身以及他们的生活环境的变化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更明确的认同,但这种认同回到现实中又没办法完全检验或者持续下去,因为他们内心都存在着某种自卑,这种自卑不是与生俱来的,是社会或者环境强加的,所以他们无法完成超越。这也是上岭的悲剧,也是小人物的悲剧。然而蓝能跟对充气娃娃“老婆”付出的真心,愿意为她受骗受累甚至牺牲一切的真挚的情感令人震撼;韦宝路无法适应监狱外的社会,他在完成了帮助小女孩举办音乐会的梦想后,用他善意的谎言把自己再次关入监狱,他的所有国家补偿款全部献给了上岭。这或许又不是悲剧,这是凡一平发出的无声的抗争,传递的是故乡带来的不变的温情,他试图用温情来对抗这光怪陆离的世界。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上岭村,这是我们一出生便将我们与土地相连的地方,是我们最切近土地的地方,也是我们的根系所在。一部艺术作品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欣赏那些在无人凭吊的坟墓中安息的每一个平凡人生的价值。凡一平给了我们很好的示范,他从都市回到自己的故乡,书写故乡平凡人的生活和平凡的故事,他并不避讳书写乡土中的陋习与愚昧,深刻地揭示了平凡的价值。在书写中,他一方面实现了对于故乡的感恩的回馈,同时他把故乡的种子播撒开来,直面传统乡村与现代城市文明的关系。在他看来传统的乡村不一定就是落后的,不一定只有苦难,而改变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改变的过程中他在寻找着一个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或许就是永驻内心的故乡的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