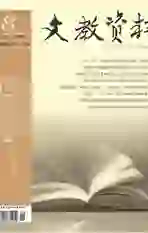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版本述评
2021-06-24吕红光
吕红光
摘 要: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是新中国成立前文学史领域内最具有系统性的文学史之一。然而这部文学史自问世以来,几经波折,三经修改,饱经沧桑。四十年代出版之后,众多学者虽有质疑的声音,但总体盛誉颇多。此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以各种不同原因修改三次,虽然经历了多次风波,但仍有内在的生命力。
关键词: 刘大杰 《中国文学发展史》 版本 述评
二十世纪初,受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中国学人开始了撰写文学史的征程。据陈玉堂《中国文学史旧版书目提要》统计,从二十世纪初到四十年代,各种通史性质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达八十六部之多。四十年代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出版,成为新中国成立前文学史领域内最具有系统性、成就最突出的一种。然而这部文学史自问世以来,几经波折,三经修改,可谓饱经沧桑。陈尚君先生说:“其改写之频,影响之大,遭遇之奇,在现代学术著作中是十分罕见的。”
一、四十年代:初版之盛誉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初版本分为上下两卷,八十万字。上卷完成于1939年,194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下卷完成于1943年,因书局种种原因,1949年才出版。抗战年代出版作品之不易,不难想见。
在结构上,与传统的纪传体、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不同,《中国文学发展史》采取的是受西方影响的章节体,时间上以封建王朝的更替为顺序,具体章节突出作家作品,主要内容包括时代背景、作家生平经历及思想状况和代表作品的介绍等大方面,基本确立了我国文学史的编写范式。在文学史观上,刘大杰因早年曾出国留学而受到西方文学思想的影响。自言在文学理论上给其影响最深的是:1.泰纳的《艺术哲学》和《英国文学史》;2.朗宋的《文学史方法论》;3.佛里契的《艺术社会学》和《欧洲文学发达史》;4.勃兰克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他说:“我当时读了这些书,非常钦佩,认为是进步的理论。我编写《中国文学发展史》,就是把这些理论组织成自己的系统,说明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历史。”刘大杰在书中引用了朗宋在《文学史方法论》中对文学下的定义:“文学便是叙述记载种种在政治社会的事实或制度之中,所延长所寄托的情感与思想的活动,尤其以未曾实现于行动的向望或痛苦的神秘的内心生活为最多。”对于撰文学史者应持有的态度,遵行朗宋的“三个切勿”:“写文学史的人,切勿以自我为中心,切勿给予自我的情感以绝对的价值,切勿使我的嗜好超过我的信仰。我要做作品之客观的真实的分析,以及尽我所能收集古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部作品的种种考察批评,以控御节制我个人的印象。”
此书上卷在1941年一出版就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产生了巨大影响,同年的《图书月刊》称这本书为“巨帙”,比以往文学史是“后来居上”的,认为这本书在整体上“作者□述所把握之中心意识,则殊常而扼要”“故举凡代表作家与作品之介绍,大体均妥帖;而每一时代文学思潮之轮廓,亦殊明晰”。于具体内容而言,《图书月刊》认为刘《史》多有令人称赞之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1.能够征引史实材料证明观点,且能做到“无征不信”;2.善于运用卜辞、唐代变文等新材料;3.能够“力扫古人以道德伦理观念谈诗之谬”,而能从时代与社会形态方面阐述诗歌的演进;4.能够突破以往治文学史者死守的纯文学范围,将诸子之文列入散文范畴。
《图书月刊》亦在具体内容上提出了刘《史》的几点不足之处:1.西汉文学部分没有述及散文,“作者似亦不免拘于韵文范围矣”;2.魏晋文学部分“唯当时有风趣之书简小品文字未述及”;3.北朝文学部分未提《洛阳伽蓝记》与《水经注》等;4.唐代文学部分过于偏重诗歌。
《图书月刊》虽然指出了刘《史》的几点不足,但总体评价还是相当高的,认为这些不足是“瑕不掩瑜”的,而且对刘《史》的下卷持相当高的期待:“下卷问世想不致过迟,一般文学史于晚清以后,叙写大多简率,实非有完整翔实贯穿到底之叙写不可。现代文学方面固较多,头绪固较繁,亦不能即便节略,或竟付缺如,以待专著;本书既称文学发展史,作者想能力矫详古略今,避重新轻之病,便成完璧也。”
刘《史》在当时相当风行,龚鹏程后来回忆说刘《史》是“流行最广而影响最大的文学史书,初学往往以此书为基础,建立起文学历史的概念的知识”。
1943年,余冠英在《人文科学学报》上发表文章评论刘《史》。余冠英在回顾了刘《史》出版前国人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四十年历程后,高度赞扬了刘《史》在总体撰史观念和具体撰写方法上的成就。余文首先肯定了刘《史》总体撰史观念的正确,有如下几点:1.人类心灵的活动脱不了外物的反映,在社会物质生活日益进化的途中,精神文化取着同一步调,所以文学的发展是进化的。2.文学者的任务在叙述文学进化的过程与状态,在形式和技巧上,以及作品中表现的思想与情感。3.文学史应特别注意每一时代文学思潮的特点和造成这种思潮的政治状态、社会生活及其他种种环境与当代文学发生的联系和影响。4.文学史者要集中力量于代表作家代表作品的介绍,省除不必要的叙述。因为那些作家与作品正是每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的象征。
余冠英亦在五个方面提出了商榷意见:1.关于叙述范围方面,认为刘《史》割去了汉代的散文,是个“缺陷”,不应该省略一些能站在潮流之外的大作家,如温庭筠、刘禹锡等;2.关于说明方法方面,前文已列出的刘《史》用来说明诸文学现象的因素,余文嫌其“不曾廣泛地彻底地应用”;3.关于组织条理方面,对刘《史》的一些文学潮流段落的划分不同意;4.关于史实考证方面,指出刘《史》除关于屈原的一二点外没有新考证加入,“考证不是本书擅长的部分”“文学史里夹杂些考证文字原非必需,但如对史实的认识与众不同或是他人聚讼未决而自己下手判定的时候,就不能不将考证经过发表”;5.关于源流观察方面,认为刘《史》对于源流的观察有时不免疏忽,如第十五章论由李贺到李商隐一派的诗歌,“本书以李贺为晚唐唯美文学的开先人,是极正确的,但于李贺之后只叙了杜牧与李商隐而不叙温庭筠”“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直至今日,学者们仍从时代的高度给予这部书以高度评价。陈尚君在《刘大杰先生和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写在〈中国文学发展史〉初版重印之际》一文中赞扬这部书:“综合了足以代表三十年代学术前沿水平的中外各家文学见解和研究成果,刘先生的文学史研究观念和其新著所追求的学术目标,都超过了他以前的各种文学史撰写者。”
魏崇新、王同坤在《自成一家:刘大杰的文学发展观》一文中认为刘《史》“点线结合,眉目清晰,叙述简洁,文笔优美,在众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显得卓然不群、自成一家,他以清醒的历史主义和逻辑力量赢得了广泛的读者”。魏、王两位从四个方面肯定了刘《史》的著作特色:1.认为刘《史》在叙述中国文学发展历史时,关注点在于“求因明变”,探寻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体的兴衰消长,以进化的理论阐述各体文学发展的因果。2.认为刘《史》在叙述文体的变化时,“比较注意对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挖掘,注意到文学思潮对文体演变的影响”。3.重视文学形式和唯美主义思潮,他们说:“刘大杰不受传统思想与文学偏见的束缚,在文学史中给唯美主义以一席地盘,实为难能可贵。”4.指出四十年代出版的刘《史》具有一种较为鲜明的时代意识,“表现出一种反传统的意识,使他的文学史具有当代性”。
骆玉明在2005年的《文汇读书周报》上高度评价刘《史》:“此书不仅影响了后来多种同类型著作的撰写,自身也一直没有完全被替代、没有停止过在高校教学及普通读者中的流行。总之,要论影响的广泛与持久,至今还没有一种文学史能够超过它。”
二、刘《史》的三次修改
对于初版的刘《史》,刘大杰感到“错误遗漏的地方是难免的”,希望能有一个“修补的机会”。新中国成立后,刘大杰“由于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初步学习和看到了一些从前没有看到过的史料,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某些问题,已有不同的看法”,于是,他产生了“想把这部书重写一遍的想法”。
1957年,刘《史》的第一次修订版出版。与初版上、下两卷不同,这次改为上、中、下三卷,七十六万四千字。1957版仍然是以朝代为演变顺序的,在体制上和初版出入不大,但在章节具体名称上的改动比较大,改后的刘《史》更加突出作家作品。对于1957版文学史,刘大杰认为“这次印出来的只在文字上做了些改动,体制内容仍如旧书”,陈尚君比较赞同这一点:“从总的方面来看,这一版的改动幅度并不太大。”经对比后,他认为改动有以下几点:1.删去了一些与当时政治有违碍的内容,如初版大量引用胡适的见解;2.补充了一些新见史料和四五十年代学者的最新见解,如胡厚宣的甲骨文研究等;3.修订了旧著中的一些提法,如将南北朝的“唯美文学的兴起”改为“形式主义文学的兴盛”等;4.增写了《司马迁与史传文学》等初版未及的章节。
1962年,刘《史》第二次修改版在中华书局出版,这次也是分为上中下三卷,九十三万四千字,比初版多十三万字。章次安排上比1957版又有所改动。董乃斌认为1962版“不但体系框架未变,具体观点的改动也很少,反不如从初版到1957年版的变动大”,并指出第二次修改的功夫“主要花费在内容的增补和叙述规范的整饬上”,他还举了许多具体例子说明。但董乃斌认为如果“从内容的丰富坚实、章节安排的清晰合理、叙述文学和论析话语既保持个性又具有相当的时代色彩等方面来看,《中国文发展史》的1962年版应该说比1957年版前进了一大步”。他对初版、1957版、1962版作了如下评判:“二者比较起来,1957年版只能算是一个由旧变新的过渡性版本。今天,如果想领略刘先生的学术锐气和充沛才情,不妨看该书的初版;如果想了解刘先生的学术功力并想获得更多更准确的知识,那就最好去读该书的1962版。”
总体上,1962版较前两版规范,其书以较高的学术质量和鲜明的个人风格长期以来普遍受欢迎,“文革”前后被列为大学教材和研究生考试的主要参考书,甚至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喜爱。1965年5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上海接见了刘大杰,谈了两个多小时。和刘大杰谈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家,如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宋代的王安石、苏东坡、李清照等。还鼓励刘大杰拿出勇气,发表独到见解,不要怕失掉什么,要发扬争鸣的精神。并说:“学术问题一定要百家争鸣,才能促进文化的繁荣、艺术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毛泽东还曾重读刘《史》,因字小阅读不便,还曾印成三十六磅大字本。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刘大杰开始进行第三次修订。以阶级斗争的观点修正书中的唯心主义,1973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文革版第一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卷于1976年出版。文革版的刘《史》带有鲜明的政治特色,书中许多地方大量引用毛泽东语录,并以醒目的黑体字排出,以表示对领袖及指导思想的崇敬。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虽然经历了多次风波,但仍有内在的生命力,直到现在,六十年代的修订本还在不断重印,历史会给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以公正的评价,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的刘《史》的评价已经比较公允了:“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是一部上起殷商、下迄清朝的通代文学史巨著,重点阐述各代文学之胜,兼顾其他文学品种;文人创作与民间通俗作品一并重视,在阐述各个历史阶段和文学体裁的同时,尤其注意揭示文学发展进化的脉络。它是作者在长期教学研究基础上獨立完成的学术著作,体例之统一、观点材料取舍标准之一致,文气之流畅、个人风格之突出,为集体编纂之作难以企及,故在众多同类著作中独树一帜、久享盛誉。”
参考文献:
[1]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上海:中华书局,1941.
[2]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3]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
[4]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