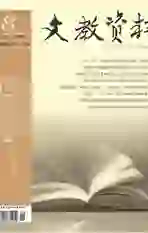“破鞋”与“妖妇”怎样反叛
2021-06-24胥亚慧
胥亚慧
摘 要: 陈清扬和田小娥,分别是新时期中篇小说《黄金时代》和长篇小说《白鹿原》中两个叛逆女性形象,虽然所处时代环境不同,但同样面临“荡妇羞辱”的生存困境。本文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就二人“荡妇”身份的成因和反叛精神的体现两方面,比较陈清扬与田小娥的异同。
关键词: 女性主义 《白鹿原》 《黄金时代》 “荡妇”形象
陈忠实的長篇小说代表作《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村为缩影,通过讲述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表现了从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书中创造了许多鲜活的女性形象,其中田小娥是最具反叛精神的一位。她从未屈服于封建礼教和男权政治的双重压迫,用身体交换生存的同时本能地追逐自己的欲望,散发着朴素而野蛮的人性之光。
王小波的中篇小说代表作《黄金时代》以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为背景,作品通过直面性爱的书写彰显了人性的自由本真,同时辛辣地批判和嘲讽了现实,对人类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反思。女主人公陈清扬是一个因美丽招致“破鞋”骂名的下放女医生,她试图摆脱污蔑,阴差阳错结识王二并与之建立了同为特立独行的反叛者之间的“伟大友谊”。她的抗争是对个性解放和女性意识的召唤,令我们重新审视了女性的价值。
《黄金时代》首版于1991年,《白鹿原》首版于1993年,成书时间相近,同属于新时期文学。两部作品虽然叙述了不同时代的故事,主人公生活的环境并不相同,但田小娥和陈清扬这两位女性角色所遭遇的“荡妇羞辱”生存困境却是相似的,她们同时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追求人性的解放。
一、荡妇何以为“荡妇”?——“荡妇”身份的成因
陈清扬被众人称为“破鞋”,而田小娥则被众人称为“妖妇”“烂货”等。其实这些称谓均是“荡妇”的变体。“荡妇”明显是男性话语体系下的一个侮辱性词汇,用于贬斥那些失贞或行为不检点的女子,与之相对的名词是“圣女”。正如当代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创始人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所提出的“屋子里的天使”[1](22)和“阁楼上的疯女人”[1]两个重要概念,男人为了巩固性的主体地位,也使用了“分而治之(dicide and rule)”[2](34)这一“支配统治的铁定法则”[2](34):“支配者总是将支配对象分离隔断,让他们相互对立,绝不允许他们之间产生连带感。”[2](34)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即为来自男人的对“圣女”与“娼妓”的分离支配[2](34)。“性的双重标准将女人分为两个集团,即‘圣女与‘荡妇……女人的性,被分离为‘为生殖和‘为快乐两种”[2](37)。男人们一方面歌颂着前者,另一方面在贬斥后者的同时自己不免沉沦。女人被分离隔断为两个部分,其中圣女一方满足于贞洁伴随的荣耀与利益,又痛恨着荡妇们夺走男人的潜在威胁,要求与荡妇划清界限,并不掩饰对荡妇赤裸裸的歧视。
“荡妇”们实际上受到了双重歧视与羞辱,压迫与规训的矛头不仅来源于男性,还来源于女性本身。例如田小娥在祠堂受刑时,“男人女人挣着挤着抢夺刺刷,呼叫着:‘打打打!‘打死这不要脸的婊子!”[3](220)。这些女人们显然是男权规训下的完美作品,她们一边夸耀于自己的温驯贞洁,与男性构成了同仇敌忾的利益共同体,一边后怕于自己的男人曾受此妖妇的引诱,让自己的生存利益有被威胁的可能。陈清扬在批斗场休息时,一帮老婆娘指着陈清扬窃窃私语,结论是“她真白,难怪搞破鞋”[4](32)。其实皮肤白和是否搞破鞋之间毫无逻辑联系,婆娘们自己分明也想变白却做不到,只能想方设法地将“白”污名化,强调贞洁抬高自己的地位,借此获得心理代偿。
然而,荡妇原本就是荡妇吗?女权主义批评家莱斯利·菲德勒说:“事实上并不存在好坏两种女人,甚至也没有什么最初似乎坏,最终却证明是纯洁无瑕的女人。存在的只是两种期望和夹在中间的一种不完美的女人。”田小娥的父亲是个秀才,她勉勉强强也能算个“财东家女子”,生长在书香门第兴许也识文断字;她被父亲嫁给年过半百的武举人是因为贪慕武举人的名声权势,并不是因为没有口粮被卖掉。少女时的田小娥尚不至于为生存发愁,残酷的命运却推着她不得不向前走。陈清扬是受过高等教育且思想觉悟高的女医生,有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她本不属于云南,是在国家政策的感召下才北医大一毕业就来支援国家的边疆建设。如果不是军代表调戏不成恼羞成怒报复,那么她仍然在医院而不是在十五队做队医。出斗争差时她也会恍惚,“这真是个陌生的世界!这里发生了什么,她一点不了解”[4](34)。
“被限于生殖的异化、被隔离生殖的异化,反面即为被隔离快乐的异化和被限于快乐的异化(当然均为男人的快乐),对于女人,都是压抑……换言之,‘圣女和‘娼妓,是压抑女性的两种形态,无疑都是他者化”[2](37)。田小娥从田小娥变成“烂货”,陈清扬从陈清扬变成“破鞋”的过程,都是男权视角下女性形象的扭曲变形,是男性自己意愿与欲望的投射,永远不是真实的女性。那么,这种异化的凭据从何而来?
1.美丽即“原罪”——性价值
“小女人正在窗前梳理头发,黑油油的头发从肩头拢到胸前,像一条闪光的黑缎。小女人举着木梳从头顶拢梳的时候,宽宽的衣袖就倒捋到肩胛处,露出粉白雪亮的胳膊”[3](109)。田小娥的美是纯洁娇憨、无攻击性、与“祸水”截然相反的美,但显然男权社会并不这么觉得。老实本分的鹿三看见黑娃“引着一个罕见的漂亮女人回到白鹿村”[3](105)时“一下子惊呆了”[3](105),“从第一眼瞧见儿媳妇就疑云起”[3](105),白嘉轩搭眼一瞅就断定:“这女人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女人。你拾掇下这号女人你要招祸。”[3](127)在他们的男权秩序里,“居家过日子”显然并不需要漂亮,漂亮只与上文的“快乐”挂钩,于生殖与宗法制度维系来说是不确定因素,因此产生了“漂亮女人都不是好货”这种奇怪的逻辑闭环。
陈清扬称自己“无疑是当地斗过的破鞋里最漂亮的一个”[4](34)“斗她的时候,周围好几个队的人都去看,这让她觉得无比自豪”[4](34)。王二对陈清扬说:“大家都认为,结了婚的女人不偷汉,就该面色黝黑,乳房下垂。而你脸不黑且白,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耸,所以你是破鞋。”[4](4)这符合上文“生殖”与“快乐”分开的原则。陈清扬的美丽是自知且众人公认的,只是这种美丽超出了公共空间对已婚女性的规范和想象,人们无法接受一个理应只用于生殖的身体竟然还拥有令人“快乐”的性价值,因此男人通过窥视,女人通过污名化实施了对陈清扬身体的暴政。
2.“二茬子女人”和寡妇——性经验
陈清扬与田小娥的遭遇近于同质。她们都曾有过婚姻又脱离了前一段婚姻;她们都离开了原先的环境而主动进入了现在的环境;她们都对前一任婚姻对象并无感情。男权话语体系下,女人被物化是不可逃脱的命运。嫁过人的女人意味着性经验并非空白,是“被用过了的东西”,不再崭新,不再纯洁,不能再被男性完完全全地拥有。其中最核心的是她的性作为生殖功能已经被使用过了,这在宗法制度中不利于血脉的纯正,有可能会损害男性传宗接代的利益。这意味着陈清扬和田小娥在进入新环境时已经失去了做“圣女”的资格,且她们都低估了群氓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人的程度。陈清扬因为是个寡妇,被先入为主地判定一定空虚,一定缺乏情欲,被理所应当地扣上“破鞋”的帽子;田小娥的境遇更可怜,甚至还不如妓女。一道做长工的孙相对黑娃说:“娃娃,拉光身汉也不要这号二茬子女人,哪怕办寡妇,实在不行哪怕到城里逛窑子,也不能收拾这号烂货。”[3](123)可见在男性视角中,從头到尾一直作“快乐”用途的女人,地位是高于先用于“生殖”、后用于“快乐”的女人的。
3.非性的时代与性的双重标准——性压抑
陈清扬与田小娥生活在不同时代,却遭受了同样的性压抑,但她们被压抑的时代原因显然是不一样的。
陈清扬的故事发生的时期,男人也不被允许谈性。阉牛时掌锤的队长每回都对以王二为代表、不服管的知青们呐喊“你们这些生牛蛋子,只要砸上一锤才能老实”加以威胁,王二后来也意识到了:“生活就是个缓慢的受锤过程,人一天天地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4](6)用公牛类比性压抑的人们,用受锤类比情欲的阉割,是王小波的神来妙笔。严格来说,“破鞋”问题纯属个人私事,但“畸形的权力场与扭曲的社会习俗”[5],使得“斗破鞋”这种荒诞之事变成了大庭广众之下群情宣泄的“正义”。但性欲不会因为被压缩就消解,集体偷窥在这种“正义”的保驾护航下竟被洗白成了合理的狂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尖锐的讽刺。例如陈清扬挨批斗时,“绳子捆在她身上,好像一件紧身衣。这时她浑身的曲线毕露。她看到在场的男人裤裆里都凸起来。她知道是因为她,但为什么这样,她一点不理解”[4](34)。
田小娥所在的年代并不避讳性。白嘉轩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封建大家族族长,“生平最引以为傲的是一共娶过七房女人”[3](1),这说明性压抑仅存在于女人身上,男人的性经验丰富反而是一种荣耀。“性的双重标准,是指面向男人的性道德和面向女人的性道德不一样。比如男人的好色被肯定,而女人则以对性的无知纯洁为善”[2](33-34)。白鹿原深受儒家传统封建礼教影响,一切秩序皆为维护男权统治和宗法制度,女人只被视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奉献不会被感激,痛苦不会被怜悯。对胆敢追求性自由的田小娥,他们采取极端高压态度,借此对女性进行控制和规训,体现了浓厚的男尊女卑色彩。
二、肉体的放浪形骸——反叛精神的体现
同样是颇具反抗意识且都借托肉体解放释放人性本真,田小娥与陈清扬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具体大概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无辜”身份的自我确认
面对类似于“荡妇”的骂名,田小娥和陈清扬都试图为自己辩护过。陈清扬是有清晰自我意识的,她最初便没有跌入群氓判定破鞋“好不好”的道德陷阱,而是不屈于诽谤,认为自己既然不是破鞋就不该被称作破鞋,旗帜鲜明地反抗“破鞋”的帽子。她显然不是因为道德约束才想要摆脱这一名号,完全是忠实于本身的存在,这是敬重真实,反抗拿捏,不容置疑地将身体的主动权牢牢握在手里。她很快发现这种证明是徒劳的。“既然不能证明她不是破鞋,她就乐于成为真正的破鞋”[4](15)。想通后她坐实了破鞋的名号,开始真正享受性爱的快乐,例如每次出完斗争差必“性欲勃发”,要与王二敦“伟大友谊”的表现,便是通过让荒谬变成真实消解这种荒谬带来的伤害。
到了后期,“陈清扬说,那也是她的黄金时代。虽然被人称作破鞋,但是她清白无辜。她到现在还是无辜的。听了这话,我笑起来。但是她说,我们在干的事算不上罪孽。我们有伟大友谊,一起逃亡,一起出斗争差……所以就算是罪孽,她也不知罪在何处。更主要的是,她对这罪孽一无所知”[4](34)。从表面看,陈清扬确实失身了,但她在拒绝被传统标准定义的同时又聪明地自创一种灵肉割裂的方式定义自己的“破鞋”行为,她认为肉体的放纵是为了回报王二的“伟大友谊”,自己的灵魂则始终保持清白无辜,直到屁股上的两巴掌“彻底玷污了她的清白”,是因为灵魂终于抵抗不住爱情的侵染,性爱最终还是合一的事实让她无法接受。换言之,从头到尾,在陈清扬的认知里,她是否有罪孽与肉体的性交毫无关系,她彻底摆脱了男权和公共标准的霸权,始终把持着自己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是主动自觉的、更高级的反叛。
田小娥的反抗完全出自生存的本能,她接受了男权社会安给她的“烂货”“妖妇”名称,潜意识里默许了他们认为自己有罪,她不能接受的是竟然连生存权也要被剥夺。田小娥的鬼魂借鹿三之口说道:“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的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的一把麦秸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哈?我不好,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着黑娃过日子……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认,俺出你屋没拿一把米,也没分一根篙子棒棒儿,你咋么着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3](392)面对污名,田小娥并没有要求揭去,她的一次次性行为并不能拔高到所谓的“自我意识”,只是为了生存下去的野兽本能。如果田小娥在郭举人家并未被虐待,她或许并不会偷情被休;如果她有别的办法能营救黑娃或者能够自己在白鹿村住下,她也不会和鹿子霖偷情;如果舆论对她宽容一点没有令她被刺刷子刷到鲜血淋漓,她也不会一听鹿子霖提议就去报复白孝文毁他的名声。她像无根的浮萍、扑火的流萤一样,一步步均是身不由己。
她勾引白孝文,以及事后对白孝文产生怜悯的行为,恰恰确证了她对自己“有罪孽”这一论断的深信不疑。她也觉得自己是肮脏污浊的,自己的污浊可以变成凶器害人,她尿到鹿子霖脸上也并不是为自己反抗,而是为白孝文抱不平。她并未意识到自己其实被鹿子霖物化成了借刀杀人的刀,反而怜悯了意志不坚定受引诱的白孝文,这体现了她身上母性的柔软、同情、不忍,也体现了她潜意识里并未逃脱男权的衡量标尺,她的反抗是基于生存本能被动触发的、不够彻底、不够高级的反抗。
2.身体的运用
陈清扬与田小娥在试图“脱离苦海”的过程中并不是靠孤身一人,她们都借了男性的帮助。为了回馈这种帮助,她们不可避免地经历“物化”自己身体的过程。田小娥最先主动勾引了黑娃,到后期就变得随波逐流,不假思索地用身体换取生存,但和鹿子霖的交欢明显乐在其中,甚至与白孝文产生了抱团取暖的相互依恋;陈清扬最初是受了王二的引诱,把身体作为“伟大友谊”的回报及歃血为盟的信物,后来才放任自己坦然享受性的美好乃至于把性当作爱无言的泄洪口。她們的共同点在于,都先物化身体,消极承受,然后慢慢取消了这种物化,夺回了性爱的主动权,变成积极接受。
就对男性的依恋方面,两个角色差异较大。王二对于陈清扬而言是唯一的救赎,具有不可替代性,前后并无参照对比,二人的关系并非一个依附于另一个,他们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王二与那些明明没病故意找陈清扬看病的男人不同,他是剩下的唯一一个有可能觉得陈清扬不是破鞋的人,陈清扬死死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证明自己的清白,又被王二的坦然和赤诚打动,发觉他和自己一样拒绝阉割情欲,在公共话语的极度膨胀下坚守个人尊严,缔结了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之间的“伟大友谊”,彼此成为对方的救赎和灰暗生活里的亮色。
田小娥的肉体付出是一个试错的过程。除郭举人外,她主动选择的三个男人,其实每一个都是对前一个的修正。鉴于郭举人的年迈昏聩,田小娥抓住了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黑娃为救命稻草;鉴于黑娃“革命”失败后束手无策只能败逃,田小娥吸取教训攀附了更有话语权的长辈鹿子霖;鉴于鹿子霖心地丑恶的施害者身份,田小娥又和同是受害者的白孝文相互依恋。她的依恋对象并无不可替代,也没有一个固定标准,不是黑娃也可以是其他年轻力壮的后生,不是鹿子霖也可以是其他有权力的上位者,如果害的不是白孝文而是其他人,那么她一样会产生同情怜悯进而依恋。她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和眼界,也意识不到男权社会对“贞洁”的苛求本就是荒谬的,只能在罪己的圈套里痛苦地走向悲剧命运。
简单来说,虽然她们对性爱的态度都是从消极承受转变为积极接受,但二者的性质仍然有所区别。田小娥是向下走的,她把身体当成货品与凶器,将白孝文拉入生活的无解泥潭,造成了黑娃和白孝文的嫌隙,破坏了家族宗法,早就和她说的“跟着黑娃过日子”的初衷背道而驰;陈清扬是向上走的,她的性爱不仅是对“伟大友谊”盟誓的回报,是个性解放的闸口,还是对自己的那一段“黄金时代”的纪念与留存,见证了她与王二曾经对生命本色矢志不渝的追寻。
三、结语
通过对田小娥、陈清扬被称为“荡妇”的成因和反抗精神两方面的分析来看,女性被压抑、被规训、被污名化的命运,并不是某个时代的特定产物,而是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广泛痼疾。但女性面对不公命运的压迫奋起反抗的方式手段、成功与否,却和她们所在时代、所处阶级、所受教育密切相关。我们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剖析人物心理,认识她们命运,呼唤女性自主意识的萌动与勃发。
参考文献:
[1]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 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M].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2]上野千鹤子.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M].王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3]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4]王小波.王小波小说全集 黄金时代[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
[5]丁晓卿.论《黄金时代》“性”权力隐喻[J].抚州师专学报,2000(01):34-36,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