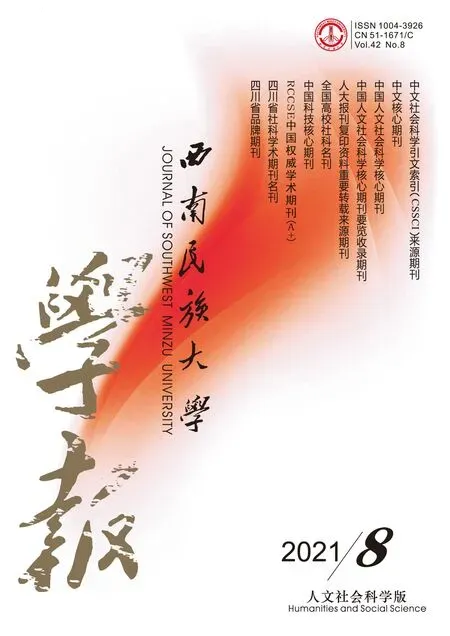论宋代的文人礼治模式
2021-04-17韩伟
韩 伟
[提要]“文人礼治模式”是宋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学家与文学家的共同参与下,文人阶层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启蒙者角色,建构了形而上与形而下、宗经与实用、礼法与礼俗相融通的礼治模式。这种模式的构建方式包括两种,一是家礼,二是学礼。家礼以尊祖、敬宗为指导,完成了对宗族行为的约束,补足了周代以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德进化模式中的宗族环节。学礼的载体是各类书院,它是主流教化体系的民间变体,亦寄托着知识分子阶层建构理想社会的愿景。家礼与学礼虽形态不同,但性质相似,不仅实现了“天地君亲师”道德信条的具体化、民间化,也使普遍的社会理性得以建立。
有宋一代是文人地位获得提升且在社会中发出自己声音的时代。宋朝自太祖时期便定下了偃武修文的基调,并被赵氏子孙一直延续,后人总结称宋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1](P.12940)。据有的研究者考证,北宋每年平均登科人数为357人,南宋为334人,虽然减少23人,但是“南宋的疆域比北宋大约减少了五分之二,其户数及人口也大约减少了五分之二”,所以就此而言,“南宋取士的比例数无疑是大大增加了”[2](P.901)。很难想象,一个军事方面日趋软弱且始终没有形成大一统局面的王朝能够持续三百余年之久。更加吊诡的是,其文化还能在历史上独树一帜,不仅超过了同时代的辽、金政权,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也塑造了独特的“宋型文化”。
一、文人礼治的基础
“宋型文化”的基本动力是文人阶层话语权的增强。文人的价值观得到了政权的承认,最终实现了与官方价值体系的同构,在这一过程中文人的礼乐观念是重要内容。与前代相比,宋代文人成了礼仪建设的主体。他们的礼治观念不再仅仅局限在庙堂之上抽象的仪轨复兴层面,而是参与了整个社会的治理过程。因此,如果将唐代以前的礼治模式称作贵族礼治或官人礼治的话,那么宋代则属于文人礼治模式。
就文人群体而言,宋代可以粗分成两大阵营,一个是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家群体,另一个是以欧阳修、司马光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家、文学家群体。就理学家阵营而言,他们往往将“礼”上升到“理”的高度,以“理”言“礼”。“理”较“礼”具备更强大的统治能力,“违礼”属于道德领域,但“违理”则属于天道层面。正因“理”的存在,现实之“礼”才获得了更加强大的保障。作为理学奠基者的周敦颐,专门在《通书》的第十三、十七、十八、十九章讨论礼乐。在他看来“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夫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3](P.24),他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种种人间秩序全部纳入到了“理”的范围。这里的“理”虽然还没有达到二程、朱熹理论中的高度,但基本趋势已经具备。如朱熹所言,周子《通书》“其所论不出乎阴阳变化、修己治人之事”[4](P.1836),这个总结一方面指出了周敦颐理论的特征,另一方面也明确了其体系的两面性,即阴阳(后来理学家提升为“理”)与治人(“礼”)之间仍处于分离状态。这种情况在二程以后的理学家思想中被最大限度地弥合了,二程言:
人者,位乎天地之间,立乎万物之上;天地与吾同体,万物与吾同气,尊卑分类,不设而彰。圣人循此,制为冠、昏、丧、祭、朝、聘、射、飨之礼,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义。其形而下者,具于饮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极于无声无臭之微;众人勉之,贤人行之,圣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与其家与其国与其天下,礼治则治,礼乱则乱,礼存则存,礼亡则亡。[5](P.668)
在二程的观点中,以人为代表的人间社会与天地是“同气”(即“同理”)的,作为人间秩序的“礼”与作为天道的“理”之间的区别在于不同的表现形态。这就使得冠、昏、丧、祭诸礼,以及君主、父子的秩序成为天经地义,礼与理之间仅是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的分别,而并无本质差异。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礼在人生、社会中的地位就变得重要异常,足可关系天下存亡。南宋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在礼的问题上也同样如此。他眼中的礼是“天理之节文”,并解释称:“礼谓之‘天理之节文’者,盖天下皆有当然之理。今复礼,便是天理。但此理无形无影,故作此礼文,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故谓之‘天理之节文’”。[6](P.1494)在朱熹看来,日常的洒扫应对、起居动作都可以视作是天理的具体展现,由此将礼与天理的关系愈发明确化。
就政治家、文学家而言,他们更多从儒家礼教传统的角度申说礼的现实意义。需要说明的是,宋代很多文人兼具政治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这里将两者并列主要是想同理学家做出区分,以便讨论范围更加完善。如果说理学家对宋代礼治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学理层面的话,那么政治家和文学家们则是在复古的外衣下更加强调政治有效性。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如范仲淹、欧阳修、李觏、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尽管诸人在尊奉《周礼》还是尊奉《仪礼》的问题上存在争议,但他们借助经典观照现实的基本倾向却是一致的,都具有鲜明的政治与现实相结合的实用理性。在欧阳修看来,“六经者……《书》载上古,《春秋》纪事,《诗》以微言感刺,《易》道隐而深矣,其切于世者《礼》与《乐》也”[7](P.673),认为六经之中只有《仪礼》和《乐经》最具有现实意义,还说“礼乐,治民之具也。王者之爱养斯民,其于教导之方,甚勤而备。故礼,防民之欲也周;乐,成民之俗也厚”[7](P.673)。这种治民理念亦对其史学观有所影响。在被誉为“最得春秋之法”的《新五代史》中,他直言“礼义,治人之大法”[8](P.611),此语貌似平淡无奇,但其中却渗透着欧阳修作为史家深沉的历史思考。除此之外,欧阳修也是修订《太常因革礼》(现存八十三卷)的主力,该礼典是对太祖朝《开宝通礼》的补充,原则是“以《通礼》为主而记其变”,强调礼仪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虽然该礼典所述仍停留在国家礼法层面,但其不僵化拟古的观念是值得肯定的。
欧阳修的这种礼治思想和史学观念被司马光进一步延续下来。在《资治通鉴》(成于1084)开篇,司马光就谈到了礼的重要性,“臣闻天下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9](P.2)。这段话出现在开篇部分,可以将之视作司马光对“史鉴”的认知,将礼义名分看成是深蕴在历史底层的基本质素。事实上,他的这种倾向是一以贯之的,在写于嘉祐七年(1062)的《谨习疏》中,他就以礼为线索梳理了各代兴亡,认为“三代之王,皆习民以礼,故子孙百年享天之禄”,以此寄托对现实的思考,“陵夷至于五代,天下荡然,莫知礼义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远者十余年,近者四五年,败亡相属,生民涂炭”[10](P.270),以史为鉴的良苦用心呼之欲出。作为史家,除了有这种宏观的历史意识之外,司马光的特殊之处是真正注意到了民间的力量。因此,他又将对礼的认知向百姓生活和民间日常贯彻,于是他又有《书仪》10卷,这是一部典型的面向社会中下层的日常礼典。按《书仪》自述,他制定新礼仪的标准是“参古今之道,酌礼令之中,顺天地之理,合人情之宜”[11](P.473),其中参古今、顺天地属于治史者的一贯抱负,但是斟酌礼令、和顺人情,则渗透了司马光礼仪下移的考虑。
在政治家、文学家群体中,还有一些人对礼治局面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与欧阳修、司马光一样,或者从传统礼教立场撰作文章(如李觏《礼论》7篇、《周礼致太平论》51篇),或者从现实政治实用角度发出倡导(如王安石《礼论》《礼乐论》《周礼新义》),等等。总之形成了整体推崇礼乐、建设礼乐的良好局面,这种氛围在轴心时代以后的整个古代社会都很少出现。
上述两个群体呈现的不同礼治倾向,在南宋朱熹处得到了整合。概而言之,他充分地实现了内与外、正统与民间的多维统一。首先来看内与外的统一。所谓“内”指的是内在的学理性建构。这一点在上文中已有涉及,他继承周敦颐、二程以来的论礼传统,为之找到了形而上的哲学基础,从而使礼与天的关系走向一体化。所谓“外”,是指从外在功能角度建构礼的地位,这一点是儒家学者的一贯倾向,也是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文人们论礼的主要方式。其次来看正统与民间的统一。正统是指对“四书”体系和《仪礼》体系的继承,朱子“经学”体系的核心是《四书章句集注》和《仪礼经传通解》,前者为其提供了理学思想的性情基础,后者则更多体现为对礼学致用性的吸收。但朱熹较周敦颐、二程进步之处在于,他真正身体力行地对作为“节文”存在的礼进行了具体讨论,表现出对民间礼俗的承认。不仅在讲学中经常与弟子讨论礼条、礼俗之事,而且也专门撰作《家礼》《学规》,真正将视角下移到日常行为方面。其《家礼》①中大量文字源自司马光《书仪》,对民间俗礼的基本态度也与司马光一致。朱熹在自序中称“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12](P.873),于是便按照冠、婚、丧、祭的形式切近民间实用,这也是其“礼,时为大”“酌古之制”礼治思想的具体展现。
综上,宋代独特的“文人礼治模式”呈现出如下特点:首先,以宗经为基础,以实用为目标。文人是儒家道统的重要延续者,他们遵循的经典或者是《周礼》,或者是《仪礼》,以宗经为前提达到原道和征圣的效果。这就使宗经更像是一种叙事策略,以之为出发点更加灵活地对待现实问题成为可能。其次,文人在宋代社会充当了启蒙者的角色。文人地位的突出绝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庞大,更加体现为文人治国的真正实现。这种环境之下,文人不再亦步亦趋地机械拟古,也不满足于一味媚俗,而是充当了两者之间桥梁的角色,从而使宋代礼教可以真正下沉到社会肌体之中。再次,文人礼治模式的真正动力源自民间。限于篇幅,本部分仅仅列举了几位庙堂文人的代表性观点,实际上他们仅是起到的“上行”的效果,而真正的“下效”则必然要有一支庞大的在野文人队伍,对此从《宋史·艺文志》中所列的一百余部礼仪典籍中可见一斑。
二、家礼:文人礼治的实现方式之一
宋代民间礼乐属于一种隐性的文人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宋儒实现了对社会日常生活的重构。宋人推崇的“四仪”(或“四礼”)中冠礼属于成人之礼,婚礼属于成家之礼,丧礼属于慎终之礼,祭礼属于追远之礼。它们更加切合日常生活,国家层面的不实之礼被排除,代之以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冠、昏、丧三礼是对现实生命的规约,祭礼虽属于对逝去生命的追念,但其本质仍然是人们追求精神永存的美好愿望的折射。所以,“四仪”本质上都是与人生密切相关的礼仪,它们寄托了人们对生命存在的关怀和渴望。可以说,宋人将周汉以来宽泛的礼乐号召落到了实处,变得具体可操作,以类似盐溶于水的方式让百姓身处其中而不自知。
广义来讲,司马光、朱熹等人推崇的“四仪”或“四礼”都是围绕士庶阶层的日常生活而展开的,所以都可归入“家礼”的范围。“家庭”乃至“家族”是古代社会的最小单元,其稳固程度和文明状态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最根本影响。可惜的是,周代以来的儒家典籍乃至“五礼”条文或者关注君子人格的养成,或者关注官方礼仪的构建,往往忽视作为个体与社会中间媒介的家庭和宗族。宋代家礼性质的典籍大量出现,很多重要文人都有相关著述,比如范仲淹《家训百字铭》、宋祁《庭戒诸儿》、欧阳修《示子》、邵雍《戒子孙文》、二程《婚礼》《祭礼》、张载《祭祀》《丧纪》《女戒》、司马光《书仪》《家范》、黄庭坚《家戒》、叶梦得《石林家训》、陆游《放翁家训》、吕祖谦《家范》、朱熹《家礼》、真德秀《教子斋规》等等。两宋时期,家庭、宗族单元在社会治理中的意义逐渐被重视起来,“家礼”亦表现出由“理论”向“仪轨”的进步。至此,封建社会的社会治理空间才趋于完善。
限于篇幅,下面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司马光、吕祖谦、朱熹的家礼观念进行讨论。这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司马光的家礼观代表了北宋家礼的成型状态,不仅是对同时代人的继承和总结,更加奠定了后世家礼的基本结构。二是吕祖谦和朱熹是在司马光基础上的再发展,代表了南宋家礼的成熟形态,同时也是家礼真正平民化的表征。司马光《书仪》卷一涉及表奏、公文、私书、家书的内容,主要介绍这些文书的书写格式和规范。卷二为冠仪,卷三、卷四为婚仪上、下,卷五至卷十为丧仪一至六,其中卷十虽名为丧仪,但实则关于祭祀,所以可将之视作祭仪。从全书布局来看,主体部分是“四仪”,而且以丧仪为主,整体行文并未出现天子及大臣探望之类的礼节,所以明显可以看出这是针对庶人阶层的仪轨,这一点在冠仪、婚仪部分也大同小异。比如婚仪部分司马光专列“居家杂仪”,其中不仅谈到了作为父母者应该如何管理家族子女,如“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还涉及子女如何服侍父母,如“凡诸卑幼,事无大小毋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妻子如何顺从舅姑和丈夫,如“凡为子妇者,毋得畜私财。俸禄及田宅所入尽归之父母舅姑”,下人如何侍奉主人,如“凡内外仆妾,鸡初鸣咸起栉总盥漱衣服”,等等。可见,其大旨不过是对长幼、尊卑、内外的规定,或者说是对“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传统儒家礼法的具体化和家庭化。
与这种倾向相一致,《家范》表述得更具理论根据和历史味道。对于该书的特点,清四库馆臣称“其节目备具,切于日用,简而不烦,实足为儒者治行之要”[13](P.657)。全书按治家、祖、父母、子、女、孙、伯叔父、侄、兄、弟、姑姊妹、夫、妻、舅甥、舅姑、妇、妾、乳母的顺序分成十卷二十篇。与《书仪》侧重记述仪轨不同,该书主要侧重儒家典籍、言论、史实的征引,其中加入司马光自己的观点,所以一方面可为现实的礼仪规范找到经典的凭据,另一方面其分目亦紧贴家族日常关系,也就是四库馆臣说的“切于日用”。对于司马光撰作该书的宗旨,其在卷一中称“治国必先齐其家”[13](P.659)“正家以正天下者……自卿士以至匹夫,亦有家行隆美可为人法者,今采集以为《家范》”[13](P.660)。在他看来,齐家就是为治国做准备,这与周汉以来的一贯认知相一致,所不同的是,作为榜样的人物不是尧、舜、禹、汤之类的圣人,而是历史上在家庭生活中有德行的卿士和匹夫。通过对鲜活的典型人物的记述,拉近了民众与道德的距离,同时也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整体来看《家范》和《书仪》,一个侧重宏观,一个侧重微观;一个侧重理论,一个侧重实践。两者相伴而行,便是完整的关于家礼的系列礼典,实现了经、史、子、俗的完满融合,使家中之礼既是天地精神的体现,同时也起到了移风俗、正视听的效果,为民间礼治局面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南宋时期,民间礼治愈发成熟,民间礼典也逐渐定型,且与民众的距离进一步缩小,典型代表便是吕祖谦的《家范》和朱熹的《家礼》。如果说司马光由于身份的限制,其家礼思想多少还带有一定的官方、贵族色彩的话,那么吕祖谦、朱熹由于与民间社会的深入接触,使得他们的思想更加贴近现实,也更利于百姓接受、遵行。先来看吕祖谦《家范》。该书总六卷,卷一“宗法”、卷二“婚礼”、卷三“葬仪”、卷四“祭礼”、卷五“学规”、卷六“官箴”。全书的主要特色在于明确以“宗法”作为根基,反映了吕祖谦个人的家礼观念。从逻辑角度来讲,婚礼、葬仪、祭礼都是宗法的组成部分,都是其“尊祖、敬宗、收族”观念的具体实践。吕祖谦认为“尊其所自来,则敬宗”,并且将之视为天地自然之理,即“此非是人安排,盖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天使之也”[14](P.165),这种论说逻辑与司马光将家礼视作“天地之大义”的做法一致,同时也体现了吕祖谦固有的理学倾向。整体而言,“宗法”是理解吕祖谦家礼思想的钥匙,其他条文都是为之服务的具体仪轨,故不再一一分析。
这种观念同样在朱熹《家礼》中有所呈现。朱子《家礼》分为通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五卷,与司马光、吕祖谦同类著作相比条目更加清晰。《家礼》不仅在条目方面对司马光《书仪》有所继承,更加抄录了大量《书仪》文字,最典型的就是“居家杂仪”部分几乎全文照录。但在继承的同时,朱熹也意识到《书仪》过于繁琐的现象,对之做了适当裁剪以便于民众遵行,其自称“使览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详,而不惮其难行之者。虽贫且贱,亦得以具其大节”[15](P.3920)。另一方面,朱熹也在《家礼》中传达出对宗法观念的肯定,这一点与同时代的吕祖谦相互暗合。卷一“通礼”的开篇就专门陈述祠堂制度,这种安排是朱熹有意为之,按其所言“此章本合在祭礼篇,今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后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据以考焉”[12](P.875)。将“祠堂”立于全书之首,与吕祖谦将“宗法”列在全书首位的意图一致,借以表达“尊祖敬宗之意”。祠堂作为宗庙的民间形态,其中不仅规定了祖先牌位的摆放秩序“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也规定了大小宗祭祀的标准(“非嫡长子不敢祭”),同时对祭田的分派以及祭器的安置也做了明确说明。如果说宗族是浓缩版的宗法社会,那么祠堂便是民间版的君臣秩序,将天、地、君的关系落实到了亲情体系之中,同时又反过来维护了这个体系的坚固,这构成了宋代礼治秩序中的基础环节。
针对朱熹家礼观念的民间性,还需强调的是其对礼俗的承认。在通礼之外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中经常可以看到其对固有行礼程序的省俭,最大限度地表现出对民众生活的理解、对民间成规的折中。比如谈到冠礼时,针对司马光依据古礼规定二十而冠的主张,称“自十五以上俟其能通《孝经》、《论语》,粗知礼义然后冠之,其亦可也”[12](P.889),谈到婚礼时主张“合人情之宜”[12](P.895),并删去古礼中的“问名”“纳吉”等仪轨,称“今不能尽用,止用纳采、纳币以从简便”,[12](P.897)言及祭礼时,也对程序进行了简省,以诚心为主,“凡祭,主于尽爱敬之诚而已,贫则称家之有无,疾则量筋力而行之”,[12](P.941)如此等等。可见在朱熹这里,对祠堂、深衣制度的强调意在维护基本的“法则”,它们构成了维护民间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骨架。但仅仅这些还远不能令百姓安居乐业,必须尊重他们的生活信仰和习惯,因此朱熹又对固有的繁琐仪轨加以简化,从俗从简,真正做到了张弛有度、法情结合,从而使其家礼思想代表了宋代的成熟形态,并对后世民间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学礼:文人礼治的实现方式之二
宋代的文人礼治的手段除了家礼之外,还包括学礼。家礼重在强化宗法传统,形成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其主要对象是普通百姓,学礼则重在强化基层的学术传统,面对的对象主要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如果说家礼完善了“天地君亲”体系的话,那么学礼则将“师”的因素加入进来。当然,此处之“师”并非指表面的“老师”,而是代表了儒家教化体系向民间的渗透和滑移。民间学礼同家礼一样,宏观上都服务于主流教化体系,亦都是“化民成俗”的手段,但其所发挥效力的层面却较官方礼法更为广泛、深入。
学礼与学校相伴产生。按照目前史料,《礼记》中《文王世子》《学记》就已经出现关于学礼的记述。作为学礼载体的学校产生于夏朝以后,商周时期普遍以“庠”或“序”作为泛称,其时已经有了官学和乡学之分。官学一直被视为正统,是进行礼乐教化的主要机构。但是到了唐宋时期,随着书院的兴盛,乡学数量变得庞大,它们在学术自由的外衣下,对民众教化起到的作用更加明显。宋代是书院发展历程中的蓬勃期。据考证,仅北宋的书院就“当在百所左右”[16](P.4-6),出现了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嵩阳书院等历史上著名的书院。[17](P.41)这些书院风光一时,甚至得到了朝廷的赐书、赐匾、赐田。虽然北宋后期,随着官方兴办的州学、县学的增多,书院受到很大冲击,大幅减少,但到了南宋时期,理学学者讲学风气盛行,民间书院再次蓬勃起来,数量多达400余所[16](P.10-16),几乎是北宋时期的6倍,而且与民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就书院的教学内容而言,主要是经典教育和礼法熏陶。比如北宋太宗时,太宗便应白鹿洞书院之请,赐给书院《九经》;南宋孝宗时,皇帝又曾下诏国子监赐白鹿洞书院“御书石经,及印版本《九经疏》、《论语》、《孟子》等书”[18](P.757);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由此足见,在官方意识中书院实乃主流教育机构的衍生。在南宋时期,虽然学者私自讲学的风气盛行开来,但作为主讲内容的理学仍属于儒学的变体,所以其性质并不曾改变。所不同的是,主要教学内容之外,学礼、学规开始普及并以贴近学生日常的方式发挥着传统礼经的作用。吕祖谦在《丽泽书院学规》(含“乾道四年规约”“乾道五年规约”“乾道六年规约”“乾道九年规约”)中既对宏观道德信条有所规定,称“凡预此集者,以孝弟忠信为本。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遂非者,不在此位”[14](P.204);同时也更加注重具体的行为规范,比如“会讲之容,端而肃;群居之容,和而庄(箕踞、跛倚、喧哗、拥并,谓之不肃;狎侮、戏谑,谓之不庄)”“旧所从师,岁时往来,道路相遇,无废旧礼”。[14](P.204)在《乾道五年规约》中又对上述仪轨进行了补充,比如“不修士检,乡论不齿者,同志共摈之”“同志迁居,移书相报”[14](P.205)。可见,宏观的道德信条相当于一个总纲,学规则更加侧重具体行为规范的限定。
相比之下,朱熹主讲白鹿洞书院时订立的教规,更加完整,且影响深远。朱熹在江西为官时,重新修缮几近荒废的白鹿洞书院,并亲自讲学其中、制定学规,是为《白鹿洞书院学规》(即《白鹿洞书院揭示》)。该学规明确了教学的总纲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15](P.3586-3587)朱熹有感于古礼逐渐沦丧的事实,将为学、待人、接物之法进一步明确化,令学生“责之于身”而产生“戒谨”的效果。与此相配合,朱熹在书院中也身体力行地推行学礼,淳熙七年(1180)三月白鹿洞书院落成之时,朱熹亲自以释菜礼祭祀孔子,“鼓箧之始,敢率宾佐,合师生恭修释菜之礼,以见于先圣(孔子),以先师充国公(颜子)、先师邹国公(孟子)配。尚飨”[15](P.4037)。自此以后,“释菜”礼②在宋代及以后的书院中成为必备的学礼,比如南宋淳熙、嘉定年间设立的明道书院③,其《学规》的第一条即为“春秋释菜,朔望谒祠,礼仪皆仿白鹿书院”,由此可见白鹿书院学规的深刻影响。除此之外,朱熹后来又曾主持岳麓书院,不仅将白鹿洞书院的教规引入,而且沿袭了定期举行释奠礼、释菜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等学礼的习惯,且一直沿用下来。实际上,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致力于兴办书院、制定学礼的目的就是通过民间教化实现对国家礼法的襄助。其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明确指出“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19](P.3363),这里说的很明确,其目的是要回归国家教育的本意上来,即通过下学(书院)而实现上达(国家)。
对于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的意义,陈戍国先生认为这是一种带有理想主义的尝试:“此理想远绍孔孟余绪,遥承《大学》启迪,由内圣而及于外王,由格致诚正而进于修齐治平,由一人克已复礼而至于天下仁爱大公”[20]。按其所言,书院在实现“克己复礼”之小目标的基础上,为达到“天下仁爱”的大目标服务,这便凸显出了学礼的重要性。美国当代新儒学大家狄百瑞也持类似观点,但表达得更为深刻。在狄百瑞看来,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很大程度上依赖儒家社群(confucian communitarian),学校是构建这种社群的重要载体之一。宋明以后,民间书院成为学校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其功能不容小视。他对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以及《学校贡举私议》等推崇备至,称:“在他的《学校贡举私议》一文中,朱子主张的便是一种通盘的,代表中国人文传统的广泛课程。……朱熹另一个论点是:一个受教育的人不能太专注于自己学问的追求,而应该采取更为广泛、多元的态度,来瞭望圣人之道所形成的各种知识和训诲。有许多知识早已残缺不全,这已十分不幸,若学者更只钻研一经或一子,那就更加不幸了”[21](P.40-41)。书院的显性职责是交流思想、传递知识。实际上它充当了思想和学术一体化的角色,是一种潜在的“社群”形态,帮助完成了宋代市民社会中主流意识自上而下的灌输。宋代尤其南宋的学规还有一些,比如《程(端礼)董(铢)二先生学则》(程端礼、董铢)、《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徐元杰)等。这些学规与吕祖谦、朱熹的学规相比,虽然可能更加细节化、条理化,但大抵没有超出前两者的范围,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宋代文人礼治模式的存在是不争之事实,文人在社会治理方面具有极大热情,扮演了庙堂与民间的中介性角色。他们所依凭的对象是家礼和学礼。两者相辅相成,家礼的作用是使人们知其然,但学校礼仪教育则可起到知其所以然的效果,它们构成了宋代民间社会礼仪建构的重要方式。这与唐代不同,唐代更多强调民间约定俗成的定式,往往流于自发和感性层面。这种情况的好处在于人们不受过多礼教条文的限制,民间活力以及人的主体力量更容易彰显,但弊端是久而久之必将导致民间道德体系的崩塌,并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相比之下,宋人也异常关注民间社会,但在尊重日常生活和民间传统的同时,更加多了一份理性规约,试图实现理性的礼法与感性的礼俗之间的融合。在保持民间社会活跃性的同时,加以必要的节制,使其张弛有度,随心所欲不逾矩。其重要保障就是对家礼和学礼的建构和强调,因为两者的施用场合是家庭和学校,补足了从齐家到治国之间的中间环节,所以两者在宋代社会被重视的程度也高于以往。
注释:
①按:历来研究者对《家礼》的作者是否为朱熹,说法不一。比如清四库馆臣在《家礼提要》中便征引元、明诸家论说,最终认定“是书之不出朱子,可灼然无疑”。对此,今人陈来、束景南、彭林等学者都有考辨性文字,认为著者为朱子无疑,本文从此说。
②按:释菜礼,是学生入学时以醢、菜等物祭祀先师的礼仪,《礼记·学记》言:“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郑玄注:“祭菜,礼先圣先师,菜,谓芹藻之属。”一般以文王、孔子为祭主,颜回、孟子附祭,宋代以后,周敦颐、朱熹等人亦加入附祭之列。
③该书院带有纪念程颢的性质,程颢曾在该邑讲学,书院匾额为理宗所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