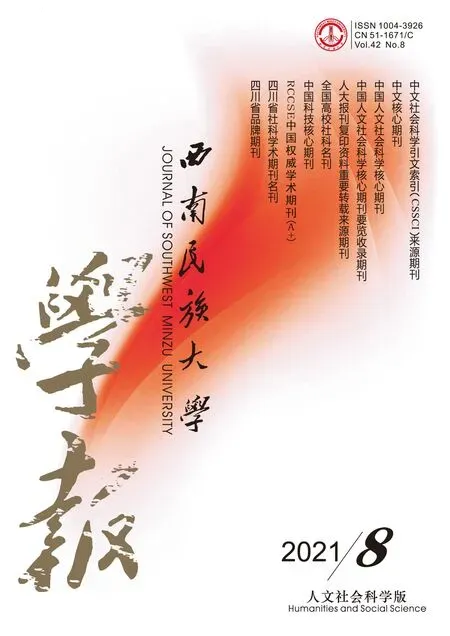诗的形而上学阐释
——马一浮诗性论抉隐
2021-04-17叶蓉
叶 蓉
[提要]马一浮将诗性问题还原为心性问题。他所谓的诗性既不同于维柯意义上的原始思维说,也不同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方式说,而是指形而上者给出自身的等流性,以及形而下者回到自性的可能性。形上之心在原初的自性等流中将自身给出,这就表征为诗性时间。形下之心在诗中运思以为形而上者的着落自身腾出地盘,这就表征为诗性空间。马一浮形而上地阐释诗性的目的在于为儒家诗教实践建立形而上的基础。在他那里,诗教问题不只是面向社会的教化问题,也是面向个人的悟道问题,亦是儒家六艺之学的判教问题。
马一浮先生为我们形而上地理解诗的本质提供了典范,他既依循着儒家的诗教传统,把作诗写字当作变化气质的即本体即工夫的道德实践,又对诗的本质进行了形而上学的阐释,以诗教践履建立形而上学的基础。在他那里,诗性语言既是我们去言说形而上者的可能方式,也是形而上者给出自身的显现形式。诗性问题既不是维柯意义上的思维方式的问题,也不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方式的问题,而是一个形而上的心性问题。诗性亦即诗的自性,要求人回到形而上的性体去寻绎,因为诗性既是形而上的心体为了给出自身而流露自身的等流性,也是形而下的思维之心能够回到形上自性的可能性。形上之心通过原初的等流来显露自身,这就给出了诗性时间。相应地,形下之思通过恒缘义理以使形上之心能够着落于己,这就给出了诗性空间。又,既然诗性是形而下者去言说乃至回归到形而上者的可能性,那么有关诗的审美实践与教化实践也就当然地被赋予形而上学基础的合法性。总之,诗性在马一浮那里被还原为心性,心性的给出自身与回到自身都是通过诗性语言来完成的。
一、诗的哲学认知形态与诗性
仅仅把诗当成一种文学形态,向来不是哲学家们所感兴趣的,因为他们更愿意把诗纳入到他们各自的哲学体系当中来认识。而哲学地去认识诗一般有两条基本路径,一是形而下地认识诗,二是形而上地阐释诗。前者多立足于诗的起源问题以寻求诗的本质,后者则往往将诗的本质同一于形而上者。就形而上地阐释诗来说,又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方式:一是将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割裂开来,如柏拉图的理念论等;二是会通二者,如儒家的形而上学。其中,就儒家形而上学来说,它对诗的阐释一般又有两种理路:一是基于时间性的形上阐释,亦即把诗释为天理发动处,因之诗便被表征为原初的时间;二是基于空间性的形上阐释,亦即把诗释为天理着落处,因之诗即被表征为理体的所居。可见二者都试图把诗的本质规定为形而上者的存在方式,而这也是马一浮去形而上地阐释诗时所因循的思维方法。在他那里,诗一方面是天理发动的最初之机,是自性充盈的最初流溢,是形而上者表现自身的元形式与元语言;另一方面,诗也是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得以沟通的所依之体,诗的活动领域即是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之间的中间场域,在那之中,形而上者可以将自身给出以使自身莅临形而下者可以进入的场域,同时,形而下者亦可亲见形而上者的显身于己以发现且回到自身的本来状态。总之,马一浮对诗的理解完全立足于心性问题,诗的本质即诗性问题已经被还原为心性问题。
这里为了更加深入地认识马一浮之诗的形而上学,我们似有必要对其它有关诗的典型的哲学认知形态进行对照认识,以期真正进入马一浮之即心性即诗性的语境中去。
如前所说,形而上地阐述诗的典型哲学形态还有柏拉图的理念论,但有趣的是,柏拉图似乎不打算仰仗真实的形而上的理念来为诗的存在谋求合法性,反而反衬了它的非法性。在他看来,形而下的现实世界已经是分有理念世界的不真实的影像,而包括诗歌在内的艺术世界复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所谓“对影像的模仿”[1](P.617),因之诗便比不真实者还不真实,而诗人也成了“除了知道模仿外一无所知”[1](P.621)的工艺匠人。可见,柏拉图之形而上地阐释诗不仅没有把诗纳入到形而上的序列中去,反而将之剔除在外。亚里士多德延续了其师的模仿说,认为诗“可以被视为模仿艺术”[2](P.641),但他并没有像其师那样藉助一个外在的形而上者来观照诗的本质,而开始在诗自身的起源问题上来寻求诗的本质,也就是,他不只关心诗人在模仿什么,而更关心诗人为什么能够模仿。他说:“一般来说,诗似乎起源于两个原因,二者都出于人的本性。从童年时代起,人就具有模仿的禀赋。……人们正是始于这种原始的天性,并且逐渐使之得以充分的发展和提高,直至能够信口赋诗的水平。”[2](P.645)亚里士多德将诗的起源诉诸人的原始天性,应该说这为形而下地解释诗的本质敞开了大门,使得后来许多哲学家都喜欢置身于人的原初天性世界来发掘诗的本质,并直言各种形式之诗的起源“都是以人类天性为基础”[3](P.6)的。黑格尔也对诗的原初性进行了探赜,认为“诗是原始的对真实事物的观念,是一种还没有把一般和体现一般的个别具体事物割裂开来的认识”[4](P.1037),也就是,诗以原始的认知方式完成了无意识的合目的性,而有别于辩证思维的有意识的合目的性。不过,将诗的原初性专门进行体系化建构的哲学家还属维柯。他把人类原初的思维方式称为诗性思维,以区别于人类理性能力成熟以来的理性思维,并将之当作一切科学的根基,进而建构了他的新科学。他说:“诗性的智慧,这种异教世界的最初的智慧,一开始就要用的玄学就不是现在学者们所用的那种理性的抽象的玄学,而是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这种玄学就是他们的诗,诗就是他们生而就有的一种功能。”[5](P.188-189)可见在维柯那里,诗性思维是人们在理性能力尚未成熟之际面对外部世界时的内心形式,是人们的原始思维。在一般人的眼中,尚缺乏理智的原始心灵往往被认为是萌动的、幼稚的甚至是蒙昧的,不过维柯却十分推崇这种“还丝毫没有抽象、洗练或精神化的痕迹”[5](P.190)的内心世界,并称它为诗性之心。且人们正是凭借诗性之心而非理性之心,才造就了那些伟大的诗篇。并且,维柯认为理性“甚至妨碍了崇高的诗出现”[5](P.193),因为理智是“一种受制于真理的被动的功能”[5](P.195),它意谓着天性智慧被阻塞,所以尽管理智可以帮助我们辨识出什么是崇高的诗,但自身却流淌不出崇高的诗。这也就是为什么维柯将原始思维称为诗性智慧的原因所在了。
除了将诗还原为人的一种思维方式之外,海德格尔也对诗进行了非形而上的阐释。不过他并没有把诗当作是人的一种特殊的思维工具,而是认为诗乃是此在的最本真的存在方式。在他看来,诗不是我们面对外部世界时所迸发出来的用以表达内心世界的语言形式,反而是诗让我们置身于由诗所创建的世界之中。因为在海德格尔那里,诗的本质在于创建,诗在它所活动的领域内创建了这个世界的根基——所谓“建基意义上的创建”[6](P.44),且诗在建基之时又“把人类此在牢固地建立在其基础上”[6](P.45),因而“人类此在在其根基上就是‘诗意的’”[6](P.45)。既然人的存在之基是诗的,那么人的最本真的存在方式便是栖居于诗之上,所谓“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6](P.51)便是这个道理。不得不说,海德格尔视诗为人的本己的存在方式,而非一种具体的语言行为方式。这简直将诗之本质引入了化境,他“诗化了诗的本质”[6](P.35)而弃绝了语言工具之诗,为人们诗意地存在于世指明了根据。更重要的是,海德格尔对于诗的本质问题的理解,既不是形而上学式的,也不是心理学式的,而是通向于语言本身的。海德格尔说:“人类此在的根基是作为语言之本真发生的对话。而原语言就是作为存在之创建的诗。”[6](P.46)这就是说,诗即是原语言,即是语言之本真,于人而言就是,语言使人存在,诗使人本真地存在。在这里,海德格尔似乎与维柯一样,也想将诗的语言作为语言的原初形式,但不一样的是,海德格尔并没有把诗的语言当作语言未成熟状态之际的自然本性言说,而是径直把它当作了语言的本真状态。也就是,诗的语言绝非语言的众多形式中的一种形式,而是通向了语言的本质。在这里,海德格尔已经不仅通过语言的本质来理解诗之本质,他还试图通过诗之本质去通达语言的本质。他说:“思与诗的对话旨在把语言的本质召唤出来,以便终有一死的人能重新学会在语言中栖居。”[6](P.31)对于存在者来说,语言意味着存在者之存在的空间的创建性,而诗则意味着这一空间之得以创建的根基。语言以诗为原初之基创建了这个世界,所以世界是语言的,同时也是诗的,人既栖居在语言之中,又栖居在诗意之上。这是海德格尔对于诗之本质的存在主义的阐释。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已经认识到两种典型的关于诗的哲学认知形态,它们为我们非形而上地理解诗性问题提供了典范,亦为我们去形而上地把握诗之自性保留了余地——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马一浮的思想世界中找到精当的阐释。
二、诗性的形而上学之道
前文之初我们已经说到,马一浮形而上地阐释诗的问题涉及两个维度的含义:一是基于时间性的形而上的阐释,二是基于空间性的形而上的阐释。我们知道,诗关乎语言问题,因此,形而上地阐释诗的原问题必定会涉及这样两个层面:一、形而下者是否可以藉助语言以通达于形而上者;二、形而上者究竟是以何种语言形式来给出自身。而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又分别指向了诗性的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一方面,形而下者所以能够通达于形而上者,在于形而下者诗性地敞开自身,以使形而上者能够在自身上发生着落,而这一着落之处便是诗性空间;另一方面,形而上者想要显露自身并着落在形而下者身上,就需要等流地给出自身,而这一给出自身的原初等流便是诗性时间。
首先,就形而下者是否可以藉助语言以通达于形而上者这一问题而言,马一浮给予了两方面的解释。一方面,他认为语言不能触及形而上者的实体,而只能指称形上实体的相状,如说:“所言之理只是理之相,若理之本体,即性,是要自证的,非言说可到。”[7](P.31)另一方面又认为证悟自性以来的语言是可以言说形而上的实体的:“一切名言诠表,只是勉强描模一个体段,得到此理显现之时,始名为知。……证后所说之理方是实理。”[8](P.91)这就是说,当我们尚未了知自性而试图去言说形而上者时,只能言及形而上者的相状,而一旦我们已经证得了自性再去言说形而上者,便可通达于形而上者的实体了。在这里,马一浮实际上为我们指出了两种异质的语言形式,亦即气质所发言说与自性等流言说。这里的气质所发言说指的是人们思维取相以来所发起的概念言说,如笔者当下的行文言说即是。而自性等流言说其实就是诗性言说,因为所谓诗性并不是指别的什么,而恰恰是悟道以来的自心的烱然焕发性与自然显现性。诚如马一浮所说:“人心无私欲障蔽时,心体烱然,此理自然显现。如是方为识仁,乃诗教之所从出也。”[8](P.238)总之,当我们想要藉助语言以通达形而上者之时,就必须仰赖诗性语言,而我们获得诗性语言的前提又在于开显形而上的自性本身。而至于开显自性的关键在于什么,则会在后文进行专门解释。
其次,就形而上者是以何种语言形式来给出自身这一问题,马一浮亦有两方面内容的阐释发明,并分别指向了理体之相与理体之性。马一浮认为,形而上的理体想要流露自身而给出自身,实际上存在两种情形,一是形而上者要给出自己的相,二是形而上者要给出自己的性。形而上者之所以要给出自己的相,是因为它自身是一个实在之体,它既然实在地而非虚无地存在着,那么它势必会有它实在的体相。又形而上者之所以要给出自己的性,是因为它复是一个自身充盈的活泼泼的性体。它既是自身充盈着的,故而能流溢自身,它既是活泼泼的,故而能感物而动。至于形而上者是以何种语言形式来给出自身的性与相,马一浮说道:“至道离言,凡言皆寄。净名云‘不离文字而说解脱’,以文字即解脱相,故不悟实相般若,决不能会文字般若。”[9](P.489)此即谓形而上的实体虽然是离言之体,但却可以将自体之相寄附在语言文字之上,彼时之语言文字即是实体之相的所依,它在佛语言之即谓之“文字般若”,在儒家言之即可谓为“相性言说”。又马一浮说:“诗固是人人性中本具之物,特感缘而发。”[9](P.478)复说:“湛寂之中,自然而感,如火始然,如泉湧出,莫之能御。”[8](P.230)此即谓吾人自性感缘发动处即是诗性的,且这种诗性的感动是不假安排的,而是吾心自性自然流溢出来的,此在佛语言之即谓之“法界等流”,在马一浮言之即可谓为“诗性言说”。而诗性语言又不必定是有言说的,因为诗全然是自性发动,自性发动也全然是诗,而自性的发动自身亦是在说出自身,所以它们全然都是诗性的语言。故马一浮说:“若有言,若无言,莫非诗也。”[9](P.458)在这里,诗的本质抑或诗的自性已与语言无涉,它全然是心性的给出自身而已。
到这里,我们似可再次回到诗性问题的原问题,以揭橥马一浮诗性论的核心要义了。概言之,就前一问题来说,形而下的语言虽无法触及形而上者的实体,但即心性而诗性的语言是可以通达于形而上者本身的,这一即心性而诗性的语言便是形而下者合于自性的诗性敞开,便是诗性的空间;就后一问题来说,形而上者通过相性语言以给出自体的相貌,复又通过诗性语言以给出自体的性格,而这一给出自性的诗性语言便是自性的原初等流,便是诗性的时间。不过,由于形而上者给出自身的问题本来就不是思维领域内事,所以马一浮并没有将之作为一个可供探讨的问题提出来,而是将关注点放在了如何藉由言说理体之相进而言说理体本身的活动上。这其实也就指向了前文所遗留的问题,亦即形而下者究竟是如何开显自性以获得诗性语言的?换言之,形而下者究竟是如何将自身置身于诗性空间以为形而上者的着落于己而敞开自身的?对于这一问题,马一浮认为,尽管吾人的日常语言只能言及到自性之相,所谓“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了”[9](P.459),但是吾人想要发明本心显扬自性以使诗性语言从自性流出进而再去言说形而上者,这还须藉助形而下的诗的语言以为阶梯。
所谓形而下的诗的语言是指有理有节的诗的语言而非散乱无秩的日常语言,其以思维为性。而在诗中运思,正是马一浮给出的吾人所以能够证悟形而上者的方法论。他说:“用思才能入理。”[7](P.22)又说:“体究如何下手?先要入思惟。”[7](P.31)可见,马一浮是将形而下的诗的语言作为获得形而上的诗性语言的必要条件的。马一浮曾确切地说到:“当知从初发心至究竟位皆是诗,不得但以加行方便为说。”[9](P.471)这就是说,当我们进行诗的言说或者诗的创作之时,应当确信它就是即心性即诗性的诗性语言,而不应只作方便言说观。这种本然地而不现象地看待诗的语言的思维方法,在马一浮那里被称作正念或正思维。他说:“唯缘义理,即为正念。”[7](P.69)又说:“摄心亦无他术,心缘义理,久久自然调伏。”[9](P.448)总之,对形而下的诗的语言甚至是日常语言进行即心性即诗性地看待,这便谓之唯缘义理,这便谓之在诗中运思。这种思不会使吾人之心在各种境界上来回游离,而是使之定着性地敞开自身,以使形而上的理体能够在自身上有以着落。马一浮说:“思也者,贯乎知能,即理之所由行也。”[8](P.557)这说的就是,形上理体乃是以诗性之思为所行之处也即着落之处的,因之,诗性地运思便是形而上者能够着落在吾人心上之所以,而彼时境界便可谓之诗中“证悟”[10](P.235)。
又,既然形下之思可以返身于形上理体,或谓诗的言说可以返身于诗性言说,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诗是一种合于形上追求的道德实践。这复又引向了马一浮之即心性而诗性的诗教问题。
三、诗教的形而上学基础
马一浮将形而下的运思与作诗视作通达形而上自性的阶梯与资粮,这就为形而下的诗教活动确立了形而上的基础。不过,诗教问题经由马一浮的分殊实际上又涌现出三个层面的内涵,即个人层面上的悟道问题、社会层面上的教化问题以及儒家六艺之学的判教问题。
首先,作为悟道工夫的诗教,它面向的是自己的事情,也就是,我们个人可以通过诗格语言与诗学修养来变化气质,进以回到自性本然中去。正如马一浮所说的:“作诗写字,皆可变化气质。”[9](P.443)但问题是,我们应该作何等诗复又应该如何作诗乃称得上是在变化自身的气质呢?对此马一浮分别从两个层面予以强调,即所谓情与理者。其中,就情以成诗而言,马一浮说:“《诗》以道志而主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凡以达哀乐之感,类万物之情,而出以至诚恻怛,不为肤泛伪饰之辞,皆《诗》之事也。”[7](P.95)这说的是,诗不在辞而在于志,此志即是心的内有所向性,它外向地表现出来即为性情。因此作诗并不是别的什么事情,但能将真性情呼唤出来,便合于真正的作诗之道,正所谓“诗只是道性情,性情得其正,自然是好诗”[9](P.789)。不过,也许情以成诗的难度太大,毕竟性自天然已几于圣,所以马一浮并没有直接将之作为学诗之门,而是主张多教人悟理以成诗,此可从马一浮教人学诗先从读陶渊明诗入手有以观之。他说:“且先读陶诗,毋学其放,学其言近而指远,不为境界所转而能转物,方为近道。……陶诗佳处,在一‘安’字,于此会得,再议学诗。”[9](P.541)由此可以看出,马一浮所以教人学诗要先读陶诗,并不是要学他放逸的生活态度,而是要去领会他究竟是如何不为境界所转而能转物的。马一浮认为,陶渊明之所以能够达于不为境界所转而能转物的安心之境,乃是因为他总是在缘义理以为境,而非缘物境以为境,故而才得以任运自如地以诗说理,复又以理成诗。马一浮亦希冀学诗之人能够如是地把作诗之事当作运思之事,并把缘会义理之思运化于作诗之中,如此方可谓学诗。毕竟,作诗工夫终究是为了体贴义理而回到自性,只不过,“义理虽为人心所同具,不致思则不能得”[7](P.44),因此,作诗之道应须臾不离于缘会义理之思,也只有如此运思,作诗才能变化气质。这便是面向于自己的诗教之旨。
其次,作为道德教化的诗教,它面向的是众人及社会的事情,此有两方面的内涵,分别是志仁之诗与载道之诗。其中所谓志仁之诗是指,吾人浸润诗中实际上就是志于仁爱。因为诗在本质上乃是吾心志仁以来的语言流淌,所谓“摄于志而主乎仁则谓之诗”[8](P.231),所以马一浮常说“诗教主仁”[7](P.19)“诗以配仁”[8](P.135),以此来显扬诗教的仁教之旨。在马一浮看来,诗可以涵养吾人的性情、温润吾人的性格、锻造吾人的气质,以使吾人臻于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进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始终保持在礼乐和同的状态之中,所谓“诗至则礼乐皆至”[8](P.234)。其次,所谓载道之诗指的是,诗乃是道体流行的所依与所寓,所谓“文以载道”“文章不离性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诗在形式上始终表现为语言文字,而语言文字又是形上道体所以寓居自身的载体,因此,倘使吾人也寓居在了诗性的语言文字当中,那么也就能与形而上者同寓一处而又能与道为一了。只不过,个人的寓居于诗是悟道事,众人的寓居于诗才是同化事,因此从圣人层面或者国家层面来说,若能化导众人徜徉于诗的世界之中,那么整个社会也就可以通达于复礼归仁的理想社会了,而这其实也是儒家立诗为教的原始大义。
最后我们再来看作为马一浮判教体系的诗教,它关乎马一浮对儒家诗教思想进行创造性阐释的理论问题。之所以说马一浮对儒家诗教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主要因于他所运用的方法论之新,也就是他通过运用佛教的判教方法,对儒家的六艺之教进行了判教处理,并将诗教判为儒家之圆教的始教。所谓圆教的始教是说,儒家诗教既是始教也是圆教,既是最初之教也是圆成之教,而有别于佛教之权教的始教。那么马一浮何以说诗教是始教呢?这是因为诗教乃是一切教化实践的初始阶段。他说:“仁是心之全德,即此实理之显现于发动处者。此理若隐,便同于木石。……故圣人始教,以《诗》为先。《诗》以感为体,令人感发兴起,必假言说,故一切言语之足以感人者皆诗也。此心之所以能感者便是仁,故《诗》教主仁。说者、闻者同时俱感于此,便可验仁。……兴便有仁的意思,是天理发动处,其机不容已。《诗》教从此流出,即仁心从此显现。”[8](P.135-136)从这里可以看出,马一浮将天理发动处与仁心感动处表征为诗,诗既是天理运动流行的初始状态,也是仁心显现自身的原始形式。诗性活动既本源于天理仁心的运动初机,也是天理仁心一切当来运动最初始的阶段。因此,诗教既是合于初机运化的德行,也是一切教化实践的开端。这是诗教的始教义。而至于圆教义,马一浮认为诗教不仅是一切教化实践的开端,也是具足了一切教化实践的德行。他说:“圣人说《诗》教时,一切法界皆入于《诗》。……当知从初发心至究竟位皆是诗——此圆教义。儒家教义唯圆无偏也,不得但以加行方便为说。”[9](P.471)从这里可以看出,马一浮是借用佛教的因果圆融思维——所谓因该果海、果彻因源——来融会儒家的终始之道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作为始教的诗教自然也就该摄了一切教化的德行,这也就是马一浮讲“举一《诗》而六艺全摄”的道理所在。因为从本源上来讲,儒家的六艺之教都是一心之用,所谓“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只不过诗教表征的是一心的初始之德,而初德又该摄了一切德行,所以诗教就既是始教也是圆教了。
由上可见,马一浮的诗教思想与一般意义上之教化的诗教已经不尽相同了,他既赋予诗教以回归自性、证悟本体的内涵,又将之作为儒家的圆教的始教,显然是将诗教问题纳入到了形而上学的领域中去,而为我们形而上地理解诗的本质开辟了新径。尤其是他的六艺判教思想,更是别开生面,具有很高的思想史价值。
结语
在诗的形而上学的阐释问题上,马一浮将诗性问题还原为心性问题,认为诗性既是形而上的心性本体给出自身的等流性,也是形而下的思维之心证悟自性的可能性。对此本文认为,心性的等流性实际上指向了一种诗性时间,它表征的是形而上的本体正在给出自身的原初状态,也意谓着将自身的充盈实体流溢出来。相应地,思维之心的恒缘义理指向了一种诗性空间,它表征的是形而下的思维之心定性地敞开自身的状态,亦即为形而上者的着落于己腾出地盘。马一浮对诗性的如是阐释,使得他对儒家诗教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一方面,因为诗性即是心性,回到诗的体验,也就可以回到形而上的自性本体,所以诗教践履便是关乎个人悟道的工夫事业。另一方面,因为诗性指向了原初的时间,而人心每一次面向形而上者的敞开自身都是诗性的,也就是诗性就既是原初的也是圆成的,所以马一浮便用判教的语言说诗教既是始教的也是圆教的。总之,马一浮关于诗性问题的见解既有哲学上的深度,也有思想史上的价值,十分值得人们更进一步地探究与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