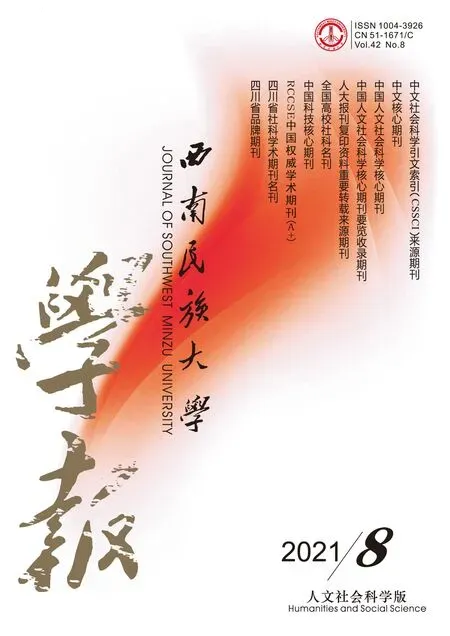对牟宗三诠释朱熹仁说的方法论反省
2021-04-17杜保瑞张雅迪
杜保瑞 张雅迪
[提要]牟宗三的哲学思维模式和方法论对当代中国哲学影响巨大,本文以牟先生对朱熹“仁说”的讨论来反省牟先生对朱熹学说的整体思考,说明牟宗三先生的哲学问题意识,在于对比中西哲学而主张儒学系统是唯一能完成形上学的系统。以此之故,牟先生特别关心儒家道德形上学的证成义,于是所说之本体宇宙论的纵贯创生系统,成了绾合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的天道流行义与圣人践行义的综合型态形上学,并以此为孔孟思想之根本型态、唯一型态。以此解读朱熹哲学时,便将朱熹纯粹谈论存有论的概念定义及概念解析的儒学系统说为别子,关键是在此系统中并不说明主体活动;又将朱熹诠解《大学》所说工夫次第的格物穷理工夫说为只管认知不管意志纯粹化的活动。本文即是对牟先生的思考重做分析,指出朱熹所说存有论与工夫次第论并不违背孔孟实践义,只是说了不一样的形上学系统及讨论了工夫次第问题,而工夫次第问题亦不是对立于本体工夫的问题,以此还原朱熹学说的型态定位。
朱熹“仁说”继承程颐而来,说仁是性、说爱是情。牟先生说这是“本体论的存有系统”,此语确然。说为“存有论系统”即是将“仁”概念仅仅视为一存有的对象而进行概念解析的思辨研议,说“动态的存有论”就是另一种哲学问题的系统了,那是牟先生绾合本体论、宇宙论、工夫论、境界论的一大综合系统的道德的形上学,所以说牟先生的“存有论”概念有二义。此处说为“本体论的存有系统”者,指的是如同西方哲学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多玛斯等的思辨哲学传统而谈概念的系统,朱熹此时确实是在作这类的研究工作。而牟先生讲的纵贯创生系统的动态存有论、无执的存有论、非分别说的系统,却是包含了更多的哲学问题而总称为“道德的形上学”一辞。也可以说讨论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有两种议题:其一为宇宙本体工夫境界融贯为一的实践义的形上学,其二为仅仅进行概念解析的存有论的形上学。也可以说,这正是中西形上学特色的分野,中国哲学长于实践义的动态存有论,西方哲学长于概念解析的存有论,但是中国哲学也有讨论概念解析的存有论的系统,朱熹之所论即是。此二系无需强分优劣,亦无须强分彼此,使其无关,甚至对立。概念解析的存有论思路自是对动态存有论中诸概念的使用意义的界定而形成思考模式以为实践的所依,此所依自然是知识上的所依而非实践意志的提起,实践意志的提起是主体的道德性活动,概念义涵的解析是主体的哲学思辨活动。
笔者之意即是:牟先生毋须以儒家道德的形上学是有主体的实践以及道体的创生的理论型态来否定朱熹之仁说诸义无有此一意境。朱熹此说确实不是在谈实践活动,确实只是在谈实践活动中的价值意识的存有论定位,甚至可以说是在进行概念使用的重新议定,议定之从而清晰地使用之而讨论之,至于要进行工夫实践的活动,朱熹亦可说“我欲仁斯仁至矣”的逆觉体证的话。牟先生关心道德实践及其证成的问题,说存有论的问题非关道德实践活动是可以的,但说存有论非孔孟嫡传而见道不明,以致工夫滑落至一平铺的认知系统,而为他律道德,只是别子为宗的种种话语就是说得过多了。
一、仁性爱情说
朱熹依存有论思路说“仁爱”概念是一性一情的概念,牟先生以为这样谈“仁”概念是静态的分解系统。牟先生定位谈“仁体”需依明道所体贴的意旨,而为即本体即工夫的义理架构:
他依据伊川仁性爱情之说,把“仁体”支解为心性情三分、理气二分,而以“心之德爱之理”之方式去说,这便把仁定死了。故对于道体、仁体终于未有“亲切处”,未有“实见处”,而明道之纲领却正是相应“仁体”而说者。明道并非真是浑沦,其表面之浑沦亦如孔子之浑沦,皆是指点语,其骨子甚清晰。彼亦非形下形上不分者。如诚不分,何言“仁体”?其对于仁体之体悟亦如其对于“于穆不已”之天命流行之体、易体、诚体、忠体、敬体,乃至神体、心体之体悟,彼不是心性情三分、理气二分。仁只是性、只是理,而心傍落、心神与情俱属于气之格局。彼所体悟之仁是理、是心、亦是情,而心是本心,不是心统性情之心,情是本情,不是喜怒哀乐之以气言之情,是以能维持住其为仁体之义,而仍不失形上形下之分。至于形上形下之圆融乃是进一步说。此仁体之特性曰觉曰健,以感通为性,以润物为用,其本身是全德,是一切德之源,故即本体开工夫,即工夫是本体,此是一道德的真实创造性,此是一道德创造的实体,与“于穆不已”“纯亦不已”之天命流行之体意义全同,此其所以为生道。[1](P.232-233)
牟先生认为朱熹依据伊川之思路所说的“仁性爱情”说把仁体说死了,而明道说的识仁之仁体是一能创生万事万物之实体。依据牟先生这样的说法,牟先生所指谓的仁体,一方面是天道,另一方面则是体贴了天道的圣人境界。但是此说中实有若干义理须待疏解厘清。将儒家的天道说为创生作用自是儒学义理格式中事,论者可以先予尊重而不批评,毕竟这就是儒学的天道观——主张有此一天道创造天地万物,并且是一道德意识义下的创造,因而使天地万物有其存在及可被理解之本性,这是说的天道。但是在说天道创生的道德意识中说及此一道德意识即为仁者的本心仁体者,则只能是就圣人境界而说,而非能就任何人的一般存在状态而说的。说圣人时才可说其心是本心,其仁体以感通为性、以润物为用,本身是全德,故即本体即工夫、即工夫即本体,并与天命流行之体意义全同。天道创生天地万物并以道德意识赋予其存在的可被理解的意义,但是天地万物并不即显现为全在有道德理性的存有状态中,亦即,现象中会有为恶的人存有者,这是需要经由圣人的具体实践而点化之,才能使整体存在界全幅地呈显道德理性,因此牟先生所说之此一仁体之活动即是并合天道之流行与圣人之实践而为一之说法者。
这就是牟先生全套思路的系统性架构及问题意识的定位。可以说体贴天道的道德意识的圣人之心,在其提起本心实践的体证状态中,即将天命流行之体、易体、诚体、神体皆体之于己心中,而使己心即此天命之体、易体、诚体、神体,而说为即存有即活动。此说甚善甚美,亦是牟先生建构甚力的说天道及圣人境界的一致性系统之说。问题是,牟先生即以此一系统框架朱熹所有的系统,以致以朱熹之说皆不能呈现此系统之要义而批评朱熹“心性情三分、理气二分、仁只是性、只是理、而心傍落、心神与情俱属于气之格局”,就是把朱熹谈存有范畴的概念关系的思路,视为割裂存有——仁是抽象的理体,心是现象的气,一切割裂,成就不了圆教的系统。
牟先生批评朱熹承程颐之说法而使此理只是存有论之理而非道德之理:
伊川一见“恻隐”便认为是爱,此已顺流逐末,泯失恻隐之心之本义,而复以端为“爱之发”之情,视仁为其所以发之理,即性。视性为只是理,是一个普遍的理,而爱与恻隐乃至孝弟都视同一律,一律视为心气依这普遍之理而发的特殊表现,而表现出来的却不是理,如是,仁与恻隐遂成为性与情之异质的两物,此非孟子之本意也。朱子牢守此说,以为界脉分明,遂有“仁是心之德爱之理”一陈述之出现。此一陈述当然有其道理。此完全是从伊川“阴阳气也,所以阴阳理也”一格式套下来。气是形而下者,理是形而上者。如是,遂将心一概视为形而下者,一往是气之事。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亦皆是形而下者,皆是气之事。此一义理间架完全非孟子言本心之本义。如此言理或性是由“然”以推证其“所以然”之方式而言,此是一种本体论(存有论)的推证之方式。如此所言之理是属于“存有论的存有”之理,而不必是道德之理。但仁义礼智决然是道德之理。心之自发此理(此为心之自律)足以决定并创生一道德行为之存在,但却不是由存在之然以推证出者。[1](P.241)
牟先生认定朱熹所说心、仁、理都不具创生道德行为之功,此说实是混淆了哲学基本问题的诠释进路。就哲学问题之讨论言,并不是一个概念有一个固定的意义,而是一个问题有一套固定的思路以及所使用的概念,因此有这个概念在这个问题的思路下的使用意义,而所有的概念都因所思考的问题不同而有不同的界定,而且并非概念的不同界定都是对立冲突的,它只是同一个名词在不同问题中的意义内涵有所不同,而不是同一个名词被不同的主张割离,以致有义理对错的问题。
孟子的“本心”在朱熹就是“性善之性”之义,孟子的“本心发动”即是朱熹的“心之依性做工夫”之义,因此孟子之概念使用意义在朱熹系统中亦皆被继承。但是朱熹在理气论架构中的“心”概念之使用义,则确实就是牟先生所说的存有论讨论中的使用义,“心”指人之主宰,就人存有者而言,是由理气说的存有论结构来说心,任何人都有此一存有论义的理气结构及心性情结构的心,即便是牟先生所说的圣人亦有此一理气说的存有论结构义的心。每一个人都有理气说的存有论结构,这就是朱熹在讨论的问题,这就是存有论问题,是心概念在存有论问题的讨论中而有的性情结构及理气结构之实事。
就存有论讨论时说心为理气,然而,就工夫论讨论时,则要说心必须处于本心状态而直接做工夫,这时就回到牟先生的纵贯系统了。而所谓“操则存、舍则亡”之说,并非说舍则亡之时就无有此一人心之存在了,只是它不在提起本心或依性而行的状态中,此时说其为在一实然的气存在状态中则可也,而这时就又回到了由存有论的理气说说人心的脉络。
牟先生说程朱之此理是存有论的存有之理而非道德之理,此说实不必要。朱熹从存有论进路所讨论之理即是儒家道德意识之天理,虽然亦含具存在之物之物理、化学的自然之理之义,但是根本上还是以道德意志以创生天地为其本义,不见其说“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吗!只是就人存有者说,经验存在上的实然的人即是理气共构的架构,人本具性善之理,但只在工夫发动的时候它才呈显,谈本具此性而说心统性情是从存有论说,谈呈显是从工夫论脉络说,谈实有此道德价值之理之验证是就圣人境界的全幅呈显此理而证实之的牟先生的纵贯系统之说,因此牟先生不必以实证问题说朱熹就存在而推其所以然之理的存有论讨论非为道德性的。谈实有此理之实证问题是牟先生有以比较于中西形上学的证立问题的关切,以儒家圣人体证而实践而为形上学的圆满义,但朱熹的存有论诸义并不是在谈这个问题,不是谈这个问题就不必批评他的说法不具此义,因此说朱熹的理气说中的理不能活动因而不具道德义是不必要的评价。
牟先生以本体论的纵贯系统批评朱熹所说的理是只能静摆、不能活动,而失自律工夫义,其言:
朱子不加分别,一概由存在之然以推证其所以然以为理,而此理又不内在于心而为心之所自发,如是其所言之理或性乃只成一属于存有论的存有之理,静摆在那里,其于吾人之道德行为乃无力者,只有当吾人敬以凝聚吾人之心气时,始能静涵地面对其尊严。若如孟子所言之性之本义,性乃是具体、活泼、而有力者,此其所以为实体(性体心体)创生之立体的直贯也。而朱子却只转成主观地说为静涵静摄之形态,客观地说为本体论的存有之形态,而最大之弊病即在不能说明自发自律之道德,而只流于他律的道德。[1](P.242)
并不是朱熹把理说成只能静摆在那里,而是朱熹在说理的存有论定位——永恒地就是仁义礼智而不能改变,并且本身不是一经验存在,故而有其作为不变的理存在的意义。孟子讲工夫实践义,此一永存不改的仁义礼智之性发为主体心的情,而活泼生动地实践着,此义与朱熹之义毋须视为相悖。事实上朱熹当然是就孟子的性善说的人性论而建立心统性情说的存有论诸说,只是朱熹进入存有论问题领域中来谈,而孟子在本体论、人性论、工夫论上谈。因此说到工夫义的自律他律问题时,也并不是朱熹主张了他律道德,而是朱熹转入了存有论,故而不指出实践目的,但是朱熹并没有就工夫论问题而主张只要穷此思辨义的心性情理气诸概念的解析定义,即是工夫的完成。朱熹确实说了心是气之灵的话,此说被牟先生严重地视为他律工夫。笔者认为,并不是朱熹主张心不能是道德的超越的本心,而藉由认知活动以为外部工夫而为他律之工夫论张目,而是朱熹在讨论存有论的人存在之心,此实是一经验存在的人之有理气结构及有性情结构的问题,故而就气之灵说人心。总之,当朱熹在说心统性情的存有论问题时并不是在谈工夫论问题,因此也就不能说朱熹成就了任何一种自律或他律的道德理论。
牟先生又说朱熹的心不是道德本心,不是本质地具此理:
心并不是道德的超越的本心,而只是知觉运用之实然的心,气之灵之心,即心理学的心;仁义礼智本是性体中所含具之理,是实然之情之所以然之理;心之具此理而成为其德是“当具”而不是“本具”,是外在地关联地具,而不是本质地必然地具,是认知地静摄地具,而不是本心直贯之自发自律地具,此显非孟子言本心之骨架。[1](P.243)
牟先生说孟子的本心是本具,是本质地、必然地具此仁义礼智之理,此说过于跳跃,笔者不同意。此说表面上是存有论问题,其实是工夫境界论问题。这是主体提起本心做了工夫后才得有的说法,主体若不提起本心,则也无有这些必具、本具的状态可以发生的,所以牟先生的说仁说心概念实在是就着工夫境界论脉络说的。在此脉络中,性善之理先天本具,后天因实践而持守不退而已具,因其不退说为必具。而牟先生说朱熹的心不是道德的超越的本心,因此心与性理的关系是外在的关联的当具关系,而不是本具关系。此处说当具亦合理,然为何当具?乃因其本具也。而本具者何?先天性善之理本具也,而非纯善之德行已而成也。总之,笔者认为,牟先生所说的明道等嫡传系统的本具,其实就是此处说朱熹的当具之义而已,朱熹就是从存有论脉络来说,于是说性就是先天之性善之性,说心就是说人的理气结构的主宰体,它在一般状态中有善有恶,做了工夫以后才会转恶为善,牟先生却因此就存有论的脉络说它不是在本心的状态,因此朱熹之心跟性善之理的关系是外在关联地具有,所以朱熹所言的做工夫以成圣之事业是他律道德。
以上牟先生的思路,笔者不同意。笔者以为,朱熹从存有论进路所说之心,一旦提起此心本具之性时,即得在一本心状态了,即是来到牟先生所说的自做主宰的自律地具有了,即是当具者已具矣!但是这就是从存有论脉络转到工夫境界论脉络了。至于牟先生另说朱熹此心是认知地静摄地具此理者,实是就朱熹强调于格物穷理工夫而说的,这本来就是谈工夫次第的问题,完全不是存有论的问题,因此是二事,不是一事,不必关联至此。朱熹说格物穷理是就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目的工夫次第而说的格物穷理之为次第之先之义,不是说得本体工夫的只要认知不要行动的工夫理论,至于朱熹因此被指责为只谈外部工夫,这是牟先生把朱熹谈工夫次第的说法割裂其义之后再对朱熹所做的批评,是牟先生在朱熹各种不同的观念系统中作不当连结而致生的定位,此义当然不是朱熹之型态。
二、以觉训仁
牟先生对朱熹反对“以觉训仁”之说批评甚重,其言:
至于其驳“以觉训仁”之说,则谓“彼谓心有知觉者,可以见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实也”。夫以觉训仁者,此所谓觉显然是本明道麻木不觉,“委痹为不仁”而来。觉是“恻然有所觉”之觉,是不安不忍之觉,是道德真情之觉,是寂感一如之觉,是人心之恻然之事,而非智之事,是相当于Feeling而非Perception之意。(当然人心恻然不昧,是非在前自能明之)。今朱子以智之事解之,而谓“心有知觉,可以见仁之包乎智,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实”,此则差谬太甚。以朱子之明,何至如此之乖违!不麻木而恻然有所觉正是仁体所以得名之实。今乃一见“觉”字,便向“知觉运用”之知觉处想,不知觉有道德真情寂感一如之觉与认知的知觉运用之觉不同,遂只准于智字言觉,不准于仁心言觉矣。此驳最为悖理,其非甚显,不必多言。[1](P.251)
笔者以为,朱熹批评“以觉训仁”之说确实是朱熹过度用力于从概念定义以及从存有论思路说仁概念是一理概念、性概念之角色,而忽略了在实践中仁体确实是由主体的逆觉而体证的意旨所致,但是,朱熹从存有论进路说仁概念是性、是理亦是无误。至于在工夫论问题中,朱熹就一般人的状态说知觉,实是朱熹不信任一般人的价值主宰能力,则以此一般人的知觉来说仁时极易流于任意恣性之弊,此亦属实。朱熹一方面从工夫论脉络上不信任一般人说的以觉说仁,另一方面又从存有论进路说仁概念是性、是理概念,并此二路而导致牟先生的强力批判。虽然如此,仍不表示朱熹不能即见仁之为性、已具于心,当心提起,即此本心全幅是仁体流行之工夫境界义的仁。从知觉说觉只能说是朱熹的概念运用的型态如此,并不表示朱熹否定可有人心体贴仁性而发为工夫作为之觉润义之工夫观念。此说确实是朱熹说得过度,但牟先生整个否定朱熹不能体贴仁体流行的主体自觉的工夫义也是不必要的。
牟先生又总评明道说仁及孔孟言仁之义与程朱思路不类,其言:
在互联网发展的今天,图书馆馆员应与时俱进,及时更新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确定自己担负的责任和义务。高校图书馆传统的服务内容有借阅、推荐导读、提供信息检索、数据库浏览与下载、信息素养培训等。高校的图书馆馆员顺应技术发展的趋势,坚持为教学科研服务,坚持为师生服务,除掌握必要的图书馆专业知识以外,还要掌握这种互联网+知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此,图书馆馆员应更新理念,主动承担起图书馆的教育功能——做好网络开放资源的收集整理和引导利用服务。
故依孔子之指点及明道之体会,仁与诸德关系亦非仁性爱情,心之德某之理之关系:仁并不专限。仁固可说是性,但却是纯一的性体,仁体即纯一的性体,性体亦即心体(超越的本心天心之心体)。若如朱子之所理解,性体只是一综名(或通名),并不是纯一的性体,结果终于分散而为许多理,而仁只是这许多理中之一理。又性只是理,而不是心,故仁亦只是理,而不是心。心统性情,心外在地关联地具这些理,而复外在地存在地依这些理中之某某理而发为某某情。……故仁是全德,是一切德之源,因而可以统摄诸德,而不为任何一德所限,故仁不能专主于爱而单为爱之理。……本情以理言,不以气言,即以仁体、心体、性体言而为即心即理即性之情。此非朱子之境界也。朱子必又以为是浑沦儱侗矣。然而如果真言道德行为之创生,当然的道德理性真可付诸实践而有力呈现,则必须如此讲始透澈。[1](P.269-271)
牟先生说朱熹所说的仁只是诸理之一。其实,依朱熹之说,仁与义、礼、智的关系既可分说亦可统说,分说时仁义礼智各为一性之德,合说时四德统于仁德,此时其义即同于牟先生所说的“故仁是全德,是一切德之源,因而可以统摄诸德,而不为任何一德所限,故仁不能专主于爱而单为爱之理”。至于性情分说亦是就存有论脉络说的,并不是就工夫提起时的主体状态说的,工夫提起时当然不必再予分说,但就存有论言,则分说绝对是必须的。
牟先生批评朱熹分说心性情理而致性外在于心,其实,依朱熹之说,“性是理不是气”“仁是性不是情”,是就概念分解的存有论问题而说,若就主体做工夫说时,则此心提起本具之仁义礼智之性,即直证天理,且呈显此理,此时朱熹亦得说“心即理”,而事实上朱熹曾经对弟子讲的“心即理”的话表示认可①。心就是同一个主体的心,性就是这个主体的性,如何可说朱熹言性是外在于心呢?心统性情就是一个主体的存有论结构中性情皆具于此人心之内,怎么能说是外在地关联地具?牟先生说的外在关连地具是说只在认知心下而不涉及逆觉体证而说为外,亦即不能在主体的工夫境界状态中而说为外,但这是工夫论议题,讨论工夫论议题时是有没有做工夫以致有没有呈显的问题,也不是是否为本具必具的问题,此时呈显不呈显有其状态上的差异,欲其呈显即是要做工夫,在做工夫时,则主体拳守此性此理而成一能觉润遍生的圣人境界,如此即可转入牟先生说明道识仁的诸义,亦即可说理在心内本具必具呈显地具。但若是在就概念说其存有论问题时,仁自是可说为就只是性而且是爱之理。
牟先生其实是清楚地分疏了朱熹“仁性爱情”说是存有论意旨,而明道识仁说是本体工夫论旨,此义笔者完全接受,可惜牟先生却批评朱熹言仁不及明道,关键即在牟先生只管实践呈显的仁概念使用义,而不能重视概念本身的存有论意旨关系,因此此处的问题只在哲学问题意识的转移,而不在任一概念之只能就特定问题而说其意旨,但是牟先生自己却总是以本体工夫论的纵贯系统去斥黜存有论系统,这才是笔者批评牟先生言说儒学的重点。牟先生只以一义说儒学诸概念的使用意义,他亦并非不理解各个概念在不同系统中的殊义,实际上牟先生从存有论说朱熹所论之义已是对朱熹学说最准确的定位,既已清楚定位,即以此定位理解此诸义即可,实不必又从主体实证天道的本体工夫论脉络再说朱熹诸义不是此脉络,而说朱熹不能体贴此义:
《论》《孟》《中庸》《易传》皆如此发挥,濂溪、横渠、明道皆相应此义而体会道体。惟朱子于此不能相应,遂转成另一系统,而以“心之德爱之理”之方式说仁。伊川对于道体仁体已无相应明澈之契会,而只以分解思考的方式清楚割截地理解成只是理,则其成为朱子之以“心之德爱之理”说仁,乃甚顺适而自然者。是以朱子与伊川之间,可说并无距离,即有之,亦甚小。朱子实可了解伊川也。[1](P.269-271)
牟先生说孔孟之心能当机呈现,而批评朱子之说非此境界。笔者以为,牟先生说的此当机呈现的即心、即理、即情、即仁、即天之诸义,是只能就境界哲学的圣人状态而说的,在圣人状态中,圣人之心即已提起性善之理,因而其情皆发而中节。牟先生说此非朱子之境界,实际上是此非牟先生所引朱熹谈存有论诸文所谈之议题,而非朱子本身的修养无此境界。至于事实上明道、伊川、朱熹、象山、阳明谁能有此境界,这是另外的问题,根本不能从他们的理论内说出。能谈的就是他们的理论,至于理论,事实上是这几位儒学家所谈的问题各不相同,明道是谈境界,故而语多圆融而合一,朱熹说存有,故而语多分解而独立,但是朱熹也曾说境界、说工夫、说本体工夫等议题,且有圆融话语出现之时,但是牟先生又不许其说有此义之贞定。此实不甚公平。说朱熹能承伊川思路是实然,说朱熹反对《论》《孟》《易》《庸》、周、张、明道说本体论的创生系统是不公平之事。朱熹有权力讨论新的问题,《庸》《易》即有新意于《论》《孟》,孟子亦有新意于孔子,因此是牟先生不许朱熹有谈新问题的权力。从本体论说工夫以致境界是一大系统,此诚其然,这是牟先生关切的部分,但是说存有论亦非不能是儒学的义理,这是朱熹“仁说”诸文的问题意识重点。问题意识分解清楚了,即不必提此朱熹不能接续孔孟境界之批评。
牟先生一方面认为朱熹谈“心之德爱之理”的说法于工夫有碍,一方面也明说了朱熹是对一般人的不信任而提出反对“以知觉说仁”的话:
夫由“恻然有所觉”了解仁,即是识仁之名义,岂必“心之德爱之理”方是识仁之名义耶?于恻然之觉而施存养之功,正是有根本可据之地,且比由“心之德爱之理”之说下工夫更为真切,何言“反之于身,愈无根本可据之地”耶?此皆隔阂太甚,故不能声入心通也。末言“『所谓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传闻想象如此耳,实未尝到此地位也。”。胡伯逢亦许诚未到此地位,然试问有几人真能到此地位?此并不碍其“传闻想象”所表示之义理方向之为是。何必由人之造诣以衡量其言乎?此亦不免有过分轻视对方之嫌也。……原夫朱子之所以深厌“以觉训仁”之说,除其误认觉情为智德外,还有一种禅之忌讳之心理。[1](P.282-283)
牟先生说“仁体”之客观面已由主体实践之主观面来证实,而所成之一体实为道德理想主义之真正实现:
明道识仁篇……此客观地说者须由主观地说者来证实:一、证实(印证)天命实体即仁体,使天命实体有具体而真实的意义,不只是一个客观地说的形式词语,仁体与天命实体两者完全同一,其内容的意义完全相同。二、证实(印证)万物一体并非虚说,非只由本体宇宙论的同一本体而说的“一体”之义,此“一体”只是虚的,而且由仁者(大人)的真实生命体现这仁体而真至“一体”之实(感通无碍,觉润无方,莫非己也),此是澈底的道德理想主义之实现。由此两步印证,即可由“一体”直指“仁体之真”,即可认“一体”即是“仁之所以为体之真”。……故感润无方是“仁之所以为体之真”,而必然地所函之“一体”亦是“仁之所以为体之真”。古人说仁体(仁心觉情)都是就具体而真实的仁体之义说,并不就其潜存之义说。[1](P.286-287)
牟先生此文中即明确地以形上学天道论的命题须由主观的实践来证实其真,以说古儒之仁体义涵,此即笔者提出的牟先生关心的是证实的问题,是形上学说实有之路在儒学之以道德意识由圣人实践之而证实之而保住实有。实体是就天道的理性意志说,仁体是就圣人的价值意识说,说两者内容意义完全相同,实是以圣人的价值意识以为所设想的整体存在界的天道原理,因着圣人之真有仁体发为实践,而证成天道实体亦真有其实存者。因此牟先生说形上实体必拉着圣人实践而说,而圣人实践实是一工夫境界论的问题,因此笔者说牟先生的形上学系统中涵摄了工夫境界论而为一整套系统,否则所说之形上实体变成只是一概念的设想,今因圣人之践行,而使天道实体有一作用之真实而宣说,因此以圣人实践仁体之作为即成了同时是本体宇宙论的形上学意义,同时是社会实践的圆满完成的工夫境界义。因此我们可以说牟先生是把社会实践的活动结果置入形上学理论建构之中,结果牟先生谈的是圣人的活动,而不只是儒家的形上学,是形上学理论并合圣人实践活动而成为道德的形上学理论。
牟先生强言古人说仁体一定是就着具体而真实的仁体之义说,并非就朱熹所讨论的存有论地说潜存之义说。其实,古人说仁当然是会要求主体实践的,但是随着哲学问题意识的发展而有新问题的提出也绝对是必须的。说本体论义的仁体是为一价值意识而为天道原理是说仁的一义,说工夫实践义的仁体的在主体上的提起的境界状态也是说仁的一义,说存有论的仁体的作为性即理的意义也是说仁的一义。牟先生强调其必有真实实现的一义,此是就圣人境界说,说圣人境界之仁体而说为必然呈现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就众人之仁体而言,因其尚未实践,但却亦潜存地有,故而只在存有论的潜存上说,亦是应有之说,这就有了当具之义。就众人而言之尚在潜存故应做工夫以实践之之说者,此说更能于工夫义上得其凸显。而为说工夫之实做之必然性要求及必成性之保证之义,而说其“性即理”之性善说的存有论,此一说法事实上更具有现实的功能,是为一要求于每一个人皆需做工夫的理论上的需要。依牟先生所关切的圆满的系统而言,从头至尾就说那必然实现、已然呈现的一体之仁体者,反而是只能说到圣人境界,只能说到天道理体自身,而不能即于一般人。牟先生所论之形上学的被证实为真之圆满义固然无误,但是儒学不可能只谈此主体臻至圣境之义而已。这样的说法是牟先生企图证说儒学作为一说实有之学在一中西哲学比较中之优异之学之心态下的强调,此一强调亦是牟先生有所创造于中国儒学的重要义理,但是不必要因此牺牲朱熹学之若干部分亦为一有意义的理论建构,而强说朱熹学思之为非是。
牟先生甚且直指朱熹是不喜谈主体活动的,其言:
原朱子所以故意这样文致料度亦只在不喜就主体(观时自己处之本心呈露)言仁体耳。一、不喜就主体言;二、不喜言仁体。[1](P.316)
笔者要强调的是,朱熹没有不喜就主体言,朱熹亦有众多就主体言之本体工夫的话语,只是朱熹为制止一般学者就知觉任意上说仁,而转到先从存有论思路定义仁概念,再转出从工夫次第脉络说本体工夫的讨论而已。所以牟先生说朱熹不喜言主体亦是批评过度了。
三、逆觉体证
牟先生对于朱熹批评他人言仁之说法为近禅之事极为在意,牟先生皆以之为朱熹不解逆觉体证之工夫,其言:
盖朱子视“于实际践履中就主体而体证仁本体心”为禅。实则此只是反身逆觉体证之方式内容相同,并非内容意义“切要处”相同。若因方式相同,即认为是禅,则“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之全部孟子学皆成禅!宁有斯理耶?朱子于此何不自反乎?儒者言心言性,称为内在而固有,于此建立真正道德主体性,若不采取反身逆觉体证方式以肯认之,进而体现之,试问敎人采取何方式以体证汝所宣称为“内在而固有”之道德主体(心性)以明其为本有耶?朱子于此总不回头,全走平置顺取之路。难怪其言性最后只成一个消融于太极之普遍之理而平置在那里。[1](P.322)
牟先生以儒者说于识仁、觉仁之语为与禅家形式相同但价值意识不同之说,笔者完全同意,但是朱熹对于此类话语之批评近禅,皆是就说此话语者之实证不足,以致话头落空而批评的,亦即皆是批评人病,因此都不是对于做工夫应是反身体证的反对,朱熹对做工夫是主体实践之事都是肯认、主张且强调的,而朱熹所提之观点则都是切实笃行的实功,参见牟先生引朱熹语:
大抵向来之说皆是苦心极力要识仁字,故其说愈巧,而气象愈薄。近日究观圣门垂教之意,却是要人躬行实践,直内胜私,使轻浮刻薄、贵我贱物之态,潜消于冥冥之中,而吾之本心浑厚慈良、公平正大之体常存而不失,便是仁处。其用功着力,随人浅深各有次第。要之,须是力行久熟,实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盖非可以想象意度而知也。[1](P.320-321)
由此文其实正能见出朱熹的问题意识及关怀重点,实在充满了主体性自觉的本体工夫,只是对仁概念做了存有论义涵的范畴约定,即“仁性爱情”者是,牟先生实不必指责朱熹“只在反对于实际践履中就主体而识仁体耳。”[1](P.321)
牟先生说逆觉体证为自律工夫,说逆觉体证才为真道德,因此主张必须确有一道德本心,但为证说此逆觉之本心如何而有,则是诉诸主体的自我不安之体会,所以笔者说牟先生一直是在证实道德本心的实践活动义上说道德本心作为形上实体的思路,其言:
凡由心之自知而言逆觉体证者,皆是就自觉地作道德实践之工夫言,亦皆是就对遮不自觉地顺物欲气质之私滚下去,而并不知何者为真道德,而说。如果道德行为真是自发自律自定方向,而并不为任何条件所制约,则自觉地作工夫乃是必须者。惟有通过自觉地作工夫,方有真正道德行为之可言。如果真要相应道德本性而自觉地作道德实践,则必须承认有一个“自发自律自定方向而非在官觉感性中受制约”的超越的道德本心而后可。……人在此可问:真有那样一个自发自律自订方向不受任何条件制约的本心吗?茫茫生命海,波涛汹涌,何处寻觅此纯净的本心?汝能指证之乎?汝所说之真正的道德行为真可能吗?[1](P.337)
牟先生要谈真道德行为,这当然是儒学要义、本义、核心义、终极义,在道德实践之时也绝对应该是主体自律自做主宰的意境,主体于此时当然必须认定实有此一主体自觉之本心,然而此一自我认定是一工夫活动的意旨,以谈活动状态中的主体的仁体的活动义而为形上实体的实证是当代新儒家的思路,问题只是牟先生一往直前地就只认定这个脉络的儒学义理,而对于存有论的讨论皆以不能证成此实体而批评朱熹学说,此笔者所欲为朱熹辨正之处。
自持其自己而凸现,吾人即顺其凸现而体证肯认之,认为此即吾人之纯净之本心使真正道德行为为可能者。此种体证即“逆觉的体证”,亦曰“内在的逆觉体证”,即不必离开那滚流,而即在滚流中当不安之感呈现时,当下即握住之体证之,此即曰“内在的逆觉体证”。但是既曰“逆觉”,不安之感停住其自己而凸现,此即是一种隔离,即不顺滚流滚下去,而舍离那滚流,自持其自己,便是隔离。此曰本心之提出。此隔离之作用即是发见本心自体之作用。有隔离,虽内在而亦超越。[1](P.338)
牟先生说逆觉体证的话语在本段文字中是说得极详的,此说反而见出牟先生是以主体在不仁、不安的状态中的感悟此不仁、不安而当下逆反、当下提起、自证仁体而为工夫本义,实际上孟子尚言“扩而充之”的工夫,即是由性善本体论的依据而直上提起,而为扩充,而非逆反。笔者亦非欲以孟子说“扩充”反对牟先生说“逆觉”,其实扩充也好、逆觉也好都是本体工夫。然而牟先生此种对于主体的有恶之不安的察觉以为本领工夫之说法,正预设了主体有不仁的状态,而更见出程颐、朱熹言于理气善恶诸存有论说法的理论必要性。由此正可见出:牟先生以对准工夫实践以证成仁体一路,来驳斥朱熹说存有以分析本体一路,实无其必要。
本文中见出,牟先生对于工夫实做中,主体由不安之自觉而自律提起而呈显仁体而为一体的路径,言之甚深甚详,亦即由此见出,牟先生一直是在谈活动,是并合活动而与,谈活动状态中的主体的仁体的活动义而为形上实体的实证是成立的路 形上道体同义齐谈,是把实践证成与道体义理视为一事,反而排斥了只说道体的存有论思路之种种义理。
而牟先生又不断地说朱熹的从存有论进路说仁体、道体之义是一顺取之路,而只成了他律的工夫,其言:
朱子力斥此“观心”之义,只在误解假能所为真能所,而又不识逆觉体证是自觉地作工夫之本质的关键,故不敢由逆觉体证言仁体,而力反之,因而亦终于不识仁体为何物。此路一堵绝,便总不回头,而只走其“顺取”之路。只顺心用而观物,即曰“顺取”。故其正面意思只是“以心观物,则物之理得”,“本心以穷理,而顺理以应物”,此即为“顺取”之路也。如是,心只停在其认知的作用,而永远与物为对,以成其为主。此非本心仁体之为于穆不已的创生大主之义也。故其“顺理以应物”之道德只成为他律之道德,而非自律之道德。此其所以不识体也。……孔子固未言逆觉,然其所言之仁如自仁道而落实于仁心觉情上说,则一切指点皆是在“即工夫便是本体”中体现此体,同时即是体证此体,因而逆觉体证为其所必函。[1](P.341)
牟先生说朱熹走的顺取之路,是就做工夫由不安而逆觉之对立面而言的,实际上牟先生所有言说朱熹顺取之路的话语,或者一方面不是朱熹在说工夫的话语,而是在说存有论的话语,或者另方面朱熹的话语意思不是牟先生所解读的只认知不实践之义。对牟先生以为是朱熹顺取工夫的话,牟先生自己明确地说这些是存有论而不是本体宇宙论的纵贯纵说系统,笔者完全同意这一点,问题是,牟先生的纵贯创生系统是并和工夫境界论而谈的,而朱熹所谈的存有论并不是在谈工夫论的,牟先生所谓之顺取地谈存有论,是就着认知意义的脉络谈的道体、仁体、心体、性体诸义,这些思路本就不是作为工夫论在谈的,是牟先生把这种非谈工夫而为概念认知的存有论系统视为一种工夫论,并称之为顺取的进路,以有别于他的逆觉之路。其实,言于工夫只要谈本体工夫即可,说为本领工夫亦得,说为逆觉、说为扩充、说为求放心都是本体工夫的话语,本体工夫毋须定为只是逆觉一路,程颢不就甚至说得“不需防检、不需穷索”的话以谈境界工夫的观念吗!而牟先生又以他所定义的顺取之工夫为他律道德,此实不能切合朱熹之意。牟先生以“认知心与物为对”说为外在、说为他律,实是将存有论的认知活动说成了工夫论,而这本就不是朱熹之意,朱熹并不在此处说工夫,那么又何来工夫的他律呢?说荀子的“礼义外于人性”而为他律、说董仲舒的“天意志作为君王行仁政的要求”而为他律皆犹有可说,但是说朱熹在谈存有论的话而变成了他律工夫实在是义理错置。问题是发生在朱熹说存有论的话确实只是认知活动,而朱熹说工夫问题时又因着《大学》文本诠释而说工夫次第问题,而说先格物穷理再诚正修齐治平的话,牟先生就将先格物穷理与只说概念定义的存有论思维为朱熹对立于逆觉体证的顺取之路,只管认知,故是外部他律工夫。笔者之意即是:这些都不是朱熹的意思,而说到工夫,朱熹的工夫论亦是逆觉体证的本体工夫,而且工夫次第并不是与本体工夫对立的另一种工夫。
文中说孔子境界高,故而即本体即是工夫,而一般人做工夫时需为逆觉,明道之识仁即此逆觉,此些话语皆是可说,笔者并不反对。但实亦毋须将逆觉之说说成了与顺取之路正面冲突,而批评朱熹是他律工夫,因为并没有牟先生意下的顺取工夫之朱熹本义这一回事。
结语
本文以牟先生对朱熹对仁概念的意见为讨论对象,对于牟先生讨论朱熹哲学的方法论进行反思。此一工作实是关乎当代中国哲学诠释系统的一大关键问题,因为牟先生的思考模式及方法论架构已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形成一大诠释系统,影响力最为巨大。然而,牟先生固有创造于儒家哲学的新义理,但是也有过度强势的个人意见,本文重点在指出,朱熹说仁、说心性情、说理气的存有论问题不必跟实践哲学问题作较竞而致对立,应独立地讨论及理解其理论功能。而朱熹说工夫论的问题更毋须置入存有论以为同一系统,而致存有论问题意识混乱,朱熹说的格物穷理就是工夫次第中的一项目,并不是唯一项目,更不是只知不行。将朱熹学说的问题意识厘定清楚,还原朱熹学说的理论地位,准确理解及诠释传统中国哲学各家系统,才是促进中国哲学当代化及世界化的正确做法。
本文亦同时处理牟先生思维的根本特质,说其别异中西以实践为要目,辩证三教以实有为要目,而建构其即存有即活动的道德的形上学型态。笔者以哲学基本问题的解释架构,重构牟先生的理论架构,企图将牟先生所形成的坚实的儒学诠释系统适做厘清,期能更清楚见出传统中国哲学的命题意义与理论间架,以使程朱之学、甚而道佛之学能有以摆脱牟先生的强势诠释系统,以及被批判的命运。此一理论工程十分繁琐,笔者有意努力于此,并非执意否定牟先生之学,而是有意接续其说,汲取其养分,转出新意,而更公平地对待传统中国哲学的各家理论,期使中国哲学还能更有创意,这当然也才是牟宗三哲学的再创造之真正意义,亦即从牟宗三之说中走出新说。笔者认为,这样的努力才是牟宗三哲学的新生命所在。
注释:
①参见:先生问:“公读大学了,如何是『致知、格物』?”说不当意。先生曰:“看文字,须看他紧要处……。”次日禀云:“……夜来蒙举药方为喻,退而深思,因悟致知、格物之旨。或问首叙程夫子之说,中间条陈始末,反覆甚备,末后又举延平之教。千言万语,只是欲学者此心常在道理上穷究。若此心不在道理上穷究,则心自心,理自理,邈然更不相干。所谓道理者,即程夫子与先生已说了。试问如何是穷究?先生或问中间一段『求之文字,索之讲论,考之事为,察之念虑』等事,皆是也。既是如此穷究,则仁之爱,义之宜,礼之理,智之通,皆在此矣。推而及于身之所用,则听聪,视明,貌恭,言从。又至于身之所接,则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以至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鬼神 之所以幽显,又至草木鸟兽,一事一物,莫不皆有一定之理。今日明日积累既多,则胸中自然贯通。如此,则心即理,理即心,动容周旋,无不中理矣。先生所谓『众理之精粗无不到』者,诣其极而无余之谓也;『吾心之光明照察无不周』者,全体大用无不明,随所诣而无不尽之谓。书之所谓睿,董子之所谓明,伊川之所谓说虎者之真知,皆是。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先生曰:“是如此。”(朱子语类,卷十八,大学五或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