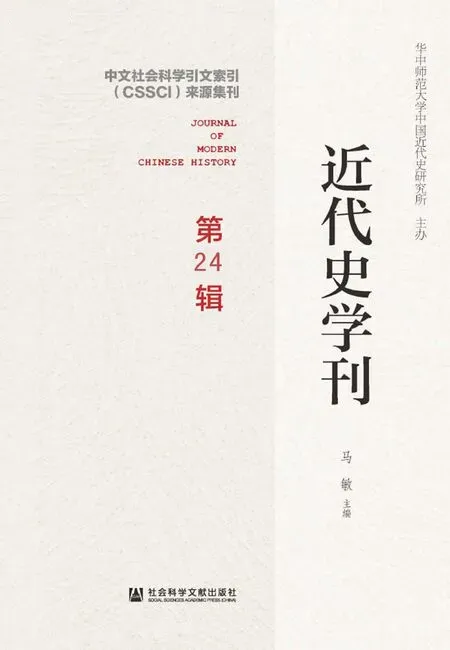政治影响、派系斗争与组织异化*
——战后厦门记者公会纠纷事件再研究
2021-04-17张继汝
张继汝
内容提要 抗战胜利后,因应政治选举和新闻界的现实需要,厦门记者公会筹备成立。然而,因内部职员选举纠纷,部分会员公开宣布退会,导致公会陷于分裂。其后厦门记者公会与退会会员、主管官署围绕该会的合法性问题发生持续争论,矛盾不断发酵,背后派系缠斗若隐若现,导致记者公会沦为各种政治势力争夺政治资源的工具,最终被福建省政府明令停止活动。厦门记者公会纠纷事件凸显了1940年代中后期地方政治、派系斗争对职业团体的复杂影响,它不仅使职业团体异化为政治势力较量的工具,而且动摇了其存在的根基,反映了战后中国新闻记者群体构建职业共同体过程中的困局。
抗战胜利后,随着抗战期间迁往内地新闻机构的回迁,大批新闻记者相继返回故地,因应战后各项政治选举的展开及维护自身职业权益的需要,恢复或重建职业团体被提上议事日程,厦门记者公会就是在此背景之下酝酿成立的。然而,厦门记者公会宣布成立后内部就因职员选举发生纠纷,部分新闻记者公开宣布退会,导致会务中断。其后,纠纷各方围绕记者公会的合法性问题不断缠斗,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被福建省政府命令重新整理,但因利益各方矛盾重重,厦门记者公会无形消解。由于种种原因,目前除笔者前此对厦门记者公会与“胡文虎媚敌”事件的探讨之外,①张继汝:《侨商胡文虎何以被厦门记者公会检举“媚敌”》,《福建论坛》2014年第3期。学界对厦门记者公会纠纷事件尚无研究。鉴于此,本文尝试回到职业团体本身,在厘清该会纠纷事件脉络的基础上,探讨战后中国新闻记者群体构建职业共同体的困局。
一 职员选举纠纷与厦门记者公会的分裂
抗战胜利后,复员工作在光复各地紧锣密鼓地展开,抗战期间迁往内地的机构相继回迁。与此同时,国民政府非常重视新闻机构的复员工作,以填补抗战期间国民党在沦陷区域宣传的“空白”,抢夺舆论的制高点。因此,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行政院就发布训令,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将“原在收复区各地沦陷前所办之报社、通讯社……在原地迅即恢复出版,以利宣传”。①《行政院颁发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电影杂志广播事业暂行办法训令》 (1945年9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2页。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作为舆论之先导、大众之喉舌的新闻记者随军抢先回到光复各地,展开大规模新闻复员和接收工作。
厦门作为华侨聚集的港口城市,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在光复之初成为国民政府复员和接收的重要区域。伴随大规模的复员和接收,厦门新闻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各种报馆、通讯社层出不穷,甚至形成“有街皆报,无巷不社”的局面,②罗美莲:《厦门市记者联谊会整肃新闻界害群之马》,《社会》(厦门)第1卷第6期,1948年11月30日,第12页。可以说这是厦门新闻业最为繁盛的时期,直接推动了厦门新闻记者群体的结社活动。③洪卜仁主编《厦门旧报寻踪》,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第62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厦门记者公会的迅速筹备,还与这一时期厦门的地方政治态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抗战胜利前后,迫于民意压力以及党际竞争,国民党决定实行宪政,“还政于民”,普遍建立各级民意机关成为国民党“实行宪政之真诚与决心”的重要举措之一。④《促进宪政实施之各种必要措施案》(1945年5月18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932页。在此背景之下,1946年2月,厦门地方临时参议会成立,正式参议院的选举工作于5月启动。为了能够以自由职业团体身份参与厦门地方参议员选举,1946年3月16日,中央社厦门分社特派员冯文质、中央日报社(厦门)社长郑善政等25人联合发起申请组织厦门记者公会,并得到厦门市政府的支持,指派冯文质、郑善政、颜子平(厦门《中央日报》),以及胡资周(《星光日报》)、郭荫堂(《星光日报》)、刘长泗(《立人日报》)、叶清泉(《江声报》)、赵天问(《闽南新报》)、王哲亮(《厦门民报》)等9人为筹备员,以冯文质为召集人,负责筹备成立记者公会,设筹备处于中央社厦门分社内。①《请示本市记者公会是否应准存在及对外活动由》(1946年7月),厦门市档案馆藏,A10-001-518。之后,由于《闽南新报》和《厦门民报》相继停刊,赵天问和王哲亮并未实际参与该会筹备工作。对此,当时有记者明确指出,“倘若(记者公会)仅仅为了点缀,为了竞选,没意思”,并号召“正直的新闻记者应该自动携起手来,不看主子的颜色!”②砂己:《整理云何哉》,《厦门大报》1947年10月1日,第4版。可见厦门记者公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新闻界“自动的携起手来”,而是受到了“主子的颜色”之影响。此番言辞可谓将厦门新闻界为了政治“竞选”成立职业团体的真实意图表露无遗,也反映了成立厦门记者公会蕴含的浓重政治色彩。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厦门记者公会筹委会于4月24日召开会员资格审查会议。因各报社登记会员名单中有“少数年资不足,惟均系必要人员”,此次审查会上有筹备委员提出会员资格“应否放宽尺度,准予全部参加”。经筹委会讨论决定,除厦门《青年报》组务主任以及中华出版社发行人、编辑不符合《新闻记者法》规定的新闻记者资格外,“其余照各报所送名单通过,一律准为本会会员”。③《厦记者公会昨审查会员》,《中央日报》(厦门)1946年4月25日,第3版。5月3日, 《江声报》将审查合格的60名会员名单在该报公布。5月5日,厦门记者公会召开成立大会,国民党厦门市党部、厦门市政府分别委派党部干事周永权、社会科科长丘启明到场监选。从职员选举结果来看,《江声报》和《立人日报》在记者公会理监事席位中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江声报》占据理事3席和监事1席;厦门《青年报》也取得理事、监事各1席;但作为记者公会筹委会召集人的冯文质仅当选为候补监事,而战前即已创刊、在厦门颇具影响力的《星光日报》仅获得两个候补理事的席位。④张继汝:《侨商胡文虎何以被厦门记者公会检举“媚敌”》,《福建论坛》2014年第3期。
5月6日,在职员选举中失利的中央社厦门分社、《中央日报》、《星光日报》的23名会员,以该会章程草案在限定会员资格时规定的“凡任有俸给之公职人员均不得参加组织”的内容在成立大会上“不获通过”,导致一些“公职人员”亦加入记者公会,与《新闻记者法》不符,不仅影响“新闻记者之尊严”,而且不利于“工作之进展”,公开声明退出记者公会,导致该会内部出现严重矛盾。①《联合声明退出厦门市记者公会启事》,《星光日报》1946年5月7日,第1版。其后,厦门市市长黄天爵致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代电也明确指出,因“当时会场受一部分人操纵”,上述规定未获通过而在会后引起部分会员宣布退出。②《请示本市记者公会是否应准存在及对外活动由》(1946年7月),厦门市档案馆藏,A10-001-518。
退会会员公开发表的声明和官方往来的信函,似乎都表明是会章草案对会员资格的界定导致了分歧而引起记者公会的纠纷。然而,在表象背后其实还存在更深层次的纠葛。虽然记者公会会员中确实有公职人员,但退会会员中也不乏公职人员,厦门中央日报社社长郑善政就兼理国民党侨务方面的工作。③《厦门新闻志》编撰委员会编《厦门新闻志》,鹭江出版社,2009,第241页。因此,这种双方都存在公职人员参与记者公会的现象并非部分会员宣布退会的主要缘由。此外,抗战期间公布的《新闻记者法》因新闻界的抵制并未付诸实施,似乎也不能成为法理依据。实际上,社会部最初也主张新闻记者资格“依当地习惯斟酌办理”,④《为电请解释新闻记者公会会员疑义一案电仰知照由》(1946年9月27日),浙江省档案馆藏,L51-000-224。只是由于各地新闻记者公会在界定会员资格时出现诸多争议和纠纷,社会部才于1947年6月26日再次指示各地“关于新闻记者公会组织,除应遵照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办理外,仍可参照《新闻记者法》办理”。⑤《福建省政府社会处代电》(1947年8月19日),福州市档案馆藏,0901-7-612。厦门记者公会的筹备显然早于此时间节点,因此,退会一方以《新闻记者法》作为退会的理据,大半只是一种托词。事实上,在厦门记者公会筹委会负责人冯文质看来,该会之所以发生分裂,在于“少数人未能认清公会之意义与作用,致选举时多有偏颇”。⑥《声明不就厦门市记者公会理监事职务启事》,《星光日报》1946年5月7日,第1版。厦门记者公会自身也承认该会纠纷是部分同业因“选举不达目的”突然登报声明退会导致的。⑦厦门市记者公会编印《厦门市记者公会横遭摧残经过》,1947,第3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厦门记者公会最初分裂的真实原因。
在部分新闻记者发表退会声明的同时,中央社厦门分社、《中央日报》和《星光日报》方面当选的理事、监事郑善政、胡资周、郭荫堂、冯文质等人亦联合发出声明:“同人等业经退出厦门市记者公会,所当选职务自应不予就职。”①《声明不就厦门市记者公会理监事职务启事》,《星光日报》1946年5月7日,第1版。至此,虽然记者公会仍极力宣称记者成立大会“经过情形良好”“大会圆满结束”,并在首次理监事会议上做出该会章程“并无自由退会之规定,凡在厦门就业新闻记者不得自由退会”的议案,但厦门记者公会因内部职员选举纠纷而发生分裂的事实已经形成。②《记者公会昨开首次理监事会议》,《江声报》1946年5月8日,第3版。
二 厦门记者公会分裂后的合法性争论
厦门记者公会因内部职员选举发生纠纷之后,虽然也有一些活动,但会务基本处于停顿状态。③《本市记者公会省令准予整理》,《江声报》1946年9月25日,第3版。再加上退会会员向主管官署申诉,致使团体组织的合法性受到很大质疑,并因组织备案问题出现新的矛盾。
7月8日,厦门记者公会向市政府社会科呈请备案,社会科方面认为该会成立“已经过二月之久”,且未将组织章程、会员名册及职员简历呈报,“予法未合”,指示该会“先行补具前来,再凭核办”。但这样的指令对记者公会来说其实比较尴尬,记者公会之所以迟迟未能进行备案,主要原因在于筹备阶段的资料均掌握在退会一方主导的筹委会手中。其后,社会科以记者公会对此指令“置之不理”为由,将该会纠纷情形呈报福建省政府“核夺”。④《记者公会被人盗用竞选不成借端攻讦》,《星光日报》1946年12月19日,第3版。9月10日,福建省政府社会处以厦门记者公会“选举不合”,指示该会重新召开会员大会,“依法办理报核”。厦门市政府社会科奉电后随即指定叶清泉、胡资周、郑善政、王兆畿、冯文质为整理员,负责该会重组事宜。⑤《奉电转饬依法重组记者公会具报由》(1946年9月),厦门市档案馆藏,A10-001-518。
然而,记者公会方面对该会纠纷持不同看法。该会负责人表示,“此次问题之发生,在于‘选举不合’四字,而所谓‘省令’,省方亦系依凭市府社会科之呈报”,并特别强调该会是经市政府派员筹备成立,社会科科长亲临指导监督选举,“倘曰‘不合’,则其不合之责任应由社会科长负之。然事实上却绝无丝毫不合,盖记者公会会员纯与其他一般职业工会或公会会员不同,即使社会科长故意造成‘不合’,而许多记者公会会员亦必当场纠正,断不至于时至今日,犹无一人说出选举时之所谓‘不合’者何在也”。最后,该负责人严正指出,“兹事曲直之判断,必以当时事实为依据,吾人职司舆论,负有纠正社会之责,决不至文饰己遇,反而颠倒是非,苟当局能明白指示‘选举不合’之所在,吾人亦何惮‘重新召开会员大会’,而忠诚接受其命令也”。①《选举有何“不合”,社会科应负其责》,《立人日报》1946年9月23日,第3版。由此可见,记者公会方面认为“省令”中的“选举不合”是依据社会科之呈报做出的,仅是一面之词,并强调该会成立程序的合法性,将该会纠纷之责任推向社会科。
其后,该会编印的《厦门记者公会横遭摧残经过》小册子,指责厦门市政府借该会职员选举的“微细纷歧”扩大双方矛盾,“乘此兴风作浪,舍大多数于不顾,认此为本会发生纠纷,不仅对无故退会会员不加以纠正,且火上浇油,助长事态扩大,朦报省府,捏造本会选举纠纷,故意欲陷本会前途于不幸”。②《厦门市记者公会横遭摧残经过》,第12—13页。同时, 《江声报》也在报端公开指责丘启明“操纵社会团体”。虽然丘启明公开回应人民团体之整理均遵照相关法令办理,并有“报据存案”,③《本市记者公会省令改选 邱启明说明经过情形》, 《中央日报》 (厦门)1946年9月21日,第4版。但《立人日报》仍继续指责丘氏企图操纵记者公会。该报称,虽然厦门记者公会依法成立,并由丘氏亲自出席监选,“毫无毛疵足资吹求”,但丘氏仍沿用其一贯作风, “企图垄断操纵未果,因而多方挑剔,对该会之呈报成立、请颁图记均置之不理,嗣后更变本加厉,颠倒是非,妄报省府以选举不合,而图制造纠纷”,并强调这些行为已“激起该会公愤”,并将依法提出控诉。④《丘启明操纵社团 厦市人民团体书记大都派其私人充任》, 《立人日报》1946年9月23日,第3版。很显然,厦门记者公会与退会会员及地方官厅之间围绕记者公会的合法性问题产生了较大分歧,记者公会与退会会员也依托自身的报纸展开激烈的笔战,导致矛盾持续发酵,成为厦门新闻界备受关注的事件。
11月中旬,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到厦门视察期间,有一些记者专门提及厦门记者公会纠纷之事,厦门《青年报》发行人、记者公会监事郭熏风在发言中报告该会成立经过,强调该会成立程序“依法并无不合”。⑤《昨记者招待会刘主席发表谈话》,《江声报》1946年11月14日,第3版。当天召开的记者公会理监事会议也决定呈请市政府“收回成命”,并由新任理事长吴雅纯将决议案呈报厦门市市长黄天爵。①《为本会组织依法并无不合奉令重组一节恳请收回成命由》(1946年11月),福建省档案馆藏,0011-009-6379。翌日,《江声报》的报道也声称刘建绪在谈话中希望厦门新闻界应“破除成见,切实合作”,试图借此改变记者公会被重组的命运。②《昨记者招待会刘主席发表谈话》,《江声报》1946年11月14日,第3版。然而,退会一方的《星光日报》则在当日的新闻报道中宣称刘氏主张记者公会“最好能够重新改选,以臻健全”。③《刘主席昨假市府招待记者并解答各项询问》,《星光日报》1946年11月14日,第3版。由此可见,《星光日报》与《江声报》对刘建绪的谈话内容可以说是各执一词,代表了矛盾双方的基本态度。随后,厦门记者公会专门致函《星光日报》,强调“翌晨本市除贵报外,各报亦未有此记载”,指出该报登载内容“显系失实”,要求该报进行更正。④《厦门市记者公会代邮》,《江声报》1946年11月15日,第3版。11月15日, 《江声报》记者还专门赶赴漳州采访正在该地考察的刘建绪,并刊发刘氏对该报记者的谈话内容,再次强调刘氏希望“新闻界应切实合作,破除成见……并未谈及重新改选之语”。⑤《刘主席在漳对本报记者谈话》,《江声报》1946年11月18日,第3版。
然而,《星光日报》对此并未给予回应。几天之后,厦门记者公会再次要求《星光日报》更正,表示“勿再缄默为要”。⑥《厦门市记者公会致星光报代邮》,《江声报》1946年11月21日,第2版。面对记者公会的一再交涉,11月22日, 《星光日报》做出回应,仍坚持刘氏的确谈到记者公会“须要重选,以臻健全”,并声称此项内容是否失实,“容将来事实证明”。⑦《记者公会是否改组容事实证明》,《星光日报》1946年11月22日,第3版。在此期间,吴雅纯曾试图缓和双方矛盾,通过时任厦门市市长的黄天爵转达可以让出部分理事、监事职位,由退会一方补缺,但这项提议被冯文质及《星光日报》方面拒绝,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纠纷双方的矛盾在不断积蓄,甚至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之下,11月24日,黄天爵专门密电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呈请省府停止厦门记者公会的对外一切活动,强调该会组织“于法不合”,虽经省府指示改选,但“迄未遵办”,并且“自行刊用图记,擅挂会牌,并利用记者公会名义任意对外活动”,声称这些行为已经引起了退会会员的强烈不满,呈请将该会“自刻图记缴销,并停止对外一切活动”。⑧《厦门市政府市长黄天爵致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密电》(1946年11月24日),厦门市档案馆藏,A10-001-518。
虽然在记者公会纠纷问题上各方仍争执不下、矛盾重重,地方官厅还不止一次地要求该会重组,甚至指令“停止一切对外活动”,但是记者公会方面不仅对这种形势置之不顾,还要求以自由职业团体身份参加厦门地方参议员选举。①《厦门市新闻记者公会通告》,《江声报》1946年12月17日,第3版。这种行为引发了退会会员的极大不满,记者公会的合法性问题再度凸显。12月17日,《星光日报》发表《记者公会参加竞选,组织未合,恐有问题》的文章指出:“本市记者公会因生纠纷,前有一大部分会员登报退出,嗣市府将情报省,经省饬令再行改选成立在案,近该会为积极准备参加选举参议员,造送会员名册(连前退出者亦在内)到市府,并订于十七日召集会员大会,选举初选人三名。民政科以该会名册系本月六日送达已逾法定期间之规定,且前省令改选,乃将之转送社会科审核,社会科以该会组织尚未合法规,且擅行刻用图记,更有未合,该案经已再电省府请示处理中,该科签注后,已于昨再送民政科核办矣。”
《星光日报》虽以“新闻”的形式发表这篇文章,但其目的仍然在于否定记者公会的合法性,这显然激怒了记者公会方面。在当天召开的记者公会第二次会员大会上,原定选举自由职业团体参议员初选代表的议题因当局未派员监选而被暂时搁置,大会聚焦于《星光日报》董事长胡文虎抗战期间的“东京之行”问题,做出“检举胡文虎媚敌”的决议,并以记者公会名义电请国防部将其扣留惩办。随后,支持记者公会的《江声报》、厦门《青年报》等报刊对此大肆渲染和报道,号召会员对胡文虎的“劣迹”进行检举和揭露,其背后所蕴含的意思其实已不言自明。②张继汝:《侨商胡文虎何以被厦门记者公会检举“媚敌”》,《福建论坛》2014年第3期。
针对记者公会做出的“检举胡文虎媚敌”议案以及以《江声报》为首的几家报纸对“胡文虎媚敌”事件的报道和评论,《星光日报》进行了强烈的回击。12月19日,《星光日报》发表长篇文章指责部分报纸操纵记者公会,“竞选不成,借端攻讦”。该文以醒目的文字强调记者公会的违规事项包括职员选举“与记者法规定不符”、对市府要求记者公会呈报成立经过及相关资料的命令“置之不理”、官厅认为其“组织并未合法”,指出记者公会“因开会欲选举参议员,遭市府暨市党部拒绝派员指导监选,致迁怒及本报,攻击政府及本报董事长胡文虎先生,其盗用名义,当不难一目了然”;并表示“记者公会虽经省令改组,该会竟置之不理,居然召集会议,盗用名义肆意攻击他人,近且为参加选举列册送市府申请参加,市府以该会乃为非法组织,昨已批示具呈人吴雅纯所请不准”。同时, 《星光日报》积极寻求地方官厅的支持,专门派记者走访厦门市市长黄天爵,询问黄氏对记者公会不遵法令有何意见。据该报报道,黄氏表示“记者公会纠纷,倘撇开不谈,该会选举迄未报请备案,亦属不合。记者询及该会既不遵政府法令,且公开盗用名义攻讦他人,政府对此有何严处之法。黄氏此时不答,仅摇头代言,观其用意,似有无限感慨”。①《记者公会被人盗用竞选不成借端攻讦》,《星光日报》1946年12月19日,第3版。
同时,退会会员及理事、监事也联合起来公开发布否认厦门记者公会的启事,指出“记者公会亦已蒙省府命令改组,乃近日犹复有人擅开会议,妄出主张,同人等为恐淆乱听闻,特再郑重声明,该所谓记者公会未经政府正式承认以前,一切言行与同人无关”。②《否认所谓厦门市记者公会启事》,《星光日报》1946年12月19日,第1版。作为记者公会筹委会召集人的冯文质还单独发出声明称:
本人忝居新闻界,自赴厦后,承各同业爱戴,推举筹组记者联谊会记者公会,惟当公会成立之日,因少数人未能认清公会之意义与作用,致选举时有多偏颇,当以公会不能代表全体个人,自无参加必要。本人始终认为新闻记者不应有任何派别观念存在,九月间曾接市府转省府社乙申直电嘱负责改组记者公会,当以厦市报人前此既失去联络,今后必须增进感情,彻底合作,借谋业务之进展。但在未经彻底改善之前,对外任何行动本人概不参与,而各单位最好亦以自身名义对外负责为当,以免再度发生意见。特此声明。③《否认所谓厦门市记者公会启事》,《星光日报》1946年12月19日,第1版。
由上可知,由于记者公会做出“检举胡文虎媚敌”的议案以及一些报纸的大肆渲染,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不但《星光日报》极力反击,退会会员也再一次集体发声,公开否认厦门记者公会,并表示该会“一切言行与同人无关”。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冯文质单独对外发表的声明不仅指出了记者公会内部职员选举的“偏颇”,而且间接地公开了牵动厦门新闻界的“派别观念”,这种状况反映了厦门记者公会纠纷的复杂性,甚至可能牵出厦门地方各派系之间更大的争端。
但是,对于纠纷双方来说,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收手或者做出妥协,因此,《星光日报》及退会会员的回击又引起了新一轮的辩论。 《厦门青年报》发表社论《厦市二三事》,谈到记者公会检举“汉奸”胡文虎一事,指出:“有些被资本家的钞票蒙住了眼睛的人,竟不看清事实,对记者公会这一为正义而发出的呼吁,竟认为是‘肆意侮辱侨领’?其实,侨领不侨领,我们尽可不去管他,如果真的是通敌为奸,地位高如汪精卫者,还不免要受人民唾骂,何况是一个胡文虎呢!”①《厦市二三事》,《厦门青年报》1946年12月20日,第1版。
同一天,厦门记者公会为维护该会的合法性,专门发出告各界书,说明少数会员因职员选举失利擅自退会,存心破坏团结,勾结社会科科长丘启明,诬陷记者公会不合法;再次强调记者公会系依据法定程序成立,理监事亦为合法之产生,“如有不合法情事,当时丘启明既不加纠正,一切自应负其全责”;号召同人对于合法成立之厦门记者公会表示维护,对于依法选出之理监事一致拥戴,希望同人联合起来“本大无畏精神,力争到底,绝不忍国家法令之尊严为少数野心家所摧毁与否认,更不忍社会之是非为小数权势所颠倒”。②《厦门市记者发表告各界书》,《江声报》1946年12月21日,第3版。
虽然记者公会方面极力阐述该会的合法性,甚至将其上升到国家法令尊严、政府威信的高度,但是事态显然开始向不利于以《江声报》为首的记者公会方面发展。《中央日报》报道称,厦门市政府以厦门记者公会“置法令于不顾,近且私刻图章,擅开会议,公然发表告各界书,肆意造谣,混淆听闻”而呈报福建省政府核办,省政府以该会“组织未合,竟又藐视政令,目无法纪”,指令厦门市政府严加取缔,停止该会一切对外活动。③《厦市记者公会不得对外活动 省令市府严加取缔》,《中央日报》 (厦门)1946年12月22日,第4版。虽然该会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融通与拖延,但终究未能摆脱“停止一切活动”的命运。几天后,福建省政府又以厦门市记者公会“仍用记者公会名义,到处活动,殊属不合”,训令厦门市政府饬令记者公会“克日将自刻图记长戳缴销,并停止一切活动,勿得违延”。④《通知缴销记者公会自刻图记并停止一切活动由》(1946年12月),厦门市档案馆藏,A10-001-518。厦门市政府在接到省府方面的训令之后,随即饬令厦门记者公会“遵办”。但厦门记者公会显然并没有“遵办”的意思,而是表示记者公会“究竟选举何处不合,无从臆解”,呈请市府“明文指示,以便遵循”,①《记者公会何处不合呈请市府明白指示》,《江声报》1946年12月31日,第3版。并于第二天召开记者公会第四次理监事会议,议定1947年1月3日下午2时假国际联欢社举行正义辩论会,“呈请市府黄市长、丘社会科长及函请社会贤达莅临指导外,合应通告,凡我会员暨各地驻厦同业届时出席参加为荷”。②《厦门市记者公会通告》,《江声报》1947年1月1日,第4版。
资料显示,1月3日召开的正义辩论会虽然有“社会贤达”十多人、会员三十多人参加,但市政府社会科科长丘启明“知道是这事,马上把呈文退回,拒绝参加”,厦门市市长黄天爵也没有出席。会议由记者公会理事长吴雅纯担任主席,阐述记者公会成立及纠纷产生的经过。出席会议的“社会贤达”对记者公会纠纷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要塞司令部代表张元贞提出以调解方式解决记者公会纠纷,厦门市律师公会理事长林大绥提议由出席大会的“社会贤达”组织调解委员会。座谈会结束后,“林大绥等当即进行调解,并请高等法院院长李襄宇、海军要港司令刘世桢等参加奔走。讵费时数月,当局毫无诚意,诸多拖延,迄至本月(五月)五日本会成立周年止,仍无头绪。理事长吴雅纯自以在调解中空耗时间几达半年,会务无法进行,乃引咎辞职”。③《厦门市记者公会横遭摧残经过》,第12—13页。虽然1947年9月末曾传出厦门记者公会重新整理的消息,但此后未见记者公会重新成立。至此,厦门记者公会终究还是无形解散。
三 派系缠斗与厦门记者公会的组织异化
在一般的叙事中,无论是基于外部环境的影响还是内部职业发展的需要,近代中国新闻记者构建职业团体,都被认为是该群体职业意识或职业认同逐渐强化的外在表现。然而,战后厦门记者公会的纠纷事件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
厦门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连接着临近腹地与东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贸易网络,其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有人就指出:“厦门在中国的几个普通市中,当然是一块弹丸小地,虽不能与上海相比,但它复什的情形是与上海差不了许多。如国际外宾聚集,五洋什处,而且环境特殊,党派如林。所以特殊的它是福建华侨出入地区,黄金遍地,即成为宦海角逐场所。”①诸葛军:《厦门政治波澜》,《社会》(厦门)第1卷第1期,1948年9月6日,第10页。厦门的特殊重要性使其成为战后国民党各派系争夺的战略要地。当时任厦门警察局局长的余钟民后来指出,“厦门地方派系的斗争,抗战胜利后尤为剧烈,国民党CC派与三青团,军统与中统之间……可以说‘遇事必争,无孔不入’”,特别是1946年厦门第一届参议会议员选举,“是中统、军统两派斗争最剧烈的一个场面”。②余钟民:《我在厦门警察局长任内的见闻》,政协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厦门文史资料》第14辑,1988,第8页。
为了在厦门扩充势力,报纸成为各派系竞相争夺的重要资源,有的报纸甚至直接由军统或中统等派系创办。例如,《立人日报》就是军统势力在厦门创办的报纸,由军统闽南站站长王兆畿担任发行人,刘长泗担任社长。厦门《青年报》则由三青团厦门分团创办,该团干事长郭熏风担任发行人,在该团任职的吴雅纯任社长。厦门《中央日报》则是厦门市党部的机关报,由与厦门市市长黄天爵“颇有交情”的大学同窗郑善政担任社长,系厦门和闽南CC系的报纸。这些报纸都是由地方派系创办,因此,在言论上多为地方派系的利益服务。据《厦门报业》记载,《立人日报》 “是厦门军统派的喉舌,为在厦军统人员争权夺利制造舆论”,“处处维护军统派系的利益”。而厦门《中央日报》在“当时国民党中统派系与军统派系文字竞争时期,是厦门的中统派系报社的领头羊”,③《厦门新闻志》,第241页。从创办之始就与《立人日报》《青年日报》等报纸“互争权益,互相攻击”。④胡立新、杨恩溥编撰《厦门报业》,鹭江出版社,1998,第76—77页。不仅如此,当时被选为厦门记者公会理事的林纯仁还曾指出,即便是一些私人办的报纸“亦都有背景或有其他目的……这时,厦门报社分为中统、军统两大派。中央通讯社驻厦特派员冯文质参加中统,星光报社长胡资周表面上接近中统,江声报叶清泉表面上接近军统”。⑤林纯仁:《历经沧桑话报史:厦门新闻业的变迁》,政协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厦门文史资料》第7辑,1984,第62—63页。同为记者公会理事的陈一民也表示, “军统、CC、三青团所办的报纸自不待言,就是原来的《星光报》,这时亦投靠CC,染了颜色”。⑥陈一民:《我所知道的〈江声报〉》,政协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厦门文史资料》第1辑,1963,第138页。正是因为厦门各新闻机构存在明显的派系色彩,各报为了生存之需要,“在表面上不得不依附军统和中统两大派别,为此各报之间少不了摩擦”。①江向东:《解放前厦门报刊沿革述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新闻研究资料》第48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207页。厦门记者公会纠纷事件无疑成为各派系在新闻界较量最为集中的表现。
事实上,根据前文的论述亦可发现,厦门记者公会纠纷双方“阵线分明”,主要集中在中统创办或接近中统的新闻机构中央通讯社厦门分社、《星光日报》、《中央日报》和军统创办或接近军统的报纸《江声报》《立人日报》《厦门青年报》之间,退会会员则正属于所谓的中统“阵线”之内。显然,新闻界台前的纠纷其实幕后正是中统和军统之间的较量。对此,林纯仁在后来的回忆中也并不讳言:“记者联合会选举时,冯文质等两名理事落选,《江声报》采访主任林纯仁、《中央日报》采访主任邵庆恩中选理事,中统方面认为所选理事不合预定人选,要再重选,军统方面认为理监事业已选出,可召开理监事会议互选理事长。但理监事会召开时,中统中选的理监事均不出席,可是出席人数过半,即举行理监事会议,结果叶清泉中选理事长,会址设在江声报社。越日中央和星光两报即登启事否认,双方遂进行笔战。”②林纯仁:《历经沧桑话报史:厦门新闻业的变迁》,第62—63页。正是因为理事、监事职位的分配事关中统和军统在厦门新闻界的势力较量,职员选举中失利的亲近中统的会员才迅速发表退会声明,使得厦门记者公会陷于分裂。
受地方派系缠斗的影响,厦门记者公会应有的组织职能被极大边缘化,相反非组织职能成为纠纷双方关注的焦点。虽然新闻记者群体希望通过组织建构维护自身的职业利益,其实际运作却异化为地方派系争夺政治资源的工具,这无疑极大地削弱了新闻记者群体对团体组织的认同感,并引起了一些新闻记者的不满。例如,针对厦门记者公会的纠纷,有人就不无讽刺地指出:“厦门为什么没有记者公会?真笑话。然而知道厦门环境的人,明白当局是怎样去领导组织记者公会,也就了解不尽是‘笑话’的笑话了,而是一种成功的作风?”③江风:《如是我见厦门的记者公会》,《厦门大报》1947年10月1日,第4版。有知情的新闻记者还愤愤不平地指出:“‘记者公会’一名词简直已成为‘赃物’,你要染指,我也要插足,大家分一杯羹算了!于是实行分配,把某职某位畀予某人,横直你我都沾有份儿,不是皆大欢喜吗?”虽然该记者对当时的社会还抱有一丝希望,认为“社会还没那么黑暗,在某个情形之下还有光明的,有了光明就有正义,有正义感的人,是决不会把自身的权益让人们当做‘赃物’去分配的”,但这最后一丝“光明”其实也被记者公会的最终结局彻底湮没。①《记者公会是怎样被酷刑腰斩的》,《厦门大报》1947年10月4日,第1版。还有一些记者表示不愿“卷入(记者公会的)漩涡”:“我是冷眼地看过记者公会竞选、退会诸种把戏的,我也看过正面侧面的批评、谩骂、新闻、启事之类文字的,还有新名堂‘正义辩论会’等等。总之,要写非数十万言不可,不适于贵晚会。而且纠纷双方均为同业,都是吃文字饭的,所以,厦门记者公会之组织不成的内幕,只好让有福的人们去写,吾人雅不愿加入漩涡。”②砂己:《整理云何哉》,《厦门大报》1947年10月1日,第4版。从这些言语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治和派系因素对厦门记者公会组织建构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般而言,近代中国新闻记者构建职业团体主要基于外在执业环境的变化和对自身职业利益的维护,这也是职业团体之所以能够存在的根基,亦应成为职业团体最为主要的职能。然而,厦门记者公会的实践则表明职业团体已然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夺政治资源的工具,政治利益超越了职业利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失却了职业团体应有的职能,无疑动摇了团体存在的基础。厦门记者公会纠纷只是近代中国新闻记者团体纠纷事件的代表之一,它既反映了1940年代中后期新闻界与政治态势的微妙关系,也显示了新闻记者群体构建职业共同体进程中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