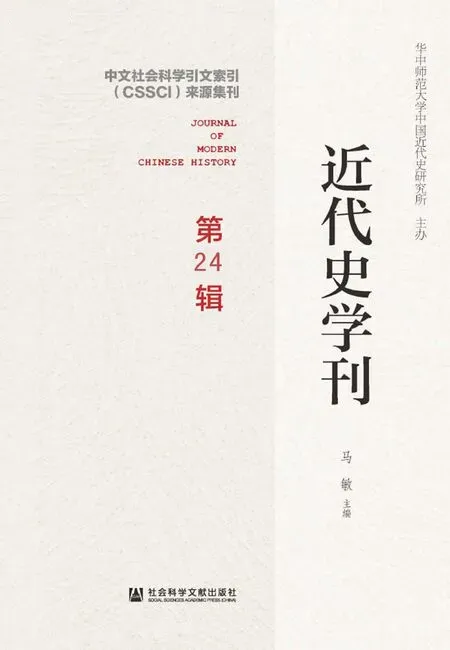植树与现代国家构建
——以近代兰州林业发展为中心*
2021-12-01邵彦涛易仲芳
邵彦涛 易仲芳
内容提要 植树活动不仅提供了新国家建设所必需的物质基础,还体现了新政权的国家能力建设,反映了国家一体化的进程。在近代兰州,刘郁芬的中山植树节比蒋介石的“总理纪念植树节”早了整整两年,反映了冯玉祥系在“中山符号资源”上的争夺;蒋介石“中正山”造林运动的启动,则标志着国民政府对西北前所未有的掌控。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植树成为一种炙手可热的精神资源,它是现代政权通过解决公共性问题以确立自身现代性,进而转化为现代化政绩的集中体现,其意义在边缘地区更为突出。
引言:植树的象征性力量
植树造林运动在近代中国的兴起,是国内生态问题压力释放的内源性表现,也与西方林业思想传入所产生的外力性影响有关,进而成为现代国家构建的一种内在需要。许多政权在建政之初都极为重视植树问题,如19世纪末的犹太政府和20世纪初的苏联政府。近代中国也不例外,袁世凯出任大总统不久,就颁布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森林法》,并在1915年下令以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北伐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也很快颁布了《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各省植树暂行条例》16条,并于1930年重新规定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为植树节,还发起了造林运动。新生政权对植树之重视,主要是因为林业是新生政权财力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基础。袁世凯的《森林法》即以明确山林所有权为主旨,尤其是明确国有林的所有权并加强管理。植树作为控制木材交易的物质利益的象征性力量,是许多新政权积极介入造林、砍伐、交易等一系列行为的重要动机。这一点已为研究林业史的诸多学者所揭示。①中国近代林业史的研究一直受到学界重视,已有成果集中于林政史、区域林业史和林业人物研究等方面,多关注于近代林业发展之过程,而未对林业发展之表征进行过多的讨论。影响较大者有陈嵘《中国森林史略及民国林政史料》,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林业推广部,1934;农林部林业司:《中国之林业》,农林部林业司,1947;焦国模:《林政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熊大桐:《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王长富:《中国林业经济史》,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0; 《中国森林》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森林》,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樊宝敏:《中国清代以来林政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林业大学,2002;樊宝敏: 《中国林业思想与政策史(1644—2008年)》,科学出版社,2009;胡勇:《民国初年的林政分析》,《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E.Elena Songster,“Cultivating the Nation in Fujian’s Forests:Forest Policies and Afforestation Efforts in China,1911-1937,”Environmental History,Vol.8,No.3,July 2003。相关研究成果概况,参见胡坚强《中国林业史研究概述》,《浙江林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苏全有、闫利琴:《对近代中国林业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但是,在为现代国家建设提供物质支持之外,植树活动还具有某种精神层面的价值。如中国传统社会就有在清明节植树的习惯,这种行为是家族性的。北洋政府将植树节定在清明节这一天,就将植树活动从家族行为上升为国家行为,将对祖先的纪念转化对北洋政府的认同。蒋介石在1930年规定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为植树节,则进一步将植树活动从家族内部纪念活动——清明节中剥离出来,变为纪念国父而设立的全国性节日。这不仅以改变前政权设定的国家纪念日的方式转换了权威,更建立了蒋介石本人与孙中山之间的象征性联系。“事实上,通过参加新的植树节和纪念孙中山,民众在蒋介石的领导和贡献中纪念国家,从而在象征性和物质性的意义上,增加了它的资源。”②E.Elena Songster,“Cultivating the Nation in Fujian’s Forests:Forest Policies and Afforestation Efforts in China,1911-1937,”Environmental History,Vol.8,No.3,July 2003.一旦成为一种炙手可热的精神资源,植树活动本身就成为值得争夺的对象,尤其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植树法规和政策在地方的推行往往成为其与中央政府关系的一个风向标,要么是各省遵从中央权威积极实施植树造林法规的结果,要么是该省意图抢夺这一精神资源进而确立自身权威的一种方式。前者体现了地方对中央的服从,由于民国政局的分裂,植树政策在某些省份的实际推行,也往往成为该省真正开始服从中央统治和领导的一个标志,E.Elena Songster笔下的福建即是如此;后者则体现了地方对中央的反叛,某些省份意图通过抢占精神资源在权威形态上与中央政府进行对抗,本文即将讲述的1926年的兰州即是如此。因此,本文试以近代兰州林业的发展为例,分析其与近代国家一体化的关联,进而揭示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将林业发展转变成一个争夺政治资源、展示现代化政绩、获取政权合法性的资源空间的多重历史面相。
一 生态危机与植树造林运动的兴起
清代以后,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农业的发展,山林面积逐渐缩小,毁林开荒、燃料消耗使各地森林大量消失,由此引起的生态问题极为严重。而这种情况在西北地区更为突出。西北的森林资源曾经非常丰富,但因为自然地理条件变迁和人类活动,森林大量退化或消失,到了清末已经相当匮乏。林业的匮乏和生存的需要,不期然地使近代兰州和西北成为植树活动的先驱。
兰州地处西北黄土高原,气候干燥,降水量少而蒸发量大。地面自然植被以荒漠草原为主,多由旱生禾草和旱生灌木组成,低矮而稀疏,一遇干旱便极易枯死。这也导致兰州附近地区森林资源少、森林覆盖率低。尽管兰州南北两山也曾松杉葱郁、绿树成荫,但伴随人口增加而产生的滥伐、滥垦、火灾及战争导致的破坏,兰州附近的植被到清末已经所剩无几。同治回民起义中,皋兰山成为战场,多次大火烧山,不仅其精华所在五泉山被付之一炬,天然森林也几乎焚烧殆尽。进入民国以后,兰州城市建设的消耗又进一步破坏了附近的林木。1916年张广建在兰州建府第,派人进兰州附近林区砍伐林木不计其数。1928年刘郁芬在西固设兵站,将西柳沟及西固川的树木砍伐殆尽。①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兰州市林业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兰州市志》第26卷《林业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第2页。据时人记述:“去过西北的人,无不异口同声说西北是一个黄土的世界,黄土的确是西北的特征。在兰州看不到青山绿水的,登城远望四周都是童山濯濯,不要说树木成荫,连草都不容易看见。”②张沅恒:《忆兰州》,《良友》第156期,1940年。兰州市政府也承认:“本市地高土燥,草木稀少,四围群山,童山濯濯,景象萧条,不仅气候失其调节,环境枯寂,尤足影响市民生活。”①《教育行政》,《兰州市政三周年要览》,1944,甘肃省图书馆藏。到1949年,兰州“除北山在徐家山有一小块榆、柏树林与南山在皋兰山上零星几株老榆树外,其余诸山均是荒山秃岭,极目荒凉的状态”。②施寿:《话说兰州城关区南北两山林业》,政协兰州市城关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城关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90,第90页。
兰州脆弱的生态环境早就引起了官方的重视,其中最早也最有影响的事件自然非“左公柳”莫属。同治五年(1866)陕甘总督左宗棠畅言栽种的左公柳,有“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之美誉,可以视为近代中国官方主导林业经营活动的先导。美国人兰登·华尔纳强调左公柳具有政治意义,他在1923年率福格艺术考察队前往敦煌时指出:“左总督用这笔申请来的巨款,使这条大西北的道路绿树成荫,作为对他的主子君王统治树立一座永久性的纪念碑,同时,也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和为数不多的旅行者们带来恩惠。”③甘肃省档案馆编《晚清以来甘肃印象》,敦煌文艺出版社,2008,第353页。左宗棠在西北的这一举动,与甲午战后清政府真正意识到林业发展的重要性并采取措施相比,早了近30年。鸦片战争以后,魏源等人就提出要振兴林业、设置林业管理机构,可惜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甲午战争之后,朝野上下逐渐意识到林业发展的重要性,许多人发声建议清政府重视林业发展。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要数御史华辉于1896年所上的奏折,他提出,“天下无论何土,必有相宜之树;无论何事,必有可收之利。此则南北各省皆有之,皆宜之”,进而提出了“广种植、兴水利”的建议。④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第3862、3863页。之后康有为、张之洞、刘坤一、岑春煊、赵炳麟等陆续上奏,呈请振兴农林业。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政府设立农工商总局,并于其中设有农务司,掌管林业。宣统元年(1909),农工商部提出了“通知各省将军和督府,调查宜林地和天然林,绘制图说报部,以便制定经营方案”等措施,⑤樊宝敏:《中国清代以来林政史研究》,第73页。并制订了发展林业的年度计划。而就各省而言,最早响应林业发展的,当为驻节兰州的陕甘总督陶模,他在御史华辉上奏的次年(1897)即发布了《劝谕陕甘通省栽种树木示》,罗列了植树造林的六大好处,做出了荒地植树、谁栽谁有、免纳粮银的规定。①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第八册卷三十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第550、551页。福建省官府曾参照陶模的劝文,制定了更为完善的《福建省劝民种树利益章程》,这一章程之后又被刘铭传在台湾引用(详见熊大桐《中国近代林业史》,第96—98页)。光绪二十七年(1901),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均上奏折建议发展农林业。就清末各省份而言,陕甘总督陶模的劝谕种树文是笔者所见最早响应林业发展的地方政策。
尽管我们很难对陶模这一规定的具体成效做出分析,但陶模在西北地区倡导林业发展的思想无疑被继承下来。进入民国以后,朝野人士纷纷宣传、提倡植树造林。1915年北洋政府规定以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1916年的清明节也成为中国第一个植树节。作为袁世凯的亲信,甘肃都督张广建借中央权威结束了辛亥革命以来甘肃混乱的政局,自然十分积极地推行植树造林政策。1917年3月,甘肃省署根据农商部林务处暂行章程的规定,设立甘肃大林区署,管理全省林业事务,由罗经权担任大林区署林务专员。随后,甘肃省署又在兰州举院开办了公立甲种农业学校,罗经权兼任校长。1918年4月,甘肃大林区署召集兰州各界在五泉山二郎岗,举行首次清明植树节大会。甘肃省省长兼督军张广建发表“植树之关系在甘肃尤为当务之急”的演讲,大林区署林务专员罗经权则宣讲了植树造林技术和护林方法,最后共同植树。②《七年三月始行植树典礼》,慕寿祺:《甘宁青史略》第八册正编卷二十九,台北,广文书局,1972,第42页a。
二 全国最早的中山林与政治资源争夺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之后上自中央政府下至地方政府都以各种方式开展活动以示纪念。1928年3月12日,国民政府举行首届植树仪式,国民党要员和南京各界代表数万人齐集尚未完工的中山陵,举行了隆重庄严的植树典礼。该年8月,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于总理逝世纪念时举行植树典礼,并通电各省政府:“此经决议,每岁三月十二日,全国各地一致举行植树典礼,以为全国造中山林之提倡,务期蔚成大观,昭垂无极。”③《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中央党务月刊》1928年第1期。每次植树节时,不仅党政要人均出席参加,以身示范,而且要举行一定的仪式,使这项活动政治化、严肃化、典范化,进而建构一个仪式与实践共同构成的意识形态象征符号。因此学界一般认为,“从1928年开始,植树成为每年孙中山逝世纪念中的一项重要活动”。①罗福惠、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第1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215页。但是,不管是“中山林”抑或是纪念孙中山的“植树节”,都并非自1928年才开始,早在两年前的兰州,就举行过与之十分类似的完整仪式。
中山林在兰州城南里许,原系南郊荒地,“东起方家庄、二郎岗,西至西北大厦,南到山边。这里原先叫萧家坪,是肃王妃子的胭脂地。二十世纪初是一片荒滩坟茔,野草丛生,很少有人活动”。②王文元:《兰州中山林的如烟往事》,《西部时报》2010年6月29日,第11版。1925年底,素有“植树将军”美誉的冯玉祥命其部下刘郁芬率军进驻兰州,并一纸电文招来他的重要幕僚之一、时在绥远主持开荒垦田的杨慕时,委之为甘肃省建设厅厅长。杨慕时到任后,迅速动员省政府机关职员、在校学生参与植树造林,并用以工代赈的方式组织大批民众参与。杨慕时亲自带领民众在龙尾山下栽植树木,疏浚被称作“小五泉”的窟沱,又开沟引左右之水汇聚于下,用来灌溉,成活率很高的苗木逐渐成林。在杨慕时的强势督导下,植树总量被分解到各单位,之后又落实到每个人身上。许多政府机关职员,如时在民政厅工作的赵世英,每年都要去栽树,每周都要提水浇灌,以保证树木成活。1927年,甘肃省署又在雁滩中河滩创建雁滩苗圃,有育苗地0.5公顷,所育苗木专供中山林造林之用。
在1926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之际,国民军决定在兰州城南一带植树造林以缅怀孙中山生前的伟绩。在3月12日这天,国民军驻甘司令、代理督办刘郁芬主持召开了“中山林”命名大会,在兰的机关、学校和团体、部队参加了大会,会后栽植榆、槐、椿等树木数千株,并划定龙尾山及五泉山麓为中山林造林用地,即日开始造林。营造工程由甘肃省建设厅厅长杨慕时负责完成。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中山林已经绿树成荫。1938年,中山林林区面积达到四五平方里,植活各种树木约十万株。③刘亚之:《兰州中山林的兴废》,政协兰州市城关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城关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8,第56页。随后又将其开放为公园,成为抗战时期兰州市民几乎唯一的游玩场所。
刘郁芬建造中山林,也是其进驻兰州取消绿呢大轿后的第二项重要政治举措。反观1926年3月12日的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从中央到地方各有自己的做法。国民党治下的广东召开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北京的纪念活动则分为三派:在中央公园举行的右派、在太和殿举行的左派和自称国民党同人的一派。三派各自为政对孙中山逝世周年进行纪念,反映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各方争夺“孙中山纪念”政治符号资源的态势。①罗福惠、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第1卷,第150、151页。与之同理的是,冯玉祥一派也在争夺这一颇具话语权力的政治符号资源,②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控制了北京,但由于不能见容于其他北洋派系,在政治上非常孤立。因此,冯玉祥积极与孙中山、国民党和其他进步势力靠拢,以摆脱自己的被动地位(参见刘敬忠、王树才《试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1925—1927年的政治态度》,《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尤其是1926年1月冯玉祥在奉、直军联合进攻下被迫通电下野,其在北方的孤立局势变得更为危险。这就促使其在地缘战略上更为接近孙中山和国民党。因此,惯于使用纵横捭阖的政治手段及实用主义权术的冯玉祥通过在其部下刘郁芬控制的兰州城市举行“中山林”命名仪式,成功将孙中山树立为国民军的精神领袖,俨然与国民党军队拥有了共同的“出身证明”。并在国民党方面提出将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定为植树节的两年前就决定在兰州开展孙中山逝世纪念活动,并先创性地将植树实践与孙中山纪念仪式合为一体,形成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孙中山纪念体系。之后,几乎每年的植树节,冯玉祥都会出席各种植树仪式或植树典礼。冯玉祥及其部属刘郁芬的这一举动,成功地将孙中山树立为国民军的精神领袖,自然使国民军的身份更具正统色彩。
三 “中正山”造林与西北政治意蕴
1931年“雷马事变”后,蒋介石先后委派邵力子、朱绍良等官员入主兰州,逐渐实现了对甘宁青等地区的羁縻和掌控。1940年12月,谷正伦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上任前,蒋介石特意接见并赠送他一部《左文襄公全集》,③蔡孟坚:《怀念铁腕将军谷正伦》,《传记文学》(台北)第35卷第3期,1979年,第57页。意在让谷氏效法前贤,能够像左宗棠那样将西北完全纳入掌中。1942年夏,为了解决新疆问题,蒋介石来兰视察。休息期间他登上省署后花园北城墙之“望河楼”,看到蜿蜒在黄河北岸之北山童山濯濯、荒凉不堪,即以“为何不在山上种树”询问陪同参观的谷正伦和建设厅厅长张心一。张心一如实回答说: “以山上缺水,不能种树。”但蒋介石指着皋兰山东侧的一株榆树说:“山顶都有大树,为什么山坡干旱,不能种树?”随即拨给甘肃省200万元,①《兰州市志》第26卷《林业志》认为蒋介石拨款为200万元,但张敦田则认为有2000万元之多。详见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兰州市林业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兰州市志》第26卷《林业志》,第107页;张敦田:《兰州“中正山”的由来》,《兰州日报》2006年5月10日,第B3版。存于农业银行,专做兰州南北两山造林之用,并责令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南北两山的植树造林工作。蒋介石还要求其将造林工作与进展情况每年上报一次。蒋介石的这一指示迅速被贯彻实施,该年12月,甘肃省政府即成立省会造林委员会,谷正伦亲自担任主任委员,张心一任总干事,省农业改进所所长汪国舆任副总干事,刘亚之为技术员。为了响应蒋介石的这一提议,甘肃省政府还将兰州北山一部分命名为“中正山”,范围西起金城关,东止枣树沟,总面积约3.5平方公里。②《兰州市志》第26卷《林业志》,第107页。1943年8月5日,甘肃省政府在徐家山之中峰正式竖立《中正山造林碑记》,谷正伦题写的碑文称:
本市黄河北岸通东之荒山向无定名,三十一年(1942)夏总裁蒋公节钺西巡,对于本省林政建设多所指示,本府根据原订之五年造林计划,遵照指示要点,审度事实,积极进行,并组设省会造林委员会主持策划。旋定名该山曰中正山资为纪念。秋间开始经营,今春继以栽植。复发动群工,辟平沟,洛山洪,用备灌溉。工作虽云艰巨,胼胝未放言劳。继此扶植,孜孜不已,行见十年树本,蔚为车草长林,大业观成,则此山之令名,当与总裁之功业共垂不朽矣。③《中正山造林碑记》,《兰州市志》第26卷《林业志》,第305页。
为了使“此山之令名,与总裁之功业共垂不朽”,甘肃省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于中正山的造林工作。除了动员机关、学校、厂矿、社会团体及市民开展季节性的荒山造林活动外,省会造林委员会还聘用了很多短工。其中尤以邓宝珊所辖新一军驻防盐场堡的军人为多,采取给士兵补贴生活费的办法,由部队士兵承担造林整地工程;或通过兰州市难民救济组织与难民签订合同,以承包形式造林。据刘亚之回忆:“当年在西起金城关,东至枣树沟一带的荒山上,栽种成活了白榆约七八万株(后来都被蛀虫所毁),红柳、侧柏、洋槐等树种共十三万多株。在他(指张心一——引者注)离职时,只交待了十万株,还有三万株因是初栽成活的小树,故未列入清册。”刘亚之认为,当时“名为‘义务植树’实则独具虚名,全靠林场工人专业种植”。①刘亚之:《金城“中正山”》,《城关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49页。不管是军人造林、难民造林还是专业工人造林,要完成十六万株的种植,花费必然不小,这也说明当时甘肃省政府为中正山植树造林所投资的经费之多、决心之大。
中正山植树造林对于蒋介石和在兰政府有着不同的政治意蕴。1942年8月、9月间,蒋介石巡视西北的这一举动,代表着国民政府对甘宁青地区的军事控制达到了其统治历史上的新高峰。而此时“蒋介石对控制甘肃河西走廊的成就,以及即将对新疆的政治治理极为兴奋”。②刘进:《中心与边缘: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第159页。在兰州视察时蒋介石说道:“我们现在如果真正是有事业心,有远大志向,就必须到荒僻边远的地方,开辟我们固有的疆土,来充实我们的国防,巩固我们的国基;凡是军力所及的地方,要使行政权能完全实施,治安绝对良好,人口日益繁庶,物产日益丰富。”③蒋介石:《开发西北的方针》 (1942年8月17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第1614页。由此可见,蒋介石的用意是,在以军事手段确定政治秩序以后,要求各级政府充分发挥行政权能,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其对兰州南北两山植树造林的关心,可视为其要求兰州各级政府积极发挥行政权能的一个体现。在得到蒋介石的指示后,兰州各级政府确实积极行动起来,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力图以南北两山绿化的绝好成绩向蒋介石邀功。
但是,现实似乎总是事与愿违。由于山体干旱、没有水源且在早期设计时存在许多不合理处,中正山的造林成绩一直不甚理想。刘亚之等造林委员会的技术员一直被“始而不活,活而不长,长而不壮”的问题困扰。兰州市政府也坦承:“历年植树运动,又多虚应故事,忽略保护,以致人人皆有‘年年植树、何时成林’之慨。”④郭西园:《两年来之兰州社会》,兰州市政府编《兰州市政二周年》,1943,甘肃省档案馆藏。据统计,从1937年至1949年,中正山共植树39.1万株,成活9.87万株,成活保存率仅为25.2%。⑤《兰州市志》第26卷《林业志》,第108页。更可悲的是,中正山种植的为白榆单一林,⑥上文提到蒋介石在望河楼上以一棵榆树为例,试图证明兰州南北两山是可以种树的。而之后省会造林委员会在中正山上所植树木多为白榆,似乎与蒋介石手指的榆树存在呼应关系,也更说明了甘肃省政府执行蒋介石指示的彻底性和忠诚度。在1952年发生了白榆小蠹蛾,不出几年白榆树即全部毁灭。①刘亚之:《金城“中正山”》,《城关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53页。
中正山植树造林运动的发展可谓颇具戏剧性,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植树运动在兰州所具有的特殊“现代性”,则更能够品味出其中的讽刺。尤其是在兰州市政发展极其落后的情况下,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发展林业,不得不说其中颇有避重就轻的政治投机心理。
四 落后的市政与先进的林政
刘郁芬之后,在兰各级政府对植树造林活动的重视不降反升。1935年邵力子上任后,聘请德国林业专家芬次尔博士来兰主持造林工作。1936年又将甘肃第一农业学校改名为甘肃省立兰州农业职业学校,并公布了《甘肃省森林保护法》。1941年,兰州市政府成立,规定兰州市民每年植树5株,当年就在市内街道、河岸、中山林栽树44.2万株。②《兰州市志》第26卷《林业志》,第9页。植树造林需要资金的支持,为此,1941年4月24日,甘肃省政府与中国银行合资,设立甘肃水利林牧股份有限公司,资金1000万元,专门用于办理农田、水利、森林、畜牧业务。③《兰州市志》第26卷《林业志》,第8页。兰州市工务局成立后,旋即开始在兰州街道两旁栽植行道树,每隔3公尺栽植一株,五路共植树万余株, “责成各该路两侧商店住户,随时浇灌保护,并订定故肆折损赔偿补栽办法,严格执行,俾全数成活,荫庇行人”。④《工作纪实,工务部门》,兰州市政府编《兰州市政一周年》,1942,甘肃省图书馆藏。每年春季,兰州市政府还发动各小学在水车园西园等处植造教育林;各工商团体在中山林总理铜像前一带植造工商林;划定红泥沟荒地数十亩由市党部发动全市党员于秋季植造党员林;划定红泥沟牟家湾作苗圃,由农业推广所负责育苗以利植林;同时规定各团体于每星期日运水灌溉所植树苗。⑤郭西园:《两年来之兰州社会》,兰州市政府编《兰州市政二周年》,甘肃省档案馆藏。
就植树效果而言,据《甘肃省乡土志》对1944年各县市植树株数的统计,兰州市当年植树60200棵。⑥朱允明:《甘肃省乡土志稿》,第547页。1943—1945年,由甘肃省会造林委员会自办荒山造林和指导市内各机关团体植树造林共249666株,其中指导造林120667株,私人植树数量微乎其微(详见表1、表2)。

表1 甘肃省会造林委员会造林或指导造林数量

表2 兰州市历次植树情况不完全统计
但是,在近代兰州城市其他现代化事业处于十分缓慢的发展状态之时,林政的快速发展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由于林政的发展并不特别需要西方现代技术手段的支撑,也不需要过多的经费支持,还与西北严重的生态问题相呼应,故很容易被兰州政府拿来作为一个表现政绩的工具。首任兰州市市长蔡孟坚在其回忆中就坦承,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市政建设若着眼于社会与教育等改革,“收效迟缓,且难奏功,只有改善交通,促进市区繁荣与建设,才是工作重点”。之后,“中央对开发西北,主张在荒山普遍植树”,“当时我大声亟呼:‘要绿化兰州’,使四周围山区,将来变为绿荫葱葱”。①蔡孟坚:《首任兰州市长的回忆》,政协兰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第5、12页。1942年,中国工程师学会各专门工程学会在兰州举行第十一届年会,蔡孟坚以“如何建设新兰州理想中未来陆都”为题,提出了绿化兰州问题,提请出席年会的各工程师讨论。他说:“绿化兰州为一般人士之殷切企盼。亟应利用山岭,广治林木,调节气候,增进风景,改善市民生活,俾尽地利。惟水源缺乏,种植困难,应如何竭尽人力以技术补救自然缺陷。”在是年8月10日举行的兰州市政府纪念周会上,蔡孟坚又邀请内政部张维翰次长演讲“如何造成一个园林化的兰州市”,同年还制定了《兰州市保护树木办法》共14条。②《民国首任兰州市长的绿化情》,《晚清以来甘肃印象》,第64页。
据熊大桐对1932年全国种植中山纪念林数量的统计,在21个省份中,甘肃省兰州中山林植树数量217000株,仅次于福建省,位列全国第二。③熊大桐:《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第183页。据《实业月刊》对抗战前各省造林情况的统计,1935年的苗圃面积以四川第一、甘肃第二、贵州第三,育苗株数贵州第一、甘肃第二、四川第三,造林株数则四川第一、贵州第二、福建第三、甘肃第四。该年各项统计的前三名几乎都是偏处西部的贵州、甘肃和四川三省,甘肃也多处于第二或第四的位置。④《抗日战争前各省造林统计表》,《实业月刊》1937年第2期。以三省的财力而言,能够在造林工作中居于全国前列几乎不可思议。
这正说明,以植树造林为现代化的政绩并非仅存于兰州一隅,在整个西部地区都很普遍。1946年春季的植树节上,马鸿逵在训话中就提及:“甘肃有‘左公柳’,我们宁夏也要有‘马公杨’。”⑤裴景福:《河海昆仑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第177页。张世明在研究中也提到:“左宗棠大西北植树所树立的不仅是有目共睹的‘左公柳’,而且在后来者心目中树立了一种景行仰止的标尺。在民国年间,许多‘西北王’们企图效仿左宗棠而千古留名,杨增新、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概莫能外。”①戴逸、张世明在研究中就指出,由于春播和植树同凑一时,青海农民当时有的要到几十里路以外的指定地点种树,有伤农时。而所有树苗均强行摊派,农民有地无树,只得变卖家产高价求购或以劳力向富户换取树苗。在栽树过程中,警察手持棍棒监工,稍不如意,即行打骂、罚跪和顶石头。详见戴逸、张世明《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第125、126页。但这种林业开发并非田园歌式的变奏曲,而往往成为以普通百姓的沉重负担为代价的苛政。“现代化的开化目标在军阀政治之下以原始野蛮的方式实行不能不说具有反讽的诡吊意味。”②戴逸、张世明:《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第125、126页。时人旅行青海时感叹:“青省造林为全国第一,平均每年栽植两千余万株,学生公务员一齐出动,不像内地各省,仅在植树节点缀点缀。”③时雨:《青海行》,《西北通讯》1947年第7期,第26页。这一评论用在兰州身上也并无不妥,在兰各级政府的重视使近代兰州的林政事业获得令人意外的发展。在城市现代化的其他方面乏善可陈的情况下,具有现代化属性而又无须过多现代化技术和资金支持的林政事业的快速发展就成为边缘地区面向国家展现“现代化政绩”的绝佳手段。
五 结语
近代中国林业的发展既是现代化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国家通过解决公共性问题确立自身现代性的手段,进而形成了某种象征性的精神资源。从中央政府层面而言,裹挟了现代化属性的林业发展,不仅是中央政府现代性的体现,也是国家能力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而为其政权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持。在地方政府层面,林业政策在各省的推行与否,正体现了国家一体化的进程;一些省份在林业政策上的亦步亦趋,则反映了它与中央政府的亲疏关系。与此同时,林业发展也成为地方政府现代化政绩的集中体现。这种象征性意义在边缘地区更为突出。
在以现代化为核心话语的民国版图中,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十分突出。对于一些偏僻落后的地区而言,它们在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市政现代化等方面都大大落后于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政府要想取得较为突出的现代化政绩,就不得不另辟蹊径。而在偏僻落后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最能够代表现代性的各项事业中,林业显得尤为特殊,它既不特别需要先进技术的支持,又与本区域严重的生态问题相呼应,自然会成为一个既不特别费钱费力,又能格外展现出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现代化手段。所以如冯玉祥、阎锡山、马步芳等人才会对植树活动产生不寻常的热衷,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来推动植树造林活动的开展。①参见李玉才《冯玉祥植树造林的理念与实践》,《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蒋萱:《马步芳在青海的植树造林》,《兰台世界》2005年第9期;王社教:《民国初年山西地区的植树造林及其成效》,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3辑;李三谋:《民国前中期山西的林业活动》,《古今农业》2001年第1期。在兰政府对植树造林事业的热衷,也包含着这种以植树为现代化政绩的政治投机手段,这也反映了在兰政府以植树为自身塑造现代性外衣的政治统治策略。
只是,如果现代国家构建非但没有给边缘地区的发展带来促进改善,反而遗忘了国家的旧使命,甚至使国家的不同地区“沿着不同的方向在运行、某些地区的成功与其他地区的失败密切联系在一起”,②马俊亚:《国家服务调配与地区性社会生态的演变——评彭慕兰著〈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那么这个政府体制的合法性必然要遭到质疑。对民国时期的兰州市政府来说,市长蔡孟坚极力呼吁的“绿化兰州”,在兰州市民看来,只是在给兰州戴“绿帽子”。③蔡孟坚:《首任兰州市长的回忆》,政协兰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第12、13页。兰州市政府在林政发展上所获得的有限成功远远比不上由普通市民利益受损所带来的合法性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