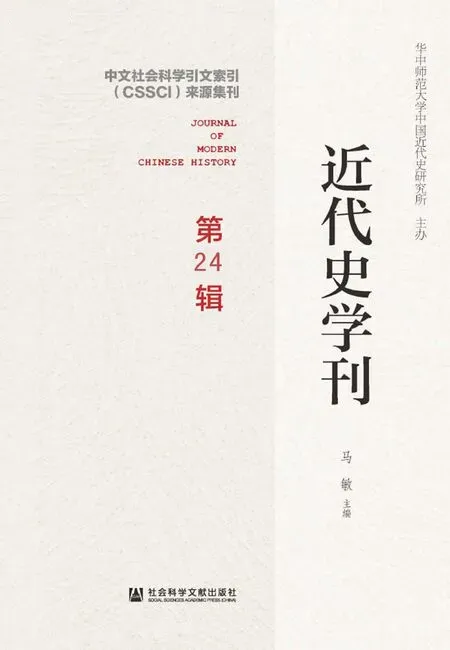行欠清偿与近代中国外债的产生*
2021-12-01马长伟
马长伟
内容提要 行商作为清政府授权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代表,执行朝廷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策略,清政府对其债务负有担保责任。行欠源于中英贸易间商业信用,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政府走向前台,以军事服务经济侵略,要求清政府偿还300万两行欠,以维护英方的权益。清政府由债务担保方变为承担方,行欠由或有债务变为直接债务。行欠表面上是行商与英国商人的商务纠纷,其背后是中英政府之间的博弈。行欠经历了商业信用向国家信用的转变、商人私债向国家债务的转变,成为近代中国政府直接负有偿还责任的外债。
清朝前期,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被泛称为“十三行”。十三行又称“洋行”,洋行商人被称为“洋商” “行商”。清政府“为避免可能出现的政治问题,极力避免与外国发生政治联系。在广州口岸,西方各国甚至无法与中国地方政府进行交往,一切交涉都通过十三行商人作为中介”。①王泉伟:《天朝意识与明清中国的朝贡外交》,《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行欠是指行商对外国商人的欠款,又称“夷欠”或“商欠”。
外债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产物,研究中国近代外债,必须研究清代前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国际贸易、外资政策以及广东十三行“行欠”。②许毅等:《近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第35页。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的外债始于晚清咸丰年间。咸丰三年(1853),上海道台吴健章为了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募雇英美船3艘,议价银洋13000元。这是经清廷允准认可,由地方当局筹借的第一批外债,可视作中国近代外债的起源。①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编印《清代外债史资料》上册,1988,第1页;邓子基、张馨、王开国:《公债经济学——公债历史、现状与理论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第177页;吴景平:《关于近代中国外债史研究对象的若干思考》,《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但是笔者认为,中国外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南京条约》中由清政府代为偿还的十三行“行欠”。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强迫中国与之建立了不同于传统体制的条约关系,中国走上了由无债、借债到依赖外债的道路。目前学界对行欠的研究多局限在行欠的产生以及国家的治理层面,②参见彭泽益《论鸦片战争赔款》,《经济研究》1962年第12期;林延清:《试论清中期的“夷欠”问题》,《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郭双林:《〈南京条约〉中的“商欠”问题》,《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章文钦:《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的商欠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蔡晓荣、孙宝根:《鸦片战争前的“行欠”纠纷与中英交涉问题新探》,《天府新论》2006年第6期;吴义雄:《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前夕的行商体制》,《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张坤:《道光九年(1829)前后的行商制度危机及其调整》,《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5期;葛彦波:《略论鸦片战争前的“商欠”偿还》,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04。而且关于行欠的属性、终结,以及行欠与债务的关系存在争议。基于此,笔者拟从历史层面剖析洋商、外商之间的商业信用关系,从学理层面剖析英国政府逼迫清政府直接偿还行欠的根源,进而阐述行欠与国家债务之间的渊源与联系。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追本溯源,厘清国债债务产生的缘起,有利于推进当前的财政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 商业信用与行欠产生
商业创造信用,商业也依赖信用。国际间商业信用是国际资本流通的一种形式,是金融国际化的一种表现,也是外债产生的缘起。近代中国行欠问题,就源于中英商人国际贸易之间的商业信用。
研究行欠问题,必须从行商制度入手,明确贸易双方的地位与权限。清康熙年间创设海关,设置闽、粤、浙、江四大海关。1757年,乾隆皇帝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制度。广州贸易的主要特征,是中国海关由海关监督与地方督抚共管,或地方官员兼管,但各官员并不直接与洋人交涉,而是采取“以官制商、以商治夷”的政策。朝廷授权“十三家”被称为“行”的商号,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代理人。开办这些行的人,即所谓“行商”。洋商与中国官府之间不允许有任何直接接触,洋商只能通过指定与他们做生意的中国特许商人,向总督、巡抚和“户部”转呈禀帖。①〔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计秋枫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第102页。1757年,清政府限定华洋通商于广东一港,更使广州为华洋之唯一所在。当时之华洋贸易,专利于公行之手,故称“公行时代”。②谭春霖:《广州公行时代对外人之裁判权》,《燕京大学政治学丛刊》1936年第28号,第4页。马克思指出,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外国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领有政府特许执照从事外贸的行商进行交易。这是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③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96页。
鸦片战争之前,中外交易主要是以货易货,外国商品在行商中按额分配。由于市场需求不旺盛,行商代销商品往往不能及时售完,其未售之货,等到下次洋商到时,一面归清旧欠,一面又交新货。由于“不能年清年款”,④梁廷枏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校注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第500页。外国商人将货物赊销给行商,待下次来华时,再行结账,便产生“商业信用”。随着中外贸易扩大, “夷人违禁放债,又复重利滚息”,⑤梁廷枏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校注本》,第498页。行商难以清偿。行商一旦经营不善,甚至破产倒闭,就无法偿还货款,形成商欠。
林延清总结,“商欠”指中国洋行商人欠下外国商人的借款而言。这种借款主要由三个方面产生:其一,正常交易中,洋行商人欠下的应付给外商的货物款项;其二,洋行商人向外商的借款,以及洋行倒闭欠款;其三,洋行商人挪用应付给外商的货物款项以缴纳税款或贡派、摊派而造成的欠债。⑥林延清:《试论清中期的“夷欠”问题》,《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马士指出,行商拖欠外商的债务,是在两种情况下发生的:通过买卖货物的普通贸易过程以及由于外商贪图高利而做的放款。在由这些原因发生的一切债务之外,还必须加上另一项有优先索偿权的债务,就是在货物上欠缴政府的关税税款。货物的买卖,行商们享有绝对的垄断权,因而对于关税和勒索,他们也须负责。⑦〔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第183页。简单来说,行欠是买卖货物中的赊销行为造成的,是商业信用的体现。但是,也受到政府征税和勒索的影响。这为英国商人向要求清政府代为清偿行欠留下了口实。
“河泊”(粤海关部)或广州海关监督,是皇帝的直接代表。担任这个官职的人员,在广州享有法定的和实际的对外贸易垄断权的整个时期,也极尽搜刮之能事。在广州不再享有对外贸易的独占权和公行被取消之前,清廷均保留粤海关部的权力和收益上的直接利益。①〔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17页。行商具有官与商的双重性质,除经商外,他们也充当中国政府与外商的媒介,代表清政府参与外商和外贸管理事务。同样,当行商经营出现债务负担时,政府也多有干预或救助。
乾隆四十二年(1777),行商倪宏文的欠款,一半由其兄弟偿还,一半由地方官员代赔。乾隆五十六年(1791),奉圣谕:“行商吴昭平揭买夷商货价久未清还,情殊可恶,应照拟发遣。所欠银两,估变家产,余银先给夷商收领,不敷之数,各商分限代还。但内地商人拖欠夷商银两,若不即为清欠,转致贻笑外夷。着福康安等即将关税盈余银两,照所欠先给夷商收领,再令各商分限缴还归款。”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来华,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的信中,特地写进了行欠处理问题。信中说:“前次广东商人吴昭平有拖欠洋船价值银两者,俱饬令该管总督,由管库内先行动支帑项,代为清还,并将拖欠商人重治其罪。”乾隆六十年(1795)7月,“此后各行商等似此拖欠过多,或该国王闻知,以内地行商拖欠夷人账目多至数十万两,或竞具表上闻,实属不成事体。着传谕广东督、抚及粤海关监督,嗣后洋商拖欠夷人货价,每年结算,不得过十余万两。如有拖欠过多,随时勒令清还,即自今岁为始,通饬各洋商一体遵照办理。将此谕令知之”。②梁廷枏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校注本》,第500页。
上述案例中,行欠事涉外交,清政府不断加强管理,主动由财政拨款代为偿还商人私债,说明政府已经承担了债务偿还责任。但是,从乾隆到道光,行欠问题有增无减。一般而言,政府债务包含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和政府或有债务。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是指须由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属政府债务;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是指由政府提供担保,当某个被担保人无力偿还时,政府须承担连带责任的债务;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是指政府不负有法律偿还责任,但当债务人出现偿债困难时,政府可能需给予一定救助的债务。后两类债务均应由债务人以自身收入偿还,正常情况下无须政府承担偿债责任,属政府或有债务。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2013年12月30日公告,第1页。
显而易见,行欠产生于行商和英国商人之间的贸易,是行商的私债,是商业信用的表现。但是,清政府主要是通过行商代征和行商承保纳税来保证进出口货物的税收征收。行商是清政府特许的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他们具有官与商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凭借政府的特许,从事对外贸易,垄断所有进口货物和大宗出口商品的买卖;另一方面,他们又充当中国政府与外商的媒介,代表中国政府参与对外商和外贸事务包括海关事务的管理。②曹英:《近代中外贸易冲突及中国应对举措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213页。从历史史实来看,清政府及外商均将行商的债务认同为政府负有担保和救助责任的或有债务。
二 行用征收与行欠整理
行商因各种原因,难以及时、足额偿还债务时,会出现信用风险,甚至出现破产违约的事件。这种违约事件牵涉到国家声誉、外交等问题。1759年,洪仁辉控告广州行商欠款不还。乾隆皇帝认为,“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③《清高宗圣训》卷20“圣治”6,第1—2页。此后,清政府力图通过制度设计来减少违约概率,降低违约风险,缓解内外压力。1759年,粤督李侍尧奏准管理外商章程《防范外夷规条》,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公行不可负外人之债。”④陆丹林:《广州十三行》,《逸经》1936年第1期。此后,嘉庆与道光年间,清政府不断颁布法规严禁向外商借贷。可是,这并没能阻止行欠的产生,相反,行欠问题越来越严重,到鸦片战争前夕,甚至成为英国武力侵略中国的借口。
清政府对行欠整理的举措主要有:其一,整顿行商,加强管理,表现为严厉惩戒欠款行商。一旦事实确凿,就查抄行商家产,归还欠款。更有甚者,遣送充军。上文提到的倪宏文,就因无力偿还,被遣送伊犁。1813年,采用“总散各商联名结保”的办法,通过公同挑选和集体作保制止财力薄弱的人充当行商。
其二,采用征收行用的办法,偿还欠款。1780年,清政府开始执行征收行用,偿还欠款的制度。行用原是行商向部分进出口商品从量征收的一种附加税,用来“办公养商”,是“洋商公行的公费”。行用因早期是供应公共开支,由行商公司统一管理使用的基金,所以被西方称为“公所基金”。该项税收始于1780年,是从对外贸易中征收3%的金额,帮助行商摊还泰和行颜时瑛、裕源行张天球等商欠款。后来成为惯例,“查出欠款,或奏设公柜,抽提现商行用;或由各商分摊归款”。①《卢坤奏查办粤海关商欠饷银大概情形由》,蒋廷黻编《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道光朝》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第149页。行用用于支付包括行商欠款在内的各项额外公共开销,如清偿拖欠、罚款、亏折等债务。
从表1可以看出,公行以行用支付行商欠款2669296元,支付行商欠缴关税793836元。其中1829年支付最多,达到648859元。征收行用,偿还商欠,是行商群体对行商债务承担了连带赔偿责任。嘉庆十八年,粤海关监督德庆奏言:“外洋夷商,来广贸易,全赖洋行商人妥为经理,俾知乐利向风,以昭天朝绥怀远夷至意。从前办理洋商欠饷之案,俱移会督、抚,将乏商家产查封变抵,其不敷银两,着落接办行业之新商代为补足。如行闭无人接开,众商摊赔完结。倘再有亏欠夷人银两,即会同督、抚专折奏明,从重治罪。”①梁廷枏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校注本》,第502—503页。

表1 1825—1834年行商支付商欠数量单位:元
清政府要求全体行商分摊行商欠外国人的债务,行商就用收取行用的方式支付。但是,行用是个别行商从每笔交易中零星收取的,支付却是整批付出的,每次支付行欠对行商都构成现金需求压力。自1770年至1843年,行商团体共负担7846000两夷欠。②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第284页。如表2所示,行商每年需要支出关税、捐输、分摊行欠、设施及家族费用,还要满足官吏榨取,开支巨大。行商在纯粹商品交易以外,每年需要100万至230万两白银的开支,而其资金极其有限,全体行商资本总额也不过100万两。若将开业之初地方官吏强行取去的数额去掉,则行商的可用资金少得可怜。因此,行商破产事件时有发生。

表2 行商每年所需最低总周转金单位:两
行用征取后由行商支配,不必直接上缴,此项税收为清廷所许可,但西方人将其视为一项不堪忍受的不合理收费。③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第183页。1829年,英国散商在给两广总督李鸿宾的禀帖中说,按广州贸易中的通行做法,如有行商破产欠债,便要其他行商还钱,而被要求摊还债务的行商便向“外商所贩货物征取额外税费,对贸易大有损害”,④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第185页。要求政府更改制度,减轻外国货物的税费。1834年,道光皇帝就地方官吏、行商额外征税事颁发谕旨:“近年来粤商颇多疲乏,官税之外,往往多增私税。甚有官商拖欠夷钱,盈千累万,以致酿成衅端。”①蒋廷黻编《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道光朝》第2册,第125—126页。
1840年3月18日,自诩“从1834年开放对华贸易以来,经营不列颠制造品的对华输出上做得比任何人都广泛得多”的莫克·维卡致函巴麦尊,指出:
行商每有新的倒闭,公行所承担下来的债务一般都相应地加到进出口关税上去,而这种负担却又并没有按照它的加税目的去开支,而是浪费到贿赂上去,亦即是被总督和他的下级人员榨取去了。这是一种经由帝国海关监督的安排而造成的政府关税,是为了个人利益而阻碍将来商务的负担。
目前破产行商积欠英商大量债务,其数可能达到75万镑之多,中国政府是承认这笔债务的。我只想提出,政府不可允许中国人用损害我们将来对华商务的办法去筹还这笔债务,以免失策。如果允许他们对我们的商务课加新税,借以筹款还债,那我是强烈反对的。②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三联书店,1958,第53页。
行商问题牵涉到国际关系,清政府必须把这种中外商人之间的商业纠纷视作两国之间的外交事务来处理。政府作为债务担保人,执行了“行用征收”的办法,转移债务负担。但是,由于官员的勒索,加上税负转移触及洋人的利益,洋人反对征税还债。为避免交涉,对于行商的债务,谕令众行商共同摊赔,甚至由中国官府清偿,使得行欠纠纷陷入了一个“外交化”的误区。③蔡晓荣、孙宝根:《鸦片战争前的“行欠”纠纷与中英交涉问题新探》,《天府新论》2006年第6期。事情发展到19世纪30年代越发严重,一直到鸦片战争前,行欠问题都未能解决,在华贸易的商人开始鼓动英国政府采取新的解决方案。
三 国家信用与行欠清偿
1837年初,广州的十三家行商中有三四家公开承认无力偿还欠款,行欠总额达到300万元,外加75万元的欠税。其中,兴泰行宣布破产,该行欠款达到2261439元。①曹英:《近代中外贸易冲突及中国应对举措研究》,第207页。英国商人不愿意按照惯例办事(行欠由公行摊分的方式逐年偿还)。他们认为,“这种债务与以前所有的债务都不大相同,它完全是产生于实际的交易活动”,“第一次在自由贸易体制下解决债务纠纷就建立一种拖延支付的先例是不得当的”。他们希望借机解决所有破产行商的债务问题,以便“将未来的贸易置于更加安全的制度之上”。②曹英:《近代中外贸易冲突及中国应对举措研究》,第207—208页。英国商人开始向政府求助,要求解决商欠问题。
其实早在1835年6月,格拉斯哥印度协会等与对华贸易有关的团体纷纷致函外交大臣巴麦尊,指出中国行商垄断贸易、压迫英商,且常常发生破产事件,而广州英商又无生命财产的保障。凡此,都妨碍英国对华贸易借着中国的庞大市场向英国开放贸易自由的机会做迅速而广泛的扩张,因此促请英国政府采取步骤。③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37页。
1836年7月17日,格拉斯哥工商联合会理事会上首相迈尔本子爵备忘录:“中国对外贸易背负许许多多的税饷和沉重的勒索,税率和征税方式都是随意决定的,绝大部分由政府责令行商负责缴纳,这样英人财产就有被行商用来归还对政府欠债的危险,而大家知道行商多数都是在破产状态中的。备忘录提呈人深信陛下政府会采取各式各样的办法来扫除妨害达到目标的障碍的。”④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38页。
1836年7月24日,胡夏米⑤胡夏米,广州鸦片贩子,对华航线船舶投资人,兼英国国内货物经销商。1832年乘“阿美斯德”号自福建至盛京沿海进行侦察活动。致函外交大臣巴麦尊:“我们的对华关系不能让现在这样的反常状态继续下去了。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有两条路可走:第一,这是我要建议采取的,就是直接用武力来对过去的损害取得补偿,对将来取得保障;第二,取消一切政治关系,撤回一切代表,一直等到出现了情况,使我们有权利采取另一种态度来规定贸易条件的时候为止。”⑥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39页。在信函中,胡夏米还列出了对华作战方案。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的作战计划,有许多是依据胡夏米的方案拟定的。
道光十六年(1836),兴泰行倒闭,外商提出索欠2738768元。当时由外商和公行共同成立债务清理委员会,经调查,委员会承认债务为2261439元,另有京官欠外商约100万。外商向两广总督邓廷桢提出由政府负责归还欠款,宣称:“我们有皇帝和阁下的多次承诺,对我们的要求应尽力偿付。天朝是我们的债务人,行商们迄今是偿付的渠道。”①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中华书局,1993,第272页。外商认为,中国政府向来强制旅居广州的英商将货物卖给某些行商,而不得卖予其他人等,中国政府既这样限制英国商人的经营,那么对于它所限定的承办行商,自当负责。所以,英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将各该倒歇行商的欠银,赔还英国债主。②〔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701页。
英商认为,公行这种不合理的贸易方式是他们的财产不能得到合理的保障,导致行商破产及商欠无法偿还的主要原因。公行制度的设计者是清政府,所以,清政府理应成为行商的债务人。他们还向英国政府提交书面申请,要求其干预商欠清偿问题。
1838年3月21日,英国在华21家洋行联名向英国政府递交请愿书,控诉其“合法贸易中所有主要商品的交易都被限于约12家行商或保商”,为了将来的贸易更加安全,他们希望政府关注商人的利益,对中国行商的欠债问题进行“强有力的干预”。③转引自曹英《近代中外贸易冲突及中国应对举措研究》,第208页。
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向义律发出第一号秘密训令,提出与清政府谈判交涉的条约草案。条约草案中有关行商与商欠问题规定,中国政府的行商体制应“停止实行”;以往由这一制度造成的商欠,“由中国政府偿还此数,交英国首席商务监督,或总领事,或英国政府指定的其他人士,由其交付应收者”。④转引自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第331页。巴麦尊所拟条款,后来均作为正式内容写入《南京条约》。
1840年2月20日,英国政府在给全权公使的训令中说明:应要求退还鸦片,如果鸦片已经焚毁,应该要求照价赔偿等办法;行商因为过去享有贸易垄断权而积欠英商的债务应该偿还,这种垄断制度应当取消;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一支足够的兵力立刻封锁中国各主要港口……远征费用应该要求中国偿付。①〔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附录1,第308页。这是一个指导原则。
1841年1月7日,英军攻陷广东沙角、大角炮台,清钦差大臣琦善派鲍鹏去穿鼻议和。1月20日,义律②查理·义律(1801—1875),1836—1840年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1840—1841年任驻华全权公使及商务监督。因未达到英国政府的要求,被召回国。单方面公布了《穿鼻草约》,清政府不承认此约。③熊月之等编著《大辞海·中国近现代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第70页。巴麦尊子爵禀告女王说:“义律大佐似乎已经把寄给他的训令完全置之度外……他好像还是同意了极其不够的条件。鸦片赔款不及被勒缴的鸦片的实价,而且此次远征费用以及倒闭行商所欠英商债款都毫无着落。”④1841年4月10日巴麦尊子爵上女王书,《维多利亚女王书牍》第1卷,第260页,转引自〔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06页。4月30日召开的英国内阁会议议决,英国政府不能批准根据这个初步协定所订立的任何条约,同时召回义律,派璞鼎查爵士前往接替。
巴麦尊子爵致亨利·璞鼎查爵士函(第16号)
因你现在正要启程前往中国,所以我再继续给你一些最后的训令,作为你履行你所负职责的指针。应该坚持的各点是,1839年作为对监督和同他一起在广州遭拘禁的英国臣民的赎金而从英国臣民勒索去的鸦片的全部赔偿;中国政府所应负责的歇业行商的债务的十足偿付;以及英国为雪耻目的而派出的两次远征军赴华所用费用的偿付。⑤〔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附录10,第747页。
1841年4月中旬,英国船队攻击广州城,15日,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广州将军阿精阿、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怡良、广东副都统裕瑞在上报并奏请准其贸易折中写道:“英夷求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付准通商,立即退出虎门,缴还各炮台,不敢滋事。众洋商禀称,只求照前通商,并将历年商欠清还,伊即将兵船全数撤出虎门以外。”⑥《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01-01-004-06-005。奕山等认为“虎门藩篱既失,内洋无所凭依,与其以全城百万生灵,与之争不可必得之数”。奕山等又奏请垫借商欠洋商银两:“查粤东与各国通商近二百年,洋商、夷商彼此交易,历年既久,商欠遂多。节经夷商禀请清理,经各前任监督将积欠最多之洋商斥革监禁,其欠项分与各商摊认归还,此系向来之办法。自十九年停止英夷交易,至今未能归结。兹蒙饬令迅速清理……除商等自行筹措外,尚不敷银280万两,时既仓促,且茶丝各商俱已迁避,一时无可借贷。仰恳将库贮款内,拨借银280万两,由商等俱领以清夷欠,分作4年,在各行生意估价行用内按数摊出,将现借之项全数归补等。”①《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01-01-004-06-005。虽是商欠,但从当时的情形来看,清政府也只能准洋商所请。5月12日,朝廷在发给奕山等人的廷寄中指示:“所有借拨库贮银280万两,着即着落该商,分年归补,不得延宕。”②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卷,中华书局,1964,第146—147页。
1841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条约的内容实际上包含了巴麦尊子爵在两年半前提出的条件。③〔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35页。其中第5款规定:“凡英国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近大皇帝准其嗣后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国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且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300万元,作为商欠之数,由中国官为偿还。”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国家间的战争,其追求的权益,需要通过谈判后改变国际关系来实现。尽管围绕商欠数目、政府垫还的性质存在争议,“商欠之数于官何预,且何从得其确数?”④《清经世文献续编》卷113“洋务”13,清光绪石印本,第2344页。“贸易利归洋商,宜商欠商还,何以官为赔垫?未免公私混淆。”⑤《夷氛闻记》卷4,清刻本,第89页。但是,最终这笔债务写进了条约,清政府被迫接受。英国人认为,清政府对其有管理的权利与责任,同时,也负有担保债务、清偿债务的责任。最终在列强的干预下,行欠由私债变为国债,由商业信用上升到国家信用。
四 结语
经过鸦片战争的酝酿,西方列强要求从根本上打破中国传统对外体制,建立与此完全不同的新关系,即中外条约关系。⑥李育民:《晚清中外条约关系的基本理论探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南京条约》是在英国舰队的炮口和英军即将攻取南京的威胁下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列强由此“揭开了对华事务的新纪元”。①〔英〕菲利普·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胡滨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3页。清政府答应以洋银300万元“官为偿还”。这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中国开始由传统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型,逐步认识西方的财政体制、贸易体制,开始以新的方式建立与国际社会的联系。
第一,近代中国外债时代的到来。
狭义的外债,是指国家外债或公共外债,指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通过借款、发行债券等形式或有政府予以担保而形成的对外国的债务。②张雷宝:《公债经济学——理论·政策·实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第280页。许毅先生指出:“外债是指一国政府采用国家信用形式对外筹集到的和通过其他途径转化而来的债务的总称。中国的外债始于晚清,是指这一时期中央政府举借的或事后承认的各种欠款、借款、赔款转化来的,甚至于以地方政府或个人名义借的外债的总和。外债是国与国之间的资金运动,无论是政府本身举借的,还是以团体或个人名义举借的,一旦发生偿还困难,就会要国家偿还,也就是说,最终的债务人只能是国家。”③许毅等:《近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第40页。
行欠由清政府代为偿还,就把正常的商业信用转变为国家信用,使正常的企业私债变成清政府的国债,从而在英国的压迫下,以特殊的方式开启了中国近代外债的历史。梳理其历史进程,可以用图1表示:

图1 近代中国行欠-外债关系
虽然历史进程表明“官为偿还”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还债款项仍主要由行商摊付,但是国家层面的债务真实产生了。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财政空虚,无论是军费开支、经济建设,还是统治需要都大举外债,开启了借债度日的日子。据统计,到1911年,清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共举借外债208次,债务总额(包括庚子赔款)达到1305888297两(库平银)。④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1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471页。也有学者指出,“近代西方列强利用外债控制中国财政、经济以至政治、军事的侵略活动,可以从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的商欠中找到历史的根源”。①章文钦:《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的商欠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第二,中外关系由“天朝时代”转入“条约时代”。
15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奉行重商主义,通过对外贸易法等推行保护工商业的经济政策,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符合扩大商品出口和货币输入要求。与20世纪西方国家的“凯恩斯主义”相区别,西方重商主义又被称为“原始国家干预主义”。②王涛:《变迁时代的经济与法(1600—1911)》,中国方正出版社,2011,第8页。随着对华贸易的拓展,西方贸易制度与中国经济体制的格格不入越发凸显。1840年3月,莫克·维卡指出:“中国海关要有一部明文条例的海关法规,庶几一方面使中国官吏无权榨取非法的关税,另一方面也使得外国商人不至欺骗中国人。”③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53页。西方人希望中国改革外贸制度,但是,行商制度不具备从内部废除的条件。其一,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晚期,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发展方向是内向的,对外贸易既不发达也不受重视。中国不存在像英国一样能够与垄断势力相对抗的社会力量。其二,行商垄断制度并不是单纯的经济制度,它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是为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服务的。清政府不可能主动从内部废除该制度。④曹英:《近代中外贸易冲突及中国应对举措研究》,第213页。
在中外贸易中,西方人一直试图打破行商制度。嘉庆十九年(1814),英国军舰私入虎门,中国不允,几乎停止通商。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商人因为行商专横,往往欠债不还和征税过重,遣使罗尔美来中国陈诉一切,目的在于取消行商制。但是当时规定,外国人要到总理衙门陈诉,必须先和行商接洽。英使因为没有经过这项手续,所以又被拒绝。英国人三番四次受行商的苛待无处申怨,所以,碰到鸦片战争发生就“借端开衅,以图报复”。⑤张廷灏:《不平等条约的研究》,光华书局,1927,第18页。
《南京条约》第5款规定:“凡英国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近大皇帝准其嗣后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国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1843年中英签订《虎门条约》,其中第8条关于片面最惠国条款规定:“西洋各国商人一体赴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港口贸易,英国毫无靳惜。但各国既与英国无异,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此后,多口通商体制建立,行商制度终结,中国步入不平等贸易时代。自此,中国关税不再由中国做主,同时,关税税收和国家债务紧密相连,成为西方借债的重要抵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