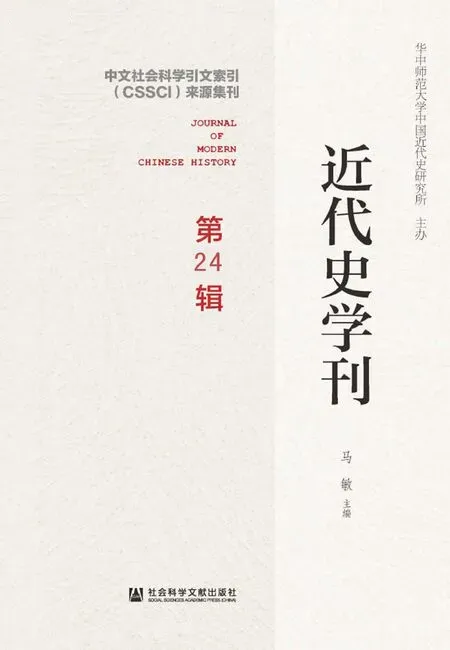人事嬗递与行政实践:清末湖北提学使研究
2021-12-01王静
王 静
内容提要 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是清末地方教育官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聚焦湖北一省,提学使虽由学部奏请简放,但张之洞在世时对实授提学使的选任有重要影响;而暂署者均出自湖北道员,得到时任督臣的信任是其关键;加之提学使任职期间出现的“由学署藩”“由学升藩” “由道署学”现象,均反映出从学政到提学使转变的实质在于提学使成为督抚属官,署任与升转均比照按察使。对于提学使主政下的湖北教育,从立宪背景下承令学部的统一兴学、禀承总督创办存古学堂的湖北经验和学款支绌下因地制宜的勉力维持,可见提学使受学部与总督双重节制,湖北教育逐渐淡化张之洞督鄂时的地域特色而融入学部领导的统一兴学浪潮。
引 言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日(1906年5月13日),湖北学政裴维侒将学政官防文册移交给湖广总督张之洞,料理行装回京供职,①裴维侒:《奏报交卸湖北学政篆务日期事》(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03/5458/201。至此湖北学政退出历史舞台。追溯其因,明清时代学政的主要职责在于主持岁科两试和考校学风。②《清史稿》卷116《职官三》,中华书局,1977,第3345页。清末新式学堂兴起后,事务繁杂艰巨,已非科举时代的学政可以从容应对。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停废,学政更成为闲差。一年后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司获准,此后提学使取代学政掌管地方教育。
关于提学使,已有研究主要回答了为什么设立提学使及提学使的职官特征,①代表性的著作有关晓红的《晚清学部研究》第二章(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六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第七章(三联书店,2014),左松涛的《变动时代的知识、思想与制度:中国近代教育史新探》第六章(武汉出版社,2011),迟云飞的《清末预备立宪研究》第五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吕顺长的《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第二章(商务印书馆,2012),安东强的《清代学政规制与皇权体制》第五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相关论文有霍宏伟《晚清教育转型中学政的角色转变与裁改》, 《学术研究》2012年第3期;王园园:《晚清广东提学使司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14;张寅:《清末提学使司制度建构及实施困境探析》,《历史档案》2019年第3期。论述重心在于清末新政的教育官制改革,但对这一新制在实践层面的运作鲜有涉及。钱穆主张“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②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序”,第1页。受此启发,本文尝试将提学使这一职官放在地方实践中,通过考察人事嬗递及行政作为,进一步分析其在清末地方官制改革中的作用及对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之所以选择湖北作为考察区域,一则因为清末湖北的教育革新走在各省前列,为此后提学使掌管教育创造了良好条件。二则因为张之洞之于湖北的影响巨大,自光绪十五年(1889)任湖广总督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离鄂赴京,造成了“各省考查学制者必于鄂,延聘教员者必于鄂,外省学生负笈远来者尤多”的教育盛况。③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湖北通志馆,1947,第17页。回京后,张之洞充体仁阁大学士、补授军机大臣,但仍“奉旨管理学部事务”,④吴剑杰编《张之洞年谱长编》下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第992页。其对鄂省提学使是否还有影响,亦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关于湖北提学使的研究较为匮乏,一般教育史的著作仅提及湖北新式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⑤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教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李珠、皮明庥编《武汉教育史》,武汉出版社,1999;熊贤君编《湖北教育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还有一些关于个别提学使的论文。⑥洪震寰:《黄绍箕的生平及其教育业绩》,《温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李凤勇:《山东大学创始人——王寿彭》,《山东档案》2007年第2期;王静:《黄绍箕与清末学堂教育研究》,《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张寅《清末提学使司的定制、实践和审思》专辟一节讨论“湖北提学使司与鄂省教育由盛而衰”,涉及部分教育举措,①张寅:《清末提学使司的定制、实践和审思》,《教育研究与实验》2020年第1期。但对湖北提学使的人事嬗递及教育行政,还有非常大的探讨空间。同时,如何认识这一时期张之洞对湖北提学使、湖北教育的影响,亦有讨论的必要。
一 从学政到提学使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学部奏陈各省学务官制折,六月初八日(7月28日)奏续拟提学使权限章程。就官制变革来看,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将学务处改为学务公所作为省级教育行政办公机构。学务公所设议长一人,议绅四人,辅佐提学使“参画学务”并备督抚咨询。此外,公所下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课,分掌各项教育行政事务。各课设课长、副长各一人,课员不超过三员。②后改课为科,“其课长、课员均改为科长、科员,以归一律”。《学部通咨各省本部前奏学务公所分六课为六科文》(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2卷《官制·任用·外交》,荆月新等点校,商务印书馆,2011,第184页。提学使下还设省视学六人,巡视基层学务。各厅州县劝学所,设县视学一人,兼充学务总董,从而确立了一套完整的地方教育行政系统。
提学使由学部奏请简放,秩正三品,为督抚属官,排位在布政使次、按察使前,“总理全省学务,考核所属职员功课”。从学政到提学使,学政的职权主要有主持岁科两试、考校生童教官、宣扬教化、遇事向皇帝密奏等;伴随废科举兴学堂,新制提学使不再具备学政最重要的科举考试权,亦不再作为皇帝耳目制衡地方,而是作为省级最高教育行政长官,拥有了更为广泛的人事任免权和学堂管理权。
具体而言,提学使督饬地方官举办地方学务,除学务公所议长由督抚咨明学部奏派,其他议绅、各课长、副长、课员及省视学,各厅州县劝学所之学务总董、县视学,自高等学堂以下小学堂监督、堂长、教员等皆由提学使聘用委派,外国教员受提学使监督节制。同时,因兴学列入考成,与钱谷刑名并重,提学使还拥有了与藩臬两司会同补署举劾州县官的职权。此外,提学使拥有了一定的教育财权,通省学款可以会同藩司、运司、盐粮关道及税厘、银元、铜元各项局所合力统筹,详请督抚核定。对于提学使的考核,一面归督抚节制,一面由学部考察,受到地方督抚和中央学部的双重领导。①《学部奏陈各省学务官制折并清单》(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学部奏续拟提学使权限章程折附片并清单》(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八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2卷《官制·任用·外交》,第177—181、181—183页。
总体来看,由学政到提学使的转变,核心在于从客差到实缺,提学使成为实实在在的地方官。学部、政务处奏请裁撤学政时,言及“现在停止科举,专办学堂,一切教育行政及扩张兴学之经费,督饬办学之考成,与地方行政,在在皆有关系”,学政“于督抚为敌体,诸事既不便于禀承;于地方为客官,一切更不灵于呼应”。②《裁学政设提学使司折》,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2册,中华书局,1928,第129页。改制后提学使最大的变化就是可以广泛参与地方行政事务,这恰恰是原来学政无法做到的。因此,笔者认同关晓红的判断:“新制提学使作为督抚的正式属官,引发整个直省官制由传统的内外相维格局转向上下有序。”③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292页。
在这样的官制改革背景下,湖北学政迎来了历史性谢幕。最后一位学政裴维侒上任与清末废科举密切相关。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六日(9月4日),光绪帝谕称: “昨已有旨停止岁科考试,专办学堂。所有各省学政,均着专司考校学堂事务,会同督抚办理。所有奉天府府丞兼学政,着改为东三省学政。奉天府府丞一缺,着即裁撤。”④《清德宗实录》卷548,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丙午,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274页下栏。引文中提到的“奉天府府丞”时由裴维侒担任,同一天“裁缺奉天府府丞裴维侒提督湖北学政”,原湖北学政李家驹则调为新设之东三省学政。⑤《清德宗实录》卷548,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丙午,第275页下栏。
裴维侒到鄂接任时雄心勃勃,自言“查荆楚为钟毓人文之地,学政有宣扬风教之权,当兹时局需材、新谟创制,惟有恪遵圣训,注意学堂……俾人知实学之讲求,务得真才之效用”。⑥裴维侒:《奏报到任接印日期并谢恩事》(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03/5450/024。此时学政已无主持岁科考试之责,主要配合督抚考校学堂。尽管裴维侒有宣扬风教、兴办学堂的雄心,在鄂省却未能施展抱负,到鄂不久即因水土不服、积受寒湿呈请开去差使回京供职。或许关外所受积寒使其身体堪忧,但其折中所述“湖北学堂早已办理有年,向由督臣主持”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①裴维侒:《奏为不服水土积受寒湿病症恳请开去学政差使回京供职事》(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03/5458/019。其实,对于湖北新式教育,张之洞作为总督负总责,学务处作为辅助机构具体执行,②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第161页。学政则伴随科举停废丧失了主要职权而成为闲差。
随后,裴维侒呈请开去差使的奏折于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二日(4月25日)奉朱批“已有旨”,同日上谕下达裁撤各省学政。四月二十日,裴维侒奏报交卸学篆的同一天,③裴维侒:《奏报交卸湖北学政篆务日期事》(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03/5458/201。学部奏请简放首批提学使,“湖北提学使着黄绍箕补授”。④(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丁巳,张静庐等点校,中华书局,1958,第5514页。
提学使简放后并未立即赴任,因“提学使司为学堂官绅表率,尤宜亲自出洋,详加考校,借可补充识力,于地方学务实有裨益”,⑤《遴保直省提学使人员折》,《学部官报》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一日,“本部章奏”。朝廷命新任提学使赴日本考察学校制度及教育行政事宜,归国后再行赴任,湖北首位提学使黄绍箕还担任了赴日考察团团长。据此,原有学政回京供职,新设提学使又身在国外,过渡时期湖北教育行政继续由学务处代为主持。
湖北学务处开全国之先,在张之洞推广湖北新式学堂教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光绪三十年(1904),张之洞札令学务处下设审订、普通、专门、实业、游学、会计六科,并调整人事安排——“原派文武管理提调武昌府知府梁守鼎芬应改为学务处总提调”,进一步完善了学务处作为“总司全省教育之区”的职能设置。⑥《札学务处分设六科》(光绪三十年九月初十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6册,武汉出版社,2008,第445页。梁鼎芬本就是张之洞的得力幕僚,担任学务处总提调后更全力协助张办理湖北教育: “香涛调督两江,以至还任鄂督,先生均随其左右,始则主管学务处,大兴新学,凡兴办新政中之文武学堂,及派遣游学,悉惟先生是任,当时未有提学司,一切学务,皆由学务处主理。”⑦吴天任:《梁节庵先生年谱》,台北,艺文印书馆,1979,第258页。
二 湖北提学使的人事嬗递
(一)人事嬗递概况
据黄绍箕自述:“(光绪三十二年)六月遵旨前赴日本考察学务,十月事竣回国到鄂,十二月初八日,奉湖广总督臣张之洞派员赍送部颁印信前来。”①《奏报湖北提学使到任日期折》,谢作拳点校《黄绍箕集》上册,中华书局,2018,第38页。从此(1907年1月21日)提学使登上历史舞台,开启了清末最后五年主政湖北教育的序幕。现将湖北提学使的人事嬗递情况列表如下(见表1):

表1 清末湖北提学使人事嬗递情况统计
从首位提学使简放到武昌起义爆发的五年多时间里,湖北省先后出现了6位提学使。首位提学使黄绍箕是晚清清流派重要人物黄体芳之子,青年时代跟随张之洞学习“古今学派之流别,中外事局之变迁”,深受张之影响。后于光绪十六年(1890)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历编修、侍讲而至侍读学士,科第出身荣尊。黄提学湖北之前在中央和地方已有非常丰富的办学经验。在中央,光绪二十四年(1898)担任京师大学堂总办,“辄本中国教法,参考东西洋学制,手定管理教授规则,是为中国新学之滥觞也”。在地方,与湖北夙有交谊,光绪二十六年(1900)任两湖书院监督期间,“讲堂操场,每日亲自督课,寒暑不辍”,①周邦道:《近代教育先进传略·初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1,第72页。并于此时向张之洞建议改学务处为湖北全省学务处,推动了湖北及全国新式教育变革。因而,黄绍箕虽出自旧学,却有提倡新学、改良教育的进步眼光。
值得一提的是,黄绍箕上任时张之洞尚任湖广总督,两人关系非同一般。黄十九岁师从张学习,三十一岁与张的哥哥张之渊之女成亲,成为张的侄女婿。②《黄绍箕年谱》,谢作拳点校《黄绍箕集》,第942页。光绪二十七年(1901)受到张的保荐:“该员品端学博,沉细不浮,于中西政治纲领、学校规制,实能精思博考,而趣向纯正,力辟邪诐之说,洵为今日切于世用之才。”③《胪举人才折并清单》(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4册,第48页。而其出任湖北首位提学使,据时派在学部参事厅行走的罗振玉所言,是学部尚书荣庆堂上集议,“以提学使应以何资格请简”,罗“意举沈太守曾植、黄学士绍箕、叶编修尔恺”,并得到在场汪康年、张元济首肯。④罗振玉著,黄爱梅编选《雪堂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26—27页。罗振玉曾为张之洞的得力幕僚,罗是否迎合张或得到张的授意值得玩味。
总之,黄绍箕获任应得到了张之洞的认可和肯定,无奈上任一年便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8年1月26日)“病逝于鄂署”。⑤《黄绍箕年谱》,谢作拳点校《黄绍箕集》,第1042页。据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记载:
公好夜谈,达旦而兴犹未已,僚属体弱者视为苦事。光绪三十三年,黄仲弢先生以提学使来鄂,公侄女夫也,每晚必招之议事,仲弢先生因之致疾不起。公挽之云:青蓝教泽留江汉,生死交情痛纪群。⑥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第60页。
黄绍箕去世时,张之洞已离鄂赴京任职,继任的湖广总督赵尔巽在黄去世后的第四天上折报告其病故及在任情况,并委“久办学务、才识俱优”的候补道高凌霨署理提学使,⑦赵尔巽:《奏为委任高淩霨署理湖北提学使员缺事》(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案全宗,04/01/12/0659/155。此外还请旨迅简提学使“以重职守”。可见提学使已成为督抚属官,其署理、简放等事宜均经督抚之手向上呈报。而由高凌霨随后的谢恩折所言“惟有随时禀承督臣认真经理,断不敢以暂时摄蒙,稍涉因循”,①高凌霨:《奏为奉旨署理湖北提学使谢恩事》(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03/5497/064。亦可见其作为督抚属官的小心谨慎。
高凌霨为举人出身,《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对其记录如下:
直隶天津县人,由甲午科举人于光绪二十五年报捐内阁中书,八月到阁行走。二十七年报捐同知,指分湖北试用。二十八年三月到省,因劝办顺直赈捐保俟补缺,后以知府用。三十一年十二月捐过知府班。三十二年四月,捐过道班,仍指分湖北试用。②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7册,第758页。
高出身既非进士之荣尊,仕途亦无翰林之显赫,在清末提学使的选任中具有较大的特殊性。高初到鄂时,湖北巡抚端方将其派充抚署文案处缮校,不久裁同城巡抚,端方交卸时擢其为文案委员,一并移交督署。但当时张之洞幕府人才众多,高未引起张之洞重视。后因一次偶然的文案撰写机会得到张的注意始被重用,并协助张办理学务。③《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4册,第89页。据说高后能获任提学使是受到张的保举:“各省之设提学使,膺简湖北提学使者为黄绍箕,而凌霨在督幕司全省学务如故。其头衔则迭次过班,历府而道矣。未几绍箕因病出缺,时之洞奉召入京,即推荐凌霨继其任,去过道班甫数月,亦峻擢也。”④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上册,中华书局,2018,第162—163页。
张之洞是否推荐高凌霨继任提学使,尚无其他史料佐证,但张举荐高凌霨确实不虚。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二日(8月10日),朝廷下旨“着张之洞迅速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⑤吴剑杰编《张之洞年谱长编》下册,第981页。离鄂之前张之洞上奏举荐了高凌霨、齐耀珊、邹履和三人,举荐原因为“近来举办新政,在在需才”,给高凌霨的荐语为“心地光明,才器干练,剔除积弊,甚有担当”,随后光绪帝朱批“高凌霨等均着交军机处存记”。⑥张之洞:《奏为举荐湖北试用道高凌霨等员历委要差成效可观请量予录用事》(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03/5487/004。说明在张之洞即将离鄂时,高凌霨是其非常重视的地方人才,这也是他为湖北新政预谋人才之举。
高凌霨前有张之洞的举荐,后有赵尔巽让其暂署提学使,可谓得到两任总督的信任与认可。署理不久,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二日(2月13日)奉上谕“湖北提学使着高凌霨补授”。①高凌霨:《奏为奉旨新授湖北提学使谢恩事》(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03/5500/007。高的任职时间最长,达两年七个月,但在任期内两度署理布政使。第一次是宣统元年(1909)冬,因湖广总督陈夔龙赴京陛见,布政使杨文鼎暂时护理总督,故委派提学使高凌霨署理布政使、江汉关道齐耀珊署理提学使。②《陈制军奉谕入京陛见》,《申报》1909年12月1日。第二次是在宣统二年(1910)春,因布政使杨文鼎被调署湖南巡抚,湖广总督瑞澂委派提学使高凌霨再次署理布政使,并令署按察使(盐法道)马吉樟署理提学使。③《汉口函》,《申报》1910年4月24日。其后由于马吉樟奉旨接任按察使并请旨陛见,瑞澂又改派候补道李孺署理提学使。④《派员接署学篆》,《申报》1910年6月14日。
齐耀珊、马吉樟、李孺均为暂署提学使,三人的共同点在于均为湖北道员,对湖北地情较为熟悉。前所提及张之洞举荐高凌霨的奏折也举荐了齐耀珊,评语为“见事明敏,才具开张,公余忘私,不为利疚”。⑤张之洞:《奏为举荐湖北试用道高凌霨等员历委要差成效可观请量予录用事》(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03/5487/004。马吉樟曾被学部奏派赴日本考察政治,后奉旨补授湖北盐法武昌道,宣统元年“因订造炮舰,经费解清,筹款无误,经调任湖广总督陈夔龙奏保,交部从优议叙”。宣统二年三月初十日(4月19日)经署理湖广总督瑞澂委署提学使,“是月十三日到任,二十三日奉旨补授湖北按察使……四月十七日奉朱批着来见,遵于五月初三日交卸学篆”。⑥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8册,第541页。李孺于光绪三十年正月经前兼署湖广总督端方派充日本游学生监督,任职期间张之洞多次发给李孺电文,内容涉及各种游学游历事务。宣统三年,李孺还得到湖广总督瑞澂奏请从优议奖。⑦《会奏议覆鄂督奏湖北试用道李孺请奖折》,《学部官报》宣统三年三月初一日,“本部章奏”。以上三员在湖北任事多年,均得到时任督臣的认可与推荐,且与经营湖北近二十年的张之洞关系匪浅,这或许是实授提学使临时离任时得以兼署的重要原因。
宣统二年八月二十四日(9月27日),曾两度兼署湖北布政使的高凌霨因原布政使王乃徵调任河南布政使,成功获任藩司,⑧《清实录(附)宣统政纪》卷41,宣统二年八月乙未,第738页上栏。第二天王寿彭补授提学使,①《清实录(附)宣统政纪》卷41,宣统二年八月丙申,第739页上栏。直到武昌起义爆发后与总督瑞澂等弃城逃跑。王寿彭虽出自科举旧学,但其进身之途与传统科举应试有很大不同。王以癸卯科(1903)状元授职翰林院修撰;后入进士馆修习法政,毕业获最优等;光绪三十三年由学部给咨赴日本考察学务;回国后学部奏调为图书局行走。②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8册,第517页。据韩策的研究,“癸卯、甲辰二科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两科会试,亦是清季科举改制在会试层面的实践”,③韩策:《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172页。科举改制一为光绪二十七年颁行考试新章,以废八股、罢试帖,改试论、策、经义,废誊录等为内容;二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变通新进士章程,诏开进士馆,令新科进士授京职者入京师大学堂肄习法政等“新学”,接受学堂教育。④韩策:《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第117页。由此看来,王寿彭可算是科举改制后应试的佼佼者,不仅有中学功底,还修习法政,赴日考察学务,出任湖北提学使亦可反映“最后的进士”的时代命运及清末最后几年取官用人的面貌。此外,与前几任提学使相比,王寿彭并无任职湖北的地方经验,亦未发现其受到鄂督举荐的踪迹,由京官直放学司,在湖北提学使群体中具有很大的独特性。⑤据说王寿彭以修撰实授提学使,出自学部尚书荣庆之力。“荣督学山东时,寿彭以岁考一等补廪,受知甚早也。”《凌霄一士随笔》下册,第1615页。
(二)提学使与总督、藩臬关系
由上一节的分析可以看出湖北提学使的任用部分沿袭了科举时代的选官特点,如进士出身与否仍是朝廷任命提学使的重要参考因素。但亦出现了新的动向,如少量提学使出自举人,功名较低却同样获任;大多数提学使拥有赴日考察经历;提学使实际在任时间较短,更动频繁;等等。正是这些新动向折射出清末取官用人的特殊风貌。此外,湖北提学使的人事嬗递还具体呈现出其与总督、藩臬二司的关系。
关于提学使与总督的关系,黄绍箕获任与总督张之洞关系密切;高凌霨先署后补,均得力于督臣赵尔巽,而其自身又与张之洞颇有渊源;高任职期间三位暂署者均为湖北道员,不仅熟悉湖北地情,亦深得督臣的信任与认可。光绪三十四年湖广总督陈夔龙的一份密考清单恰好可以说明问题:
湖北省布政使李岷琛,才猷老练、器识宏深、资劳并著、能持大体。提学使高凌霨,清刚拔俗、有守有为。按察使杨文鼎,干练精明、才足肆应,遇事举重若轻……盐法武昌道马吉樟,稳练安详、克尽其职。汉黄德道齐耀珊,心精力果、措施裕如,于外交尤多补救……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25辑,中华书局,1995,第670页。
也就是说,对于临时署理的提学使,地方督臣具有重要的选择权,如果地方道员得到督臣的认可,极可能临时兼署学司。
最后一位提学使王寿彭并无湖北经验,且以京官直放学司,与前几位任职者形成鲜明对比,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清末强人张之洞对湖北的影响逐渐弱化。张之洞督鄂时对提学使人选的影响是明显的;到京后恰逢管理学部事务,负有考核甄别提学使之责,②张之洞:《奏为续保堪升堪署提学使人员缮单呈览事》(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03/5497/043。因而亦有可能影响到湖北提学使的选用。实际上,在张生命的最后两年——管理学部期间,湖北提学使的人选大致符合其期待。然而,张病逝后再也无法左右湖北提学使的人选,新起之秀王寿彭的获任也体现了这一点。
关于提学使与藩臬二司的关系,笔者想从三司互动的角度加以探讨。首先,高凌霨任职期间两度署理布政使,王寿彭亦曾暂署布政使:“窃臣于宣统三年闰六月初六日,奉湖广总督臣瑞澂行知湖北布政使余诚格现奉电传谕旨升授陕西巡抚,所遗布政使篆务委臣兼署。”③王寿彭:《奏报兼署湖北藩篆日期并谢恩事》(宣统三年闰六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03/7458/013。就传统人事任用来看,“凡百官之任,有管理以重其务,有行走以供其职,有加衔以显其秩,有稽察以慎其法,有兼充以省其官,有差委以寄其责,有分发以练其事,有署理以权其乏,与额缺官相辅焉”。其中“有署理以权其乏”明确规定:“总督、巡抚印务或互相署理,或以藩臬护理。藩臬印务或互相兼署,或藩以臬署,臬以道署。有奉特旨者,有由督抚奏请者,其道府署印皆令奏闻。”④光绪朝《大清会典》卷7《吏部·文选清吏司一》。也就是说藩司乏人即以臬司署理,臬司乏人即以道员署理,但从高凌霨、王寿彭的经历来看,提学使亦可署理藩司。同时,齐耀珊、马吉樟、李孺均以道员暂署提学使,与“臬以道署”的成例亦相仿,可见学臬二司在相关署理方面相似。
此外,高凌霨后由提学使补授布政使,马吉樟署理提学使期间奉旨补授按察使,从中可窥见提学使的升转情形。 《钦定吏部铨选则例》规定,“从二品各省布政使开列具题,由各省按察使升任,升太常寺卿、光禄寺卿、太仆寺卿、各省巡抚”,“正三品各省按察使开列具题,由各省运使、道员升任,升通政使副使、大理寺少卿、各省布政使”。①(清)锡珍等撰《钦定吏部铨选则例汉官品级考》卷一,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7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239页下栏、第241页上栏。魏秀梅的研究亦证明了这一点: “嘉庆朝至光绪朝,由按察使升布政使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余者亦有由运使、道员超擢者。”②魏秀梅:《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布政使之人事递嬗现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1971年第2期,第525页。而提学使这一新职官的出现则突破了“由臬升藩”“由道升臬”的成例,也就是说提学使亦可任布政使、按察使。
此为湖北一省经验,放大到全国来看,清末先后出现了59位提学使。③统计提学使人数时,以《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中“学部奏派各省提学使姓名及任职时间表”和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中记录的各省提学使名单为底本,进一步查阅《清实录》以重新订正,并根据《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清史稿》《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以及各类年谱资料等对个人信息进行核查确认。进一步分析每位提学使的入仕履历,发现多位提学使拥有署、任布政使、按察使(提法使④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一日(8月25日),按察使改成提法使。)的经历,具体情况如下(见表2):

表2 清末提学使与藩臬两司的互动关系
表2中共有22位提学使的任职经历与布政使、按察使密切相关,占总人数的37.29%,可见湖北提学使与藩臬两司的任职互动并非一省独有,而是提学使职官产生后一种新的用人趋向。其中最普遍的情况为“由学署藩”,即在提学使任职期间兼署布政使,亦有3人由提学使升授布政使。而提学使与按察使之间的署、授则较少,比较特殊的是出现了两人“臬学互调”的现象:“调云南提法使秦树声为广东提学使,以广东提学使沈曾桐为云南提法使。”①《清实录(附)宣统政纪》卷50,宣统三年三月己亥,第890页上栏。
综合来看,出现以上各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提学使“照各直省藩臬两司,例为督抚之属官”,在布政使之次、按察使之前。从品级来说,布政使秩从二品,提学使、按察使均为正三品,且“提学使由四五品京堂及实缺道员简任者,升转与臬司同”。②《学部奏陈各省学务官制折并清单》(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2卷《官制·任用·外交》,第178页。提学使与按察使品级相同,提学使的升转亦比照按察使的成规,因而出现了“由学署藩” “由学升藩” “由道署学”等多种情况,这也是从学政到提学使的一大变化。
三 提学使主政下的湖北教育
自近来水陆交通,四方辐辏,风气虑或稍杂,故管理为最难。臣惟有恪遵谕旨,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随时禀承督臣,认真经理,务使人知爱国以挽浇风,士皆成材以应急用。③《奏报湖北提学使到任日期折》,谢作拳点校《黄绍箕集》,第38—39页。
这是黄绍箕上任时秉持的办学宗旨。一方面, “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与光绪三十二年学部颁布的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相适应,为提学使行政奠定了基调;另一方面,黄所言“禀承督臣,认真经理”深刻反映出从学政到提学使之变——从学政与督抚地位齐平,到提学使成为督抚属员受其节制。实际上,提学使在地方既要承学部之令施政,又要禀承督抚有所革新,这就使其主政下的湖北教育既有统一兴学的色彩,又充满湖北经验。
(一)承令学部——立宪背景下的统一兴学
清末新政改革中新设立的学部作为“总汇之区”,对全国学堂教育“以资董率而专责成”,④《清史稿》卷107《选举二》,第3143页。而普及教育是其兴学的重心。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8月27日),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将所拟宪法大纲、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及议院成立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会奏。该清单中关于教育者有7条,主要内容为编辑及颁布简易识字课本和国民必读课本、创设厅州县及乡镇简易识字学塾等,旨在普及教育,提高人民识字率及知识水平,进而有利于立宪顺利推行。①(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四年八月甲寅,第5976—5984页。
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八日(4月18日),学部根据这一清单,以九年为期分年胪列了兴办教育的各项事务,宣统元年应举办者主要有分编中小学各科教授细目、筹设简易识字学塾、推广城镇乡两等小学堂,以及筹设省城优级师范、中等实业、各府中学及初级师范学堂等。宣统二年主要包括继续筹定师范、普通、实业、专门四项教育等。②《通行各省分年筹备事宜文》,《学部官报》宣统元年十月初一日,“文牍”。学部在宪政编查馆筹备事宜清单的基础上对各项教育行政进行了扩充,包含了不同类别、级别的学堂教育措施,并饬令提学使司一体遵照,同时特别申明提学使的职责:
该提学使司不得因循玩愒,致误限期,亦不可粉饰外观,有名无实。至以后每年仍每届六个月将已办成绩先期送部考核具奏,以符定章……该提学使身负教育重任,倘未能督饬所属实力奉行,届时均有难宽之责。③《通行各省分年筹备事宜文》,《学部官报》宣统元年十月初一日,“文牍”。
从中可见学部对提学使自上而下的严格领导。就湖北省而言,在原来兴办的新式学堂基础上,从省城到府再到州县各级,师范、普通、实业、专门四项教育均按部令筹设。④《督部堂陈奏遵章胪列第二届筹备宪政成绩折》,《湖北官报》宣统元年九月二十日,“本省公牍”;《本司详督宪遵报宣统元年下学期关于宪政筹备事宜文》,《湖北教育官报》宣统二年二月,“文牍”。时任提学使高凌霨主要行学堂筹办及管理之责,如宣统元年将汉阳府道师范学堂改办完全师范学堂、在夏口厅开办商业中学堂等。⑤民国《湖北通志》卷60《学校志六》,商务印书馆,1921,第1593页上栏。高凌霨重视发展师范、实业教育,其行政作为亦受到湖广总督陈夔龙的赞赏:“高凌霨开敏通达,办事认真,惟日孜孜以振兴专门、实业,推广小学为要义。臣督鄂瞬将两载,深资赞助。”⑥《督部堂陈奏湖北去今两年新办各项学堂情形请敕部立案折》,《湖北官报》宣统元年十月三十日,“本省公牍”。可见提学使承令学部兴学亦需要地方督抚的积极配合与支持。
至于筹办简易识字学塾,目的在于“辅小学教育之不及,而期以无人不学为归”。根据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应从宣统元年开始,由学部和各省督抚同办。但学部奏拟的《简易识字学塾章程》于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10年1月10日)才奉旨通过,①《奏遵拟简易识字学塾章程折(并单)》,《学部官报》宣统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本部章奏”。故各省实际开办的时间是在宣统二年。宣统二年三月初八日(4月17日),高凌霨遵照学部颁发的《简易识字学塾章程》饬令地方官员及学务人员:
凡官立、公立、私立各项学堂均可附设此项学塾,即穷乡僻地尚无学堂者亦可租借祠庙及民房随处设立,图书器具不必求备,教员科学不必求全,但令期月之间学堂可增一倍,贫寒子弟无论少长均可就学。盖学堂多一读书之人即地方多一明理之人。地方官绅及劝学所视学总董均有提倡教育之责任,限文到五日内将本司所编白话告示随即照刊,广为传布,刻期举办。②《本司札各属遵设简易识字学塾文》,《湖北教育官报》宣统二年,“文牍”。
提学使所负之责主要有两个方面,上则须每半年向学部汇报本省简易识字学塾办理情形,下则须认真考核地方官及劝学所总董实地兴办之况,“其成绩较优者量加奖励,不力者轻则记过,重则详请督抚参办”。③《奏遵拟简易识字学塾章程折(并单)》,《学部官报》宣统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本部章奏”。到该年十月左右,提学使向总督呈报办理情况称:“推广厅州县简易识字学塾一条……陆续开办者计全省共一千零七十所,学生约二万二千四百有奇。至有学塾业已开办而学生名数未经开列者,亦暂从缺如,以期核实。”④《本司详报督宪湖北已办简易识字学塾表文》,《湖北教育官报》宣统二年十月,“文牍”。
看似成效显著,实则存在兴办过速、欲速则不达的问题。高提学曾要求各厅州县“一月之内务将办理情形具报”,“二十州县业经电复外,其余各属究竟已否照章开设限五日内据实电禀,如有未经开办者,亦限五日内一律办讫。大县至少须开三十堂,中县至少二十堂,小县至少十堂”。⑤《致各府厅州县电》,《湖北教育官报》宣统二年四月,“文牍”。如此过急过速,导致出现了“除广济外其余禀报开学甚少”的问题。⑥《湖北教育官报》宣统二年四月,“文牍”。此外还造成了停办初等小学专办简易识字学塾的本末倒置,如学部致电湖广总督及提学使称:“至简易识字学塾,系为年长失学者而设,不过为初等小学之补助。前闻各省间有停办初等小学专办简易识字学塾者,有将初等小学改办简易识字学塾者,既非立法之本意,且于初等教育之进行不无障碍。”①《北京学部来电》,《湖北官报》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要电”。可见从上至下要求过急过速,并不符合地方实际教育情况,结果难尽人意。
以上可视为预备立宪的第一阶段。宣统二年十月初三日(11月4日),清廷谕令缩改预备立宪时间,于宣统五年开议院。②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第78页。随后宪政编查馆修正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以“巡警、教育等项属普通事务”为由从清单删除,并命令“按照原定清单分别最要次要,妥筹办理”。③《清实录(附)宣统政纪》卷47,宣统二年十二月丁亥,第834页下栏。此后学部奏报了《普及教育办法分别最要次要清单》。④《奏酌拟改订筹备教育事宜折(并单)》,《学部官报》宣统三年二月十一日,“本部章奏”。
此时的提学使为王寿彭,他将湖北学区划作省城和府州县分别推行。就省城而言,主要是倡导私塾改良,以补学堂不足,“先于省城切实试办,责成学务公所普通科经理,会同江夏首县劝学所筹商,依照警察划分区域,先之以调查,次之以劝导,分区设立研究所,讲授单简管教方法”。就府州县各属,则奉学部之令提前赶办初等小学。但限于学款不支的困境,王寿彭拟定:“自宣统三年起所有官立初等学生未能足额或办理无效者应即改为公立学堂,就地筹款。其腾出官款即拨为补助私立学堂及奖励教员之用,所有半日学堂及简易识字学塾均仿照办理。又饬各属酌量情形,设立单级教授及塾师改良研究所、体育会、教科书发行所等。”⑤《本司详学部具报到任后办理学务情形文》,《湖北教育官报》辛亥第8期,“文牍”。旨在府州县各属推广公立、私立学堂,借助地方自治力量筹资兴学,普及教育。
(二)禀承总督——保存国粹的湖北经验
提学使是督抚属官,教育行政亦受督抚节制,这里必须提到的就是地方强人张之洞督鄂末期对湖北教育的影响,而时任提学使黄绍箕是禀承总督、精诚合作的典范。
张之洞在发展新式学堂教育时已关注保存国粹,“学失其本则无学,政失其本则无政”,由其筹定的癸卯学制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⑥《学务纲要》,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2册,第12页。光绪三十年黄绍箕尚未提学湖北时,张之洞就曾致电黄,提出兴办存古学堂以保存国粹:“近日风气,士人渐喜新学,顿厌旧学,实有经籍道息之忧,故拟于武昌省城特设存古学堂,以保国粹……救时局,存书种,两义并行不悖。”①吴剑杰编《张之洞年谱长编》下册,第831页。并请黄劝说孙诒让前来就任学堂监督。②黄绍箕与孙诒让同为浙江瑞安人,交往颇深,合称“瑞安二仲”。因而在湖北创办存古学堂是张之洞由来已久的想法。
光绪三十三年,设立存古学堂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黄绍箕作为提学使“禀承督臣,认真经理”,主要协助制定学堂章程及延聘师资。延聘师资是一大难事,黄绍箕前曾延请孙诒让,孙的回信以“意兴阑珊,凡百灰心,亦必不任鞭策”为由婉拒,虽另向黄推荐宋育仁和林颐山,但终未成行。③孙诒让:《答黄仲弢书》,张宪文辑,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温州文史资料》第5辑《孙诒让遗文辑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139页。到该年七月开学时,先后延请的孙诒让、曹元弼、赵炳麟等均不就,无奈之下张之洞只能自任监督,以黄绍箕为提调,原勤成学堂总教习杨守敬为总教习。④吴天任:《杨惺吾先生年谱》,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第140页。初办之时师资难得,以致“开馆之日,讲席犹虚”。
从该学堂后续发展来看,学部在宣统元年将“图书馆暨存古学堂则并应按期举行,一律开办”写入《次年筹备事宜折》。⑤《奏遵章陈明次年筹备事宜折》,《学部官报》宣统二年二月十一日,“本部章奏”。四川提学使赵启霖“特委学务公所总务科副长冯家玮来鄂调查办法”,⑥《调查存古学堂及图书馆》,《湖北教育官报》宣统二年四月,“纪事”。四川总督赵尔巽在宣统二年上奏将“参酌鄂苏办法暂定简章”。⑦《四川总督赵尔巽奏筹设存古学堂折》,《学部官报》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京外奏牍”。因此,对于创办存古学堂保存国粹,湖北确开全国风气之先,并得到学部认可在全国推行,实与张之洞、黄绍箕的早期擘画密不可分,亦是湖北提学使禀承总督施政进而将湖北经验推向全国的重要体现。
但应注意到,湖北创办存古学堂并非完全成功。光绪三十四年学部奏派右参议戴展诚等前往各省查学,对湖北、江苏之存古学堂的调查结果为“意在保存数千年相传之文学,然未免仍沿书院之旧习”。⑧《学部奏派员查学事竣大概情形折》,《湖北教育官报》宣统二年七月,“章奏”。说明学部对此并不满意,实则湖北官方亦不满意。据郭书愚的研究,“张之洞在湖北存古学堂正式开学后即离鄂进京,尽管他对该校乃至湖北学务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但该校的实际运作自开办伊始即与张氏的办学理想大异其趣,尤其体现在课程教学和校务管理方面”。①郭书愚:《开放而不失其故:张之洞兴办湖北存古学堂的努力》,《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6期。张离鄂赴京后,就兴办存古学堂与继任总督赵尔巽、陈夔龙,提学使高凌霨等多有电文往来,然而毕竟鞭长莫及,该学堂虽一直持续开办到武昌起义爆发,但其保存国粹在“救时局”的时代环境中并未取得显著成效。
(三)因地制宜——财政支绌的勉力维持
前两节主要从承令学部和禀承总督两个角度来分析新制提学使施政兴学,但两者不可能完全区分,很多情况下需要提学使因时制宜、灵活应对,筹集学款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证。
财政支绌是新政改革过程中全国性、普遍性的困境,在湖北尤为突出。这是多年累积愈演愈烈的结果:“鄂省财政自升任督臣张之洞兴学练兵、购造军舰以及筹办一切新政,百端具举,久已入不敷出。”②《督部堂瑞奏鄂省本年试办预算不敷甚巨遵议切实增减折》,《湖北官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奏议”。
黄绍箕提学湖北时已面临学款支绌,黄曾亲自捐款助学,“甫视事以学务款绌,首捐廉俸二千余金为省会初等小学堂经费,续设专门实业各学堂”。③伍铨萃:《黄绍箕传》,谢作拳点校《黄绍箕集》,第767页。而高凌霨提学期间,窘境有增无减。宣统元年、二年高凌霨分别参加了湖北谘议局第一次、第二次常年会议。两次会议关于学务的核心议题都涉及学款不敷导致办学困难。就学款如何使用的问题,督抚、提学使和谘议局议员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矛盾重重。谘议局议员认为办理学务不应重内而轻外,致州县学务毫无起色;督抚和提学使则坚持主张省城学务当先,应移缓就急。④《湖广总督札复》,吴剑杰主编《湖北谘议局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第136—141页。
等到王寿彭上任之前,湖北财力困窘尤甚,甚至出现了各学堂经费短缺、开学甚少的状况:“将川、淮盐要政加价提拨四分之三改作赔款。各学堂因经费无着,以致同时观望。”⑤《呈请咨达度支部将川淮盐要政加价仍归专办学款文》,吴剑杰主编《湖北谘议局文献资料汇编》,第348页。因而,王寿彭兴学时时考虑经费问题,并因经费短缺而停办、归并学堂,如停办方言学堂、安襄郧荆道合办之初级师范学堂、郧阳府高等小学堂,将施南府模范初等小学堂移并府署龙神庙多级小学堂内。当然,王并非盲目停办、归并,而是尽量调整学堂结构,兼顾变通。如停办方言学堂,是在湖北高等学堂即将开办、中学堂亦复渐次添设的基础上,随后又开办德文研究所以弥补不足。停办道初级师范学堂,是因各府即将开办府初级师范学堂。总之,当学款有限之时,教育行政的重心就在于撙节经费,使有用之款不至于消耗于无用之地。
宣统三年,全国试办预算。具体到湖北省,自宣统二年已开始清理财政,主要是裁撤各类财政局所,设立度支公所,统归藩司经办。①《湖广总督瑞澂奏湖北第四届筹办宪政情形折》(宣统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786页。至此,湖北藩司统一掌管财政事务,教育经费收支各款也一律由其负责。提学使原需会同藩司、运司、盐粮关道及各项局所合力通筹学款,现在则只需明确学务经费的预算。
宣统三年预算案具体从四月初一日(4月29日)开始实行。为明晰预算时期各学堂收支情况,王寿彭首先饬令:“凡四月初一日以前各堂结存之款,无论数目多寡应一律缴还本司衙门核收转解。”②《本司移(札)各学堂四月以前存款应缴本司衙门核收转解文》,《湖北教育官报》辛亥第8期,“文牍”。其所言“转解”应指由提学使司转还给布政使司存储。而各学堂预备经费,则按照各堂学生、班数分别核定,按月发放,并特别申明“如班数不足,原领经费应有盈余,即由各堂按月将余款划出,具文缴解本司衙门核收,以便缴还藩司衙门存储备拨。幸勿(毋得)多糜学款,与原案不符”。③《本司移(札)各学堂应余学款按月解由本司缴还藩署存拨文》,《湖北教育官报》辛亥第8期,“文牍”。然而,从其呈给学部的情况看,办理预算并非得心应手:“惟鄂省此次预算案仓猝成立,疏漏颇多,原定各学堂经费恐实有入不敷出之处。”④《本司详学部具报到任后办理学务情形文》,《湖北教育官报》辛亥第8期,“文牍”。
总之,伴随清理财政、试办预算,湖北由藩司统一掌管财政,提学使不必再像从前苦于筹措经费,反而如释重负。如王寿彭所言:“兹幸财政统一,教育费收支各款概移藩署主持。本司自可一意兴学,不似从前多所牵制。”⑤《本司详学部具报到任后办理学务情形文》,《湖北教育官报》辛亥第8期,“文牍”。
四 结语
关于湖北提学使的研究,笔者尝试发掘官制背后的人事因素及行政实践。
就人事嬗递而言,提学使虽由学部奏请简放,但张之洞在世时对实授提学使的选任有重要影响。三位暂署者均为湖北道员,熟悉地情是其优势,得到时任总督的信任与认可则是关键。最后一任王寿彭乃京官外放,既无湖北经验,又非督臣举荐,展示了张之洞病逝后提学使获任的新面相。通览六位提学使的任职经历,“由学署藩” “由学升藩” “由道署学”的现象恰恰反映出从学政到提学使转变的实质在于提学使成为督抚属官,列布政使次、按察使前,署任、升转均比照按察使。这非湖北一省独有,而是新制提学使取官用人的新趋向。
在此基础上观察提学使主政下的湖北教育,一方面受学部节制,扮演着承令中央、贯彻地方的角色。提学使在普及湖北地方教育过程中的按部就班深刻展现出学部统一兴学的色彩。另一方面禀承督臣,施政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保存国粹是张之洞兴学后期的一大特点,据此其领导的湖北经验与直隶经验各放异彩。①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第193页;陆胤:《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293—294页。提学使侧身其间,在将湖北经验推向全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得不提的是,随着张之洞离鄂赴京,继任总督在兴学方面无甚谋划,湖北教育的走势亦反映出学部统一制定全国兴学规章后,地方兴学的特色逐渐削弱,张之洞对湖北教育的影响也越来越淡化。
当然,关于兴学的其他面相,如留学教育、整顿学风(严禁学生剪辫、赌博、私议开会等)、筹办图书馆及公园等,因本文非专篇探讨教育并未涉及。总体而言,湖北教育在各位提学使的统筹管理下有所发展,但已不复张之洞督鄂时的教育盛况。新式学堂教育的发展客观造成社会风气开化,提学使主管学堂教育却无法完全控制学生思想,辛亥之际武汉成为起义首镇,提学使王寿彭与总督瑞澂等弃城逃跑,可谓辛辣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