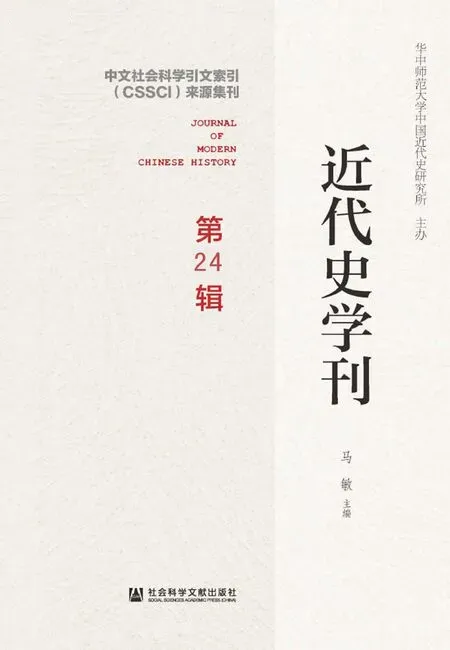慈善群团与都市社会治理*
——以民国时期上海慈善团为例
2021-12-01阮清华
阮清华
内容提要 辛亥革命后,上海老城厢各个慈善组织合组上海慈善团,经过不断扩张、壮大,发展成为一个涵盖各类慈善事业的大型慈善群团。上海慈善团拥有数量庞大的房产和地产,有着相当稳定且随着都市化的发展而不断增加的收益,并由于其在上海的历史地位而可以获得众多各类捐款。受益于上海都市化发展而获得稳定经费来源的慈善团,机构庞大、经费充沛,带领其他众多慈善组织在上海都市社会治理中之收殓掩埋、拯溺育婴、收容教养游民乞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慈善组织朝着规模化、跨地域合作方向发展的趋势,表明近代上海慈善组织发展的主流并非“小社区化”。
梁其姿认为,中国传统慈善组织到19世纪中期后出现了“分散地设立在较小社区的基本特点”,“不能有太大的规模,以免有夺县政之光之嫌”,也即传统慈善组织出现了“小社区化”倾向。①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253、248页。但在开埠后的上海,却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倾向,即综合性慈善组织的扩张和发展,形成规模巨大的慈善群团。这些慈善群团不仅继续举办原有善举,而且从组织、资金以及慈善活动等方面不断加强联系与合作,在近代上海都市社会发展和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立于1912年的上海慈善团,是民国时期上海最大的民间慈善组织,也是慈善群团的主要代表。本文以上海慈善团为例,分析慈善群团在近代上海都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进而探求中国传统民间组织的生命力和适应性。
上海慈善团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慈善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现有研究中提到它的仅有数篇论文,且大多一笔带过。①梁元生:《慈善与市政:清末上海的堂》,《史林》2000年第2期;李学智:《1923年中国人对日本震灾的赈救行动》,《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张礼恒:《略论民国时期上海的慈善事业》,《民国档案》1996年第3期;张化:《试论地方政府与教会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2期。小浜正子认为上海地方自治运动推动了上海慈善团的成立,并从社团史的角度重点介绍过慈善团在上海市政厅管理下建立贫民习艺所与新普育堂的情况,认为“与以往善堂相比,上海慈善团的理念和活动内容都开始发生很大变化。它以济贫和职业教育为中心,试图解决贫困等社会问题”。②〔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葛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52—53页。关于上海慈善团本身的状况、它在近代上海慈善事业中的地位以及它在近代上海都市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则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 上海慈善团的构成
1912年3月,上海老城厢各慈善组织主事人假座同仁辅元堂,共商慈善大计,正式决定成立上海慈善团,由“市区旧有之同仁辅元堂、果育堂、普育堂、育婴堂、清节堂、保节堂、全节堂、同仁辅元分堂、施粥厂、救生局暨新成立之新普育堂、贫民习艺所”等组成。③杨逸编《上海市自治志——各项规约、规则、章程》丙编,《上海市政厅章程——慈善团办法大纲》,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吴馨等修,姚文枏撰《上海县志》,1935年刊本,第699页。慈善团设立董事会,作为全团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处理慈善团的主要事务,对慈善团所属团体的财产统一收支、统一管理,根据需要,统筹规划,以便更好地适应时代变化的特点,更加充分地利用现有资源。董事会设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各一人,由董事会推举产生。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对外代表慈善团,负责全团事务。成立初期董事名额没有限制,可以随时按照章程增补,但是,“为实行负责办事起见,由董事中公举常务董事七人,执行本团事务”,分管总务、财产、建设诸事宜。董事会每月中旬开会一次,由董事长召集之,如有特别事项,得开临时会议。④据《上海慈善团章程》,上海市档案馆藏,R15-2-71。1912年5月,上海慈善团组织参议会,每四周开会一次,“提议本团事件,以期集思广益,有裨善举”。①《慈善团事务所报告》,《上海市公报》1912年第1期。董事会、参议会这些新型组织形式越来越多地被慈善团体采纳,实际上正是近代上海民间慈善组织适应都市社会发展变化、更好推进慈善事业的举措。
上海慈善团在同仁辅元堂设事务所,由慈善团董事会领导,处理全团具体事务,“酌盈剂[济]虚,统一办理”上海的慈善事业。1911年上海地方自治机构——上海城自治公所改组为上海市政厅,管理包括慈善在内的地方事务。市政厅试图对上海民间慈善事业进行全盘规划和整合,因而慈善团刚一成立,市政厅即命令将其所属各善堂业务分类调整,划分为六科:第一科办理恤嫠、赡老、矜孤和济贫;第二科办理施棺、赊棺、赊葬、义冢;第三科办理育婴、保赤;第四科办理养老院、残废院、贫病院;第五科办理贫民习艺所;第六科办理妇女工艺院。同时规定,各善堂向来办理之黄浦江救生移交给警务、水巡等部门;向来办理之义学、义塾移交给学务科;向来办理之救火水龙改隶救火联合会;向来办理之施医施药改隶卫生科。但市政厅强调调整工作要循序渐进:在养老、残废、贫病各院成立以前,原有之普育堂照旧办理;妇女工艺院成立以前,原有之清、保节堂照旧办理;卫生科完全成立以前,医药事宜暂由事务所照办。②《上海市政厅慈善团办法大纲》,《上海市公报》1912年第1期。据此,上海慈善团将走上专业办理慈善事业的道路,不再兼顾救火、义学、施医施药等工作。此举表明上海民间慈善组织在地方绅商领导下尝试进行大规模整顿,试图将自发无序状态调整到协调发展,朝着专业化和分工合作的道路前进,以更好地解决都市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这也是上海民间慈善事业的第一次整合,不仅将失去官款资助而难以维持的果育堂、普育堂等整合进慈善团,而且试图全盘统筹慈善事业的发展。
上海慈善团依据市政厅命令,对所属各善团业务进行初步归并和调整,将相同或相似业务并入同一机构办理,统一救济名目和救济标准,尽力做到统一规划,以利慈善事业之持久。③《慈善团各种条约案》,《上海市公报》1912年第1期。然而地方自治很快停办,1914年3月,上海市政厅撤销, “复自治为官治”,④杨逸编《上海市自治志》,“序”,第1页。上海慈善团亦自此恢复自由之身,重新成为地方士绅负责的民间慈善组织,其所属各团体善举亦继续进行,且加入慈善团的善会善堂逐渐增加。1912年,慈善团有12个组织,随后慈善团第一、二、三义务小学校,以及上海栖流公所、妇女教养所、上海孤儿院、辅元堂南市办事处、保婴局、吴庆馥堂、保安司徒庙、同仁保安堂(后改为保安养老所)、顾德润堂、上海慈善团养济院①《上海慈善团养济院沿革》,上海市档案馆藏,Q130-6-61。、上海游民习勤所、淞沪教养院(即游民习勤所第二所)②上海游民习勤所编印《上海游民习勤所第一届报告》,1931,上海市图书馆藏。、赊葬局、普安施粥厂、保赤局③《上海慈善团章程》,上海市档案馆藏,R15-2-71。、慈善病院④《上海慈善团十九年度预算册(1930.7.1—1931.6.30)》,上海市档案馆藏,Q6-18-329。等组织先后加入或者直接由慈善团兴办,成为慈善团的组成部分。这些组织共计30余个,基本上都在慈善团董事会领导下,一起从事慈善活动,它们构成一个巨大的慈善群团。此外,上海慈善团还给予其他诸多慈善组织资金资助,并以此为纽带形成一个更大的组织网络。
加入慈善团的各团体大都保留原有组织机构,分别领导本团体活动,而且其内部各个组织之间的地位并不完全一样。围绕上海慈善团,至少有三种不同关系。
首先,是完全隶属于慈善团的组织。这些组织由慈善团管理或者由它直接开办,由慈善团董事会领导,慈善团事务所负责经营,每年的经费开支直接并入慈善团的预算。如同仁辅元堂(包括它所属的同仁辅元分堂、救生局、辅元堂南市办事处等),普益习艺所(贫民习艺所),游民习勤第一、第二所,所属第一、第二、第三义务小学,⑤《上海慈善团十九年度预算册(1930.7.1—1931.6.30)》,上海市档案馆藏,Q6-18-329。清节堂(1929年改为妇女教养所)、保节堂、育婴堂等。⑥吴馨等修,姚文枏撰《上海县志》,第699页。
其次,是接受慈善团董事会领导,但不由其直接经营的团体。这些组织加入了上海慈善团并由其兼管业务,但有独立的经营机构,有单独的会计核算,如栖流公所、同仁保安堂(后改为保安养老所,并入慈善团)、慈善团养济院⑦《上海慈善团十九年度预算册(1930.7.1—1931.6.30)》,上海市档案馆藏,Q6-18-329;《上海慈善团预算书》,上海市档案馆藏,Q6-18-331(1)、Q114-2-1。、新普育堂等组织,“各设主任,各自收支,金[经]费不敷,堂[团]中按月补助”。⑧吴馨等修,姚文枏撰《上海县志》,第699页。
最后,是接受慈善团资助的组织。这些组织可以算作慈善团的外围组织,没有直接加入慈善团,业务也不受慈善团董事会的监管或领导,甚至地域也不限于旧城区,但能收到慈善团的资助,可以算作以慈善团为核心的慈善群团的组成部分。1933—1936年经常得到慈善团资助的主要有:上海医院(1200元)、复善堂(300元或600元)、安老院(200元)、残疾院(1000—1500元)、普善山庄(375元)、庇寒所(6000元)、孤儿院(500元)、高桥三知堂(120元)、保产医院(48元)以及南区救火会(30—50元)。①《上海慈善团二十三年度预算书》,上海市档案馆藏,Q6-18-331(1)、Q6-18-331(2)、Q6-18-332。实际上,整个民国时期都有很多慈善组织(最多的时候有50多个)从慈善团获得经费支持。当然,这些组织并非每年都能得到慈善团的资助,其数额也不固定。
慈善团与上述三个层次中的慈善组织的关系并非恒定不变。有些组织可能会在三个层次中变动,如新普育堂就是如此;也有一些可能会从受助对象中被取消,如普善山庄、上海医院等在1934年以后就不再出现在慈善团预算表的补贴对象栏中。②上海市档案馆藏,Q6-18-331(2)、Q6-18-332。从慈善团的预决算表中可以看到,每年列入慈善团补助经费开支中的团体都有增加。
同时,上海慈善团还是上海邑庙董事会的成员,该董事会成立于1926年,由上海县公款公产管理处、上海医院、上海慈善团、上海市公所、整理邑庙豫园委员会、上海乞丐教养院等组成,③《申报》1927年2月8日。其主要职能是管理城隍庙的香火、房租、店租收入,以便补助给市内主要慈善团体。该会1937年的收入为67983元,一共补助了19个慈善组织。④《上海邑庙董事会章程》,上海市档案馆藏,Q114-1-9。因此,通过邑庙董事会的董事身份,慈善团还可以影响到其他许多慈善组织。
上海慈善团以自身所属组织为中心,通过直接或间接向其他慈善组织提供资金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些团体的活动,从而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通过此途径,上海慈善团在上海慈善界构建起一个同心圆式的多层次慈善网络,形成一个巨大的慈善群团,成为上海慈善界的翘楚,在民国时期的上海社会问题处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上海慈善团经费来源
上海慈善团从成立之初就因统一管理所属慈善组织而拥有了巨大的财产规模,而且在此后的建设中,慈善团积极利用身处上海这个日新月异、机会良多的都市社会的特点,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在保有传统投资方式的同时,广泛涉猎各种新式投资领域。上海慈善团在民国时期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土地出租和房屋出租所取得的租金收益,也有慈善组织传统的捐赠收入,以及一部分投资于股票、债券等方面的新式收益,存放钱庄、银行取得的利息收益,慈善团所属机构出产品的收益等。
(一)不动产收益
上海慈善团能够成为上海慈善界的领袖,与它本身庞大的财产规模是分不开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逐步在形式上完成对全国的统一,这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同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直辖于国民政府行政院。上海市政府设有社会局(开始为公益局,后归并农工商局,最后设立社会局)专门管理社会福利、慈善公益等方面的事务。市政府社会局为了有效控制民间慈善事业,与慈善界进行反复交涉与较量,逐步建立起对慈善组织的监督管理。①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慈善界与市政府社会局之间的交涉,小浜正子有比较全面的论述。参见〔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第110—117页。正是在此基础上,社会局与慈善界主要领袖共同对慈善团体的财产进行了一次比较详细的调查和整理。下面根据这次调查结果来分析慈善团这一时期的财产状况。
这次调查包括了上海民间主要的慈善组织,小浜正子对其中的28家主要慈善团体拥有不动产的状况进行了统计。②见〔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第86—87页表。本段叙述主要依据该表,后不详注。28家慈善团体拥有不动产价值14100391元,其中上海慈善团8783767元,占被调查慈善团体不动产的62.29%;另外,受慈善团领导的新普育堂拥有1083462元,占7.68%。在实际的现有收入中,慈善团为442931元,租米6828石,占整个现有收入618763元的71.58%,租米更是占总额的百分之百;新普育堂现有收入为42327元,占整个现有收入的6.84%。无论从所拥有的固定资产价值还是现有收益来看,慈善团都占据着上海慈善界的最大份额,从中亦可见上海慈善团在整个上海慈善界所具有的地位。正是因为拥有如此庞大的财产,上海慈善团才能在日常工作中对其他慈善团体进行资金补助,也才能够不断扩大自身影响,树立在上海慈善界的领袖地位。
此后,慈善团的财产仍在不断增加,就在社会局对慈善团财产进行调查时,慈善团在法租界建筑房屋出租,以后又有利涉菜场的建立以及收回政府部门占用的地产等,这些财产每年都为慈善团带来大量收益。抗战爆发以后,上海慈善团的许多房屋被毁,地产田产被大量侵占,设在同仁辅元堂的事务所也“因兵燹堂毁”,①《上海慈善团章程(修订稿)》,上海市档案馆藏,R15-2-71。其他所属团体的财产损失无法统计。抗战结束以后,上海市社会局对民间社团进行重新登记,其时上海慈善团在市区各区拥有地产上千亩,房产占地1404亩,各类房屋数千间,在郊区和外地拥有田产6749亩。②《上海慈善团财产登记表》,上海市档案馆藏,Q130-6-61。可见即使受到战争的严重摧残,慈善团的财产规模依然相当可观。
30年代上海慈善团的经费绝大部分来自房地田产租金以及菜场等摊位租金,这类收入从根本上支持了慈善团的日常活动。表1显示了这类收入在慈善团收入中的地位。

表1 1930—1935年上海慈善团租金收入所占比例单位:元
在上海慈善团1930年度收入中,其所保管的法租界房产收益委员会当年收入123760.436元没有计算在租金收入中,但算入了总收入。实际上这是当年从法商高易处借来建筑法租界房屋的款项,不是慈善团的真正收入,不应该计算在总收入中,所以租金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实际更大。同样,此后的几年中,每年都有一项收入叫作“本届收支不敷数”,这也主要是借款,不属于真正的收入。①《上海慈善团决算书》,上海市档案馆藏,Q6-18-328(1)、Q6-18-328(2)。表1列出了各项不动产租金的具体数额,从中可以看出,房租在整个租金收入中占绝大部分,这反映出近代上海慈善事业的都市性格。②〔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第95页。总的来说,慈善团本身不动产收益占整个慈善团收入至少一半以上,甚至经常维持在70%以上,这是慈善团经费开支的根本保障。
(二)捐款收入
捐款收入是传统慈善组织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对慈善团来说也不例外。中国民间慈善组织一直以来就拥有比较固定的各业善捐,根据《民国上海县志》的记载,固定为慈善团提供善捐的主要行业有南北钱业、典业等十四个行业。③吴馨等修,姚文枏撰《上海县志》,第311—312页。慈善团1930年度的预算书中,更是明确列出各业捐款的数量(详见表2)。借助该表,我们能够大致了解慈善团在此前后的各业善捐情况。

表2 1924—1931年慈善团部分年度常捐银来源单位:元

续表

续表
慈善团在1920—1930年代捐款收入变动不大,从表2目前我们可以明确的几年数据来看,1924年慈善团常捐收入为7995.287元,占当年慈善团总收入328792.284元的2.43%;1925年为10196.49元,占当年慈善团总收入303101.465元的3.36%;1930年度预算的常捐收入为9353元,只占当年预算收入的0.85%。捐款总量虽然不是一成不变,但变动值不大,而且稍微可以看到一个上升的趋势,如1922年慈善团的各业捐款数为7262.52元,①《上海慈善团征信录》(1922年),参见〔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第97页表。到20年代末和30年前期基本上维持在1万元左右。另外在具体的捐款行业以及数量上,每年都有比较大的变化。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1930年慈善团正在借款建法租界房屋,所以将借款作为收入计算,即使扣除此一因素,当年慈善团的预算收入为688458元,②《上海慈善团十九年度预算册》,上海市档案馆藏,Q6-18-329。常年捐款只占总收入的1.36%。可见,在慈善团的收入中,各行业和固定善姓提供的常年捐款并不占特别重要的位置,其在慈善团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反而有下降趋势。实际上,慈善团对常年捐款的预算一般并不准确,最终能够收到的捐款与预算数相比,经常会有比较大的出入。慈善团预算表中1925年常捐收入预算数为8940元,实际收到10196.49元;①《上海慈善团民国十四年度岁入决算表》,《上海市公报》1926年第23期。1930年实际收到的常年捐款为12821.59元,②《上海慈善团决算书》,上海市档案馆藏,Q6-18-328(1)。超出预算3468.59元;1933年预算的常捐收入为8902元,③《上海慈善团预算书》,上海市档案馆藏,Q6-18-331(1)。实际收入为4286.30元④《上海慈善团决算书》,上海市档案馆藏,Q6-18-328(1)。,比预算少了4615.7元。而且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此后几年都存在较大的差距。
从表2可以清楚地看到,个人慈善捐款对于长期慈善组织来说并不可靠。无论是从年捐还是月捐的情况来看,慈善团每年收到的“各姓善捐”都呈减少趋势,而且在整个慈善团收入中所占地位微不足道。另外还可以看出,各业的捐款中,虽然有一些行业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一直坚持提供捐助,但不仅总数极为有限,而且从数额上来说,也存在不断减少的趋势。这一方面反映常年捐款在慈善团收入中不占重要地位,慈善团在做预算的时候都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捐款的不稳定性,民间慈善事业要为长久之计,必须有其他方面稳定的资金来源。
慈善团体的捐款收入除了常年捐以外,还有特别捐款和临时捐款两类。这两类捐款一般视各团体情形而定,有的是每年都必须大量募捐才能维持善举,如果募捐不力,当年的善举规模就必须紧缩。慈善团并不依赖此类捐款,在慈善团每年的预算中对此项收益并不预计很高,有时甚至根本不把其预算在内,比如1930年慈善团上报社会局的第一份预算书就没有把特别捐款、临时捐款列入,后来修改后在岁入临时门中列入捐款收入2700元,最后因为考虑到要“弥补收支不敷数”,又修改当年预算,列入特别捐款55535元。⑤《上海慈善团预算书(1930年度)》,上海市档案馆藏,Q6-18-329。但慈善团每年收到的实际捐款相当可观,1930年慈善团实际收到的特别捐款84503.95元,另有临时捐款1342.95元,⑥《上海慈善团决算书(1930年度)》,上海市档案馆藏,Q6-18-328(1)。远远超出原来的预计。在此后的几年中,这两项捐款收入都在1万元以上。这种状况的出现无疑与慈善团在上海所具有的声誉相关,因为声誉好,所以吸引民间主动捐献很多,这项收入因而经常超出预算之外。
(三)其他收入
慈善团还有一些事业收入如同仁辅元堂的棺木售价,普益习艺所、游民习勤所、妇女教养所等的工艺品变价以及少量教育收入。这些收入既不稳定也不多,对整个慈善团的影响不大,此处带过不论。慈善团暂时不用的现金也有存放钱庄和银行生息,虽然为数不多,但也是其收益之一。另外,慈善团积极投资于新式企业,购买股票和债券,以获取股息和债息。慈善团地处上海这个新兴都市,办事诸人也积极利用这一有力条件,因而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变卖自身公产是民间慈善组织筹措资金、维持运转的方式之一。一般而言,民间慈善组织不能依赖捐款来维持运作,应该尽可能置产兴业,以期获利而维持并发展自身事业。但是在非常时期,变卖自身资产又成为慈善组织维持自身运转不得已之法。当然,慈善团体拥有的财产是地方公产,乃地方利益所在,不能轻易处理。这实际涉及如何处理维持善举与维护地方公产的矛盾,这一问题也反映出地方精英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上海慈善团成立以后添置了大量产业,同时也对继承下来的以前善会善堂的一些产业进行了处理。早期处理自身产业主要是为了适应市政建设的需要或者出于更好利用这些资产的目的。1930年,因为公共租界、法租界筑路所需,慈善团不得不出让了部分土地,在当年的收入中就有英工部局、法公董局筑路地价9316.485元;1931年更有公产变价108334.33元;1934年有变卖收入1639元。①《上海慈善团决算书》,上海市档案馆藏,Q6-18-328(1)、Q6-18-328(2)。抗战爆发以后,慈善团的活动受到很大影响,许多善举不得不先后停办,三所义务小学全部在抗战中停办。②《上海慈善团章程》,上海市档案馆藏,R15-2-71。战争不仅摧毁了慈善团的许多财产,而且使得剩余的财产因为没有有效维护而收益大减。战后,慈善团为了维持自身运转,不得不大量出卖公产。此类收入成为战后慈善团得以勉强维持的主要资金来源。
三 上海慈善团的主要善举
上海慈善团作为一个民间慈善组织,其最主要的活动自然是“救生送死”——救济生者和安葬死者的业务。
上海慈善团是由同仁辅元堂等组织发展而来,其中有些组织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们一直在从事传统的救济各种社会弱势群体或者需要特别予以关注的群体(如节妇等)的活动,并入慈善团以后,虽然有些活动进行了调整(如清节堂、保节堂改办妇女教养所等),有些逐渐被取消(如保节等),但是,其他绝大部分的传统慈善活动还在继续进行。慈善团主要通过下属的同仁辅元堂、育婴堂、保安养老所等进行传统的善举活动,至于妇女教养院、游民习勤所(第一所、第二所)、普益习艺所、上海医院以及慈善团第一、第二、第三义务小学等所进行的活动,则带有新的特点,这反映了这一时期上海慈善界理念及实践的发展变化。
有关民国时期上海民间慈善活动,小浜正子分成九类进行论述,基本可以涵盖此时民间慈善事业的主要活动范围。①该分类中有诸多重复之处,如说救济贫民,慈善组织绝大多数本身都是为了救济贫民而设立的,绝大部分慈善活动都可以包括在这一类里面。另外,收养丧失劳动能力者与收容教化贫民、游民、妓女、孤儿等,这样的分类,作者自己也没有完全弄清楚,如作者就把游民习勤所收养之人先当成丧失劳动能力者,接下来又在收容教化类里再次说明,如此等等。参见〔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第68—81页。这九类中,除了第八类——放生、惜字以外,其余都可以在上海慈善团的活动中找到。上海慈善界在民国时期开展了全方位的慈善活动,慈善团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处理死者问题是传统慈善组织最主要的业务之一。慈善组织对于死者的服务主要包括提供棺材和冢地、帮助掩埋、收埋路毙尸体以及举行盂兰盆会祭祀、超度等。许多慈善组织免费为那些死后无以下葬的贫穷者提供棺材、义冢、石灰等,甚至义葬。为死者提供服务的大型慈善团体一般都拥有棺材加工场,它们同时向有钱的人出售棺材,作为慈善组织主要的业务收入。1934年上海慈善团的业务收入为25068.16元,其中同仁辅元堂出售棺材收入为24253.50元,占全部收入的96.75%。②《上海慈善团决算书(1934年度)》,上海市档案馆藏,Q6-18-328(2)。慈善团对死者的服务主要由同仁辅元堂及其分堂提供。根据《慈善团办法大纲》的规划,改组以后的同仁辅元堂及其分堂主要应该负责施棺、掩埋等活动,③《上海市自治志·公牍丙篇·慈善团办法大纲》。由于地方自治取消,原来的规划化为泡影,同仁辅元堂不得不继续从事以前的诸多慈善活动,但在慈善团的统一管理下,对死者提供服务仍然在其业务中占有重要地位。同仁辅元堂不仅自身从事施舍棺材、收拾路毙、掩埋无主尸骨的工作,还处理其他团体送来的尸骨。1934年同仁辅元堂的全部事业开支中,用于对死者服务的施棺、掩埋等花费62093.70元,占其全部开支94707.77元的65.56%;1935年,同仁辅元堂的施棺、掩埋花费50288元,占其全部开支83087.19元的60.52%。①《上海慈善团决算书(1934、1935年度)》,上海市档案馆藏,Q6-18-328(2)。同时,慈善团也向上海最主要的办理施棺、掩埋工作的团体普善山庄提供经费补助。1930年,慈善团补助普善山庄1000元,1931年补助750元。②《上海慈善团收决入算书》,上海市档案馆藏,Q6-18-328(1)。
救济贫民是慈善团体最主要的救生活动。慈善团所属同仁辅元堂、妇女教养所、保安养老所等大多数机构都开展对贫民的救济活动。救济贫民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提供固定生活补助、临时补贴、集中收养等。提供生活补助的工作主要由同仁辅元堂进行,1912年上海慈善团为其制定的生活补助计划为:恤嫠300人、赡老270人、残疾30人、矜孤40人;前三者每月发放0.5元,孤儿每月0.4元;每年底发给每人白米8升,每两年发棉衣一件。1922年补助名额有所增加:恤嫠320人、赡老和残疾共320人、矜孤50人,另设孤贫100人,但是补助依然是每人每月0.5元。这种生活补助对于受救济者究竟有多大的作用?1912年一石粳米的价格是7.94元,善堂每月提供的补助能买到约6.3升米,而1922年粳米价格上升到每石11.18元,0.5元只能买到约4.5升米。③〔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第70页。也就是说,这些补助大概能勉强维持一个人十天左右的生活,对于那些急需救济者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作用相当显著。
其他济贫活动我们可以从经费开支中窥见其大概。妇女教养所1934年的支出为17740元,保安养老所支出为14841.32元,该年同仁辅元堂的此类支出为1611.70元,三者共计48793.02元,占整个慈善团当年支出总额404523.63元的12.06%。1935年,妇女教养所的支出为18680元,保安养老所支出为14750元,该年同仁辅元堂此类支出为19033.35元,三者共计52463.35元,占整个慈善团当年支出总额386812.58元的13.56%。④《上海慈善团收决预算书(1934、1935年度)》,上海市档案馆藏,Q6-18-328(2)。
施医、施药历来是慈善组织的重要活动。上海慈善团所属的上海慈善医院是一所专业医院,它不同于一般的善会善堂临时聘请医师,而是有比较固定的医师和护理人员。1931年,慈善团拨给慈善医院的经费为7360.910元,以后基本维持在每年6000元左右。①《上海慈善团收决预算书》,上海市档案馆藏,Q6-18-328(1)、Q6-18-328(2)。另外,慈善团每年还会对一些给贫民施医施药的医院进行补助,1931年补助上海医院2400元,保产医院44元,松江若瑟医院1000元,圣心医院694.45元,虹口时疫医院100元。此后,慈善团对这些医院几乎每年都有多少不一的补助。②《上海慈善团收决预算书》,上海市档案馆藏,Q6-18-328(1)、Q6-18-328(2)。
育婴堂是上海最早建立的民间慈善组织,③康熙年间设立的育婴堂最早是由士绅倡建的,因此可以说是上海最早的民间慈善组织。参见《上海县志》,同治十一年刊本,第191页。育婴事业也是慈善团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上海育婴堂负责办理。上海育婴堂1926年收养的婴儿人数为325人,占当时上海最主要的育婴机构收养总数2083人中的15.60%;1927年收养245人,占主要收养人数1943人中的12.61%;1928年收养298人,占主要收养人数1889人中的15.78%。④〔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第75页。虽然在整个育婴事业中慈善团不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但30年代慈善团为育婴堂每年支出均在万元以上,⑤《上海慈善团收决预算书(1934、1935年度)》,上海市档案馆藏,Q6-18-328(1)、Q6-18-328(2)。仍然对整个育婴事业有着重要贡献。
处理城市中的流浪人群,是近代城市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在近代上海更加是一个关系民族尊严的问题。⑥近代上海地方精英们深刻地认识到上海作为中国代表性城市,应该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不然就会被外国嘲笑。从这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出发,收容、救济城市中随处可见的游民、贫民就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近代上海许多的慈善组织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设立并得以维持的。参见〔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第56页。收容游民、贫民,并对其中有劳动能力者进行一定程度的教育,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以便将来能够自谋生路,是近代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方向,⑦关于近代民间慈善理念的发展变化,参见周秋光、梁元生、王卫平等人的相关成果。也是上海慈善团着力最多的活动。
慈善团所属游民习勤所、普益习艺所、保安养老所、栖流公所乃至妇女教养所等,其活动基本可以归入此类。上海市社会局的调查显示,民国时期上海主要的慈善组织收容游民、贫民、孤儿以及残疾等各类弱势群体人数为5598人,而慈善团所属的保安养老所、妇女教养所、淞沪教养院(游民习勤第二所)、游民习勤所、普益习艺所、沪北栖流公所等机构收容的人数为2182人,占总数38.98%。另外,收容人数最多的新普育堂也在慈善团董事会的领导之下,慈善团每年的定额补助高达24000元,还经常根据需要提供多少不等的特别补助,如1930年就为其提供了特别补助5132.2元;上海残疾院、上海孤儿院、中国妇孺救济总会等也接受上海慈善团的补助。①《上海慈善团收决预算书》,上海市档案馆藏,Q6-18-328(1)。这些机构收容人数为3144人,占整个收容人数56.16%。②本段叙述参照〔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第77页表格。这两部分相加,慈善团所属或者其影响下的慈善团体所收容的人数占到整个收容人数的95.14%,可见在收容救济游民贫民方面上海慈善团的贡献非常大。
慈善团每年为此的支出也是相当可观的,下面根据30年代慈善团的决算书对此问题做进一步探讨。慈善团所属保安养老所、妇女教养所、淞沪教养院、游民习勤所、游民习勤第二所、普益习艺所、沪北栖流公所等每年的支出及其在慈善团整个慈善事业经费开支中所占比例见表3。

表3 1930—1935年慈善团收容救济贫民、游民经费开支单位:元
慈善团对游民、贫民的救济收养支出一度超过其慈善支出的一半,即使后来游民习勤所支出减少,这项开支一般也维持在整个慈善事业开支的三分之一以上。另外,前文也已提及,慈善团每年还对上海的大型收容机构给予相当可观的资金援助。从表3可以看出,1930年度慈善团用于救济、收容游民、贫民的主要机构的补助支出达41832.2元。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民国时期,慈善团对上海游民问题的处理,对于上海无家可归者的救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其他团体的补助,更是大大促进了这一事业的发展。
兴办义学也是慈善团的重要活动之一。上海慈善团将所属团体义学重新组织,先后在市内设立三所义务小学,招收贫苦儿童入学,大部分实行完全免费,另有小部分仅收取少量的书本费。慈善团在事业经费中单列教育事业门,义务小学每年的经费直接由慈善团拨给,30年代以后教育经费不断增加。1934年度慈善团预算的教育经费为6679元,比1933年度多出661元;1935年度增加到7269元,1936年度教育经费更是增加到7608元。①《上海慈善团预算书》,上海市档案馆藏,Q6-18-331(1)、Q6-18-331(2)、Q6-18-332。当然,慈善团这方面的活动在其整个慈善活动中不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其支出方面也相对比较少;在上海这一时期慈善组织所办的义务小学中,慈善团的义务教育也不占有很大比重,当然,它也通过对其他义务学校的资金援助,加强了自身在这一方面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上海慈善团在民国时期的上海各项慈善事业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以来的上海民间慈善事业还在救济各地自然灾害乃至兵灾等方面采取积极行动。民间慈善事业的新形式“义赈”就是由上海慈善界创造的,②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并且在历次重大灾难的救济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民国时期上海民间慈善界对外救济(此处既指对国外,也指上海以外的国内地区,主要是后者)活动主要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的组织、领导之下开展,上海慈善团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上海慈善团虽从典型的中国民间慈善组织同仁辅元堂以及果育堂、育婴堂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是与近代上海城市社会发展相适应,其活动具有诸多自身的特色。上海慈善团的成立本身就是为了重组上海的慈善事业,使之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更好地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慈善团成立后,上海地方精英基于自身对时代发展的认识,对一些他们认为不适合新时代发展的观念予以抛弃,重新对民间慈善事业进行整合,从而使得上海民间慈善事业呈现出较多的新特色。
传统的善举活动对于贫穷者的救济主要是通过施舍一定的钱物,使其勉强维持生命,这种救济一般而言不可能改变受济者贫穷的境遇,因此一旦对其提供的救济中断,受济者就可能重新回到死亡的边缘。设立工艺作坊,教授贫穷者一技之长,庶几使其在离开救济机构以后可以自谋生路,成为上海慈善团经营新理念的主要表现之一。上海慈善团所属的普益习艺所、游民习勤所、妇女教养员等都设有工场,并聘有专门的技师等教授被收容者一些基本的工艺,以便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将来能够自谋生路,同时也可减少社会上的不良分子,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如普益习艺所就明确宣称:“本所……以人民生活技能教授贫寒子弟,俾减少社会上分利者为宗旨。”①《普益习艺所章程》,上海市档案馆藏,Q114-1-9。即使是以收养“年六十以上之男女无力生活并乏人赡养者为目的”的保安养老所,也在所内设有工场,根据被收容者的身体状况安排一定的工作,以将工艺品变卖补贴开支。②《保安养老所章程》,上海市档案馆藏,Q114-1-9。可见慈善团的活动不仅适应了这一时期慈善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且实际上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慈善事业的看法。慈善组织考虑到被救济者以后的生活安排,更反映了这一时期慈善界理念的改变:变传统的消极救济为积极救济,救人救彻。这一时期上海慈善界对于游民、贫民习艺所或习艺工场,咸抱乐观之态度,不仅认为其“是生利的,而非分利的”,甚至有人将其提高到“事关国计民生、社会安宁”的高度来认识。③《南北慈善团体联席会大会纪》,《申报》1922年11月17日。非慈善界人士也对贫民工场之类的举措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时人在《申报》刊文称对贫民施衣、施米等不过是使他们“苟延残喘罢了,于他们既没有多大益处,于社会或且有害”,慈善家应该“改变那种消极的治标的不彻底的慈善活动,代之以积极的治本的彻底的慈善”。该作者提出的方法首先就是“设立贫民工场,收养贫民,授以技术使做工自给”。④徐直:《对于慈善家进一言》,《申报》1923年1月26日。可见,慈善团的这种改变不仅适应了慈善事业本身发展变化的需要,也无意中顺应了人们对慈善事业的要求。
慈善团在对生者的救济方面还抛弃了一些带有较多过去意识形态特点的观念。上海市政厅在开始设计慈善团活动时,就没有把那些传统善举中被认为具有较多儒生意识的惜字、放生等活动列入慈善团的六科当中。对于传统善举极为重视的救济节妇等活动,①关于惜字、保节活动的意识形态特色,参见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江南的慈善组织》,第五章。慈善团也并不重视,宣称“恤嫠不限年例,故保节可并入赡老”,②《上海市政厅章程——慈善团办法大纲》,《上海市自治志·各项规约、规则、章程》丙篇。实际上是否定了特意救济节妇的必要性。但是妇女作为社会弱势群体仍然是慈善团的重要救济对象。清节堂、保节堂等专门针对寡妇的救济机构被改造成面向所有贫穷女性的妇女教养所,另外,保安养老所等也收养女性,实际上上海慈善团对女性的救济范围大为扩张。
如果说中国民间慈善组织在晚清以来逐步向小社区发展的结论是成立的,③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江南的慈善组织》,第297页。那也可能只是适合个别地方的结论,或者只是那一个特定时期的现象。晚清以来,上海慈善界在经历了小刀会起义的短暂衰落后就一直在扩充善举,并出现新建善会善堂的高潮,尤其是同仁堂与辅元堂合并以后,规模在不断扩大,善举也在不断增加。④阮清华:《慈航难普度——慈善与近代上海都市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第一章、第三章。上海慈善团建立以后,更是把上海老城区的主要慈善组织纳入麾下,组织规模越来越大,不但没有向小社区发展的趋势,反而不断越出上海地区,直接面对更多的需要救济者。也许可以说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除了“小社区化”趋势以外,还有一个更大的趋势,即整合区域内的慈善组织而不断扩展其组织规模和功能,成为跨区域和跨慈善门类的超级组织或慈善群团。
四 结语
1912年,上海慈善团成立后,上海市政厅要求慈善团董事会对上海慈善事业进行统一规划,上海慈善事业形成了新的合作关系。以慈善团为中心,出现了一个由慈善团体组成的同心圆式网络结构。慈善团成立以后,在原有机构的基础上接纳和新建一些机构,组织起一个规模巨大的慈善群团。而民国时期,在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的闸北地区,也出现了类似上海慈善团的慈善群团,如仁济善堂和闸北慈善团等,都是由许多慈善团体组成,拥有诸多产业,并广泛开展各类慈善活动,它们共同构成了民国时期上海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海慈善团为代表的慈善群团的许多活动已经与传统的善举有所不同,对于与都市社会健康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社会问题,如救济贫民、游民,对贫穷孩子的义务教育等都大力投入,其目的都在于通过教会受济者一技之长或者掌握一定的知识,让他们可以到社会上自谋生路,以摆脱贫困。慈善群团对于传统的放生、惜字以及救济贞节寡妇的活动比较消极,对于救济妇女等采取比较新的形式。另外,慈善群团通过对其他慈善组织的大量资金援助,不仅扩大了善举范围,也提高了自身的影响力,使得以它们为中心的慈善网络不断扩大,影响远及周边乃至上海以外的地区。1927年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的成立,实际上是各慈善群团的联合,也进一步推动了上海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
上海慈善团的发展表明:小社区化现象在上海慈善界并不显著,近代以来民间慈善事业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大大发展,进一步扩展了其业务以及活动空间。通过对上海慈善团的分析,可以认为民国时期上海慈善界在上海慈善团的带动下,出现了诸多新的现象,这反映出积极救济、救人救彻的慈善观念开始成为慈善界的共识。同时,以上海慈善团为代表的慈善群团,积极应对各种都市社会问题,为上海经济和都市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贡献了力量,表现出中国传统民间慈善组织在近代上海都市社会发展中强大的适应性和顽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