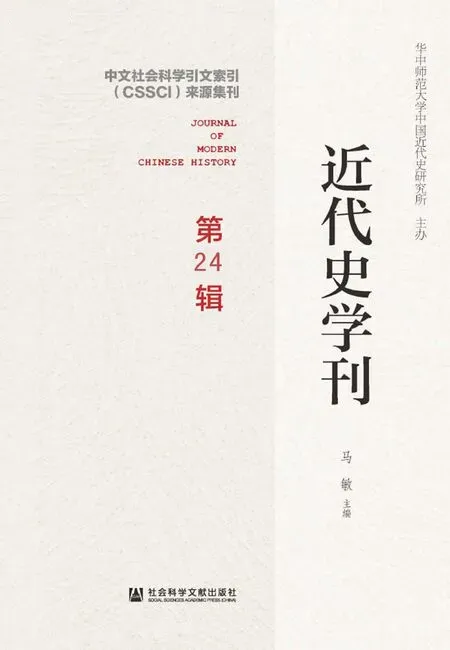蔡增基:中英借款谈判的推手*
——李滋罗斯与招商局贷款往来书信解读(1936—1937)
2021-04-17李培德
李培德
内容提要 笔者于英国国家档案馆收集到的两份英国财政部档案,是1936—1937年时任财政部顾问李滋罗斯与英国政府不同部门负责人讨论有关招商局贷款问题的来往书信,其中透露了借款谈判鲜为人知的复杂过程,以及英国对招商局和蔡增基所抱态度和施行策略,对于了解1930年代蔡增基主政下的招商局发展,蔡增基为扭转财政危机所采取的策略及与英方谈判时的出色表现,都颇有助益。本文利用这批书信,讨论招商局向英国购买轮船的借款问题,试图弥补1930年代招商局史和中国外债史研究的不足。
一 引言
出身英国银行世家的李滋罗斯(Frederick Leith-Ross,1887-1968),于1909年加入英国财政部,1911年起任英国首相阿斯奎斯(H.H.Asquith)的私人秘书,1932—1945年出任英国政府财政顾问。1935年9月,李滋罗斯被派往中国,协助中国推行币制改革。1936年6月,李滋罗斯回国,其后仍对英国的对华政策发挥影响。有关李滋罗斯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他如何协助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已多被学界讨论。①相关代表性论著有但对于一笔招商局向英国购买轮船的借款,李滋罗斯是如何被卷入谈判的则甚少被注意。当时,代表中国与英方交涉的是招商局总经理蔡增基,他在谈判中表现得甚为出色。由于购船借款对拓展航运业务有直接帮助,此次谈判值得深入研究。有关中英两方的谈判,特别是李滋罗斯和中英两国政府不同部门负责人的讨论,不仅可反映英国的对华政策,更可见到李滋罗斯等英国官员对招商局和蔡增基的看法。
本文依据的是笔者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收集到英国财政部档案中有关招商局的两份档案②National Archives,Kew;Treasury;T188 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Ltd..,分别为T188-159:轮船招商局——清理债务(The 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Settlement of Debt),包含13封书信;T188-160:轮船招商局有限公司——购买新船(The 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Ltd.:Purchase of New Ships),包含14封书信。其中以后者的内容更为完整,对于了解1930年代蔡增基主政下的招商局甚具参考价值,只是过去学界在招商局史或中国外债史的研究中没有注意这一方面的外文档案。③张后铨:《招商局史(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吴景平:《关于近代中国外债史研究的对象的若干思考》,《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这些往来信件皆为英文,笔者挑选其中15封译成中文,并进行分析。
二 英国对招商局的贷款政策
一般来说,很多和中国有接触的英国官员认为1930年代的招商局存在经营不善的问题,例如财政不佳、管理紊乱。国民政府成立专责委员会对其进行整顿时,就发现“各地方分局如烟台、香港、广州均被个人把持,舞弊营私十分严重,年年亏蚀”,④陈玉庆整理《国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19页。李滋罗斯对招商局的印象也不例外。1932年,招商局改称“国营招商局”,标示着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1936第577号、1988年2月、20—30);吴景平:《英国与1935年的中国币制改革》, 《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Niv Horesh, “Whitehall vs Old China Hands:The 1935-36 Leith-Ross Mission Revisited,”Asian Studies Review,Vol.33,June 2009,pp.211-227。年,蔡增基就任总经理,积极发展招商局业务,遂有更换旧船只和扩充船队的计划,但碍于经费难筹,没有真正展开。蔡增基在自传中说,他先向英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比尔(Louis Beale)求助,当李滋罗斯来华时,又向李提出借款要求。①Jun Ke Choy,My China Years,1911-1945:Practical Politics in China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San Francisco:East West Publishing Co.,1973,p.165.蔡增基认为如果英国能够提供借款,对招商局的发展将有莫大的帮助,因而对之十分重视。蔡接手招商局后,即着手推行一连串改革。其一,废除买办制,以接受新训练的年青学生充当“舱务长”(purser),代替原来的买办;其二,与青帮谈判,在租界当局的协助下,重夺金利源码头的控制权;其三,购买新船,扩充船队,以与英资怡和、太古洋行和日资航运公司竞争。在蔡增基看来,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还是汇丰银行没收借款抵押品引发的危机。②1923年汇丰银行向招商局贷款150万两,其后增加至500万两,年息8厘,分16年摊还,每年一次,1928年4月26日进行第一次还款。有关借款合同内容,见陈玉庆整理《国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第601—626页。蔡增基在自传中自嘲,美其名曰“总经理”,不如说是“清盘人”(liquidator),可见当时处理危机的迫切性。蔡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重组汇丰银行的1600万元旧债,否则招商局难有转机。③Jun Ke Choy,My China Years,1911-1945:Practical Politics in China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p.166.值得注意的是,蔡并没有把这些他所推行的改革,特别是有关与英方进行购船借款谈判的事情写入自撰的《招商局最近三年来之革新》(1940)中,甚至其自传中亦无只字提及,可以说耐人寻味。④Jun Ke Choy,My China Years,1911-1945:Practical Politics in China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p.166.
根据蔡增基1973年出版的英文自传,他接任招商局总经理职位后,遇到的最大的危机来自汇丰银行的威胁:由于长期积欠贷款,汇丰准备取消招商局回赎抵押品的权利。换句话说,如果招商局无力还款,汇丰可以变卖它的抵押品,这样的话,招商局等同于破产。因此,他趁李滋罗斯访华的机会,向英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比尔提出与李会见的请求,希望可以重组积欠汇丰的债务。蔡提出的方法有二:其一,向汇丰借更多的钱来清还旧债,实行以新债还旧债;其二,减低借款利息和逐年分期摊还。⑤Jun Ke Choy,My China Years,1911-1945:Practical Politics in China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p.166.笔者认为,蔡增基的真正目的在于后者,同时,为使英方同意,不惜使用了声东击西、转移视线的策略。
站于英国立场来看,如果能够通过贷款来插足招商局的业务,稳固英国在华航运业的利益,对英国大有好处。况且,当李滋罗斯完成对中国的访问后,曾向英国政府提出十三点建议,其中第五点便是“出口信贷应主要用于鼓励英国对华贸易,应要求出口信贷担保部拟出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案,并尽快使之生效”。①吴景平:《李滋罗斯中国之行述评》,《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笔者认为李滋罗斯积极推动英国政府尽快批出对招商局的信贷借款,目的也是如此,即加大对华贷款的总量。
需要指出的是,英国对批准招商局贷款,并非没有其他附加条件,从下面几封李滋罗斯收到的信函中可以清楚见到英国在贷款谈判过程中表现出的对于招商局的态度。
蒋介石顾问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1875-1946)1936年7月6日给李滋罗斯的信中写道:
蒋介石夫人要求我对你说一下她会向总裁提及有关招商局的事情,总裁说他会进一步了解并讨论你对招商局提出的有关建议。我在香港时与孔博士(指孔祥熙)讨论过汇丰银行对招商局提供贷款的事,看来这宗交易有点复杂。据我所知,此事曾在一个没有足够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上投票,这里好像还有一两点内容我遗忘了,但我提出这一事情纯粹是兴之所至,并非为了争论,我估计此事将来会得到调整而最终获得解决。……
英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比尔1936年7月26日给端纳的信中写道:
请向蒋介石夫人道谢,她为我们向总裁提说有关招商局的事情,这可说是一件“可怕地卷进” (horribly involved)的事,不可不防,而我相信汇丰银行会聪明地不做出任何反应。坦白说,汇丰借款一事在没有足够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上通过,我认为是不可理解的,我希望汇丰和招商局两方均可在合理的条件下讨论和解决问题。
比尔又在1936年12月23日给李滋罗斯的信中写道:
招商局改变了购买新船的要求,蔡先生(指蔡增基)已向我提交一份购买新船型号的清单,他想买的船合共8艘,总价值908000英镑,分15年付款,年息5%,由国民政府交通部提供担保,不过招商局并不认为自己可在船舶付运前还清欠款。
蔡先生说已有意大利制造商愿意以100万英镑,分12年付款,年息5%等条件来向他争取合约,此外尚有其他欧洲有兴趣的投资者,估计是挪威厂商愿意提供国币约1000万元的货船。蔡先生表示希望购买英国造的船,并祝愿我们能争取到合约,因此希望我们提供船舶造价的参考,以显示比其他商人提供更为优惠的条件。我已告知蔡先生以目前招商局的财政状况和15年的还款期条件来看,这并不算是一宗吸引人的生意……姑勿论中国的交通部会否愿意提供担保,我也不认为这是一宗具吸引力的交易。
我从庚子赔款委员会副主席马歇尔(Calder-Marshall)先生处得知招商局向该委员会要求过以更优惠的还款条件向英国购买4艘新船。……
我从信昌机器工程公司(China Engineers Ltd.)董事总经理处得知招商局正向他们处订购引擎、锅炉、钢板和其他物料,准备建造3艘新船,以应对急速扩展的长江航运需要。
我认为在未做出任何判断时,最需要考虑的是招商局的财政状况,不管是多少年的还款期,招商局的管理制度须进一步改善,并要彻底地重新检讨和重组公司的财政。我会和蔡先生保持密切联系的。
从以上三封信函可见,令英方最为担心的可以说是招商局的管理和财政状况。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招商局虽然已成为国营机构,也将不会有能力偿还购买新船的欠款。例如,在讨论汇丰银行借款一事上,很难令人相信是在没有足够出席人数的董事会上通过的,招商局的管理制度显然存在问题,令人难以相信它仍可正常运作。此外,招商局的财政一向欠佳,光是汇丰银行的旧欠便有1600万元,在此情况下再举新债,是否有危险?值得一提的是,李滋罗斯是从各方面去打听招商局的情况的,他的消息渠道可谓多样化。例如通过英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比尔,联系到信昌机器工程公司和庚子赔款委员会,甚至通过蒋介石顾问端纳,打听到蒋介石夫妇对招商局的态度,足见李滋罗斯对人际关系网络的重视。
从招商局的角度来看,虽然被英方批评为管理不善、财政欠佳,但是蔡增基接手后的招商局,特别在购买新船方面表现得甚为进取。蔡一方面向庚子赔款委员会要求购买4艘新船,另一方面又向信昌机器工程公司订购造船的机器和材料,实行自己造船,如果向汇丰银行购买8艘新船的贷款同时获批的话,招商局则可有超过10艘新船,足以重编船队。同时,从订购、建造新船的数量来看,蔡增基是有周密部署的,如果庚子赔款委员会不接受招商局要求的话,汇丰银行购船的借款便可马上派上用场了。相反,如果汇丰银行的购船借款告吹,庚子赔款委员会的新船就可成为保障了,有点儿像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道理。显然,蔡增基是懂得耍手段的,虽然在与英国谈判,但同时又向意大利的制造商打听建造新船的造价和条件,甚至自行订购造船所需的机器和材料,故意营造一个竞逐的气氛,从而争取对招商局最为优惠的条件。
不可不提的是,蔡增基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英方同意招商局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改革过程中,原来的1600万元旧债需要降低利息和以分期方式来摊还,这样招商局才有机会渡过难关。
三 蔡增基被认为是“狡猾”的人?
上文提到招商局总经理蔡增基在与英国谈判时,采用了一些策略,处处从招商局利益出发。由于蔡在美国夏威夷长大,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对国际商务比较熟悉,加上能写流利的英文信件,在国际谈判桌上自然可以大显身手了。不过,李滋罗斯对他的评价是“狡猾”,对他敬而远之。到底蔡增基采用了什么策略来应对像李滋罗斯般老练的英国外交对手?以下的信函中有所提示。
比尔1936年12月24日写给伦敦英国海外贸易部高尔爵士(Sir E.Crowe)的信中提到:
有关招商局购买新船事,我想说一下蔡是一个颇为“狡猾” (slippery)的人,他有可能已接触过意大利或其他欧洲大陆的制造商并已收到他们提供的建议书。如果招商局有能力购买新船和提出一个吸引我们的方案的话,我认为我们不能放过这一次大做生意的好机会,所以我一直与蔡保持密切的联系。我想,你会同意我这样的想法,蔡提议12至15年的信用贷款期,这对我们毫不诱人,因为招商局的财政状况不佳,长期还款对我们不利。招商局从汇丰银行得到国币130万元的借款,很可能在短时间内便可安排妥当,我会向你报告一切有关此事的进一步发展。
1936年12月30日蔡增基写给李滋罗斯的信中提到:
你可能从别的渠道知道法国的一家公司正向中国提供国币3400万元的贷款,在四川建造铁路。另外,一群德国商人也将提供价值国币4000万元建造铁路用的物料给中国。……
在中国进行这个领域的投资,可真有利可图。我该认为对所有具有潜力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平等的。不过,对我们的英国朋友来说,由于中英两国的相互了解和特别友好的关系,应对将来有可能合作的生意给予特别优惠。对于英国投资者来说,唯一的威胁来自欧洲大陆,因为欧洲的制造商可以在物料上提供比英国更低的价格,而物料价格又往往占去大部分的融资,但我相信大英帝国将有能力提供一个反建议,给予中国更长的信贷年期和更低的利息优惠。
最后,我们也收到好几名欧洲大陆的代表向我们供应新船只的建议书。为了让我们的英国朋友也可以参与这一宗生意,我已向比尔先生提供一份清单,列明我们最低购船吨位的要求,而所需款项将由出口信用保证来支付。
我记得你在中国时我曾向你提议从长远角度来看,大英帝国和中国,在东方的航运事业上,应有所合作。因此,我热切期盼这一天的到来,中英两国的航运业务,不管是江运还是海运都可以联合起来。对此,中国的航运业必须经过改革,以提升至一个可以和英方合作的水平。在这样的理解下,双方可共同合作,撇除不必要的商业风险。
有关你的最后一点提议——把招商局改组为有限公司,我认为是相当不错的提案,当时机成熟,招商局被政府改为国营后,便有可能实现这一方案。
我们要购买的新船清单如下:(1)2艘5700吨的客货两用船,340尺×48尺×25尺,造价204000英镑;(2)1艘7600吨的客货两用船,385尺×53尺6寸×29尺6寸,造价182000英镑;(3)1艘客货两用船,430尺×63尺×39尺,造价260000英镑; (4)2艘河运船,280尺×48尺×9尺3寸,造价110000英镑;(5)2艘河运船,280尺×48尺×9尺3寸(加大客舱容量),造价120000英镑。以上8艘船造价876000英镑,运费32000英镑,总额908000英镑。
英国财政部专家白池(Edmund Hall-Patch)1937年1月14日写给李滋罗斯的信中提到:
我一直在留意中国是否已聘用了意大利的工程师,或意大利人是否已开始控制招商局,但我并没有得到任何情报。
你或许仍记得在上海的一名比利时人彼德斯(Maurice Pieters)——他在中国工业部担任荣誉顾问并同时在布鲁塞尔出任荣誉中国总领事,此人向招商局提交了一份促进中国与欧洲贸易和协助欧洲在华企业的计划书。
你在1936年5月21日给比尔的信中提及你和他会面后对他的印象:彼德斯并无提及过与朗西曼(Philip Runciman)有任何关系,或说任何一个有关海洋计划的事,对我来说他只是一名二等公司推销员。在彼德斯、孔(指孔祥熙)和蔡(指蔡增基)之间流传的有关购买招商局新船的总金额约为100万英镑。
无论怎样,蔡于数天前通知比尔,他已获悉彼德斯已直接与朗西曼联系,准备在英国集资,为招商局购船筹款100万英镑,听说此事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我个人认为,比尔也有相同的看法,英国最好不要介入彼德斯和蔡之间所订立的任何财政计划。事实上,招商局正与汇丰银行磋商借款及进行公司(指招商局)管理和财政上的各种改革,我认为目前不应让中国人期盼可在伦敦筹得足够款项来购买新船。
李滋罗斯在1937年1月20日给英国海外贸易部通尼(Tony)的信中写道:
这里附上一封由蔡增基寄来的信件,是一封典型的出自蔡手的作品(a typical Choy production)。信中说蔡已向比尔打听英国的出口信贷部能否为招商局购买新船提供信贷,如果你知道有什么其他消息的话,请立刻通知我。一两天前,比尔发来一封电报,说蔡正与朗西曼谈判。
从我们的利益角度,实在不希望看到招商局发展海外航运业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因为招商局的当政者(指蔡增基)表现得十分决断,他们果真要做的话,是很难阻挠的。我可以说,如果我们还未准备好给他们贷款的话,就简单地让德国人来接这一宗生意吧。
而通尼在1937年1月22日给李滋罗斯的信中写道:
我明白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招商局经营得不错,通过庚子赔款委员会买了4艘新船,不过他们并没有缴付第一期信贷还款……巧合的是,我不明白为何朗西曼要通过比利时人彼德斯做中介去进行谈判?
中国人的航运事业已在长江上游发展得不错了,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我们的航运公司曾反对使用庚子赔款为中国添置新船,以帮助他们发展海岸航运。哥默索尔(Gomersall)说得好——他认为中国人始终可以他们的船队发展沿岸和内河航运,但问题是他们需要多长时间来完成呢?而我们为什么要帮助他们呢?我不敢确定,如果没有我们给中国船舶的话,是否有其他国家可以给他们船舶呢?
李滋罗斯1937年2月2日给比尔的信中写道:
蔡写给我一封很长和表现得很“滑腻腻”(soapy)的信,讲述招商局购船的细节。我十分同意你在报告中所说的,我并不想和蔡一同被卷入此事。因此,我给他回复了一封不提供任何承诺的信。
李滋罗斯1937年1月27日给蔡增基的信中写道:
我十分高兴地知道你为中国争取信贷所付出的努力,我希望情况会继续好转,这样会对在中国的投资者和与我们贸易的贵国政府都有所裨益。
我已从比尔先生处收到一份有关你对购船要求的报告,我相信你和他会保持密切联系,因为他对争取信贷的情况比较了解。
从以上信件的内容可见,英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比尔和李滋罗斯对蔡增基的印象都是负面的,无不认为他是“狡猾”之人。话虽如此,他们仍认为英国应该争取招商局这宗生意,可谓充分遵守了“在商言商”的原则,同时显露了老牌英国外交的手腕,即一面批评,一面则去着手应付。蔡增基因为要争取更长的还款期和更低的借款利息,不惜展开与包括英国在内的多方的谈判。目的很简单,为招商局争取最有利和最优惠的条款。笔者认为,1936年12月30日蔡增基写给李滋罗斯的信,无论在立场、措辞还是技巧等方面,都显露出他的智慧。蔡增基提醒李滋罗斯,招商局绝对有能力向第三方争取到贷款,英国无法控制所有的造船商。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信末更高调地提到将会采纳李滋罗斯对改革招商局的意见,成立有限公司,不过要在国营化过程完成后方可施行。①有关招商局实施国营前的经营管理问题,参见张后铨《招商局史(近代部分)》,第284—364页。该书作者对蔡增基的评价不高,主要基于抗战时期在香港的售船舞弊案,见张后铨《招商局近代人物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364—369页。不过,该案本身存在不少疑点,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这虽不是最令其满意的答复,因为他本人也没有充分的把握,但足以令李滋罗斯不再与他纠缠下去。
李滋罗斯对于蔡增基另起炉灶的策略可谓处之泰然,不愧是老练的英国银行家和外交家,他还不断提醒自己不要被卷入蔡和其他敌对阵营的谈判,充分揣测蔡的心理和动机。英国虽然愿意帮助招商局,但并非没有考虑将来招商局会可能成为英资航运公司的竞争对手。正如李滋罗斯在信中提及的,招商局的实力正不断壮大,在长江上游已稳住脚,终有一天会伸展到长江下游去,这样会造成与英国在华航运事业上的激烈竞争。李滋罗斯和英国政府官员并非没有察觉到招商局的发展潜力,事实上由庚子赔款委员会代购的4艘船已经付运,如果再加上现在蔡增基所要求的8艘,招商局的实力将会大大提升。不过,根据李滋罗斯等人的估计,招商局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有这样的能力。
四 招商局的购船借款信贷问题
彼德斯1937年1月26日写给船舶及保险经纪公司(Ships&Insurance Brokers)朗西曼的信中提到:
今早我收到蔡先生(指蔡增基)的一封航空信件,是1月9日从上海寄出的私人信件,内里说为了回复我1月7日发给他的电报,他已通过英国驻华商务参赞比尔向朗西曼先生发出电报,表示中国的交通部已同意为100万英镑的信贷做担保。蔡先生还补充说:“我们期待信贷定息为5%,与庚子赔款委员会提供的船舶借款条件相同,即有15年的还款期。”蔡先生说是次借款是以交通部的名义进行的。
你是否已从英国驻华商务参赞处得知此事?如否的话,我相信你很快便会从外交部收到正式的通知文件。
汇丰银行伦敦分行经理巴恩斯(O.J.Barnes)1937年4月21日写给李滋罗斯的信中称:
知道你关心我们银行上海分行在招商局问题上的损失,如果白池还未通知你的话,我特意呈上一封刚刚拟好的有关解决问题的信件,这封信是和另一封由孔博士(指孔祥熙)于3月31日写给亨奇曼(A.S.Henchman)的函件的副本一起寄出的。
正如你所观察到的,汇丰银行将会有不少的牺牲,但此后将消除我们经常和中方摩擦的来源,我们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
彼德斯1937年2月2日写给英国出口信贷保证局波伊尔(David Boyle)的信中提到:
可能你已知道蔡先生(指蔡增基)已通过上海的商务参赞向朗西曼先生发出一封与购船事有关的电报。
你能否告诉我英国政府是否已知道蔡先生所提出的要求?如果还没有的话,我将发一封电报给蔡先生,我将十分感谢你对蔡先生的回复所做出的评论。
相信你已知道法国于1936年底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历史上最大一笔借款合同的消息,借款金额高达国币3450万元,该笔借款将用作兴建成都至重庆的铁路。
1937年5月5日,英国外交部向上海英国驻华使馆发出电报:
如财政顾问李滋罗斯所说的,昨天接获汇丰银行的通知,他们尚未收到于4月1日到期的招商局借款的首笔分期还款。我已对孔(指孔祥熙)说这绝非正常做生意的方法,我们必须遵照协议的条款去履行责任,孔感到恼火并答应马上发电报去上海催促还款。孔声称麻烦是宋子文引起的,宋并不准许中国银行为招商局做担保,认为这样对中国银行的经营并无好处,我认为中方总要拿出一些方案来解决还款问题。
英国财政部专家白池(Edmund Hall-Patch)1937年5月7日发给外交部的电报中写道:
麻烦并不如孔博士(指孔祥熙)所声称的,宋子文和中央银行已采取最可行的方法去完成还款,由于招商局尚未授权汇丰银行上海经理亨奇曼把抵押品交给中央信托局,中央信托局未能与汇丰银行核证,以致无法发出还款用的本票或现金。我已催促所有相关部门尽快办好全部手续。又,已收到孔博士发来的电报,说在未来数天便可把现金和本票一并交给汇丰银行,以解决所有的还款问题。
招商局购船的清单已备,借款利息和还款期也已谈妥,唯一欠缺的是由谁来做借款担保。正如上文信件中所提到的,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人间存有间隙,但看起来李滋罗斯和蔡增基,甚至是英国政府各有关部门的官员,都没有利用孔、宋二人的不和去谋取利益。无可否认,国民政府内部并不团结,会对招商局的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至少在招商局购船借款的担保问题上,孔、宋二人就有不同的意见。最后,仍得由交通部来承担保证人的责任。
如果细心观察上面函件的内容,英方对招商局借款问题的处理还是十分灵活的,虽然汇丰银行是有所“牺牲”,把借款利息由6%降至4%,但所谓“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目的是再显易不过了,在支持招商局渡过难关的同时,去争取一笔巨额的出口信贷的购船贷款,使英国再次插足招商局业务,以保护英国在华的航运利益,这可以说是一举而数得。根据汇丰银行史专家景复朗(Frank H.H.King)所指,李滋罗斯曾向英国政府大事批评汇丰银行,虽然他无证据证明汇丰的“牺牲”和李的批评有任何关系,但汇丰愿意让步肯定是和李有关。①Frank H.H.King,The Hongkong Bank between the Warsand the Bank Interned,1919-1945:Return from Grandeu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401-402.无可否认,在蔡增基的管理下,招商局对汇丰的积欠果真于短短数年间由1600万元大幅减至1000万元。1937年2—4月,蔡成功从金城银行取得两笔合计815800元的借款,建造锦江轮、巴江轮和岷江轮三艘新船,②朱荫贵:《从轮船招商局的债款看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与英资怡和、太古洋行及日资日本邮船公司进行竞争,成为与英国借款谈判的唯一赢家,而这与蔡增基的努力密不可分。
五 结语
李滋罗斯对于1930年代的中国经济,影响并不限于币制改革,他在个别中国企业如招商局的经营发展上,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可惜过去学界并没有注意。李滋罗斯是英国政府财政部顾问,他与蒋介石夫妇、孔祥熙等人都有交往,应该说维持了不错的关系,李通过他们可影响到国民政府对招商局的决策。不过,他对蔡增基并无好感,因为蔡充分掌握了与英方谈判的技巧。蔡的方法是“一石多鸟”和“故弄玄虚”,一方面吸引英方在旧债未清的情况下向招商局提供购船借款,另一方面则要求降低旧欠的还款条件,使招商局能安然渡过难关,在达到扩张船队目的之余,仍可向汇丰银行还清欠款。事实证明这一策略是对的。像蔡增基这样能够懂得使用这样出色的谈判策略,为招商局谋取利益的人,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可惜过去学界对他的评价只集中于他抗战时期的舞弊嫌疑案。
值得一提的是,李滋罗斯和其他英国官员对蔡增基的评价,由最初的“狡猾”到后来的“滑腻腻”和“在没有足够出席人数的董事会议上讨论借款”,都值得深思。有关100万英镑的购船借款细节和与英方的谈判内容、过程,在蔡增基自撰的《招商局最近三年来之革新》和1976年出版的自传中均没有提及,就连李滋罗斯的回忆录中也难找到线索。③Frederick Leith-Ross,Money Talks:Fifty Year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London:Hutchison,1968.一般人以为是因谈判最终没有成功、贷款并无施行等,笔者认为这些看法都不对。蔡增基的真正目的,是逼使英方接受招商局提出重组汇丰银行旧欠的方案,使招商局在危机中仍能有喘息的机会来实行各种改革。结果,汇丰借款的利息由6%降至4%,招商局更可以分期的方式来还款。无可否认,汇丰是做出“牺牲”了,而汇丰的退让显然得到了李滋罗斯的支持。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如果没有李滋罗斯在背后积极推动购船贷款谈判,使之有竞逐者威胁性的心理去支持招商局不断修正借款的条件,恐怕蔡增基还是难以成事。从这个角度看,李滋罗斯可真是被蔡增基利用了,因此在李的回忆录中当然没有记载此事。
李滋罗斯对招商局的支持,可谓直接出于他增加英国对华贸易贷款的目的,从李的立场来看,蔡增基当然是英国的朋友。不过,李亦非盲目地支持招商局,他也考虑英国在华航运利益的各种问题。万一将来招商局有能力与英资航运企业竞争的话,蔡自然是英国的敌人。至于蔡是如何把招商局的局面扭转,为何出现“在没有足够出席人数的董事会议上讨论借款”这一情况,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不过,这已超出本文范围了,有待将来撰文另加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