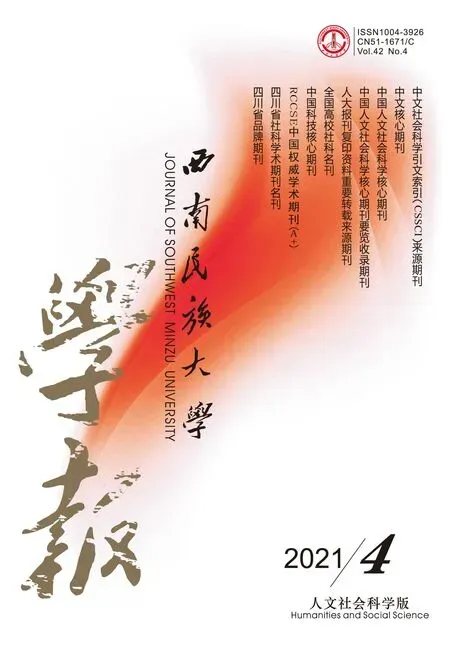焦点变换的多重观看与对象的立义游戏
——以贾斯培·琼斯的艺术品为例
2021-04-17肖伟胜
肖伟胜
[提要]作为从抽象表现主义向波普艺术过渡的关键性人物贾斯培·琼斯,他对基于浪漫主义主观假设之上的抽象表现主义深表质疑,决心在作品里摒除自己的情感、品位和记忆,从而在绘画上形成了一种明显的非内省性的风格。在早期的《国旗》《射击靶》《白色大数字》《错误开始》等作品中,琼斯主要采用图画、文字或数字来呈现他与对象之间的立义游戏,而在后期近似杜尚现成品的《着色的青铜》《傻子的房子》《根据什么》等作品中,则采用将普通物品装配到不同语境的方式来实现物品的功能或语义的转换。这些作品围绕着“变化的焦点”的构图方式使观众随着焦点的变换而看到同一事物的不同面向,琼斯通过建构出这样一个观众与对象立义的嬉戏空间,从而凸显了观看活动中对象立义的复杂性及其意义的多重性。
杜尚以术语“现成品”来描述他选择、购买批量生产的普通物品,然后在上面题字签名,并界定它们为艺术作品。自从这种原创性的新的艺术种类出现后,它就一直引发着人们这样的思考:在各式各样的物品中,什么决定了艺术品的独特属性?是艺术品自身内部的东西,还是艺术家围绕物品所进行的创作?这些问题不断回响在二战后新前卫派的艺术实践领域。二战结束后的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是抽象艺术在欧美艺术界走向极盛的时期。为了追求审美形式上的自律性,抽象艺术家们的工作越来越极端,不但放弃了来自现实生活中的经验,也放弃了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最后在作品中留存下来的只是形式上的色彩、线条和结构,这是按照格林伯格现代主义绘画追求“纯粹性”原则自然发展的结果。对于他来说,纯粹性原则能够有效地防止不纯粹的现实信息或者庸俗文化侵入艺术的领地,使得现代主义绘画能够摆脱模仿性和文学性在绘画和雕塑之间带来的混乱,从而捍卫绘画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内部独有特征即平面性和媒介性,进而维持自身的“精英文化”特色。不过,抽象艺术的纯粹性原则会导致不断追求形式简化,这必然会带来一个绘画的逻辑问题:如果形式不断简化下去,那么是否最后空白画布也就成为一件作品呢?格林伯格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一张绷着的空白画布也可以成为一件绘画作品”,但是它不一定是一件好作品。[1](P.153-154)虽然一块绷着的空白画布完全符合格林伯格定义的抽象原则即平面性、纯粹性和媒介性,但它显然已经突破了绘画的二维平面进入到了第三维,正如格林伯格式抽象艺术简化到了这地步,这块绷着的空白画布也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现成品,一个物体了。这样,追求纯粹性的抽象艺术推进到极端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它们可以转变为任意物品,这或许是绘画的零度,也预示着抽象艺术发展到了内在动力已完全耗竭的地步。
一、集合艺术对“历史前卫”艺术的突破和超越
对抽象艺术的突破主要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乌尔里希·莱瑟尔写道:“在形式范式多样化的魔力笼罩之下,另一种意识形态在50年代中期渐渐深入人心,它试图摆脱形式跨栏跳的角逐,导致现代主义丧失根基。”[2](P.6)它突出表现在一些艺术家开始重新对现成材料和拼贴法产生兴趣。拼贴法是由立体主义艺术家毕加索和勃拉克于1912年所首创,他们把纸片、布片等生活中日常之物的碎片粘在画布上,抨击绘画的模仿作用,强调将“实相”置于画面上。而对现成材料的运用意味着一度处于潜隐状态的杜尚重新出场,他很快成为此时年轻一代艺术家的精神领袖。1961年在美国纽约现代美术馆举办的一个名为“集合艺术”的展览,最能体现这方面的艺术旨趣。在这次展览的前言中,策展人美国批评家威廉·C·塞茨正式提出了“集合艺术(也称为装配艺术)”的概念。“Assemblage”这个词在英语中有“集合、集成和装配”之意,他对这种艺术形态所作的解释是:“首先,它们主要是装配起来的,而不是画、描、塑者雕出来的;其次,它们的全部或者部分组成要素,是预先形成的天然或人造材料、物体或者碎片,而并不打算用艺术材料。”[3](P.599)本次展览包括立体主义的拼贴和装置作品、达达主义的照相蒙太奇、杜尚的现成品以及达达派、超现实主义的实物拼接和二战后出现的废品雕塑、装置作品以及绘画拼贴等。这些艺术品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像抽象艺术为了追求形式上的纯粹而完全排除来自现实生活的经验,而是试图通过物质形式上的变化,重新调整艺术与现实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对于材料的并置、罗列,并由此将观众的视点吸引到这些材料所体现出的生活背景上去。正如塞茨在展览的前言中所说的:“当前的装配潮流……标志这样一个转变:从一种主观的、易变的抽象艺术转变为一种与环境修正过的关系。并置法是表达清醒情感的一个工具,它使用的是老套的国际惯用俗语——表达不缜密的抽象往往就变成这样的俗语,还使用这种形式所反映的社会价值观。”[4](P.106)因而,集合艺术不仅代表从抽象表现主义到明显不同的波普艺术观念的创作手法的转变,而且它还代表了对视觉艺术创作形式进行激进式的重新审视,进而成了后来环境艺术和偶发艺术的起点。
在“集合艺术”概念中,“集合”一词有两个重要观点:其一,无论多少确切的图像与物品被结合在一起构成艺术品,这些图像和物品从未丧失它们源于日常世界的功能性身份;其二,如果一个人毫无顾忌,艺术和日常生活的连接性使他可以使用很多迄今为止和艺术创作毫无瓜葛的材料和技术。[5](P.12)这两点实际揭橥了包括“集合艺术”在内的新前卫派与二战前艺术流派的重要差别,如果说二战前的历史前卫艺术所采用拼贴法是出于审美的目的,也就是那些被纳入艺术品之中的图像与物品的功能性身份要发生形式上的嬗变,而在新前卫艺术中不仅要保留和尊重这些图像和物品本身的质感和物性,而且还要使画布、颜料具有物质感和存在感,如此一来,先前那些被认为根本没有审美价值的材料和技术也可以纳入艺术品中,同时对媒介的物质性的强调,带来了传统绘画中图—底关系的终结,这实际上已销蚀了绘画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边界,“虚构这一在绘画作品中一直必不可缺的定语被推翻,感知的视觉确定性被质疑”。[2](P.7)事实上,这些新前卫艺术品的衍生最初来自于对绘画这一媒介新的表达的可能性之尝试,并直至这一艺术类别开始土崩瓦解,最终架上绘画被实物所取代。这种艺术上的探索尝试始于杰克逊·波洛克突破画框的行动绘画,经由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的美国图像《国旗》和《射击靶》,直至罗伯特·劳申伯格的保留为白色的画布《白色画》,阿德·莱因哈特的《黑色画》和弗兰克·斯特拉的成形画布。难怪蒂埃利·德·迪弗对此解释说:“早期的极简主义在格林伯格的地盘上与格林伯格战斗,他们把绘画推进到第三维,这些作品确实在三维中变成了物品。在现代艺术的历史上,这当然不是第一次出现单色画或者准单色画。每一次,它的出现都清楚地说明绘画的零度。”[6](P.180)
二、对象的立义游戏与非内省性风格的形成
作为从抽象表现主义向波普艺术过渡的关键性人物贾斯培·琼斯,对于基于浪漫主义主观假设之上的抽象表现主义的看法提出了疑问,在一次对本体论不言明的攻击中,他“将人重塑为信息之间的联系,重新调整信息输入,而不是创造信息内容。”[7](P.207)到1950年代末,对于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来说,人类的头脑开始像一个复杂处理“自然”的电路板,同时“自然”越来越是事物本身的表现以及对事物的表现。这种意识的激进转变典型表现在麦克卢汉的说法“媒介即讯息”之中,[8](P.18)所谓“媒介即讯息”的意思是:媒介使我们的感官的形貌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新的媒介的使用会引进一种新的尺度,它将会派生出一些心灵习惯,从而会改变我们的意识,进而改变我们理解和构建周围的世界的方式,而这种方式的一部分是由我们用来描述世界的语言建立起来的。这种专注于表达媒介的自觉使琼斯将绘画作为语言的叙述来进行创制,他所画的都是数字、星星、旗帜、地图等,这些“脑子里固有的”形象表达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汤姆金斯看来,琼斯和劳申伯格作为抽象表现主义之后的第一代艺术家里最有天赋也是最具创新性的两位,他们俩和约翰·凯奇以及默斯·康宁汉都有过深厚交情,虽然艺术手法各有不同,但他们的美学观点和凯奇有许多共同之处。在二战后年轻一代艺术家里,凯奇可以说是艺术领域内除杜尚外最有影响力的精神领袖。这位前卫作曲家在创作和教学中提出的艺术概念不亚于他的实验音乐,他所提倡的随机艺术的概念可以说与抽象表现主义背道而驰,他不主张艺术要强调艺术家的个人“笔痕”和其内心深处的感受,而倡导一种“无自我艺术”,要求尽量排除艺术家的个性,人们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发现艺术,使艺术成为一个永恒持续的过程。此外,艺术的目的是“无目的的玩耍”,这个目的会使艺术家和大自然步调一致——我们要同步的并不是大自然的表象,而是大自然的运行方式。[9](P.429)1952年来到纽约的年轻琼斯,在两年后的春天认识了凯奇和劳申伯格,才成为了艺术圈的一员。他1954年留下的作品显示出他对当时即兴组合或者废品艺术美学的兴趣。当有人指出他的作品跟德国达达派的库尔特·施维特斯(Kurt Schwitters)的作品相似时,琼斯毁掉他所有的作品然后重新开始。他把这看作是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我决定只做我想做的,而不是别人做的。当我观察到别人做的,我会尽力将它们从我的作品中消除。我的作品是在不断地否定冲动……我做的事是发现我所做的是别人没有做过的,我是我自己,而别人不是我。”[7](P.210)
深受凯奇和劳申伯格影响的琼斯,也希望自己的作品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而非它的仿制品,他也决心在作品里摒除自己的情感、品位和记忆。在绘画上,琼斯形成了一种明显的非内省性的风格,这种风格强调艺术品复杂的符号学,也就是关注它怎样表达它所意味的东西,符号和艺术之间的区别成了他聚焦的主题。琼斯在创作于50年代的系列画《国旗》《射击靶》和《地图》或数字和字母画所充分演绎的,是看似简单却又惊人的他与对象(由物和画组成)之间立义变换的游戏,并最终关涉到他对自己艺术手法所进行的反思。例如,在《有石膏模型的靶子》这件作品中,琼斯用新闻报纸打底,在上面涂了几层薄薄的蜡,底下的新闻报纸依稀可见,这让一些观者尝试去解码那些报纸上的文字。但由于文字只是依稀可辨又不足以支持图像学的解读,这种中间模糊状态往往带来观者在文字的语义与它作为印刷字体之间来回折返。对于这种体验他曾说:“印刷的无论是什么对我都不重要,有时候,我看报纸是为了看不同的色彩,不同印刷字体的大小,当然,一些文字也可能钻进我脑子里,但我对此毫无感觉。”[7](P.209)正如画中的靶子一样,它是如此忠实于实物,但艺术家又是很明确地用艺术材料描画而成,那这靶子到底是实物还是绘画艺术品?此外,作为绘画的靶子同样也具有现实靶子的功能,这种相似性揭示出艺术意图在定义一个物品为艺术品中所担当的角色,创作者(包括观者)既可以将其展现为绘画作品,也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具有现实功能的靶子,这完全取决于你看取它的意图而定。事实上,靶子是一种测验,琼斯以一种不动声色的讽刺态度对待之,想测验一下人们期望艺术品干什么。一幅画出来的靶心图,等于自动否定了真靶的用途,一旦以艺术的眼光来看靶子,那么它就是一种统一的艺术符号,成为了一个形象的靶子,它的实际用途自然就没了。对于这种立义转换替代的游戏,我们对此并不知道得很清楚,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需要思考的问题。
琼斯所做的在他与对象之间立义变换的游戏在国旗画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国旗画以多种变异一再出现在其作品中。国旗跨越了琼斯的整个职业生涯,他的第一幅《国旗》画是用蜡彩画技法创作的,这是一种古老的技法,将溶解于蜡的颜料分好几层热热地涂抹到画布上。他所描绘和展现的其实是在摹仿性地描摹包括48颗星和13根横条的美国国旗。就像《射击靶》中的靶子一样,国旗是如此忠实于实物,与此同时,它的功能被颠覆。它并不迎风招展,而是像紧绷的画布一样僵硬,画布上只有蜡彩画技法所造成的错觉效果暗示着旗帜的飘动。这幅画既没有象征含义的横向关联,也没有任何信息提供给观者,只有题材和色彩呈现。对此同样的疑问是:人们看见的是什么?是具有象征意味的代表美国的符号、抽象画,还是一面实物国旗呢?作品《三面旗帜》里面的国旗,重复了同样一个很平淡的主题,它来自一个现成的形式图像,而不是一个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特殊的实际物体。画中最小的国旗在空间中处在前面,同时在感觉上它又按国旗大小递减的顺序往后退。超厚的三层画布让《三面旗帜》更像实物,而不像早期的旗帜绘画,但是,通过将画布的边缘处理成跟图像一样,琼斯消除了任何意义上的构图感,而只留下对表面的处理作为形式解读的基础,也就是它强调了更多的图像平坦性。费恩伯格指出,乍一看,琼斯的这些作品的笔触与图像的表面意义是冲突的。艺术家不仅使用感官触觉的、姿态的风格,而且用蜡彩画技法进一步突出了每一笔触的特征;因为融化的蜡几乎瞬间凝固,它可以让每一笔触保留其特征,不会在后一笔涂抹下被擦得模糊不清。不过,尽管旗帜和靶子留存着表面上的感性,它们却有预定的严格秩序,而其他的只是网格,甚至每一个单独的笔触相互之间有一种冷静的独立,而不是自发的互动,这就使画面不能传达一个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画布上那种强烈的内省性情绪。很明显,琼斯故意与抽象主义保持着距离,“我不想让我的作品曝光我的情感。”[7](P.210)他如是说道。鉴于这一点,阿纳森提出应该把他与劳申伯格列为一类艺术家,因为在探索新题材包括美国日常生活的形象方面,在创造新的或者使人印象深刻的推陈出新的观察方式方面,以及在艺术本质的再思考方面,他们两人的作品都有着重要意义。[3](P.622)
不管是琼斯所绘制的靶子还是系列国旗,他的用意都在于揭示这样一个事实:画可以使任何东西变得抽象,连一个像美国国旗这样高度充满意义的主题,也可以被弄得很抽象。尽管条纹的绘制表现出制图般的精确,但它已没法在空中飘扬,它凝止不动,它的平面是艺术的平面,而非布匹的平面。在画与它意欲“再现”的旗帜之间,并无实际差异。可以说,在琼斯这些作品中,媒介与信息之间的距离,几乎——但尚未完全——缩减至零。[10](P.429)后来琼斯也一直偏好现存的、与习俗紧密相关的题材,或者说那些不属于任何美学等级秩序的平凡之物,例如数字、地图、灯泡、手电筒、温度计、啤酒罐、扫帚等,使观者得以专注于他所见。他以现成品诉诸观者的感知能力,并模糊销蚀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界限,尽管不像杜尚那样以智性杂技方式推动他与对象之间的立义游戏,但他其实也是把每个物体视为潜在的现成品,进而寻求物质世界里观看感知的复杂性和矛盾,试图在他的作品中捕捉这种世界的纯粹多样性,以及智性观念中事物之间不会间断、不会枯竭的可变性。不管是早期的系列画《国旗》《射击靶》《探戈》,还是随后的《错误开始》《傻子的房子》《根据什么》等作品,都是围绕着上述主题进行探索描绘。如果从现象学认识论角度来看,琼斯实际上是在探究对象被感知的各种方式,而对每一个对象的不同立义方式会带来诠释的多重可能,这往往使对象的意义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就拿《射击靶》来说,我们对于所绘制的靶子的画作来说,一般把画中的靶子视为对现实靶子的模仿,这实际上是将它立义为靶子的图像,现象学上将这种意向性行为称为图像意识。在胡塞尔那里,狭义上的图像意识意味着与图像(Bild)有关的意识,是指在观看照片、图画、影像等以图像为基本表意符号时的意识体验。①它作为一种认识经验,不同于知觉、想象以及符号意识,是一种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的非直观行为。“图像意识”也被胡塞尔称之为“图像表象”(Bildvorstellung)。较之于“感知表象”,它已经不是素朴的意识行为,因为在它的本质结构中包含着多个对象和多种立义。这些对象和立义相互交织,它们随注意力的变化而得以相互替代地出现。在图像感知的整个过程中,它包含着三种客体,即(1)物理图像或物理事物(das physische Bild,英文:physical image),(2)图像客体(Bildobjekt,英文:image-object)与(3)图像主体(Bildsujet,英文:image-subject)。这三个客体构成“图像意识”的“图像本质”。与三个客体相对应的是包含在“图像意识”中的三种立义,即(1)对“物理图像”的感知立义,(2)对“图像客体”的立义,(3)对“图像主体”的立义。这三种立义分别代表着“图像意识”中的“图像事物意识”、“图像客体意识”和“图像主体意识”,并且构成“图像意识”的总体组成。[11](P.101-102)
这里首先以《射击靶》为例,来看看将所绘制的靶子立义为一幅关于它的图像,在这种图像化的立义行为中所特有的层级结构:第一个客体即物理的图像:打底的新闻报纸、颜料色彩、形状尺寸等。这一图像的客体是物理层面上的感性之物,只有在我完全滞留在通常的、朴素的感知上,也就是在专题地把捉图像物,仅仅把这幅关于靶子的画看作世间之物时,它才显现出来。这种立义基本上是一种正常的感知立义,在这种感知立义中,这幅关于靶子的画呈现出一种被胡塞尔称作“自在的符号”的物性特质,如同一颗树、一座桥或诸如此类的东西。第二个客体是图像客体,它是“展示性的客体”。在对这幅画作的感知中,这个展示性的客体就是画中的靶子。它是通过“物理图像”而被体现或被映像的那个对象,与前者相比,它是一种“精神图像”。胡塞尔之所以将它视为“精神图像”,是因为这个展示性的对象即靶子不是作为一个感知对象显现出来,而是显现为一个图像形式的非感知对象。换言之,只要我们把这幅画看作是关于靶子的图画,那么我们不会将画中的靶子感知为现实存在或不存在的靶子,而是将它感知为现实存在的靶子的图像。但这种感知由于“缺少”存在设定的特征,所以这种感知并不关注靶子的现实性特征。用胡塞尔的话说,“这个建立在感性感觉之上的立义不是一个单纯的感知立义,它具有一种变化了的特征,即通过相似性来展示的特征,在图像中观看的特征”。[12](P.207)图像意识中的靶子的显现不同于本源性感知中具体有形的显现,而是通过一种“感知性的想象”,也就是在一种“感知性的当下化”中立义为某种展示性的东西,所以它是一种作为“精神图像”的“显像客体”。第三个客体是图像主体,它是“被展示的客体”。在《射击靶》这幅画中,也就指通过“图像客体”所意指的实在的靶子。按照胡塞尔的说法,图像主体是图像意识行为中“所意指的客体本身”,它仅仅通过想象在图像客体中被意指,所以它本身不在图像之中。换言之,对图像主体的立义是想象性的立义,但却不是正常的想象性立义,而是一种非显现的立义,这意味着图像主体是作为图像客体的“观念的相关物”,而没有任何显现与它相符合,因此只有图像客体显示出来。在图像客体和图像主体之间存在着图像与被展现者的关系,胡塞尔说:图像客体并不是简单地显现出来,而是在它显现时还有某个东西被带出:图像主体。[12](P.210)换言之,作为图像主体的实在的靶子是在它以图像客体显现时被带出来的,因此,通过感知性的想象而展示的图像客体即靶子,不同于这个图像意识中真正意指的那个绝然对象即靶子本身,在这种图像感知中,实在的靶子仅仅通过这幅绘制它的画而被唤入意识之中,并且在这个图像中一同得到展示。
综上所述,《射击靶》这幅关于靶子的画作所特有的层级结构:物理图像唤起图像客体,而图像客体又表象着另一个图像:图像主体。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对这幅关于靶子画作的图像意识结构:这幅关于靶子的画作(物理图像)是关于靶子(图像主体)的图像(图像客体)。在《射击靶》这幅关于靶子的画作的图像意识体验中,我们的注意力主要朝向作为图像客体的靶子,也就是既不能专注于作为物理图像的靶子,也不能朝向作为图像主体的靶子。不过,如果要实现对这幅关于靶子画作的图像意识,由于图像意识是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的非直观行为,那么作为图像客体的靶子与作为图像主体的实在靶子必须具有相似性,“图像通过相似性而与实事相联系,如果缺乏相似性,那么也就谈不上图像。”[13](P.53)也就是展示的图像客体即靶子与它一同被带出的图像主体,也就是图像客体的“观念的相关物”即靶子本身,二者必须是相似的才能联系在一起,否则就谈不上是图像意识。但另一方面,图像客体虽然必须与图像主体相类似,但一个是作为图像感知意向行为的“内容”或“意义”,而另一个是通过这个“内容”而相关于“它的”对象,因而它们二者不能完全相同一。胡塞尔认为,“如果显现的图像在现象上与被意指的客体绝对同一,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图像显现在任何方面都与这个对象的感知显现没有任何区别,那么图像意识也就几乎无从谈起了。”[12](P.211)
事实上,在对这幅关于靶子的画作的图像意识体验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立义方式:针对作为物理图像的靶子,使用的是正常的感知立义,将其立义为感知对象;针对作为图像客体的靶子,由于它使用的是一种“感知性的当下化”,因而被立义为一个“精神图像”;针对作为图像主体的靶子,它虽然是一种想象性立义,但却不是正常的想象性立义,是一个非显现的立义,所以在这个立义中,它并不显现出来。很显然,较之于“感知表象”素朴的意识行为,在关于靶子画作的图像意识本质结构中,就包含着多个对象和多种立义,并且这些对象和立义相互交织,它们会随观者注意力的变化而得以相互替代地出现:这幅关于靶子的画作既可立义为是一件具有物理性质的普通物品,即现实中的靶子,也可以立义为是关于靶子的图画或图像,还可以立义为是关于实在靶子的简捷表象,即那个绝然对象——靶子本身。在琼斯的系列画《国旗》《地图》或数字和字母画中,实际上都揭示出对象可以被各种方式所感知,从而显示出对象意义的多重性,琼斯一直被这种不同立义方式带来意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所吸引。例如,在创作于1958年的作品《白色大数字》中,画面由从零到九的11排数字组成,数字描画得颜色浅淡,却可辨认。在这幅画中,琼斯把注意力放在了数字作为字母本身的感性特征上,因而不关注数字作为符号表象的语义内涵,正如《射击靶》中那些作为打底的新闻报纸上的文字,他关注的是这些文字作为印刷字体的大小或颜色,而不是它们作为符号表象的语义内涵如何。不管是数字还是文字,它们既可被立义为符号表象,也就是专注其语义内涵,这是对于这类符号一般的立义方式,也可以仅仅朝向单纯作为声响或形状构成物的文字或数字,也就是仅仅朝向感性之物,这样数字或文字便不再是表意符号,而至多只是被胡塞尔称作“自在的符号”的东西,例如书写的数字本身、被印刷出来的文字本身。从它们仅仅是感性之物转变为表意符号,存在着胡塞尔所谓的“体验的意向性质的改变”,尽管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作为感性质料的文字或数字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但意指它们的行为却发生了本质变化,也就是观者对这些感性质料的赋义行为发生了改变,正是由于这种立义方式的改变带来作为对象的文字或数字像变戏法一样交替显现。②
我们大致可以说,琼斯在《射击靶》中主要关注图像表象的立义行为,而在《白色大数字》中偏重于探究符号表象的立义行为,而在《错误开始》这幅画中,他将意识的这两种立义行为混合在了一起,更为集中而复杂地关注对象被各种方式感知而带来意义的多重性问题,当然对此问题的探讨是以油画的形式呈现出来。在创作于1959年的作品《错误开始》中,琼斯用了油画而不是过去他习惯涂在报纸上的蜡画,或许是油画允许更自由的姿态风格。琼斯将表面画成相互穿透的三原色,即红、黄、蓝编辑的网,然后把颜色的名字用模板印出混在其间。在这幅画中,红、黄、蓝三种颜色各自凸显自身,并未产生构图上的互动,每一种颜色尽管既可以立义为作为实物的颜料,也可以立义为关于红或黄或蓝的图画,此外还可以立义为这个图画的“观念相关物”,即那个绝然对象——红或黄或蓝本身。但一般情况下,观众对于这三种颜色的立义通常是第二种,也就是把它立义为是一幅对红或黄或蓝的图画。这种立义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图像表象意识体验,而对于像《白色大数字》或单色画《庆典》中一样的数字或文字的立义,也就是说,观众对《错误开始》中表示红、黄、蓝颜色相对应的名字RED/YELLOW/BULE通常立义为符号表象,注意力放在这些名字即文字的语义内涵上,当然也可以将这些名字作为印出来的字母来进行立义,也就是关注其本身的感性特征,仅仅把它们作为各颜色立义基础的质料来看取,此外还可以从图像表象来立义。由于这些字母本身又涂抹着不同的颜料,而且字母涂抹的颜色和字母的语义之间并不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就拿名字RED来说,它作为模板印出来的字母在画中涂抹成或红色或黄色或蓝色,其他名字YELLOW/BULE同样如此。这就带来了或许第一层错误,观众以为表示RED的名字应该是红色,结果它可能绘成黄色或蓝色,其他两个表示颜色的名字也面临着同样情况。此外,这些用模板印出来的颜色的名字混在三种颜色之间,它们可以作为符号表象来立义相对应的颜料,从而形成一种语义关联,这就带来第二层错误,观众以为表示RED的名字指涉的应该是红的颜色,但其实在画中与它貌似存在语义关联的既有红的也有黄的或蓝的,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三种颜色名字作为字母本身涂抹颜色的不同,加之它们混杂在三种不同的颜色之间,与各种颜色之间存在或不存在着语义关联。换言之,在作品中纳入颜色的名字,但又没有用该颜色来绘出,甚至在颜色名字周围也没有使用,这样一来,三种原色加上表示它们的名字,均有各自不同的立义方式,这样对象和立义相互交织,必然会带来意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呈现一幅非常复杂的斑驳图景。因此,这幅画通过将符号表象和图像表象混合在一起,这些文字提示(红、黄、蓝)与人们所见的颜色不符,它强调了名字和视觉感觉(在人所知道的和人所看见的)之间的不和谐或错位。琼斯同年创作的《温度计》与《错误开始》有着类似的观念,画中有一样的色彩和姿态应用的星状放射图案,在一个真实的温度计两边用模板印出来大量的数字,在构图中心拉紧。不过,琼斯没有把三原色名字编进无景深的立体主义的网格,它有效地消除了构图的运动,在画面中心形成一个完美对称的拉链。在这些画作中,这一简单而有意识的误导或多种立义方式带来文字或数字意义的模糊和不确定,反过来质疑画家本身的艺术手法,尤其是通过绘画进行再现式描摹的可能性。
三、现成品语义的转换与观看感知的复杂性
1958年琼斯发现了杜尚的作品,对他来说,杜尚的现成品意味着每一件物品都可以是艺术,就像对凯奇来说每一种声音都可以是音乐并自我完善。在杜尚的影响下,他开始采用平凡的日常生活用品和消费品,包括可口可乐瓶子、啤酒罐、手电筒等,创作了如《着色的青铜》《傻子的房子》等近似现成品的艺术。在《着色的青铜》这件雕塑品中,乍一看以为是真的两个淡啤酒罐,不过观众能看到它们的手工制作模样,同时啤酒罐的青铜颜色添加了额外的青铜铸造的模糊性,此外每一个淡啤酒罐和它的底座作为单独物体分别铸造,然后用大部分看不清的、绘画方式的风格画上标签,在底座上摁有琼斯的拇指印,就像那些绘制的字母一样,观众逐一巡视完这件作品,就会发现它一开始能有效地给人以真的错觉,随着其手工修饰痕迹的凸显这种错觉会逐渐消失。如果将这件雕塑品与杜尚的现成品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其制作的流程与现成品存在着一致的地方,随意选择一个日常普通之物,然后再在上面题字签名。只是在这件作品中,虽然选取的是一件琼斯平时常喝的啤酒的罐子,但这个啤酒罐经过了手工上的诸多“修饰”,或者说作者制作它比杜尚的现成品多了较多的手工制作环节。其中相当于现成品中“题字”的标签是绘制上去而不是直接写上去的,同时作品确实是以雕塑品的样子制作的,对选择的物品手工的“雕刻”非常明显,不仅画有标签,还专门制作了雕塑的底座。至于作者的签名是用手工制作的一个拇指印而不是直接写上去,这些不同或许是作者强调雕塑的手工制作特征,与机器制作的物品即真实的啤酒罐形成对比。但琼斯的本意更多是激起观众首先去思考作品中的淡啤酒罐是否是它们看起来的样子,它们到底是艺术品还是普通寻常的物品?“我喜欢人们将一个认为是另一个的可能,”琼斯解释道:“但是我也喜欢。在经过一点审查后就很清楚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7](P.214-215)在《傻子的房子》作品中,那个吊在上面的扫帚和悬挂在下面的杯子,尽管不像淡啤酒罐那样在似与不似之间,但至少会激发观众去思考作为油画上的扫帚或杯子,到底是视为真实物还是作为艺术品中的象征物来看待?在这些率波普艺术风气之先的作品里,出现了物品在不同语境中身份和定义的转换,他对此解释说:“我认为对象本身就是一个有点含糊不清的概念……一个人在看一件事物时能不能转移一下关注点,让事物处在别处或者根本不在那里。”[7](P.216)很显然,他改变了早期作品中用图画、文字或数字来呈现他与对象之间的立义游戏,而采用将普通物品装配到不同语境的方式来实现物品的功能或语义的转换,对于物质世界感知的复杂性和矛盾的主题依然贯穿在这些作品中。乌尔里希·莱瑟尔指出,在这些画作中,艺术与现实的二律背反被重新审视,现实的碰撞所带来的冲击造成了某种感知困境,这一困境由平凡之物的魅力所引发,却不能告知魅力背后隐藏着什么,显然其中并不存在对物的客观观照。这些画作中的图像实物也激发出观众的不同视角:乍一看俨然是赞同态度,并且浅显易懂,细看之下才会发现,它们既非全然是象征、描摹,也不完全是实物。[2](P.70-71)这种似与不似之间的物品呈现游戏,如同前面同一质料以不同立义方式会形成不同表象一样,琼斯说,绘画应该是一种“人们可以在愿意的时候去单独体验的事实……因此,人们对它的体验是可以变化的。”[7](P.210)可以说,他的作品一方面关注观看方式本身的复杂性,同时也强调对象显现的多重性,这实际上是观看活动的一体两面,只不过一个是基于观看主体的视角,另一个是从观看对象的角度予以考察而已。
创作于1964年的《根据什么》是另一幅重要的、壁画尺寸的作品,在最左边的画板上,琼斯固定了一小块画布。在画的左上角,琼斯放置了一个头朝下的真实椅子的横截面,上面又坐着一个大腿以及屁股的模型。下面有杜尚的剪影,脸朝下对着这件作品的更大的画面。这揭示了小画布的背面,琼斯在上面题写了日期、他的签名和标题“根据什么”。其中的绘图观念显然有借鉴杜尚现成品的成分,不过这不是一件现成品,只是将现成品的制作转换成了油画的部分内容,在这幅画中,琼斯关注的依然是观看的感知复杂性。他对于画中杜尚的剪影做了这样的解释:“影子会随着作品周围情况而变化……每一件东西都因为某件事而变化,而我是试图制造情况从而引起事物发生变化。”[7](P.218)因此,这幅画为眼睛改变焦点提供了可能性,换言之,它围绕着“变化的焦点”的构图观念让观众处于他/她所在的现实的位置上,朝不同的方向去看,而不是让观众进入一个幻觉的空间,从一个人为的单一的角度来观看。观众不同朝向的注意力也就是不同的焦点会看到同一事物的不同面向,换言之,观众对于同一质料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立义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对象来,琼斯对此解释说:“我们朝某一个方向去看,我们看见一个东西,我们朝向另一个方向去看,我们又看见另外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称之为‘东西’的东西变得非常难以捉摸和非常灵活……它涉及我们集中注意力的方式。”[7](P.218)
结语
现代艺术家,从古斯塔夫·库尔贝到纽约画派,都曾尝试使他们的媒材越来越透明,从而作为他们形而上学观念或主观情绪的载体,希望观众体验到一种顿悟,一种超越所有物质的纯精神活动。作为集合艺术家的琼斯转到了相反的方向,他在真实存在的东西面前停下来,瞩目于艺术品的物理存在以及艺术品各个方面的具体性。这种对于画面感性的诉求,让艺术家似乎更接受他周围的世界,于是,他要全身心地去体验和理解他周围存在着什么,而不是去记录内省的行为或者透过媒材玄想什么,这实际上是要尽量呈现对象被各种方式感知的可能性以及经验的多重复杂性。琼斯告诉大卫·西尔维斯特(David Sylvester):“意向涉及我们的意识、头脑和生活中的一小部分,我认为绘画应该包括更多经验而不单单是意图的表达。”[7](P.210)正是立足于艺术品的物理存在以及艺术品各个方面的具体性,琼斯的作品提供了观看活动中对象立义的复杂性及其意义的多重性,换言之,由于观看感知的复杂性和矛盾,使得作品中呈现的对象具有多样性,这样一个观众与对象立义的嬉戏空间,同时在其中物品的感性特征又被凸显出来,这个空间就变成了一个对象语义相互指涉缠绕的世界,它既不会被画框外的有形世界所主宰,也不可能被艺术家的意图所左右。事实上,琼斯的作品引发人们关注认知、记忆和完整性的问题,通过绘画,他观看周围的事物,在这个具身性过程中让一个视觉事实转换至另一个视觉事实,这种本能过程强调观看本身的切身体验以及在观看中感受活力,诚如他晚年所说:“人们想从画中得到一种生活的感受。这种最后的示意或者说最后的声明,不应该是有意的,而应该是不由自主的。它一定是你不能说的,而不是你准备好了要说的。”[7](P.221)
纵观集合艺术家(也是原始波普艺术家)贾斯伯·琼斯的整个职业生涯可以发现,他绘画中关注的观看感知的复杂性、对象意义诠释的多重性,以及“变化的焦点”带来的具身体验等议题,很明显直接影响到弗兰克·斯特拉的条纹画以及后来的极简主义。同时他欲将主客体在问题重重的视野中融为一体的种种努力,对于文字、数字、星星、地图等日常普通物品的大量使用,对六十年代的美国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正如批评家马克斯·科兹洛夫所指出,琼斯把他的旗帜和靶子缩减成“不过是被赋予了社会用途的抽象形式,但现在把它们错置在新的语境下,其社会功能就没有了。就从这一惊人的洞见中,产生了波普艺术的动力和大量具有象征特性的抽象作品”。[10](P.430)从某个意义上说,琼斯的作品永远意在面对大众文化环境为绘画而辩护,这种辩护在六十年代,对美国艺术家来说,无疑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艰难。
注释:
①“图像意识”的德文是Bildbewuβtsein,英文是image-consciousness,它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我们把所有与图像有关的意向行为叫做广义的图像意识,它不仅包括以照片、图画、影像等为对象的图像感知行为,也包括了本源性感知和简捷性感知的表象直观行为,甚至还包括非直观的符号表象行为,而主体方面也相应地存在各自不同的立义方式。而狭义的图像意识,是指在观看照片、图画、影像等以图像为基本表意符号时的意识体验。参看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0-102页,另参看拙著:《视觉文化与图像意识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②对于符号表象的意识体验过程,相关内容参看拙著:《视觉文化与图像意识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