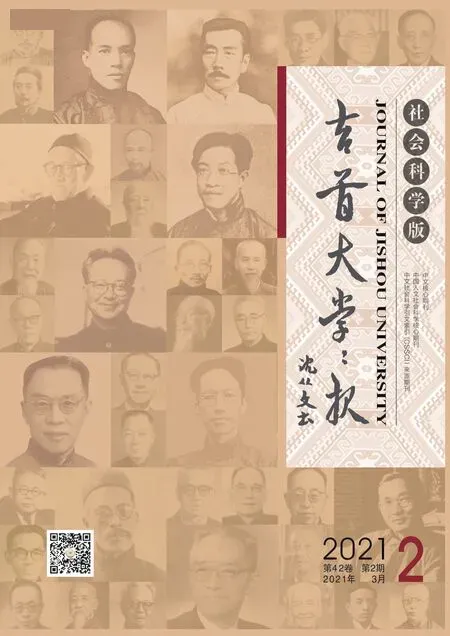《文选》“杂诗”类文体内涵*
2021-04-17田雨鑫
田雨鑫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杂诗”在《文选》中被列为诗歌二十四种类别中的一类,归于其下的共有九十三首诗歌,而其中以《杂诗》为诗题的仅有十五例(包含成组的同题诗歌),再有三例汉诗无题,其余均不以“杂诗”为题。因“杂”字意义模糊的特殊性,相较于其他设立标准更为明晰的诗歌类别,“杂诗”的意义引发了后人不断地阐释与讨论,多认为“杂”即“总杂”之意,或是认为此类并没有明确的收录标准。本文则认为《文选》“杂诗”类作品具有较鲜明的文体内涵,选录标准并不存在矛盾,“杂诗”类收录诗歌是以《古诗十九首》为范式的追认归类。正因此种标准与其他现存可见总集、类书不同,往往引起研究者的困惑,引发较多争论。
一
古人对“杂诗”的内涵已有许多讨论,如李善注在王粲《杂诗》题下云“杂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杂也”[1]415。六臣注本李周翰也于此篇下注“兴致不一,故云杂诗,此意思友”[2]546;并在卢谌《时兴》题下注“时兴,感时物而兴,喻情也,亦杂诗之类”[2]560。《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云:“杂诗者,古人所作,元有题目,撰入《文选》,《文选》失其题目,古人不详,名曰杂诗。”[3]229吴淇《六朝选诗定论》评曹植《杂诗》六首云:“诗不专指一事,亦不必作于一时,称物引类,比兴之义为多,故题名曰‘杂诗’。”[4]113除《文镜秘府论》从失题的角度解释外,其余诸家主要强调“杂诗”诗意较为宽泛,不被具体单一的主旨或者内涵所涵盖,且多从具体事物起兴。
当代学者对此也多有讨论。傅刚《〈昭明文选〉研究》认为“杂诗”的含义如李善注“不拘流例”,并没有固定体例[5]271。钱志熙《魏晋“杂诗”》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独立之一体,但《文选》“杂诗”类还收入了不少在体制和创作宗旨上与魏晋“杂诗”毫不相关的作品,是把不能归入其他类目的诗都归入“杂诗”类[6]。徐国荣《〈文选〉杂诗立类辨析》[7]、张旭《魏晋南北朝“杂诗”研究》[8]也持这一观点。颜庆余《“杂诗”的文献学考察》扩大了研究视野,对《文选》“杂诗类”、历代总集别集、明人《杂诗》创作几方面综合考察,认为“杂诗”主要是一种编辑手段。而《文选》的“杂诗”只是编辑时的权宜之计,不能成为总集的一种体类,也不能得到后世选家的传承。“杂诗”的抒情传统是后世建构的结果。[9]前人研究中,仅有赵超《汉魏六朝“杂诗”的诗史意义——以〈文选〉“杂诗”为例》认为萧统对“杂诗”有明确的认识。该文总结杂诗的体类特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遇物即言”、有兴即发的创作方式,二是诗作不具有政治功利和社会功用性,三是自娱自适。但同时也认为此类中魏晋作品与南朝作品存在较大差异。[10]
《文选》收录的作品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比如陶渊明《咏贫士》《读山海经》似乎可以归入咏史类,谢朓、沈约较多和诗似乎与赠答类更为接近,且谢朓《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和王著作八公山》诗歌内容也涉及歌咏史事,还有许多作品也可以归入咏怀、祖饯、行旅等类。题为《杂诗》的作品中所抒写的怀抱、志向、情感也颇为复杂并不统一。“杂诗”收录了14首齐梁作品,是收录齐梁诗歌最多的一类。其中多有齐梁时期新兴盛的诗歌形态,如带有文字游戏性质的鲍照《数诗》。再如沈约《应王中丞思远咏月》《咏湖中雁》等咏物题材,这些作品又很难被划归入《文选》已设立的其他诗歌类别。因而这类诗的收录,的确会给人带来编者难以细分暂且搁置的印象。
然而,正如傅刚《〈昭明文选〉研究》所指出的,萧统对《文选》一书的编成是十分满意的,且对此前编纂的《古今诗苑英华》称“犹有遗恨”[5]174。《文选》是一部“略其芜秽,集其清英”[1]2的作品,其编纂体例、分类在各方面都是更加谨慎、力求圆满的。《文选》也非后世“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11]这一类总集,并没有必要广为收录不具代表意义的新兴作品。以《文选》为代表的古代总集、类书诗歌分类,其中有的以创作目的和情境划分,有的以诗歌内容划分,一部书中存在不同的分类标准,与后世严格的诗体观念及题材划分并不相同。且《文选》中多有标举一首或一组诗歌为一类的情况,如“补亡”“述德”“百一”“反招隐”“军戎”“郊庙”等等。以此种编纂逻辑来看,将“杂诗”视为搁置无法归入他类的驳杂作品,或者认为其中所收魏晋诗歌与齐梁诗歌具有不同标准或意义,都与《文选》所呈现的编纂思想与分类体例存在较大的冲突。针对所谓齐梁新异之作,如足够重要,可以别立他类;如不足以代表一种类型风格或并非“清英”,可以摒弃不选。
再从文献角度来看,《文选》著录诗题为“杂诗”的作品中,曹丕《杂诗》二首、陶渊明《杂诗》二首,都存在与本集诗题相冲突的情况。曹丕《杂诗》二首,李善注曰“集云:枹中作。下篇云:于黎阳作”[1]495。所谓“集云”应是李善当时可见的曹丕别集,别集中两首各有不同题目,《杂诗》诗题或许经过《文选》编纂时更改,或许是《文选》所依据的版本与李善所见别集诗题不同,现今材料缺乏的情况下无法明确判断诗题具体在哪一环节发生了改变。陶渊明《杂诗》二首更为特殊,“结庐在人境”“秋菊有佳色”二首诗在陶集中明确归属于《饮酒》二十首,且陶渊明另有《杂诗》十二首,《文选》并未选录。与前举曹丕《杂诗》二首的情况不同,诗题更易的原因是收录版本依据不同的可能性很小,《文选》与陶集诗题的明显区别更可能是有意为之(1)关于《文选》《陶渊明集》是否萧统亲自编纂,在其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有多少,学界历来有一定争议。但无论萧统是挂名还是亲自编纂,都基本可以判断他阅读过《陶渊明别集》。。同时李善注对此的忽视也使我们意识到,不能因为李善并未注明其他诗题,就轻易判断《文选》并未更易诗题。由此可以推论,《文镜秘府论》统论“杂诗”为“失其题目”,故“名曰杂诗”[3]229是不正确的,这一论断并不能覆盖“杂诗”类中的所有诗歌[9]。
二
结合《文选》的编纂思想与体例、“杂诗”类中更改诗题的例证,我们可以试着推测,萧统虽未言明,对于“杂诗”却应是有个人较明确的理解和认知的。傅刚在《〈昭明文选〉研究》中提出,从每一类别中作家作品入选的数量,可以看出该作品或者作家在此类题材中的重要地位[5]252。以此种方式考察,“杂诗”类数量居首位的,则是《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排列于此类最前的位置,虽然可以说《文选》以类相从之下每类主要遵循时代先后次序排列,但每类的第一首也是《文选》对此题材追溯到的最早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具有开创意义。
此十九首,当是萧统认为艺术和思想成就最佳,最有影响力的古诗作品。对比《玉台新咏》卷一收《古诗》八首、枚乘《杂诗》九首,《古诗》八首之中有四首、枚乘《杂诗》九首之中有八首也见于《古诗》十九首。梳理可知《文选》所录《古诗》十九首中,有七首不见于《玉台新咏》,而《玉台》收录的古诗与枚乘诗中,有五首不见于《文选》。与此相关的是,《文选》卷三十录陆机《拟古诗》十二首。《玉台新咏》卷三录陆机《拟古诗》七首,此七首不出《文选》收录范围。陆机拟诗中,《拟兰若生朝阳》一首,应是模拟《文选》未收、存于《玉台新咏》的《兰若生春阳》。《拟东城一何高》从文本看应是模拟《东城高且长》,此首虽见于文选,但从陆机诗题也可看出陆机所据古诗版本与《文选》不同。而从锺嵘《诗品》“古诗”一条论述,可知锺嵘所见陆机拟诗应至少有十四首,而所见的古诗总数则数目更多,除“陆机所拟十四首”以外,还有“去者日以疏”等四十五首[12]91。陆机《拟古诗十二首》并非是针对《古诗十九首》的模拟,而是针对“古诗”。在《文选》编定《古诗十九首》之前,可能已有别的古诗集合版本流传,《文选》应是面对较多的汉代五言诗作品,经过细致挑选之后形成了十九首之数。综合考虑《古诗十九首》在“杂诗”类之中的数量占比、所居次序,以及筛选整合的过程,可以看出萧统应是有意识地将《古诗十九首》在“杂诗”类中置于范式地位。
本文认为,此类中所录的后代诗歌,尤其是并非题为《杂诗》的作品,其实是萧统追认的与《古诗十九首》内容、风格相近的,或者说受到《古诗十九首》影响的作品。《古诗十九首》并非出于一人之手,在艺术风格、表现手法上呈现出一定的整体特征,但其中各首包蕴的不同思想与情感本就是极为复杂的,的确无法被某单一类型所笼罩。前文所引古人对“杂诗”的解读,其实恰好可以阐释古诗。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总结《古诗十九首》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主要涉及游子思乡情绪、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仕途失败时的失落,思妇盼望对方归来的迫切情绪和独居的孤独;思考永恒与有限的关系、人的心态与生命周期的关系、忧郁与欢乐的关系、来去亲疏的关系。从艺术表现上共同点在于对节序、空间的敏感,长于抒情,多用比兴等。[13]经过分析可以发现,“杂诗”类的诗歌或多或少地都存在上述特征,内容情感和艺术手法上都可以在《古诗十九首》抒写的主题中找到源头,只是显隐不同。李善及五臣时而注明的诗歌主旨,多可以在《古诗十九首》中找到对应,如王粲《杂诗》周翰注“此意思友人”[2]546,曹植《朔风诗》周翰注“时为东阿王在藩,感北风思归,故有此诗朔北也”[2]547,曹植《杂诗六首》李善注“此六篇并托喻伤政急,朋友道绝,贤人为人窃势,别京已后,在郢城思乡而作”[1]416,曹摅《思友人诗》刘良注“摅与欧阳建俱以名称相得,故作此诗,思之也”[2]552,曹摅《感旧诗》李善注“此篇感古旧相轻,人情逐势”[1]418,左思《杂诗》李善注“因感人年老,故作此诗”[1]420等等。胡应麟《诗薮》也曾指出这一特点,云“子建杂诗,全法《十九首》意象,规模酷肖,而奇警绝到弗如”[14]。只是前人注语与评价主要聚集在魏晋诗歌,尚未覆盖“杂诗”类的所有作品,也不是从萧统追认、归纳诗歌类型这一角度考虑。
经过整理分析可以发现,《文选》“杂诗”类作品许多诗歌内容直接涉及叙写男女相思或是对友人、故乡的思念之情,表白人生志向,感慨宦海沉浮、世态炎凉、光阴流逝等,且在继承《古诗十九首》传统的基础上多有所发展。以思念、离愁这一脉络为例,《古诗十九首》中的别离愁绪多发生在男女之间,苏李诗的作者归属在梁时虽有争议,但抒情对象已从男女拓展变化至友人,魏晋作品更进一步深入详细抒写友人之间的珍贵感情和复杂心绪。例如曹植《朔风诗》即融合感时、思乡、怀人等内容,第一章用“朔风”“代马”“越鸟”等比兴,明显可见受到古诗“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1]409的影响,层层推进,在联章体较为宽裕的空间中从各个角度极力描写人生困境。至沈约《咏湖中雁》,选用齐梁更为流行的咏物体式描写思乡的内核,结尾“刷羽同摇漾,一举还故乡”[1]434也可看出古诗“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1]410的影子。再如“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赠物以寄托情思这一典型模式及经典诗句,在“杂诗”类的后世作品中也反复出现,影响极大。张华《情诗》“佳人不在兹,取此欲谁与”[1]418将古诗中直陈赋写改为疑问口吻,更能体现怅惘、无奈的心情。谢灵运《南楼中望所迟客》“瑶华未堪折,兰苕已屡摘。路阻莫赠问,云何慰离析”[1]426用于友人且又翻出新意,结合《九歌》典故,在已知道路阻隔不通音讯的现实下,通过“屡摘”的细节体现深情。再如“故人心尚尔”一句,在古诗“客从远方来”之中,是相隔万里仍心意相通的真情,至谢朓《和王主簿怨情》“故人心尚尔,故心人不见”[1]433则变为今昔对比的哀戚感叹。
有的作品表面上看似与《古诗十九首》相去较远,也多引起前人争论,其实也都可以寻得关联。如刘桢《杂诗》:
职事相填委,文墨纷消散。驰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
沈迷簿领间,回回自昏乱。释此出西域,登高且游观。
方塘含白水,中有凫与雁。安得肃肃羽,从尔浮波澜。[1]415
吴淇认为“无甚深意,只是不耐簿书之烦”[4]142。不耐簿书之烦的确是诗歌前半部分主要的情绪,而与《古诗十九首》可以对应的,其实是下半部分出城登高游赏的模式,以及用比兴寄托手法表达诗人对自由闲适生活的向往。再如枣据《杂诗》,开篇叙伐吴事,似乎应归入军戎一类,但诗中表达在随军途中因路途艰险邈远的忧惧心情,描绘山中所见萧瑟阴冷的景物,“恻怆心哀伤”[1]420,虽理智上明白士人的义务,内心仍盼望可以躲避此种艰辛和危险。同样写从军,与王粲《从军诗》的情调完全不同,而与《古诗十九首》中游子的忧虑感更为接近。以这样的角度考虑,暂时忽略诗歌外在体式,以内容和主要艺术手法寻求与《古诗十九首》的对应和嬗变,或许更能理解一些看似可以归入他类的作品存录于此的原因。如陶渊明《咏贫士》与《读山海经》,萧统有意选择了两组组诗中咏史痕迹最弱的二首,诗歌呈现出的是以比兴描绘个人情志、境况以及关于人生的哲思。谢惠连《七月七日夜咏牛女》其实是对古诗“迢迢牵牛星”主题的继承,又作为南朝咏牛女诗歌流行倾向的一个代表(2)刘铄、谢庄、谢灵运、陈叔宝等人均有此主题诗作。。鲍照《数诗》文字游戏之作的外壳下,内里对于繁华都市、士人聚会的描写与古诗“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多有相通之处,末尾“十载学无就,善宦一朝通”[1]429流露的鄙夷则比“明月皎夜光”一首揭露更为深刻;《玩月城门西解中》从诗题看似乎写赏月,其实是羁旅客愁主题。谢朓《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和王著作八公山》二首则明确涉及史事,不入“咏史”类也不以唱和入“赠答”的原因,或许是萧统认为二首诗中的重点不在于描写歌咏具体的某人某事,而是慨叹古今之变与个人怀抱,且多景物描写,多用比兴。沈约《三月三日率尔成篇》在《文苑英华》中被归入上巳类,其实上巳节仅仅是个引子,兴发思妇愁绪,主体与“青青河畔草”的结构和主旨一脉相通,《文选》将其置于“杂诗”类中较《文苑英华》从表层归类更为精准。
“杂诗”中还有一类主题的诗歌较为特殊,抒写对隐逸的向往、独居之乐以及君子固穷的品格。如张协《杂诗》“结宇穷冈曲”和“墨蜧跃重渊”二首,陶渊明《杂诗》“结庐在人境”和“秋菊有佳色”二首、《咏贫士》其一、《读山海经》其一,谢灵运《田南树园激流植援》《斋中读书》《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迥溪石濑修竹茂林诗》,谢朓《直中书省》《观朝雨》《郡内登望》,沈约《学省愁卧》等。这一类作品和《文选》“招隐”类所收的三首诗相比,最明显的区别是“招隐”类均有山中遇“幽人”的设置,而上述作品多写自身,更多个人心绪的剖白。且除了主旨接近以外,各个诗歌描写重点、对隐逸的认识也各有不同,不如“招隐”的目的明确。这一类作品,也可以在《古诗十九首》中寻得较为隐秘的源头。其中对仕宦的疲倦及世态炎凉之感与多首古诗相通,对于人生出处行藏的思索、不群的态度,与“明月何皎皎”中的独自忧愁、“青青陵上柏”中面对繁华浮世“戚戚何所迫”[1]410,以及“西北有高楼”中“但伤知音稀”[1]410的心境是十分接近的。这一部分作品的精神内核从古诗十九首之中生发,随着社会背景变迁、隐逸思想变化而逐渐形成新的传统。
《文选》对汉末古诗的推崇并非个例,我们可以借从后一类诗歌“杂拟”中看出这一经典逐步建立的部分过程,其中陆机、刘铄拟诗及江淹《古别离》是最为明确地指向汉末文人诗的。古诗似乎从未淡出文人们的视线,从西晋至萧梁很可能曾有更多的模拟学习作品。经由各代文坛领袖的学习、创作,会不断稳固汉末古诗的经典地位。萧梁时期,无论是追求“新变”还是“通变”的文人(3)傅刚将齐梁时期的两种文学批评观概括为“新变”与“通变”。参见:傅刚《〈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都对汉末古诗十分推崇。《玉台新咏》所收录的汉末古诗虽存在作者归属判定问题,也表露了推崇和溯源的倾向。《文心雕龙》评云:“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15]《诗品》则言:“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2]91我们推测萧统将《古诗十九首》置于一类诗歌中的范式地位,此种可能性与当时文学批评的整体背景和风气是相符的。
诚然,随着社会背景与文学自身不断向前发展,反映时代的具体现实、思想等不断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可写入诗歌的内容范围不断扩大,纵使汉末五言诗写人心之至情具有极强的普世性,也绝不可能以《古诗十九首》彻底笼罩后世的诗歌。“杂诗”类的诗歌也已经体现出各个时代的不同特性,如同样关注时光流逝,晋诗写景体察刻画更为细腻,至宋齐,景物描写艺术更加成熟,且在诗歌中所占篇幅更大,对人生的思索、感慨有时仅在末尾才出现;再如嵇康《杂诗》与何劭《杂诗》都写夜间游赏,也都与友人相关,与古诗最明显的不同是嵇康写及玄理,而何劭写及求仙。这些特性,以及前文所述“杂诗”类时代较晚的作品中的新变因素,也体现出文学“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其丽”[1]1的发展过程,与萧统的文学观念相符。且《文选》“杂诗”类是萧统作为后来的编集者的归纳,编集者的辩体意识针对已有的作品,却并不能说明被收录作品的诗人们在创作时全都有意识地继承了《古诗十九首》的传统,诗歌中的部分内容情感溢出古诗范围也是自然的。
三
《文选》“杂诗”类的文体内涵和《玉台新咏》《艺文类聚》等书存在很大差别。《玉台新咏》中“杂诗”首先出现在卷首目录中,有较多题为某人杂诗若干首的情况。经过梳理,除了卷一《古诗八首》《古乐府诗六首》、卷九《歌辞二首》、卷十《古绝句四首》、《近代西曲歌五首》《近代吴歌九首》《近代杂歌三首》《近代杂诗一首》无作者归属以外,《玉台新咏》卷首目录一般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1.作者+具体题目+若干首,如辛延年羽林郎诗一首、秦嘉赠妇诗三首等;
2.作者+“杂诗”+若干首,如枚乘杂诗九首、吴孜杂诗一首等;
3.作者+“乐府”+若干首,如傅玄乐府七首等;
4.作者+“诗”+若干首,如王献之诗二首、高爽诗一首等;
5.作者+若干首,如沈约二十四首、朱超道一首等。
目录中“某人杂诗若干首”,绝大多数在卷中作者姓名之下并未标“杂诗”,而是直接题写与杂诗无关的具体诗题。其中诗题确为《杂诗》的占极小比例,仅有枚乘《杂诗》九首、刘勋妻王宋《杂诗》二首、曹植《杂诗》五首、张华《杂诗》二首、张协《杂诗》、王微《杂诗》二首、施荣泰《杂诗》、柳恽《杂诗》。《玉台新咏》中“某人杂诗若干首”“某人诗若干首”与“某人若干首”的卷首取题方式,从诗歌内容上看并无任何区别。从编纂体例来看,仅卷十无“杂诗若干首”的题名。“某人若干首”的题名出现在卷五至卷八,卷五几乎全用此种取题方式。“某人诗若干首”的题名出现在卷七至卷十。据傅刚总结《玉台新咏》编辑体例“前八卷收汉魏以迄齐、梁历代有关艳歌题材的五言艳诗,后二卷中的卷九收录历代杂歌,卷十收历代五言短歌”,“前六卷是已故作家,卷七、卷八诗现存作家”[16],与这几种题名方式也不存在清晰的对应关系。造成此种较为混乱的卷首目录题名方式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后人修订时编辑修改,也可能是徐陵本身对此的态度并不十分严谨。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玉台新咏》在卷首目录将诗人的作品题为“杂诗”与“诗”并没有区别,且有许多在目录题为“杂诗一首”,卷中另有具体诗题的诗歌作品,故《玉台新咏》中的“杂诗”不存在诗体层面的意义。
《艺文类聚》收录《杂诗》与《文选》存在若干重合。《艺文类聚》又收录了许多不见于《文选》《玉台新咏》的《杂诗》作品,如曹植《杂诗》、“悠悠远行客”、应璩《杂诗》“细微可不慎”、“散骑常师友”、繁钦《杂诗》“世俗有险易”、傅玄《杂诗》“闲夜微风起”、张协《杂诗》“太昊启冬节”。而《艺文类聚》以《杂诗》题目收录的陶渊明“开荒南野际”和“种豆南山下”在本集中明确归于《归园田居》五首之下。鲍照“十五讽诗书”,本集归于《拟古诗》八首之下。而《文选》所录张协《杂诗》十首中“黑蜧跃重渊”一首,《艺文类聚》题为《苦雨诗》。《艺文类聚》中引用诗句常省略诗题,仅云“诗曰”,故其“杂诗”的使用,并没有明显的标准,也有可能并不是作为明确的诗题,而是近似于“诗曰”的编纂便利手段。
此外,《隋书·经籍志》著录江邃撰《杂诗》七十九卷、刘和注《杂诗》二十卷、《二晋杂诗》二十卷、谢灵运撰《杂诗钞》十卷[17],已佚不可知其原貌,是否对“杂诗”有各自的理解和判定则不可知。
如前所述,现今可见的南朝总集、初唐类书中对于“杂诗”的著录情况十分复杂,而《文选》对于“杂诗”文体层面的认知和理解较为独特。此种理解或许仅代表萧统个人,或许代表当时文坛上的某一部分人的共识,却不能因为现存文献多未继承此种诗歌分类方式就否定其存在。确认“杂诗”类与其他二十三类诗歌相同,有着明确的收录标准,而非勉强搁置一些难以分类的作品,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文选》的严谨与细致。萧统正是通过《文选》收录作品与设立类目的内在逻辑,来彰显他考镜源流的意识和对于文学发展脉络的理解。“杂诗”这一立类或许没有得到认同与继承,却集中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类抒情性极强的诗歌作品的特征和演变脉络。《古诗十九首》的经典地位、对后世诗歌的深远影响正由此显现,也因《文选》的推重在后世得以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