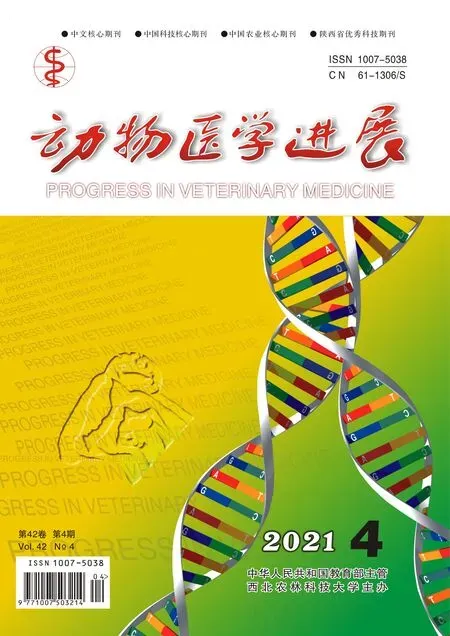MicroRNA在非洲猪瘟研究中的应用
2021-03-31张兆博张思诗汉可欣李晓易文雪霞汉丽梅
张兆博,张思诗,汉可欣,李晓易,文雪霞,汉丽梅,4*
(1.沈阳农业大学畜牧兽医学院,辽宁沈阳 110866; 2.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上海 200241; 3.长春师范大学,吉林长春 130031; 4.东北畜禽疫病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辽宁沈阳 110866)
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是由非洲猪瘟病毒(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ASFV)感染引起的急性、热性传染病,家猪和野猪都为该病的易感对象。ASFV是一种20面体、有囊膜的双链DNA病毒,不同来源的分离株病毒基因组长度在170 kb~193 kb之间[1]。ASFV约有151个~167个开放阅读框(open reading frame,ORF),编码5个多基因家族,但目前部分ORF编码蛋白的功能尚未明确[2]。ASFV的传播方式多样,其既可以通过易感动物之间的直接接触传播,也可以通过污染的猪肉、毒蛇、车辆、人及扁虱等途径间接传播[3]。作为一种急性动物疫病,其强毒株可导致患病猪只出现发热、出血及多器官损伤等症状,并在短时间内死亡,部分强毒株感染后病死率可达100%。由于疫苗和特效药的缺乏使得目前ASF的防控十分困难,因此,每年给全世界养猪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4]。2018年8月1日,我国辽宁省沈阳市发现ASF疫情,这是我国本土首次发生ASF疫情。目前ASF在我国的流行已严重危害我国养猪业的正常发展[5]。本文主要对ASF发病过程中microRNA的来源、功能及其在ASF防控等领域的研究进行综述,并对未来microRNA在ASFV致病机制的研究及其防治进行展望,旨在为未来ASF的预防与疫苗的开发提供新思路。
1 microRNA概述
microRNA(miRNA)是一种核酸长度为19 nt~23 nt的内源性单链非编码RNA,自1993年首次在秀丽隐杆线虫中发现后,它被广泛的在真核生物中所发现。miRNA是非编码RNA中小非编码RNA(small non coding RNA,sncRNA)的一种。miRNA由核内编码miRNA的基因转录后经过剪切、折叠形成miRNA前体,并在Dicer酶的作用下,将pre-miRNA加工为成熟的miRNA,成熟的miRNA具有保守性与稳定性[6-7]。miRNA不具有编码的能力,但其可以通过诱导AGO蛋白至3’非编码区,使装载有miRNA的AGO蛋白形成miRNA诱导沉默复合体,对mRNA的转录或翻译起到调控作用,从而介导基因沉默[8]。miRNA可广泛的参与各种细胞过程,在细胞增殖、细胞凋亡、基因表达、胚胎发育、蛋白质编码和癌症发生等过程起到重要的作用。而miRNA本身也受到多种因素的调控,如特异性转录因子、基因突变、染色体缺失、表观遗传因子等[9]。目前,对miRNA的发掘及其功能的鉴定已经成为研究病原与宿主互作的热点方向之一。
2 ASF发病过程中miRNA的来源及功能
ASF发病过程中miRNA的来源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来源于猪体内的miRNA,它们来源于猪本身,即内源性miRNA;而另一类则为来源于ASFV的miRNA,它们是由ASFV中特定的miRNA经一系列作用形成的,健康状态下的宿主细胞内并不存在该种miRNA,即来源于病毒的外源性miRNA。
2.1 来源于猪体内miRNA的功能研究
在体外细胞水平研究发现,ASFV的感染引起miR-10b、miR-486-1、miR-144和miR-199a等miRNA表达显著上调,值得注意的是动物在感染ASFV后极短时间内miR-10b就发生了差异表达,并在感染6 h后恢复正常水平。研究表明,在巨噬细胞中,miR-10b可以通过靶向三磷酸腺苷结合转运体A1(ATP binding cassette transporter A1,ABCA1)调节宿主细胞的胆固醇外流[10-11],而宿主细胞胆固醇代谢与ASFV感染及其在宿主细胞中复制密切相关[12],且ASFV可通过内吞作用进入猪巨噬细胞,因而推测miR-10b、ABCA1可能在巨噬细胞内吞作用介导的ASFV的早期感染及病毒复制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但其作用机制还需进一步研究[10]。
在动物体内研究发现miR-451、miR-145-5p、miR-181a及miR-122miRNA在病毒感染后7 d出现表达上调,在同期miR-92a、miR-23a、miR-92b-3p、miR-126-5p 、miR-126-3p、miR-30d、miR-23b和miR-92c表达下调。应用KEGG数据库对上述miRNA进行靶标及生物学功能预测结果表明,有7种miRNA(miR-23a、miR-30e-5p、miR-92a、miR-122、miR-125b、miR-126-5p和miR-125a)参与免疫反应过程[13],如T细胞受体信号通路、B细胞受体信号通路、细胞凋亡、自噬调节及FcεRI信号通路(Fc epsilon RI signaling pathway)调节等;而ASFV编码的蛋白如A179L、DP71L、EP153R及p54等在逃逸宿主抗感染免疫、细胞自噬等一系列免疫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14-15],推测miRNA可能与ASFV编码基因的功能发挥密切相关。
2.2 来源于ASFV miRNA的功能研究
基于动物体内的研究结果,筛选出6个候选病毒miRNA,通过试验验证与分析表明没有符合条件的病毒源miRNA,并由此得出ASFV不会产生miRNA的结论[16]。将研究范围扩大到sncRNA,对符合条件的sncRNA进行研究与鉴定,发现存在3种由ASFV所编码的病毒sncRNA,并将其分别命名为ASFVsRNA1、ASFVsRNA2与ASFVsRNA3。它们均在攻毒后16 h动物体内被检测到,而ASFVsRNA2则可以在攻毒后6 h与16 h均被检测到,并在动物实验中也得到验证[10]。通过对ASFVsRNA2的进一步研究发现,ASFVsRNA2的过表达可以显著下调病毒的复制,且ASFV可通过3′尿苷化和非尿苷化的互变来调节ASFVsRNA2的表达,以此来调控病毒自身在感染不同阶段复制的速度。而miRNA的合成、稳定性与靶向性也同样被认为受到3′尿苷化的调控[17]。免疫沉淀结果显示,ASFVsRNA2并非通过经典miRNA产生途径所产生,且无法预测到合理的miRNA前体[18]。上述3种sncRNA是否具有miRNA的作用,以及其生成方式和生物学功能等,仍有待深入研究与探讨。
3 miRNA在ASF防控过程中的作用
3.1 用于疫苗的研发特定靶点筛选
miRNA在ASF发病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使研究人员拟通过对它们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以有利于探索对ASF的防控途径及疫苗的研发。研究发现miR-142-3p可在猪巨噬细胞中大量表达,通过靶点预测及试验验证发现ASF病毒E183L是miR-142-3p的靶基因,即p54基因[19]。其编码的p54蛋白是ASFV一种重要的结构蛋白,具有高度免疫原性,并在ASFV感染入侵过程中起重要作用,p54蛋白可以与p30蛋白共同参与ASFV与靶细胞结合的过程,并在ASFV进入宿主细胞后与宿主的动力蛋白相互作用,从而参与成熟病毒在宿主细胞内的转运[20-21],此外,p54蛋白与caspase-3的激活和caspase-3诱导细胞凋亡的过程存在密切关系。因此,p54蛋白可能是针对ASFV的DNA亚单位疫苗研发的重要候选抗原蛋白[4,22]。通过对miR-142-3p的深入研究,可为ASFV诱导细胞凋亡及病毒在宿主体内的复制方式的研究以及疫苗的开发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3.2 ASFV毒力与miRNA的差异表达
ASFV的不同毒株毒力不同,使用不同毒株攻毒动物,其miRNA的表达情况也存在差异,这些差异表达的miRNA对ASFV强毒株致病机制的研究、ASFV疫苗生产用毒株的选择及ASF免疫机制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23]。在应用强毒株与其传代的减毒株的攻毒试验研究中发现,与用减毒株攻毒的动物相比,使用强毒株攻毒的动物在感染后出现8种差异表达的miRNA,其中miR-126-5p、miR-92c、miR-92a、miR-30e-5p和miR-500a-5p呈差异上调表达,而miR-125b、miR-451和miR-125a呈差异下调表达[9],这些差异表达的miRNA可能与ASFV毒株毒力及其致病性相关,并可能在减毒毒株的制备及免疫原性的提高等与疫苗研发相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通过miRNA靶向特异位点的方法已获得减毒黄病毒毒株[24]。
4 展望
ASF作为近年来在中国新发并流行的一种重要动物传染病,已严重危害我国养猪业的正常发展,对ASF的深入研究及相应疫苗的研发迫在眉睫。而近年来病毒与宿主互作机制研究的热点之一miRNA等非编码RNA在ASF发病机制的研究过程中均取得重要的研究进展,但受限于研究技术等因素,对miRNA等非编码RNA功能了解较少。随着二代测序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使组学水平上大量发掘miRNA成为可能[25]。传统的细胞测序技术是在多细胞水平上进行的,这种方法忽略了细胞间的异质性,而单个及少部分细胞在疾病发生过程中独有的细胞特性往往被忽略,从而影响试验结果的可靠性[26]。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单细胞测序技术应运而生,通过单细胞测序技术,少数特异性细胞的差异表达可以被准确地检测与鉴定,从而获得更加准确与科学的结论[27]。随着这一技术的迅速推广,将会对miRNA及其他非编码RNA在ASFV感染及致病过程中作用以及ASF的发病机制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并为ASF的防控与疫苗的开发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