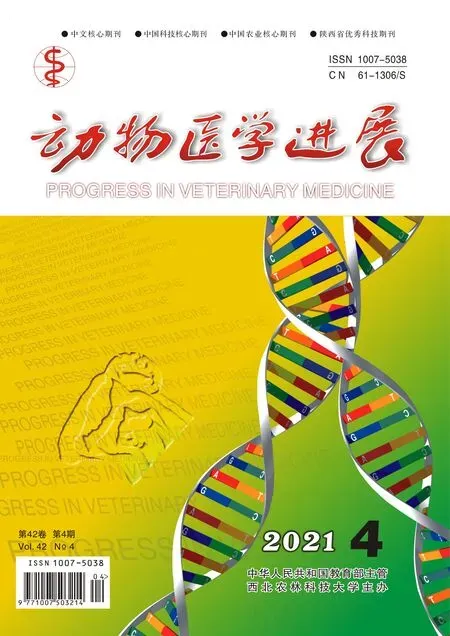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研究进展
2021-03-31轩慧勇陈万昭夏利宁
轩慧勇,陈万昭,夏利宁
(新疆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52)
自20世纪80年代首次报道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ancomycin-resistantEnterococcus,VRE)以来,肠球菌从“普遍认为安全”的细菌发展为重要的病原体,并且由于VRE能够在物体表面长期存在,其传播越来越难控制[1]。VRE引起的感染常见于各种癌症、泌尿系统疾病和脑梗死等重症患者,VRE的感染常与高死亡率相关,引起的感染主要为腹腔感染和肺部感染,其次为泌尿道感染、皮肤感染和血液感染,严重时可导致脓毒血症,在美国医院内感染率高达20%~30%[2]。中国VRE感染的病原体中74%为屎肠球菌,而VRE引起血液感染的病原体中20%为粪肠球菌[3]。在巴基斯坦住院的癌症患者中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VRE菌血症患者12周的死亡率为63%[1]。
VRE可在健康人和动物的胃肠道中存在,并在合适的条件下进行定植和传播。定植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临床使用抗厌氧菌药物(包括万古霉素)进行治疗,而这些抗菌药物的使用会去除机体的定植抗性,为VRE入侵提供条件,进而在胃肠道中建立耐万古霉素肠球菌种群[4]。有关VRE致病性的因素尚未完全确定,但诸如肠球菌表面蛋白、聚集物质、明胶酶和胶原黏附素分子Acm等因素与VRE在不同组织的定植能力有关[5]。经抗菌药物治疗后,VRE可以在小鼠的胃肠道中定殖,并在使用免疫抑制剂后可以在小鼠模型中传播[6]。VRE的天然耐药和通过质粒或转座子获得的耐药使临床治疗变得困难,需要新型抗菌药物,细菌素是一种新的治疗选择,既可以作为单独治疗方法,也可以与现有的抗菌药物协同作用。
1 VRE的起源
糖肽类抗菌药物万古霉素于1955年被分离出,主要用于对青霉素和头孢菌素类药物治疗无效的细菌性感染[7]。随着万古霉素在临床使用频率和剂量的增加,1987年VRE在英国伦敦被首次分离出来,随后在美国的纽约,爱尔兰、加拿大、日本、比利时和德国等国家,以及包括我国在内都有检出的报道[7]。VRE的出现主要归因于以下两方面:20世纪80年代,欧洲地区长期应用阿伏帕星来促进动物生长以及预防疾病;肠球菌在万古霉素治疗中,自身结构改变,消除了与万古霉素的结合靶位。
1.1 VRE的产生原因
通常认为医院内感染VRE的危险因素包括住院时间的延长、患者年龄较小、暴露在ICU(重症监护病房)和滥用抗菌药物(如头孢曲松和万古霉素等抗厌氧菌的抗菌药物)[8]。此外,医院工作人员也可以传播VRE,因为即使洗手后,VRE也可以在手指上存活约30 min[8]。
VRE在食品动物生产中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欧洲和其他国家/地区广泛使用亚治疗量阿伏帕星促进动物生长,使畜牧业成为VRE菌株的重要来源之一。相反,加拿大和美国等其他国家直到2008年从未批准使用阿伏帕星,也未在动物中报道过VRE,故美国VRE的出现主要归因于临床环境[9]。由于VRE很容易在含有阿伏帕星作为食品添加剂的动物肠道内定植,最终在人类肠道内定植,因此各国农业委员会禁止阿伏帕星用于食品动物中,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1995年的丹麦和挪威,1996年的德国,1997年的欧洲和韩国等,2000年的中国台湾和新西兰[9]。但欧洲的最新数据显示,肠球菌一旦产生耐药后,其耐药性并不会随着禁用时间的延长而消失。据报道,在阿伏帕星被禁10年后,在4%的食品动物源样本中检出VRE;在阿伏帕星被禁用15年后,丹麦仍从家禽中检测到VRE耐药基因型,并且在47%的粪便样本中发现可变抗性表型和多种粪肠球菌克隆株。并且,意大利和德国也在禽肉和猪肉产品以及健康人的粪便样本中检出VRE[10]。VRE的持续存在,一方面归因于万古霉素耐药基因VanA和大环内酯类耐药基因ermB存在于同一个结合质粒上,这两个基因通过共转染使细菌保持耐药性,而质粒编码基因是质粒生存所必需的自然选择结果。另一方面归因于VRE能够在体外环境中长期存活。
此外,伴侣动物也可成为VRE的贮存者[10]。在欧洲禁用阿伏帕星之前,有报道称狗的VRE携带率很高,在随后的研究中,荷兰在阿伏帕星禁令执行5年后,发现VRE可以在健康的狗和猫体内定殖,并且,从狗身上分离到的VRE分离株与医院人获得性感染VRE菌株亲缘关系相近。而在意大利,波兰和匈牙利的健康马匹中也分离出携带vanA基因型的VRE菌株。
1.2 VRE定植和传播的主要因素
目前主要通过小鼠模型研究VRE在体内定植前和期间发生的过程以及在体内的传播,该模型的研究大大增加了人们对VRE与肠道菌群相互作用和抗菌药物给药效果的了解。
定植在VRE感染过程中至关重要,多项研究表明,抗菌药物的使用对微生物群的组成以及VRE的定殖能力具有深远的影响。小鼠模型研究显示[4],抗厌氧菌抗菌药物(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和头孢西丁等)可促进VRE定植,在同一模型中,抗厌氧菌活性较小的抗菌药物如头孢吡肟和氨曲南则不促进VRE的定植。此外,甲硝唑、新霉素、卡那霉素和万古霉素的联合用药也增加VRE的定植。值得注意的是,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是一种具有较强抗厌氧作用的抗肠球菌药物,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治疗期间,VRE定植被阻止,但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停止治疗后,VRE可定植,这表明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VRE的定植。一般来说,胃肠道微生物菌群的丰度和多样性会在抗菌药物治疗过程中降低,虽然当停止抗菌药物治疗后,肠道微生物菌群的丰度会增加,但成分有改变。具体来说,抗菌药物治疗后乳杆菌科和拟杆菌门的丰度明显减少,肠道微生物由大量梭菌和肠球菌组成[6]。减少乳杆菌科和拟杆菌门的抗菌药物包括甲硝唑、新霉素、卡那霉素、氨苄西林和万古霉素等,这几种抗菌药物治疗对乳杆菌科和拟杆菌门的影响较大,给病人服用这些药物会增加肠道中肠球菌的数量,从而增加VRE感染和传播的可能性。在没有抗菌药物治疗的情况下使用免疫抑制剂不会影响肠道菌群,因此免疫受损患者VRE易感性增加是由于抗菌药物的使用。
一些对VRE在肠道内定殖后的传播研究结果显示,传播是VRE引起全身感染所必需的过程[6]。研究表明,给小鼠使用由新霉素、甲硝唑和万古霉素组成的广谱抗菌药物配方,然后灌胃VRE可以诱导VRE在胃肠道中定植并扩散到其他组织。而另一项研究则对VRE是否可扩散到肝脏和脾脏等组织进行研究,在这项研究中,除灌服配方抗菌药物外,还给小鼠灌服环磷酰胺,在改变微生物菌群同时还可使小鼠免疫受损。研究结果表明VRE可以传播到肝、脾、肠系膜淋巴结和血液,尚不清楚是否由于免疫受损导致VRE传播到组织中。但人体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个体免疫功能低下才发生VRE传播,一项研究发现,在216例VRE定植的人类患者中,只有3例发生血液感染,而发生血液感染的患者均受到免疫损害。因此,免疫抑制可能是VRE在人类和实验动物中传播的必要条件[11]。
2 VRE耐药机制
2.1 肠球菌对糖肽类药物的耐药机制
糖肽类窄谱抗生素万古霉素是从土壤中东方拟无枝酸菌中分离出来。该抗菌药物主要通过以下3种方式对细菌杀灭:①抑制细胞壁糖肽的合成;②抑制RNA的生物合成;③改变细菌细胞膜的渗透性,临床主要用于因长期服用广谱抗生素所致难辨梭状杆菌引起的伪膜性结肠炎或葡萄球菌性肠炎的治疗。自VRE首次被报道后,VRE的检出率逐渐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VRE有明显的种间差异,大多数万古霉素耐药株是屎肠球菌[12]。
VRE一般是由于菌株携带5个~7个基因构成的基因簇介导对万古霉素耐药,目前,万古霉素耐药基因型被分为vanA、vanB、vanC、vanD、vanE、vanF、vanG、vanL和vanM这9种[13]。VanA、VanB、VanD型可产生一组连接酶,该酶导致合成D-丙氨酰-D-乳酸取代正常的细胞壁肽聚糖末端的D-丙氨酰-D-丙氨酸,使万古霉素不能与其靶位结合,造成细菌对万古霉素高水平耐药[13]。VanCl、VanE、vanG和vanL基因则导致合成D-丙氨酰-D-丝氨酸取代正常细胞壁的结构,介导对万古霉素的低水平耐药。其中vanF基因仅在类芽孢杆菌中检出,vanA基因仅在耐万古霉素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中检出。不同的基因型结构大致相仿,但基因编码蛋白的氨基酸序列有差异,且基因簇中的基因组成及排序不同,因此同源性在60%~80%之间。常见的耐药表型主要有vanA、vanB和vanC等3种。
2.2 VRE多药耐药的出现
肠球菌对万古霉素耐药以及对新型抗菌药物产生多药耐药引起全球关注,多药耐药的出现与人类医学中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高度相关。而肠球菌可进行耐药基因的交换和/或将耐药基因转移到其他革兰氏阳性菌(如葡萄球菌和链球菌)的能力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
VRE的出现给传染病的防控带来巨大隐忧。新型抗菌药物如利奈唑胺、达托霉素和替加环素等逐渐应用于临床上代替万古霉素的治疗,使万古霉素成为“最后一线药物”,但目前这些新型抗菌药物也出现敏感性降低或消失的临床分离株。抑菌剂利奈唑胺于2000年获得批准并被广泛使用,耐药性的出现与其在VRE以及万古霉素易感肠球菌的治疗有关。耐利奈唑胺肠球菌尽管在肠球菌中的检出率低至不足1%,但由于产生耐药性发展速度极快受到广泛关注[14]。对恶唑烷酮抗菌药物的耐药性(或敏感性降低)主要是通过获得氯霉素-氟苯尼考耐药基因(cfr)或染色体点突变(23S rRNA或核糖体蛋白)介导的,此外,2015年在动物源和人源中检测到的新型耐药基因optrA也可介导对恶唑烷酮类的耐药。cfr基因的获取通常是通过可移动元件进行耐药传播并降低VRE对多种抗菌药物的敏感性(氯霉素类、林可霉素类、恶唑烷酮类、截短侧耳素类和链阳霉素A类)[15]。而德国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在屎肠球菌移动元件和/或染色体DNA上检测到cfr(B)变异基因,与艰难梭状芽孢杆菌的cfr相似基因具有99.9%的相同序列[14]。
目前,对替加环素耐药肠球菌的耐药机制尚不清楚,通过对替加环素耐药肠球菌进行基因组分析,发现耐药性的决定因素主要由外排泵基因tet(L)和核糖体保护蛋白tet(M)所介导[9]。最近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Tn1549vanB基因型耐药性的传播,主要归因于vanB基因在肠球菌分离株染色体片段之间的交换,对多重耐药性病原体传播提供理论支撑[16]。
3 VRE在人-畜间的传播
养殖场是耐药菌/耐药基因产生的主要场所之一,现有研究表明,食源性致病菌耐药性日益加重,虽然不能证明人与动物之间相同的VRE型是由于人们食用动物性食品引起的,但是,通过使用不同的分子分型技术研究的结果表明,食源性耐药菌和/或耐药基因可沿着食物链“动物-环境-食品-人”传播,动物和人中VRE菌株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17]。如美国禽源弯曲菌耐药性研究发现,养禽业使用恩诺沙星引起弯曲菌对喹诺酮类药物耐药,导致人感染弯曲菌后使用喹诺酮类药物治疗失败率增高[17];由于阿伏帕星的使用,导致欧洲养殖业中VRE的出现,在阿伏帕星被禁止使用于养殖业后,欧洲VRE检出率降低;2000年-2002年丹麦猪源庆大霉素耐药粪肠球菌的检出率从2%增加到6%,与此对应的是,丹麦北部地区引起心内膜炎感染的耐庆大霉素粪肠球菌也增加相同比例,此外,体外试验表明,来源于动物的VRE可在人类肠道内定植。以上事例说明动物性食品源耐药肠球菌可通过“生产-储存-运输-销售-消费”中的多个环节进入食品链,进而传播给人类[18]。
我国养殖场源肠球菌对临床常用抗菌药物耐药性严重,耐药菌通过多种途径污染食品,进而引发食物中毒事件,而耐药肠球菌则会导致疾病治愈时间延长,并提升感染率和病死率,给疾病治疗造成负担[18]。肠球菌中一些菌种长期作为发酵剂和人畜肠道菌群调节剂用于饲料、食品和药品生产,如果这些工业用菌株获得耐药性,将加剧细菌耐药性的传播和危害。
4 VRE流行现状
2018年,有报道瑞士伯尔尼州医院内ST796 VRE菌株的暴发,由该克隆型屎肠球菌导致的血液感染已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现[19]。ST796 VRE分离株不仅显示出对万古霉素的耐药性,还对氨苄西林、左氧氟沙星和庆大霉素有很高的耐药性。瑞士暴发的分离株(ST796)与澳大利亚分离株的同源性达97%以上,经分析发现ST796型菌株由ST555进化而来,由此推断院内屎肠球菌型别变迁可能受医院的环境影响[20]。研究发现,随着乙醇的使用频率和时间延长,屎肠球菌对乙醇耐受性增加,进一步表明菌株在选择压力下有一定的适应性[21]。对患者和环境中的VRE研究发现,69.2%患者样本为PFGE-A型,84.6%环境样本为PFGE-E型,22.2%的PFGE-A型患者样本和81.2%的PFGE-E型环境样本明胶酶E(增加生物膜生成)阳性,溶血素激活物阴性[22]。在加强手消毒后,VRE阳性率有所下降,由此可见感染预防控制策略的实施对于控制VRE暴发和减少传播至关重要。对108例耐万古霉素血流感染患者定量PCR检测发现,利奈唑胺(600 mg/12 h)和大剂量达托霉素(≥9 mg/kg)比常规剂量(6 mg/kg~9 mg/kg)达托霉素治疗组能更快的清除VRE[23]。
研究显示,2014年-2016年[24],北京协和医院VRE检出率为1.3%~3.0%,耐万古霉素屎肠球菌的检出率为3.6%~4.9%。由此可见,在耐万古霉素肠球菌中,屎肠球菌更为常见,其中CC17是携带vanA基因的主要ST型。2012年我国研究报道,96株耐万古霉素屎肠球菌和5株耐万古霉素粪肠球菌均以携带vanA耐药基因为主,仅1株屎肠球菌为ST362(CC362),其余都属于与CC17相关的ST型。76株VRE(69株屎肠球菌、7株粪肠球菌)均携带vanA耐药基因,MLST型别均属CC17[25]。2007年-2015年天津地区医院内人群鼻拭子、手拭子样本中,VRE定植率(0.1%)低于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0.9%)和革兰氏阴性杆菌(8.8%)[26]。VRE感染死亡率(64.6%)明显高于万古霉素敏感肠球菌(39.4%),并且分离出VRE菌株患者抗菌药物花费约为分离出敏感株患者的2倍[27]。因此,有效降低VRE感染颇为重要。
5 VRE治疗的局限和新型治疗方法
VRE是胃肠道共生菌,在胃肠道定植是VRE感染的第一步,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由于肠球菌的固有耐药以及对新抗菌药物可迅速产生耐药,而临床有效的治疗方法很少,故VRE在肠道的持续定植和引发的感染对人和动物的健康及经济产生严重影响。目前认为有效治疗VRE引起感染的药物有喹奴普丁/达福普丁、替考拉宁、奥利万星、利奈唑胺和达托霉素等[26]。这些抗菌药物中的一部分只被批准作为治疗皮肤相关感染的药物,有些还处于开发的试验阶段。VRE耐药形势日益严重,耐药机制复杂,但新抗菌药物的研发速度缓慢,因此,寻求新型的抗菌药物替代物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
许多革兰氏阴性菌和革兰氏阳性菌产生的细菌素,是一种天然的、具有抗菌活性的物质,且一株菌可产生多种细菌素,而同一种细菌素也可由不同菌株产生[28],因此细菌素具有替代抗菌药物潜力。细菌素是小分子多肽,由长短不同的氨基酸组成,并且具有抑菌活性,是细菌在代谢过程中通过核糖体合成。最近通过抗性突变体的基因组测序逐渐阐明细菌素的作用机制[29],而了解细菌素是如何发挥抗菌作用是进一步研究细菌素在体内治疗感染的关键。
细菌素与传统抗菌药物相比,其特点和优势在于:①抗生素由非核糖体合成,细菌素由核糖体合成,抗生素可以杀死很多细菌,但是细菌素的抑菌谱不一样,相对来说它有一定的特异性。②细菌素是由基因编码、核糖体合成的一类胞外分泌蛋白,大多数细菌素是蛋白类抗菌活性物质,为靶向靶细胞中的特定成分[30],因此对那些已经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致病菌依然具有杀菌作用。在鼠模型中研究结果显示[31],使用不同的细菌素可治疗其他耐药细菌引起的感染(如MRSA)。Galvin等报道,由乳酸乳球菌亚种产生的广谱细菌素Lacticin 3147对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Staphylococcusaureus,MRSA)、VRE、耐青霉素的肺炎球菌都具有抑杀作用[32]。③细菌素在不同的酸性和碱性条件下稳定性很强,因此易于储存,在进入肠道、消化道中又能够被蛋白酶降解,对人和动物非常安全。④细菌素能够在动物体内发挥作用(抑制病原菌的生长),但细菌素在发挥作用的同时又不会影响肠道内正常的菌群平衡。大多数细菌都能产生细菌素,因此,细菌素作为大规模的天然储备是细菌素全面取代抗生素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需要对更多的细菌素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将细菌素运用于相关的治疗选择中。
目前,人们已经将细菌素作为天然食品防腐剂或食品中添加剂应用于食品工业[33]。细菌素在畜牧业中作为饲料添加剂应用,在药品、化妆品以及动物保健中也有应用。细菌素具有广阔的前景,需要深入的研究使细菌素得到充分应用。
6 展望
肠球菌作为机会性致病菌,随着住院时间的延长以及抗菌药物治疗的不合理和不当使用,导致VRE的出现,因其传播迅速,而选择治疗药物的局限,并且伴随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逐渐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医院内感染菌之一,先前认为的抗生素空白和所谓的后抗生素时代似乎已经来临。全球范围内都需要有新的抗菌药物来对抗细菌耐药性,尽管细菌素目前尚未被充分利用,但它们在治疗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应通过深入了解它们的作用方式以增加其用途。
有关VRE的研究数据较少,在耐药和传播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有待完善。VRE检出率不断升高,同时耐药机制复杂化,传播机制不明。因此,应对VRE进行长期的流行病学监测,限制万古霉素和头孢菌素等广谱抗生素的使用,建立本地VRE数据库,防止VRE的发生和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