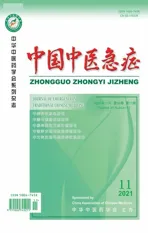中医学对鼠疫防治之认识*
2021-03-28陈腾飞齐文升马成杰刘清泉
陈腾飞 张 伟 齐文升 马成杰 刘清泉△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北京 100010;2.中医感染性疾病基础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10;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北京 100015;4.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北京 100053)
鼠疫是我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我国存在12种类型的鼠疫自然疫源地。鼠疫的致病原为鼠疫耶尔森菌,主要在啮齿类动物之间通过蚤类相互传播。鼠疫在自然疫源地时有散发病例,目前治疗鼠疫的特效药物为链霉素,为提升治疗效果常与其他种类抗菌药联合应用[1]。
鼠疫的流行历史久远,据医史学家范行准研究[2],“鼠疫可能在我国2世纪左右已由印度传入”,对于鼠疫大流行,范氏认为“鼠疫自12世纪30年代在广州登陆之后,就蔓延了今之山西、河南、河北诸省,人们用它的症状来做病名,如‘时疫疙瘩’‘大头天行’‘阴毒’‘阳毒’等。它们已具备了鼠疫中的败血症、腺鼠疫、肺鼠疫等的病象”。本文就古代中医参与鼠疫防治的概况、鼠疫的中医病名、发病特点、核心病机、治则治法、方药进行梳理,并探讨在当今具备先进的防疫条件和特效药物的情况下,中医在鼠疫治疗中可发挥的作用。
1 中医参与鼠疫防治的历史概况
范行准研究认为《金匮要略》的阴阳毒可能包含了鼠疫。但笔者认为阴阳毒其症状简略,尚不足为凭,在此之后的医学典籍中有更类似鼠疫的记述,如《千金翼方》论述[3]“凡恶核似射工,初得无定处,多恻恻然痛,时有不痛者,不痛便不忧,不忧则救迟,救迟则杀人,是以宜早防之……初如粟或如麻子,在肉里而坚似皰,长甚速,初得多恶寒,须臾即短气”。金元四大家李东垣曾在济源遭遇“大头天行”之疫[2],并拟定普济消毒饮防治[4],范行准认为此次疫病即鼠疫。但此后关于鼠疫,始终无专著系统论述。直到清末广东鼠疫大流行[5],医家开始大量救治本病,并出版了一系列鼠疫专著。首部专著为吴宣崇所著《鼠疫治法》(1891年,广东),其次为罗芝园之《鼠疫汇编》(1891年,广东),尤其以罗氏著作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此后又出现了《急救鼠疫传染良方》(1894年,广东番禺)、《恶核良方释疑》(1901年,广东南海)、《鼠疫约编》(1901年,福建福州)、《鼠疫抉微》(1910年,江苏嘉定)等系列鼠疫专著[6]。当时清朝政府尚无公共卫生防疫体系,这些医家虽然挽救了大量的鼠疫患者,但比起十万余人的死亡而言,无疑杯水车薪。
1894 年法国人耶尔森至香港疫区分离出鼠疫杆菌,鼠疫的致病源始为世人所知[7]。1910年东北鼠疫暴发流行,清政府任用伍连德采用“封城”“隔离”等“切断传播途径”的防疫法,控制了鼠疫的蔓延,“肺鼠疫”可通过飞沫传播亦在此时被发现。从此,鼠疫的病原学和传播途径已经明晰,现代的隔离防疫措施也逐渐开始推广[8]。但当时针对鼠疫传染源的控制、发病人群的救治仍然缺乏有效手段,中医界仍在积极使用中医药方法继续鼠疫防治工作,鼠疫著述更是借助出版事业的发达大量问世。随着清政府1912年灭亡,国家陷入纷乱,缺乏强力有的行政干预手段,通过“切断传播途径”方法防控鼠疫已经难以施行,如1917年晋绥鼠疫流行时便难以达到1910年的隔离防控力度,鼠疫有蔓延态势,中医曹巽轩、孔伯华等申请得北洋政府许可,前往疫区救治患者并取得成效,著成《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9]。
2 中医对于鼠疫之病名及发病之认识
“鼠疫”这一病名最早即由中医提出,吴宣崇所著《鼠疫治法》即确定了“鼠疫”病名。在此之前的鼠疫历次流行中,人们根据鼠疫患者之临床症状赋予其病名,在医籍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命名有“核瘟”“疙瘩瘟”“大头天行”“阳毒”“阴毒”“蛤蟆瘟”“瓜瓤瘟”。各地因地域差异而出现的病名更是多样化,如“发人瘟”“起核瘟”“老鼠瘟”等,仅广东各县对于鼠疫之称呼便多达十余种[10]。在本病的流行中人们逐渐意识到本病发生与病鼠有关,但对于本病的暴发流行的认识,并未专注于病鼠,而是认为鼠疫作为一种“疫病”,其暴发流行与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罗芝园论鼠疫暴发原因云[11]“城市污秽必多,郁而成沴,其毒先见。乡村污秽较少,其毒次及。故热毒熏蒸,鼠先受之,人随感之,由毛孔气管入达于血管,所以血壅不行也”。曹巽轩、孔伯华等论述晋绥鼠疫暴发流行的原因时,对于鼠疫杆菌及其传播途径已经有了明确认识,但仍注重从自然环境气候等方面论述鼠疫流行之原因[9]“方今战事几遍全球,国内用兵亦经多时,马革裹尸,血流成渠,加之去秋大水为灾,入冬地气闭塞,一旦初阳上升,乖戾不正之气,随在皆可感触。苟卫生不能,表里兼至,即无传染之影响,亦恐不免。执此以观,则今流行时疫,又岂仅鼠疫之为患使然耶?”
对于人接触疫毒后的发病,易巨荪认为“疫者,天地恶厉之气也。人感毒气或从口鼻入,或从皮毛入,其未入脏与腑之时,必在皮肤肌腠经络胸膈之间”[12]。疫邪进而“直行中道,流布三焦,散漫不收,去而复合,病入血分,故郁而暴发”[9];“亦有因外感,或饥饱劳碌,或焦思气恼,触动而发”[9]。一旦发病,则疫邪充斥奔迫,轻浅者“微痛微热,结核如瘰疬,多见于颈胁腌膀大腿之间——尔时体虽不安,犹可支持”[11],重者即“脉闭体厥”[9]。以上医家论述,基本代表了当时中医界对于鼠疫起病原因、发病特点的认识。
3 中医对鼠疫病机演变及危重程度之辨识
鼠疫之发病,为疫毒之邪在血分郁而暴发,其核心病机为“热毒迫血成瘀”,此已成为治疗鼠疫之临床医家之共识。在此核心病机基础之上,不同患者之间因体质禀赋及病情轻重差异,病机演变有所不同。易巨荪认为[12]鼠疫之病机演变分入脏与入腑,入脏者死,出腑者愈,“脏,心肾也,在心则谵语,神昏直视,在肾则牙关紧闭,失音难治;腑,胃也。在胃虽谵语仍有清时,口渴,便闭,此病甚轻”。罗芝园认为本病在热毒成瘀之基础上,可见传表而现白虎汤证、传里而现承气汤证,毒甚而见热闭心包之证[11]。易氏与罗氏所言基本吻合,传表传里之白虎证承气证即“出腑”,毒甚至热闭心包即“入脏”。易巨荪所云“入脏”为心、肾二脏,是对鼠疫最严重传变结果的高度凝练概括,但在个体患者中,并不仅限于心、肾,“舌卷囊缩、手足瘛瘲”等“肝风”症状亦可见到。
中医对于鼠疫患者危重程度之辨识,主要从意识状况、躯体症状、脉象3个方面进行。
1)从意识状况对鼠疫患者危重程度之辨识:神清者病轻,谵妄烦躁者病重,躁扰不宁或昏迷如“尸厥”者病危,此为所有疫病危重程度之通用识别法,鼠疫亦不能例外。如吴瑞甫云[13]“其神气清者,可多迁延数日”;罗芝园云[11]“尔时体虽不安,犹可支持,病尚浅也”;易巨荪云[12]“在心则谵语,神昏直视,在肾则牙关紧闭,失音难治……在胃虽谵语仍有清时,口渴,便闭,此病甚轻”,此皆从意识改变的轻重程度来辨识鼠疫之危重程度。2)从躯体症状进行危重程度之辨识:罗芝园从淋巴结的外观和伴随症状进行辨识[11],轻症表现“核小、色白、不发热”;稍重症表现“核小而红、头微痛、身微热、体微酸”;重症表现“单核红肿、大热、大渴、头痛、身痛、四肢酸痛”;危症表现“陡见热渴痛痹四证”或发病即“面身红赤,不见结核”。易巨荪从淋巴结肿大与发热症状出现之时间先后,辨识鼠疫患者之轻重,其认为“大约以先发核为轻,热核并发次之,热甚核发又次之,病将终发核,始终不发核为重”;又从结核之部位辨识轻重,“以在顶,在胁腋,在少腹为重,在手足为轻”[12]。3)从脉象对鼠疫患者危重程度之辨识:曹巽轩等通过救治鼠疫发现杨栗山论瘟疫之脉完全适用于鼠疫,鼠疫患者脉象见“洪、长、滑、数”者为轻症;脉象见“沉”、“甚而闭塞”者为重症;脉象见“沉、涩、小、急”或“脉两手闭绝或一手闭绝”同时多伴见四肢厥逆者为危证;脉象见“沉涩而微,状若屋漏”或“浮大而散,状若釜沸”者为死证[9]。
4 中医对于鼠疫之治则治法及方药应用
鼠疫由疫毒侵袭人体而发病,治疗的基本原则在于透解毒邪。疫毒与正气相搏,出现“热毒迫血成瘀”之病机,针对此核心病机之治法为解毒、清热、活血[11]。中医在鼠疫防治中使用频率最高,有效率最高的方剂为王清任《医林改错》之解毒活血汤。但亦有医家在论述鼠疫治疗时,反对早期使用解毒活血汤,认为早期使用苦寒、破血之品,有阻遏气机之弊、开门揖盗之嫌,进而提出应早期透邪外出给邪以出路,如冉雪峰提出[14]“清芳润透”之“太素清燥救肺汤”与改良版的“急救通窍活血汤”。
民国时期关于鼠疫之论,百家争鸣,其间亦多有矛盾而不可调和之处。但如果还原历史进行辨析则发现,论述鼠疫之医家大约可分两类:一类为疫区之医家,所救治者大多为重症鼠疫,就诊时已是“热毒迫血成瘀”状态,故针对来势凶猛之疫情极力推广解毒活血汤,以救治更多患者,代表医家如罗芝园、吴瑞甫、梁达樵等;另一类为非疫区之医家,结合自身所治疗的鼠疫疑似病例或鼠疫轻症个案,从学术角度发论,代表医家如张锡纯、冉雪峰等。前者从临床需求立论,适宜于鼠疫暴发大流行医疗资源匮乏之时的“通治”;后者从学术严谨立论,适宜于救治鼠疫散发病例之时,或医疗资源充裕可以实现个体化精细化治疗之时;二者并行不悖,缺一不可。以下则融合二者以总结出中医对于鼠疫之完整认识。1)鼠疫之轻症:多选择四诊合参,灵活辨证施治,总体原则为“给邪气以出路”,避免寒凉阻滞气机,多选用王孟英“治结核方”、梁达樵“辟秽驱毒饮”、易巨荪所提倡之升麻鳖甲汤等加减,代表药物如银花、蒲公英、连翘、升麻、大青叶、鳖甲、生石膏、菖蒲、郁金等。2)鼠疫之重症:多选用解毒活血汤类方加减,代表方如参与福建鼠疫治疗的医家李健颐之“二一解毒汤”[15](按:即活血解毒经过21次改良后之版本),北方参与鼠疫治疗的医家曹巽轩等拟定有“温役之经验方”。3)鼠疫之危证:证见神昏、肢厥、身冷、瘀斑、脉伏等,通常先服用芳香开窍辟秽之急救中成药,如紫雪丹、安宫丸、神犀丹、紫金锭等,或配合针刺委中等处出血,以急开邪闭,继而使用上述重症处方大剂,一日数剂。4)鼠疫治疗中,不同患者会出现兼夹症、并发症等不同,对症加减之法亦极为丰富,如肺鼠疫咯吐血水予鲜芦根汁频频灌服,如败血症鼠疫服用解毒活血汤仍不效,予藏红花二钱煮水送服真熊胆等。鼠疫之预防,各医家亦曾拟定处方,或焚烧以辟秽,或内服以清热湿,在当时缺乏卫生防疫体系的情况下,起了一定的作用。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5 中医在当今鼠疫治疗中的作用
上文详述了古代中医针对鼠疫之治疗认识,本节重点探讨中医在当今鼠疫治疗中可发挥的作用。因鼠疫为自然疫源性疾病,尚无有效疫苗,难以彻底灭绝。且鼠疫菌株已经出现了耐药现象[16]。鼠疫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鼠疫杆菌导致的外毒素血症,可引起全身炎症反应,出现感染性休克、DIC、急性肾衰竭、意识障碍、呼吸衰竭(肺鼠疫更为常见)等[1]。抗菌药物在鼠疫治疗中虽然至关重要,但上述并发症并非单纯依靠抗菌药所能解决。患者的治疗需要重症医学的全方位参与,进行综合的脏器支持救治。中医在以往鼠疫的治疗中并非针对鼠疫杆菌起效,而在针对病机(即西医所说之病理过程)用药取效,所谓“热毒迫血成瘀”即剧烈的炎症反应诱发DIC的过程,解毒活血系列方即通过阻断此病理过程而取效。西医的特效药物可以解决病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中医所说的“毒”的产生和释放,液体复苏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医所说的“热”,也会掩盖或延缓中医所说的“迫血成瘀(DIC)”,但鼠疫患者基本的病理过程并未被改变,“热毒迫血成瘀”的核心病机依然存在,中医的清热解毒凉血活血治疗仍然存在优势。
对于腺鼠疫患者肿大之淋巴结,《鼠疫诊疗方案》处理建议为“予0.5%~1%的链霉素软膏涂抹,必要时可在肿大淋巴结周围注射链霉素并施以湿敷,病灶化脓软化后可切开引流”[1]。局部使用链霉素易诱导细菌耐药。中医针对腺鼠疫的淋巴结肿大积累之方药可促进淋巴结消散或促使其成脓,以便早期切开引流,从而缩短病程,减少抗菌药暴露时间,降低耐药菌的发生率。
在鼠疫大流行期间各型鼠疫皆有发生,但从资料记载来看,古代南方医家积累之鼠疫治疗经验更偏重于腺鼠疫、败血症鼠疫,对于肺鼠疫尚缺乏经验。现代通过特效抗菌药物及呼吸机支持治疗,肺鼠疫死亡率较前有所下降,但仍属治疗棘手之危重症。通过近期针对肺鼠疫病例的临床诊治观察发现,肺鼠疫归属“温热疫病”,符合“卫气营血”传变规律,又具有“三焦”传变的规律,热毒之邪或经口鼻伤及肺卫,病情深入出现热毒内闭,阳气暴脱之危症。结合中医温热病诊治理论及鼠疫治疗经验,肺鼠疫临证之时可分3期论治。1)初期症见发热,汗出,口渴,全身乏力,肌肉疼痛,咳嗽咯痰,偶有痰中血丝;舌红苔薄,脉数。证属邪犯肺卫,气分热盛,治疗宜清热解毒宣肺邪热,麻杏石甘汤、银翘散、白虎汤、清瘟败毒饮(小剂量)、清燥救肺汤可供选用。2)极期症见高热,有汗,咳甚,咯黄痰或脓痰,痰中带血,喘憋明显,皮疹,舌红绛,脉大,证属热毒闭肺,营血热盛,治疗宜清热解毒,凉营宣肺,宣白承气汤、清营汤、清瘟败毒饮(中剂量、大剂量)可供选用。3)厥脱期症见发热,喘促持续加重,四末不温,皮疹多,色暗,甚者神昏,脉微欲绝,证属邪闭阳脱,治疗宜回阳救逆,开闭泻热,独参汤、参附汤、生脉散、承气汤、安宫牛黄丸可供选用。
以上仅针对原发病鼠疫治疗中,中医药所能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探讨。而重症鼠疫患者,一旦脏器衰竭即属于危重症范畴,中医药在危重症救治中的优势作用亦会在鼠疫重症中得到体现,如针对ARDS的通腑泻肺、针对AKI的活血通络、针对应激性溃疡的通腑泻热等,均是中医药在鼠疫患者整个治疗中所能发挥的作用。随着传染病防护的严格执行,像1910年东北肺鼠疫那样,大批医师前赴后继牺牲的局面已经一去不返,中医临床医生可以在防护服下游刃有余地进行四诊合参,本着“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学术理念,在传染病防控中更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