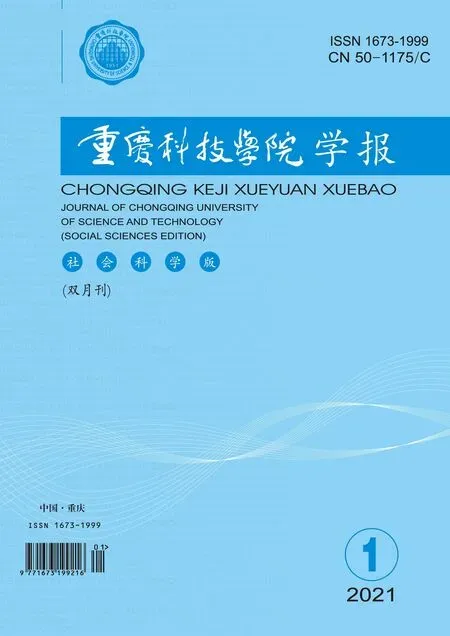论明太祖朱元璋的文化治国方略
2021-03-25杨孝青
杨孝青
(南京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南京 211167)
元朝统治者实行“马上治天下”政策,推行蒙古文化本位,中华伦理纲常多遭废弃。在元末群雄混战中,朱元璋率先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明朝立国以后,朱元璋从定礼乐、办学校、厚风俗等方面努力恢复社会秩序,推动了中华文明继续向前发展。
一、定礼乐 正纪纲
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礼是推行王道教化之根本纪纲。《礼记·曲礼上》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1]1可见,是否懂得礼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根本标志。礼的作用在于淳化民心,维系社会稳定。元朝虽然也制定了五礼,但只有祭祀之礼(吉礼)与前代较为相似,其他诸如军、宾、嘉、凶诸礼都源于本俗,“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惟祭祀稍稽诸古”[2]1181。而且,元代天子大多都没有亲自参加郊祭的习惯,一直到元文宗的时候才略有改变。元代祭祀有个重要特点就是敬畏上天和鬼神,并让巫祝参与相关活动。“北陲之俗,敬天而畏鬼,其巫祝每以为能亲见所祭者,而知其喜怒,故天子非有察于幽明之故、礼俗之辨,则未能亲格,岂其然欤?”[2]1181这与儒家倡导的“敬鬼神而远之”的精神大相径庭,反映其游牧民族固有的迷信习俗。
由于元朝统治者在吸收汉族先进礼仪文化方面的成效不足,在其统治后期,统治者骄奢淫逸,人情风俗流于浅薄,寡廉鲜耻者甚众,导致社会道德严重滑坡,这也是元朝政权覆灭的重要原因。朱元璋深知礼仪制度的重要性,视之为维系天下安定的精神防线,他即位之初便将制定礼仪规范作为优先任务。他说:“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自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变易几尽。朕即位以来夙夜不忘,思有以振举之,以洗污染之习……以复中国之旧。”(《明太祖实录》卷八)朱元璋认为,世道的治乱本乎人情风俗,在全社会倡导礼义忠信等纲常伦理,民风就会淳朴;若任由投机取巧风行,民众就会学会诈伪。为了扭转被元朝统治阶级败坏的社会风气,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朱元璋主张在借鉴西周礼义制度的基础上,制定新的礼仪规范以教化民众,他说:“礼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设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礼,修政莫如礼,故有礼则治,无礼则乱。居家有礼,则长幼序而宗族和;朝廷有礼,则尊卑定而等威辨。元以夷变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礼几乎熄矣!而人情狃于浅近,未能猝变。今命尔稽考典礼合于古而宜于今者,以颁布天下,俾习以成化,庶几复古之治也。”(《明太祖实录》卷七三)洪武年间,朝廷制定了五礼,相关礼仪规章制度也非常多,主要有《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诸司职掌》《稽古定制》《国朝制作》《大礼要议》《皇朝礼制》《大明礼制》《洪武礼法》《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礼书》等。这些礼仪规章制度彻底纠正了元朝遗留的礼仪陋习,其规模宏大远超汉、唐[3]1224。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无疑是礼仪制度最为重要的内容,是统治者证明其政权合法性来源于天命的重要体现。朱元璋以布衣之身进阶天子,高度重视通过祭祀来宣扬天命论。他要求祭祀不能照搬往朝旧习,下令对祭祀的仪式进行相应的改革,祭祀仪式不能过分繁琐,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否则,就是对神灵的不敬,是非礼的表现。明初将祭祀分为大中小三等,由礼部负责制定相关的规范:“明初以圜丘、方泽、宗庙、社稷、朝日、夕月、先农为大祀,太岁、星辰、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山川、历代帝王、先师、旗纛、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寿星为中祀,诸神为小祀。后改先农、朝日、夕月为中祀。凡天子所亲祀者,天地、宗庙、社稷、山川。”[3]1225大祀必须要有天子亲自参加,这既宣誓了君权至高无上的权威,也明确了君主亲自参加大祭的法定义务。中祀和小祀则安排相关官员进行致祀,民间可以祭祀谷神、土地神等神祇。
相见礼在日常生活中最为常用,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要遵守相见礼仪。洪武年初,朱元璋看见上朝百官礼仪失序,遂规定百官入朝规矩:“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侍从、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指挥使、六部尚书、侍郎等官许上殿,其余文武官五品以下,并列班于丹陛左右,违者紏仪官举正之。”(《明太祖实录》卷四八)朱元璋认为,元代的台宪官假公济私、相互倾轧,是导致政权灭亡的重要原因。因此,朱元璋在洪武三年(1370年)下令改革唐宋以来台宪官与地方官员相见的礼仪,要求台宪官不能恃权重而废礼,规定“其监察御史按察司佥事如出巡,当依品级拜知府、知州,知府、知州有罪,监察御史按察司官按问得实,则于市中依律断罪。如是则风宪官知有品级不敢凌辱有司,有司官既受风宪官礼,自知羞耻、畏惧,不敢干犯法度。此法虽异前代,然亦激劝之道也。”(《明太祖实录》卷四八)
朱元璋对元朝官民饮宴行酒过程中行跪拜之礼非常反感(元俗相见行礼时先跪一只脚,次以磕头表示拜见之敬意,随后再跪一只脚),下令予以禁止。洪武四年(1371年),诏定《官民揖、拜礼》,规定了行跪礼、揖礼和拜礼的具体要求,并禁止一切蒙古礼仪。拜礼根据不同情况分为“稽首”“顿首”“控(空)首”等,按照《周礼》的解释:“稽首,拜,头至地也;顿首,拜,头叩地也;空首,拜,头至手,所谓拜手也。”[4]962说明朱元璋推行官民揖、拜礼是以恢复儒家礼仪制度为指向。
乡饮酒礼始于周代,此后历代多有损益,到元代基本在民间绝迹。洪武三年(1370年),《大明集礼》将乡饮酒礼列入嘉礼;洪武五年(1372年)在全国各地儒学、里社及武职衙门推行之;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礼部申明乡饮酒礼,其要求有:“府、州、县则令长官主之,乡闾里社则贤而长者主之。年高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笃者次之,以齿为序,其有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杂于善良之中。”(《明太祖宝训》卷二)通过制定乡饮酒礼来教化民众,让百姓遵循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人伦之道。
“礼以道敬,乐以宣和。”有礼自然少不了乐,礼乐共同担负着社会教化的功能。《礼记·乐记》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1]237元朝是以夷变夏,元太祖铁木真时期的礼乐来自西夏旧乐,元太宗窝阔台曾大力收集亡金礼乐,并诏宣孔子五十一代孙孔元措来朝领衔组建通晓礼乐的乐官队伍(《元史·志第十九·礼乐二》)。但是,由于元朝统治者对汉族礼乐制度不熟悉,加之延续游牧民族的文化生活习性,其宫廷礼乐仍然沿用蒙古旧俗。本应庄重严肃的宫廷礼乐时常充斥着粗鄙不堪的淫词艳曲,“太常乐工,知以管定谱,而撰词实腔又皆鄙俚,亦无足取。”(《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二)而在地方官员举行的祭祀等庄重场合,淫曲俗乐充斥其中更是常见。据《元典章》记载:延祐五年(1318年)三月,一位监察御史亲眼目睹了京兆路地方学校举行的春秋释奠礼仪,“有司差遣俳优,鼓以俗乐,中间歌调,皆是淫曲。”(《元典章新集·礼部》)为此,该官员上书礼部建议选用专门乐师对地方学校的儒生进行培训,指导他们如何举行春秋祭祀。虽然该建议得到礼部批准,在地方上也进行了一些雅乐培训,但实际上推行效果极不理想,“礼崩乐坏”成为元朝治下的常态。例如,“天历二年(1329年)彰德路‘乐工执俗乐,歌哇淫之声’;至正三年(1343年)东平‘历二十九年,礼乐坏缺,无复留意者’。”[5]这些现象说明,元朝最高统治者虽然在主观上希望引入汉族的先进礼乐文化,但客观上却放任俗乐充斥庙堂与民间,传统的礼乐教化功能在元朝大为削弱。
朱元璋认为,古圣制作的音乐具有合天地万物之性情、陶冶情操、教化民众之功效,只有礼乐并行才能振朝廷之纲纪,然后天下可治。他说:“治天下之道,礼乐二者而已。若通于礼而不通于乐,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达于乐而不达于礼,非所以振纪纲而立大中。必礼乐并行,然后治化醇一。”(《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二)乐的功能在于宣扬广大和平之意,元朝废弃了雅乐,让淫词艳曲充斥社会,又让胡虏的音乐与雅乐相混杂,无以教化民众。朱元璋要求新制定的乐章,必须要尽行革除一切“流俗、諠譊、淫亵”的音乐。洪武四年,詹同、陶凯等人奉命制成《宴享九奏》乐章。朱元璋不仅推崇雅乐,而且在音乐方面也有相当造诣,一次他让朱升辨认五音,朱升却将宫音误认为徵音,因此遭到朱元璋的嘲笑。此外,朱元璋还亲自撰写了不少乐章和乐歌,如《方丘乐章》《合祭天地乐章》《先圣三皇历代帝王乐章》《大祀文并歌九章》等。
综上,洪武年间,朱元璋革故鼎新,不仅恢复了被元朝废弃的儒家礼乐文化,而且有所创新和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礼乐的教化功能,初步实现了“治国之道在礼,君子安、野人正”(《明太祖文集·命中书劳苗人敕》)的治国宏愿。
二、兴科举 办学校
开科举士是隋唐以来政府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唐朝科举重在考察诗赋,能考中进士的人数极少,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而且政治世家对朝政影响甚大,平民阶层进阶仕途渠道有限。宋代科举考试内容侧重经义,录取人数比唐代有所扩大,增加了平民阶层从政机会。元初几十年内没有实行科举,元太宗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开科举士,虽然待士甚优,但由于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汉人、南人不仅考试内容要比蒙古人和色目人难得多,而且位高权重的官爵都被权贵豪门占据,官吏来源也五花八门。“其出于宿卫、勋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于宣徽、中政之属者,重为内官。又荫叙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选用之科……诸王、公主,宠以投下,俾之保任。远夷、外徼,授以长官,俾之世袭。凡若此类,殆所谓吏道杂而多端者欤!”(《元史·志第三十一·选举一》)正是由于元朝选拔官吏的途径极其混乱,真正怀才抱德的贤才耻于与他们为伍而归隐山林,使官场的生态日益恶化。
为了匡正元朝科举之失,让朝廷能够真正选出德才兼备的人才,洪武三年,朱元璋下诏开科取士:“务在经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庭,观其学识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彼游食奔竞之徒自然易行。”(《明太祖实录》卷五二)洪武年间的科举考试由低到高分为院试、乡试和会试3个级别,院试报考者为“童生”,考试以州、县为单位,考取高等者称为“秀才”、一二等称为“录科”;乡试是省级考试,每3年一考,考取者称为“举人”,有资格做官。朝廷规定:包括全国各省及直隶府、州乡试通选500人为准。最高级为会试,3年一期,只有“举人”才有资格参加。考中者分为三甲:第一甲3名,赐进士及第,又称为“状元”“榜眼”“探花”,“状元”为从六品,“榜眼”“探花”均为正七品;第二甲17名,正七品,赐进士出身;第三甲80名,正八品,赐进士出身。乡试、会试都有固定程式:第一场,试五经义,各试本经一道,限500字以内;四书义一道,限300字以内。第二场,试礼乐论,限300字以内。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一道,要求文字精炼,不尚文藻,限1 000字以内[6]。明初科举考试废除了民族歧视政策,确定了《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录用人才规模也比元朝大为增加。
明朝开国之初百废待兴,急需治理国家的各种人才,但仅靠科举难以为朝廷选拔数量充足的优秀人才。因此,通过学校来培养人才就成为重要的途径。朱元璋指出:“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先于学校。自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弛,人纪荡然。加以兵乱以来,人习斗争,鲜知礼义……今朕一统天下,复我中国先王之治,宜大振华风,以兴治教。”(《明太祖实录》卷四六)明初在中央建立国子学(即太学)成为培养贤能人才的主阵地。国子学地址最初选在应天府学,随着生员规模扩大,洪武十四年,国子学搬迁至南京鸡鸣山下新建的校址内,次年改称国子监。洪武八年(1375年),中都凤阳也设立了国学,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废止,将其师生并入南京国子监。
国子监学生统称“监生”,来源较为多元化。举人入学者叫“举监”;品官子弟叫“荫监”,又称为“官生”;皇帝特别恩典者称为“恩生”。为使西南等地少数民族接受汉族先进文化,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下令接纳云南、四川等西南地方土官子弟入国子监接受教育,这部分学生被称为“土官”。此外,国子监还有来自日本、琉球、暹罗等国的外国学生等。国子监在课程教育方面以“四书”“五经”为主,还有《说苑》《大明律》《御制大诰》等,反映了国子监以儒学为根本取向的教育方针。国子监每月初一和十五放假,其余时间监生都要按照要求温习功课,每月还要举行一次考试。朝廷对监生及其家人在物质上给予优待,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但对于监生的功课和日常生活要求也十分严格。监生的衣着、饮食、步履都要符合礼仪。晚上睡觉有宿监负责管理,监生若要外出,需要向本班教官报告,并由斋长带其向祭酒汇报。对于犯错的监生,则由监丞按照学规给予相应的惩处。由于对监生的教育和管理甚为严格,国子监成为了明初选拔人才的摇篮,“历科进士多出太学,名碑由此相继不绝”(《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八)。不少人得到了朱元璋的重用,如洪武二十六年,提拔监生刘政、龙镡等64人为行省布政使、按察使,还有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监生当四方大吏者,更是不计其数。总的来看,洪武后期,由于科举制度日益完善,监生的出路已经大不如前。
为了让各地民众接受儒家经典教育,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下令在府、州、县广设学校。府设教授1名、训导4名,招收生员40人;州设学正1名、训导3名,招收生员30人;县设教谕1名、训导2名,招收生员20人。老师按照级别领取月俸,师生每人每月领取官粮6斗,政府还提供一定数量的肉类补助。教学内容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学生必须要精通一经。为打通民间教育“最后一公里”,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下令在民间设立社学,延揽师儒教育民间子弟。社学生员除了学习必要的儒学知识外,还要读《御制大诰》和《大明律》。由此,明初学校教育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国子学—府州县学—社学”完整的教育体系,连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也建立了学校,在当时的条件下,实现了教育面覆盖最大化,使明初学校出现了空前的兴盛。“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7]
明初学校教育之所以能够超越唐宋,跟朱元璋亲力亲为分不开。他不但将农桑和学校列入地方官政绩考核的内容,还要求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亲赴太学祭孔,并诏令各地郡县官员于每年春秋两季在地方庙学祭祀孔子,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朱元璋把孔子抬高至无以复加的地位,巩固了儒学在中华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三、正人伦 厚风俗
元朝统治中国90余年时间内,在婚丧嫁娶、日常人伦关系、生活习惯等方面维系蒙古文化习俗,不少陋习影响非常深远,败坏了社会风气。朱元璋即位以后,在文化习俗上拨乱反正,恢复中华文化。
元朝时期,蒙古人在婚丧嫁娶等方面存在诸多陋习,不守伦理纲常。婚姻上存在“兄收弟妇,弟收兄妻,子承父妾”等丑恶现象,朱元璋严厉斥责此类败坏中华伦理纲常的行为,称之为中国的不幸。因此,朱元璋在制定的《御制大诰》中对这种乱伦的婚姻予以明令禁止,违者予以治罪。在丧葬方面,有丧事期间,京师人民按照元朝旧俗,“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殽厚薄,无哀戚之情”(《明太祖实录》卷三七)。还存在火葬、水葬等与儒家丧葬制度不合的习俗。于是,朱元璋诏令中书省礼官制定“官民丧服”制度,以恢复儒家“慎终追远”的文化传统。例如,对无地的贫民,死后由地方政府提供义塚免费安葬;对于在外地任职去世的官员,由政府提供返乡安葬费。此外,朱元璋命令官民服饰一律按照唐朝的风俗穿戴,还禁止一切“胡服、胡语、胡姓”等。
尊老优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传统德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明太祖朱元璋对社会伦理道德非常重视,大力提倡尊老优老,其推行的养老措施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主要表现在:首先,在物质上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对于家中有70岁以上的老者,应该安排1名子女侍养,并免除该子女的差役;对于年龄达到80岁以上的老者,政府官员要定期慰问,并提供一定物质保障,规定:“若贫无产业、年八十以上者,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者,岁加赐帛一匹、絮一斤。其有田产能瞻者,止给酒、肉、絮、帛。”(《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八)对于鳏寡孤独废疾而生活不能自理者,由官办孤老院加以赡养;孤独残疾者若外出乞讨,所到之地的人民应该提供一点食物助其活命,若受到殴打,施暴者将会受到法律制裁。其次,在政治上提升老年人的社会地位。朱元璋对于京城和中都年龄在八九十岁以上的老人给予特殊礼遇,规定:“惟应天、凤阳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者赐爵里士,九十以上者赐爵社士,皆与县官平礼。”(《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八)朱元璋还注重发挥耆民(年高德劭者)的社会影响力。明初允许民众有冤情可以赴京告状,但有些诉状却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且不真实,耗费了政府资源。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开始控制越级上访,下令耆民帮助教化乡里,协助地方官处理“户婚、田宅、斗殴”等民间诉讼,从而把矛盾消除在基层。
孝居八德之首,是中华文化的遗传基因密码。朱元璋大力倡导“孝治天下”,将其作为厚风俗之本。他说:“人情莫不爱其亲,必使之得尽其孝,一人孝而众人皆趋于孝,此风化之本也。故圣人之于天下,必本人情而为治。”(《明太祖实录》卷四九)朱元璋推行孝道体现在多个方面,主要表现为:首先,身体力行加以倡导。早在吴元年(1367年),他就要求礼部记录其父母的忌日,每年按时加以祭祀。朱元璋称帝后回乡看望父老,要求他们教育乡村子弟要行孝悌之道。对于大臣的行孝之举,朱元璋也大力予以支持。如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同意有父母年事已高者,可以归家赡养。当元朝归降将领陈兴要求回家赡养80岁老母时,朱元璋慨然应允,并赐给他白金和衣帽。在选拔官员时,朱元璋要求将有孝悌德性的人推举出来。洪武十三年(1380年)十二月,全国各地所推举的“聪明正直、孝弟力田、贤良方正、文学才干”等人才至南京的多达860余人(《明太祖宝训》卷三)。其次,大力表彰有孝道者。朱元璋大力表彰孝行突出的官民,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例如,浙江金华儒士范祖干父母80多岁终老后,由于祖干家贫未能下葬,邻里为其营造冢圹,祖干悲哀3年如一日。朱元璋听闻其孝行后,表彰其所居住的地方为“纯孝坊”。(《明太祖实录》卷六)洪武八年,有山阳县民因罪当施以杖刑,其子要求代父受刑。刑部将事情向朱元璋作了报告,他下令对犯罪者予以赦免,并为“孝子屈法”作辩护。洪武十六年(1383年),表彰山西阳城县民叚节妻宋氏贞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将“东浙第一家”郑氏家族的郑济选为东宫“春坊左庶子”[8]。再次,制止违背人伦的愚孝。如郭巨埋儿、卧冰求鲤之类的愚蠢孝行,皆不在表彰之列。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青州府日照县民江伯儿母亲生病,他割下自己胁下的一块肉,煮熟给母亲吃,但其母仍未病愈。江伯儿又到岱岳祠祈祷,对神灵发誓:若他母亲病愈,则杀子以祀神。后来,他母亲病好了,江氏竟然真的把其3岁儿子杀了以祭神。朱元璋接到有司报告后大怒,指责江伯儿灭绝人伦,伤坏风化,下令将其杖一百,谪戍海南。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朱元璋认为:“惟俭养德,惟侈荡心。”他不仅将勤俭视为美德,更是视为事关社稷兴衰的德政。至正二十年(1364年)二月,在剿灭陈友谅之后,江西行省以陈友谅的镂金床进献,朱元璋认为它与孟昶的“七宝溺器”没有区别,遂下令将之打碎。朱元璋称帝后告诫太子诸王厉行节俭,他与马皇后等人都能以身作则,如朱元璋要求天子的乘舆服御等诸物应该用铜来代替金子。马皇后衣着朴素,衣服破了也舍不得换新的,“平居服大练浣洗之衣,虽敝不忍易”,并能体恤鳏寡孤独的年高老人,多余的帛丝赏赐给王妃公主,让她们体会到种蚕桑、做纺织的艰辛[9]。朱元璋对于身边官员的穿着奢侈行为也予以严厉制止,有一次他在奉天门看见散骑舍人衣极鲜丽,在得知该官员衣服花了五百贯钱,而这些钱可以够一家数口农民一年的花费,遂以严词斥责其暴殄天物,令其加以戒除奢侈。在宫殿的修建方面,朱元璋要求以朴素为主,不过分加以雕琢。此外,朱元璋还对官员乘坐交通工具的标准作了严格规定:在京三品以上的官员乘坐轿子,在京四品以下和在外官员必须骑马,七品以下的官员骑驴。超出标准者一律治罪。
朱元璋能够厉行节约既有吸取元朝奢侈而亡的教训,也有以上率下,开新王朝良好社会风气的愿望。由于明初以来奉行勤俭节约,国库渐渐充裕,百姓赋税较轻,政府没有财政赤字。明中期以后,这种勤俭节约优良传统逐渐丢失,奢靡之风盛行,朝廷逐渐入不敷出,逐渐走向衰败。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咏史》有言:“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可谓道出了历代王朝兴衰的根源。
四、几点评价
明太祖朱元璋是继汉高祖刘邦之后又一位功勋卓著的布衣天子。因其复杂的人生经历,故造就了其身后的诸多争议,如有人指责其大肆屠杀功臣,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等。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观点,不能因此抹杀其对复兴中华文化的历史贡献,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振兴中华”的国家观。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率先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建立了由汉族为主导的大一统中国,恢复了中华文化的勃勃生机,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朱元璋的“再造华夏”之功超越唐宗宋祖。他的“恢复中华”思想为孙中山先生所继承,成为近代以来激励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武器。
第二,以儒立国的指导思想。朱元璋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重用儒生,与刘基、章溢、叶琛、宋濂为代表的“浙东四贤”关系密切。明朝治国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释道思想辅之,开创了文化繁荣新景象。虽然朱元璋对文人以严酷著称,与茹太素饮酒时说“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但茹太素也以“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作答,反映了儒家知识分子的风骨。有明一朝,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风骨不输于唐宋任何一朝,敢于上书谏言的大臣不计其数,这正是朱元璋大力推行儒学教育的结果。朱元璋在位时期推行儒学教育,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国子学—府州县学—社学的一整套学校教育体系,使明朝的教育规模超越了唐宋时期。正是由于明初大力推行教育,才出现了明朝在文化和艺术上的繁荣局面,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明初还恢复了中华宗主国地位,扩大了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
第三,注重德治的文化传统。朱元璋恢复中华礼乐精神,将之作为治国之纲纪;设立养济院,收留孤苦无依的人,设立漏泽园,安葬死去的贫民,推行尊老优老措施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肃清元朝在婚丧嫁娶等方面的文化陋习,回归儒家伦理传统;大力倡导中华孝道,表彰事迹突出的孝行,反对愚孝;大力倡导勤俭节约,并且能够以上率下,开明王朝风清气正之局面,体现了“厚德载物”的文化精神。
当然,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朱元璋恢复中华文化的措施更多是为维护自身统治利益的需要,不可避免带有局限性,但不能因此否定朱元璋在复兴中华文化方面的历史贡献。朱元璋所推行的中华文化本位主义不仅影响了明代,而且对清代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历史上有“清承明制”之说。清康熙帝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亲题“治隆唐宋”,肯定了他的丰功伟绩。清代名臣张廷玉对明太祖高度赞誉:“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风教……用此子孙承业二百余年,士重名义,闾阎充实。至今苗裔蒙泽,尚如东楼、白马,世承先祀,有以哉。”[10]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对朱元璋开创明朝也给予高度评价:“明承法纪荡然之后,损益百代,以定有国之规,足与汉唐相配。唐所定制,宋承之不敢逾越,明所定制,清承之不敢过差,遂各得数百年。”[11]34总之,明太祖朱元璋对复兴中华文化居功至伟,应充分肯定其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