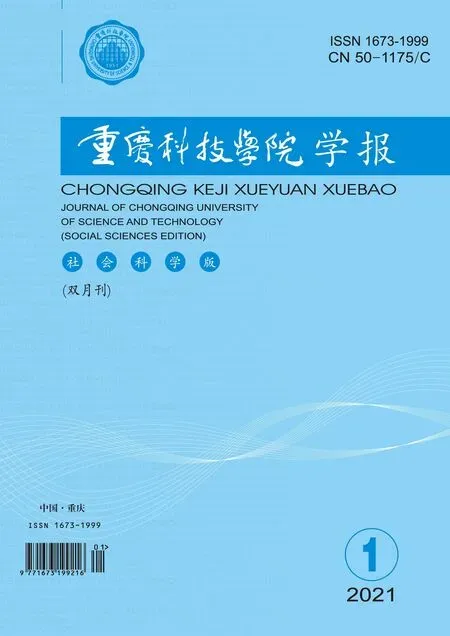唐宋《杞菊赋》与文人情怀
2021-03-25张申平李荣菊
张申平 李荣菊
(重庆科技学院,重庆 401331)
唐宋文人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和高深的艺术修养,也有着雅致的生活趣味和充盈的精神寄托。日常生活中的一花一草、一石一水等,在他们的笔下都充满了人生况味和思想内涵。研读陆龟蒙《杞菊赋》、苏轼《后杞菊赋》发现,“杞菊”与“脱粟”这些寻常茶饭有着别样的文化内涵,也折射出唐宋文人丰富深邃的情怀。
一、枸菊的功用与文化意蕴:轻身延年,比德兰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药膳同源。枸杞和菊花这两味中药也因其药性配伍而合称“杞菊”,并被诗词歌赋所吟咏。中华传统医学认为,枸杞全身是宝,春采枸杞叶名曰天精草,夏采花名曰长生草,秋采子名曰枸杞子,冬采根名曰地骨皮。枸杞具有补肾生精、养肝明目及安神等功效。《神农本草经》认为:“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1]现代医学认为,枸杞具有降血糖血脂、抗动脉硬化等多种医药价值。
古代诗词多有吟咏枸杞之作。例如,唐代刘禹锡《枸杞井》道:“枝繁本是仙人杖,根老能成瑞犬形。上品功能甘露味,还知一勺可延龄。”描述枸杞药树老枝千姿百态,可成犬状,其质料坚固可为手杖。宋代苏轼《枸杞》称颂“神药”枸杞“根茎与花实,收拾无弃物。大将玄吾鬓,小则饷我客。似闻朱明洞,中有千岁质。”宋代陆游《道室即事》道:“松根茯苓味绝珍,甑中枸杞香动人。劝君下箸不领略,终作邙山一窖尘。”陆游《玉笈斋书事》道:“雪霁茆堂钟磬清,晨斋枸杞一杯羹。隐书不厌千回读,大药何时九转成?”宋代蒲寿宬《枸杞井》言:“四时可以采,不采当自荣。青条覆碧甃,见此眼已明。目为仙人杖,其事因长生。饮此枸杞水,与结千岁盟。”宋代释文珦《幽处》言:“洗眼菖蒲水,轻身枸杞根。”宋代赵庚夫《清泉》言:“衰齿尚能餐枸杞,余龄断未泣牛衣。”宋代方回《治圃杂书二十首》言:“新立蒲萄架,初尝枸杞苗。”宋代周文璞《既离洞霄遇雨却寄道友》言:“重来只要斋盏饭,副以常堂枸杞羹。”看得出枸杞是唐宋人日常生活中深爱的珍品,或饮或食,希冀借此康体健身、延年益寿。
至于作为梅、兰、竹、菊“四君子”之一的菊花,更是深受国人喜爱,被赋予了吉祥、长寿、坚贞、清高等多种文化品质。清代刘灏称菊花“久服令人长生,明目,治头风,安肠胃,去目翳,除胸中烦热、四肢游气,久服轻身延年”(《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四十七)。中国古代有“比德”的文化传统,文人雅士们在吟咏吐纳之间津津乐道菊花的品性和象征意义。宋代刘克庄《题建阳马君菊谱》云:“菊之名著于周官,咏于诗骚,植物中可方兰、桂,人中惟灵均、渊明似之”,其《念奴娇·菊》称道菊花“尚友灵均,定交元亮,结好天随子”。宋代刘蒙泉《菊谱·序》言:“予尝观屈原之为文,香草龙凤,以比忠正,而菊与菌桂、荃蕙、兰芷、江蓠同为所取。又松者,天下岁寒坚正之木也。而陶渊明乃以松名配菊,连语而称之。夫屈原、渊明,实皆正人达士坚操笃行之流,至于菊犹贵重之如此。是菊虽以花为名,固与浮冶易坏之物不可同年而语也。且菊有异于物者。凡花皆以春盛,而实皆以秋成,其根柢枝叶,无物不然。而菊独以秋花悦茂于风霜揺落之时,此其得时者异也。有花叶者,花未必可食,而康风子乃以食菊仙。……夫以一草之微,自本至末,无非可食,有功于人者;加以花色香态,纤妙闲雅,可为丘壑燕静之娱。然则古人取其香以比徳,而配之以岁寒之操,夫岂独然而已哉。”[2]这段话对菊花的好处描述得可谓周全。三国魏将钟会《菊花赋》言菊花之“五美”道:“圆华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流中体轻,神仙食也。”[3]这就简明概括了菊花的贞正、高贵、谦让、劲直、益生等美德。
二、陆龟蒙《杞菊赋》:隐逸者的安贫乐道与追慕圣贤
唐代诗人陆龟蒙(836—881年)自号天随子,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六世祖陆元方为武则天时期宰相,五世祖陆象先唐玄宗时亦为相,龟蒙父则进士出身。陆龟蒙早年有光复家门之志,惜乎举进士不第,后长期沉沦隐居,诗文与皮日休齐名,世称“皮陆”。《新唐书·隐逸传》称陆龟蒙“不喜与流俗交,虽造门不肯见。不乘马,升舟设蓬席,赍束书、茶灶、笔床、钓具往来。时谓江湖散人,或号天随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渔父、江上丈人。后以高士召,不至。”[4]陆龟蒙性情高洁,不乐为官,自认为是心散、意散、形散、神散的散淡之人。他追慕陶渊明,认为其“靖节高风不可攀”(《漉酒诗》),又言“我醉卿可还,陶然似元亮”(《纪事》),“往往枕眠时,自疑陶靖节”(《和酒中十咏·酒床》),感觉自己距离陶渊明并不遥远。陆龟蒙亦钟情于菊花,其《重忆白菊》云:“我怜贞白重寒芳,前后丛生夹小堂。月朵暮开无绝艳,风茎时动有奇香。何惭谢雪清才咏,不羡刘梅贵主妆。更忆幽窗凝一梦,夜来村落有微霜。”其《杞菊赋》生动描绘了宅前宅后树以杞菊的“春苗恣肥”景象,叙述了自己掇拾杞菊不已给外人带来的困惑。世俗之人认为他完全可以将满腹经纶售与官府或者富贵之家,何必“君独闭关不出,率空肠贮古圣贤道德言语”而自苦如此。这使得陆龟蒙哭笑不得,只好以赋明志。赋中“偕寒互绿”的杞菊被作者视为精神寄托,其“或颖或苕,烟披雨沐”的生机勃勃景象,是作者独立桀骜个性和旺盛生命力的象征。虽然是“我衣败绨,我饭脱粟”,穿着破旧的衣服,吃着粗茶淡饭,但依旧向往着饱食杞菊这世间的高贵盛宴,故而“羞惭齿牙,苟且粱肉”,为那种蝇营狗苟的人生感觉羞愧和悲哀。
陆龟蒙《杞菊赋》的思想内涵集中表现为安贫乐道,追慕圣贤,亦即宋代周敦颐等理学先驱所推崇的“孔颜之乐”。《论语·雍也》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5]65孔子赞美他最为“好学”的学生颜回的安贫乐道精神,还主张“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5]80。陆龟蒙宁愿以“空肠”来储存“圣贤道德”且乐在其中。这情形正如周敦颐说的那样:“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6]作为一个隐居求道者,陆龟蒙不以日食杞菊为苦,把杞菊视为自己人生追求的寄托,这在唐末是难能可贵的。陆龟蒙寄情于杞菊,这显示了他不同于凡俗,不愿与世周旋、同流合污的思想和人格境界。陆龟蒙《杞菊赋》表现安贫乐道、追慕圣贤的“孔颜之乐”,这和后来宋代文人产生了思想上的巨大共鸣。
三、苏轼《后杞菊赋》:能文者的旷达超然与无往不乐
苏轼(1037—1101年)作为宋代“能文者”其学术特色和思想境界颇不同于理学家朱熹、张栻这些“知道者”。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十一月始,苏轼知密州两年。密州位于京东路东部,因治所诸城为汉之东武县,故宋人常称“胶西”“东武”。当时此地自然灾害连年发生,苏辙曾言苏轼:“既得请高密,其地介于淮海之间,风俗朴陋,四方宾客不至。受命之岁,承大旱之余孽,驱除螟蝗,逐捕盗贼,廪恤饥馑,日不遑给。”[7]苏轼贬知密州,原想与身处齐州的苏辙相近,不料密州境况如此不堪,故性情直率的他作诗倾诉道:“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绿蚁沾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其二)》)干旱、蝗虫造成饥荒、盗贼横行,生灵涂炭,甚至有百姓抛弃子女。苏轼这些为百姓诉苦的诗歌后成为政敌罗织其罪名的依据,他们弹劾苏轼讥讽新法,“讥讽朝廷减削公使钱太甚”,罗织了差点让苏轼送命的“乌台(即御史台)诗案”。苏轼此时所作《后杞菊赋》虽受到陆龟蒙的影响,但其创作心境和陆龟蒙差别很大,两人的人生际遇和性情学养也颇有不同,故作品的题旨迥异其趣。陆龟蒙出于“羞惭齿牙,苟且粱肉”的“君子固穷”心态,有意识拒绝“好事者”“屠沽儿”的酒肉,虽身处“千乘之邑”而“忍饥诵经”,惟杞菊是食。苏轼食用杞菊经过了由单纯果腹到精神愉悦的变化,其身处“敝邦”又逢饥荒、蝗虫、盗寇等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地方官日子也拮据,衣食之忧发自于肺腑。东坡具有直率本真、通达可爱的个性,当他与刘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后“扪腹而笑”,幡然领悟陆龟蒙钟情杞菊的妙处,其食杞菊经过了由被动到主动、由自嘲到自觉的过程,实现了由物质需要到精神满足的超越。苏轼借助主客问答自嘲贵为太守,却日食杞菊,也含蓄讽刺新法推行不合理加重了百姓的苦难。苏轼思想与苏洵一脉相承,融合儒释道多元文化,虽驳杂亦通达。苏辙尝谓苏轼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8]庄子“无所待”“与物俱化”的人生价值观都从骨子里濡染了苏轼。人生苦短,“如屈伸肘”,故对贫与富、美与丑等都应有超脱的看法。芸芸众生或食“糠核”或食“梁肉”,或“瓠肥”或“墨瘦”“卒同归于一朽”,与万物同迁化。苏轼之旷达让人感叹弗如,他在饥饿和逆境中“以杞为粮,以菊为糗”,不但没有一味沉沦抱怨,反而产生了对“西河、南阳之寿”的不懈追求,实现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超越。
苏轼的解脱思想在其同时期的其他作品,如熙宁九年(1076年)元月所作《超然台记》中有着更为明确的流露,这可和《后杞菊赋》互证。苏辙曾言苏轼在密州“后少安,顾居处隐陋,无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废台而增葺之,日与其僚览其山川而乐之。”[9]《老子》曾言:“虽有荣观,燕处超然。”[10]可见,超然台是东坡所修葺的登高远瞻、“放意肆志”的自放之所。苏辙为其命名“超然”,以明东坡“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之志。《超然台记》言:“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凡物皆有可乐,这个认识的产生和密州经历分不开。东坡言:“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密州任上,苏轼因祸得福,不但饱尝杞菊之美,而且体味到守拙养生、随缘自适之乐,其称赞超然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11]如果说东坡《后杞菊赋》还流露出若干生活的苦难和无奈,诗人思想经过政治风波正努力趋向平静,而《超然台赋》则可以见得出东坡的真超然。他在元祐六年(1091年)知颍州时再次提及密州斋厨索然,“采杞聊自诳,食菊不敢余”(《到颍未几,公帑已竭,斋厨索然,戏作》)的拮据生活,心态亦安然自适。苏轼的命运及其在《后杞菊赋》中表达的人生理念和生活态度深深感染了同时代的文人,如时任临淮主簿的张耒曾应苏轼之约和作《杞菊赋》以勉励同侪、坚固己志[12]。
四、张栻《续杞菊赋》:知道者的中和冲淡与以道自任
张栻(1133—1180年)字敬夫,丞相张浚之子,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和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其诗歌被南宋罗大经称赞为“闲澹简远,德人之言”[13]。张栻对菊花情有所钟,他赞美菊花高洁独立的品质和德风,“不肯竞桃李,甘心同艾蒿。德人一题品,愈觉风味高。”(《题曾氏山园十一咏·菊隐》)张栻称许陶渊明“人品甚高,晋宋诸人所未易及,读其诗,可见胸次洒落”[14],其《题城南书院三十四咏(其一)》道:“今年少雨菊花迟,青蕊方开三两枝。但得悠然真意在,青山何处不相宜。”张栻把陶渊明菊花诗的旨趣和自己的生活感受融洽地结合在一起。另外,张栻菊花诗的独特之处是把菊花和“家园”“家国”关联起来,视其为心性、灵魂家园的象征,如“梦回故园好,兰菊罗中庭。”(《次韩机幕韵》)“却指飞鸿烟漠漠,故园茱菊老江潭。”(《九日登千山观》)“年年桂绽菊开时,长忆芳樽共一卮。”(《寿定叟弟》)“行李秋将半,家园菊正滋。”(《曾节夫罢官归盱江以小诗寄别》)张栻父亲张浚系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唐宰相张九龄弟九皋之后。张浚主持北伐失败,贬谪病死,自觉无颜见故园祖先,故叮嘱葬其在湖湘衡山之下。张栻随其父多年湖湘为官和讲学,死后亦葬湘江之畔。故而绽放在寓所园圃中的菊花,成了张栻潜意识中的家园标识。
作为理学家的张栻,其《续杞菊赋》反映了推崇中和所萃、天壤正味的杞菊之眷。该赋作于淳熙六年(1179年)春,其时张栻除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抚本路,其为政颇有作为,使北方金朝惊叹“南朝有人”。张栻曾在其居家讲学的潭州(今湖南长沙)城南书院,种植了许多杞菊。其《续杞菊赋》作于江陵(今湖北荆州),回忆城南书院纳湖之阴杞菊“雪销壤肥,其茸葳蕤”的茂盛景象。开篇写仲春季节“非花柳之是问,眷杞菊之青青”,烹饪杞菊方法是“汲清泉以细烹,屏五味而不亲”,对杞菊的简单加工保持了其“甘脆可口,蔚其芬馨”的特性,以至诗人胃口大开,“尽日为之加饭,而他物几不足以前陈”。张栻还像东坡一样“饭已扪腹,得意讴吟”,然张栻之乐食杞菊和苏轼颇有所不同,苏轼贬谪胶西遭受党禁之荼毒,故“叹斋厨之萧条,乃览乎草木之英”,这多少有些对现实的无奈;而张栻其时为官生活境况尚可,其“乐从夫野人之餐”让常人觉得近乎做作,以至于提出“不然得无近于矫激,有同于脱粟布被者乎”的疑问。
这正是张栻思想不同于苏轼之所在。赋中“天壤之间,孰为正味”的质问,引出“惟杞与菊,中和所萃。微劲不苦,滑甘靡滞”的好处。在张栻的眼中,山珍海味虽“极口腹之欲”,但未必裨益身心,相反却可能给五脏六腑带来累赘;倒是杞菊“既瞭目而安神,复沃烦而涤秽。验南阳于西河,又颓龄之可制。此其为功,曷可殚纪”,他充分肯定了杞菊的药用价值。宋人林洪《山家清供》中“紫英菊”条记载了菊花和枸杞搭配的家常吃法:“春天釆苗叶洗焯,用油略炒煮熟,下姜盐羹之,可清心明目,加枸杞尤妙。”[15]张栻称许杞菊“和合”“中和”的保性和神属性及功效,这恰是宋儒非常看重的文人秉性。故有研究者指出,张栻《后杞菊赋》“寓意于物,以‘杞菊’意象呈现中和之性,表现物我相得的自适心态”“在理学家的经学文本和文学文本间存在着互文性,常能互为阐释资源”[16]。
张栻《后杞菊赋》除表达对杞菊“中和”之性的肯定外,还流露了终身与之为伴且要“贻夫同志”使其沾溉恩泽的愿望。张栻以古圣贤自期作《希颜录》,渴望成为孔颜后继传道者,投身书院教育,是张栻传道之举。绍兴三十一年(1161),张栻将湘江东畔的妙高峰居所改办为城南书院。隆兴二年(1164年),湖南安抚史刘珙修复岳麓书院,委任张栻为书院主教,自此张栻常往来于湘江两岸的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后朱熹于乾道三年(1167年)秋由福建崇安赴湘,逗留两月有余,不仅在书院讲学,还与张栻就《中庸》以及理学的“中和”“太极”等命题进行切磋,留下许多传播学术思想和智慧的佳话。在张栻家居读书、讲学传道、修身交友的城南书院,不仅有着青青杞菊,还有志同道合的师友“高论唐虞,咏歌书诗”。宋代理学家热衷于书院教育,推崇“孔颜之乐”和“曾点之志”。从周敦颐到程颢、程颐,再到朱熹和张栻等人,宋儒崇尚颜回以道自任、安贫乐道的人生情怀和处世态度,还有那种个人情趣和理想壮志浑然一体的非功利性超越境界,而这正是理学家们追求成圣成贤、实现“圣贤气象”的必由之路。由此就不难理解张栻为何会“眷杞菊之青青”,因为杞菊之眷代表对“中和”之性的推崇,体现了对“孔颜之乐”的向往,是团结同志追求“圣贤气象”的宿愿所在。难怪张栻要满怀深情地嗟叹:“嗟乎,微斯物,孰同先生之归!”
五、眷杞菊与脱粟饭:唐宋文人的精神标识
从陆龟蒙、苏轼到张栻,他们《杞菊赋》所表现的思想内涵,恰恰反映了唐宋社会转型期文人思想转向内在的时代趋势。赋作的时代和个性特色鲜明,反映了当时文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由于写作的时代和思想出发点不同,因此不宜轻易断言作品孰优孰劣,或思想孰深孰浅。陆龟蒙生活在唐朝末年,他淡薄功名,隐居求志,延续了古代隐逸文化中文人为保全人格而自甘清贫的优秀品质,同时兼有儒家以道自任、追慕圣贤的理想信念,这和单纯的消极避世、遁迹江湖有所不同。北宋苏轼的思想受道家影响,张扬自我追求个性自由,因而赋作具有强烈的思想情感和主观色彩。日食杞菊不仅带给东坡健康长寿,也让他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有了超越性认识,处世态度更趋于超脱和旷达。南宋张栻具有深厚的理学修养,对杞菊的认识更贴近于其“中和”药性所涵摄的哲学意义,流露出对“人间正味”的探求和对志同道合者的呼唤,这反映了当时文人个性修养的内敛节制和对道德心性的关注,体现了宋人精神气质和意识形态的变化。
宋代文人在推崇杞菊的同时,还对脱粟饭念念不忘。杞菊和脱粟成了他们精神追求的象征。陆龟蒙《杞菊赋》念叨“我衣败绨,我饭脱粟”,苏轼《超然台赋》亦曰“瀹脱粟而食之”“乐哉游乎”,张栻《续杞菊赋》也提及“从夫野人之餐”“有同于脱粟布被者”。脱粟就是糙米,即只去谷壳不加精制的米。古代脱粟饭不仅仅是生活清贫的表现,更多时候是高人雅士砥砺志节、廉洁自守的象征。例如,北宋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年)在西京河南府洛阳,聚集了一批以司马光为中心的旧党致仕文人以及洛党和游学士子等,先后有文彦博、范镇、富弼、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邵雍、程颐、程颢等著名人物。这一时期的文人雅士先后举办了五老会、耆英会、同甲会等恬然自适的文化沙龙。《宋史·范纯仁传》记载:“时耆贤多在洛,纯仁及司马光,皆好客而家贫,相约为真率会,脱粟一饭,酒数行,洛中以为胜事。”[17]简陋朴素的脱粟饭成为了风雅盛事,这才是文人返朴归真的真风流。
同样钟情杞菊和脱粟的还有和张栻并称“朱张”的理学家朱熹。他有《药圃》诗道:“渐看杞菊充庖下,即见芝英入笼中。”《菜畦》道:“雨余菜甲翠光匀,杞菊成畦亦自春。骨相定知非食肉,可能长伴个中人。”朱熹在给陈亮的信中言:“近方措置种几畦杞菊,若一脚出门,便不得此物吃,不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撺掇,留取闲汉在山里咬菜根,与人无相干涉,了却几卷残书,与村秀才子寻行数墨,亦是一事。”[18]这些话妙趣横生让人忍俊不禁,吃杞菊、咬菜根在朱熹眼中都不是小事,这反映了朱熹对南宋社会政治的失望,因而甘心退守山野,栖居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朱熹的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在民间创办书院、聚徒讲学和编撰刊刻典籍,杞菊和脱粟饭自然成为他乡野书斋生活的家常便饭了。但也有凡夫俗子、酒囊饭桶之类人物,对脱粟饭嗤之以鼻。朱熹在武夷山讲学的时候,慕名求学者不计其数,门下弟子云集。由于朱熹多年都是担任半俸的祠官,生活甚为拮据。即便是有些家境优裕的学生投身门下,朱熹仍然需要刻书补贴教学日用,但书院生活运作依然是捉襟见肘,师生饮食常常就是脱粟饭和蔬菜,没有丰盛的菜肴。《宋史》记载有一个叫胡纮的进士,“未达时,尝谒朱熹于建安,熹待学子惟脱粟饭,遇纮不能异也。纮不悦,语人曰:‘此非人情。只鸡尊酒,山中未为乏也。’遂亡去。”[19]这个没有吃到鸡喝到酒的士林败类,在后来迫害朱熹等人的党禁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诋毁攻击朱熹为“伪学罪首”。由此可见,杞菊、脱粟已经不再是宋人日常饮食中的寻常事物,它们作为一种文化标签,是区别道德高下、品质优劣、境界深浅的分水岭和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