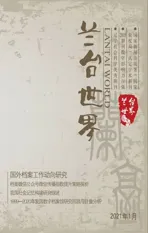我国档案学热点问题的可视化研究
2021-03-16杨棉月
杨棉月
一、引言
档案是社会组织或个人在以往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清晰、确定的原始记录作用的固化信息[1]6。现代档案学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新的研究视角、理论范式、档案载体层出不穷,档案学学科的发展呈现出非同寻常的繁荣的知识图景[2]40-44。档案学的研究方向越来越广泛,档案学的研究热点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变化。如社会记忆、电子文件、社交媒体以及大档案、大数据等关键词的出现,可以视为档案学学术外延的拓展。如何从档案学这一知识领域中,从海量的档案学文献中找到学者们最感兴趣的主题,抑或从中挖掘出最为重要和关键的有效信息,这就需要借助科学文献可视化软件。
借助CSSCI 数据库,来源期刊限定为《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以主题检索方式进行。检索时间设定为1999—2018 年,二级学科设定为“档案学”,以“档案”作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检索4765 篇文献,除去卷首语、人物介绍、政府信息、纪念性论文、学术会议述评等关联不大的文献,得到4211 篇文献。
二、我国档案学研究前沿热点分析
1.作者合作网络分析。运行CiteSpace,得到1999—2018 年我国档案学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如图1 所示。

图1 1999-2018 年我国档案学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图1 中,1999—2018 年我国档案学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谱节点的大小表示作者的发文量,连线表示两位作者之间有合作,连线的粗细表示合作的强弱。由图1 可知,选取的4211 篇文献的作者有626 个,作者之间的连线为1297 条,作者共引图谱的网络密度仅有0.0066,这表明档案学研究领域学者之间的研究合作非常弱。图谱的主要节点有“丁华东”“张美芳”“陈忠海”“倪丽娟”“马仁杰”等。
经过CiteSpace 软件分析后,导出1999—2018 年我国档案学研究发文量排名前10 的核心作者信息数据,如表1 所示。在档案学研究领域,1999—2018 年发文量排名前10 的高产作者依次是丁华东、张美芳、陈忠海、倪丽娟、马仁杰、徐拥军、王协舟、李财富、周耀林、傅荣校,这些学者在档案学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其中,来自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的丁华东长期从事档案学教学、科研工作,在档案学理论范式、档案与社会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等方面形成研究特色[3];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的张美芳主要研究档案有害生物防治、传统档案制成材料耐久性以及电子文件的保护等;来自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陈忠海主要研究方向为档案法立法与执法、档案网站建设调查与评估、档案学术评论[4];来自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倪丽娟一直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专业教学工作,主要研究档案管理学、档案信息资源等[5];来自安徽大学管理学院的马仁杰主要研究方向是档案利用理论与实践、政府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文秘制度与办公室管理、历史文献编纂与利用[6]。从年度分布上来看,高产作者的发文量波动变化较大。发文量排名前10 的核心作者,发文年份最早是陈忠海、马仁杰,其次是丁华东、张美芳、周耀林、傅荣校,李财富最早发文是2001 年,倪丽娟、徐拥军最早发文是2003 年。

表1 1999—2018 年我国档案学研究核心作者信息(TOP≥10)
2.关键词的共现分析。在CiteSpace 软件中,设置分析时间为1999—2018 年,时间切片为1 年,Node Types选择Keyword,每个时间切片选择Top50,Top N%=10,C/CC/CCV 的值分别为(2,2,20)(4,3,20)(3,3,20),连线强度选择Cosine,网络裁剪使用Pathfinder+Pruning sliced networks+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
(1)关键词知识图谱。运行CiteSpace,得到1999—2018 年我国档案学研究关键词知识图谱,如图2 所示。根据图2 可知,选取的4211 篇文献中有关键词831 个,关键词之间的连线为1657 条,共现网络密度仅有0.0048。关键词之间的联系比较多,但是网络密度很小。1999—2018 年我国档案学研究关键词知识图谱节点越大,就表示关键词在有关文献中出现的频次越高,节点之间的连线越多就表示关键词之间共现关系越密集,连线越粗就表示关键词之间的共现越强。图2 中,重要的节点有“档案管理”“档案学”“档案工作”“档案”等方面。

图2 1999-2018 年我国档案学研究关键词知识图谱
(2)高频关键词分析。经过CiteSpace 软件分析后,导出1999—2018 年我国档案学研究高频关键词排名前10 的统计信息数据,如表2 所示。排名前10 的高频关键词中,档案管理、档案学、档案工作、档案馆、档案利用、档案保护、档案信息首次出现时间均为1999 年,档案、电子文件首次出现时间为2000 年,数学档案馆首次出现时间为2001 年。档案管理出现的频率最高,达到402 次;其次是档案学,出现频率248 次。进一步分析高频关键词出现年度得到:档案管理的论文数量在1999 年达到最高值,此后论文量不断减少,2009 年论文量有所回升,之后一直处于较低的数值。档案学的波动较大,2002 年、2015 年到达峰值,2010—2015 年是突发性变化较强的时间段。档案在2011—2018 年论文变化较大,从2010 年开始逐渐增加,2014 年达到峰值,随后又逐渐减少。总体来看,高频关键词档案管理、档案学、档案工作、档案、档案馆这五个词的共现词频较高,是我国档案学研究前沿的重点方向。

表2 1999—2018 年我国档案学研究高频关键词信息(TOP≥10)
对近三年(2016—2018)关键词(如表3)进行分析,得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是“档案”“档案管理”“档案学”“档案馆”“档案工作”“档案服务”“数字档案馆”等内容,这说明我国档案研究学者在近三年来对以上几个主题的关注度较高且成果丰富。中心度较高的关键词是“档案信息服务”“大数据”“社交媒体”“档案资源”“电子文件”“传统村落”“互联网+”“档案微信”等内容,这表明“档案信息服务”“大数据”“社交媒体”“档案资源”等关键词在近三年来,不再是独立研究,而是与其他热点之间有着较高的关联性。“档案信息服务”属于中心度较高但频次较低的关键词,说明档案信息这一主题还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值得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表3 2016—2018 年我国档案学研究高频关键词信息
3.文献共被引分析。论文的文献共被引分析以单个文献题录作为节点内容,通过分析1999—2018 年《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有关“档案”主题的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探寻我国档案学研究领域的关键文献,继而找出其热点主题。
(1)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运行CiteSpace,得到1999—2018 年我国档案学文献共被引图谱,如图3 所示。选取的关键文献中,共被引文献有633 篇,共被引文献之间的连线为897 条,共现网络密度只有0.0045。

图3 1999—2018 年我国档案学文献共被引图谱
(2)高被引文献分析。经过CiteSpace 软件分析后,导出1999—2018 年我国档案学文献共被引排名前10的统计信息数据,如表4(见下页)。
由表4 可知,排名前10 的高被引文献中,从发文期刊来看,《档案学通讯》4 篇、《档案学研究》4 篇、《档案管理》《浙江档案》各1 篇。从发文作者来看,冯惠玲4篇,特里·库克、徐拥军、丁华东、任越、潘连根、安小米各1 篇。从文献的发文年度来看,文献年度2011 年3篇,2012 年2 篇,1998 年、2004 年、2005 年、2009 年、2014 年各1 篇。从文献内容来看,与记忆相关的文献5篇,如潘连根从社会因素的层面考察档案记忆的属性,指出档案部门参与社会记忆构建的方式[7]32。丁华东从档案记忆观的兴起入手,分析其成因、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以及档案记忆观对档案学理论的影响[8]16-17。冯惠玲则是从档案数字资源建设的角度来分析档案记忆观、档案资源观[9]4。与电子文件相关的文献2 篇,主要探讨了电子文件的长久性以及电子文件的管理风险。与档案资源相关的文献3 篇,主要是从数字档案资源的整合与服务、“中国记忆”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等方面分析。从1999—2018 年我国档案学高被引文献中可以看出,近20 年来我国档案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记忆或档案记忆、电子文件或档案信息化、档案资源与档案开放以及档案的价值、档案的理论、档案专业等方面。
三、结语
档案学是系统研究档案及与之产生联系的各种现象和活动的学科。王玉琴认为,档案现象及其本质与规律由档案与档案现象基本理论的研究、档案管理基本理论与方法原则的理论研究、档案管理业务及方法技术的理论问题研究、档案事业和国家档案行政管理体制中涉及的宏观管理理论方面的研究、档案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方面的研究等五个方面组成[10]9。从宏观的角度可以是研究档案、档案事业等内容的学科,从中观的角度,可以是研究档案学科、档案工作、档案馆等方面的学科;从微观的角度,可以是研究档案工作者、档案收集、档案利用等问题的学科。
我国档案学学科的前沿热点问题依旧是档案理论与档案实践两大部分,根据关键词的共现分析、文献共被引分析以及期刊共被引分析等研究数据,档案管理、档案学、档案工作、档案、档案馆这五个词的共现词频较高,代表着我国档案学研究前沿的重点方向。此外,档案记忆、电子文件、档案信息服务、大数据、社交媒体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就“2016—2018 年我国档案学研究高频关键词”而言,档案信息服务、大数据、社交媒体、档案资源、电子文件、传统村落、互联网+等关键词的中心度较高,在今后的档案学领域研究中具有研究的价值和研究的空间。档案信息资源、档案知识管理、档案学理论范式、社会记忆等方面将成为我国档案学前沿问题。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随着机构改革,各省、市、地区档案馆的专业人员也将进一步参与到档案学学科领域研究中。从作者共引图谱网络密度与机构共现网络密度的参数来看,研究者之间、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联系非常弱,仅有0.0066 和0.0179。档案研究者和研究机构之间应该加强交流与合作,不断促进档案学理论体系与应用知识的创新和发展。
徐欣云在《档案“泛化”现象研究》一书中指出:档案“泛化”现象的普遍存在,档案界和社会大众对“档案”概念偏离传统的使用,档案学术外延的过度拓展,导致档案学术核心弱化或去档案化,档案工作制度理想和档案工作现实的落差使得档案工作的边缘模糊不清等问题[11]3-4。因此,学者们在进行我国档案学领域研究时,无论是研究档案的多元化,还是分析档案的学术动向,都要尽可能地避免档案的“泛化”现象,从更加学术化、专业化的角度进行档案学研究,构建符合实践发展需要的档案学学科体系,摆脱“档案热”的世俗特征。

表4 1999—2018 年我国档案学文献共被引信息(TO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