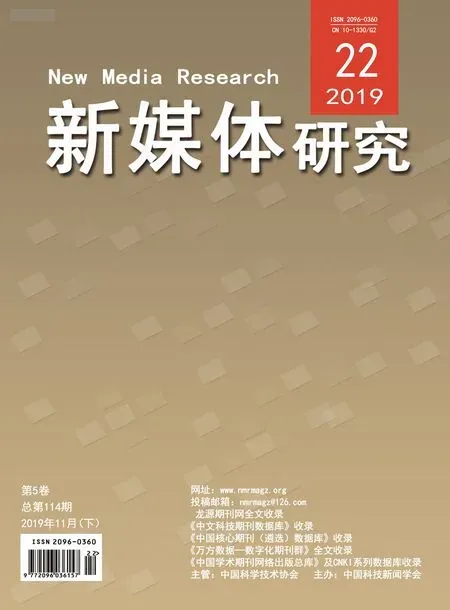“游”与“俗”的美学转向与社交货币:近年网络综艺爆红之道
2021-03-16张灿荣
摘 要 自2016年以来,网络综艺高速发展,网络综艺的连续爆红已经呈现出与电视综艺此消彼长的态势。以爆红网综《吐槽大会》《乐队的夏天》为典型样本,探讨近年网络综艺热播的内外部因素,认为从媒介环境变化到网络文化影响下网络综艺由“圣”向“游”“俗”的否定性美学转向,以及与此相关的新媒体经济逻辑下表现突出的社交货币特征,是近年网络综艺爆红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 网络综艺;爆红;美学转向;社交货币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22-0106-05
在传统媒体市场,电视综艺节目是与电视新闻、电视剧并列为电视收视率保障的三驾马车之一[1]。在融合媒体与新媒体逐渐兴起为主流媒体的今天,电视综艺、电视剧市场向互联网扩散甚至偏倚的趋势日益明显,其表征就是网络综艺、网络剧逐渐抢占年轻受众的视听娱乐文化消费市场。
和传统电视综艺相比,网络综艺显然更能凸显互联网的文化基因,并且迅速发展成网络文化展现的重要符号。2016年,国内掀起了“网络自制综艺热”,网络综艺迎来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PGC的长视频平台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齐齐发力,网络综艺以有别于电视综艺的风格与特质,席卷综艺消费市场,它的连续爆红已经呈现出与电视综艺此消彼长的态势。那么,与电视综艺相比,滋生于互联网空间、延续电视综艺的部分基因的网络自制综艺,其爆红的因素究竟为何?目前虽已有零星文章探讨过网络综艺爆红的原因,但迄今依然未能系统性地深入揭示爆红网络综艺席卷市场的根本因素所在。
2017年开始热播至今(2021年)已播出5季的《吐槽大会》,2019年、2020年连续播出两季的《乐队的夏天》,以其开播即热播的市场反响,以及更具后现代审美体验的节目形态,成为视听娱乐文化市场的现象级节目。尽管《乐队的夏天》制作人马东认为,米未传媒并没有什么把小众题材做成“爆款”的逻辑[2]。但是,制作者凭借行业经验完成的爆款,却值得我们加认真以剖析,为寻求网络综艺乃至网络长视频节目的爆红之道,提供有益的借鉴。基于此,笔者拟以《吐槽大会》《乐队的夏天》为典型样本,探讨近年网络综艺爆红的重要成因与路径。
1.1 消费市场转移与后现代美学走向
毫无疑问,PGC的长视频网站从购买电视综艺节目版权发展到自制综艺节目,直至接二连三推出爆红节目,与电视综艺争奇斗艳,是综艺节目市场从传统的客厅媒体市场向多屏化媒体市场偏倚,直至以智能终端为主要播出端口的演变过程。视听传媒技术的走向,决定了视听传媒市场的走向。这是网络综艺节目能够爆红的基本背景。
网络社会的媒体文化,是去中心化的价值走向,传统媒体所制造的社会中心化场景被碎片化的媒体及其文本所颠覆。即使是众声喧哗的媒体文本,也是以显著的“互文性”为其主要特征——“互文性”是由法国符号学家茱莉亚·克利斯蒂娃(Julia Christeva)提出的,其内涵主要指的是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在网络文化的影响下,对传统的社会文化中心及其权威的狂欢化解构,成为网络综艺节目的重要美学走向。这一走向,以《奇葩说》为开端,《拜年祭》《吐槽大会》《乐队的夏天》等爆红网络综艺发扬光大。与其说这是网络综艺节目的创新创造,不如说是媒体市场变化之后,随之发生的受众市场的文化变迁导致的媒体产品的应对策略,由此催生了让视听传媒市场耳目一新的后现代美学风格的网络综艺。
1.2 时间就是空间:新旧媒体的效益诉求区隔
网络综艺的兴起,还在于传统媒体市场的制度性助力。由于传统媒体的国有属性,媒体的组织目标决定其社会效益要求绝对凌驾于经济效益之上,需要承担更多的国家责任与社会责任,政府的政策性约束与规定,比网络媒体来得更严也更早,而这个时间差,在网络新媒体发展日新月异的短短几年里,就足以使综艺节目从电视综艺的一家独大,迅速转向电视综艺与网络综艺并行发力甚至是网络综艺势头超过电视综艺的新局面。早在2011年,广电总局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要求各卫视频道在晚上黄金时间,每周娱乐节目不能超过两档,选秀节目数量也严格受限。这就是著名的“限娱令”。限娱令使各家卫视不得不下架大部分的综艺节目,这些综艺节目立即给各个视频网站提供了机会,它们转而在视频网站上线。
新旧媒体在传播制度之中的地位差异,导致在媒体的组织目标与运营环境上存在时间维度上的显著差异,在媒体市场乾坤大转移的背景中,这个差异在2011年直接作用于综艺节目市场,促使网络综艺节目市场迅速崛起。2014年《奇葩说》热播,可以说是揭开了网络综艺黄金时期的序幕。服务主旋律的政治叙事与政治景观建构使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多元文化形态在电视综艺的全面生长,而发端于《奇葩说》的后现代美学则在接下来的热门网综《吐槽大会》《乐队的夏天》得以成功延续。
网络综艺的后现代美学转向,有其必然性。我们可以用社会学的“圣—俗—游”三元图式来分析网络综艺的美学转向。“圣—俗—游”三元图式是由法国社会学家R.Caillois提出来的,其中的“圣”即神圣性,包括令人颤栗的一面和令人着迷的一面,都是“对日常性的违背/侵犯”;“俗”则是“世俗事物”;“游”指的是游戏性,“相对于‘圣’和‘俗’的‘认真’,它以‘不认真’为特征;相对于‘圣’,它有以自由、非生产性、假构性为特征。”[3]这个图式被运用到现代社会青年文化的研究,主要在于图式中“游戏”的概念与艺术学中的“游戏说”相通。“游戏”具备文化创造功能,通过颠覆、解构“神圣事物”进而实现新的意义创造。综艺节目从电视进入互联网,正是从“圣”与“俗”进入“俗”与“游”,互联网文化催生了网络综艺节目的后現代美学风格,同时,新媒体经济的社交化传播,也促成了从电视市场转入多屏化市场的综艺节目的美学转向。
2.1 内容创意的“离经叛道”
作为新媒体节目,网络综艺获得市场青睐的关键在于成为关系产品,因此,社交货币化是其不二选择。在互联网,社交货币化只有针对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才能实现爆红。“从2019腾讯视频年度指数报告的研究数据可以看出,节目用户中,29岁以下互联网核心用户占比近九成”[4],而互联网文化的代际文化是青年亚文化,青年亚文化的象征符号是网络青年相互连接的有效工具,要创造“95后”互联网用户的社交货币,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野蛮生长的青年亚文化场无疑是必备的文化资源,因此,无论何种网络视听节目,与青年亚文化遇合是节目生产的重要逻辑。作为青年亚文化,对服膺于“圣”的角色型青年的非角色化的“俗”与“游”的反抗姿态,是其天然的第一要义,而对于内容产业来说,则内容创意是反抗主流的美学转向的关键。
《吐槽大会》的横空出世,首要因素恰恰在于其内容创意的“离经叛道”:把主流文化中通常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极尽调侃讽刺挖苦之能事的“吐槽”,作为节目的内容主体。在中国的互联网文化中,吐槽是以青年为主体的网民的重要言说方式,尤其是其表达异见、反抗主流文化、反抗角色型青年规范的象征符号,是互联网原住民的身份标签。《吐槽大会》直接将最具有互联网文化特征的言说方式作为节目的娱乐元素,进入节目的“关键业务”,是以互联网青年亚文化具备鲜明反抗属性的符号转换为节目内容,换言之,《吐槽大会》在符号学的意义上与青年亚文化融合为一。《吐槽大会》第一、二季的栏目标志语“吐槽是门手艺,笑对需要勇气”,将“吐槽”题材在面子文化源远流长的语境中当代青年亚文化的反抗属性,设定为栏目品牌的显性要素。而《乐队的夏天》的创作逻辑,与《吐槽大会》如出一辙,它把乐队文化这一典型的青年亚文化作为节目内容的主体。这些乐队表演的音乐类型——摇滚、朋克、灵魂乐、放克、城市民谣等,往往处于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社会文化之外——对摇滚乐的放逐与批判历来是主流精英文化的共同倾向[5]——他们的演出舞台通常是在Livehouse和音乐节而难以进入大众化的主流音乐市场与主流意识形态符号之中,但这些音乐类型恰恰是在现代中国青少年中颇具影响力的青年亚文化内容。《乐队的夏天》第一季在改编流行音乐这一环节中,所有乐队都不屑于改编张杰的歌曲,他们对于鹿先森乐队的流行名曲《十里春风》不以为然,第二季中白日梦症候群主唱白举纲则竭力表态尽管自己快男出身但热爱的却是乐队……凡此种种,《乐队的夏天》毫不掩饰地展现乐队文化与大众流行音乐的对抗姿态。这种真实呈现,就是《乐队的夏天》与乐队文化的同一价值立场,换言之,是与青年亚文化的同一性价值立场。
以“圣—俗—游”三元图式观之,如果说,《吐槽大会》的文化意义是从离弃“圣”直接投向“游”,那么,《乐队的夏天》则是从“俗”转向“游”,在“俗”与“游”之间随性切换——是音乐美学的游戏精神与生活态度的凡人精神的叠加。但《乐队的夏天》更具有新的意义创造的意味。相对于“俗”文化的主流流行音乐,作为典型的青年亚文化的乐队文化,具有强烈的自由精神的游戏属性,譬如五条人乐队的临场换歌、野孩子乐队不在节目规定的歌包里选歌等行为的意识特性。《乐队的夏天》尽管无法拥有“吐槽”的互联网文化属性,但其所具备的反抗色彩与“吐槽”不分伯仲,作为自发的、后现代色彩浓郁的乐队圈层文化,其美学共同体的建构潜能较之“吐槽”更加强大。
2.2 嘉宾角色的精英解构与凡人精神
嘉宾角色在综艺节目中是内容元素,嘉宾符号的所指,实际上反映的是节目传播主体赋予节目的精神导向。“电视节目商业模式的核心是价值主张,需要满足多元市场的需求,其中,受众元最为关键。因此,整个商业模式优化必须从受众的价值主张优化开始。”[6]因此,节目传播主体赋予节目的精神导向,务求表达受众的价值主张,这是吐槽式内容创意的来源,也是嘉宾角色设计的主要依据。
作为具有后现代色彩的互联网青年亚文化,吐槽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网民对公共事件、公众人物的狂欢化批评。在提出狂欢理论的巴赫金看来,人们在狂欢中遵循的是平等的规则,摆脱了常规生活中的等级秩序,采用世俗化的、喜剧性的、宣泄式的方式尽情表达,完全是对生活中心规则的颠覆与放逐[7]。狂欢化的话语与后现代社会的青年亚文化天然遇合,互联网虚拟空间则为这一遇合提供了纵横捭阖的广阔天地。青年吐槽式的反抗意志与独立立场表达,正是综艺节目价值主张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嘉宾作为节目内容表现的主要元素,承载这一功能天经地义。《吐槽大会》的主咖在常规生活中是社会精英(明星、名人),进入《吐槽大会》狂欢化的节目规定情境,他们成为被面对面猛烈吐槽的对象。即使是唐国强这样的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在主咖的位置上依然是被年轻一辈当面吐槽,地位、年龄在这个场域中退位,精英形象通过吐槽被解构,明星、名人作为凡人的一面在吐槽与应对吐槽之中毕现。这是满足受众价值主张——反抗权威、戏谑主流——的符号建构。它不仅仅借助演播厅里的表演,也借助了提供给屏幕前的观众尽情吐槽的弹幕。
创丰资本大文化产业基金合伙人梁建勋在谈到《乐队的夏天》的成功时,曾说:“任何亚文化能否影响观众,其实只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产品能不能商业化,第二个就是在当前的市场中,它有没有重新支配重新定义的权利。如果两者具备,就会有观众,《乐队的夏天》做到了这一点。”[8]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吐槽大会》。狂欢的精神必是一种游戏的精神。在《吐槽大会》中,调侃了精英并且重新定义了精英——后来甚至被吐槽为洗白明星——在嬉笑怒骂之间完成了青年对掌握社会资源的精英人物的解构与凡人精神呈现。这是一场在游戏中完成的权力更迭——从精英的手中,转到亚文化情境中的普通青年。吐槽的本质,“伤花怒放”的本质,正在于对于代际权力主导的不满与抗争。《乐队的夏天》的嘉宾,老牌乐队可能被颠覆,而无名乐队可能胜出,评选的标准只有一个:观众喜欢——毫无疑问,观众都是青年。最具有游戏精神的非角色型青年的五条人乐队,成为《乐队的夏天》第二季最为爆红的乐队——他们穿着人字拖鞋,上场前临时换曲目,三进三出,几乎是被网民抬进了最后的决赛并最终夺得亚军。五条人乐队的仁科戏称自己是“农村拓哉”“郭富县城”,以“俗”的姿态进入“游”的文化,正是一场凡人精神与对当代青年的重新支配、重新定義的游戏化权力演出。借助于游戏的产品化,亚文化被商品化,受众的价值主张,在游戏中得以彰显。
2.3 主持人的去权威化与边界模糊化
主持人与嘉宾同样是综艺节目的内容元素。主持人的角色往往被观众视同传媒的代表。在大众传媒时代,主持人扮演的是大众传媒制造媒介的社会中心化仪式的“司仪”,因此,主持人不仅处于节目内容结构中的中心地位,甚至具备传媒内容的前台发言人的权威属性,但在网络时代,传媒的去中心化已经成为普遍现实,网络综艺节目主持人的“司仪”功能下降,为网民代言的功能上升,主持人由“圣”入“俗”甚至入“游”,是互联网环境下的大势所趋。换言之,互联网青年亚文化背景下,任何人格化中心形象主动实现自我解构的去权威化、去中心化,是符合互联网年轻用户的价值主张的。
主持人角色的去权威化是从电视综艺开始的美学转向。从湖南卫视综艺节目《我是歌手》胡海泉以参赛歌手的非职业身份担任主持人并因读错音反而走红开始,综艺节目主持人由“圣”入“游”初露端倪。这样的端倪,在网络综艺中展开为共同趋向。
网络综艺节目主持人的去权威化,正与网络文化的反主流文化走向息息相关。它始于《奇葩说》,主要反映为主持人边界模糊化、非精英化、娱乐化的后现代美学风格,在《吐槽大会》《乐队的夏天》中被发扬光大。马东在《乐队的夏天》中最突出的形象特征是一个主持音乐类综艺节目的音乐门外汉,这个特征通过各种情节与细节加以凸显,并成为乐队(嘉宾)、超级乐迷(嘉宾兼部分主持人功能)、网友调侃与嘲笑的材料。作为现场的主人,他比乐队和超级乐迷承担了更多的被调侃的角色功能,而原本属于主持人的场上的串联、访谈乐队的功能,很大一部分让渡给超级乐迷群体(嘉宾),在去职业权威化的同时,弱化中心地位,提高了小丑化角色的娱乐功能。而《吐槽大会》在这条道路上,堪称无所不用其极,这是《吐槽大会》爆红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马东在《乐队的夏天》中被调侃和戏弄的角色,在《吐槽大会》里由身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央视节目主持人的张绍刚担任。张绍刚在节目中备受嘲笑的花哨衣着,随时遭遇的调侃吐槽,甚至被设定与嘉宾易立竞强行拉CP,如此等等,极尽所能去除主持人的传统权威性;在第五季《吐槽大会》,作为主持人之一的李诞,则直接加入嘉宾团队参与脱口秀表演,从主持人到“嘉宾”的随意切换,无所顾忌地放逐了传统媒体主持人的中心化地位。就在这样的符号游戏中,《吐槽大会》了完成对主流媒体文化的“嘲弄”与颠覆,从而赢得青年亚文化圈层对于文化权力反转的情绪共鸣。
2.4 社交货币化:卓越的超常规与圈层归属的成就满足
《创造101》制片人多晓萌认为“所谓爆款,就是拥有社交货币,是在社交场合大众都在议论的内容。”[9]。节目的社交货币化,是新媒体经济的本质要求。设计关系产品、建立转换机制、实现共享价值,被认为是新媒体经济运行的三大构成[10]。网络综艺节目在完成由“圣”向“游”“俗”的后现代美学转向,主动接轨互联网虚拟空间中生机蓬勃的青年亚文化,其重要的驱动力,正在于完成自身的社交货币化。
乔纳·伯杰(Jonah Berger)提出的三种塑造社交货币的方式是:通过卓越的、非常规的事,或者神秘的、有争议的事情来获得标志性的内在吸引力;撬动游戏杠杆,通过人际社会的比较来完成一种有形并且可视的标志,展示优越地位;通过产品的稀缺性和顾客拥有如此稀缺的产品的专有性,来使人们有归属感[11]。总之,一定是借助于自己拥有或者参与到某种超乎寻常的事物,或者撬动游戏杠杆,让人们可以貌似掌握了专用的权利,从而被他人刮目相看,赢得社会资本。
极富游戏精神的网络综艺节目必须具备超常规或卓越的内容,这是在精神文化层面与青年亚文化获得一致性之后叠加的文化资源,以供用户在满足娱乐需求之后,进而作为与卓越事物共在的社交货币,向社群转发有关此社交货币的信息或者“盗猎文本”。网络综艺如果仅仅具有符合网络青年用户群体规范的游戏精神,还不足以成为观众/用户遍告各自的“传播网络”的社交货币。
在综艺节目的商业模式中,核心资源和关键业务,是决定其内容质量的要素。核心资源包括节目版权(内容)、人才(主持人、嘉宾、优质制作团队等),关键业务首要的是节目创意(或者版权引进)制作与传播[6]。综艺节目实现内容层面的卓越与超常规,需要将核心资源与关键业务推向极致。马东认为一个节目能“爆”,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他提出的“人和”,就是指嘉宾和制作团队的状况[2]。《吐槽大会》汇集了广为网民议论的具有槽点的明星、名人,到2021年的第五季,干脆把当年度网上热度最高的名人如五条人乐队、刑法学家罗翔等网罗殆尽;《乐队的夏天》则汇聚了全国民间乐队中的佼佼者,顶级乐队更是囊括其中,新裤子、痛仰、旅行团、木马、重塑雕像的权利、达达、后海大鲨鱼、野孩子等著名乐队均在列。在制作层面,它们也以极致追求为能事。《吐槽大会》的脱口秀演出,在演播空间中设置了3个演出区,脫口秀表演更是力求热点、槽点、笑点的极致统一;《乐队的夏天》在演播现场的灯光舞美制作精良,其舞台配置远胜于各种音乐节现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音响工程师金少刚担纲节目的音响制作人,乐队演出创意叠出,加之有灯光舞美的惊艳加持,又有经典曲目改编、流量女星合作演出等核心资源加持,节目从核心资源到关键业务同样追求极致。
网综中的弹幕使得受众成为拥有话语权的传播者。爱奇艺为《乐队的夏天》开通了“助力通道”,投票把已经被淘汰的但受观众喜爱的乐队选回舞台,这种互动的方式让受众身兼传播者与决策者的双重身份;《吐槽大会》甚至实现了在节目直播现场,主持人直接对弹幕内容做出回应,让受众的话语可以影响节目的内容。这样的互动机制,解决了社交货币的撬动游戏杠杆问题,本质上是青年亚文化共同体的价值共鸣机制与被网络命名为“屌丝”的非角色型青年翻身做主人的圈层归属的成就体验满足机制。精英阶层没有这样的需要,他们已经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了社会权力,但是作为“屌丝”的非角色型青年需要。这是把“游戏”进行到底的权力转移与成就满足。
当代美学审美观念所提供的,是否定性的美学主题。这种美学主题意味着当代美学的内涵从“强者”的美学转向了“弱者”的美学[12]。这种美学转向在社会文化层面,表现为由“圣”入“俗”或“游”,它与互联网空间蓬勃生长的青年亚文化一拍即合。当然,必须看到,这种与青年亚文化关联的后现代美学的否定性主题,并不具有破坏性,相反,“亚文化不仅表现为对主流文化的抵抗,也表现为一种妥协。被收编的亚文化利用流行时尚(当下的风格)换得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不同程度地失去了抵抗性。”[13]它不过是在互联网的助力下,年轻人从日常生活中的经济、文化束缚中解放出来,以青年亚文化话语为连接,“结成跨地域、可交流的新联盟”[14]。在新媒体经济的资本驱动下,网络综艺节目以这样否定性的美学转向,进入极致的社交化媒体产品的圈层化赛道,完成节目在青年网民之中的社交货币化。这或许正是近年网络综艺爆红的重要路径。
参考文献
[1]张灿荣.电视综艺节目的价值变迁与社交偏倚[J].当代电视,2020(9):50-55.
[2]刺猬公社.从《奇葩说》到《乐队的夏天》,小众出爆款的逻辑是什么?[EB/OL].[2020-09-03].http://www. 360doc.com/content/21/1024/18/77463279_ 1001118263.shtml.
[3]陈映芳.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84.
[4]2019网络综艺内容与用户最犀利洞察,腾讯视频的这份年度指数报告拿得死死的|网络综艺|腾讯视频|吐槽大会_新浪新闻[EB/OL].[2019-12-27].http://k.sina. com.cn/article_5787163139_158f11a0301900uuap. html.
[5]郝舫.伤花怒放:摇滚的被缚与抗争[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133-151.
[6]张灿荣.文化类电视综艺节目商业模式优化之道[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9(5):55-58,101.
[7]巴赫金.拉伯雷研究[M]//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李兆林,夏忠宪,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8]创丰资本.媒体报道|乐队的夏天到底是怎么火的?_网易订阅[EB/OL].[2019-09-02].https://www.163.com/dy/ article/EO3D5GRR05390SGG.html.
[9]北京乐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后置的爆款,前置的新趋势|中国网络视听大会网络综艺干货合集[EB/OL].[2019-06-02].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 35227870150966774&wfr=spider&for=pc.
[10]谭天.新媒体经济是一种关系经济[J].现代传播(中國传媒大学学报),2017,39(6):121-125.
[11]乔纳·伯杰.疯传:让你的产品、思想、行为像病毒一样入侵[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51.
[12]潘知常.美学的边缘: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观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9-53.
[13]周敏,杨富春.新媒介环境与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J].新闻爱好者,2011(19):24-25.
[14]闫翠娟.从“亚文化”到“后亚文化”:青年亚文化研究范式的嬗变与转换[J].云南社会科学,2019(4):178-184,188.
2444501186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