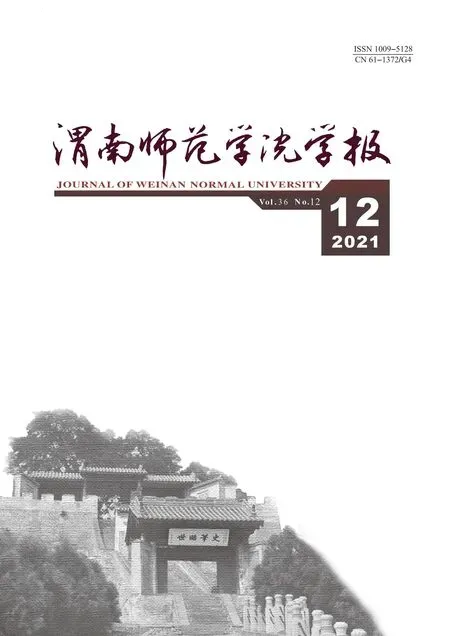从《史记·孔子世家》的正文与三家注的异文对比看司马迁的叙事意图
2021-03-07刘力铭
刘 力 铭
(香港浸会大学 文学院,香港999077)
程苏东在《失控的文本与失语的文学批评——以〈史记〉及其研究史为例》一文中提到了“失控的文本”这一概念,即《史记》存在一些由文本编纂而成的衍生型文本,司马迁通过各种形式的“钞撮”,实现了对原有材料的“重写”,而在这一过程中,因其文本嫁接处、补缀处或截取处难免疏漏,所以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了一些“失控的文本”,体现出编钞者试图构建有序文本的过程及其所遭遇的困境。[1]166《史记·孔子世家》的史料来源颇为总杂,符合衍生型文本的特点。钱穆曾言:“余读《史记·孔子世家》最芜杂无条理。其他若《年表》,若鲁、卫、陈、蔡诸《世家》,凡及孔子,几于无事不牴牾,无语不舛违。诚如崔氏之讥,所谓自为说而自改之者。”[2]47这既揭示了《孔子世家》文本编纂的复杂性,也启示读者探寻司马迁钞撮背后的编纂意图。
三家注对《孔子世家》文本的编纂提出过一些质疑。注者多引异文,为同一事件的记载提供了不同材料,其背后反映了注者对异文选择作出的价值判断,而这一价值判断又与注者对原文作者意图的理解密切相关。因此,笔者拟从三家注入手,检视司马迁在钞撮《孔子世家》时存在的疏漏,探讨三家注对这些疏漏表现的价值判断,并借此回溯文本本身所体现的作者叙事意图。
逐条检视过三家注后,笔者认为值得探讨的有三条注释,并将这三条简称为“孔子要绖”条、“匡人围孔子”条、“归与之叹”条。
一、从“孔子要绖”条的正文与异文对比看司马迁的叙事意图
孔子被司马迁评价为“至圣”,其道德形象在后代流传中渐趋完美,但在一些先秦史料中,孔子多以普通人形象出现,具有与常人一般的情感、欲望,在面对道德冲突时也有实际的考量。司马迁与司马贞对于“孔子要绖”史料的选取,反映了各自对于孔子的道德想象与期待。
《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要绖”的原文如下:“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3]1907在“孔子要绖”四字下,《史记索隐》曰:“《家语》‘孔子之母丧,既练而见’,不非之也。今此谓孔子实要绖与飨,为阳虎所绌,亦近诬矣。一作‘要经’。要经犹带经也,故刘氏云嗜学之意是也。”[3]1907“绖”,指丧服所系之带,一般由麻制成。[4]117“要绖”即腰绖,是一种丧服制度。这条注释指出了两个问题:首先,根据《孔子家语》对“孔子要绖”的记载,《孔子世家》的描述不合史实;其次,司马贞提供了改字之说,即“孔子要经”,孔子之所以被季氏拒绝,是因为腰间带着经书赴宴。侯文学认为《史记》的任何版本均未有“孔子要经”异文,这一说法难以成立。[5]100因此,笔者将主要关注《孔子家语》与《孔子世家》对于“孔子要绖”的记载有何不同。
《索隐》所引《孔子家语》的内容见于《公西赤问》:
孔子有母之丧,既练,阳虎吊焉。私于孔子曰:“今季氏将大飨境内之士,子闻诸?”孔子曰:“丘弗闻也。若闻之,虽在衰绖,亦欲与往。”阳虎曰:“子谓不然乎?季氏飨士,不及子也。”阳虎出。曾参问曰:“语之何谓也?”孔子曰:“己则丧服,犹应其言,示所以不非也。”[6]550
对于这一记载,理解的关键在于“示所以不非也”。王肃注云:“孔子衰服,阳虎之言犯礼,故孔子答之,以示不非其言者也。”[6]550由此,“非”可理解为责怪之意。在这一阐释中,阳虎以犯礼形象出现,而孔子对阳虎不加责备,既遵守了母丧礼节,又宽宥了犯礼之人。与之相比,《孔子世家》所呈现的孔子则躁进又落魄:在居丧期间有赴宴、出仕之意,似是违礼之举;季氏在后来僭离正道,陪臣执国政,并非理想的栖居之主;而面对“阳虎之绌”,孔子以“由是退”为反应,显示出阳虎与季氏的积威——一代至圣也曾遭遇如此被动无力的局面,卑怯不已。
《史记志疑》针对“孔子要绖”引过两种观点,它们实际上殊途同归,都力求维护孔子圆满的道德形象。具体说来,第一种观点否定了“孔子要绖”的真实性:
杨慎曰:“孔子不就季氏,亦无要绖与往之理。”邵氏《疑问》曰:“丧而要绖,丧未除也,而与享者有乎?至闻虎一叱,由是而退,则礼乐之宗,曾不若一窃宝玉大弓之盗已。瞷亡之拜,将仕之言,迁应不知也。”[7]1114-1115
杨慎的话不知所本,似是因孔子后来不仕季氏所呈现的道德判断而断定先前必无“要绖往之”一事。邵氏之所以质疑,一是因为孔子在丧期赴宴有违礼之嫌;二是因为孔子在与阳虎的对峙中落于下风,情境窘迫,不符合自己对圣人的道德想象,最后又引阳货劝孔子出仕一事否定“孔子要绖”的可能性。此事见录于《论语·阳货》: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8]1174
大部分学者认为阳货与阳虎为同一人。这则轶事恰好可以弥缝邵氏的质疑:首先,面对阳货劝仕,孔子有礼有节;其次,孔子与阳货的关系显然并不紧张,阳货是守礼的劝说者,而非无礼的罢黜者。
在《史记志疑》中,另一种观点则肯定了“孔子要绖”的真实性:
方氏《补正》则云:“季氏飨士,卒欲用之。古者既葬,金革之事弗避,孔子所居在季氏分地,要绖而往,庶人召之役则往役之义也,故阳虎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正义》谓飨文学之士,误矣。”[7]1115
方苞援引了《孟子》的说法,将孔子“要绖而往”解释为“庶人召之役则往役之义”,本无碍于礼义,但其本身仍然在为“孔子要绖”一事寻找合理性,孔子的道德形象在方氏的阐释中仍较圆满。
通过司马贞、杨慎、方苞等人对“孔子要绖”所作的阐释,可以感受到一种焦虑。他们期待孔子的前后行为具有整一性,在儒礼上没有瑕疵,面对出仕保留自己的道德坚持与主动权,为此,他们指出“孔子要绖”说的破绽并作出种种辩护。那么,面对众多史料,司马迁为何要“钞撮”孔子“由是退”的事迹,去书写看似弱者的形象呢?
首先,孔子要绖而赴季氏飨士之宴,实涉血缘亲情与政治公义的碰撞,即礼学所讨论的“亲亲”与“尊尊”之关系。要绖是一种丧服制度,当“亲亲”与“尊尊”的关系落实于丧服制度上,从先秦至唐代,历代学者对二者的主从关系均持不同看法。张寿安认为,清儒通过探寻礼制认为先秦时“亲亲”与“尊尊”实为并列结构,彼此互动,兼顾血缘之亲与政治之尊。在二者发生冲突时,则“依时而动”,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调整。[9]88例如,《礼记·曾子问》曾记“父母之丧,既卒哭,金革之事,无避是也”[10]619,则当国有大事,人子在卒哭礼后可无须避讳,以免有违公义。降至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派虽有意限制君权,但从大一统的角度仍有尊君倾向,且善权变。[9]96-97司马迁的经学思想有公羊学的成分,因此,面对孔子暂将政治公义置于血缘亲情之先,他并不视之为违礼之举,在记载时不加避讳。魏晋以降,在家族关系中,则母亲地位上升;在社会关系中,则有忠孝之争。[9]98司马贞所引的书为《孔子家语》,旧说为魏代王肃所伪造,以攻击郑玄之学。虽然今天的出土文献已证明此书的内容真伪参半,但学者亦承认此书在流传过程中多有增删[11]7,王肃未必没有修改机会。在司马贞所引的《孔子家语》中,孔子相当重视母丧,且以孝为先,王肃在注语中对此持肯定态度,颇能代表魏晋时人对于血缘亲情与政治公义之关系的看法。时至唐代,在家庭关系中,官府于贞观、开元两度修订服制,均在“亲情恩重”的前提下加厚丧服,如武则天曾提议“父在,为母齐衰三年服”,有别于《仪礼》所规定的“父在为母期,父殁为母齐衰三年”,母亲的地位得以持续提升;在社会关系中,唐代君臣实行共存共治的主从关系,尊重父丧。[9]102-104司马贞,据考证活动于唐睿宗景云至玄宗开元年间[12]117,对于丧服的看法受当时唐律与政治现状影响。他之所以在《索隐》中采纳《孔子家语》的故事版本,或是出于唐人在丧服制度中对家族亲情的尊重。
其次,孔子生于春秋晚期,其时士阶层的构成较为复杂,而司马贞只承认“季氏飨士,孔子与往”为历史事实,否认阳虎之黜,或是因为士的概念演化至唐代,已较为单一。阳虎所说的“季氏飨士,非敢飨子”实际反映了阳虎与孔子对“士”的认知的分野。据李向平研究,春秋晚期的士包含宗法之士与非宗法之士,宗法之士为卿大夫的宗族成员及支庶族人,时常被任命为邑宰、家臣。[13]159担任这些官职的宗法之士获取卿大夫世族的经济、政治或军事力量后,或以反叛作乱,实现地位上升。阳虎作为孟孙氏的支庶、季孙的家臣,就曾“陪臣执国政”。为了制约横行的家臣,卿大夫或会起用非宗法之士。孔子便是一位不具有宗法身份的士,其先人为宋人,经历了由贵族沦落为士、奔鲁后为大夫、继而再次沦落为士的过程。[13]156从宗法身份上看,孔子与阳虎显然有别。在季氏飨士时,这或许影响了阳虎对孔子的排斥。司马迁记载此事,则是为了客观呈现当时宗法之士与以才学著称的非宗法之士的矛盾。
再次,在司马迁看来,孔子面对出仕是较为实际的——他渴望被任用,有时并不在意任用者的德行。例如,公山不狃曾据费邑反叛季氏,召求孔子。孔子本欲前往,但子路予以阻拦。孔子认为,只要能被任用,恢复东周的典章制度,那么,自己被谁任用是不重要的。[3]1914此外,在孔子周游列国时,佛肸也曾据地反叛赵简子并征召孔子,他又欲应召。子路认为佛肸德行有亏,孔子则以匏瓜为喻,认为自己无法像它一样结在空中而不被食用。[3]1924
前文曾提到,邵氏在《疑问》中引阳货劝孔子出仕一事,反驳“孔子要绖”的真实性,司马迁之所以选择记载后者,当是不知前者。但是,众家在阐释阳货劝孔子出仕时,本就众说纷纭,其理解大概有三种倾向:第一种倾向以孔安国为代表,认为此则故事展现了孔子如何以顺辞免害保全自己[8]1177;第二种倾向以朱熹为代表,认为孔子有出仕之心,但不愿仕于阳货,他的言行既符合礼仪,又表现了“理之直”[8]1177;第三种倾向以今人李零为代表,认为故事展现了孔子拙于谋生、急于用世的一面,有助于研究其人格的复杂性[14]296。前两种解读倾向颇为有趣,面对孔子的同一言行,一者解读为“曲附他意”,一者解读为“直道而行”。第三种解读倾向则较符合司马迁对孔子的认识。在司马迁看来,阳货劝孔子出仕一事与“孔子要绖”或许并不冲突,它们甚至属于同类事迹,表现了孔子的汲汲用世之心。因此,邵氏认为司马迁未曾了解过此事,是说不通的。
最后,若结合司马迁的生平经历,可见他并不会回避高低异势的人生。在《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列举了周文王、李斯、韩信、彭越、张敖、周亚夫、窦婴、季布、灌夫等一系列为积威所劫之人,并在此后总结道:
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15]1895-1896
人与人之间地位的高低、势力的强弱天生如此,难以为人力所更改,正如司马迁本人遭受宫刑,在这样人生异势的背景下,司马迁呼唤“怯夫慕义”——虽然就势力而言,有的人处于下风,或许可以称之为弱者或怯夫,但是,人依然可以在此形势下,受此激励,成为“激于义理者”,即“慕义”之人。因此,孔子被阳虎斥退,其退却的一面既丰富了其形象本身的内涵,也有利于司马迁书写一位“怯夫慕义”式的人物。
二、从“匡人围孔子”条的正文与异文对比看司马迁的叙事意图
司马迁通过选取、重组材料探索孔子的复杂形象,亦体现于“匡人围孔子”条。《孔子世家》对孔子受围于匡的记载如下:
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从者为甯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3]1919
《索隐》在“孔子使从者为甯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下注云:
《家语》:“子路弹剑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围而去。”今此取《论语》“文王既没”之文,及从者臣甯武子然后得去。盖夫子再戹匡人,或设辞以解围,或弹琴而释难。今此合《论语》《家语》之文以为一事,故彼此文交互耳。[3]1920
这条注释中的引文见于今本《孔子家语·困誓》《论语·子罕》:
孔子之宋,匡人简子以甲士围之。子路怒,奋戟将与战。孔子止之,曰:“恶有修仁义而不免俗者乎?夫《诗》《书》之不讲,礼乐之不习,是丘之过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为咎者,则非丘之罪也。命夫!歌!予和汝。”子路弹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而罢。[6]281
(《孔子家语·困誓》)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8]576
(《论语·子罕》)
司马贞认为,孔子曾两度被围于匡,一次是设辞而解围,一次则弹琴而释难,司马迁在重组史料时,融合《孔子家语》与《论语》的记载,合二事为一事。其实,《孔子家语》与《论语》所载的孔子被围于匡未必不是同一件事,因为两则记载中均有类似的天命之叹。那么,司马迁在钞撮史料时,为何摒弃了弹琴释难说,而选取了设辞解围说呢?
首先,这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有关。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15]1898
(《报任少卿书》)
司马迁在编纂史料时,格外关注身怀抱负却遭遇厄困之士,当他们身负理想却在现实中受阻,就选择通过书写传达志意、舒泻愤懑。在《孔子世家》中,司马迁多次强调孔子周游列国时陷入绝境:在宋国时,宋司马桓魋拔树欲杀孔子;又在陈绝粮,几近于死。弹琴释难说则淡化了孔子面临的危险境地,他甚至获得了解除危机的主动权。像这样神化孔子解围的记载屡见不鲜,如《琴操》记载孔子得以脱困是因为暴风袭击匡人,匡人由是知孔子为圣人。[7]1126司马迁不单放弃了主动却兵说,也放弃了外力相助说,是为了突出孔子所处的绝境,似乎越是绝境越可催发人对天人关系的思考。
此外,若选取弹琴释难说,则在情节上与后文有相犯之嫌: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闲,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闲,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3]1930
孔子困于陈、蔡时,讲诵弦歌不衰,其主体意识已不在意外在绝境。《庄子·秋水》记载孔子受围于匡时,也提到孔子与弟子弦歌不绝:“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16]465在这则记载中,孔子最后之所以得以解围,是借助师生间安然自若的弦歌与对话,使匡人意识到他并非阳虎,自动散去。泷川资言认为《孔子世家》的记载本于此[17]2334,实误,因为《孔子世家》所选取、组合的史料形成的情境要紧迫许多,匡人最后并未主动退去,反倒是孔子派出随从甯武子前去谈判,才化险为夷。弹琴释难所呈现的情境其实与弦歌不辍的情境相类,说明司马迁所面对的匡人围孔的史料,大概有一类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优游不迫的情境。从材料安排上而言,若选择弹琴释难说,则与孔子困于陈、蔡时的解围方式有重复之感。
三、从“归与之叹”条的正文与异文对比看司马迁的叙事意图
“归与之叹”条的情况较为特别。司马贞认为司马迁将同一句话分抄于两处,是钞撮之误,但若对比分析相关史料,则可发现这两句彼此相似的引用来自不同的儒家典籍,各有语境。司马迁在重组材料时,不存在失误。
具体而言,《孔子世家》有两处“归与之叹”:
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彊,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孔子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于是孔子去陈。[3]1923
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赣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3]1927
《索隐》则于“归乎归乎”下指出司马迁的编纂之误:
此系家再有“归与”之辞者,前辞出《孟子》,此辞见《论语》,盖止是一称“归与”,二书各记之,今前后再引,亦失之也。[3]1927-1928
司马贞认为,孔子居陈的“归与”之辞与他面对季康子召回冉有的“归乎”之辞,虽分别出于《孟子》《论语》,但二语实为一事。
不过,细按《孟子》《论语》文意,这两句话的语境其实不太一样: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 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18]340-341
(《孟子·尽心下》)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8]343
(《论语·公冶长》)
孔子的“归乎”之辞在《孟子·尽心下》中的语境比较显豁,与他思念鲁之狂士有关,因此才引发孟子与万章对狂狷的讨论。而在《论语·公冶长》中,孔子“归与之叹”的意义在后代注家眼中颇为含混。孔安国认为孔子意在批评弟子进取自大。他训“简”为“大”,“狂简”则为“进趋于大道”,“斐然成章”指“妄穿凿以文章”,语含贬义。正因为弟子不知如何裁制自己,孔子才认为自己应当回到鲁国教导他们。[8]344朱熹的训诂与孔安国颇为不同,他训“简”为“略”,则“狂简”意为“志大而略于事”,“斐然成章”则指弟子的文理成就有可观者,语含褒义。但是,在讨论“裁”的意义时,朱熹吸纳了《孟子·尽心下》中孟子与万章对狂狷的讨论,认为“裁”为裁正之义,因为担忧弟子有失中正,自己才要归去引导他们合于中道:
夫子初心欲行其道于天下,至是知其终不用也,于是始欲成就后学,以传道于来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为狂士志意高远,犹或可与进于道也,但恐其过中失正,而或陷于异端耳,故欲归而裁之也。[8]344
《四书辨疑》则批评朱熹将《孟子·尽心下》与《论语·公冶长》的语境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的语境完全相反,应去掉《孟子·尽心下》中“子思狂士”的语境理解之。不过,他对“斐然成章”的理解则颇契合宋元理学家的极端文道观,认为作文害道,具有时代特色:
孟子之答万章者,亦不可施之于此也。“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此乃思其狂狷也。“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却是抑制狂者,不令妄有述作之意,非思之也。说者宜云夫子知其终不用也,于是特欲成就后学,以传道于来世。虑其门人狂而志大,简而疏略,突以斐然之文而成章篇,违理害道,不知裁正,恐有误于后人,故欲归而裁正之也。[8]344-345
中井积德则由朱熹说而进一步申说:“‘裁’字由‘章’字而生,是以锦文彩段为喻也。夫子盖欲归而裁之以就人才也。”[17]2449
要之,孔安国、朱熹与《四书辨疑》的作者、中井积德虽然对于具体字句的理解各有所得,但他们均认为孔子对弟子之狂简持抑制态度,则“不知所以裁之”的主语当为“吾党之小子”。因为弟子“不知所以裁之”,故孔子认为自己当归去裁之。这样的语意是较深曲的,程树德就曾指出“以弟子为不知”在语意上较隔[8]344。事实上,《孔子世家》的“归与”之辞与《论语·公冶长》的原句有一字之差,即“不知所以裁之”上多一“吾”字。王叔岷在《史记斠证》中考证,《孔子世家》只有枫山、三条本无“吾”字,与《论语》相同,“吾”当是涉“吾党”而衍。[19]1765-1766虽然 “吾”可能是衍文,但这确实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不知所以裁之”的主语是否是孔子本人。
此外,虽然“小子”在《论语》中多作为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代词指称孔子的弟子,但此处的“吾党之小子”并不一定指代其弟子。司马迁曾于《儒林列传》再引“归与之叹”: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齐鲁之闲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3]3117
在此语境中,“吾党之小子”指研习礼乐的鲁儒,孔子对他们浸淫学术的精神与氛围充满赞叹。
通过梳理历代注家对于《论语·公冶长》中“归与”之辞的理解,可得知其情境与《孟子·尽心下》中“归乎”之语的情境并不一致。在《孟子·尽心下》中,孔子如此感叹是出于思念狂士,渴望进取态度。而在《论语·公冶长》中,孔子作此感叹,或许是心系学术。此前,面对鲁国三桓之乱,孔子不仕,转为研习礼乐、传道授业,司马迁将这一行为称为“退”。[3]1914对比思狂进取,可见退修礼乐的感叹夹杂了多少无奈。那么,司马迁在处理这两则史料时,实际上融合了自己的辨析,并非如《索隐》所言,分一语而入二事。
四、结语
《史记·孔子世家》的三家注为正文所记的人物事迹提供了不少异文,通过对比正文与异文,可以看到司马迁所塑造的孔子较接近普通人形象,有着与常人一样的情感和欲望。至于司马迁为何会如此选择、重组史料,则与他曾受折辱的生平经历、发愤著书的创作理念有关。司马迁在钞撮史料时,也会注意史料与上下文的呼应,体现了他对传主本人的思考、传记结构的整体构思。除此之外,读者还可看到异文所呈现的不同孔子形象。这些形象歧异部分反映了汉唐之际学术思想与“士”概念的变迁。透过历代诠释者不断的回望与争论,现代人将看到孔子更丰富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