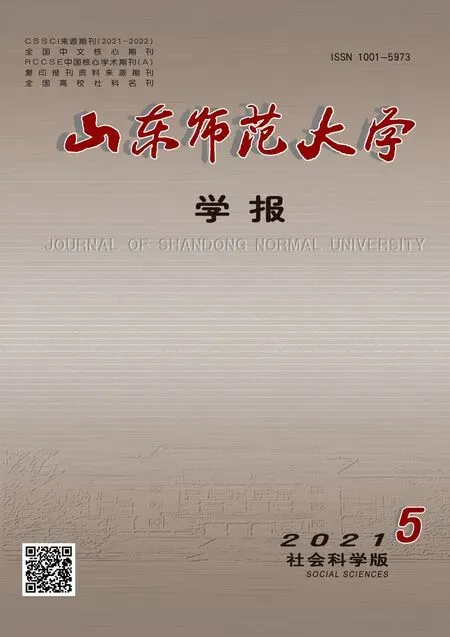乡土身份认同的失败之旅*
——鲁迅《故乡》重释
2021-02-01胡峰
胡 峰
(齐鲁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200)
按照英国社会学家阿兰·德波顿的界定,身份一词是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从狭义上讲,它是指个人在团体中法定或职业的地位;从广义上讲,则是指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而身份认同就是每一个有主体意识的个体,期待他人看待自己的态度与自我期待的一致性。(1)[英]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5页。简单说来,如果主体的自我定位与别人的认识相一致,则主体的认同度就高;否则,认同度就低。由此可见,在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他者的眼光对主体的认同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人对我们的关注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原因便在于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认同完全受制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评价”。(2)[英]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7页。也正是由于他者认知态度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主体身份认同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是现代社会每一个正常的个体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都会遭遇的一种体验。对处于社会、文化和思想剧烈变化中的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而言,这种体验尤为明显。鲁迅的《故乡》便可以视为鲁迅乡土身份认同的失败之旅的真实写照。
一
晚清之后,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动和冲击,新文化运动更是把这种变动推向高峰,使知识分子在知识结构、思想观念、意识行为、社会定位等方面逐渐与传统决裂并开始寻求新的范型。“五四”时期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从乡村走向都市,也就意味着从熟悉的文化圈子进入到生疏的生存空间;从具有血缘关系的熟人场域转移到以工作关系为主体的陌生人群中。他们需要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处事方式和思想观念,需要重新寻找自我身份的定位,同时也更期待获得他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而这种调整和寻找不仅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转变过程,有时还会遭遇心理及情感上的困惑乃至痛苦。此时,作为生活了多年、人事皆已熟悉,尤其是乡土身份与情感认同能够自动契合的故乡,则会以理想化的形象出现在他们的记忆中,正所谓“身体往城市去,精神往乡村回”。从故乡中“‘找回失去了的,遥远了的,朦胧了的一切’:理想,希望,爱,群体……,归根结底,就是寻找软弱、孤独的个体赖以支撑自己的‘归宿’。这确实是一种时代的心理欲求”。(3)钱理群:《“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侧面》,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版 下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第50页。钱理群对于20世纪40年代流亡者文学的心理分析,同样适用于“五四”初期寓居异乡而生活事业皆不如意的现代作家。即是说,他们是在以看起来是熟悉的、稳定的而且温馨的乡土身份来抵抗陌生的、流动的和冷漠的都市身份。需要补充的是,这些现代作家在寻找“归宿”的过程中,实际上饱含着从故乡的风物、亲人以及童年伙伴对其原初身份、亲情、友情的接纳与认同的期待。因此,在“离乡——返乡——再离乡”结构模式的现代小说中,“离乡——返乡”隐含着漂泊在外的现代作家从故乡寻求身份认同的心理期待与过程,“返乡——再离乡”则是其乡土身份认同失败后的无奈之举。这是因为返乡后的现代作家感觉现实故乡已经没有了返乡前想象中的那样美好。相反,与破败衰落的故乡风物相伴随的是人情的冷漠、人性的麻木与思想的愚昧。这使得他们无论是情感上还是理智上都无法接受,反而滋生的是启蒙式的否定态度与批判意识,而从中获得精神慰藉和身份认同的最初设想也就无法实现,无奈之下的“再离乡”也就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
除了社会文化转型、知识分子身份的变化及其生活空间的转换促使知识分子重新确立自我定位之外,鲁迅还有着比一般的知识分子更为敏感与孤独的现代体验。鲁迅对于周围环境的感知、对故乡的人和事的态度以及对于未来的道路选择等,都有着其他作家所不具有的独特性。具体来说,他创作于1921年的小说《故乡》,既是他对工作、生活环境的情感立场与主观态度的反映,也是他在这一心境下寻求新的身份认同与情感慰藉的文学表达。
《故乡》的情节来源于鲁迅1919年底的返乡搬家事件。这个搬家打算早在1918年3月他在写给好友许寿裳的通信中就开始流露出来。同时,流露出来的还有与搬家相关的对工作、生活环境的主观判断与心理体验。
近来部中俸泉虽不如期,尚不至甚迟,但纸券暴落,人心又不宁一,困顿良不可言。……既须谋食,更不暇清理纠葛,倘复纷纭,会当牺牲老屋,率眷属拱手让之耳。(4)鲁迅:《书信·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0-361页。
时隔不久,鲁迅还提到了他对所工作的教育部人事环境的无奈:
部中近事多而且怪,怪而且奇,然又毫无足述,述亦难尽,即述尽之乃又无谓之至,如人为虱子所叮,虽亦是一件事,亦极不舒服,却又无可叙述明之,所谓“现在世界真当仰东石杀者”之格言,已发挥精蕴无余,我辈已不能更赘矣。……该杂志销路闻大不佳,而今之青年皆比我辈更为顽固,真是无法。(5)鲁迅:《书信·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2页。这里“该杂志”指《新青年》。
两个多月之后,鲁迅再次向好友诉苦:
部中风气日趋日下,略有人状者已寥寥不多见。……作事如此,可谓极人间之奇观,达兽道之极致,而居然出于教育部,宁非幸欤!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6)鲁迅:《书信·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6页。
在临近春节的又一封信中,他说道:
仆年来仍事嬉游,一无善状,但思想似稍变迁。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7)鲁迅:《书信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70页。写这封信的当日为旧历戊午年12月15日,“明年”指的是春节过后,为新历的1919年。
这四封书信至少包含了这样的信息:一是鲁迅在教育部工作得并不顺心,或者说相当郁闷。教育部内部以及整个社会污浊的风气致使他对于生活与工作环境的态度明显地表现为:最初是无可名状,后来则到了极为愤慨的程度,以致同侪的行径已经没有了“人状”而“达兽道之极致”,甚至逼着他爆了粗口(“仰东石杀者”即为绍兴方言骂人的话),可见当时的愤懑之情已到极点。二是他一直支持的《新青年》杂志销路不好。本想通过这份杂志能够唤醒并凝聚一帮青年,使其成为启蒙道路上的同行者,但“恨铁不成钢”的残酷现实令人失望。再加上在此期间,胡适还因《新青年》的政治“色彩过于鲜明”而提出“另办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的主张,最终导致《新青年》阵营的分化。三是经济上的压力。一方面源自物价的上涨与工资的拖欠所带来的生活成本的加大;另一方面是由于购买八道湾房产所产生的经济问题,使其承受了压力。为此,出卖绍兴老宅就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当然,老宅易主不仅是为购置北京新宅筹集款项,而且还有“为族人所迫”即家族内部纠纷等因素使然,这是给鲁迅带来心理困扰的又一原因。如果说出卖老宅代表着他与故乡的物质联系被切断,那么族人的逼迫则使他在情感上不得不放弃与故乡的关联,由此产生一种“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的心态,与绍兴的感情日益交恶。因此,在鲁迅写给好友的书信中流露出郁闷、愤怒、无奈与逼仄,也就可以理解了。
实际上,鲁迅在返回故乡之前所遭遇的困扰并不仅仅如此,而是还有着其他诸多的不如意,这从当时他在《新青年》杂志《随感录》专栏发表文章的情况就可见一斑:从1918年9月至1919年11月(这与作者向好友倾诉心声的时段大致吻合),鲁迅共发表了27篇杂感,内容涉及多个方面。他后来这样说:这些“短评”,“除了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8)鲁迅:《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7-308页。鲁迅利用具有“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9)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特点的杂文对社会、文化、思想进行批判,其实正是其内心激愤不平之情的表达。
可见,无论是社会、历史、文化、现实中根深蒂固的旧传统、吃人的旧礼教、顽固的复古思想,还是鲁迅工作的北京包括教育部以及《新青年》团队和远在绍兴的家族亲友,都无法给鲁迅带来相对宁静舒适的情感慰藉,反而增加了其愤懑不平的情感体验与精神困顿。“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一般来说,中国传统文人通过空间转换与寄情山水实现对现实苦闷与命运困厄的排遣,而现代作家能否通过返乡来实现情绪的抚慰与心理的释放?即是说,借助返乡之旅暂时摆脱在北京的工作生活、人际交往、心理情感等困惑,从故乡获得乡土身份的认同和精神慰藉,成为现代作家的一种心理期待。
二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小说开头的一句话,交代了与故乡的现实关系——空间上相隔2000余里,时间上相距20余年。这意味着“我”和故乡之间已经有了时空上的较大隔膜,这种时空的隔膜也是“我”与故乡之间的情感关系的隐喻。尽管“我”是冒了严寒,行程不易,但“我”对故乡的认同和故乡对作为游子的“我”的认同却没有那种自动连接。而接下来的风景描写确定了这次身份认同的情感基调: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10)鲁迅:《呐喊·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1页。
远观故乡的景色,带给“我”的是萧索与悲凉;近看故居老屋的境况,同样给“我”凄冷与孤寂之感:
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所以很寂静。(11)鲁迅:《呐喊·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1页。
这里的景物是“我”通过视觉、听觉和触觉感知到的,按照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说法,“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12)[日本]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5页。。此次返乡的“我”更关注的是自己的感受和感情的安放问题,即乡土身份的认同问题,客观存在的风景本身并不是“我”重点关注的对象。而且,“我”眼中的风景是一种“不是美而是不愉快的对象”的“现代的风景”(13)[日本]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文版作者序),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页。。这种不愉快的风景显然不是内心期待已久的、能够得到“我”的认同,反过来也能够给予“我”身份认同与情感接纳的故乡和老家。
既然现实的故乡风景无法契合对“我”的乡土身份认同,那么这一心理需求还需要寻求其他的途径和方式来实现。这里首先找到的是记忆。记忆激活的是记忆主体对此前与自身有着密切关联的人和事,但并不仅仅是“回头看”的时间指向,而是使其在当下发生作用,并勾连起将来,形成过去、现在、将来的历史连接,并在这种连接中使记忆主体身份得到确认、改变自身所处的位置。因此,“在人类对自身的一切认识和反思中,记忆是最深刻也最不可或缺的参照。没有记忆,人就无从知晓‘我之为我’的缘由和过程,更无法探究‘我之有别于他人’的独特性和差异性”(14)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导论第1页。。那么,失望于现实故乡的荒凉与衰败的“我”记忆中的故乡又是怎样的呢?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15)鲁迅:《呐喊·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1页。
按照心理学的观点,自传体记忆的效果与人的情绪关系非常密切。尽管“我”试图按照一般文人的思维惯性寻找故乡温情的一面,但这种尝试和努力却最终失败。而要想去叙说故乡的好处,却只能陷入“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16)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3页。的失语状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这次返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如果把情绪视为一种内源性场合,那么“在某些情形下,这些内源性场合往往还要比记忆获得时的物理环境对记忆保持的影响更大”(17)杨治良等:《记忆心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0页。。可以说,都市生活使“我”不能开心,而故乡的老宅又被迫卖掉。在这种情况下,冒着严寒、辗转2000余里返乡,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这种既无奈又苦闷的心境,完全取代了“我”想象中的本身并不牢固、并不清晰的故乡“美好”记忆。因此,对故乡的“美好”记忆也就无从谈起了。不独《故乡》如此,鲁迅的小说集《呐喊》的创作也深深地植根于情绪这种内源性场合之中。正如鲁迅在《自序》中所说:“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18)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7页。从救治父亲、异地求学、弃医从文、《新生》夭折,到在北京S会馆里的孤独寂寞,可以说是一直萦绕于鲁迅心头的“创伤性记忆”并长期伴随着他的创作,成为其小说独特的主题基调。
现实的景色萧瑟、荒凉,给人以悲伤之感。而记忆中的景色模糊、朦胧,令人无法打捞。那么,“我”是否就此放弃对故乡景色的搜寻?一旦如此,也就意味着完全放弃了从风景中寻求乡土身份认同的努力。这一困惑,在“我”刚刚听到闰土的名字时出现了转机,“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19)鲁迅:《呐喊·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2页。
这幅经典的瓜田月夜刺猹图早已经被读者所熟知,而且一再被研究者提及。王富仁认为,鲁迅在小说中写了三个故乡:回忆中的故乡,现实中的故乡和理想中的故乡。上面这段描写属于第一种。(20)王富仁:《精神“故乡”的失落——鲁迅〈故乡〉赏析》,《语文教学通讯》2000年第21-22期。其实,与其说这是“我”对过去的故乡的回忆,还不如说是一幅作者想象出来的乡土乌托邦图景,这是由下文中闰土对“我”讲述“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后激发出的一种渴望。对于“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的孩子们来说,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美丽、静谧、浪漫、刺激的幻想。事实上,“我”和闰土真正相处的日子只有从新年到正月结束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此后尽管两人互相赠送礼物,但再也没有见过面。无论是装弶捉鸟雀,还是海边捡贝壳,以及瓜田守夜的故事,都是闰土讲给“我”听的。“我”从来没有去过闰土的家里,更不用说亲身体验刺猹的浪漫经历了。因此,“我”的脑海里忽然闪现出来的这幅神异的图画,是现在的“我”在听到母亲提起闰土时想象出来的一个场景。这种想象,并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正如沃尔夫冈·伊瑟尔所说:“要使想像变得明确,需要一个外在的刺激,而反过来说,这个外在的刺激又会被卷入想像所激发的游戏。因为能力是无根源的,所以它不能决定主体的性质。因为主体不能立刻找到自身的根源,所以它需要借助自身的想像力来出现在自己的面前”(21)[德]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像:文学人类学疆界》,陈定家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6页。原文中想象的“象”都是“像”。。这段话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我”想象出的场景:一是闰土是“我”在故乡除亲人之外曾经有过最亲密的友谊因而记忆最深刻的一个人,他的突然被提起成为激起“我”美好想象的直接刺激物;二是“我”带着悲凉的心情返回故乡,亲眼目睹了故乡的衰落与萧索,这种现实的不如意,特别是无处找寻的自我认同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刺激物,使“我”从现实穿越想象的、虚构的空间,到温馨的、浪漫的童年岁月中寻找可以获得精神安慰的寄托物。这样一来,“幻想对抗不完善的事物,改变它所在的世界,漫游于人的精神世界,呈现欲望受挫时的镜像。也就是说,幻想不是以物质形式出现的,而是以事物出现之前的功能形式出现的,虽然幻想只能以事物来表现”(22)[德]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像:文学人类学疆界》,陈定家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5-226页。。苏珊·桑塔格也指出:“怀旧情绪和乌托邦情结是典型现代情感的两个极端。”(23)[美]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陶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328页。当然,怀旧情绪和乌托邦情结之间并不是完全绝缘,有时候相互融合。因此,这幅瓜田月夜刺猹图和闰土带给“我”的许多新鲜、稀奇事,并不着眼于物质本身的新奇,更多的是将“我”的单调而枯燥的生活与“我”的小伙伴们形成鲜明对比。它揭示出“我”对想象中的闰土自由自在的生活情形的渴盼,寄希望于从中获得现实中无法满足的宁静浪漫的乡土情结与自我认同。日本学者藤井省三曾经指出,鲁迅的散文诗《好的故事》所描写的梦里神游故乡绍兴的河流时所遇到的优美的初夏之景,“对鲁迅来说,这是在黑暗与孤独中唯一留下的确认同一性的地方”(24)[日本]藤井省三:《鲁迅比较研究》,陈福康编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7页。,而刺猹的美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如果说瓜田月夜刺猹图是一幅虚构的、想像的图景,那么闰土讲给“我”的其他稀奇的故事则是留在“我”脑海里的深刻记忆。即是说,后者真实存在的可能性更大些,因为这些故事的建构是以闰土讲述、“我”的回忆为基础的。换言之,“我”和闰土是讲述这一事件的亲历者或者共同参与者。对“我”而言,在和闰土朝夕相处的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所获得的各种有趣的回忆就带有了一种自传的性质,也有人称之为“自传体回忆”。“人们对某事件的情绪反应强度与其对生命的影响程度以及记忆清晰度和鲜活性存在正相关。由此可知,与情绪有关的知识在自传体记忆中被结构化,当我们加工某类概念时,相关的自传体记忆很容易被提取,甚至会自动进入‘脑海’,以至于我们有时对这种‘自觉’回忆感到惊讶。”(25)杨治良等:《记忆心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7页。这其实与闰土这个名字刚刚被母亲提及时,想象画面便“自动地”出现在“我”眼前的原理基本一致,即情绪以及外在现实的刺激成为促成想象和记忆呈现的重要触媒。在《记忆:实验与社会心理学研究》这部经典著作中,Bartlett 认为记忆具有功能上的重构性,记忆总是为了迎合当前意愿的需求而对过去事件进行重构。而Brewer则认为自传体记忆因具有“自我参照”(Self-Reference)特征而与其他记忆类型相区别(26)杨治良等:《记忆心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2-313页。。
因此,无论是虚构的瓜田月夜刺猹图,还是回忆起来的闰土给“我”带来的新奇、有趣而又充满诱惑性的讲述,都是“我”对故乡现实失望之后产生的、希望能获得精神慰藉特别是乡土自我认同的寄托。
三
当然,故乡并不仅仅是那些外在的故土景物和风俗,或者通过幻想虚构起一个乌托邦式的美景,更重要的还有生活于此的亲人、乡邻与好友。而后者,才是真正和回忆主体有着共同记忆、保存并确保主体身份认同的存在。在《故乡》中,除了母亲,最能够唤起“我”童年回忆的就是闰土了。也就是说,闰土的作用并不只是作为激发“我”对乡土美景的乌托邦想象的刺激物而存在,更重要的,他还是这幅美景中活跃着的主角,也就是“我”的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一切的美景都是由他带来的,而且也是围绕着他展开的。离开了他,“我”对故乡的美好记忆或想象将不复存在。可以说,闰土就是“我”的乡土记忆中的核心人物。有这样一种观点:“记忆是一种源起于人际深厚关系,并帮助维护这种关系的责任。记忆特别与‘关爱’(caring)相关。关爱也就是在乎,在意,当一回事。关爱是一种‘朝后看’的感情,因为关爱是通过记忆来起作用的。……就关爱的关系而言,记忆不只是一种知性的记忆,而且更是一种感情的记忆。也就是说,记忆不只是‘知道’(如记住孩子的生日),而且是‘感受’。感情的记忆留住的是对共同事件的感受。”(27)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序第3页。
不难发现,闰土是“我”留存在故乡情感记忆中的人物,“我”和他有过一段一起相处的美好时光。因为闰土不仅是带给“我”从未有过的新鲜讯息的人,还是和“我”有着共同记忆的人。“人们在深厚的关系中以共同的记忆来形成‘我们是谁’的意识。这样的群体,它的自我意识是和群体成员对共同过去的记忆分不开的。拥有某种共同记忆的‘我们’和不拥有这一记忆的‘他们’之间因此区别出亲疏不同的关系。”(28)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序第7页。“我”和闰土是那段美好童年记忆的共同缔造者与经历者,闰土也就成为与“我”有着深厚关系的人,是“我”的关爱所在,更是能够确认“我们是谁”即实现“我”的乡土身份认同的关键人物。
“我”在最初听母亲提到闰土时,一切美好的记忆便瞬间涌现在脑海里。而当年那个飒爽英姿、行动敏捷、活泼灵动的少年英雄——闰土的形象也恍然出现在“我”眼前。这是“我”记忆中的闰土,更是想象中的闰土。他的身上不仅寄寓着我们曾经两小无猜、其乐融融的纯真友谊,而且他本人还是“我”对故乡友群中有着极为难得的美好记忆的共同经历者,也是“我”在故乡的唯一的亲密伙伴。换言之,“我”对故乡的美好记忆只能维系在闰土一个人身上。因此,“我”要想从故乡人中获得身份认同,也只有闰土才能担当起这个重任。这一点,“我”对闰土满怀信心。
但是,当闰土真的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我这记忆中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这与当年“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的灵巧少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如同“我”对故乡景色的乌托邦想象遭到毁灭一样,“我”对闰土的美好记忆也遭遇了严酷现实的猛烈撞击。文中写道: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
“阿!闰土哥,——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29)鲁迅:《呐喊·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7页。
尽管“我”努力从记忆中寻找着美好的一面,通过可以唤醒记忆的事物和话题,试图激发他的记忆,希望能够和他一起回到童年时期的美好场域。但是,他仅以“老爷”二字,轻易击碎了“我”的殷切期望和良苦用心,割断了我们之间最初的亲密无间的伙伴关系,切断了可能通向共同记忆的所有通道。“近在咫尺而丧失了沟通的语言,叙述者这一刻遭到了强烈的精神震撼。”(30)南帆:《表征的张力:农民叙事话语、文学修辞与数码语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0期。这种震撼更多地源自“我”从美好幻想与期待中被惊醒而重新回归残酷现实之中的事实。也可以说,“闰土哥”“迅哥儿”是过去的、记忆中的共同话语与身份认同的基础和前提,而“老爷”才是当下难以逃避的真实存在。母亲所提出的还是照旧以哥弟称呼的建议以及为试图恢复“我俩”之间曾经的温情关系所作的努力,也遭到了闰土本能而清醒的拒绝。在这个意义上,“老爷”不只是等级观念的呈现,更是二者无法回到童年、回到活泼灵动而无拘无束的共同记忆中的那层“可悲的厚障壁”。“我”期待中的平等而温暖的共同记忆只好被迫终止,“我”的精神返乡之旅也由此被再次搁浅,乡土身份认同的努力又一次以失败告终。
如果说闰土是和“我”有着共同记忆的、而且是“我”一直关爱着的故乡伙伴,那么豆腐西施则是被“我”遗忘的老家邻居。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我愕然了。
“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31)鲁迅:《呐喊·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5页。
“我”先是吃惊,见到了像圆规一样的杨二嫂,本身就没有好感;而她一再通过讲述过去的事情来强调和“我”的亲密关系,而“我”对这些事情却毫无印象。这样一来,我也就难免愕然。直到母亲的提醒,“我”才从记忆中搜索到一点朦朦胧胧的印象。如果说“我”一直努力从闰土身上激活我们共同生活的童年经历的共同记忆,希冀从中获得乡土身份的认同,那么与之相似的是豆腐西施也在努力唤起“我”和她那段有着共同经历的回忆,以此作为“我”对她身份认同的基础(尽管二者在动机上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我”对我们之间“所曾有过的”共同记忆却完全遗忘了。在这里,“我”和闰土、杨二嫂之间就形成了明显的双重错位关系:“我”亲近闰土,但他拒绝了“我”;杨二嫂亲近“我”,“我”却遗忘了她。对闰土的遗憾和对杨二嫂的惊讶同时叠加在了“我”一个人身上,因此,在这一刻对故乡的失望与疏离感被自然而然地放大了许多。
按照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哲学教授马各利特的说法,在“我”眼里,豆腐西施并不是与“我”有着共同的过去和共同的记忆的“深厚”(thick)关系的人,即亲近者或亲爱者。至少她并不是“我”希望能够获得身份认同的人,二者之间至多只能算作是“浅淡”关系(thin),即陌生人或遥远者,因此,双方之间牵涉的是“道德”关系而非“伦理”关系(32)参见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序第2页。。但是,在豆腐西施看来,二人之间的关系却应该是前者而非后者,这从“我还抱过你”中就可以看出。这种对双方关系认定上的严重错位,势必带来身份认同上的巨大差距,因此“我”也就无法从她那里获得所期望的乡土身份的认同。不仅如此,文章还写道:
然而圆规很不平,显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冷笑说: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那有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来说。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33)鲁迅:《呐喊·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6页。
对于“我”的遗忘,豆腐西施表现出“不平”和“鄙夷”,这就意味着她已经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可以理直气壮地对“我”的健忘进行审判。面对这些,“我”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只能感觉“愕然”和“惶恐”,而她又凭着自己的主观臆断或者说别有用心地对“我”现在的身份进行“认定”:“贵人”“阔了”“放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和“八抬大轿”。这些身份的认定和“我”的现实身份相差甚远,并与“我”的自我身份定位判若云泥。从杨二嫂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主动追求还是被迫塑造,有限制的身份认同几乎总是建立在一种对‘集体记忆’的呼唤之上。而这仅仅是把一种传递(untransmis)变为了一种获得(unacquis)”(34)[法]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第二版序言》,王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页。。但是,这绝不是“我”希望得到的身份“获得”,甚至可以说是“我”一直拒斥的一种身份,至少从一开始“我”就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
就豆腐西施而言,“什么都瞒不过我”的自以为是的态度,体现的正是她作为势利者的心态和眼光。“势利者最明显的特征其实并非是简单的社会歧视,而是在社会地位和人的价值之间完全画上等号”,“势利者最关注的无非是权力,一旦权力的分配发生了改变,他们所崇拜的对象亦会自然迅速地随之改变”。(35)[英]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3页。可见,势利者是与现代意识中的平等观念背道而驰的,他们试图从权力的拥有者一方获得好处。不仅如此,势利源自内心的恐惧,即对自己不如别人有一种深深的焦虑感。因此,明察秋毫、无所不知的“自信”,恰恰是豆腐西施对自身内心焦虑的一种掩饰。另外,势利者对他人还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压力:“与势利者相处,可以使我们恼怒,也可以使我们紧张和气馁,因为我们会感觉到内心深处的自我如此渺小,也就是说我们身份之外的自我如此渺小,我们根本无力改变势利者对我们的歧视。我们也许有所罗门的智慧,有奥德赛的足智多谋,然而,只要我们不具备一种社会认可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所有这些优点都形同虚有,势利者只会漠视我们的存在”(36)[英]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3页。。“我”在豆腐西施咄咄逼人的絮絮叨叨中,感受到的是这种“势利者”对“我”的身份认同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和焦虑,还是对于“势利者”唯利是图、自以为是的心理的不屑与鄙弃?从最终导致“我知道无话可说,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的结果来看,前者的成分显然更多。更进一步讲,这种“失语”的状态,同时也是“我”再一次遭遇到身份认同的失败的表现。
“我”既没有从闰土那里获得乡土认同的成功,无法慰藉自己漂泊的疲惫与孤单,也不能从尖酸刻薄的杨二嫂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上获得小市民阶层的认可与接受,反而在他们的严重误读之下陷入“尴尬”的境地。不仅如此,作为“我”的血脉之源与亲情之根的母亲,同样也没有能力承担起“我”的故土身份认同的责任;更令人担忧的是作为下一代的侄子宏儿,他和水生的关系恰如当年的“我”和闰土,身份认同的问题同样无法落地。而这次返乡后老宅的变卖与搬家既意味着“我”与故乡关系的割裂,也意味着“我”与故乡在情感上的割舍,更意味着切断了乡土身份认同的唯一通道。正如海德格尔在谈到荷尔德林的诗《追忆》时所说的那样:“由于灵魂的自我开放意味着开始时在得以起源的家乡因素中直接把握故乡,所以,灵魂恰恰不能找到故乡,因为故乡逃避这种把握意愿。关注家乡因素并且在其中意求着故乡,灵魂在开始时就被故乡所摈斥,并且被推入一种愈来愈徒劳无益的寻求之中”,因而故乡使灵魂“憔悴”。(37)[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08页。为此,试图从故乡中寻求自我认同的“我”也遭遇被故乡的一切所摈弃的结局,无处安放的乡土认同成为“我”再次陷入绝望的重要推手。在双重失落的挤压下,“我”的情感认同与心理期待无法实现正常着陆,只有寄托于若有若无的希望。《故乡》的深刻之处在于,对于这种无法把握的希望进行了反思——尽管“我”嘲笑了闰土所崇拜的偶像,但“我”对于希望的期冀又何尝不是一种有所寄托的“偶像”?本来“我”是不相信任何希望的,因为“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而只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最后的结语“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并不是要为他人指出一条未来的出路,而是自己回归内心后对抗包括自我认同在内的各种失败和黑暗的一种表达。有学者在研究周氏兄弟失和事件时指出:“实际上,独立门户不仅意味着兄弟之间从经济上割断了同胞关系,还意味着在社会地位、政治文化思想上也确立了自我独立的人格。”(38)李宗刚:《现代社会的主体性确立与传统社会的关系裂变——以鲁迅、周作人周氏兄弟失和作为考察对象》,《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这对于理解鲁迅与故乡之间的关系同样具有启发意义:“我”返回故乡而得到的是乡土身份认同失败的结果,这使“我”不得不割舍对故乡所能提供身份认同与情感接纳的幻想,即清醒地意识到“世上本来没有路”这一严峻的现实,也就是通过他者对“我”的自我身份予以接纳、认同以及给予情感慰藉的希望最终只能归于绝望的事实。在这种绝望的现实下,只有独自前行,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才能实现真正的身份认同和“自我独立的人格”。“鲁迅没有上帝,只有依靠自己,依靠内在的意志力;当他面对强大的外在黑暗,而外在黑暗会转化成为内在黑暗时,就只有依靠内在的光明面来抵御。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具有强大意志力的自我成为鲁迅的‘上帝’,这可以看成是鲁迅的‘宗教’。”(39)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80-81页。这种强大的意志力成为鲁迅实现愿望的支撑点。
当然,对故乡现实的失望并不能断然决然地导致怀乡情结的彻底割裂,这在情感上也无法真正实现。作者稍后创作的《社戏》则是“我”再次通过回忆故乡儿时经历和实现精神返乡的一次尝试。与《故乡》不同的是,在《社戏》中作者把对现实中看戏的失落处理成催生回忆的动力与背景,而不是像前者那样着力于书写“我”所见到的故乡的现实,因而“我”很容易而且很顺利地进入到童年回忆的乌托邦情境中,完成了精神返乡后对乡土认同的整个过程,同时也获得了心灵的慰藉与满足。这一过程的成功实现,同时也反衬出在强大的清醒的现实的观照之下,记忆的乌托邦无法存在,而惨淡的人生才是真正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