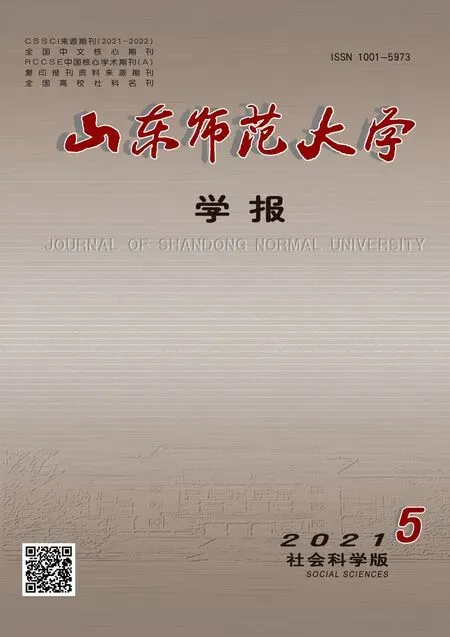苏联小说《第四十一》的叙述修辞*
2021-11-10谭学纯
谭学纯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350007)
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小说《第四十一》自1924年出版以来,我国出现了多个译本,(1)[苏联]拉夫列尼约夫:《第四十一》,曹靖华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此为修订重译本,篇末记有“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原作于列宁格勒,一九二八年七月译于莫斯科,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修订译文”。本文写作的版本依据为1985年外国文学出版社译本。也译作《第四十一个》。近一个世纪中,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对这部曾经“用蜡版油印的形式,印在红绿包装纸上的除政治理论的小册子外”的“革命的文学作品”(2)[苏联]拉夫列尼约夫:《第四十一》,曹靖华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93页。阐释并不充分,有些重要的问题亦未触及。这便是本文的写作动机。
一、《第四十一》:不同时期的接受反应、未触及的问题与重释逻辑
在兼有“爱情/革命/战争/死亡”元素的文学叙述中,《第四十一》讲故事的方式是独特的。对此,不同时代的中国读者,有不同的接受反应。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接受反应是积极的。1929年,鲁迅竭力支持李霁野在《未名丛刊》上推介《第四十一》曹靖华译本,赞赏原著以洗练的技术制胜,力促译著尽早出版。1931年,未名社解散后,鲁迅又推动该书在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以《苏联作家七人集》之名再版,并抱病作序。从曹靖华所说“这部作品在三、四十年代的我国,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也该是历史事实”(3)[苏联]拉夫列尼约夫:《第四十一》,曹靖华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94页。来看,当时的中国文坛对这部出版后即在苏联引发争议的小说的接受是肯定的。这是在国内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下,我国“迫切需要有助于煽起革命斗争火焰的、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气息的”苏联文学作品的历史要求。因此,我们不宜将鲁迅认为苏联文学“写战斗的比写建设的对我们有益”的观点(4)[苏联]拉夫列尼约夫:《第四十一》,曹靖华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95页。理解为鲁迅所持的文学政治观,而应理解为当时革命对文学的政治诉求。比较《第四十一》和同时期中国普罗文学“革命”的宏大叙述和“爱情”的私人话语合成的文本策略,似可见出普罗小说爱情想象的小资情调和寻找革命方位的努力,以及战争动员中革命对文学的政治诉求,只是其中潜隐的文学政治后来被提取出来,推向了另一个接受维度。
20世纪50年代的接受倾向从潜隐的文学政治走向凸显的政治想象,读者反应从前期的认同转向批判,且政治批判覆盖了艺术批评。1958年的《读书》比较集中地汇集了当时的声音,其中有稚嫩的政治激情(5)刘心武:《谈〈第四十一〉》,《读书》1958年第7期。按:此文为刘心武时年16岁的创作。,也有真诚但略带粗暴地理解文本人物感情的评述(6)张孟恢:《这不是战士的一枪——谈〈第四十一〉》,《读书》1958年第6期;张铁铉:《〈第四十一〉主要在写什么》,《读书》1958年第6期。。虽有读者认为小说“亲切有味”(7)赵一鹤:《亲切有味的〈第四十一〉》,《读书》1958年第7期。,但在当时的政治文化生态中,意识形态敏感的话语空间处于折叠状态。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经过20多年的接受空窗期,从此前凸显“政治”的接受反应,转为面向“人”的文学批评。较早调整认知站位的学术生产,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思想解放的话语生态,但调整中夹杂着论争和质疑,焦点相对集中为如何诠释《第四十一》中的人性。从80年代初 “什么是人性”的诘问(8)邢汤风:《什么是人性?——从〈第四十一〉谈起》,《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到张先瑞、王肇亨、蔡谦、叶继宗、赵中平先后在不同话语平台的回应(9)张先瑞:《阶级性战胜抽象人性的严峻形象——重评苏联小说〈第四十一〉》,《零陵师专学报》1982年第1期;王肇亨:《一部理智与感情相矛盾的作品——重读苏联小说〈第四十一〉》,《零陵师专学报》1982年第1期;蔡谦:《对马柳特迦形象的思考——也评〈第四十一〉,兼与有关论者商榷》,《韩山师专学报》1984年第3期;叶继宗:《枪声与祈祷——〈第四十一〉与〈土牢情话〉之比较》,《江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赵中平:《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中的人性问题》,《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1期。,争论背后的情感逻辑仍是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选项:阶级的人性、抑或抽象的人性。这一阶段的短暂接受史,既接续了50年代末的政治接受,也孕育了80年代中后期的审美接受。
1985年,外国文学出版社推出《第四十一》曹靖华修订译本,似可看作具有某种“召唤”意义的文化信号。召唤理论与批评从评判非此即彼的“人”,转向探索亦此亦彼的“人”。80年代中后期,本土学术语境中理论热点频繁更替,但围绕《第四十一》的话语兴奋点却较少转移或扩散,总体上似未溢出“性格组合”的解释框架。(10)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371-377页。从分析人物性格发展机制、人物塑造的突破和回归,到弥散着宗教关怀的“十字架下的浪漫”,再到诠释仇敌相爱和阶级搏杀,不同程度地涉及马柳特卡作为红军战士和女人的身份分化,以及人物所处“同质环境”和“异质环境”的转化,包括阐释马柳特卡的本我、自我、超我。(11)朱宝荣:《玛琉特卡的性格发展机制——读〈第四十一个〉》,《龙岩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张冰:《自我的突破与回归——〈第四十一〉中马柳特卡个性探微》,《外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1期;洪新:《玛柳特卡——一个双重角色的矛盾体现者——评苏联小说〈第四十一〉》,《杭州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孙建芳:《十字架下的浪漫——〈第四十一个〉宗教情结初探》,《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张海涛、郑绍楠:《〈色·戒〉和〈第四十一个〉里的“孤岛之爱”》,《电影文学》2012年第2期;曾思艺:《人性与文明视角下的阶级搏杀——〈第四十一〉仇敌相爱的战争叙事》,《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肖沁浪:《〈第四十一〉的心理学分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所有这些,也似乎可以读出心理分析版的“性格组合”。
但“性格组合”“异质环境”无法解释下面的问题:为什么马柳特卡与战友同处时她作为战士的刚性性格没有“组合”进女性柔情?为什么马柳特卡对战友关闭的爱情之窗却为自己押解的俘虏打开?怎样解释小说悬搁“红军/白军”(互为对象的异质性他者)的身份区隔,重建“咱们”合目的性的身份认同?怎样解释文本结构中的男女主角“敌人→人→恋人→敌人(恋人)”的身份转换与纠结及其爱情生态的变化?怎样解释与此关联的事件在叙述推进中的修辞干预?(12)本文所涉“修辞”,是在以下意义上使用的:其一,不限于遣词造句的修辞技巧,而延伸到指向文本建构的修辞诗学和指向人的精神世界的修辞哲学;其二,不同于耶鲁学派视为文本解构元素的“修辞性”,本文着重分析作为文本建构元素的修辞性。对此笔者有过系列探讨。这些都存在现有研究相对忽略的认知前提和叙述逻辑,也是本文重释经典的观察维度。
细读《第四十一》,可以观察到:从“红军/白军”敌对的共同体收缩和失联,到孤岛临时共同体重建与撕裂,叙述走向注定了红军女战士最终射杀重回敌人身份的恋人的结局。在文本叙述推进的不同阶段,马柳特卡负有三种不同的使命:
一是不让被俘中尉逃。小说第三章,红军政委叶甫秀可夫指令:“你好好留神看着。要是放跑了,就剥你的皮!”
二是不让被俘中尉死。小说第六章,面对高烧昏迷的中尉,马柳特卡自语:“他要死了……我怎么去对叶甫秀可夫说呢?”
三是不让被俘中尉活。小说第四章,叶甫秀可夫曾交代负责从海上押送俘虏的马柳特卡:“万一遇上白党,不能交活的给他们。”
实际上,白军中尉之死在小说第二章红军女狙击手子弹射偏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中尉之死是故事的闭环,死亡延迟只是为了故事换一种方式讲下去。第三章开头,作家就“剧透”白军俘虏是活人中的多余数字。第五章,作家借马柳特卡的心理活动向读者传递的信息是,俘虏押解到目的地,审讯之后必死无疑。第十章结尾,即文本叙述终端,马柳特卡执行上级指令(不能把俘虏活的交给白军)。从接受指令到执行指令的叙述长度,是死亡推迟出场的过程。死亡在爱情叙述中修辞化地包装并延期,却不会改变结局。正是死亡推迟出场的叙述空间,演绎了从爱情发生,到爱情速冻、解冻,再到爱情之殇的凄美故事。文本反预期的叙述满足了从爱情发生到爱情之殇的关键条件:男女主角各自所属共同体收缩、失联和荒岛重建临时共同体,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人物角色关系变化;爱情海葬的结局,也是因为被动重建的临时共同体撕裂,以及红军白军力量对比发生逆转。以下分析,将逐层展开《第四十一》反预期叙述几个关键拐点的修辞干预,每一次修辞干预,都是在原有叙述能量渐弱的情势中,为故事推进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红军/白军”:共同体收缩和失联及其现场力量对比
作品人物的身份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被定义,文本主角马柳特卡和俘虏戈沃鲁哈-奥特罗克的第一身份,分属“红军/白军”共同体。这是文本叙述人(作家)为文本角色设定的共同体。
马柳特卡接受红军的纪律规约,入伍时将爱情交给对革命的承诺,签字保证战争胜利之前不谈情说爱。她与革命组织之间的契约,不能将其简单理解为红军对一个渔家少女的爱情禁令,而是表达作家希望革命高于一切的价值信仰。这种信仰暂时封存了马柳特卡的爱情期待,关闭了女战士接收战友爱情信息的通道,也使战友收起了对她的非分之念。不了解情况的新战友甚至因为痴情的凝视和鲁莽的动作,付出了被打落三颗牙齿的代价。
马柳特卡的幻想世界和激情释放的方式是写诗,她的革命美学和诗歌美学是叠合的,虽然精准的枪法和稚拙的诗语代表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不对称的表达,但丝毫没有影响她在押解俘虏途中与之谈诗的兴致。这个看似有点生硬的叙述片段,是引出后续故事的修辞设计。因为谈诗,松绑俘虏,也松绑了敌对的紧张关系。按照福柯的理论,对人的控制,首先是对身体的控制。松绑意味着解除对身体控制、解除对人的控制,并重新分配了由押送者绝对掌控的话语空间,从敌我之间对立的局面转为“人和人之间”的交流。马柳特卡为诗而狂、也为诗所虐。从战友到编辑部的编辑,对她的诗几乎全是差评,唯一没有给出负分的竟是她押解的俘虏,这或许为马柳特卡写诗的自我认知注入了些许自信的能量。
分属“红军/白军”的敌对双方、超越身份政治的“围炉诗话”,也许存在身份定位的模糊地带。谈诗的话语权,关联着交谈者的身份和文化资本。在谈诗问题上,俘虏比俘虏押送者更有话语权,这样的修辞设计有利于淡化谈诗现场双方的当前身份。此时由于没有凸显双方拥有的其他身份,又都没有建构新的临时身份(这要等到二人共同面对荒岛生存才有可能),似乎属于二人身份转换的空档期。
比身份转换的短时空白更具有叙述转向意义的修辞干预,是作家设计了“红军/白军”的共同体收缩和失联,以及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红军从突围时的100多人减至25人(男兵23人、女兵1人、加上带队政委1人);白军中尉被俘虏时,同属一个共同体的6人中5人被击毙。在红军带着白军俘虏穿越沙漠的艰苦跋涉中,人员单方面递减;当海浪吞噬了马柳特卡身边两名战友的生命时,“红军/白军”的现场力量对比发生结构性变化。在上述过程中,递减的量化关系比依次呈现为: 25:1→11:1→10:1→3:1→1:1。
原先的多对一转化为一对一,敌对的两个共同体同时失联,原先的社会关系网络在陌生化空间处于屏蔽状态。不过即便在一对一的博弈格局中,马柳特卡仍然把控节奏,猫鼠游戏的几率并不存在。从身体条件、荒野生存能力以及对海岛生存环境的熟悉程度来说,马柳特卡比奥特罗克更有优势。但强者生存与马柳特卡的阶段性任务不匹配,革命赋予了当时情境中的强势方和弱势方都活着的某种“合理性”,在白军俘虏对红军所需的情报价值没有兑现之前,押送者要确保自己活着、并且将活着的俘虏押解到目的地。此时马柳特卡押送俘虏所承担的风险已经从不让对方逃,转为不让对方死。
与“红军/白军”共同体分离后的女战士和男性俘虏必须都活着的孤岛现实,以及增加共同存活概率的内生性需求,作为前在事件之果和后续事件之因,共同导致押送俘虏的事件链条由于不可预测的自然力暂时中断,既定叙述规则随之搁置。由此压缩了原初的叙述空间,叙述惯性难以延续,叙述拐点转向押送俘虏的次生事件。演绎这个次生事件的新的共同体,是事件主角在被困海岛临时重建的。
三、“咱们”:临时共同体重建和撕裂状态下的孤岛爱情及其终结
流浪孤岛的个体是脆弱的, 避免孤独的个体成为“孤岛中的孤岛”的可能性,是一个人释放利他的善意,另一个人相向而行;一个人的优化选择和另一个人的优化选择达成默契,这是1+12的关系理性。新的关系理性,是新的临时共同体的无言契约。与此相应,一个悬置“红军/白军”身份区隔的人际修辞代码“咱们”在文本中活跃起来,它意味着原属“红军/白军”的个体向被动重建的临时共同体位移。构成“咱们”的俘虏和其押送者以新的角色身份的相互表达,按新的意义秩序,组织文本事件主角的对话。文本中“咱们”的部分对话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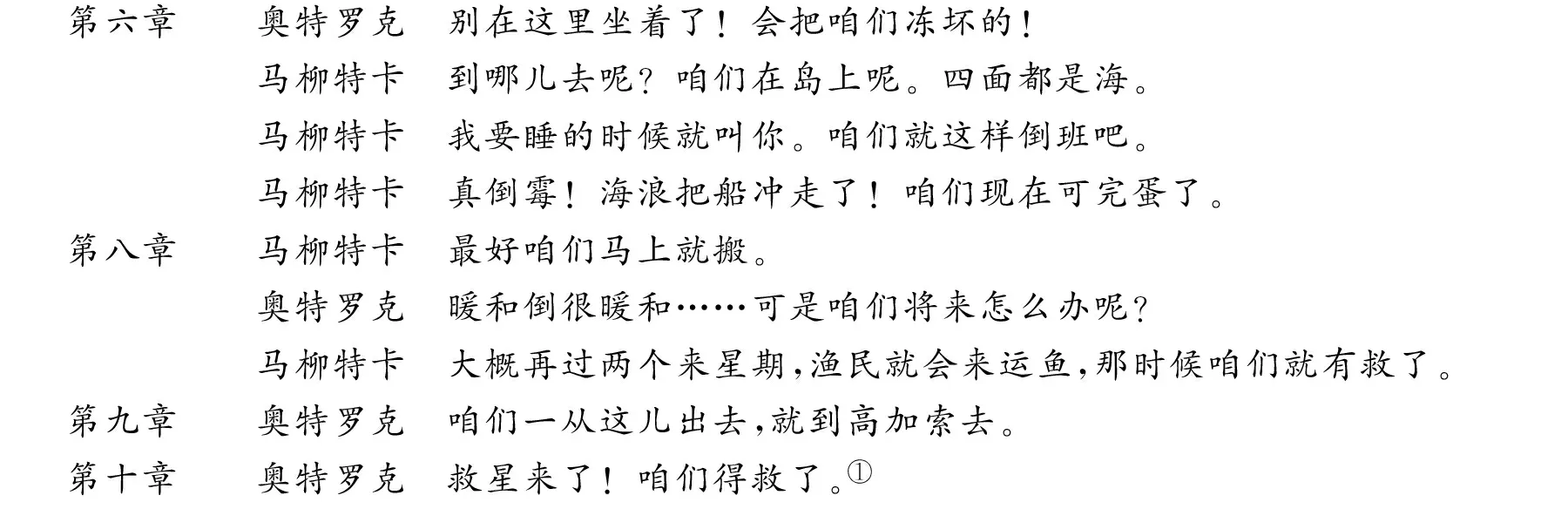
第六章奥特罗克别在这里坐着了!会把咱们冻坏的! 马柳特卡到哪儿去呢?咱们在岛上呢。四面都是海。马柳特卡我要睡的时候就叫你。咱们就这样倒班吧。马柳特卡真倒霉!海浪把船冲走了!咱们现在可完蛋了。第八章马柳特卡最好咱们马上就搬。奥特罗克暖和倒很暖和……可是咱们将来怎么办呢? 马柳特卡大概再过两个来星期,渔民就会来运鱼,那时候咱们就有救了。第九章奥特罗克咱们一从这儿出去,就到高加索去。 第十章奥特罗克救星来了!咱们得救了。①
“咱们”是对文本叙述人称“她/他”、文本对话人称“我/你”在搁置他者异质性状态下的重新编码,或者说重新组织了“她/他”“我/你”的意识中无法获得一致性的意义。“咱们”既是最小的共同体,也是荒岛生态中最大的共同体。这个被动重建的共同体,以“咱们”的方式,而非“她/他”“我/你”的方式,从战争伦理个体转向生命伦理个体的临时合作。
社会学意义上的“合作”,用语言学的义素分析,可以提取“+彼此配合 +共享彼此配合的成果+为他人着想”的语义成分。“咱们”的“合作”,明显具有上述语义特征:两人在鱼仓里用干鱼烧火烘烤湿衣服的场景,使这个静态的自然空间具有了动态的“人化”秩序,奥特罗克表现出对女性裸体的尊重和马柳特卡放弃女人的身体保护(不让中尉长时间受冻),可以理解为海岛上的孤男寡女身体性地参与“为他人”的合作。两性近距离接触的审美,可欣赏而不可亵玩的自觉,修辞化地暗示了“政治的/阶级的人”以“身体的人”重新出场、“敌人”作为“人”重新出场。此时“敌人→人”的转换还没有演绎出“恋人”的剧情,“两个人的篝火”还没有“照亮整个夜晚”。这种身体性呈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后来的感情发展的“前叙述”。只不过这个叙述推进是缓慢的,这是延缓死亡所需的修辞策略。
(一)临时共同体“咱们”的爱情蓄势和发生
悬搁了敌对情绪的关系理性和荒岛互助共存的生命伦理,不一定直接导向爱情。所以,文本叙述急转弯之后的反预期推进没有选择冲动型的爱情速递,而是为非常态的爱情打开方式继续积蓄修辞能量。“咱们”没有思想准备的爱情生长因素,需要更重要的转换:从理性的生存诉求转向感性的心理重建,这个心理过程伴随着彼此的重新认识和发现。
从行军路上写诗并想象将来书上印有自己名字的女兵,到持枪命令自己往海岸拖船的押送者,再到用子弹中的火药烧鱼干烤火取暖的渔家姑娘和“去身体避讳”的丰满异性,在奥特罗克看来,马柳特卡从可接近变得可接受,甚至有某种可依赖的成分,如同鲁滨逊对“星期五”的依赖。“星期五”用作奥特罗克对马柳特卡的修辞化面称,意味着身份符号背后身份主体在场方式的改变。
在马柳特卡眼中,俘虏从“像套着链子的狗”,到作为“人”的形象,在她的感性世界映现出模糊影像:良好的教育背景,有知识、懂艺术,在女人面前不失绅士风度,身为俘虏在被押解途中却不曾放低身段,不知道自己死之将至而微笑着等待未知的下一站。所有这些,连同俘虏(中尉)讲述的陌生世界,对人生只有捕鱼和打枪、但憧憬“诗和远方”的马柳特卡来说,也许具有激发她尝试了解、读懂的某种神秘意味。她的情感边界是逐步开放的,面对中尉那双“对女人危险”的“蓝眼睛”,马柳特卡保持克制;面对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的中尉,马柳特卡押解俘虏的强势姿态转换成了几天几夜的人道守护。战士的使命使她担心如果俘虏死了,自己不好向上级交代;同时战士身份中也显现了女人的柔性刻度,她轻抚中尉蓬乱的卷发、温存低语,这似乎是魔鬼枪手的另一个形象。文本中透露马柳特卡内心世界微妙变化的一处细节是:她将战友吸剩的烟末烘干,将自己写着诗的纸拿来给中尉卷烟抽。细读文本不应该忽视:写诗是马柳特卡的精神需求,抽烟是中尉的物质需求,女人写着诗的纸用来给男人卷烟,这是作家运用的一种特别的隐秘转喻。文本叙述的这一切,只是修辞化的爱情铺垫,表现出作家对这段不该发生的爱情的足够耐心。接下来的修辞干预是更有关键意义的话语行为——苏醒过来的白军中尉问马柳特卡为什么照顾“敌人”,得到的回答是:“哪里还是敌人?连手都抬不起来了,算什么敌人?我和你是命该如此。没有一枪把你打死,我生来第一次打空了,哦,那我就照顾你到死”。(13)[苏联]拉夫列尼约夫:《第四十一》,曹靖华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65页。如果说此前两人裸身烘烤湿衣服的细节表现出“敌人”以身体的方式回到了“人”,那么此处的对话则表现出“敌人”以认知的方式回到了“人”。
《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的“敌人”是指敌对的人、敌对的方面,也就是具有“+利益冲突+不能相容”的语义特征,这是“敌我”对立的身份体系的构成项之一。随着“咱们”的临时共同体重建,白军中尉原为“敌人”的语义特征被悬搁。没有攻击能力、也没有防御能力的弱势对手,不是强悍敌人的面相,不属于马柳特卡定义的“敌人”。女战士对“敌人”的认知,改写了原先的“敌我”关系。“敌人”概念从话语中退出的同时,也从马柳特卡紧绷的神经中退出,由此带来的是消除爱情权属中的身份区隔,这是作家制造文学叙述可能性的修辞干预,而且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没有被神枪手一枪致死的“敌人”,由枪手原先的承诺“那我就照顾你到死”,转换成“我和你是命该如此”的表达,这也是“敌人→人→恋人”转换的修辞信号。“敌人”退出马柳特卡心灵敏感区,“人→恋人”的转换在荒岛异性的“讲述”与“倾听”中推进:中尉讲故事、马柳特卡听故事,思想在不同层面碰撞,“爱”的距离渐次拉近,直到有一天,他们触碰了爱情按钮。
马柳特卡在经历了爱情高冷之后姗姗来迟的温度,是对爱情的妥协?还是爱情长时蓄势之后的短时泄漏?马柳特卡在革命队伍中的战士身份有着革命先于爱情的承诺,当红军女战士和白军男青年固定的军人身份在“咱们”的临时共同体被悬搁时,马柳特卡和奥特罗克暂时走出了原初的身份规定,海难幸存者从对生命伦理的坚守转向对爱情伦理的找寻,是非常态的爱情打开方式。就此而言,孤岛爱情的发生不是奇迹。这是一个反纪律、但合乎特定情境中情感逻辑的生命插曲。暂时疏离战争伦理的身份主体,游离于各自的军事集团,在临时构建的共同体中,以个人的名义行使个人的权利,包括爱的权利。但在小说第八章结尾才呈现“形式化”特征的“爱情进行时”,延伸到第九章前半部就跌宕起伏,在作家反预期叙述不断翻盘的同时,文本建构的修辞动能不断强大。
(二)临时共同体“咱们”的爱情速冻和解冻
作为荒岛重建的临时共同体,“咱们”的身体虽时或相拥,灵魂却无法共情。不同的人生坐标,由于种种因素经常被重新找回。当二人隔着信仰鸿沟相互输入各自的价值观时,交谈变成了夹杂着詈语的争吵。在奥特罗克的价值判断中,自己忠诚的共同体“白军”小于临时共同体“咱们”。在海岛被困和被救期间,马柳特卡填充了奥特罗克的生活,他希望远离战火和血腥,隐身“咱们”的江湖,他的“去政治化/去战争化”理想,得到的回应是一记耳光。因为在马柳特卡的价值判断中,自己忠诚的共同体“红军”大于临时共同体“咱们”,她相信红军为真理而战、为穷人而战、自己是正义之战的一部分。伴随着争执、语言暴力和行为暴力,“咱们”的临时共同体松动,文本对话中成为“咱们”的“我/你”,回归到各自最初的样子。爱情快速冻结,也为此后爱情沦陷作了铺垫。
但是,爱情从发生到终结的直线距离往往不是文本叙述的修辞距离,因此接续此前的爱情发生和速冻,又快速解冻,仅仅三天之后,爱情冰点消融,“咱们”的对话从相互的鄙称重回昵称:奥特罗克对马柳特卡的面称从“烂货”变为“马申卡/皇后”; 马柳特卡面称奥特罗克从“软体动物/小蛆虫/无赖/狗崽子”回到“蓝眼睛的鬼东西”。身份符号频繁转换,浓缩了爱情速冻到解冻的过程。不过,打破读者预期的叙述并没有就此完结,而且爱情解冻之后的文本叙述没有按照情绪平复的轨道推进。此时,作家再次选择反预期叙述路线。
(三)撕裂“咱们”临时共同体的爱情海葬和最后的爱情呼喊
临时共同体“咱们”的重建和撕裂,是《第四十一》的事件序列“打开”和“收拢”的弹性叙述空间,其间有一个重要的叙述道具:船。
小说第六章,马柳特卡和奥特罗克漂流至荒岛,船被海浪冲走,产生连锁反应:俘虏及其押送者共同面对荒岛生存,以及由此带来的角色关系改变,提供了暂时消除敌对紧张感的海岛生态,也打开了引入次生事件的叙述空间。小说结尾,出现在海平线上的船,打破荒岛二人世界的临时共同体,次生事件的叙述空间闭合。消失的船和出现的船,是荒岛上“咱们”的爱情短暂维持和最终崩裂的叙述道具。起初“咱们”激动地以为远处隐现的船帆将带来福音, 奥特罗克甚至情不自禁地吟诵起莱蒙托夫《帆》的诗句。但进入视线的船,很快引起了马柳特卡的警觉。奥特罗克也随即发现船上是自己人,归属意识驱动他奔向海边,他跌倒又爬起的肢体语言,撕裂了临时的共同体,撕裂了“咱们”不可持续的爱情关系。更严重的是,马柳特卡始终处于强势的力量对比格局将发生逆转:从中尉被俘时“多对一”的红军强势,到滞留海岛时“一对一”的马柳特卡强势,再到中尉跑向海边时“一对多”的白军占优势的格局,马柳特卡将由强势方转为弱势方。
马柳特卡抢在双方力量强弱转化之前,越过爱情伦理,将荒岛上共存性的生命伦理拉回到对抗性的战争伦理,荒岛重建的共同体,重新向已经中断的各自的共同体位移。马柳特卡的枪声,不是意识到形势逆转的自救(已经不可能),而是向所属战争集团的忠诚表达,在最后的时刻完成使命:不能交给白军活的俘虏。
作为一种修辞设计,作家没有放弃最后的反预期叙述机会,让射杀中尉的女战士隔着生死两界呼叫海葬的爱情。如果说开枪是军人马柳特卡管控女人马柳特卡,那么目标中枪之后的抱尸痛哭,则是军人的子弹击碎的爱情伦理在女人心中复燃,她想抱起的那个被打碎的头颅还留着她的体温。她向那个困惑怜惜地望着自己的眼睛的男人发出的最后的爱情呼喊是:“我心爱的蓝……蓝……眼……睛……的……人……哪!”这是一个女人对一场伤不起的爱情的悲恸释放,爱情悄悄来临时的温度,化作瞬间离场的凄美,融入阿拉尔海浪的悲怆诉说。这种设计填充了小说的开放式结尾。
四、爱情包装的死亡:数字修辞“第四十一/第一”
本文第一部分已经提及白军中尉的死亡结局早已注定,只是被爱情叙述修辞化地包装并延缓了。文本叙述的死亡被爱情包装并推迟出场的结构安排很明显:从叙述长度看,在小说前五章中,马柳特卡处于爱情空白期,为第六章的爱情蓄势留足了修辞空间。从叙述节奏看,在从第六章爱情发生到第十章爱情海葬,都是叙述急转弯,叙述拐点的流畅转换对应于共同体位移,不断显示爱情启幕到落幕的情感变化。小说第九章起始叙述,以最简约的方式概括了爱情包装的死亡:
近卫军中尉戈沃鲁哈-奥特罗克,本来应该是马柳特卡生死簿上的第四十一名。
可是却成了她处女的爱情簿上的第一名了。(14)[苏联]拉夫列尼约夫:《第四十一》,曹靖华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75页。
“第四十一/第一”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和一个有故事的男人的数字修辞:“第四十一”是奥特罗克的黑色数字,“第一”是马柳特卡和奥特罗克的粉色数字。奥特罗克是马柳特卡瞄准的第四十一个射杀目标,但鬼使神差地打偏了。暂时没有加入第四十一个死亡数字的目标成了俘虏,并由马柳特卡看管,最终仍是她的第四十一个击毙对象。马柳特卡击毙的第四十一个敌人是她的第一个恋人。她的第一次爱情,包装了第四十一个死亡。第四十一个死亡造型,因荒岛上第一次亲密接触而令人唏嘘。
从“第四十一”到“第一”,伴随着“敌人→人→恋人”的慢节奏转换;从“第一”到“第四十一”,是“恋人→敌人(恋人)”的快速“化学反应”。敌人倒在战士马柳特卡枪下,恋人被女人马柳特卡的哭喊象征性地“召回”。“敌人/恋人”的影像快速切换的同时,马柳特卡不仅要复制作为神枪手的自己,更需要战胜自己。那个一度从她的心理警戒区分离的“敌人”归位、“恋人”重回“敌人”身份,她必须朝他开枪,并必须致死。但“敌人”一分钟前还是“恋人”,她的枪口需要同时对准自己的感情。在这样的修辞情境下,开枪忠于革命,不开枪忠于爱情,两难抉择指向同一个男人。马柳特卡扣动扳机的秒杀,是军事速度,也是政治速度。同时被射杀的,其实还有马柳特卡多重身份中的另一个自己。奥特罗克在这个世界上听见的最震撼的声音,是马柳特卡第四十一次死亡表达;这个男人没有听到的,是马柳特卡射杀第一个恋人之后的抚尸痛哭。至此,爱情传奇中延迟出场的死亡终结。海天之间回荡的生者对死者的呼唤,是死亡终结之时的爱情回声。
五、身份固化和身份变化及其预设:应如何/是如何/能如何
人的社会活动,是社会角色以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共同体及其位移过程中呈现的不同在场姿态。作为文本反预期叙述的修辞干预,作家不断以文本角色的身份变化冲击其身份固化。身份主体对“我是谁”的叩问,在“你认为我是谁”的预设中打开。而“你认为我是谁”无法脱离身份认知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当下此时的身份主体处于什么样的共同体。评判《第四十一》男女主角的行为,需要联系身份主体与所属共同体,忽视或重视这个条件,会对小说男女主角身份认知和行为选择产生不同预设。
静态的单一认知以身份固化遮蔽角色身份的复杂性,据此解读《第四十一》,马柳特卡作为红军战士和奥特罗克作为白军中尉,在分属“红军/白军”共同体中的身份固化,角色行为被固化的身份所规约,甚至不排除身份固化携带的身份暴力。背后的预设是:固化的身份主体只能作为“这一个”(唯一)而存在,当且仅当主体身份固化为“红军/白军”的“是如何”,定格为永远“是如何”,不考虑“应如何”和“能如何”的冲突。这种身份认知及其预设的本质,规避了人的完整性和主体自由,引导对身份主体心理的丰富性及行为可选择性的平面处理。
动态的复合认知正视身份变化及角色身份的复杂性,据此解读《第四十一》,承认马柳特卡和奥特罗克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与“红军/白军”的共同体失联,及重建“咱们”临时共同体的合逻辑性。小说男女主角的行为方式偏离固有身份的变化,是死亡被爱情短时包装的关键。小说结尾的爱情之殇,是“咱们”临时共同体撕裂、身份主体向“红军/白军”共同体回归的必然结果。“咱们”没有可能真正建立二人世界,不管是马柳特卡曾经承诺的照顾对方到死,抑或奥特罗克希望二人逃离战争的想象,背后的预设是:变化的角色身份可能作为“这一个”(之一)而存在,当且仅当主体身份固化为“红军/白军”的“是如何”,并非永远“是如何”,身份主体“应如何”无法从“是如何”推导,也无法预测“能如何”。身份主体接受“是如何”的规约,有“能如何”的选项,却未必符合“应如何”的剧本。“能如何”是理论上开放的一种可能性,面对可能性的主动或被动选择,是开放的可能性在当下此时的现实在场。这种身份认知及其预设的本质,直面人的完整性和主体自由,引导对身份主体心理的丰富性及行为可选择性的立体处理。
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政治文化生态中,能够为小说争取到的叙述空间有多大,《第四十一》作了大胆的尝试。当文本叙述不该发生的爱情与被动位移的共同体产生冲突时,身份主体“是如何/应如何/能如何”的自我意识被重塑,但又不稳定。作家的修辞处理,力求不稳定中的稳定:荒岛生存的红军战士和白军俘虏暂时脱离原先的共同体,但是马柳特卡内心没有撤出红色底线,革命犹如程序编码,植入了马柳特卡的肌体。随着革命程序休眠和激活的循环往复,读者看到了爱情发酵、爱情速冻、爱情解冻、爱情海葬和海葬之后的爱情呼喊。马柳特卡和奥特罗克短暂爱情关系中的互相伤害,是因为各自对世界的理解;爱情关系最终撕裂,也是因为对各自世界的选择。重释经典,不宜从道德层面“应如何”定义现实层面的“是如何”,将《第四十一》解读为爱情出位,或爱情毒药;也不宜从行为层面“能如何”,想象《第四十一》“是如何”,礼赞“伊甸园的复归”(15)吴静、郑栋鹏:《〈第四十一〉:“伊甸园”的复归》,《潍坊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或臆测性别象征秩序中的女性主体话语建构(16)参见张培勇:《〈第四十一〉:走向女性中心主义的范例》,《社会科学家》1995年第5期;《俄罗斯有女性文学吗?——谈谈〈第四十一〉女性主体话语的建构》,《俄罗斯文艺》1996年第2期。。而应该忠于文本,尊重文本所呈现的变化中的关系在运动中的转换。关系的改变,必然改变关系中的个体;关系的改变,必定有着改变关系的条件。需要正视的是,人作为关系中的个体,不是“恒在”,而是“变在”,这是“存在”的真相,也是思考和定义作为精神自主和身体自主的“人”及其命运的认知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