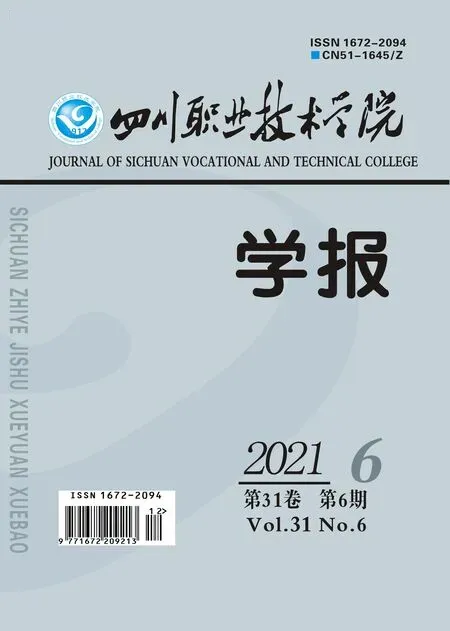论李洱《应物兄》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2021-02-01张佩欣
张佩欣
(南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小说《应物兄》以八十万字的庞大篇幅,向读者展开了一幅当代知识分子生存百态的宏图,其中,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是《应物兄》的主题和核心,“一时代文学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时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塑造。”[1]《应物兄》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当代知识分子生存现状映射,探析其中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对当代知识分子自我生存现状的定位与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自省与借鉴意义。
一、知识分子类型群
本文所探讨的《应物兄》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处在学院体制内,更接近于托马斯·索维尔所说的“理念的处理者”[2],即知识分子是一种职业种类,从事此类职业的人是专门处理理念知识的,泛指作家、学者,教授等等,是与医生,工程师等等有实操性专业知识的职业区分开来的。《应物兄》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形象众多,根据年龄层和性格气质,笔者将三代知识分别归类为立法者、阐释者、消解者,分别对应以双林院士为代表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以应物兄为代表的中坚代知识分子和以易艺艺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但任何一种定义都只是一种知识性的认识,无法涵盖概念的全部复杂性及其内涵,唯有结合文本人物形象,才能更好地探析。
(一)立法者
老一代知识分子是1966 年之前考上大学,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立法者”的角色,拥有权威性,是知识的“仲裁者”,其地位无可代替。在《应物兄》中,这类知识分子有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程济世、济大教授柏拉图权威何为、济大教授张子房、导弹专家双林院士等。这些立法者,在各自的知识领域掌握了一套客观、中立、程序的陈述和规则,并且这套程序和规则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得到社会的认可[3]17。造出新中国第一颗导弹的双林院士“像是一个范例,一个寓言,一个传说,就像经书中的一个章节。”[4]121重译了《富国论》的张子房“曾经风靡经济学界”[4]270,在国内开讲座的程济世无需微言,用七十二张票就让听众置身在儒学文化中。立法者不仅是权威,他们身上还带着一种马克斯·韦伯所说的80 年代知识分子的天职感(calling),即一种对社会充满忧患意识,随时能启迪民众,并准备献身于国家的使命感,他们有着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但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他们大多数从神坛被拽向世俗,从圣贤变成凡人。双林院士被称为是个闷葫芦,他被“请”到巴别开讲座,年轻一代讨论他时充满不屑,认为他老糊涂了,“他现在有多种身份,但没有一个身份对我们有用。”[4]110张子房因忍受不了体制环境内知识分子的谄媚,不得不装疯卖傻,远离尘世。商品经济社会不再需要立法者的使命感,他们的权威也受到了挑战和质疑,并且大多数被边缘化。
(二)阐释者
中坚代知识分子是下乡一代,在当代社会中扮演着阐释者的角色,即将自己共同体内部的知识翻译、阐释为其他共同体成员所能理解的知识[3]18。一方面,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知识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已经不需要全能型的专家了,知识分子只需拥有一技之长,他们更多的成为学院内的学者,只为本领域的成员所认识,体制环境让他们没有了立法者至高无上的权威。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冲击下,面对金钱的诱惑,不少知识分子选择为钱或为权,转向做生意或政治领域,市侩气让他们失去了普遍的社会关怀。这些阐释者类型的知识分子包括济大教授儒学研究专家应物兄、生物学家华学明、芸娘、文德能、程济世私塾弟子敬修己、省长栾庭玉、出版商季宗慈等等。阐释者的天职感被志业感(vocation)所取代,知识对他们来说更多的只是一份工作,而不是使命。
在阐释者身上,我们能看到文化生产的商业化、物质化和失语化。应物兄的著作《<论语>与当代人的精神处境》在出版时被改成《孔子是条“丧家狗”》,而他本人为了这本书更是在一个月内不停地在全国各地参加促销活动,频繁地与媒体接触让他在言语间染上夸张主义倾向,变成一个文化思想的明星。出版商季宗慈出书考虑的不是书本作者的权威、内容的厚实,而是书籍的作者能不能达到新闻宣传效果,引起社会效应,为此他表示不喜欢出版年长学者的书,因为没有新闻效应。省长栾庭玉在得到何为教授去世消息时,迅速对着何为的遗像墙举行默哀仪式,为的是第二天上新闻头条。这些阐释者谈论多于实践,喜欢唱道德高调来掩盖人性弱点,在交往中普遍带着虚伪性。在李洱的笔下,中坚代知识分子更多处在自我消耗和矛盾性的挣扎中。
(三)消解者
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是在新世纪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属于消解者类型。他们游戏人生,消解人格,体现出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倾向。这一代知识分子包括乔引娣、金彧、卡尔文、易艺艺、珍妮、程笃刚、张明亮、文德斯等等。如果说阐释者类型的知识分子还处在过渡阶段,他们尚有一些权威和公共性,那么消解者的公共性已经完全丧失,他们既没能为自己设定对社会的使命,社会也没有赋予他们特殊的任务,他们达不到立法者的高峰,又不屑于成为阐释者,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社会缺乏统一的价值尺度,他们或把堕落放纵当成时尚,或通过手段上位,或消解传统,游戏人生。
乔引娣通过在元宵晚会上谄媚校长得到在校长办公室实习的机会,甚至挤走旧助理。易艺艺不精学术,热衷社交,她背着应物兄和程笃刚抽大麻,性交,最后产下一个畸形婴儿,只为能依靠婴儿在太和研究所谋取一职。留学生卡尔文,自杀时采用直播的方式,还要喊着“吾日三省吾身”,将儒学的传统文化地位娱乐化消解……这些消解者大多笼罩在虚无主义的阴影下,游戏人生。就像应物兄对易艺艺的评价“一个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的人,她的话就是不真实的。她的生活也是不真实的。”[4]850他们的生存方式,是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去游戏人生,在虚幻与不真实中寻求意义。
二、失落的家园:空间与精神家园丢失
立法者、阐释者和消解者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遭遇和经历不尽相同,也有着不同的知识分子品质特点,但在《应物兄》中,却呈现出相似的精神困境:立法者站在知识顶峰,拥有高度话语权后成为边缘人;阐释者在权利、物质与学术间周旋,最终作茧自缚;消解者不精学术,游戏人生,纵情狂欢。李洱在《应物兄》中通过集体筹建儒学研究院这一主线展现不同类型知识分子想摆脱精神困境的意象与努力,但他们在筹备儒学研究院过程中各自的挣扎和努力没能使他们摆脱困境,反而使他们陷入了群体迷失。
这种群体迷失,是商品经济下知识分子失去家园无家可归的迷茫和失去自我精神空虚的焦灼。海德格尔在阐释荷尔德林的《返乡——致亲人》中,认为诗中的“家园”是“指这样的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有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已要素中存在。”[5]这一家园概念在《应物兄》中也同样适用,空间家园和精神家园对知识分子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但在《应物兄》中,一方面,仁德路错位,知识分子空间家园的消失,另一方面,情感体验疏离,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荒芜。
(一)生存家园消失:身份认同困难
《应物兄》小说的主线是建立儒学研究院,整篇小说都是围绕着邀请程济世回国入驻儒学研究院展开的。
应物兄前往美国拜访程济世时,多次试探程济世想回济州大学任教一事是否确定,程济世对此展开了一系列对济州的童年回忆。程济世的童年是在济州度过的,在他的记忆中,济州的桃花、红叶、济哥、雪、仁德丸子等等,无一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但记忆是一个“基于过去的经验和经历,以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为原始素材”[6]进行重构和回忆的过程。在重构和回忆的过程中,由于主体的遗忘与想象色彩,很容易产生“情绪记忆”,即“当某种情绪或事件引起个人强烈或深刻的情绪、情感体验时,对情境、事件的感知和记忆。”[7]程济世对于济州的记忆是遥远的童年时代,当他身处异国,半生颠簸之后再次回忆起童年时,不免唤醒他对济州的特殊情感。对他而言,济州是家园,是他的出生地,是故乡,所以济州的一花一草一木都在记忆的重构中蒙上了美好的色彩,带上了他的个人情绪。程济世对济州童年记忆的再现和重构,其实是在寻找自身的身份认同,仁德路是他确认自我的“根”的一个重要途径。
仁德路原本只是儒学大师程济世的精神家园,而济大为了请程济世回国任教,把儒学研究院建在了仁德路,这使仁德路不仅仅只是程济世的单人精神寄托,也成为了知识分子们的生存家园。然而在小说中,知识分子们多次召开会议,甚至实地考察,都找不到仁德路,仁德路已经在城市化现代化的建设中消失了。仁德路在历史的洪流中被卷走,暗示知识分子的生存家园在现代化中被边缘化,但知识分子们仍不放弃,试图重建“仁德路”。他们不顾民间的反对,将住宅拆迁,重建程家大院,克隆仁德路,但他们所重建的仁德路并不是真正的仁德路,这种重建工程寻觅的知识分子生存空间是没有根基的,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华丽生存空间,缺乏精神内涵。一个生存空间倘若是虚幻不牢固的存在,那空间中的价值秩序也容易失范,儒学研究院作为知识分子的生存家园,是知识分子们的精神寄托,然而仁德路错位,生存家园丢失,价值秩序失范,导致知识分子对群体身份产生质疑,陷入群体迷失。
(二)精神家园荒芜:自我精神危机
儒学院的建立过程中,在表象上是仁德路的错位,生存家园的丢失,然而在更深层次上,导致知识分子群体迷失的,是他们精神家园的荒芜。一方面,知识分子之间的情感关系扭曲而疏远,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世界也软弱荒芜。
在爱情上,应物兄的婚姻名存实亡,他与乔珊珊分居多年,他们各自生活,互不干涉。在亲情关系中,应物兄是缺席的。应物兄母亲早逝,他没有尽到孝道,甚至连母亲的坟在村里的哪头都不知道。而女儿远在美国,他极少有机会跟女儿见面,陪伴她成长,以至于难得在美国见到女儿,“看到她那一瞬间,他甚至有些不适应”[4]165。在友情中,应物兄是虚伪的,他明知打电话来电台捣乱的人是费鸣,却佯装不知,在朋友询问他问题时,他极少真诚的说出自己的讲解,常常把真话烂在肚子里,选择虚情假意。不止是应物兄,小说中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间的情感关系都扭曲而疏离:乔木与姗姗父女关系恶化,双林院士与双渐父子隔阂,乔木八十多岁高龄却与学生巫桃再婚,栾庭玉与金彧暧昧。“自我借助于他人而诞生,依赖于他人而存在。”[8]人类作为群居动物,需要在社会关系中寻找自我,在与他人的交往中确定自我,在他人的肯定中证明自我。同样,知识分子需要在社会交往中不断的调整自我,确定自我,重建自我身份认同。他者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的精神寄托,但疏离的情感关系使“应物兄们”无法得到情感寄托,从而无法正确认识自我的精神世界,导致精神危机。
回归到自身的精神世界,在市场经济的消费下,知识分子也难以保持自身精神的独立性,往往不自觉地陷入消费与欲望的洪流,被环境与他人左右。应物兄出书,书名无法由自己决定,被迫多次参加促销活动,在促销现场,他又言不由衷,在公共场合发言经常陷入夸张主义,口若悬河。在他与朗月有鱼水之欢时,他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陷入了糟糕的情绪,但当朗月再次来找他时,他又情不自禁陷入诱惑。筹备儒学研究院过程中,作为学术院长,他对儒学研究院的未来做了许多美好的规划,然而现实中各路人马都来分一杯羹,他却无力左右,只能任凭时态发展。应物兄自身精神家园的矛盾与复杂性,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映射,在他身上我们能看到当代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与体制环境中清醒的意识与软弱的实践能力之间的矛盾,面对现实的一次次妥协导致他们自身精神的虚伪、孱弱与无力。
知识分子个体在他人身上证明不了自己,回归到自身,知识分子仍是被他人和环境左右,生存家园的消失使价值秩序失范、群体迷失,然而更深层次的是,知识分子自身精神家园的没落,导致精神危机、自我迷失。
三、重建人文精神:知识分子的救赎
《应物兄》中展示的时代背景与我们的现实几乎是同步的,当代社会在商品经济的疯狂冲击下,体制内同样弥漫着浓重的商业气息,学术不再是纯粹的学者研究,而是变成与权、钱相结合的圈钱工具。适者生存,不适者痛苦,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知识分子都难以寻找出路,道德秩序失范,人文精神单薄,他们对外面临着社会环境的不适,对内面临着自身生存方式的困境,只有少部分“知识分子”能如鱼得水,适应其中。李洱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筹建儒学研究院这一横切面,让读者看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这种精神危机是新世纪下艾略特荒原意识的再现:传统价值观念崩溃,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人们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
李洱曾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导师死了》,吴义勤认为“导师死了”其实是“知识分子死了”,他指出:“《导师死了》实际上是李洱一类小说的一个总主题,并由此延伸了一个‘死了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9]。李洱擅长知识分子写作,《应物兄》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延续了李洱一贯的主题,以更长的篇幅更宏大的关系来展现现代知识分子群像:在当代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从社会的中心被挤向边缘化,成为了多元社会中的一元,社会已经不需要知识分子做他们的“导师”了,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舞台消失,立法者、阐释者、消解者都对自我的认知产生困惑和迷茫。
但知识分子是否真无出路了?一方面,《应物兄》中写了不著书立说的文德能,遗世独立的芸娘,专心科研的双林院士,装疯卖傻的张子房先生等等,他们不像程济世、葛宏道、应物兄那样,害怕被社会遗落,熙熙攘攘地挤进社会的洪流,著书立说,演讲宣传,而是构建起自身的精神传统,并孜孜不倦求知,低调而安静,以自身的言行展示知识分子的品格和担当,并影响身边人。李洱曾在采访中表示,这些知识分子是他的“心仪之人”,说明了李洱对知识分子的救赎抱有信心。
另一方面,李洱曾在采访中表示:“当然有出路,我对中国文化有信心,她有一种自我更新的机制在里边,不断吸收先进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换韵”,要找到准确的韵脚。”[10]在《应物兄》中,李洱也借程济世之口,表达了自己对知识分子救赎的希望——换韵重生,即在道德秩序失范、人文精神没落的当代社会中,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厚重的文化底蕴中去寻找出路,寻找精神家园。但重建文化的根,并不是完全地继承前人,而是在断裂之后进行创新重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韵”。如同《应物兄》中的消解者,作为年轻的一代,代表着中国的未来,他们在深陷虚无的同时,痛苦与孤独的压力是否也让他们有了创造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新的人文精神的可能性,从而拥有与立法者、阐释者完全不同的学术思想和境界。
李洱把阐释者应物兄设置为主要的叙述者,是有一定深意的,在消解者未能背负起人文精神的重建重担之前,当代社会的主力军仍是中坚一代的知识分子,而李洱本人也身列其中。小说中的应物兄在言行中常常陷入自我矛盾和挣扎,这种矛盾与挣扎,其他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也常有出现。鲁迅笔下的吕纬甫、魏连殳,老舍笔下的老李等等,但同样在外部环境和自我精神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比起吕纬甫的消沉、魏连殳的孤僻、老李的懦弱,李洱却给了应物兄一个“重生”的结局。小说的结尾应物兄遭遇车祸,在混沌中他听到有声音问“你是应物兄吗?”并有人清晰地回答“他是应物兄。”应物兄面对世俗问题时经常自我提问,但却极少得到自我回复,然而在最后,遭遇车祸后的应物兄再次提问质疑自我身份,却得到一个肯定的回复,小说的结尾是开放式结局,作者并没有说明应物兄最后是生是死,但李洱借车祸后的这一问一答,说明了应物兄在找到真正的程家大院后获得身份认同,在车祸“死亡”后获得了“重生”。应物兄在结局的一问一答中获得了自我肯定,这一肯定像是中坚带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欲望、矛盾和迷失之后的一丝清醒,李洱想通过这一丝的清醒告诉读者:唯有靠每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醒与自觉,身体力行地去实践,构建自我的精神传统,才能真正修复人文精神。
四、结语
加缪曾在《西西弗神话》中提出了一个古希腊神话,西西弗斯为了主宰自己的自由与意志,不惜反抗众神的命令,因而被罚将巨石推上山顶,西西弗斯每次用尽全力将石头推到山顶时,石头便会自动滚落,他得不断地周而复始地推石头。孤独和痛苦成了西西弗斯反抗众神的宿命和代价,但在孤独和痛苦中,他获得自我,主宰了自我的意志。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也是,《应物兄》中的知识分子难逃孤独的轮回宿命,但倘若他们能坚守自我,保持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真诚,忠于知识,忠于自己,便不会在商品经济的洪流中迷失。虽然痛苦而孤独,但孤独是知识分子的宿命,不应该去逃避。唯有主宰自己的自由和意志,知识分子的精神和使命担当便能在这孤独的斗争中延续,从而在新世纪中重建新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