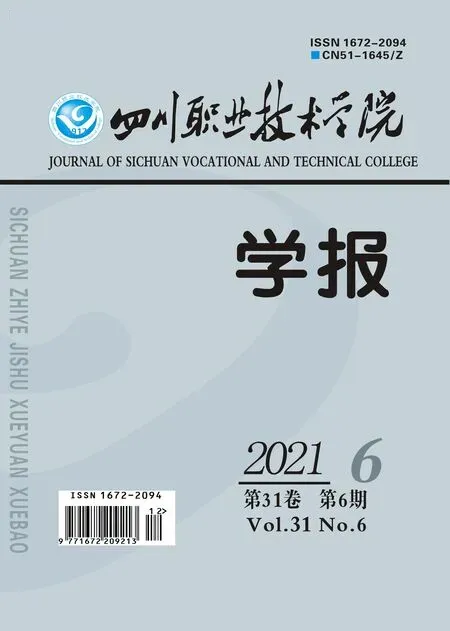互文视域下《陶庵梦忆》与《世说新语》关系探析
——兼论《陶庵梦忆》背后的喜与悲
2021-02-01王佳薇
王佳薇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从文体的源流来看,《世说新语》不仅是后世小说的源头,也是晚明小品文的参照,与《陶庵梦忆》存在一定的继承关系。因此,学界多从文学接受和文学影响的角度对两者的关系予以探究。文学接受指的是作品在流传过程中被读者关注并阐释的过程,重心在读者;文学影响强调作品对后世作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重心在作品。文学接受和文学影响将历时的作品联系起来,以明确作品和读者、前作和后作之间的交流结果为旨归。但是,若仅将文学作品以单一的线性形式予以观照,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片面性,互文性理论则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互文性理论的蕴意及在本文中的指涉
互文性理论是20 世纪60 年代兴起的理论,最早由克里斯蒂娃提出。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1]互文性将文本放至同一平面上,强调文本之间的渗透关系,将传统的线性关系铺陈为面。一个文本是无数文本交织的产物,将具体的文本之间的单向联系扩展为无数不确定文本交织的结果,是近年来新颖的研究视角。
互文性理论强调,任何文本都存在前文本的痕迹,文本的书写取材于已有的资源。一个文本可能存在无数文本的指涉,而它本身又会继续指向其它文本。《世说新语》取材于正史、传闻、笔记等多种形式,是文学与非文学的渗透,文学和史学的综合,每一则故事都存在先前材料的痕迹。因此,互文性存在于文本当中,是文本的本质属性。而《陶庵梦忆》夹杂了檄、序、骈文等其它文体的因子,引用了包括《论语》《左传》《世说新语》等在内的古事和技巧,难以言说哪些前作是张岱取材的源头。“文学大家族如同这样一棵枝繁叶茂的树,它的根茎并不单一,而是旁枝错节,纵横蔓延。因此无法画出清晰体现诸文本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图……”[2]1因此,以一个文本为中心,能够构建出庞大而没有尽头的网络,互文性的概念会变得十分广泛。
热奈特对互文性理论进行了进一步发展。他的《隐迹稿本》首次提出了“跨文性”概念,即“所有使一文本与其他文本产生明显或潜在关系的因素”[3],实则等同于广义的互文性概念。热奈特又将其划分为互文性、类文本、元文性、超文性、统文性,此时的互文性由文本的本质属性缩小为一种具体的手法。热奈特着重强调了互文性和超文性,将其定义为文本的共生和派生关系。狭义的互文性不再是无数文本的交织和延伸,而是表现为文本的某些内容在其他文本中的再次显现,要求读者必须将新旧文本放在同一平面进行参照。超文性强调新的文本是旧文本的衍生物,主要通过对旧文本的“转换”来实现自己的构建。
阿巴在海边捡到了一枚贝壳。他把贝壳放到了自己房间,就急急忙忙背着书包上学去了。突然,有个女孩挡在了他面前。
在张岱的笔下,山水和酒不再作为文化符号出现。张岱的笔触转向了富有烟火气息的都市生活。都市里有宴饮享乐的豪门富户,也有一技之长的底层百姓,因而张岱的书写对象由上层阶级扩大至都市中各类形形色色的人物,由魏晋名士的特立独行转向斗鸡、听戏、集会、观灯等市井活动,纸醉金迷的都市是张岱向往的故乡,也是晚明崇尚享乐主义的写照。茶取代了酒,成为《陶庵梦忆》最常见的饮品。晚明士人善品茶,待客访友、出入勾栏瓦肆均需要用茶,《兰雪茶》《闵老子茶》等篇目专门就茶的品种、工序、味道、品茶方式作了详细的解说,其中不乏有创新制茶方式的记载,构成了独特的茶文化,为我国茶史提供了有效的参考。由此,张岱重新书写了以都市和茶为代表的文化符号。在不同文化符号下,两书所传递的名士风度也大相径庭。如果说酒醇而酣畅淋漓,魏晋名士往往放荡不羁,以“任诞”为尚,在醉酒后以违背礼教的夸张行迹和与山水自然合一的理念凸显自我的价值;茶清而余味绵长,晚明士人多温吞儒雅,穿梭在都市的软红香土,以“痴”“癖”为美,在清醒中追求极致的世俗情欲。
二、《陶庵梦忆》对《世说新语》的暗示和抄袭
在热奈特看来,互文性手法可分为引用、暗示和抄袭。引用是文本对前文本语句的借用,作者多主动说明或以特殊符号标注,反之则会沦为抄袭。暗示则需要作者、读者的共同配合,此时的作者并未逐字摘用前文本的字句,也未明确标识,只留下不易察觉的痕迹,需要读者利用广博的阅读经验来识别,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用典”。《陶庵梦忆》对《世说新语》的互文多以用典的手法来体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二,借古人代言,增加文章论述的信服力。张岱的小品文看似随性而就,实则讲究精准立意,此类典故多置于文首借以立论,增强文章的可信性的同时方能继续下文的论说。《南镇祈梦》摘录了张岱少年时的檄文,檄文开头借用大量与“祈梦”主题相关的典故,有两则出自《世说新语》。“惟其无想无因,未尝梦乘车入鼠穴,捣齑啖铁杵”[4]66源自卫玠问梦一事,本意是没有人会想到进入鼠穴啃食铁杵,所以不会梦见类似的场景,意指日无所思,夜难成梦;“非其先知先觉,何以将得位梦棺器,得财梦秽矢,正在恍惚之交,俨若神明之赐”[4]66源自殷浩释梦一事,殷浩认为,官职是臭腐之物,钱财为粪土,故升官和发财时会梦到棺材和污秽。因此,檄文实则借卫玠和殷浩的古例说明,梦是对现实心态的影射和未来走向的暗示。作者完成对梦的诠释以后,方继续说明作文的意图,“神其诏我,或寝或吪;我得先知,何从何去”[4]66,即渴望得到神明赐梦,以对未来有所规划。又如《张氏声伎》的开篇借用王羲之、谢灵运的典故来说明音乐的魅力。“王右军曰:‘老年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4]119引用《言语》第62 则的故事,王羲之晚年喜爱音乐,以音乐陶冶情操,甚至担心会被儿孙破坏难得的闲静。“谢太傅不畜声伎,曰:‘畏解,故不畜。’”[4]119意指谢安担心领会音乐传递的深情之后会无法自持,故而不养声伎。虽然翻阅《识鉴》所记的“谢公在东山畜妓”[5]337一则可知,此典为张岱误用。但是,“谢安晚年,虽期功之惨,不废妓乐。盖藉以寄兴消愁……惟右军深解其意,故其言莫逆于心……本传言其誓墓之后,遍游名山,自言当以乐死。是其所好,不在声色”[5]103,说明张岱引用二典意在证明古人对声乐的痴迷以及音乐能够陶冶心智的功能,为下文自家乐班的出场奠定声势,虽有纰漏,仍不失为用典的范例。
第一,借古事内的相似情景来指代难以言说的情感,使得读者达到感同身受的效果。《彭天锡串戏》引用桓子野的逸事。桓子野在山林间听到清歌,必然会高呼“奈何”,展现了音乐触动心肠、情深而起却无可奈何的赤子心态。戏曲因其现场性而无法广泛流传,张岱颇为遗憾,遂以桓子野之情类比,表示见到彭天锡的表演之后,连“奈何”之类的叹息都难以发出,无奈之感远胜桓子野。《奔云石》“丙寅至武林,亭榭倾圮,堂中窀先生遗蜕,不胜人琴之感”[4]23一句引用王徽之的典故。王献之死后,王徽之调试死者的琴,却无法调好,于是掷琴于地,恸哭“人琴俱亡”,此典多用以抒发对逝者的怀念之情。昔日亭台已成废墟,黄贞父早已弃世,唯有奔云石尚在,张岱同王徽之一样睹物思人,不由悲从中来,简单的“人琴之感”四字,却能让读者品味到张岱对昔人的怀念以及物是人非的感伤之意。
方梦之(2005:43)认为,翻译不仅需要语言转换能力,还要大量捕捉概念隐喻,从源域与目标域来理解隐喻,提高翻译实践能力(李勇忠,李春华,2001)。想要把目标域中的信息准确地翻译出来,必须先理解源域,再推及目标域。Lakoff(1993:245)指出:“隐喻映射有些是普遍存在并具有普世性的,而有些则是特定文化所独有的。”所以要考虑共性和差异。
第三,“一个词有着自己的语义、用法和规范,当它被用在一篇文本里时,它不但携带了它自己的语义、用法和规范,同时又和文中其他的词和表述联系起来,共同转变了自己原有的语义、用法和规范”[2]4。因此,读者需要在前文本的参照下解读文本,也应联系文意,适当地转变语义。《二十四桥风月》曾提及族弟的戏语:“弟过钞关,美人数百人,目挑心招,视我如潘安,弟颐指气使,任意择拣,亦必得一当意者呼而侍我。”[4]112潘安仪表堂堂,颇受女性青睐,引来大量女子围观,本为风流才子的逸事,在这里则指伎女为了生存,只得取悦于男子的渴盼之意,谈笑之余饱含凄凉。《及时雨》也有类似的用典:“人马称娖而行,观者兜截遮拦,直欲看杀卫玠。”[4]194卫玠声名远扬,日常出行吸引了大量看客,卫玠不堪其扰,大病而死,故曰“看杀卫玠”。张岱用此典,意指看水浒戏的人如围观卫玠的人一般络绎不绝,观众看戏痴迷,与围观卫玠的人一般望眼欲穿,从侧面表现了平民百姓对水浒戏的喜爱。
在引用、抄袭、暗示三种手法中,暗示是采用最多的手法。抄袭虽是文学活动抵制的行为,但是,当前作的某些语句广为流传,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之后成为共识以后,作者下意识地将其纳入语言系统,并在书写新的文本时加以运用,所以不能把抄袭视为一种完全的贬义而对作者加以苛责,应当理性待之、加以辨析。例如,《朱楚生》“一往深情,摇飏无主”[4]154虽化用了“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一句,但张岱之前亦有汤显祖“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6]、陈继儒“非惟使人情开涤,可谓一往有深情”[7]等语句,可见“一往深情”之类的语词在当时广为流传,无法确定张岱具体受到了哪家的影响。所以,张岱的部分化用并非有意抄袭,而是无意的书写,有时甚至能以高超的语言功力将前文本的语词融入创作中,达到浑然天成之感。《阮圆海戏》“镞镞能新”[4]228化用《赏誉》第134 则“文学镞镞,无能不新”[5]406,形容阮圆海的戏不落俗套。《柳敬亭说书》“悠悠忽忽,土木形骸”[4]138化用了《容止》“刘伶身长流六尺,貌甚陋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5]508一句,形容柳敬亭和刘伶一样其貌不扬。两处化用均是四字为一句,运用叠字、双声、叠韵,读来朗朗上口,节奏感强烈,没有拼凑生硬的痕迹。
三、《陶庵梦忆》对《世说新语》的模仿和超越
米家电磁炉,模拟传统燃气灶调控方式,轻轻一转,精密调节火力,准确到位。也可通过扭转直接选择烹饪模式,OLED显示屏,简单又直观,还可以根据内置菜谱增加常用烹饪模式。
超文性可分为戏拟和仿作,两者均是在旧文本的基础上进行模仿,但戏拟有讽刺旧文本的意味,并不符合《陶庵梦忆》的性质,所以下文主要讨论仿作。
《陶庵梦忆》以“梦忆”为主题,梦忆的主体是张岱本人,梦忆的对象是与之相关的自然之景与社会生活。张岱将笔触更多地留给社会生活和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各色人物,因此《陶庵梦忆》同《世说新语》一样,以人物为表现对象,用白描的手法刻画人物形象。《世说新语》重视人物的外貌,分类中特设“容止”一类,对长相俊朗的人大加赞赏,对外表有缺陷的人加以揶揄,抓住外貌的突出特色,寥寥几笔就可形神毕肖,比如,形容刘伶“悠悠忽忽,土木形骸”,讽刺卫玠“若不堪罗绮”[5]509,宛如简笔画,将人物的特色展现在读者面前。张岱笔下的人物亦是如此,黄贞父“面黧黑,多髯须,毛颊”[4]23,柳敬亭“黧黑,满面疤,悠悠忽忽,土木形骸”,而范长白“似羊肚石雕一小猱,其鼻垩,颧颐犹残缺失次也”[4]127,张岱着重描写范长白鼻子、颧骨、脸颊的不协之态,将其比作白石雕刻的猴子,滑稽之感如在目前,分外生动形象。
广播影视主要是根据观众的需求以主动的方式给他们提供,自行选择收看节目的公共服务。在数字条件下,我们不但要提供公共服务,还要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因此,节目内容生产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需求和挑战,这就要求传播内容要适应社会发展,从封闭、分散、独立的传统服务模式向开放服务、个性化服务、信息聚合服务转变,按照社会化规律和市场的要求,进行结构调整、资源重组、合理分工、高效运行。
布鲁姆认为,伟大的前作容易给后来者施加压力,在压力的制衡下,后人试图以有意的“误读”来摆脱前作的影响。文本若不想沦为抄袭之作,必须以新颖的方式来超越前作。希利·斯米勒提出“寄生”与“寄主”的理论,将文本和后作的关系比喻为寄生物和寄主,后作需要在前作的文本空间内汲取营养,形成破坏,用以重构自身。读者阅读《陶庵梦忆》,会觉得存在《世说新语》的影子,是因为《世说新语》曾对《陶庵梦忆》施加影响,后者也曾在《世说新语》的文本空间内汲取养分。但读者始终无法将二者等同,这是由于张岱在书写同类人物形象和故事模式、创造相似的写作风格之时,有意“误读”前文本以避免趋同,在前文本的基础上完成新的阐释和超越,主要表现在对文化符号的重新设定上。
除了人物形象可以找到呼应的影子外,《陶庵梦忆》亦有多处故事情节脱胎于《世说新语》。《治沅堂》叙述了几则拆字的趣闻,其中一则提到,时人憎恶许志吉,在其“大卜于门”的匾额上篡改,改为“天下未闻”“阉手下犬”“太平拿问”,后来许志吉被押送至太平府,应验了“太平拿问”四字。《世说新语·政事》第4 则记载了贺邵之事:吴中豪门鄙视贺邵,在其门写上“会稽鸡,不能啼”的字样,贺邵故意补上“不可啼,杀吴儿”一句,尔后调查这些大族,上报朝廷,多人获罪[5]138。两事都是题字——添笔——应验的叙事模式,以字来预言未来的发展和走向,颇有传奇的色彩。其它诸如“保锡堂”拆作“呆人易金堂”、“治沅堂”取“三台”“三元”意,均套用了曹操题字表意的故事模式。《捷悟》载,曹操曾在门上题“活”字,暗示门建得过于宽阔,在杯盖上写“合”字,暗示在场之人每人品尝一口酪[5]480-481。这种以汉字的拆合委婉表意的故事模式,先设悬念,后揭开谜题,令读者恍然大悟,虽文笔平淡,却有妙趣横生之感。
《湖心亭看雪》是张岱的名篇,与《任诞》第47则颇有相似之处。一方面,两者均为“雪停、兴起、外出、探友却未见(偶遇却甚欢)、兴尽而回”的叙事模式,表现了王子猷和张岱随性而至的赤子之心和无拘无束的豪爽之气。另一方面,两者的叙事语言也如出一辙:多为三至七言,以动词的连缀引导故事的发展,简单几句便能交代来龙去脉、独立成篇。王子猷探戴安道一事同样用“居”“觉”“咏”“忆”“乘”“至”“返”架构 ,77 字就勾勒出随性而至的名士形象。《湖心亭看雪》用“拏”“拥”“看”“坐”“烧”“饮”“下”等动词贯穿全文,虽比前者多了景色、细节描写,增加了金陵客、船夫的角色,依然章法有度、言简意真、回味隽永。王子猷兴起探访戴安道,不见而返;张岱独自赏雪,却碰见同样雅兴的游人,娓娓道来之际别来一笔,故事发展的波折浓缩在短小的篇幅当中,体现了《世说新语》《陶庵梦忆》相近的叙事特色。
根据笔者之前的研究可知[15],基于AHP的喷墨打印纸表面性能权重为W0=(0.6415,0.1279,0.7428,0.1056,0.0961)T。
在楚国的神话中,有很多神话形象,无论是神化的祖先,还是反对自然的各种神灵和鬼魂。有些人被视为氏族的图腾。龚维英在他的著作《原始崇拜纲要》中指出:“在原始社会默默无闻的中期,原始民族以捕鱼和狩猎为生计手段,与动物有更密切的关系。他们崇拜动物如同他们的家族的图腾祖先。这种动物用来代表氏族,命名氏族并尊重它作为神,从而产生大量的图腾神话。在迁移和发展的过程中楚国与其他民族合并,他们接受了包容各方的民族文化,因此,楚神话中的图腾形式特别丰富,鸟,兽,昆,草,树都被当做图腾显示出来[1]。
关于大学生的隐喻认知状况,本文进行了调查分析,认为将隐喻用于探索大学生对于学习、人际交往、环境适应等各方面的看法,能更深入更含蓄地诱导出大学生潜意识中的认知概念。
同时,张岱笔下的人物颇具魏晋名士的风采。张岱与好友泛舟西湖,不拘世俗礼仪与女郎夜饮,颇有阮籍醉卧酒家女之侧的坦荡。朱云崃为人多疑,将女伶们的房间封闭,在夜间亲自巡视,与曹操假睡杀害近侍、以警告他人勿近的多疑心态相仿。张岱怒砸杨髡相并扔到溺溲处泄愤的举动,与袁耽怒扔骰子的真性情相近;王羲之、谢安蓄养伎班,组织文人雅集,张岱与友人同样好声乐、爱听戏,多次组织丝社与志同者相聚。张岱和闵汶水的交往过程更像是魏晋名士的相知相交的重现。张岱不远千里与闵汶水品茶,有庞统不远千里拜访司马徽的毅力。闵汶水起先避而不见,也有王恬无视谢万的做派。张岱等候良久,闵汶水不得不见,最终被张岱的品茶技艺打动,立刻引为知己,颇有“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5]564的影子。
纵观《世说新语》,山水和酒是魏晋名士寻求心灵慰藉的依赖物。名士在自然中放浪形骸,在幽静之地研修学问、感悟哲理、陶冶性情,山水草木寄托了名士的情致而人格化,所谓“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5]101。同时,魏晋名士皆是好酒之人,饮酒成为一种优长,甚至以醉酒为耀,王献之曾夸赞其兄“萧索寡会,遇酒则酣畅忘返,乃自可矜”[5]411。战乱的频繁、政局的跌宕和人生的飘忽无常使得文人倍感不安,以饮酒来规避世俗的烦恼。“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沈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讬于醉,可以粗远世故”[8]。因此,酒不仅是魏晋文人交游助兴的催化剂,更是逃避现实、排解痛苦的麻醉品。可以说,魏晋名士的放诞,是在醉酒状态下的宣泄,力在追求返璞归真的自然之旨,酒和山水是魏晋风流的一部分,已然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
所谓文化符号,就是具备文化含义的特殊标志。山水和酒在《陶庵梦忆》也十分常见。但张岱的笔下的山水,多以园林的形式展现,经过人工雕琢之后,成为了展示主人雅兴的背景,如张元汴的不二斋、张汝霖的砎园、天镜园等。酒则多为助兴之意,湖心亭赏雪,张岱与客痛饮三大白,龙山赏雪,张岱与友人喝酒驱寒。但是,时人并不以醉酒为耀,张岱的父亲和叔伯甚至“不能饮蠡壳”[4]225,更不必说在醉酒中寻求心灵的慰藉。所以,山水和酒是魏晋名士的文化符号,却并非是晚明士人的标配。
在作者的独特构思下,作品最终呈现的特色所带给读者别样的阅读感受可以视为写作风格。“在仿作的情况里,关键不是一篇特定的文本,而是一位作者特有的写作风格,故此主题并不重要。”[2]44张岱善于把握描绘对象的突出特点,不时戏谑调侃,主人公别具特色的外貌、荒诞率真的行为给散文增添了幽默色彩;而张岱写文,用语简洁明快,篇幅短小又不乏波折,构成了简净的文风,与《世说新语》如出一辙。
由于本文只选取《世说新语》作为《陶庵梦忆》的参照文本,故本文的互文性属于狭义的互文性概念。事实上,热奈特之后的互文性理论并不严格区分共生和派生的区别,而是将互文、超文笼统地归入表现文本间互文现象的两种手法。笔者姑且跟随大流,将互文、超文视为表现《世说新语》《陶庵梦忆》互文关系的手法,以此探究两者的联系。
“痴”形容对某件事倾投大量精力,在外人看来已成呆傻的状态,历来多为贬义。但是,痴的前提是情,没有情作为支撑,自然无法达到痴的境界,故而张岱将痴作为极高的褒扬,以示对真情的赞颂和向往。他笔下的人物多有痴心。金乳生体弱多病,却爱花成痴,一年四季都在整饬花草。朱楚生视戏如命,情深而死。范与兰珍爱盆景,以“小妾”称之,偶现枯枝,惊错之余用参汁浇灌。至于张岱自己,兴之所至,夜访雪景,漫游西湖,表现了对佳景的痴迷。痴的对象多是大众可接受的活动,听戏、养花、赏雪、游览都是普遍的社会活动,而“癖”则是个人独特的习惯,如柳敬亭说书时,需要半夜擦桌子剔灯芯,要求听众保持高度集中的精神。有时,像祁止山抛妻弃子、独宠娈童,燕客朝令夕改、挥金如土之流,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不健康的行径,隐含低俗之意。张岱曾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4]123张岱将癖和疵并列,心知癖不能为大众所提倡,但字里行间依然表达了对癖的欣赏,是因为癖和痴所代表的无视世俗、特立独行的举动,实则是真情至性的投射,这与魏晋名士的“任诞”心理是相似的。但是,魏晋名士是在经历世俗的痛苦后以醉酒麻痹自我,以标新立异的方式违背世俗礼教,隐隐有对时代和人生的无可奈何之感。而痴、癖的提倡都是为了满足自我的需求,宣扬的是世俗欲望,是晚明世人在清醒的状态下对声色、享乐的极致追求。
从引用典故、化用语句,再到人物形象的呼应、情节的相似和叙事方式的趋同,《陶庵梦忆》形成了和《世说新语》一样以人物为中心、表现逸致为目的、颂扬真情为旨归的简净幽默的文风。但是,《陶庵梦忆》努力发掘前文本忽略的地方,将描摹重心由山水转向了都市,由幽静转向繁华,由隐逸转向烟火,由贵族名士转向底层技艺者,重新书写了以都市和茶为代表的文化符号,宣扬了与魏晋风流有所差异的晚明风度,可以视为对《世说新语》的一种“误读”。《陶庵梦忆》成为了崭新、独立的文本,而非作为《世说新语》的余韵而存在。
四、从写作主体和读者纬度窥探《陶庵梦忆》背后的情感
文本空间存在写作主体、读者、外部文本三个维度,《陶庵梦忆》对《世说新语》的引用、化用、模仿属于文本自身与外部文本关系的探究。下文将从写作主体和读者的关系来观照《陶庵梦忆》背后的情意。
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克里斯蒂娃曾将文本的产生看作是原始欲望与理性思维制约的产物。异质性在文本层面的投射,可以划分为生成文本与现象文本。从字面义考察文本,属于经过理性支配、浮于文字表层的现象文本。而生成文本是“构成表述主体的逻辑运作的基础,是构成现象文本的场所,是意义发生的场所”[9],属于受感性支配、隐藏在文字之外的文本。从现象文本层面观照《陶庵梦忆》,不外乎是张岱对故国繁华生活的种种回忆,又据序文“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4]1等诸语来看,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封建地主大少爷的忏悔录”[10]。但是,仔细阅读文本之后,却又并非如此。张岱与闵汶水交往时,先后猜出茶名、制茶方式、用水,使得闵汶水两次吐舌称奇,最后以“予年七十,精赏鉴者,无客比”[4]79评价张岱,引为至交。张岱能分辨各种地方的井水,自豪地表示“昔人水辨淄、渑,侈为异事。诸水到口,实实易辨,何待易牙”[4]70。张岱用松萝茶的烘焙方式制作日铸茶,创造了风靡一时的“兰雪茶”,其得意之情恰似目前。从这些记叙,读者无法读出张岱的忏悔,反而有因优长受到肯定而自豪的意味,造成了现象文本与生成文本之间的矛盾。
为了对传统理论中强调作者与作品派生关系的论调进行反拨,罗兰·巴特提出了“作者之死”,将现实的作者和文本中的叙述者区分开,读者分析的对象是文本中呈现的叙述者,而非现实生活中的作者。按巴特的理论,张岱在完成《陶庵梦忆》书写的那一刻就已经退出文本。读者所能解读的张岱,实则是张岱寄寓在文本中的人物形象,需要参照《陶庵梦忆》文本自身来解读,而并非由现实中的张岱来左右读者的理解。《二十四风月桥》文末,听到族弟自比潘安的戏谑,张岱也随之大噱。与族弟得意的大笑不同,张岱的“噱”存在分属两个主体的双重声音,一为身为作者的张岱,二为存在于文本中、被族弟生动的比喻逗笑的张岱。身为作者的张岱在写作文本时,绝非只为回忆和族弟流连烟花之地的过往。由于书写文本的时间与往事存在一定的跨度,过往的繁华与现实的凄凉形成落差,张岱的心态已然发生变化,故而在回忆年少往事的同时,大幅度地描绘妓女的悲惨生活,抒发对妓女群体的同情。“噱”代表了文中张岱的得意之笑,也是作者在现实中的苦笑。因此,《陶庵梦忆》中的自得之气,源于张岱寄寓在文中的形象所表露出的精神面貌,却并非作者此时的心态。晚年的张岱曾自嘲:“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11]一句“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写出了人生如梦的虚幻本质,此时的张岱国破家亡、隐居山林、贫困交加,“梦忆”“梦回”是一种对往事追念的怀旧心理,流露出对年少时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的怀念。之所以提到忏悔,是因为“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4]1。张岱认为,今日的贫困交加是因为少年时的奢靡,以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进行自我安慰,实则依然是对惨淡现状的心酸。“国破家亡,二十年后,追忆昔日的繁华,这个繁华,包括家园、都市以及个人生活,有的只是感叹与惋惜,而看不出什么刻骨铭心的自责或反省”[12],现实的悲凉愈发促进张岱对过去的追忆,以至于文中的得意之气愈浓,现实作者的凄凉之感也越重。因此,我们读《陶庵梦忆》很难体会到张岱的忏悔心理,却能品味到一种自得、夸耀之气,尔后又伴随着无尽的凄凉。
当然,我们在进行上述论述时不可避免地联系到张岱的生平与经历,说明读者无法彻底摆脱现实作者的影响,巴特的理论容易造成作者和文本的脱节。如果不参照作者的经历,探究作者的心路历程,可能无法体会到作者埋伏在文本中的暗示,会造成与作者本意截然不同的解读。但是,“作者之死”的意义在于,要求作者在完成创作后将阐释权移交给读者,直接促成读者在文学活动的主导权,读者在阐释文本的过程中生发的新的意义依然属于文本。不同读者会阐释不同的意义,我们不能肯定孰是孰非,只能将其都归入文本的一部分。而文本就在这样的阅读活动中不断得到阐发,持续焕发新的光彩。所以,文本的生产过程是永无止境的,直到今日,我们依然在参与各种文本的生产活动。
五、结语
互文性确立了一个广泛的文本观念。但是,互文性毕竟是近四十年才新兴的西方理论,与我国古典文学的结合虽有新颖之处,却也不能一味照搬,要根据我国古典文学的特点有所选择。现下,《陶庵梦忆》的主要研究方向多与文化挂钩,考察明代的戏剧、美术、茶艺、饮食、地理都能从这里找到资料。互文性不仅存在于文学层面,也能跨越学科的桎梏,将艺术、民俗、历史以至于整个人类的认知联系在一起,构成一种“大文本”观念。这启示我们,在强调“文学本位”论的同时,我们也应广泛博猎,参考其他学科的精髓和视角,以实现本专业的持续更新与不断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