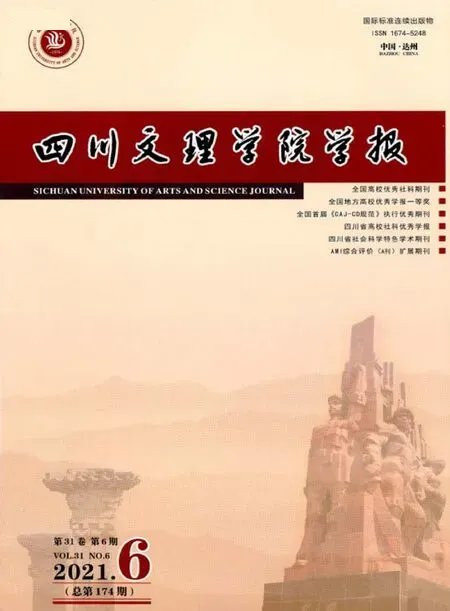《语法修辞讲话》的术语辩证法
2021-01-31张春泉
张春泉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北碚 400715)
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是语言学著作中名家写的发行量最大的著作之一,该著可谓顶天立地,既是著名语言学家写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又具有极强的可及性,即在普通人群一般读者中具有很强的可接受度、很大的影响。“一时许多地方都选作教材,成为50年代初最畅销的热门语法书。”[1]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该著术语辩证法的成功运用。在我们看来,《语法修辞讲话》的术语辩证法值得关注。
事实上,“辩证法”也是一个可及性很强的术语。据方朝晖《“辩证法”一词考》:“‘对立的统一’等等,是现代意义上的‘辩证法’,准确点说,是从黑格尔等人以来逐渐形成的辩证法概念。”[2]显然,我们这里所说的“辩证法”自身也是一个术语,术语辩证法注重对立的统一,比如创新和利旧,等等。《语法修辞讲话》的术语辩证法是吕叔湘、朱德熙术语思想和实践的某种总体体现,表现在术语的生成、辨析、运用等诸方面。
一、术语的生成:“创新”与“利旧”
术语生成后即为新术语,《语法修辞讲话》主张新术语在数量上要适度,不可盲目“创新”,要将“创新”和“利旧”统一起来。
《语法修辞讲话》指出,“现在,堆砌的是所谓‘新名词’。新鲜事物应该用新鲜词语来表达,没有理由反对用‘新名词’。”[3]199这里所说的“新名词”主要是指新术语,《语法修辞讲话》并不反对新术语的创立。“可是如果为‘新名词’而‘新名词’,不管用得上用不上,不负责任地往上砌,那就非反对不可了。”[3]199显然,不是全盘否定新术语,而是适当适度而为之,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作者还进一步指出,“所以要反对,不但因为它会使作者真正的意思隐晦不显(参看第二段‘故作高深’节),也不但因为它空泛罗嗦,浪费读者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因为它除了发生这些直接的影响外,还给我们的语言以重大的损害,因为这些很有用的新词语,由于用的太滥,也必然会失去原有的准确性,变得毫无内容。”[3]199-200简言之,不能以辞害意,毕竟内容决定形式。
不仅对于术语自身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语法修辞讲话》关于语法的某些涉及术语的核心问题的处理也是实事求是的。譬如该著明确表示汉语的词应该怎样分类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只提出在这个讲话里所用的词类的名称,以及大概的内容。”[3]8-9不难理解“词类的名称”也涉及术语问题。
不盲目追求术语的创新,《语法修辞讲话》同时积极新“开发”利用“现成的名词”,这种情形在《语法修辞讲话》之前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和其后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等论著中是基本一致的。例如,《中国文法要略》指出,关于”文法“和”语法“的术语使用,“没有一个双方通用的名称也不方便。”[4]“没有一个双方通用的名称也不方便”表明术语的使用是必要的,有意义的,《中国文法要略》中“现成的名词”说的是“利旧”,即对旧有的术语的再利用。
关于术语的创新和利旧,《语法修辞讲话》的作者之一的吕叔湘先生还有更为辩证的意见:“本文所用的术语,绝大多数都是现在通行的或者曾经有人用过的。关于术语,创新和利旧各有利弊。……本文不是为了提出一个新的语法体系,所以还是尽量利用旧的术语。”[5]只是使用旧有的术语有一个局限,因为会或多或少改变原来的意义,这样可能会给接受者造成一定的理解上的困难,或由此可能导致某种混淆。显然,以上看法富于真知灼见,辩证公允,体现了作者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二、术语的辨析:“是”与“不是”
《语法修辞讲话》较为注重对相关相近术语的辨析,辨析十分精准。例如作者关于“语法”和“文法”的讨论,作者先替读者考虑其接受情况,然后给出结论,二者“是一个东西。”[3]3“一个东西”是相对于作者分析该相应术语时提及的“两个东西”而言的,这里所说的“两个东西”和“一个东西”,或可曰是辩证统一的。作者进一步分析后得出结论:“与其管它叫‘文法’,就不如管它叫‘语法’了。”[3]3“语法”和“文法”这两个术语的分分合合,既有对立又有统一,“是”与“不是”在此意义上有其统一之时,统一于人们的相关认知域。
《语法修辞讲话》在辨析术语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常常专门指出某某术语“不是”什么。例如作者对全书的核心术语“语法”的界定即为显例。作者明确指出,“第一,语法不是文字学,……第二,语法不是修辞学,……第三,语法不是逻辑,虽然实际上离不开逻辑。”[3]4上例关于语法不是文字学、修辞学、逻辑的辨析十分精彩,廓清了相邻相近领域的相关术语的“界限”。此外,作者在后文还对“语法不是逻辑”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语法不是逻辑。’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就是我们在那一段里说明的,尽管一个句子的结构是正确的,要是事理上讲不过去,这句话还是不通。……‘语法不是逻辑’的第二层意思是:有些话虽然用严格的逻辑眼光来分析有点说不过去,但是大家都这样说,都懂得它的意思,听的人和说的人中间毫无隔阂,毫无误会,站在语法的立场,就不能不承认它是正确的。”[3]179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补充说明了“逻辑”的内涵。“是指一般人心目中的‘道理’。”[3]179我们知道,“逻辑”的内涵和外延比较复杂,也是一般人觉得比较高深的学问,而作者没有“掉书袋”,在此关于“逻辑”的这一说述十分接地气,非常便于理解,这样,关于语法和逻辑的关系的述说,作者自然辨析得十分符合逻辑、符合辩证法:“这两层意思放在一起看,似乎是冲突的。……实际上这两层意思并不冲突。”[3]180之所以如此,实际使用的语用修辞实践可以证明。
《语法修辞讲话》关于“句子”“词”“短语”等基本术语的辨析也很辩证公允。作者科学地指出了“周密”和“有用”的辩证关系。周密和实用得协调统一起来。在界定“词”时,作者指出,“词”和“字”得有效区分开来。再者,“短语”和“句子”需要区分,而区分的标准不可仅仅着眼于能指形式的长短,短语未必就比句子短,短语不短,辩证全面。类似地,《语法修辞讲话》关于“简单句”与“复合句”的辨析,也是辩证的,作者正确地、全面地指出,简单句未必短,复合句未必就长,复合句在能指形式上也未必比简单句长,简单句在能指形式上未必比复合句短。
除了语法单位这些基本术语的辨析,《语法修辞讲话》关于词类名称(术语)的辨析也很辩证,例如作者指出,“大多数副动词有些语法书里称为‘介词’,我们认为这两类词的界限很不容易划清,不如还是把它们归在动词这个大类的底下。”[3]9当然,这里需要明确的是,《语法修辞讲话》作者关于“副动词”和“介词”的辨析,也是作者语法观的某种呈现,质言之,这些术语是理解作者语法观及相应语法体系的关键词之一,所以也是我们研读《语法修辞讲话》的重点之一。如果说关于“副动词”和“介词”的辨析是“点”,作者关于词类“不能一概而论”的说法则是某种“面”,作者指出,“总之,不能一概而论。倘若一个词在句子里的地位一变,所属的类也就跟着一变,那么几乎所有的词都要属于两类或三类,多的要跨上四五类……”[3]11以上观点在视域上点面结合,看法客观辩证,即“不能一概而论”。
术语辨析是为了更恰当使用术语,更精准理解术语的意义,而不是纯粹名称问题的纠缠。这一点吕叔湘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里讲得很清楚:“摆问题自然摆的是实质性问题,纯粹名称问题不去纠缠……”[3]8-9作者以“量词”“单位词”“单位名词”及“短语”“词组”“结构”等术语为例,做了精彩的全面的、深入的、科学的辨析。作者关于以上重要术语的辨析全面、允当、精准,大大方便了读者的学术阅读,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语法学的普及传播和发展。
三、术语的运用:必须与不必
或者可以说术语的生成是微观视角,术语的辨析是中观视角,术语的运用则是一定意义上的宏观视角。《语法修辞讲话》关于术语的使用似乎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非必须不使用。
《语法修辞讲话》指出,“要讲语法,就离不开一些术语,术语是一般人最讨厌的,可是事实上少它不了。……要是一个术语也不用,有许多事情要说的很罗嗦,有许多事情简直说不明白。”[3]2这就是说,“少它不了”的术语在包括语法学在内的各学科领域广泛使用。只是在使用时需慎重,以免“一般人”“讨厌”。作者旁征博引,但没有堆砌术语,而是用很接地气的日常用语“讨厌”“生毛病”“罗嗦”等深入浅出地说明术语使用的原则。由此也可看出作者使用学术语言的高超和文风的扎实。
在使用术语时,需慎重,尽量“不立异”。“不立异”的一个表现即不轻易修改、改动。《语法修辞讲话》指出,“第一讲里的语法概要有不少地方跟现在通行的体系不一致,为了避免牵动第二讲以后的用语,没有修改。”[3]2这里所说的“用语”实际是指术语。类似地,在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里,吕叔湘先生说道;“这本书讲的是汉语语法,却以‘中国文法’命名,这也是当时通例,现在也不去更改,免得误会是另外一本书。”[4]12同时也不急于从众,《语法修辞讲话》有言,“里面用的术语以及它们的意义也许跟他原来所了解的有点不同。并不是我们故意要立异……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头有所取舍。”[3]3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要请求读者耐烦点,把这数目并不很多的术语记住,并且把它们的意思弄清楚。”[3]3毕竟,在读者那里,这些术语或许有些生疏,但潜心读下去未必难懂。
稳健使用术语,但又不泥于术语,这似乎也是一种辩证的方法,也是术语使用者严谨的治学态度的表现。这在吕叔湘和朱德熙两位先生的其他代表性论著中时有体现。例如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修订本序中曾提及汉语的语法结构时的说述即表明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需特别说明的是,这里作者有一个注:“因此,在我写《语法学习》以及和朱德熙同志合写《语法修辞讲话》的时候,在许多还没有定论的场合,宁可迁就点通行的说法。要说是彼愈于此,那倒也不一定。因为有些读者来信问我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改变,在这里说明一下。”[4]9此处“通行的说法”直接涉及术语(通行的术语)。显然,之所以“宁可迁就”是为读者计,是考虑到读者的接受情况,也必将有利于读者的接受,事实上也提高了包括术语在内的学术话语的可接受度。
朱德熙《从作文和说话的关系谈到学习语法》说得更显豁:“不论哪一门科学,都有一套专门术语。但术语只是科学分析的工具,并不就是科学本身。……离开了规律,术语本身就没有多大意义了。”[6]305-306使用术语不是目的,术语是为表征科学规律服务的,使用术语还要讲究效果,不可舍本逐末或本末倒置。朱德熙《从作文和说话的关系谈到学习语法》还指出,“仅仅抱住一些干巴巴的术语和条文不放,那是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的。”[6]307上述话语是《从作文和说话的关系谈到学习语法》一文的结尾,由此亦可见这一论断的特殊意义。
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是语言学名著,值得我们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研究。我们此前从《语法修辞讲话》讨论过语法、修辞和逻辑的关系,[7]如果说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可以有一定的交集,则术语可看作这个交集里的一个要素。以上分析表明,《语法修辞讲话》虽然未及专门(专章专节)讲述术语问题,但是其关于术语的点评式的看法,可给学界以重要启示。公允地看待术语、全面地处理术语、恰当地使用术语、有效地传播术语、科学地理解术语即术语辩证法的重要内涵。运用此法,可辩证生成、辨析和使用术语。术语的创新和利旧、术语辨析的“是”和“不是”、术语使用的“必须”和“不必”都统一于术语的有效理解和接受。术语是学术话语的基本单元,是沟通作者和读者的重要工具。如吕叔湘先生所言,“语法书可以有两种写法:或者从听和读的人的角度出发,……或者从说和写的人的角度出发……这两种写法各有短长,相辅相成,很难说哪一种写法准比另一种写法好。”[4]5显然,吕叔湘先生的这一观点也是辩证的,无论哪一种写法,都需要使用术语,都需要有可接受性,术语的辩证使用都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