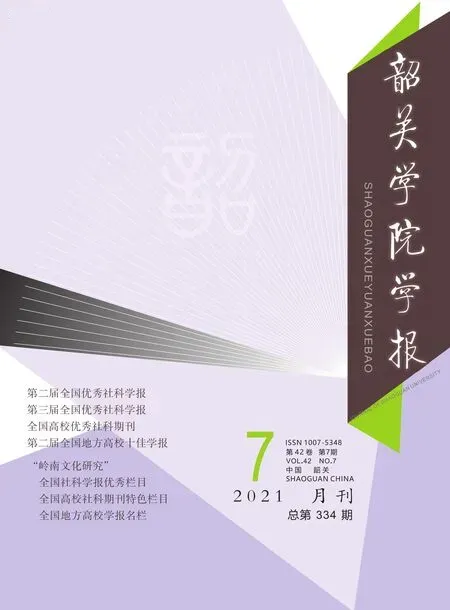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改革方向
2021-01-31汪梦龙
汪梦龙
(阜阳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2020年12月26日,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在争议中迎来了修改,刑法修正案(十一)有条件地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降低为12周岁。这一修改普遍被视为是对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恶性暴力案件频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回应。自刑法修正案(十一)公布以来,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聚讼焦点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否要下调转为新制度施行后的未来改革方向。主要观点有弹性论、维持论和上调论。
一、弹性论观点及主要理由
弹性论认为,我国刑事责任年龄不应在现有体制下继续下调,应该借鉴类似英美法系“恶意补足年龄”原则的弹性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以弹性制度配合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再次下调[1]。
理由如下:
(一)修改后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仍未改正刑事责任年龄“一刀切”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失和
刑法第5条明确规定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即刑罚的轻重与社会的危害性程度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而刑事责任能力指的是行为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这两种能力和年龄不是正比关系,只是不严格的正相关关系。这种正相关的不严格性,其程度之高,以至于我们不应当在衡量刑事责任能力的时候简单地对这种偏差予以忽视,因此单独以年龄这个因素替代刑事责任能力来决定免除行为人的罪刑是有失公允的[2]。不同地区、不同个体的青少年辨认和控制能力的发展程度差异很大,这个因素也不能被忽略,在现有体制下继续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并没有改正“一刀切”的错误,没有尊重不同个体的发展状况,反而带来了重刑主义倾向的危险。而破除现有的“一刀切”体制,以弹性配合刑事责任年龄的再次下调,既可以实现个案平衡,又可以有效降低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带来的重刑主义风险。
(二)应当重视社会年龄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影响
具体到确定刑事责任的年龄段划分问题上,人的社会年龄比人的自然年龄更加具有参考价值。社会成熟年龄趋于低龄化,信息获取途径日益发达,知识日益丰富,未成年人能够认识和控制自己行为的时机越来越早,青少年犯罪低龄化就是证据。弹性化可以在坚持罪刑法定的前提下,更好地兼顾行为人的社会年龄。
(三)更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要求
无视未成年人的社会年龄,而简单地以自然年龄作为衡量刑事责任年龄的标准,对其作出主观恶性小的推断,进一步认为他们作为犯罪主体不适格,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体现了单纯主观出罪的倾向。“衡量犯罪的标准就是它的社会危害”[3],虽然贝卡利亚此言有单纯客观归罪之嫌,但足以说明客观危害在判断刑事责任的过程中的关键性。只有尊重主客观相一致的要求,重视未成年人犯罪对社会的严重危害,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公正。
二、维持论观点及主要理由
维持论是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这一部分学者认为,修改后的刑事责任年龄不需要改变。
理由如下:
(一)修改后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已经较好地实现了预防惩治犯罪和保护未成年人的统一
刑法修正案(十一)并不是直接下调了刑事责任年龄,首先,只有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且情节恶劣的情形下,才能对12至14周岁的未成年人追诉。其次,追诉权必须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方得行使,这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对刑事责任年龄的降低附加了强大的限制,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滥诉的风险。另外,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对12到14周岁未成年人的教育和威慑作用是已经具备的,“达摩克斯利之剑”已经祭起[4]。
(二)12岁是较为合理的刑事责任起点年龄,事实上已经体现了“恶意补足年龄”原则
就我国目前的义务教育水平而言,12岁未成年人有能力对严重社会危害性行为进行辨认,也基本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为,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周岁具有合理性。而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的“情节恶劣”的实体要求和“最高检核准”的程序要求,事实上已经明确了由最高检对行为人的“恶意”进行判断的要求,已经可以看作是“恶意补足年龄”原则同我国实际的结合[5]。
(三)刑法应该有足够的稳定性
维持论者认为,14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转型期内一时的社会现象,为了回应这种现象引起的社会关切,我们对已经拟制并且成熟运用的法律进行了触及原则性的修改,可以说已经是现阶段综合各方面因素的“最不坏的方案”[6],不宜再轻易上调或者下调刑事责任年龄。法律应当以稳定为原则,以修改为例外,特别是刑法,作为社会规范的最终底线,其修改应当要坚持谦抑性原则,能用其他手段的,轻易不应动用刑法。单纯追求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继续降低,不但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青少年犯罪的问题,还会引发人们对罪刑法定原则受到挑战的担忧。
三、上调论观点及主要理由
持有上调论观点的学者比较少,其主要理论依据是刑法谦抑性原则和国际国内的轻刑化刑法改革趋势。还有学者认为,在轻刑化的大背景下,此次刑事责任年龄的下调本身就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权宜之计,终究是应该回调的。这一观点支持者甚少,主要是因为理论根基过于薄弱,仅以刑法谦抑性原则和轻刑化趋势作为理由,缺乏更为具体切实的理论构建,且有朝令夕改之嫌,终究难以服众。
四、对弹性论和维持论的辩证
弹性论和维持论各有各的道理,笔者认为,现行规则远非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改革的完全体,更像是一个过渡的阶段。然而领先时代一步的是天才,领先时代十步的是疯子。维持论者之所以能够占据主流,并不是因为大部分学者看不到现行制度仍有不足,而是因为法律终究是经世致用之学,只有放在社会的土壤之上才会有生命力,以我国当前的司法力量,如果强行适用“恶意补足年龄”原则,难免陷入重刑主义。两害相权,宁肯背负抱残守缺的嫌疑,也不可再轻易改动。但这种审慎的态度是符合法治要求的,应当被赞扬的。
笔者整体上赞同弹性论,现行制度在一定时期内称得上较为完善,但是这不应限制我们对未来的设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另一方面,我们要正确看待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它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在要求。事实上,“恶意”属于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主观方面,而现实中每个案件的判决都需要法官依据客观方面的外在表现来对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进行高度盖然性推断,刑法分则中也有许多罪名附加有“情节恶劣”的条件,因此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的“恶意”进行判断一直有迹可循,从根本上来说这并非是对现有体系的突破。当然,真正要实现“弹性论”,仍然需要结合司法体制改革、社会矫治、亲权管教法制化、学校和社会的人格品德教育等问题的解决,从社会综合治理的视角,以科学和耐心逐步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