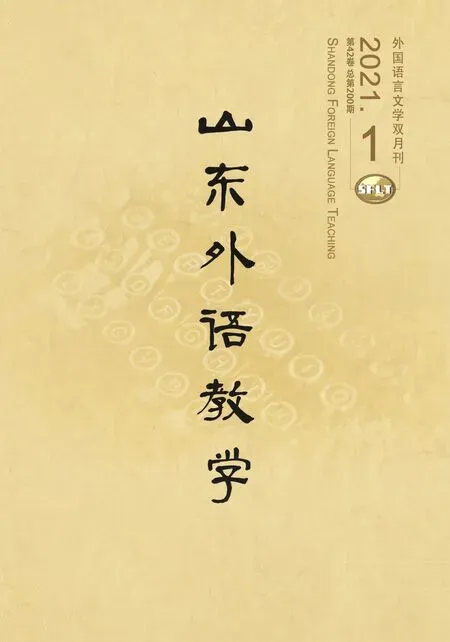论《强盗新郎》中的国家空间生产
2021-01-30刘智欢
刘智欢
(福建农林大学 国际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1.0 引言
在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1909-2001)的第一本小说《强盗新郎》(TheRobberBridegroom,1942)中,她将目光投向18世纪末位于美国西南边疆的纳奇兹(Natchez),别出心裁地将格林童话、希腊神话、圣经故事、南方民间传说以及真实历史人物等杂糅在一起,讲述了白人种植园主、剪径大盗以及印第安原住民之间的纠葛、冲突和对抗。不少评论家认为,韦尔蒂在这本小说中“模糊了历史事实和虚构小说的界线”(Wilson,1993:64),表达了对美国民族神话的质疑,“嘲讽国家对自由主体性(free agency)的应许以及驱动西部扩张的资本主义欲望”(Trefzer,2007:24)。这些论述揭示出《强盗新郎》对国家历史的批判式重写,却往往忽略了小说创作的时代语境。虽然《强盗新郎》写于1940年,但其创作灵感来源于1936年韦尔蒂在新政机构工程进度管理局(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的工作经历。在此期间,她曾前往纳奇兹采风,翻阅了许多与之相关的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创作出这部作品。在经济大萧条席卷美国、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肆虐的历史背景下,韦尔蒂为何转而书写美国南方早期的拓殖历史?她的民族神话“反叙事”隐含着怎样的现实关切?本文从空间生产的视角出发,结合文本创作时期的历史语境,解读《强盗新郎》中纳奇兹从荒野到城市的发展历程,探究韦尔蒂对美国疆域变迁及其内蕴的政治张力的独特书写。
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认为“(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1991:26)。社会空间在人类社会实践和生产过程中形成,反过来又影响、指导甚至重组生产实践和社会关系。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空间(the space of the nation-state)的生产取决于具有“层级结构”的全国市场和“控制及利用市场资源或生产力的增长以维持和加强统治的政治力量”(Lefebvre,1991:112)。也就是说,国家空间是由统一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权力主宰的抽象空间。美国独特的大陆扩张史,加之资本主义在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属性意味着美国的国家空间生产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漫长过程。国家空间的生产与民族身份的形塑密不可分。如果说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安德森,2016:6),那么正是在生产方式和权力结构以商业活动、地图测绘、社会制度、法律政令以及文化观念等形式将特定的领土疆域不断组织整合为同质化空间的过程中,共同的民族意识和身份认同才得以确立。在《强盗新郎》中,韦尔蒂以文学想象还原了美国早期领域性空间的生产过程,消解了国家叙事中“南方/美国”的二元对立,揭示出南方实际上是美国的一面镜子,折射出美国扩张主义领土实践中的种族冲突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排外性民族身份认同。
2.0 种植园南方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
在美国的国家建构工程中,南方一直扮演着“内部他者”(internal other)的角色(Greeson,2010:1)。早在殖民地时期,南方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种植园农业经济就使之走上了不同于新英格兰的发展道路。从18世纪开始,奴隶制、种族主义、贫穷、暴力、偏狭以及仇外等成为南方地域文化的标签,将这一地区与标榜自由、民主、平等、富裕的美国区分开来。用詹妮弗·格雷森(Jennifer Greeson)的话来说,南方“将国家理念和国家现实之间的差距空间化”,“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美国生活中的道德缺陷描绘成地理问题”(Greeson,2010:4)。到了20世纪30年代,南方的贫困落后、种族隔离以及政治保守主义日益被视为对国家理念和价值体系的威胁。罗斯福总统在1938年的国情咨文中称南方为“全国第一号经济问题”(Duck,2006:74)。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注意到南方白人至上的社会政治秩序与法西斯政权特别是纳粹德国的相似之处。对美国其他地区而言,除去内战前的几年,南方从未显得如此“格格不入、极具威胁以及充满危险”(Brinkmeyer, 2009: 4)。主流叙事将南方描述为“具有显著文化他异性(alterity)的场所”,一方面以“落后的南方”意象反衬出美国的民主传统,另一方面则继续“将种族等级制度编码为地域特征”进而不加干涉(Duck,2006:14)。韦尔蒂的空间书写破除了国家叙事中南方作为“内部他者”的迷思,探究了种植园南方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复杂关联,呈现出南方“地理空间的政治属性”(Jarvis,1998:52)。
在《强盗新郎》中,18世纪末的纳奇兹正处于从混乱无序的异质性荒凉边疆转变成为同质性美国领土空间的过程之中,具有明显的阈限性①。虽然纳奇兹即将被纳入美国版图,但“国家政府的规章制度、民族文化、法律政令等并不能随即自动弥漫至国家新增领土,边疆空间的‘领域性’(territoriality)需要通过多维度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实践得以确立”(郭巍,2017:84)。当早期的拓荒者来到此地开疆辟土时,他们就将新的经济政治结构引入旧有的地理空间,促进了边疆的“领域化”(territorialization)。小说中种植园主克莱门特的发家史即是一部微观的国家空间生产史。他拖家带口从弗吉尼亚长途跋涉、一路南下来到纳奇兹,却不幸成为印第安人的俘虏。劫后余生的克莱门特携女儿罗莎蒙德与同样家破人亡的莎洛姆重新组建家庭,造屋葺舍,将荒蛮之地改造为宜居之所。他们一开始在森林中搭建小木屋聊以安身,但很快就“新增了精美的卧室,墙上挂着一面镜子,卧室后面有独立的储藏室,房子后面是带有大炉子的厨房,厨房后面是小猪圈,里面有一头新买的小猪。它后面的树上栓着一头新买的牛”(Welty,1998:14)。然而,筚路蓝缕开拓荒野的并非克莱门特一家,而是他们购买的黑人奴隶。罗莎蒙德在抱怨继母莎洛姆的刁难时,透露出家里的奴隶承担了主要的劳作,“奴隶天天都挤牛奶,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做”(Welty,1998:31)。可见,作为早期的拓荒者,克莱门特带到边疆的除了积累土地和财富的欲望,还有基于奴隶制的生产模式。
克莱门特在纳奇兹发展奴隶制种植园,离不开新兴的美利坚共和国对奴隶制扩张的支持。建国初期的美国尚未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加上缺乏强大的联邦政府,新增的领土往往成为潜在的分裂因素。其他国家的虎视眈眈、印第安人的拒绝迁徙以及西部殖民者的谋求独立都威胁着国家的统一。为了团结南北的政治家,建立起全国性政治联盟,联邦政府违背了《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立国准则,支持奴隶制在西南边疆的扩张(Baptist,2014:35)。虽然克莱门特闭口不谈他来纳奇兹的动机,但驱使他南下拓荒的少不了国家政策对奴隶制的扶持。小说伊始,克莱门特刚从新奥尔良归来,把种植的烟草“以不错的价格卖给了国王的人”(Welty,1998:3)②。他的交易能够顺利进行也许要得益于美国与西班牙签订的协议,允许农场主把经济作物和其他商品通过新奥尔良港口运往世界市场(Baptist,2014:40)。克莱门特先后种植过烟草和靛青,但棉花是他发家致富的关键。用他的话来说,有一年莎洛姆“让我试着种棉花,然后我就发财了”(Welty,1998:15)。美国南方拥有棉花种植所需要的自然环境,包括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温度及降水。1793年轧棉机的发明大大提升了棉花加工效率,植棉业发展迅速。为了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种植园主开始扩大奴隶贸易。虽然1783年到1888年间禁止国际奴隶贸易,大约有17万名黑人奴隶仍然被运输至美国(贝克特,2019:102)。尽管我们对克莱门特如何购买、压榨奴隶不得而知,仅仅知道他“派新来的奴隶带着斧头去砍伐更多的树木”(Welty,1998:14),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一望无际的田地和不断扩建的种植园大宅都是强制奴隶劳役而生产的空间。可以说,南方的奴隶制种植园是在美国初创时期的拓殖领土实践中兴起的。
反过来,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也加快了国家边界向西推进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由于棉花种植容易耗尽地力,种植园主不断向西和向南扩张,形成了包括南卡罗来纳、佐治亚、阿拉巴马、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肯色以及德克萨斯部分地区在内的棉花种植带,建立起南方的“棉花帝国”(Dattel,2009:42)。到了19世纪中叶,纳奇兹已从荒凉的边疆发展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城市之一。全美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百万富翁居住在此,兴建的种植园大宅超过四十多栋(Bethea,2001:36)。美国日渐成为全球棉花市场的主要供应商。在19世纪初,南方的种植园主主宰了英国市场,到了19世纪30年代,他们还占领了新兴的欧洲大陆和北美市场(贝克特,2019:109-110)。虽然美国历史叙事把奴隶制视为南方特有的罪恶,但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了原始资本,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使之在19世纪能与欧洲分庭抗礼,成为国际制造和贸易的中心(Romine & Greeson,2016:36)。正如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所言,“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上升是建立在棉花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奴隶制的脊背上的”(贝克特,2019:110)。
韦尔蒂运用“时代误植”(anachronism)的写作手法来彰显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在美利坚帝国崛起中的重要作用。克莱门特的妻子莎洛姆和他一样贪婪无度,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化身”(Trefzer,2007:139)。除了野心勃勃地计划把靛蓝、棉花和烟草的种植面积都翻一番,她还打算建造恢弘气派的种植园大宅,“起码五层楼高,顶部有观河的瞭望台,还有二十二根科林斯柱子承托着屋檐”③。莎洛姆梦想中的豪宅实际上是竣工于1861年的温莎宅邸(Windsor Mansion)。作为密西西比州占地面积最大(约1052公顷)的种植园大宅,温莎宅邸是南方种植园制度全盛时期的空间表征。韦尔蒂把象征着奴隶制经济社会制度的种植园大宅设置为早期拓荒者为之奋斗的目标,暗示了奴隶制并非南方特有的原罪,而是国家扩张性的领土实践和资本主义发展逻辑作用于南方自然环境的结果。她也借由时代错置影射了历史和现实的交叠之处:如果说建国初期的领土扩张和经济发展是以牺牲黑人的基本权利为代价,那么30年代的新政在重新整合国家空间,把南方纳入美国的经济政治轨道时,再次忽视了非裔美国人对平等公民权利的诉求。为了实现经济复兴的目标,联邦政府容忍了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以换取南方种族主义统治者对改革举措的支持(卡茨尼尔森,2018:19)。其结果就是,新政没有改变黑人的二等公民境遇:到1938年,非裔美国人获得选举权的比例不足4%(卡茨尼尔森,2018:16)。韦尔蒂在新政机构工作期间走访了密西西比州的各个乡镇,对深陷贫穷和种族歧视的底层黑人民众抱有深切的同情,并且以摄影的方式记录了他们的尊严和抗争。《强盗新郎》中虽然没有对奴隶生活的细致描摹,但韦尔蒂通过对历史的巧妙拼接批判了美国社会对黑人长期的系统性歧视和迫害。
3.0 边疆空间的驯化与民族身份建构
除了建立统一的经济政治结构,国家空间的生产也是在划定的领土边界内形塑共同的民族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过程。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Turner)的边疆学说就点出了国家空间生产与民族品性锻造之间的关系,“那片自由的土地滋养着个人主义、经济平等及自由民主的上升空间”(1920:259)。从1776年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处于向外扩张的状态。因此,美利坚民族身份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方面要求共同体成员产生同一性的想象,另一方面也需要对进入国家空间的异族分子进行监管、驯服或清除、驱逐。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大部分土地原本是印第安部落世代繁衍生息的家园(何顺果,1992:82)。18世纪末,为了将这片土地收归国有进行有效的统治,美国国会颁布法令,取消印第安人对部落领地的自然权利,将之作为“自由土地”供移民定居开发,强迫原住民搬到政府划定的保留地去。为了把驱逐印第安人的行为合理化,主流话语不仅将他们的部落领地描述为荒无人烟的处女地,而且把印第安人妖魔化为野蛮暴戾的种族,鼓吹他们的灭绝就像季节更迭一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克莱门特在回忆自己被俘的经历时,就重复了囚掳叙事中认为印第安人“代表了人性堕落全部特点的野蛮人和魔鬼”的论调(金莉,2018:92)。他表示“印第安人知道自己大限已至……这让他们变得无限放荡凶残”(Welty,1998:12)。正是在这样的话语逻辑支配下,像克莱门特一样的早期殖民者打着驯化边疆空间的旗号大肆侵占原住民的土地,把他们放逐至国家空间的边缘地带。
韦尔蒂把小说设置在以印第安纳奇兹部落命名的地方,这一选择本身就驳斥了原住民在美利坚国家空间生产中毫无贡献的成见。不仅如此,她也再次以错置历史的方式谴责了国家版图拓展背后的种族清除。早在1729年,纳奇兹部落就遭到法国殖民者的屠戮而几近灭族,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或被当作奴隶贩卖,或加入其它印第安部落而渐被同化(Trefzer,2007:125)。韦尔蒂复活了纳奇兹印第安人,又让他们再次湮没在边疆开发的过程中,旨在揭露帝国主义殖民扩张中一以贯之的种族暴力,戳穿美国例外论的历史叙事中诸如“新世界”“大西部”“追求幸福”等谎言(Thorton,2003:55)。《强盗新郎》中最血腥的场景莫过于以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土匪威利·哈普(Wiley Harpe)为原型的强盗小哈普对一位印第安少女施加暴行。无恶不作的小哈普意欲取代小说同名主人公吉米·洛克哈特的头目地位,趁他外出之际来到强盗们的巢穴发动叛乱。他企图侵犯吉米的新娘来彰显自己的权力,却误将被劫掠来的印第安少女当作罗莎蒙德,当众剁掉她的无名指并凌辱了她。和同名的格林童话相比,韦尔蒂不仅把施暴者从强盗新郎替换成美国南方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也把受害者改为印第安少女④。正如韦尔蒂在《纳奇兹小径的童话故事》(“Fairy Tale of the Natchez Trace”)一文中所言,她的改写凸显出“历史讲述的事情比童话更为可怕”(1990:309)。就像小哈普借由杀害印第安少女获得在强盗团伙中的主导地位,白人殖民者通过驱逐原住民掌握了国家空间的统治权,进而建立起符合自己利益的社会等级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30年代见证了美国对印第安文化的重新发掘。新政时期,联邦政府资助的考古活动对南方的印第安遗迹进行了大规模的挖掘开采,出土了坟堆、洞穴、村落以及大量的人工制品等(Trefzer,2007:1)。1938年,政府拨款修建了纳奇兹小径公路(Natchez Trace Parkway)。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公路边竖立的告示牌上写道,“在你背后的公路是旧纳奇兹小径的一部分——这条荒野之路最初是西南地区的印第安部落使用的一系列小路。纳奇兹小径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军事方面对美国早期的发展都极为重要。”⑤纳奇兹小径作为印第安遗址被纳入美国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成为国家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印第安人被接纳为“美国”这一想象共同体的成员。考古更多体现的是“帝国怀旧”(imperialist nostalgia)的心态,即“殖民者对被他们摧毁或改变的生活方式的向往”(hooks,1992:189),以展现帝国文明的包容和进步。但印第安人在现代美国社会依然是被边缘化的群体。当时的好莱坞电影往往用怪异的语言和奇特的身体姿势来表征印第安人,强化他们“在语言上甚至智力上都是有缺陷的,充其量就是不合时宜的群体,注定会不复存在”的种族主义成见(Kilpatrick, 1999: 38)。美国的国家建构工程一方面利用印第安文明重构美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将美国历史往前推进了几个世纪,另一方面则以“消失的种族”话语割断现存印第安人和古印第安文明之间的纽带,淡化他们在美国空间生产中的作用。
在《强盗新郎》中,韦尔蒂不仅嘲讽了主流叙事中的印第安人刻板印象,也通过书写人物身份的转变揭秘了民族身份建构对印第安人的利用。她以局部代替整体的提喻(synecdoche)修辞手法来刻画白人殖民者眼中的印第安人:当克莱门特被俘时,“一只红皮肤的手拽着他站了起来,他直视那双世故的圆眼”(Welty,1998:69);复仇的印第安人在林中发现小哈普时,透过树木看着他的脸“是红皮肤的,裹着羽毛,眉头紧皱”(Welty,1998:70)。这些更像是出现在迪士尼动画片中的形象而非真实的历史人物(Kreyling,1998:5)。小说对印第安人的夸张表征与印第安少女的悲惨遭遇形成了鲜明对比,让读者得以窥见被种族刻板印象所遮蔽的原住民血泪史。此外,小说中的白人人物在将印第安人他者化的过程中确认自己的美利坚共和国公民身份。与边疆空间的阈限性相对应的是身份的不确定性。《强盗新郎》的人物大多具有双重身份(double identity),比如克莱门特和莎洛姆既是不畏艰苦、开疆辟土的拓荒者,也是贪得无厌、追逐利益的种植园主。而最具戏剧张力的双重身份当属吉米·洛克哈特:他既是行侠仗义、拯救克莱门特性命的绅士,也是为非作歹、夺走罗莎蒙德贞洁的强盗。外出打劫时,吉米用浆果汁把脸涂黑,而需要以绅士面目示人时,则把伪装卸掉,“像太阳一样发出光芒,整洁、年轻、睿智、乐观”(Welty,1998:34)。有论者指出,吉米的伪装“呈现出早期殖民者刻板印象中美洲原住民显著的暴戾特征”(Merricks,2005:7)。换言之,吉米借由“扮黑脸”来操演所谓的“印第安性”,把肆无忌惮的烧杀劫掠行为加以种族化。他的行径不禁让人联想到兴起于19世纪美国南方的“黑面表演”(blackface minstrelsy),即白人装扮成黑人,模仿他们的口音和举止进行音乐或舞蹈表演。这种表演是“白人凭借当时的种族政治和文化优势对黑人文化的肆意挪用,其目的就是消遣、贬低美国黑人,以达到‘他者化’黑人族群的初衷”(王卓,2016:13)。同样地,吉米也是通过操演程式化的特征来强化种族成见,为屠杀印第安人寻找正当的借口。他带回家的战利品中就有“克里克人的头皮”(Welty,1998:43)。吉米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他就彻底放弃了强盗的营生,摇身一变成为受人尊敬的绅士。他是通过把原住民塑造为嗜血成性的民族他者来完成身份变化的。
和吉米相比,罗莎蒙德获得美国人这一身份的过程更为曲折。在美国建国初期,女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极为低下。她们没有选举权,也没有拥有土地及继承财产的权利,只能以“女儿”“妻子”等附属性的身份确立自己的社会角色(王恩铭,2002:4)。罗莎蒙德和受害的印第安少女一样都是种族主义父权制社会的他者。因此,当继母莎洛姆责骂她时,罗莎蒙德只能“带着印第安野蛮人的安静神色接受殴打和虐待”(Welty,1998:33)。在目睹小哈普施暴时,藏在房间角落的罗莎蒙德甚至短暂地和那位不幸的印第安少女产生了强烈的共情,“几乎要以为她是在强盗们的注视下站在屋子中间而不是躲在桶背后”(Welty,1998:63)。然而,在意识到自己也可能面临类似的命运后,罗莎蒙德选择了与种族主义父权制结成同谋。她揭开吉米的伪装,推动了他的身份转变,并最终和他在新奥尔良成家立业;他们坐拥的湖畔豪宅是其成功实现美国梦的标志。韦尔蒂改写了格林童话,给《强盗新郎》安排了一个看似光明的结局。克莱门特一家从荒野到城市、从种植园主到商人的生活轨迹对应着美利坚共和国的发展路径。然而,细察之下,这一幸福美满的结局却有着“令人惊讶的黑暗轮廓”(Pollack,1990:22)。毕竟,无论是男女主人公的身份转变还是国家的迅速崛起都离不开对民族他者的塑造、践踏及驱逐。
4.0 结语
在《纳奇兹小径的童话故事》一文中,韦尔蒂写道,“历史和童话故事的界线并不总是清晰的,正如《强盗新郎》一直指出的那样”(1990:309)。她通过文体杂糅再现了美国初创时期风云激荡、充满张力的国家空间生产过程,修正了国家历史叙述,解构了“南方/美国”的二元对立。韦尔蒂的用意并非在于替南方免除种族主义的指责,而是借古喻今,提醒读者注意美国社会中持续并广泛存在的种族问题和民族身份形构中的排外倾向。作为初出茅庐的南方作家,她没有被当时的爱国主义思潮所裹挟一味赞美美国的荣光或哀叹南方的怪诞,而是以独立之姿反思了“现代世界中民族主义的性质及意义”(Ladd,2001:156)。此外,她也以文学想象的方式肯定了种族他者的空间实践对北美大陆的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确认了他们作为美利坚民族成员的身份。在这个意义上,韦尔蒂在这个看似轻松愉快的故事中书写了另类的美国历史。
注释:
① 在18世纪末,密西西比仍在西班牙的管辖之下。1798年3月30日,美国和西班牙签订的《圣洛伦佐约》(TheTreatyofSanLorenzo)生效,密西西比州成为美国的领地。1817年密西西比州正式成立。
② 此处“国王的人”(the King’s men)指的是西班牙在纳奇兹的殖民势力。
③ 科林斯式圆柱(Corinthian column)源于古希腊,是古典建筑的一种柱式。柱头用莨苕作装饰,形似盛满花草的花篮。科林斯柱式是希腊复兴式建筑(Greek Revival Architecture)的特征之一,而希腊复兴式建筑是19世纪美国南方流行的种植园大宅建筑样式(Bonner & Pennington,2013:6)。
④ 在格林童话的《强盗新郎》中,磨坊主的女儿和她的追求者订了婚。有一天她漫步至未婚夫在林中的屋子,却惊恐地发现他的真正身份是强盗。磨坊主的女儿躲在屋子角落的木桶背后,目睹了强盗们残忍地将一位劫来的姑娘折磨致死。她被剁下来的手指连同上面的戒指一起飞到了磨坊主女儿的怀中。在婚礼上,磨坊主的女儿当众出示了这枚戒指,揭露了新郎的暴行,成功地将他绳之以法(Pollack,1990:15)。
⑤ 关于纳奇兹小径公园的介绍,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chez_Tr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