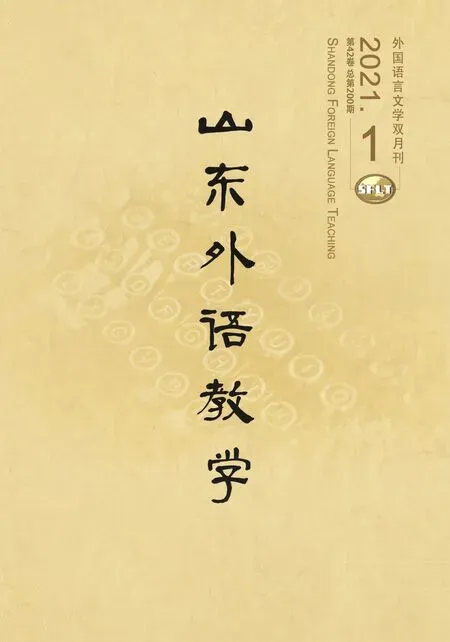后疫情时代的跨文化教育
——赫尔辛基大学Fred Dervin教授访谈录
2021-01-30张珊
张珊
(山东建筑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1)
Fred Dervin是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教授,专门从事批判性跨文化教育、多元文化主义社会学、国际学生和学术迁移等方面的研究,是欧洲跨文化传播教育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和评论家之一,是Tension研究小组(教育中的多样性和跨文化性)负责人,赫尔辛基SEDUCE博士学校(社会、文化和教育)副主任。Dervin教授还在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瑞典、卢森堡、马来西亚拥有荣誉教授或特聘教授职位。自2017年以来,他担任上海某大学与赫尔辛基大学跨文化联合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他精通多种语言,并以不同语言在国际上发表文章200余篇,出版著作50余本,在跨文化性、身份、流动性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迄今为止,Dervin教授已培养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30多名博士研究生,他们分别在反种族主义、跨文化能力、国际学生流动性、芬兰教育输出等跨文化与教育的不同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另外,Dervin教授还是《跨国教育》《北欧教育多样性研究》《后跨文化交流与教育》系列丛书编辑,以及《国际多样性教育杂志》的主编。
2020年5月12日,Fred Dervin教授与Thomas Wienold 博士举行了在线研讨会,从跨文化的视角与观众回顾了世界各国应对紧急事件如新冠危机时的经验。受《山东外语教学》编辑部委托,研讨会结束后笔者对Fred Dervin教授进行了专访,就“跨文化性”概念的发展和变化、疫情后跨文化教育的实践原则及跨文化研究的未来趋势等话题做了深入交流。
1.0 关于“跨文化性”概念的发展
张珊(以下简称张):多年来您一直在研究“跨文化性”。在以前的文章中,您曾经多次讨论“跨文化性”的概念。例如,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您曾经说过:“2015年1月可能标志着跨文化性的新纪元”,是“重构跨文化性”的时候(Dervin,2015)。在之后的著作中您也多次讨论梳理过“跨文化性”这一概念。我想,在过去的几年里,一定有某些转折点敦促您持续思考并改变对跨文化性概念的理解。您能否说明这些主要的转折点,以便我们可以了解多年来您关于跨文化性的思想发展?
FredDervin教授(以下简称德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从事跨文化性研究的学者应定期思考该问题。作为一名学者,我对跨文化性这一概念的研究已十五年有余。然而,我对跨文化性的体验和反思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我出生于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的欧洲家庭,多元文化和多种语言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有不同的“文化”和语言是正常的。在我三十岁以前,我时常被问到“你来自哪里?”“你通常用哪种语言?”“你的母语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记得自己在回答时不得不做出选择,结果是,我的答复或者取悦或者激怒了我的对话者……我始终无法确定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因此,在我人生的前三十多年里,我经历了许多饱含不确定性和感受到身份危机的时刻。这些问题无处不在,但我认为,人们并不愿意听取对“一种身份,一种文化,一种语言”的意识形态进行质疑的话语。
最终是研究挽救了我。起初我专攻语言学,之后将研究兴趣转向社会学、人类学、对话研究。我的法国博士生导师对此影响颇大。我第一次与她见面,她就告诉我应该去阅读“一切”而不“仅仅”是语言学和教育科学著作。因此,我在读博士的第一年,即阅读了我所能找到的用不同语言写的“一切”。在此过程中,我的发现是一个启示:学科界限尽管存在,却是虚假的。我们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核心问题:一个人被其他人围绕意味着什么?通过这些跨学科的阅读,我认识到前面提到的困扰我的问题,几十年来已经在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解构和重构。在此过程中我还发现,我所认为的我体验跨文化性的方式其实是18世纪以来的愿景,基于国家和国界的现代意识形态。人类学在这一发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意识到,文化在跨文化性中被赋予了太多的权力,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另外一种不那么以欧洲为中心的、不那么“现代”的方式去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当人们认为彼此不同的原因是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或“国家”,这两个词通常用作同义词)时。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它使我能够反思自己的个人经历,并开始重新思考跨文化性的概念。从那时起,我一直在努力创建“文化”的替代概念,然而对已有的提议我从未满意过,但我愿意继续前行,反复尝试。
在过去的三年中,我转向了不同的观点,批评了自己的著作,重新分析了我以为已经揭示的东西。同时,我发现许多从事跨文化研究的中国学者被西方认识论所牵制。例如,“intercultural citizenship”“tolerance”“intercultural competence”等概念的使用有很大问题。这些概念由Byram与Deardorff 等“大人物”所定义,但他们未必会翻译转化相同的经验或相同的意识形态。看到中国学者为了在世界学术研究领域争取更多话语权,不得不使用这些概念,使用这种“Intercultural-Speak”(我称之为),实在令人痛心。对我来说,在中国时的两个主要发现改变了我对跨文化性的理解和研究方式:孔子与民族教育。2012年我写了一篇文章,提醒西方学者不要使用刻板的儒家思想来研究中国人。在我开始阅读不同语言的不同译本并审视中西学者所做的不同解释之前,我对儒学的了解并不深刻。后来我发现,孔子的一些思想与关于人类的后现代观点之间有很多共通之处,而且孔子实际上是非常具有批判精神的。
张:没错。在您的新书中,您为跨文化能力的教师教育开发了两个模式,第二个即是儒家模式(Dervin, Moloney & Simpson, 2020)。
德文:是的。我对比了儒家模式与后现代模式的差异性、相似性甚至互补性。但该模式仍然在完善中。至于中国的民族教育,同样具有真正的启示意义。民族教育是西方人尚未意识到的一种多元化教育。它创建的教育形式考虑到了中国人的多样性,并且丰富了每位中国人共享的中国性。我在赫尔辛基的教授职位属于多元文化教育领域。我不知道真正的多元文化教育是什么,在工作中我只好使用了跨文化教育一词。然而所有这些标签都过于西方化以致于无法反映出多样性的理念。事实上,我们在多元文化或跨文化教育中处理多样性的方式远非多元化。通过我的同事和朋友,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Sude和Mei Yuan,我认识了民族教育,并得以再次从一个新的视角审视跨文化问题,继续质疑我被说服的方式以及我说服别人的方式。简而言之,正如您所看到的,我经历了多个接触、思考跨文化概念的不同阶段。跨文化领域的研究工作很大程度上植根于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因此,学者们应定期审视、回顾他们针对这两个要素的工作,并尝试提出新的想法,并且系统地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对话。我想提醒读者们,英语中的“dialogue”一词来源于希腊语dialogos,dia意为“通过”,legein意为“说”。与其他学者、教育者和决策者进行有关跨文化性的对话,有助于您一次次地加深对这一重要现象的了解。
张:在以往的著作中您曾经多次强调多元文化“在表面的不同之下,隐藏着相似点”(Dervin,2016)。您现在仍然坚信这一点吗?
德文:是的。我相信这是跨文化性的核心。我们对跨文化性的分析和论述通常基于我所称之为的差异偏见,同时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差异之上,我们也具有很多相似性。但是由于这种偏见,我们对相似之处往往视而不见。且由于某些原因,人们似乎怀有一种与他人相似的恐惧。我的方法是始终同时考虑差异性和相似性。比如中国的火锅,尽管味道可能有所不同,但它与欧洲的芝士火锅概念非常相似。基本上就是您加热一些液体,奶酪、肉汤甚至巧克力,而后将食物浸入其中并食用。我喜欢火锅是由于它在中国有多种不同样式。它通常很美味,但也让我想起了我在欧洲的童年。那时候我们会在冬天吃芝士火锅。是的,人与事是不同的,但也有相似之处,我们必须考虑它们。
张:有些学者认为新冠疫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或许现在推测还为时过早,但疫情过后,您可能会从新的角度审视跨文化性,能否请您分享一下您对跨文化性概念的新思考?
德文:许多跨文化主义者宣称我们正经历新冠病毒带来的时代终结,对此我不认同。至少在“西方”,我没有看到我一直在关注的学者们对跨文化性的讨论有任何变化。绝大多数人仍将跨文化性视为文化的“对话”和/或“冲突”。对我而言,新冠危机是我一生中的重要时刻。我认识到我做出的关于什么是跨文化性的假设已经得到证实。我们都对文化和文化差异着迷,然而疫情向我们展示的是,我们共享的相似性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我们都买了很多厕纸、意大利面、洗手液、肥皂等;我们都开始在阳台上唱歌;我们都在互联网上创建了各种表情包;我们都为家人感到恐惧;我们都为死者哀悼等等。这些都是已被证实的共性。但是,当前非常清晰确凿的一点是:尽管我们在跨文化研究中一直痴迷文化,更为重要的却是经济和政治。
我的意思是,西方各国政府的反应或多或少都相同,并且显示了我们新自由主义世界的真实面貌:真正重要的不是人,而是经济。我居住的国家芬兰在新冠危机期间犯了很多错误,很多严重错误。大多数跨文化主义者会说,芬兰是有秩序、专业、诚实的榜样文化。但是,在芬兰,许多老人在养老院死亡;人们由于缺少个人防护设备而导致感染。一月份(2020年)的时候,我很震惊地发现买不到医用口罩,洗手液也已售罄。我在药房里问他们时,总是得到相同的答案:我们没有口罩,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是无用的。现在在欧洲,除了芬兰以外,很多人都戴口罩。是文化的还是与经济有关呢?您在商店或药店找不到口罩,或者偶尔能找到,只是一个需要25欧元。毕竟,在我们无处可买的情况下说它们没有用处确实更容易。
疫情期间,许多文化论争被用来隐藏政治和金融问题。是的,这就是新冠疫情向我证实的:我们既有差异性又有相似性,统治世界的不是我们不同的文化方式而是对市场的普遍新自由主义态度。另外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是观察西方媒体如何讨论一些“易瞄准的目标”以分散对当地问题的注意力。在芬兰,这些“目标”包括特朗普、瑞典与中国。媒体对这三个实体有或明或暗的批评,但对芬兰当局却没有。
张:您能否解释一下您以前的理解与新冠疫情之后对“跨文化性”的理解之间最大的区别?
德文:之前的理解没有考虑到经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重要性。通常的情况是,人们专注于“文化”并将其作为一种审视跨文化性的简便方式。我多年来所做的正是如此。但这是切入跨文化性的一个错误角度。我今天的观点对翻译以及我们倾向于如何使用全球英语都较为敏感。英语语言对不同的人传达着不同的意义。因此,当我们互相交谈,使用那些我们认为能以同样的方式去理解的词语——其实这些词具有其他含义——最终导致我们无法顺畅交流,或者我们觉得互相理解,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天来,我对这些“不可翻译的东西”更加敏感。在中国的授课过程中我注意到,我认为某一单词对我的中国学生们来说意义相同,但他们的理解却往往并非一致。例如,以下这些单词是我不得不跟我的学生沟通的:exotic、tolerance、civilization、talent。很多单词的含义必须重新讨论,才能确保我们真的在互相交谈。
张:跨文化性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都存在不同的代表思路,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您选择跨学科讨论跨文化性的原因。您能否简单解释一下自己的跨文化研究方法,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您关于跨文化研究思路的变化?
德文:分析跨文化性与分析任何人类现象一样具有挑战性。我们根本没有合适的工具来应对这种复杂性。两个人交谈的过程中有许多我们无法触及的参数。人类是表演者,我们互相表演——甚至与最亲近的人……我们无法看到、听到、掌握所有沉默的思想、态度和行为。因此,当我分析跨文化的事物时,我知道我无法了解人与人之间真正发生的事情。我所描述的只是他们之间的表现——对我这个研究者而言的表现。我使用了十年的方法源自于对话主义(Dialogism)。这种方法让我们能够深入挖掘话语中的某些隐性内容并使之浮现出来。在我们所说的话语中,总有一些隐藏的迹象表明我们真正的意思或意图。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只得以窥见冰山一角。仅仅依靠人们在我们的研究中所说的、所做的或所表现出来的,不仅非常有限亦不能描述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复杂的关系。我认为承认这一失败至关重要,同时,我们也需要更深入地挖掘这种复杂性,以揭示跨文化性的新层面。
2.0 关于跨文化能力与跨文化教育
张:2019年您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了跨文化性的概念与学生的跨文化能力,认为经合组织建立的学生跨文化能力模型“抛开了差异与相似的连续体”,并且“有可能将自我与他者限制为单一身份”,不利于导向真正的跨文化对话(Simpson & Dervin,2019)。现在,您对跨文化能力有什么新的见解呢?
德文:尽管很多学者助推了跨文化性的讨论,但我真的没有搞懂当下就跨文化能力概念所做的工作。我认为,我们需要摆脱“强大”的西方学者例如M. Bennett、M. Byram与D. Deardorff强加给我们的所有模式。他们代表着这个世界上白人、美国人或英国人的特权,以英语出版,并为世界上强大的机构工作,因而象征性极大。遗憾的是,这些模式衍生出了一些教育中必须避免的新自由主义议题,存在很大问题。他们的模式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而跨文化则是通过对话发生的,至少有两个不同的人进行交互。如果人们通过研究某一谈话者的能力来评估其跨文化能力,那么我们就会遗漏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的跨文化能力取决于语境,以及其他个体的存在。我的跨文化能力就是你的跨文化能力。我们在同一时间共同努力。因此,仅评估一名对话者是不公平的。这是我对这些西方学者定义跨文化能力方式的主要质疑。
还有一点,他们对文化概念、开放与尊重理念的过分依赖也很成问题。“如果您了解一种文化会有所帮助”,但是什么是文化?谁来决定某一给定文化的哪一部分适用于正在互动中的人?另外,开放和尊重也有可能仅仅是表演,一种我假装喜欢对方的表演。目前在欧洲,Byram及他的团队提出了一种跨文化框架,将“民主文化”的错误观念置于中心。因此,跨文化性被政治化了。当然这也可能是一件好事。但是,它起源于有问题的民主定义,并且似乎在拥有民主的人与没有民主的人之间建立了等级制度。很遗憾,但作为欧洲人,我可以说民主在我的世界里不起作用。这是一场表演。我可以花几个小时谈论这个问题,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访谈的重点。如果您问我如何定义跨文化能力,那么今天您得到的答案可能与十天后我的答案大相径庭。我认为我们对跨文化能力的定义需要灵活而不是一成不变。如果您问我是否认为我们能够具有出色的跨文化能力,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个概念太复杂了,甚至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成为一个良好的社会人意味着什么?总之,我认为没有良方妙药可以快速提高跨文化能力。
张:您曾在2015年的文章中提到,“语言教育是跨文化教育的主要渠道之一”(Dervin,2015)。后来您又提出“ELF和跨文化性是两个有很多共同点的不同领域”,“促进、发展和评估‘跨文化性’一直是语言教学的主要兴趣”(Holmes & Dervin,2016)。您是否仍然认为语言教育是跨文化教育的主要渠道?您还推荐其他哪些渠道?
德文:是的,我仍然这样认为,但是我将添加“不幸地”一词。跨文化性对于所有形式的知识和所有领域都至关重要。我们经常勉强语言教育者去做“跨文化性”工作是不公平的,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做“不好”或很“笨拙”。似乎存在这么一种观点,即他们会说不同的语言,教导跨文化性就是他们的责任。我不认同。不能因为一个人会说多种语言,就认定他擅长跨文化交流。我觉得这是一种刻板僵化的观念。不同领域的专家应该聚在一起教授这方面知识。在基础教育中,每个科目都涉及跨文化知识,甚至包括数学、生物和体育。
张:如果进行跨文化教育并不能保证学生跨文化能力的提高,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充分利用当前的跨文化教育?您能分享一些有关当前跨文化教育的一般性但实用性准则吗?
德文:我承认跨文化教育实际上会适得其反。欧洲的学校实施了许多关于跨文化的项目,但是新冠危机表明我们失败了。危机期间,出现了如此多的老套成见,如此多的种族主义言论,如此多的民族中心主义观点。我不得不说,没有什么所谓的跨文化教育,有的只是学校用于训练欧洲孩子们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系列实践。根据所使用的意识形态,学习目标可能会完全不同。举例来说,如果老师相信“文化”在跨文化中的中心地位,他可能会引导孩子们采纳文化主义的观点,进而轻易转变成刻板成见以及关于自我和他人的有限或限制性论述。
在我看来,跨文化教育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学会自我省察。在接触他人之前先对着镜子看自己。了解自己的感受,批判性看待社会,拓宽我们的视野,比如将其投向我们周围发生的不公正行为;第二,考虑文化以外的跨文化性,观察并审视性别、年龄、社会阶层、种族、宗教以及其他种种因素如何导致某些跨文化现象;第三,质疑政策制定者、决策者、商业界讨论跨文化的方式。这就是我所提出的“质疑看似毫无疑问的”。例如,我们经常听到诸如“旅行开阔视野”“我们必须尊重文化”之类的断言,对此我们已习以为常,但实际上我们应该质疑它们以进行更广泛的思考。这就是在赫尔辛基我们与学生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事实上,这些都是痛苦的做法——当我们被洗脑以至于认为我们的社会是“完美的”时,开始自我批评从来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是它们养成了我们的谦虚品质和反省意识。
3.0 给后疫情时代中国跨文化教育的建议
张:在之前的著作中,您对“东方”与“西方”的关键要素进行了界定,并且从艺术与跨文化碰撞两个角度切入审视了中国与西方的跨文化交流(Dervin& Machart,2017)。据我所知,您不仅在中国多所大学做过讲座,还做了许多有关中国教育的研究。例如,您编辑了《中国语言教育中的跨文化性》一书;还分析了中国中学《思想与品德》教科书中的民主性。根据您在中国的经历,您如何看待中国教育中的跨文化教育,尤其是中国外语教育?根据您的理解,您认为我们应该对跨文化教育做出哪些进一步的改进?
德文:我认为中国老师面临着与世界各地老师相同的挑战。对不同的研究人员而言,跨文化性的概念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那么他们如何选择一个视角呢?像芬兰一样,中国很少有学者和教师尝试发展出关于跨文化性的新思维方式,对此我一直感到奇怪,因为中国无论在国家内部,抑或与外部世界之间都有着悠久的跨文化历史,理应把“故事”讲给世界以及那些应该倾听的跨文化学者们。然而,我必须再次重申,我发现中国教师在民族教育中所做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跨文化性的。以下是我对中国教师们的建议:
第一,学习和教导跨文化时切忌全盘接收西方学者的论点。对部分中国老师们“崇拜”某位西方学者的现象,我一直感到担忧。跨文化性是相当政治性的,您应该小心,确保这些西方学者的书籍或文章中衍生出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兼容并立。许多西方学者属于某些协会、团体或政治运动组织,对此他们并不经常提及,但却是他们跨文化观点的核心。因此,请务必进行细致地审察,以免间接将某些有问题的意识形态传播给中国学生。
第二,尝试阅读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领域的书籍与文章。这些领域处理跨文化问题的时间比某些领域(如语言教育)要长久得多,他们对这一概念的批判性观点也深入得多。语言教育经常从以上领域借鉴观点,甚至借鉴一些被这些领域摒弃的旧观点。
第三,培养对西方之外思想的兴趣。许多来自南美、非洲以及亚洲的学者和作家都写过关于跨文化性和多样性的文章。如果您能接触到他们的著作,阅读一下将会大有益处。
第四,在世界跨文化研究中发出中国声音。以中国悠久的跨文化历史为积淀,尝试发现中国如何能够为世界跨文化研究添砖加瓦,做出特有的贡献。
4.0 对未来跨文化研究的思考
张:您在文章《语言和跨文化交际教学法的关键转折:作为新视角的简单复杂连续体(简单性)》中曾强调:“迫切需要继续修订我们对跨文化性的理解和原则,并为过去几年的关键时刻提供更大的力量。”(Dervin,2017)您是否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发展跨文化性的概念以对教育尤其是跨文化教育有所启发?
德文:是的,我会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寻找新的观点、新的要说的东西,并补充、甚至“推翻”我以前所说的内容。我现在正在研究经济和金融在跨文化话语中的嵌入和隐藏方式。这就是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永远不满意于我们应对跨文化性的方式。就跨文化性而言,新冠危机再次证明了我们西方教育体系的重大失败。让学者们休整一下,盘点系于跨文化性的诸领域(如教育、商业、医疗保健等)所取得的成就、所遭遇的问题、已解决的问题与未解决的问题,似乎是这个概念唯一可行的未来。这些工作应该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语言中进行。审视当下,人们喜爱撰写关于跨文化问题已有研究的评论性文章,但他们只看英文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然而有那么多其他语言的出版物,我们却并不了解。我们也应该考量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可能对我们的讨论大有裨益。只有在对这些进行了反思之后,我们才能尝试提出替代方案,以及重新思考跨文化性的新方法。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研究在教育方面具有较大发言权的超国家机构,如经合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委员会等。他们如何提出应对跨文化性的建议?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他们与我们想要的世界相融合吗?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刻反思之后,我们才能展望未来。不回顾已取得的成绩就贸然尝试前进的倾向是危险的,它不仅会蒙蔽我们的视线,而且让我们重复工作浪费气力。总之,可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我认为这是非常积极和鼓舞人心的!
张:谢谢您,Dervin教授!您今天谈的这些内容,对我们更深刻理解跨文化性这一概念,理解跨文化能力和疫情之后跨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及未来研究都有重要启发。再次感谢您能接受我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