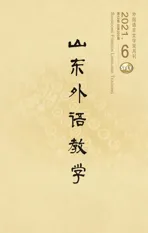重返“无返之门”
——《月满月更之时》中的奴隶制、“居间性”和家族谱系
2021-01-29綦亮
綦亮
(苏州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9)
1.0 引言
1993年,英国黑人学者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出版了《黑色大西洋:现代性与双重意识》(TheBlackAtlantic:ModernityandDoubleConsciousness)。在该书中,他抨击黑人文化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和文化绝对主义倾向,质疑现代黑人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中心和欧洲根源,从“跨民族和文化间性视角”(Gilroy,1993:15)探讨黑人文化在美国和欧陆之间的流转,呼吁把注意力从“根源”(roots)和“根源性”(rootedness)转移到“路径”(routes)。为此,吉尔罗伊(1993:190)强调奴隶制引发的“流动、交换和居间元素”及其在黑人文化中的表征,尝试从流散视角考察身份、历史记忆以及黑人意识与现代性的关系。
吉尔罗伊的理论构想为解读黑人文学,尤其是关注大西洋奴隶制历史以及黑人流散的文学作品提供了重要切入点,但是整体上看,目前从“黑色大西洋”视角对黑人文学的解读主要集中在英美两国黑人文学,缺少对其他国别和区域黑人文学的关注。事实上,因为大西洋奴隶贸易对非洲、加勒比、美洲和欧洲等地的串联,对奴隶制历史和黑人流散的文学再现远远超出英美两国的范围,作为美国黑人文学近邻的加拿大黑人文学在这方面就有突出表现。在众多加拿大黑人作家中,迪翁·布兰德(Dionne Brand,1953-)的创作又与“黑色大西洋”观念存在明显的对话关系。布兰德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中学毕业后移民至加拿大,在诗歌、小说和文学批评方面有极高的建树,是“加拿大总督功勋奖”(Order of Canada)得主,被誉为“加拿大的托尼·莫里森”。本文以布兰德的小说《月满月更之时》(AttheFullandChangeoftheMoon,1999)为例,讨论该作如何在奴隶制历史记忆以及对“路径”和“居间性”等概念的演绎上契合了吉尔罗伊的学术思想,同时借助彰显女性意识的黑人家族谱系丰富和拓展了“黑色大西洋”的内涵。
2.0 奴隶制历史记忆
“尽管奴隶制已经被废除一个多世纪,但其迷思和态度并没有完全被清除”(Patton,2000:xviii),在奴隶制终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奴隶制对黑人造成的精神和身体创伤依旧占据黑人作家文学想象的中心(邹涛、谭惠娟,2021)。加拿大黑人文学对奴隶制的关注有其历史根源。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亲英派携带黑奴从美国迁至加拿大,还有一大批黑人为了自由支持英国,也逃往加拿大。1850年,美国通过《逃亡奴隶法案》,允许南方奴隶主到北方自由州追捕逃亡奴隶,引发巨大争议,迫使许多黑人有识之士离开美国,去加拿大继续自己的事业,其中包括雪德(Mary Ann Shadd)、沃德(Samuel Ward)和德兰尼(Martin Delany)等著名黑人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加拿大也因此成为19世纪中期北美黑人解放运动的重要场所。这些关联构成了加拿大黑人文学回溯和叙写奴隶制的历史语境。
无论从构思还是内容上看,奴隶制都是《月满月更之时》的重要背景。在回忆录《一张通向“无返之门”的地图》(AMaptotheDoorofNoReturn:NotestoBelonging,2001)中,布兰德讲述了这部作品的创作机缘,提到她是在多巴哥岛参观一座展示殖民统治遗迹的博物馆里得到的灵感:“这部小说始于一座博物馆,一座小型的白色博物馆,里面收藏了18世纪英国殖民军事遗物”(Brand,2001:196)。而小说的标题就是取自其中的一件藏品——英王乔治三世的绘图官托马斯·杰弗里斯描述多巴哥岛的一段文字:“多巴哥附近的海潮十分汹涌,特别是在多巴哥和特立尼达之间。在月满月更之时,会出现四英尺高的海浪”(Brand,2001:200)。小说开场设定在19世纪初的加勒比岛国,主角是女黑奴玛丽·尤苏尔。布兰德在回忆录中告诉读者,尤苏尔这个人物来源于奈保尔(V. S. Naipaul)的《失落的黄金国》(TheLossofEldorado:AHistory),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位名叫‘提丝比’的女人,一个奴隶,一位在种植园下毒导致大规模死亡的主要嫌疑人。在审讯数月并遭受非人折磨后,她被处死”(Brand,2001:205)。尤苏尔大抵是以提丝比为原型塑造的,她是“造反者的女王,黑夜的主宰,佯病的高手,精于破坏和毁灭”(Brand,2000:5)。和提丝比一样,尤苏尔也生活在种植园奴隶制的阴霾下。她先是在加勒比的法属瓜德罗普岛为奴,因为造反被割掉耳尖,并因为粗野的行为身背多项指控。为了还债,奴隶主罗沙尔把尤苏尔低价贱卖给乌尔苏拉会修女,这些修女“四处辗转,从瓜德罗普岛到马提尼克,然后是特立尼达”(Brand,2000:9-10)。她们随身携带奴隶,来到特立尼达后买下种植园,靠经营种植园为生。她们对奴隶恩威并施,既给他们洗礼,也靠暴力维持秩序,因为无法驯服尤苏尔,将其卖给奴隶主兰伯特。生性叛逆的尤苏尔依然不服管教,她率众起义,企图杀死兰伯特,因计划泄露而失败,“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处死……她戴上了十磅重的铁环,被鞭打了三十九下,耳朵被割下塞在嘴里”(Brand,2000:5)。两年后,尤苏尔卷土重来,精心策划了集体自杀作为对奴隶制的终极反抗,最后被处以绞刑。
奴隶制情节虽然在《月满月更之时》中所占篇幅不长,但却十分关键,它奠定了整部作品的叙事基调,显现出小说与“黑色大西洋”观念的紧密关联。埃克斯坦(2006:x)指出“黑色大西洋”不仅表示一个复杂的时空体,还是“一个独特的隐喻,能够唤起大西洋奴隶贸易那段重要的历史经验,上面铭刻着数百万人的命运,他们在不计其数的洲际穿越之前、之中和之后受苦并死去”。作为一名来自加勒比的黑人作家,布兰德对奴隶制和奴隶贸易有一种自发和天然的认知,她曾说:“我是一名黑人女性,我的祖先们躺在塞得满满的贩奴船上被运到新世界。他们中有一千五百万人在航行中幸存下来,其中五百万人是女性;还有数百万人在‘中间通道’中死去、被杀害和自杀”(转引自Garvey,2003:486)。《月满月更之时》尽管没有此类情节,但尤苏尔像商品一样被辗转倒卖,显然是奴隶贸易的受害者,她遭受的精神和肉体戕害完全是拜奴隶贸易所赐。吉尔罗伊(1993:222)在评价莫里森的创作时指出:“她的作品指向并致敬一些黑人作家唤起过去的策略,这些黑人作家的少数派现代主义……可以通过与恐惧形式的想象性近缘关系进行界定,这些形式无法被理解,它们从当前的种族暴力,途径私刑,回溯至‘中间通道’的时间和认知断裂。”布兰德在《月满月更之时》中也运用了这种唤起策略,通过喻指“塑造黑人流散和历史基本概念”(Valkeakari,2012:14)的“中间通道”,恢复对奴隶制遗产的记忆,揭示出在后奴隶制和后工业时代重返“最初生产非洲流散的帝国主义、前工业资本主义以及反黑人种族主义的合力”(Valkeakari,2012:13-14)的必要性。正如吉尔罗伊(2001:23-24)所论,“奴隶制、大屠杀、卖身契、种族灭绝,以及其他难以名状的恐惧,一直存在于流散的肌体以及流散意识的生产。”
3.0 边界消解与“居间性”概念演绎
《月满月更之时》故事的缘起是奴隶制,推动叙事进程的是奴隶制引发的流动和迁移。行动前,尤苏尔把自己唯一的孩子——女儿博拉托付给好友卡门纳,在卡门纳的帮助和照看下,博拉生存下来,并且生下九个孩子,这些子女继续繁衍生息,他们的后代有的留在加勒比,有的去往他乡,在与故土和故人的情感纠葛中演绎各自的人生故事。这种叙事方式表明布兰德的创作与吉尔罗伊以“路径”为先导的“黑色大西洋”之间的相关性。彼得·迪金森(Peter Dickinson)(1998:114)注意到布兰德对边界的消解,用跨文化的流散身份认同取代“主体性的民族叙事”;马琳·戈德曼(Marlene Goldman)(2004:13)论证布兰德作品中的“漂移观念”(notion of drifting),认为这种观念“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家园和民族国家边界性的方案”。
《月满月更之时》中不乏游离于边界之外的人物形象,比如卡门纳。卡门纳在一个雨季成功逃脱,幸运地找到逃亡黑奴聚集地特雷布扬特。他和尤苏尔有约在先,等雨季结束后潜回种植园,在尤苏尔被处决前带走她的女儿博拉,把她带到特雷布扬特。卡门纳没有食言,完全按计划行事,但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回特雷布扬特的路:“之前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既神圣又无法想象,好像他只能做一次。如果他完全按照上次的路再走一遍,有可能会迷路。这是另外一个季节,一个不同的地方”(Brand,2000:32)。无奈之下,卡门纳只能把博拉带到尤苏尔曾经为奴的地方——乌尔苏拉会修女的种植园库莱布拉湾,在那里一住就是十年。在此期间,卡门纳一直对他曾经度过一段宁静时光的特雷布扬特魂牵梦绕,走遍整个特立尼达岛,不停地找寻,“每次旅行都在重复的绝望和希望中结束”(Brand,2000:54)。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没有放弃,尽管所有的尝试都是徒劳的,用布兰德的话说,“他从来没有找到他在找寻并想要得到的,它在逃避、掩藏,所有的方向都把他引向无名之地”(Brand,2001:202)。
有论者参照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块茎”、“游牧”概念以及格列桑的“游侠精神”(errantry)解读《月满月更之时》,认为该作是对传统意义上的“解辖域化”思想的反拨,在布兰德的构想中,“解辖域化”不一定意味着解放和赋权,还有可能是不断地疏远与异化,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卡门纳:“卡门纳对特雷布扬特的找寻是没有进展的,只是对无法获得的过去的迷恋,而不是朝向自我肯定的一种建构性运动”(Evans,2009:13)。这种解读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准确。卡门纳的回溯并非完全消极,而是有一定建构性,因为“每绕一圈他都带回一些上面写有故事的碎片,一些对于方位的零星建议,这些他都给博拉看”(Brand,2000:54)。在反复追寻的过程中,卡门纳不断加深对周边景物的认知,完成了自己的地图绘制:“这个岛屿附近的海潮十分汹涌而且没有规律,在这个岛和大陆之间尤其如此。在月满月更之时,会出现四英尺高的海浪……”(Brand,2000:53)稍加比对就会发现,卡门纳这段对博拉的讲述其实就是对大英帝国绘图官杰弗里斯描述多巴哥岛的改写,正如布兰德在解释对这段文字的使用中所说的,她是“把其中的一部分用作小说标题……剩下的留给我的人物卡门纳”(Brand, 2001: 202)。通过对这段描述的切割和重组,布兰德挑战了殖民观看以及强调书写和边界的帝国绘图法。在小说叙事者看来,“一张地图……只能表达有产者和统治者的意志,或者说他们的希望。这张地图无法注意到各种地图的巨大流动性,就像空气的流动性。纸张很难包容全部——即使它的纬线和经线表明延续性。纸张无法穷尽土地,就像它无法穷尽思想一样”(Brand,2000:52)。卡门纳从“属下”位置提供了一种基于流动性以及情感和事实混合的地图绘制,体现了吉尔罗伊意义上的流散绘图法,揭示出“标记在全新旅程和抵达上的无法预见的迂回和环行”(Gilroy,1993:86)。
小说通过卡门纳“突出了拥护所谓西方欧洲文化——植根于对量化、地图绘制以及线性历史进步的启蒙信念的欧洲中心主义使命——文明使命的人,与那些置身于集中体现在‘中间通道’的‘居间性’空间的‘他者’之间的冲突”(Goldman,2004:15)。另外一位具有“居间性”特点的人物是博拉。布兰德(2001:20)认为“居间性”(in-betweenness)空间是一种与流散经历相伴相生、密不可分的“无法解释的空间”,就是“在脑子里有种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既没办法出去,也没办法进来的感觉。”如果说卡门纳的“居间性”主要体现在他不断追寻而不得的错置与迷失,那么博拉的“居间性”则是在过往与未来之间对当下的占有和掌控。不同于卡门纳,博拉并不纠结于一个无法找回的过去,“她看着他年复一年不停忙活,在雨中离开,去找寻特雷布扬特,回来时一无所获。她明白找寻是徒劳的”(Brand,2000:65)。她从卡门纳的地理发现中获益良多,知道了“在哪里停泊,在哪里登陆,在哪里过夜”,但“不想离开库莱布拉湾”,因为“她已经为管口鱼的和弦和鲸鱼无尽的呼吸所吸引,为环形的天空、永恒的蓝色和无穷的夜黑所着迷”(Brand,2000:62)。尽管是奴隶的后代,但她并不为奴隶制历史所累,“痛苦将会跳过她那一代……她只知道怎么不去想它”(Brand,2000:69)。博拉不仅能与母亲那代人的惨痛历史拉开距离,也善于化解自己儿女的悲伤,面对“像啼哭的鸟儿一样”啜泣的孩子,她以看似轻淡、实则饱含哲性的话语安慰道:“你们还没有开始生活,有什么好难过的?”(Brand,2000:69)尤苏尔在博拉眼中看到的是她“游向未来”,而博拉则将其理解为一种“欲望,是嘴里的一种味道,一种让渴求中的面庞凹陷下去的需要”(Brand,2000:47)。博拉既不回望过去,也不放眼未来,她所看重的是对当下的沉浸,是身体的感受和呼唤:“任何鸟类,任何空气的流动,任何眼中看到的风景,任何食物,任何石头或鸟儿的飞翔,她都要看个清楚并且垂涎三尺,垂涎它们的形状、它们的厚度、它们的红色、它们的咸味。她对自己的肉体也有欲望。她会揉捏自己柔软的大腿,用手指轻抚上几个小时”(Brand,2000:67)。奴隶制末期,曾经人迹罕至的库莱布拉湾悄然发生变化,“生活的噪音愈发明显,岛屿外围的地平线出现了一条道路,有凤凰木和锡顶的小屋”(Brand,2000:63)。然而,纵使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博拉也不为所动,“独居了这么长时间,她已经形成了一种自我中心意识,只对自己的想法感兴趣”(Brand,2000:68)。她仿佛处于一种静止的状态,独立于年轮的转动,“虽然年近九十,却还像孩子一样率真,喜怒哀乐来得快,去得也快”(Brand,2000:69)。可以说,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博拉似乎是存在于和生活在居于两者之间的停顿中”(Grandison,2010:776)。
博拉是小说叙事进程中的重要一环,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她活了一百多岁,后代遍及全球,是始于尤苏尔的庞大黑人家族的真正缔造者。博拉的随性和超然赋予她旺盛的生命力和生育力,并给予她的孩子足够的成长空间,假如她没有这些性情去关注当下,而是像卡门纳一样无法走出过去,那么这一切很难实现。博拉的经历说明“和记忆一样,遗忘也可以成为‘新世界’黑人的未来性资源,让个体和社区在无法言说的暴力面前继续生活下去”(Gantz,2016:142)。如果说尤苏尔“曾发誓再也不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用断后和抗命让兰伯特枯竭”(Brand,2000:8)是一种反殖民主义姿态,那么博拉对黑人后代的繁衍、对黑人家族谱系的构建同样是对奴隶制的有力回击。
4.0 黑人家族谱系构建
《黑色大西洋》对非洲流散研究产生深远影响,西蒙·吉甘迪(Simon Gikandi)(2014:241)称赞其出版“是二十世纪末非洲流散社会历史的重要事件。”但吉尔罗伊的理论建构并非完美无缺,对女性元素的忽视就是其受到质疑的原因之一。的确,除了莫里森,吉尔罗伊用到的例证——比如德兰尼、杜波依斯(Du Bois)和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等几乎都是男性,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偏向。安娜莉莎·欧巴(Annalisa Oboe)(2007:5)等学者指出,“认为旅行和穿越大洋能够产生对世界的全球性看法,这种观点……本身就是对黑人流散具有明确性别指向的解读,因为它主要关注的是那些已经并且依然是属于资产阶级男性特权的经历。”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1994:319-320)更是直言吉尔罗伊的理论需要修正,因为“除了个别重要例外,它聚焦的是还没有向女性开放的旅行实践和文化生产。”《月满月更之时》一方面在奴隶制历史记忆和挑战边界等方面呼应了吉尔罗伊的理论主张,同时从女性视角与其展开对话,通过构建含纳和认可女性旅行经验的黑人家族谱系拓展和丰富“黑色大西洋”的内涵。
通过追溯家族谱系确认自我身份是黑人流散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旨。布兰德在《一张通向“无返之门”的地图》中就是从家族切入来谈黑人流散的:“我来自一个大家族,关系庞杂,还有远房表亲和朋友,他们都一大把年纪了,有着相同的肤色和血缘。在那个地方,不管是谁,只要看看你的发际线,看看你歪头和走路的方式,就知道你是哪家的……我们的源头似乎在海上”(Brand,2001:12)。莫林·莫伊纳(Maureen Moynagh)(2008:62)认为,布兰德“把谱系作为奴隶制创伤的场域,而谱系就位于她的小说《月满月更之时》的核心位置。”这个判断非常准确。小说从19世纪初一直叙说到20世纪90年代,讲述了一个黑人家族近两百年的变迁史,通过呈现这个具有庞大时空架构的黑人家族谱系的生成和延展,拓宽了“黑色大西洋”的疆域。博拉的曾孙女尤拉成年后离开加勒比,移民至加拿大多伦多定居。曾孙女玛雅生于加勒比库拉索,父亲死后移居荷兰,后又随丈夫去往比利时。博拉的另外一位曾孙女科迪莉亚生于委内瑞拉,她与父母关系紧张,还早恋意外怀孕,堕胎后回到祖上生活的库莱布拉湾,希望有新的开始。科迪莉亚的丈夫格里弗斯也是博拉的后代,他出生后被带到西印度群岛的的博内尔岛,后到库莱布拉湾谋生并在那里遇见科迪莉亚。博拉的外孙索恩斯有印度血统,他的母亲是博拉与印度人拉宾德拉纳特的女儿奥古斯塔。拉宾德拉纳特有类似于“中间通道”的经历,奴隶制终结后,他作为劳工乘船从印度来到加勒比,接替黑人从事种植园劳作。可以看出,《月满月更之时》中的迁移路线十分复杂,具有突出的发散和多维特征,挖掘出隐匿在“黑色大西洋”之下或位于其边缘的路径。“通过博拉的后代,布兰德把我们导向一个更大的流散空间,一个不仅是黑色而且也有亚洲和欧洲元素的加勒比大西洋”(Garvey,2003:492)。
《月满月更之时》一方面构筑宏大的黑人家族谱系拓宽“黑色大西洋”的地理疆界,另一方面通过彰显黑人家族成员之间的维系丰富“黑色大西洋”的思想内蕴。与吉尔罗伊没有把亲缘关系作为其理论架构的核心,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把女性的跨大西洋旅行经历排除在外不同,布兰德在这部作品中与处于叙事核心的黑人女性进行了性别化的流散认同(Garvey,2003:491)。在小说绘制的黑人流散版图中,黑人女性占据核心位置,这些女性因为流散经历生活在不同时空,却总以某种方式关联在一起,表现出某种“家族相似”。尽管博拉出世的性情阻隔了母亲那一辈的苦难,但在行为方式上博拉和尤苏尔有相近之处。和博拉一样,尤苏尔也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现实之外,即便在搜集毒药准备自杀这样严肃而悲情的行为中,也表现出明显的浪漫情怀:“她就像其他人采摘花朵一样在搜集毒药……而且就如同任何收集人,任何热恋中的人一样勤勉和投入。精确又富有激情。一切新知都是精彩的。她甚至觉察到恋人们心照不宣的悲伤和忧郁,那种挥之不去的‘总觉得不够’的感觉,就像人们渴望褐雨燕、燕鸥和欧夜鹰的飞翔”(Brand,2000:1)。而在静候最佳时机以便行动前的那一刻,“尤苏尔就像一个恋人一样等待夜幕的降临,想让柔和的光线拥抱自己。她满怀希冀地望过一排排可可树,红绿相间的新旧树叶交织在一起。她想象在几公顷的成熟果园外,有爱正在等待着她”(Brand,2000:2)。不难看出,博拉和尤苏尔都能在纷扰的现实中开辟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她们的血液里都流淌着一种随性的基因。这种基因也传承到了博拉的曾孙女科迪莉亚身上。和博拉一样,科迪莉亚也忠于感官体验和本能欲求,婚后相夫教子的平淡生活让她倍感压抑:“科迪莉亚的身体对她来说就是一种永无休止的苦涩。除了那些它被赋予的用处,那些她让自己的身体承担的用处之外,她对身体的含义一无所知”(Brand,2000:122)。科迪莉亚感叹这么多年都是为别人而活,为家庭克制欲望,无暇倾听身体的召唤,积压许久的情绪最终在天命之年迸发而出:“……一种突如其来的巨大欲望占据了她。它就像一个饱满的橙子在她嘴里炸开,涌出的汁液弄湿了下巴,溅进了眼睛。她低头看着正在给一件衬衫上肥皂的手,想有人亲吻她的手指,每一根都亲,一根接一根地亲。她还想有人亲吻她的手掌,她肘部和手臂的内侧”(Brand,2000:99)。科迪莉亚追随内心,对身体感受有异乎寻常的敏感,这些性情都可以回溯至博拉。
当然,性情上的相近只是亲缘关系的一个方面,《月满月更之时》对黑人家族谱系更为深层的构建体现在女性成员对家园或先辈的主动追寻。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内化了某种创伤性缺失,这种缺失构成了他们的主体身份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Moynagh,2008:63)。这种创伤性缺失的诱因,主要是奴隶制引发的黑人流散导致的家园缺位以及对家族谱系认知的障碍。尽管博拉阻断了奴隶制给尤苏尔造成的创伤体验,她的后辈都在一定程度上生活在奴隶制的余波中,因为他们都在以某种方式寻求与家园和先辈的关联、确认自我在家族谱系中的位置。科迪莉亚的祖上对布料有天生的敏感,能够准确辨识布料的优劣,她回到故乡后经常走访一家布店,“就是为了回忆她的家族……布料的质地让她想起他们”(Brand,2000:103)。身居多伦多的尤拉留存着母亲交给自己的家族信物——博拉的一幅画,还记着母亲讲述尤苏尔“带着铁环,在树林中跛行”,自己仿佛“看到她缠绕在树藤和乱麻之中,急着在天亮前赶回”(Brand,2000:103)。作为黑人流散的一员,面对家族谱系的分化和家园的缺席,尤拉深感困扰,在给母亲的信中,她表达了对一个明晰的家族谱系和先辈居所的向往:“妈妈,我想要一条单一的世系线索。一条从你到我并可再往前推的线索,但一定是我可以追溯的线索……我想要一个村庄,一个我可以留下来而不是想离开的村庄。一个有锡顶小屋和凤凰木的村庄。就像您对我们讲的曾祖母博拉曾住过的村庄”(Brand,2000:246-247)。尤拉的女儿也叫博拉,从小跟外祖母生活,后来精神错乱,在她眼中,外祖母就是自己的母亲。外祖母死后,博拉经常产生幻觉,与复活的“母亲”对话,还遇见尤苏尔等家族先辈的鬼魂来访:“我母亲的一位访客,一个女士一瘸一拐地来我们家,一只脚好像很疼……她的脚踝套着一个沉重的铁环,脖子上绕了一根绳子”(Brand,2000:285)。这些流离在世界各地的黑人家族后代都有一种追根溯源的心理机制,他们通过对先辈和家园的自觉追寻填补“流散经历造成的起源和谱系知识的缺失”(Moynagh,2008:66),也因为这种追寻,小说铺延开的黑人家族谱系被贯穿为一个有机整体。
5.0 结语
如果说博拉作为家族传承中枢的身份说明遗忘与记忆同样重要,那么其后代通过回溯先辈和家园而对家族谱系的彰显则表明记忆的不可替代性。奴隶制时代,无数黑奴从塞内加尔附近海域格雷岛上那扇狭长的门走出,从此背井离乡,那扇门成了再也回不去的“无返之门”,经过时间的涤荡,逐渐内化为一种无根和飘零感,成为追寻家园的隐喻。对所有走过“无返之门”的黑人来说,流散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心理意义上的。布兰德曾言这扇门是一个“缺席的在场”:“尽管我们没有几个人见过它,或者下意识地重视它,这扇门在其历史关联性上是我们先辈的一个起点,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出发,也是精神层面上的付出”(Brand,2001:21)。《月满月更之时》既借助奴隶制历史记忆以及强调“路径”和“居间性”的地图绘制,与吉尔罗伊的理论构想存在契合,也通过凸显黑人女性的旅行经验及其代际维系,在“缺席”与“在场”、遗忘与记忆之间描摹出黑人流散的心理轨迹,为重返“无返之门”绘制了一张精神地图,“更为丰富地再现了在流散中作为黑人和女性意味着什么”(Ryan,2014:1230),从女性视角对“黑色大西洋”进行了再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