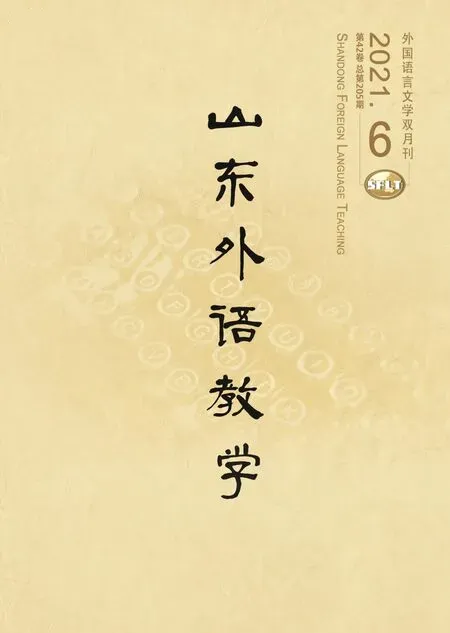美国南方“新怪谭”小说《湮灭》的后自然书写
2021-01-29张鲁宁韩启群
张鲁宁 韩启群
(南京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7)
1.0 引言
美国南方作家杰夫·范德米尔(Jeff VanderMeer)近年来创作了多部以环境危机为背景的“新怪谭”小说(New Weird)①,如《芬奇》(Finch,2009)、“遗落的南境”三部曲(The Southern Reach Trilogy,2014)、《异形博恩》(Borne,2017)、《奇异鸟》(TheStrangeBird,2017)、《蜂鸟蝾螈》(HummingbirdSalamander,2021)等。其中2014年出版的《湮灭》(Annihilation)荣获科幻文学界重要奖项“星云奖”(Nebula Award)。《纽约客》将这部作品誉为“新怪谭”小说这一文类(genre)的代表作,并称范德米尔为美国当代的“怪谭梭罗”(the weird Thoreau)(Rothman,2015)。近五年来,范德米尔受到全球科幻迷们的热烈追捧,被视为“当下最受欢迎的新怪谭小说家,或许也是目前受欢迎程度仅次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科幻小说家”(Strombeck,2019:348)。他在南方生态文学界也颇受欢迎。著名南方研究学者杰·沃特森(Jay Watson)高度评价了包括《湮灭》在内“遗落的南境”三部曲的环境伦理价值,认为主题“发人深思”,讲述了“物种之间、甚至可能是跨越星际的思辨寓言故事,令读者感到恐惧又着迷”(2019:265)。
在作品质量参差不齐的科幻文学界,范德米尔能够得到主流文学批评界的高度关注和肯定,这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很不常见”(Prendergast,2017:336)。换言之,若范德米尔只是像多数硬科幻作家一样,单纯运用怪物杀手、地球爆炸等传统科幻元素,那么他可能最多成为好莱坞编剧邀约的对象,不会成为文学批评界的关注目标。那么将环境破坏、人与环境的关系作为创作主题的范德米尔在小说创作中如何敏锐地回应所处时代、所处南方地域的生态危机?其生态叙事为何成为近五年来生态批评界的研究重点,甚至被认为代表了生态小说创作的“新趋势”(Prendergast,2017:334)?本研究拟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将范德米尔置于美国南方生态文学创作和评论语境中加以观照,挖掘范德米尔作品的生态意义和审美价值。
2.0 21世纪美国南方环境危机与范德米尔的后自然书写
21世纪以来,美国南方和世界其它地区一样“进入人类世”,“气候变化、碳排放、化学物质排放、臭氧层消耗、气溶胶负荷、生物多样性减少、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不断恶化的洪涝和干旱”等各种全球性环境问题同样影响到南方各地区(Vernon,2019:1)。除应对当代人类的共同环境挑战,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因素使南方比美国其它地区遭遇更多环境危机,如美国南部沿海以及密西西比河沿岸地区多年来持续遭受洪水威胁和化工污染,阿巴拉契亚山脉为开采煤矿而推行山巅移除计划,给当地带来巨大生态灾难。以杰夫·范德米尔为代表的南方作家积极回应21世纪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美国南方特有的环境威胁,通过环境危机书写回应了人类世时代南方环境危机现实。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范德米尔定居的佛罗里达州近年来面临海平面上升、飓风灾害等环境威胁,但州长瑞克·斯格特(Rick Scott)却禁止该州环保部门使用“气候变化”一词。2017年《异形博恩》出版不到两个月,特朗普于6月1日做出决定正式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范德米尔以“新怪谭”书写方式想象了南方环境发生灾变的末日情景,试图以文学创作形式向公众和漠视环境威胁的政府部门发出警示,体现了扎根南方环境危机语境的文学创作者的使命感与人文情怀。
范德米尔在多部作品中表现了不同类型的环境危机,因此被评论界誉为近五年来生态文学界“集文学创作、科幻体裁和环保主义于一体”的环境危机叙事典范(Prendergast,2017:334)。著名生态思想家家蒂姆·莫顿(Timothy Morton)也曾在公开场合表达对范德米尔创作的赞赏以及对其环保意识的认同②。无论是《湮灭》中因生化污染导致生态灾难的X区域,还是《异形博恩》中遭受海平面上升、生化危机等多重环境灾难的城市,都以一种沉重、充满环境警示的叙事呈现了人类当下面临的环境危机。而“遗落的南境”三部曲背景设置在美国南部,且靠近海域,更是暗示了范德米尔所在的三面临海的佛罗里达州的环境危机现状。在《湮灭》呈现的X区域中,环境遭到严重污染,到处弥漫着有毒物质,身处其中的人类最终以悲惨的方式“湮灭”,赋予该小说明显的后自然书写特征。“后自然”一词是生态文学批评领域的重要术语,常被批评界用来指涉文学作品中所传达的“污染如何改变人类的地球经验”(Deitering,1996:196);“后自然”世界指的则是人类曾经赖以生存并认同的自然已经不复存在,污染物笼罩整个地球的末日景象(Mckibben,1989:59-60)。在《科幻小说理论与生态批评》中,坦尼亚·拉封丹(Tania Lafontaine)给“后自然”下定义时,特别强调后自然是“被技术或人类干预所改变的自然”(2016:8)。她以科马克·麦卡锡的科幻小说《路》为例,分析了该小说中因遭到环境污染而呈现的后自然景观。由此可见,尽管“后自然”概念可能有不同的理论源头,但均强调了技术改造、环境污染导致地球生态恶变的现实,核心理论支撑源自“自然与人工、生物与技术的交汇和融合”(Lafontaine,2016:14)。
《湮灭》为“遗落的南境”三部曲的第一部,主要讲述了四名女性科学家组成的勘探队深入南部国境边界一处无人区考察的故事。该地区环境若干年前遭到污染后发生变异,“具有一种强大的超自然致变因素”,能“导致生物形态的改变”(范德米尔,2019:194)③,进而形成一处具有明显后自然特征的“X区域”。虽然小说未明确X区域的具体位置,但从“南部国境”、毗邻海岸、多沼泽河流等文本细节可以推测,X区域大致位于美国南部国境边界。此外,从第一人称叙事者生物学家的零星讲述看,此处发生了类似生化污染的“特殊事件”,政府的解释是“由于军事科研实验而导致的局部环境灾变”(113,114)。小说中含糊其词的表述若隐若现地指向了一个环境危机现实:科技公司和权力精英往往是生化类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这些彼此关联的因素使得该小说既可以被理解为作家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回应,也可以理解为对美国南方地域环境污染现实的批判。那么范德米尔究竟如何借助后自然书写表现南方环境危机,传递发人深省的环境警示?本研究拟从小说中X区域非人类环境的后自然特征、后自然世界中人类的“湮灭”两部分深入考察范德米尔后自然书写的叙事机制,以此透视小说的生态价值以及作家的环境伦理观。
3.0 X区域非人类环境的后自然特征
《湮灭》中最值得关注的非人类环境书写是一片遭到生物污染的X区域,也是小说中最能集中表征后自然特质的文学地理场域。与前文提到作家麦卡锡作品《路》当中的后自然书写相比,两部作品均呈现了不明原因导致的环境灾难以及自然环境不同程度的退化。但如果将两部作品仔细对比,《路》所呈现的后自然世界不再有高科技元素,文明彻底崩塌,不明原因的灾难几乎摧毁并剥夺了所有生命,废墟般的大地上只剩下包括一对父子在内的少数幸存者艰难求生;而《湮灭》的后自然世界里,依然存在以南境局为代表的科技公司或权力精英,遭到人类技术干预和污染的X区域在文本中与这一权力中心形成平行和并置。在后自然书写策略上,两部作品都以科幻想象形式书写了遭到破坏的自然环境,作家麦卡锡更多地以“自然主义笔法”书写了灾难后的末日景观以及灾难环境对父子自由意志的剥夺(Gibbs,2020:69),而《湮灭》的后自然书写不但通过各种奇怪、变异物种书写烘托后自然世界怪异、恐怖的审美特征,还着力描写非人类环境的活力,从而将读者引入21世纪环境危机背景下人与环境关系的哲学新思考。
范德米尔把X区域非人类环境的观察主体设置为一位受过环境生物学专业训练、熟谙生态系统变化机制的女生物学家,这种布局不但赋予了小说浓郁的生态意味,也体现了范德米尔新怪谭科幻创作的独特叙事格调。在女主人公出场之前,小说开篇第一段以类似云端俯瞰的全知视角宏观呈现了X区域具有明显后自然特征的空间布局和丰富地貌:依次经过黑松林、沼泽和湿地之后,在“湿地和自然水道以远,便是海洋”;“稍远处的海滩上”,则是那座处于小说叙事核心的“废弃的灯塔”(2)。紧接着,随着第一人称视角的切换,读者很快就陷入女生物学家以不经意口吻提及X区域奇特迹象时所营造的恐怖气氛:该地区“曾经有城镇存在”,如今只有“破破烂烂的小屋,红色屋顶已然塌陷”(4)。X区域沦为不再适合人类居住的无人区的细节一方面呼应了该地区环境发生异变的后自然特征,另一方面也为接下来陆续出现的变异物种书写埋下伏笔。当科考队进入一处废弃村庄时,小说借助女生物学家的观察直接呈现了苔藓地衣等植被的基因变异,不但“高达四五英尺”,而且变异成了人类的模样,“构成类似四肢、头颅和躯干的形状”(113)。此外,小说还通过女生物学家丈夫的记录间接呈现了X区域一只剪嘴鸥的变异和罕见行为:“试图利用退潮时露出水面且嵌满牡蛎的岩石杀死一条大鱼”(203)。最能体现后自然怪异特征的是一只“比平底锅还大”的罕见六指海星。这只变异的海星外形奇特,不但“浑身覆满粗棘,身体边缘隐约可以看到精致透明的纤毛,尖端呈翠绿色”,而且“在静止的水中透出暗金色光芒,仿佛燃烧的火焰”(211)。这些变异物种的书写不但赋予了小说怪异、恐怖的新怪谭特征,而且传递了深刻的环境伦理价值,呼应了当今世界人类干预和改变自然而产生各种怪诞物质的现实。
当下生物科技快速发展,人类通过基因编辑等技术实现生物改造,这种干预和改变自然的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产生很多后自然世界的伦理危机。曾经只在科幻小说中出现的怪异物种越来越多地在现实世界中出现,如在美国匹兹堡“后自然历史中心”博物馆中所陈列的怪异标本,包括无肋骨的幼鼠胚胎、能产出“生物钢”的转基因山羊等②。此外,受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因素影响,近年来媒体关于怪异物种的报道也日渐增多,如日本福岛核泄漏后附近海域出现怪异鱼类和不规则形状的水果蔬菜,受到塑料微颗粒污染的人类胎盘等。现实中因环境污染或技术改造出现的怪诞物质呼唤对应的文本想象和全新叙事方式。在此背景下,X区域怪诞物质书写以及作家的新怪谭科幻体裁,可以理解为既是范德米尔对当前各种生物技术不加节制的利用可能会催生怪异物种的隐忧,也是作家本人面对具有后自然特征的环境现实时在生态叙事策略上的调整,这种调整有效拓展了生态叙事的写作路径。
除了怪异物种书写,《湮灭》的后自然书写还有一个明显特征,即在书写怪异生态系统的同时,尤为强调非人类环境的活力。在小说第一章,当介绍完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四位女科学家进入X区域开始科考后,范德米尔并没有完全顺应读者期待立即安排科学家们开始勘测解密工作,而是透过女主人公的视角呈现了X区域非人类环境的重要特征。通过环境生物学家的视角呈现,X区域“生态系统非常复杂”,存在着“数次过渡”;“六七公里的徒步距离内,森林过渡到沼泽,又过渡到盐水湿地,然后是海滩”(12-13)。在部分生态学者看来,环境系统的“过渡”实则对应了生态系统本身不因人类意志转移的自适应性,是环境系统中各因子力量相互作用动态过程的外在表现,正如德国著名博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所言,“一切活着的有机生物毫无例外地是有感觉的,它们会区分外界的情况,并通过体内的变化作出某些反应”(2005:120);除了环境系统的“过渡”体现了非人类环境的活力,X区域所发生的生态扰动也同样体现了这种活力,如该地区出现了“适应微咸淡水的海洋生物” 、一起“共享生存环境”的水獭和鹿、逐渐适应此地居住环境的“巨型爬行动物”等(13)。之所以将生态扰动也理解为是非人类环境的活力,原因在于这种扰动的发生动因源自该地区环境在遭到外来因素干预后所做的变化和调整,这一调整过程揭示了非人类环境本身所具有的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活力。
强调非人类环境活力是范德米尔新怪谭创作中一贯秉承的创作美学,正如他在论述新怪谭小说创作的美学专著《奇迹之书》中所言,“故事发生的地点和空间并不是被动的、惰性的,也不仅仅是行为的背景”;相反,“它们拥有能量和活力”(范德米尔,2018:241)。在《湮灭》的非人类环境书写中,范德米尔不但践行了他关于非人类环境有“能量和活力”的创作美学,还将这种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活力提升为小说中的重要生态元素,从两个不同维度传达了其作为生态意识浓厚的科幻作家的环境伦理观。首先,对于非人类环境活力的强调实则强化了读者对于物的力量的认知,从而增加“生态敏感性”,即“对某些物的力量更加警觉,如云、食物、化学物质、金属、药品等,包括它们的声音、气味、无声运动、节奏和动力”(Watson,2013:149);其次,通过将物的活力、所导致的怪异生态系统、后自然世界相关联,范德米尔呈现了受到毒物污染后非人类环境的连锁生态反应,借助充满诡异惊悚的后自然书写激发读者对隐形异类之力量的恐惧,从而实现科幻恐怖和环境伦理的巧妙结合。
4.0 后自然世界中人类的“湮灭”
在《生态批评与南方研究的未来》一书中,美国南方学者弗农(Zackary Vernon)指出,在全球生态系统破坏日益严重的今天,学术界需要更多地关注作家笔下的后自然书写,而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学术界要研究后自然状况越来越严峻的世界会带来哪些文化影响”(2019:2-3)。而所谓的“文化影响”则更多地是指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从南方环境危机现实来看,美国南部沿海地带以及密西西比河沿岸地区分布了众多石化企业,生产诸如“化肥、汽油、油漆和塑料”等化工产品,其产量“占到全国所有石油化工产量的近四分之一”(Beverly, et al.,1994:114)。这些石化企业导致美国南部某些地区“癌症发病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十八倍”(Beverly, et al.,1994:123-4)。位于巴吞鲁日(Baton Rouge)和新奥尔良之间的著名“癌症谷”正是因为其空气、地面、河流中各种致癌物和毒素超标而得名。在《湮灭》中,X区域也是一个充满毒物的地理空间。侵入人体的“寄生生物和真菌子实体不仅能导致妄想症,还能造成精神分裂和逼真的幻觉,从而引起行为错乱”(162);此外,X区域的环境毒物会引起细胞突变,返回的队员最后几乎都死于全身性癌变。由此可见,在《湮灭》所呈现的后自然世界中,不但华兹华斯笔下可以疗愈人类心灵的自然无处可觅,而且自然在以人类想象不到、或者更为恐怖的方式侵袭人类身体;处于后自然世界的人类最终的“湮灭”也是最强有力的环境警示:滥用科技对人类而言无异于自取灭亡、自掘坟墓。
进入X区域考察的人类主要为四位科考队员,其中包括一名生物学家、一名人类学家、一名勘测员、以及一名心理学家。此后,小说通过女生物学家的观察或具身经历展现了先后来到X区域的人类的悲剧结局,呈现了后自然世界中人类的不同“湮灭”形态。第一种是通过废弃村庄书写展示了X区域环境发生灾变后对长期定居于此的人类的毁灭性影响。小说呈现了曾在此处生活的人类用过的厨房、客厅和卧室等,人类曾经使用过的物品,如“儿童玩具”“腐烂的衣服”“残破的桌椅”等细节(116)将读者的思绪拉回灾难发生之前人类的日常生活,引发读者对灾难带给人类灭顶之灾的想象。第二种是前几批进入X区域的科考队员的悲剧结局。小说中虽没有逐一交代之前科考队员如何受到后自然世界X区域的影响,但从女主人公断断续续的叙述可以推测历任科考队员几乎都离奇死亡。这些队员“游荡回自己家中”,最终“以某种未知方式从X区域消失”(4);女生物学家的丈夫在归来后的六个月“被诊断出患有无法手术切除的全身性癌变”,勘测队的其他成员“最后也都死于癌症”(69)。原本身体健康的人类在进入X区域后患上癌症,而癌症的病源正是由于细胞变异并发生转移,暗示了X区域内含有对人类身体造成严重伤害的毒物。
从小说叙事时间看,第一种、第二种人类悲剧的时间轴点处于现任科考队员迈入X区域之前,是一种间接展示人类悲剧的文本叙事方式,而第三、四种则直接展示了现任科考队员的悲剧结局。第三种是借助生物学家第一人称视角观察的同期其他三位科考队员的悲剧结局。小说从一开始就通过前任科考队员的诡异死亡方式铺垫了小说中现任科考队在X区域可能遭遇的不测,而随着情节的发展,已有阅读期待的读者还是被新怪谭高手的悬疑、恐怖、奇异情节所震撼。心理学家的死亡始于一个充满悬疑的意象,即“隐藏的区域里伸出一只脚”(144);而等到女生物学家开始近距离接触心理学家时,发现被毒素感染的她已经处于濒临死亡的状态,“无法完全控制面部肌肉”(152)。为了渲染被毒物感染后的恐怖,小说近距离地呈现了刚刚死亡的心理学家的古怪伤口:“从锁骨到肘部,她的胳膊上长满了纤维状的茸毛,呈金绿色,发出淡淡的荧光”(161);即便死后,毒物依然在扩散,以致“伤口的荧光比先前更加强烈”(168)。更令读者感到不寒而栗的是女生物学家所观察到的人类学家的尸体。除了“脑袋呈现出不规则的轮廓”,“浑身覆盖着一层浅色的有机组织,就像会动的毯子”;当女生物学家“俯身凑近观察”时,“发现那就是寄生于墙上文字间的细小手形生物”(207)。小说通过濒死、已死两种不同“湮灭”形式的叙事呈现,暗示了被真菌类微生物感染后人类的悲剧,从而让读者产生“怜悯和恐惧”情绪,这种心理在悲剧心理学家朱光潜看来,“是在对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审美观照中产生的恐惧”,会促使人类“感到自己的无力和渺小”(2018:121)。小说中的真菌微生物毒物虽然肉眼“看不见”(11),但却有着吞噬人类身体的巨大破坏力,因此更容易激起读者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以及对人类渺小的感慨,进而唤起人类保护环境、慎用科技的生态伦理意识。
最后一种人类悲剧书写是该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在感染真菌类微生物后最终“湮灭”的不幸事件。整部小说的五个章节围绕这一核心事件设计,五个章节的标题“起始”“融合”“献祭”“浸渍”“消融”清晰地勾勒了女主人公如何被体内毒物一步步侵蚀的恐怖过程。在第一章“起始”中,生物学家下到灯塔后为了近距离观看墙壁上“真菌或其他真核生物”而将身体靠前,不小心吸入真菌所喷射出的“一小簇金色的孢子”,瞬间感觉到“有东西钻进了鼻腔,腐败蜂蜜的气味儿在短促的瞬间陡然增强”(29)。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叙事者除了皮肤会“毫无来由地忽然泛起阵阵刺痒”(135),而且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体内逐渐增长的“光亮感”,常常“如同惊起的飞鸟一般”不断“从肺部窜上来,直抵咽喉”(204)。在讲述毒物如何渐渐吞噬身体时,范德米尔通过环境毒物与女主人公的“跨躯体”纠缠呈现了后自然世界中人类身体与环境毒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交换和转换,让读者意识到之所以污染物能产生致命的威胁,原因在于人类身体本身就是物质性存在。正如哈罗德·弗罗姆(Harold Fromm)所言:“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环境’像无尽的波浪一般涌动,贯穿我们全身,如果我们通过一个理想的微观延时视频来观察自己,我们会看到水、空气、食物、微生物、毒素进入我们的身体,而我们再把经过身体加工过的物质排出、排泄和呼出”(1997:1)。
在上述四种人类悲剧形式书写中,受毒物侵犯的身体“湮灭”过程被范德米尔以新怪谭恐怖形式呈现,无疑是最间接、最有力量的环境警示。小说有几处细节提到真菌微生物在人体内扩散,在破坏身体正常机制时,还会构筑“与外表看起来一模一样”的新组织。这种复制从叙事者丈夫的日记中可以得到印证,部分人类身体出现基因变异,蜕变后成为复制人。换言之,这里出现了具有典型赛博格意义上的后人类,而后人类正是后自然环境的产物,被认为与“后自然”概念有内在关联,“后人类是后自然环境的一部分”(Lafontaine,2016:14)。作为科幻小说中一个常见元素,克隆人具有典型后人类特征,其生态价值在于对人的概念发出挑战,指涉21世纪以来科技快速发展,尤其是生物基因改造和人工智能导致的人类、自然、科技之间界限日益模糊的现实,正如凯瑟琳·海勒丝(Katherine Hayles)所言,在后人类世界,肉体存在与计算机仿真模拟、赛博机械体与赛博有机体、机器人目的论与人类目的论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或绝对界限(1999:3)。通过后自然世界中的后人类书写,实际上也是小说对人类在掌握基因修改技术后引发的伦理危机和生态灾难的隐喻性反思。
5.0 结语
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生化技术、纳米科技等新兴科技快速发展,给人类带来生存危机和伦理困境的同时,也迫使人类重新审视长期以来以“我”自居、唯“我”独尊的人类中心思维,重新定义人与非人类环境之间的关系(韩启群,2020)。范德米尔在《湮灭》中重新审视了当前环境危机语境催生的人与物质环境关系,传达了他对于美国南方生态环境渐趋恶化,日益变成后自然世界的忧虑。尽管都表现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后自然世界,《湮灭》不同于作家麦卡锡小说《路》中生命迹象几近消逝的后末世景象,而是更多地呈现了因人类干预和改变自然后产生各种怪诞物质,进而构成其笔下后自然书写区别于传统科幻叙事、乃至传统环境危机叙事的重要特征。就后自然书写中的人物塑造而言,作家麦卡锡小说中一路向南的父子成为后自然世界中人类重返文明的希望,但范德米尔的后自然世界中的人类以不同方式“湮灭”。在诠释后自然概念核心特征的同时,将科幻恐怖与环境伦理融合在一起,通过人类在面对周围世界时的渺小和失控倡导绿色价值观。通过悲剧性的结局警示,小说在消解人类中心地位的同时,传递了宇宙万物相互依存、混溶共生的生态理念,进而强化了21世纪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核心内涵。
注释:
①“新怪谭”小说以真实复杂的现实世界为原型,被定义为是一种“融合了幻想、恐怖和科幻小说”特征的文学体裁。详见A. VanderMeer & J. VanderMeer, 2008: xvi.
② 2016年莫顿和范德米尔在美国路德学院助理教授安迪·哈格曼(Andy Hageman)主持下进行网络对话,表达认同彼此作品的生态思想和美学价值。
③ 引文出自杰夫·范德米尔:《遗落的南境1:湮灭》,胡绍晏译,成都:天地出版社,2019年。以下引文仅标明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④“后自然历史中心”(Center for PostNatural History)位于美国匹兹堡市宾夕法尼亚大道4913号。该中心致力于文化、自然和生物技术之间相互作用的知识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