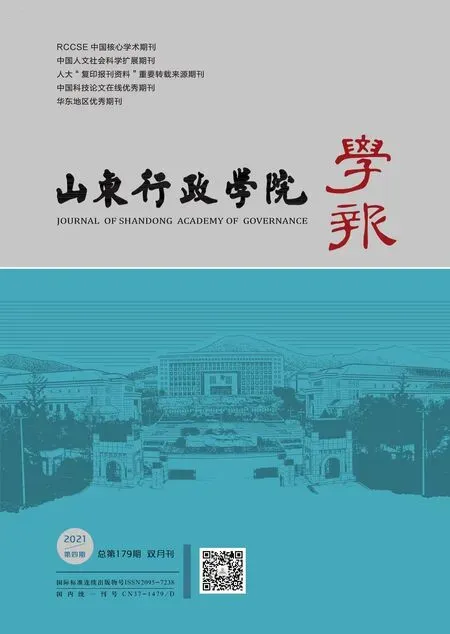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海外研究及启示
2021-01-29文吉昌
文吉昌,刘 佳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哲学与文化教研部,南京 210046;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国际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91)
自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后,海外学者对其进行高度的关注和研究,通过对理念的来源、指向、挑战等进行了高度聚焦,来理解中国新时代外交理论的创新和未来走向。对海外学者的理论成果进行梳理,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倡议的态度,也能够帮助我们在海外视角下反思自身宣传策略,找到更容易与国际社会对接的沟通和宣传方式,使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得以顺利推广,在更大范围内获得认知与认同。
一、海外学者积极评价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世界意义
在海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都能够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分析,并认为在当今时代之问日益凸显之际,中国适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这体现出中国勇于承担大国责任,积极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中国对“时代之问”的回应
西方开启的全球化已经持续500多年,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获得了利益,促进了经济发展,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模式也带来了很多发展问题,例如全球化进程不平衡,很多国家不仅没有从全球化中获利,反而受到了一些损害。当前世界上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凸显了这一问题。世界上不约而同地发起“世界怎么了?”“人类何处去?”“我们怎么办?”等“时代之问”。恰在这一时刻,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海外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回应“时代之问”积极推动全球化向更好方向发展的表现。比如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学者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认为:“中国所努力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的发展方向,中国的倡议具有引领性,为世界呈现了国际间交往的新模式。”(1)Hua Xia,Commentary: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All Humankind. Xinhua,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7-03/20/c_136142216.htm. September 1th,2019.埃塞俄比亚学者科斯坦蒂诺斯(Berhutesfa Costantinos)曾经指出:“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的发展导致国际间的关系发生变化,需要以新的思想构建国际间公共权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可以有效平衡国际间的复杂利益诉求。”(2)王守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契合非洲发展需要》,《人民日报》2017年1月23日。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体现出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力求以合作、求共赢的思维,共同解决当前全球治理中出现的问题;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贡献在于,中国提出了一种系统性治理格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3)Timothy Heath,China Pushes Global. US News & World Report. January 20th. https://www.usnews.com/opinion/world-report/articles/2017-01-20/china-stressed-a-growing-interest-in-global-trade-and-governance-at-davos. July 17th,2019.。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中国贡献的先进理念
很多海外学者认为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源于中国自身发展经历。近代中国经历被侵略、被压迫,贫穷落后的历史。尽管当前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屡屡突破发展瓶颈,走向复兴之路,但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战争、贫困、灾难等问题有更加深入的体会和感知,也因此期望能以自身发展经验、智慧为人类共同发展作出贡献。例如,英国学者凯瑞布朗提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人们之间有了更好的沟通,‘一带一路’倡议是试图让中国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需要听,因为中国发展有其独特发展历史,而且在全球日益重要。我们要听中国在向世界传递的信息,听中国讲述自己的模式和整体轮廓,尤其是倾听‘一带一路’倡议体现出的中国与世界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意愿,以及中国贡献自己的经历、经验的意图;世界应当对中国叙事予以回应。”(4)Kerry Brown,The Belt and Road:Security Dimensions,Asia Europe Journal,vol.16,No.3,2018,p.219.韩国学者宋大元指出:“习近平多次强调讲好中国故事,创新中国话语,通过参与全球治理来发挥中国在世界和平、全球发展和全球秩序构建中的重要作用。”(5)Song Daekwon,Xi Jinping Thought Vs. Deng Xiaoping Theory. https://thediplomat.com/2017/10/xi-jinping-thought-vs-deng-xi-aoping-theory/.September1th,2019.不论是从回应“时代之问”还是从“中国担当”的角度,这些从客观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研究的学者认识到当前的中国对人类共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哈佛大学教授尼尔·佛格森(Niall Ferguson)指出:“有些人反对中国的治理政策,这些人都是完全不了解当今的发展现实,中国在经济 、网络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为全世界带来了新的理念。”(6)Andrew Moody,UK Hailed for Closer Relations with China. China Daily. 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5-10/20/content_22226232.htm.September 1th,2019.英国卡迪夫大学教授罗杰·阿万·斯库里(Roger Awan-Scully)也指出:“较长时期以来,全球经济发展低迷,人们必须抱团取暖,建立休戚与共、生存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才是明智的出路。”(7)焦翔、刘睿、林芮、张朋辉、黄培昭:《指明方向,用行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7年1月23日。
总结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词汇和学术话语,受到海外学者们的共同关注。广大海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评价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国自身的努力,特别是在共同体建设的实践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强对外友好传播的力度,让中国故事、中国情感、中国风格能够真实地传播到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发现了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并且对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模式产生了研究兴趣和价值认同,很多海外学者认为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出于友好的动机,是当代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世界大同思想”的一种继承。法国学者高大伟(David Gosset)和芬兰学者马蒂·普兰(Matti Puranen)等人,在论述人类命运同体理念时,都提到了“天下一家”的治理模式(8)Matti Puranen,Tianxiaist Ideology and the Emerging Chinese Great Power Identity,Journal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7,No.1,2019,p.19.。这些高度评价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海外学者,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考察延伸到中国现当代的发展模式上来,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思想根源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坚定信念。从现阶段来看,很多国家、地区都受到“逆全球化”的影响,构建了经济贸易壁垒,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世界一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处于一种小规模的经济发展格局中,这些小规模和不成体系的自由生产很难超越区域性“逆全球化”思潮的侵蚀。很多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海外学者,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有着深入的了解,他们感受到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世界新秩序构建的决心,比如有的海外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产生处于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9)Denghua Zhang,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in China’s Diplomacy,Pacific Policy Studies,Vol.5,No.2,2018,p.200.,是时代的产物,是可以为世界性难题提供治理方案的新思想。从这些积极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海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支持来自于他们对全球性问题的担忧,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人口发展不均衡、环境污染加重、生态资源枯竭、局部战乱频发、难民数量激增和生物安全隐患等。海外学者们认为,这些全球性问题不是当今西方模式所能够解决的,甚至很多问题都是由西方模式无序治理而产生的。而近几十年,中国一直努力进行对外友好传播,让世界各国学者理解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模式,比如从1978年到199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模式逐渐从传统的“美苏模式”中解放出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政治宣传模式,通过建立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创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精简外交机构,改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等一系列工作,中国国际形象塑造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模式的对外传播形式更加丰富,央视媒体进入海外发展,很多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以及报刊杂志都开设了国际版,中国的大众传播、电信网络也逐渐在海外找到立足点,中国传媒已经在国内外形成了新的信息生态和网络文化生态,并以此为基础,通过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信息知识与中国价值观念。在近几年中国模式的对外传播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成为重要的传播内容,海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和理论的认同与接受,直接受到中国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力度的影响。应该看到,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开展和理论的构建并非一帆风顺,在复杂的国际思潮影响下,仍有一些海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存在疑惑。
二、海外学者客观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面临的挑战
海外学界不仅积极评价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而且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面临的挑战也展开研究,其中不乏一些启发和建设性建议。
(一)可能受到敌对势力的歪曲和抹黑
有的学者认为,一些敌对中国的势力向来存在零和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也很有可能被带入中国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事实上有的学者往往带有“竞争思维”和立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态度主观臆断;还有的学者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认为中国的相关倡议对美国未来世界影响力提出了挑战,强调美国要严肃对待中国的各项对外政策,抑制中国的对外发展。这些论调主要表现于两方面,一是认为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目的意在抵制美国的影响力,例如美国乔治城大学学者奥丽亚娜·马斯特罗(Oriana Skylar Mastro)认为:“中国对印度的很多外交策略都是在吸引美国的关注,试图削弱美国对印度及其周边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并取而代之。”(10)Oriana Skylar Mastro,The Stealth Superpower:How China Hid Its Global Ambitions,Foreign Affairs,Vol.98,Iss.1,2019,p.31.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学者扎克·库珀(Zack Cooper)同样认为:“中国的国际战略目的在于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中国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取得亚太地区的管理权,中国总是不断地打破传统,挑战现实。”(11)Andrew Shearer,Thinking Clearly about China’s Layered Indo-Pacific Strategy.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73. Iss.5.(March),2017,p.305.另一种抹黑论调认为,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着眼于亚洲,而是意在挑战当前国际秩序,形成一种以中国话语为中心的新国际秩序。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已然不满意只是接受世界秩序,而是期望能够参与缔造世界秩序。”(12)Richard Weitz,Understanding China’s Evolving Role in Global Security Challenges.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September,2009,p.82.还有一些激进抹黑论调成为“中国威胁论”的一部分,认为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崛起”以后,要求按照中国自身利益改变国际秩序,比如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认为:“中国不断扩张自己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如此发展下去,中国必将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重塑世界新秩序,以往的制度和规则都将被改写成符合中国的价值观标准。”(13)Evan Feigenbaum,Why China’s Highly Strategic Brand of Revisionism is More Challenging. https://macropolo.org/reluctant-stakeholder-chinas-highly-strategic-brand-revisionism-challenging-washington-thinks/. September 1st,2019.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中国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中国单方面的构想,这种构想来源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定位,认为中国试图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重写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则,“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设想最终的目标是构建全球新制度,这种制度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很大的融合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是亚洲共同体,这表现了中国希望成为亚洲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的管理者,通过掌控亚洲局势来辐射全球,以此方式确保中国在亚洲的核心地位和自身发展的安全。”(14)Andrew S. Erickson,Is China Pursuing Counter-Interven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8. No.3.(October),2015,p.145.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推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阻碍
有一些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前景持保守的态度,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践当中会遇到来自客观和主观方面的阻碍,这将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行面临巨大挑战。部分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推行将在未来面临很大困难,以“一带一路”实践为例,其沿线涉及范围广泛,情况复杂,不仅存在不同的语言、宗教、知识背景,而且在国际关系上还存在很多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障碍可能使“一带一路”受挫,进而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得到响应与反馈。例如澳大利亚学者卓少杰(Sow Keat Tok)认为:“亚洲的经济格局与政治体系已经固化,很难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有效的发展空间。”(15)王灵归、赵江林:《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挑战与未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85页。美国学者米格·凯瑞斯(Miguel Carreras),在2017年发表了题为“公众对于中国在拉丁美洲崛起的态度”一文,研究中对中国在拉丁美洲影响力进行了调查,尽管调查结果非常积极,认为中国未来十年在拉丁美洲影响力将持续上升,但研究中也提出了一些担忧,并认为,中国在拉丁美洲影响力的提升面临很多阻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化差异较大,拉丁美洲有时可能难以理解中国提出的理念(16)Miguel Carreras,Public Attitudes toward an Emerging China in Latin America. Issues& Studies:A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in China,Taiwan,and East Asian Affairs. Vol.53. No.1.(March),2017,p.70.。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部分国家的领导人以及相关学者对中国未来的国际影响力持有怀疑的态度,因而对中国外交倡议采取排斥甚至抵触的观点。例如,美国学者彼得·洛夫特斯(Peter Loftus)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否得到响应有待观察,有些邻国可能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共同发展机遇,但也有可能认为中国在整个地区扩展影响力将对其构成潜在威胁,比如日本就不希望中国在该地区发挥领导作用(17)Peter Loftus,How China’s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Will Change Asia. http://www.dukenex.us/peter-loftus-how-chinarsquos-community-of-common-destiny-will-change-asia.html. September 1st,2019.。英国学者哈师·庞特(Harsh Pant)指出:“印度受到自身经济低迷和政治低效的束缚已经失去了发展的自信,陷入了安全的困境,以至于他们对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任何周边活动都看作对印度自身发展的威胁。”(18)Harsh Pant,Rising China in India’s Vicinity:A Rivalry Takes Shape in Asia. in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9.no.2,2016,p.364.兰德公司报告指出,一些亚洲国家并不信任中国的实力,倘若中国寻求地区主导地位的努力未能充分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其邻国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某些国家已开始抵触中国的倡议(19)Michael J. Mazarr,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Rand,2017,p.xiii.。出于这些客观障碍和主观疑虑,这些学者对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持消极态度,认为该倡议可能前景挑战重重,难以得到顺利推进。
从海外学者的担忧中可以看出,西方国家部分学者对中国模式、中国理念都存在一些误解、误判,少部分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为了缓解“中国崩溃论”的难题,当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没有发生“崩溃”的征兆时,部分海外学者又提出了中国威胁论,包括“潜艇威胁论”“环境威胁论”“文化殖民威胁论”等。通过研究可以发现,部分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研究并不深刻,甚至很多研究充满了误解,海外学者凭借自己原有的学术知识来分析中国相关的国际新闻,以此得出结论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和政策进行评价,这种研究模式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海外学者在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等中国思想、中国模式时都受到了各个国家意识形态霸权的影响,海外学者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范式都突出了区域性的特色,受到个人成长背景的影响,这些范式鲜明地表现出美国范式、欧洲范式和亚洲范式三大特点,以欧洲学者为代表的研究范式在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时表现出专业性与学科化的叙事方式。相关海外学者始终从中国学、汉学出发来研究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发展模式问题。亚洲的研究范式以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的学者为代表,这些学者热衷于从地域文化、民族认同的角度来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基础与理论基础。但美国范式的研究却突出了鲜明的意识形态战略特征,美国学界最初对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问题的研究都起源于情报的搜集,美国政府在研究初期投入大量资金扶持,使得美国研究范式从发展速度上和影响力上都突飞猛进。但部分美国学者仍旧采用研究苏联和东德的模式来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更多的研究精力投入在中国军事发展、经济转型、网络科技创新、地缘政治矛盾等领域上,并刻意构造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违背的价值观念来消解全球共识,这些都是美国范式中所产生的负面效果。面对研究者及其国际背景的复杂性,中国学者要头脑清晰的进行辨认,要引领海外学者从区域性和学科性上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要努力化解国际上意识形态冲突在学术理论研究上带来的负面效应。
三、对海外学者思想认识的反思与审视
总体来讲,大多数海外学者都能够公正、客观地对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中有很多启发性内容,为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提供了良好的参考。然而,同时也要看到,海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也存在着碎片化倾向,很多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与实质等方面的理解存在盲点和偏差。
(一)海外研究的启发性内容
海外学者在近几年的研究中越来越重视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他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指向、挑战等方面进行了聚焦,其中有一些研究结论对我们有直接启发,能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策略提供借鉴。另外,这些研究的分布也存在一些规律,这些规律反映了一些海外情况以及我们的短板,能够为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行策略提供一些间接启发。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方面具有一些优势,一方面,他们能够站在国际视野上对中国进行审视,看到中国自身难以发现的情况和问题;另一方面,他们有条件及时了解海外情况和反应,能够为中国提供更快、更准确地反馈情况。因而,他们所提出的建议对中国完善自身策略十分重要。尤其是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行的挑战因素研究,海外学者掌握的资料和信息相对较全面,角度多元,应当是我们借鉴的重点。例如,美籍华人学者王铮指出,国际间的交往并不能仅仅依靠金钱和政治的交换而获得长足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互利、坦诚相待都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念基础之上,从某种程度上看,文化软实力的构建要比经济和军事的发展更加具有说服力。“中国能否实现‘一带一路’的发展目标,能够构建出完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系,很大一部分因素在于中国能否带领‘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参与者一同构建国际间的良性交往文化。通过对共同文化的培养,中国可以快速高效的实现世界新秩序的塑造。”(20)Zheng Wang,China’s Altemative Diplomacy,The Diplomat. January 30th,2015. http://thediplomat.com/2015/01/chinas-alternative-diplomacy/. September 1st,2019.除了一些直接建议以外,通过对海外学者的研究梳理也可发现,他们的研究实际上也有分布规律,这些规律间接上反映了一些海外情况和问题以及我们的一些短板,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间接启发。这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地区分布凸显地区态度差异。通过上文分析可见,相对来讲,不同地区学者态度差异较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者、欧洲以及大洋洲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持积极态度的人较多,认为中国能够为人类提供有效方案和思路。而印度地区、日本地区、美国地区持消极态度的人相对较多,认为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带给本国的消极方面多于积极方面。与此同时,不同地区民众态度差异也较大。一些学者对不同地区民众的态度也做了调查,并认为非洲、拉丁美洲对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支持度较高,在这两个地区推行的未来前景也相对乐观。例如上文中提到,米格·凯瑞斯(Miguel Carreras)在2017年发表了题为“公众对于中国在拉丁美洲崛起的态度”一文,文中通过对公众的调查数据的分析,展现出中国在拉丁美洲影响力的确有所上升。当调查对象被问及当前哪个国家对拉丁美洲影响最大,结果有54%的人认为美国在拉丁美洲影响力最大,19.7%的人认为是中国。作者认为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因为20年前,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是非常之小的,现在却有五分之一认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相比较之下,印度对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只有0.71%。除此之外,当被问及未来十年哪个国家对拉丁美洲影响最大,结果43%的人认为是美国(较之前调查数据下降11%),而27%的人认为是中国(较之前调查数据上升7.3%),因此作者认为,未来十年,中国在拉丁美洲影响力提升将是必然,中国的倡议在拉丁美洲也会引起回应(21)Miguel Carreras,Public Attitudes toward an Emerging China in Latin America. Taiwan,and East Asian Affairs. Vol.53. No.1.(March),2017,p.8.。这些研究都对我们未来战略实施提供了重要参考,一方面要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推行信心,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要注重地区差异,设计区域化推行策略。
第二,研究内容分布凸显我们传播的短板。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发现,海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并非面面俱到,而是存在研究的盲点。例如,海外学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挑战、意图方面研究较多,但在理论渊源、内涵、中国未来举措等方面的研究十分匮乏。这方面缺陷凸显出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海外传播方面的短板,显示出我们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来源、实质和具体制度化方案等方面的传播不够,使海外难以全面掌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因此我们在未来应当避免单纯地宏观上进行概念阐释,而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面化、细节化传播。
(二)海外研究的偏差性内容
尽管海外学者理论研究中蕴含着大量的启发性内容,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一部分研究内容也存在着一些认知偏差,这集中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研究:
首先,很多海外研究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指向存在认知偏差。这体现在一些学者以零和思维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在“中国威胁论”论调下阐释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此类思维与我们中国提出命运共同体的共赢思维相悖,没有从中国文化中传承至今的“天下一家”“天下大同”文化视角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其次,一些海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图存在认知偏差。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发现,还有些学者对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图也存在认知偏差,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目标是挑战美国影响力,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意在重塑国际秩序。实质上,这些学者没有以辩证的方法认识“变”与“不变”的关系,一方面他们只关注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变”的部分,而忽视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变”的部分,忽视了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出于改善性目的而非颠覆性目的;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看到“变化”是事物发展的常态,国际秩序也只能在变化当中得到发展。当前几乎所有系统内部成员都在不断探索完善之道,不仅中国如此,作为国际秩序设定者的西方国家亦是如此,而一些“后起之秀”的国家在未来也必将提出改革意见。由于缺失这种辩证思维,有一些海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研究有所偏激和夸大化倾向,误解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意图。
对于这些认知偏差,我们需要正确看待,尽管不可排除一些恶意抵制和抹黑,但对于很多海外学者来讲,导致误读的原因主要来自客观原因。从对方角度来讲,海外学者可能由于地缘差异、语言差异、信息沟通不畅等原因难以全面地掌握中国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除此之外,海外学者毕竟成长于海外社会和文化的浸染中,与我们的文化差异和理论背景差异明显,这使得他们有时不能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中国的理念。从中国角度来讲,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中还缺乏对命运共同体进行深度、细致化的阐释,这表现在我们在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重点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目标等内容,而对于我国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展开的制度化设计、进程、反馈等方面的细节报道相对较少,这导致海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了解只能停留在表层,而无法理解其深层含义,更无法全面地掌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行的具体步骤和未来预期。这无疑为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海外推行增添了困难。因而,对于这些认知偏差,我们不应当回避,也不能一味批判,而是应有借鉴海外经验的思路,尽快形成国内普遍共识的理论框架,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化。与此同时,还要利用国外视野反思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行策略,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际社会更好地实现对接,尽量消除鸿沟、促进理解。唯有如此,才能将海外研究纳入中国理论框架之下,推动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研究逐渐深入和完善,更好地为中国外交实践提供参考与建议。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理论发展需要突出的三种特质
鉴于海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研究,中国学者在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过程中要重点突出三个特质。第一个特质是共识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存在最大意义就是为全世界提供一种价值共识的理念,或是提供一套价值评价的体系;以此调和、缓解当代世界各国人民因价值观念冲突而产生的地缘政治矛盾和恐怖主义活动。第二个特质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观,这一特质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建构必须具备大历史观、将中国与世界各国放在全球生态有序发展的格局中进行思考,如此才能建构出一种共治共赢共享的理论形态。第三点就是该理论的正义性,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博爱等“普世价值”在当今世界性难题的挑战中趋于弱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构建需要突破西方“普世价值”的瓶颈,为全世界提供一种新的价值评价的体系和标准,通过对人的主体性、群体的公共性和社会空间的正义性等问题的切入,为国际秩序的重塑提供理论基础。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理论发展必须突出全球共识
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只有彻底才能够说服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价值观念之所以在全世界遭到了不同的评价,是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形成和传播仍处于起始阶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理论之所以在现阶段具有被构建、完善的可能性,正是因为疫情时期,国际关系变化、国家安全战略转型、世界性群体运动膨胀等一系列重大变化,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感受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现实基础。通过对海外学者相关理论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发展面临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进行有效阐发,通过哲学话语的转换和创新,更加有效地让海外各界人士产生价值观念上的共鸣;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吸引力的提升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扩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世界影响力,让世界各国人民在认识、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基础之上,形成一种价值共识,并且自发、自觉地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实践的过程之中,把自己变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仰者和建设者。第三个问题,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如何在未来的理论发展和社会实践中凸显出中国的特色,呈现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问题。包括上述在内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发展所必须完成的课题,而从本质上看,首要的问题还是打好理论基础,要在基础学科理论上,尤其是哲学辩证逻辑的推导中构建出凸显中国智慧又适合当下世界变局的创新理论。面对这些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相关理论理论在未来的构建必须突出全球共识性。2013年以来,国内学者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中国外交实践经验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理念加以提炼、融合,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渊源,构建了具有中国立场、中国视角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以此为基础,该理论的研究对象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同时也涉及到一些具体领域的理论与实践,比如生态文明建设、精准扶贫、党的建设、海洋文明等。伴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不断深化,该理论几乎与当代中国所有的社会科学问题产生理论上的关联,但是作为一种开放性的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要向内不断深化,在理论的延展性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相关理论还必须能够解释、解决当今世界新秩序建设、国际间矛盾冲突等问题时才能真正被全球理论学者所认同和接受;如此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构建必须具备国际视野。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结构性的调整,布雷顿森林体系、雅尔塔体系逐渐崩塌,国际间权力冲突增加,美国在全球影响力逐年提升,直到2001年“911”事件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的政治经济与价值观念才逐渐形成了世界影响力,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和谐共生成为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从2019年底开始,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这加快了旧有的世界体系与世界秩序的崩塌,权力均衡问题、单边与多边问题、国际贸易摩擦问题不断激增,全球各国和人民都需要一种新的价值理念来修正或替换被疫情所摧毁的经济自由、白人至上、民粹主义等理念;全世界需要一种更具广泛性又具有真理性的价值观共识。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构建就是整合全球各种思潮与观念,通过唯物史观对其进行批判与继承,为全世界提供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评价标准与共识性的价值理念。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理论发展必须突出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
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的逻辑就是一种大历史观,通过这种思维模式从整体上来研究全球性问题,构建一种“全球观念”和“天下体系”,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下,海外学者们所担心的“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以及很多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都能够获得不同程度的消解。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历史向世界史的转变直接影响了未来人们唯物史观研究的逻辑转变和方法论转变,而这种转变的过程伴随了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相关理论作为以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世界历史观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也必然关涉到当代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所带来的全球经济伦理问题。全球经济伦理从某种程度上看就是一种利益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在20世纪中叶以前,这种经济领域的“普世价值”都是由欧美国家主导构建,导致欧美模式成为了现代化的唯一模板。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通过对世界历史观的把握以及对当下全球性难题的分析,突出一种非欧美单一性价值评价的“共同价值”体系,在现实实践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指导人们按照多边自由贸易的原则来进行国际交往合作,在价值理念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又强调了平等、开放、共商、共赢的重要性。马克思认为世界史观的形成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实现的,全球生产力的提升是世界史观得到认同的重要驱动力,伴随着世界市场的创新发展,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被逐一打破,人类文明开始了广泛的交流,地区性的价值共识逐渐代替了民族性的价值共识。地区性的价值共识源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全球生产模式的趋同以及全球制造体系逐渐成熟,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发展也必须将全球生产模式、国际生产体系等方面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通过对以世界为工厂、全球分工合作的生产体系的研究,研究者们可以从人类利益共同体的构建深化到生态共同体、地区共同体、网络共同体的构建上,精准提炼不同领域价值观念共识形成的基本过程和基本规律,从而在世界史观的领域中构建一种全息化、结构性的世界生产体系和世界普遍的价值观念,最终总结提炼出具有共识性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范畴。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理论发展必须突出理论的正义性
从美国“911”事件到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显现的更加直白,世界贫富差距拉大、地缘冲突加剧、全球生态环境质量遭到破坏、难民数量不断增加,所有的这些世界性问题都与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紊乱有着直接关系。国内很多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仪的重要使命就是研究这些世界性的难题,并按照马克思所构建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信念,构建一种符合当代世界发展实情并能合理解释问题、消除矛盾的理论体系。当年,马克思就分析过这些难题的根本原因,指明资本主义经济对世界秩序的破坏主要来自于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肆意剥削,工人阶级将自己的生命和时间都用来为资产阶级进行劳动,自己的付出远大于社会对他们的回报,这种不对等的劳动关系,非正义的生产方式使得资产阶级从被剥削者手中“窃取了文明”(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页。。今天,资本主义产生了很多新变化,其生产、分配等多方面表现出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明显差异,但是本质上这种非正义的生产、交往、消费的模式没有变。面对这些现实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相关理论也要做出正面的回应,要能够突出理论建设的正义性特点,更突出一种平等的价值观念,这种平等性不仅是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平等,更加强调了社会制度为人们带来的机会平等。西方很多政治哲学家都从平等性原则入手来讨论社会的公正问题,比如罗尔斯所强调的平等自由原则以及机会均等原则等,很多西方理论者希望调节国家、政府的工作职能来营造一种平等的社会环境,并将具体的实践过程称作正义。与罗尔斯相类似,西方正义理论的创作者们如诺奇克、桑德尔等学者的理论虽然理论形式多样,观点多元,但关于社会正义的主题都与政治权力和自由市场相关。西方的正义理论一直受困于个人权力与国家权力、自由市场与集体治理的矛盾中,这是因为多数理论学者始终关注于抽象的人性,没有将日常生活中,参与社会实践的、真实的人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从这一点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构建,要立足于现实的人的基础之上,要摒弃西方传统政治学思维中研究抽象的人追求抽象的自由民主的思维逻辑,形成一种将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等统一在一起的系统性理论。
五、总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目的是为了推动全球各个国家开展国际友好合作,在新的世界格局下构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完善传统的国际交往体系。海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研究,始终没有中国学者在相同研究领域研究得深刻,但是海外学者却在不同的视角上为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总体来看,海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是处于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上,但仍有少部分学者受到不同地区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对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产生了误解和偏见。
面对新冠疫情的挑战,全世界各个国家都面临相同的难题,不论是世界经济复苏、世界生物安全、国际间的生物医药产业融合等问题,都不是某个国家可以单独完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就是要凸显出国际间友好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也要努力消解海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的误解。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夯实其理论基础,特别是加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领域问题的深入探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相融合,彰显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在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中的重要地位。除此之外,还要注重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实践领域的落地,使之直接嵌入全世界热点难点问题中;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逻辑来解决世界性难题,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述话语来解释世界新格局的发展趋势,以此方式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在全世界人民心中的价值认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