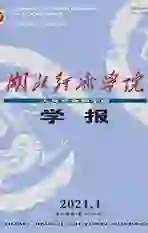《福楼拜的鹦鹉》的非自然叙述声音及其后现代人文特征
2021-01-25葛佳美赵秀兰
葛佳美 赵秀兰
摘 要:《福楼拜的鹦鹉》是英国当代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的代表作,该部小说的出版标志着巴恩斯打破了传统传记的线性写作方式,创造了一种新的混合体小说形式。非自然叙事是后经典叙事学中的一个新领域,纵观《福楼拜的鹦鹉》一书可以发现非自然叙述声音对于后现代小说文本构建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旨在分析该小说中的三类非自然叙述声音,探讨非自然声音对于后现代小说文本形式创新的作用,进一步揭示巴恩斯小说中的后现代特征及其人文内涵。
关键词:巴恩斯;《福楼拜的鹦鹉》;非自然声音;人文内涵
一、《福楼拜的鹦鹉》及其研究背景
《福楼拜的鹦鹉》是当代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 )的代表作,该小说的出版标志着巴恩斯在小说创作艺术与形式上的革新,打破了以往巴恩斯小说传统的线性结构,是巴恩斯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福楼拜的鹦鹉》一经出版,就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关于这部作品到底是传记还是小说的争论。巴恩斯在这部作品中大胆地对小说艺术形式的创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对于小说形式“零散化”的追求。此外,该部小说对于传统历史和真实概念的解构也契合了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质疑”的特点。
早在1989年巴恩斯小说《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出版之时,美国作家欧茨(Joyce Carol Oates)曾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指出,“巴恩斯是完美的人文主义者,而看上去是前或后现代主义者类型(pre-post-modernist spices)。”?譹?訛近些年来,一些国外学者也逐渐关注到巴恩斯小说中的人文内涵并展开相应的研究,梅里特·莫斯利(Merritt Moseley)在其第一部有关巴恩斯的专著《理解朱利安·巴恩斯》(2009)中就立足于人文主义研究传统,揭示巴恩斯作品中的人文关怀。正如梅里特·莫斯利在书中所说:“《福楼拜的鹦鹉》的主人公布拉斯韦特怀疑找出‘真正的鹦鹉的可能性,但是他不会就此认为没有真正的鹦鹉,他承认无法理解他妻子的生活,但并不否认生活的现实性”[4]88。“人”这一内涵在巴恩斯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福楼拜的鹦鹉》《英格兰,英格兰》和《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这三部作品深刻地反映出巴恩斯的人文关怀及其对“人”自身历史身份困境的思考。由此可见,《福楼拜的鹦鹉》不仅标志着巴恩斯小说创作形式的革新,更反映出巴恩斯对传记中人文内涵与人文关怀的大胆转变与追求。因此,本文试图从小说中的非自然声音展开深入地分析,旨在揭示这种非自然叙述声音不仅体现了巴恩斯小说的后现代性,更反映了巴恩斯对于后现代“人”这一内涵的深刻思考。
二、《福楼拜的鹦鹉》的非自然声音及其后现代性
《福樓拜的鹦鹉》中包含着大量的叙述声音,既有第一人称布拉斯韦特的主线叙述,又有巴恩斯作为隐含作者的上帝视角叙述,以及福楼拜传记故事中的亚故事人物叙述。这些声音区别于传统单一的人物传记小说叙述声音,让本应处在不同空间的多重叙述声音在巴恩斯地刻意安排下出现在相同的叙事空间之中。巴恩斯用不同人物叙述声音刻画了一个全面的福楼拜形象,使整个小说的叙述声音呈现出一种典型的“非自然”状态。
(一)多重叙述声音的并存
“多重叙述(multiple narration)”是西方文学史上一个惯用的叙述手法,在小说中并置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使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引起读者的共鸣。美国知名叙事学家布莱恩·里查森(Brian Richardson)认为,多重叙述的文本在不同的叙述位置上不断漂移,其叙述形式是模糊不定的,虽然有走向某个种类的倾向,但是却从不安分于任何一个种类,由此导致了多重叙述文本的二元对立:即“向心文本”(centripetal text)和“离心文本”(centrifugal text)[11]71。巴恩斯把《福楼拜的鹦鹉》这部小说构建成了一个典型的离心文本,以布拉斯韦特的第一人称叙述为主线,并置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使整个文本不断生产出多种不同的异质对立视角,为小说的叙述增加更多的可能性。
首先,《福楼拜的鹦鹉》一书以主人公布拉斯韦特的叙述作为主线展开,布拉斯韦特在追寻福楼拜鹦鹉的真假性过程中不仅叙述了自己的查证经历,更是戏仿福楼拜的故事在文本中插入了自己的故事。布拉斯韦特曾在小说的第七章时就提到:“我心里有三个故事争着蹦出来。一个是关于福楼拜,一个是关于埃伦,一个是关于我自己”[6]102。正如布拉斯维特所说,巴恩斯在小说中巧妙地向读者展现了三个故事,一个是福楼拜客观信息的呈现,一个是有关他妻子埃伦的故事,而另一个则是他探寻福楼拜鹦鹉信息的真实经历。在以布拉斯韦特为主线叙述的视角下,他探寻福楼拜信息的真实经历以及自己妻子埃伦的故事在其以“我”的第一人称叙述中娓娓道来,使整本小说充满虚构小说的叙事性,更像是一部叙事小说。
其次,小说中除了布拉斯韦特的主线叙述之外,还有另一条重要叙事线索,即福楼拜信息的客观呈现。小说中插入了年表、考卷、词典等文体形式,使其打破传统小说单一的文体形式,极具后现代性。就叙述人称而言,在对福楼拜信息客观呈现的几个章节中,小说以第三人称“他”的方式向我们讲述了福楼拜的生平经历以及性格特征,符合传统传记小说写作手法。在小说第四章中,作者以第三人称“他”指代福楼拜,以动物意象象征的方式展现福楼拜与几种动物性格的关联特征。此外,小说多次出现以布拉斯维特为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的交流,例如第三章中:“你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定义网,这取决于你的视角。”[6]40巴恩斯巧妙地运用第二人称“你”的形式,拉近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阅读距离。小说中并置的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使整本小说区别于传统传记小说,既像是一本以福楼拜为写作对象的人物传记,又像是一本以布拉斯韦特为主人公的叙事性小说。这种多重叙述声音的并存,创新了传统小说的写作方式,使《福楼拜的鹦鹉》在叙述位置上不断飘移成为典型的离心文本。
(二)矛盾叙述声音的对立
《福楼拜的鹦鹉》中存在多对互为矛盾的叙述声音,从不同人物的声音中塑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福楼拜人物形象。首先,巴恩斯作为整个文本的隐含作者在叙述福楼拜年表时声音具有互为矛盾性。小说的第二章以年表的形式呈现了福楼拜的生平,并按序号1、2、3的顺序把这一部分分成三个独立的福楼拜年表。年表1以积极的态度评价了福楼拜辉煌的一生,而年表2从反面以消极的态度塑造了一个消沉颓废的福楼拜形象。以福楼拜的出生为例,年表1从福楼拜1821年出生开始说起,“居斯塔夫·福楼拜出生,家里的次子……这个家庭属于成功的职业中产阶级,在鲁昂附近有几处房产。这是一个稳定开明、催人上进而且心怀大志的家庭”[6]21。反观年表2对于福楼拜家庭的叙述,与年表1的叙述基调大相径庭。年表2从1817年福楼拜的两个兄长相继去世说起,进而写到居斯塔夫·福楼拜的出生,指出福楼拜家庭出生的孩子身体都很虚弱,他的父母本以为福楼拜也活不长,这样的叙述与年表1的叙述声音形成了鲜明的矛盾性。随后,年表1与年表2以两种极为矛盾的声音对福楼拜的一生展开叙述,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彻底地推翻前者塑造的积极向上的福楼拜形象,让读者琢磨不透作者的态度。例如1832年福楼拜在鲁昂学院学习这一事件,在年表1的叙述中福楼拜的学业出色,尤其精于历史和文学,但在年表2中却说到1839年福楼拜因行为粗鲁、不守纪律被鲁昂学院开除。这种矛盾的叙述声音被巴恩斯刻意地安排在同一个章节中出现,后者打破了因前者的叙述在脑海中形成的积极的福楼拜形象,使整个小说的叙述呈现出典型的非自然性。
此外,让福楼拜故事中的人物发声,也是巴恩斯刻意营造出的一种与人们刻板印象中福楼拜形象相矛盾的叙述声音。露易丝·科莱是福楼拜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她是福楼拜多年的情人。在以往有关福楼拜的记录中,露易丝·科莱被定义为一个爱吃醋,爱胡闹的女人,使福楼拜极为头疼,这一点在杜康有关福楼拜的记录中曾提到过。同样,小说第十章中,巴恩斯在文本中再次插入了作者的声音,他说道:“让我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她(科莱)讨人嫌;她听上去就像讨人嫌的样子;虽然必须承认,我们只听到了居斯塔夫一方的说法”[6]169。随后,巴恩斯似乎是为了证明对科莱的这种偏见是因为仅听到了居斯塔夫一方的说法,接下来的一章他让科莱从女性的角度说出自己眼中的福楼拜形象,这是一种与居斯塔夫·福楼拜的说法相矛盾的叙述:“有朋友说,露易丝,你必须以牙还牙,像他那样撒谎。但是我不想如此”“我并不需要居斯塔夫进入我的生活,请看看事实”“让我告诉你居斯塔夫是如何羞辱我的”“最后我渐渐相信,他最希望从我身上得到的,是一种智性的伴侣关系,是精神上的恋爱”[6]171。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小说的这一章节通过露易丝·科莱站在女性角度上的叙述,表达出与福楼拜男性一派不同的观点,质疑了科莱被扭曲的女性形象以及福楼拜形象的真实性,与上一章节中对露易丝·科莱这一女性形象的叙述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文本外声音的介入
除小说中人物叙事声音的并存性与矛盾性以外,文本外声音的介入也是巴恩斯在《福楼拜的鹦鹉》中反映出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文本外的声音不仅有作者声音的闯入,也有世俗声音的介入。这些声音混合杂糅在一起,让读者从多个方面了解到福楼拜的真实形象。
首先,巴恩斯在小说伊始就以注解的形式交代了小说的背景以及叙述者身份,这种形式使巴恩斯作为真实作者与读者之间在非虚构层上进行了一次叙事交流?譺?訛。作者声音的闯入,符合了历史编年体元小说中作者声明自己创作过程的特点。巴恩斯在小说开篇以作者闯入的声音交代了自己的创作过程,使整本小说富于文本性与故事性,揭开了小说“虚构”的本质,从而区别于传统人物传记小说,实现传记小说由“实”向“虚”的转换。其次,小说中对世俗声音进行了收集,在小说指控一章中,作者以举例的形式,把众多质疑福楼拜形象的声音一一列举在了文本之中并用序号排列出来,再从布拉斯韦特的视角出发对福楼拜形象进行辩护,这种辩护似乎让读者置身于法庭之中,被告是福楼拜,布拉斯韦特作为福楼拜的辩护律师一一驳回福楼拜的罪证。巴恩斯巧妙地插入这些批判性的观点,使读者看到一个更加全面的福楼拜形象。与传统传记小说单一的表述不同,福楼拜的缺点与优点都被很好地囊括进这部小说中,不仅打破了传记小说的创作形式,也让呈现出来的福楼拜形象更加全面和立体。
三、巴恩斯对后现代“人”的思考
通过分析《福楼拜的鹦鹉》中混杂的非自然声音可以看出,这些非自然声音的出现不仅表现出该部小说极具特色的后现代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后现代特征背后巴恩斯对后现代社会的发展及其对“人”这一内涵的深入思考。
(一)客观历史的追寻与个人完美主义的破除
《福楼拜的鹦鹉》中两条主要叙事线索交替出现:一条是以布拉斯韦特自身经历出发,探寻福楼拜鹦鹉真假性的過程;而另一条则是福楼拜信息的客观呈现。探索福楼拜鹦鹉真假性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福楼拜历史的追寻,而福楼拜信息的客观呈现也是一种对福楼拜历史的再现过程。巴恩斯以布拉斯韦特为主要叙述者,通过布拉斯韦特的所见所闻,生动地呈现了他对福楼拜历史的探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布拉斯韦特从一个医生化身为历史的侦探家,把自己所获得的客观信息全部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布拉斯韦特还以自己的声音叙述了许多有关他妻子的故事以及个人经历,使他对历史的追寻过程变得小说化和戏谑化。这些历史信息既有客观的历史依据,也有主观上的臆测,让人们眼中的历史走下神坛。在描述布拉斯韦特的亲身经历中,巴恩斯还巧妙地插入了福楼拜的客观信息,比如小说的第二章用三个矛盾的非自然叙述声音来构建完整的福楼拜年表。正如前文所分析的,这三个不同基调的年表从互为矛盾的视角展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福楼拜形象,由此证实历史的多维性。因此,巴恩斯在《福楼拜的鹦鹉》中通过对不同叙述声音的控制,给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思维角度,进行一种历史的反拨。相比于传统历史叙事来说,正是因为巴恩斯对于历史的戏谑化描述,降低了读者受作者观点影响的程度,使读者能够更加客观地认识历史。由不同的非自然声音传达出的不同基调的信息全部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更能认识到事情的全貌。通过各种各样的人物叙述声音,巴恩斯在小说中呈现出福楼拜的优点与缺点。比如第三章中前两个互为矛盾的年表,从相反的角度呈现出一个矛盾的福楼拜形象;第十章更是收集了众多指控福楼拜缺点的声音,让读者更能清楚地认识到福楼拜作为一个人有其不可避免的人性上的缺点,从而打破人们对于个人完美主义的信仰。
(二)女性形象的建构与反拨
露易丝·科莱是福楼拜的情人,在传统福楼拜传记中,作家片面地定义了科莱的女性形象。相反,在《福楼拜的鹦鹉》一书中,巴恩斯巧妙地让科莱用自己的声音说出她与福楼拜之间的故事。这种非自然的叙事声音重塑了科莱的女性形象,质疑了在男性视角下科莱被扭曲的女性形象。在“布拉斯韦特的庸见词典”这一章中,露易丝·科莱这个词条被定义为两种矛盾的说法,一种是男性视角下,科莱的无理取闹、胡搅蛮缠的人物形象;而另一种定义与前一种定义截然不同,认为科莱是勇敢大胆、充满激情、饱受误解的女人。这无疑是对露易丝·科莱女性形象的重新建构与反拨。就整个英国的女性史来看,二战以后妇女独立意识高涨,第三产业逐渐兴起,女性劳动力需求的大量增加提高了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20世纪下半叶,妇女在福利制度下取得独立地位,家庭不再是她们的生存依托。到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社会的男女之间逐渐实现客观平等。因此,纵观20世纪的小说,女性意识的不断觉醒与女性形象的重新建构成为文学创作上的一大热潮。《福楼拜的鹦鹉》就露易丝·科莱长期在以福楼拜为主的传记中被误解的形象进行反拨,不仅体现了巴恩斯对于女性话语权力的关注,更是迎合了社会女性地位提高的浪潮。
四、结语
《福楼拜的鹦鹉》是朱利安·巴恩斯的代表作,也是巴恩斯写作生涯的一个转折点。除主线叙述声音外,巴恩斯在小说中插入了许多非自然声音,从而打破了传统传记小说叙述声音的单一性,构建了一个全面的福楼拜形象。这些互为矛盾或互为补充的声音,使整本小说极具戏剧性和后现代性。小说主人公布拉斯韦特探寻两只福楼拜鹦鹉真假性的过程,体现了人在追寻历史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表明对历史的追寻应从多角度去考察,进而建构一个较为全面的历史人物形象。从布拉斯韦特在对福楼拜信息的探寻过程中可以发现,福楼拜作为一个人也并不是完美的存在,打破了现世社会对于个人完美主义的信仰。此外,巴恩斯在小说中让露易丝·科莱以第一人称叙述声音再现她与福楼拜之间的故事,使其长期受男性话语压迫的女性形象得到重新建构,体现了巴恩斯对于女性权利的关注。探讨《福楼拜的鹦鹉》一书可以发现,巴恩斯不仅是一名后现代主义作家,也是一名后现代人文主义者。
注 释:
See Joyce Carol Oates, “But Noah was Not a Nice Man”, i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http://www.nytimes.com/1989/10/01/books/but-noah-was-not-a-nice-man.html?pagewanted=all
曼弗雷德·雅恩(Manfred John)曾在其著作《叙述学》中提出叙事交流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非虚构的层面,指超越叙事文本范围的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之间的交流;第二个层面是叙事话语层,指叙事文本范围内的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的交流;而最后一个层次则是行动层,指文本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交流。
参考文献:
[1] Frederick M. Holmes. Julian Barnes New British Fiction[M].New York: Palgrave Mac Millan,2008.
[2] Julian Barnes. Flauberts parrot[M].London: Vintage Books,1984.
[3] Matthew Pateman. Julian Barnes, Writers and Their Work[M]. Plymouth: Northcote House Publishers Ltd, 2002.
[4] Merritt Moseley. Understanding Julian Barnes[M].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9.
[5] Peter Childs. Julian Barnes[M].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1.
[6] 朱利安·巴恩斯.福楼拜的鹦鹉[M]但汉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7] 但汉松.福楼拜的鹦鹉[J].当代外国文学,2016,37(2):148.
[8] 贺宥姗.时空编织——论《福楼拜的鹦鹉》中的主体探寻[D].北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18.
[9] 刘丽霞.后现代语境中的西方朱利安·巴恩斯研究评述[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7,(3):16-27.
[10] 聂宝玉.不可靠叙述和多主线叙事——朱利安·巴恩斯小说《终结感》叙事策略探析[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35(10):54-58.
[11] 尚必武.非常規叙述形式的类别与特征:《非自然的叙述声音:现当代小说的极端化叙述》评介[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 31(2):67-74.
[12]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3] 申丹.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