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造园:明末清初江南士人的园林书写
2021-01-23彭志
彭 志
【内容提要】士人对构筑园林始终秉持着浓厚的兴趣,肇端于魏晋南北朝,迄于明清,渐渐形成了悠久的造园传统。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造园风尚特征表现为高质量园林建筑井喷式出现,专擅造园的艺术家不断涌出,以及总结性的理论著述不断出版。太仓的王锡爵、王衡、王时敏祖孙三代接续营建南园,王时敏更是新拓了东园,成为了可供探究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家族式园林的精致案例。聚焦并细读王时敏在明清易代前后的园林诗歌创作,具有较为明显地从园居宴游之乐到隐居黍离之悲的嬗递过程。通过此视角的选择、考察,则“时代氛围—造园行为—士人心态—园林书写”四者间的错综关系,或可得到较为清晰的呈现。
回望古代士人的日常活动空间,除了周旋于各种具有官方属性的衙署之外,在任之时,尤其致仕以后,往往喜好营建各式的私人园林。这一方园林既是外在错综世界的投射,也是在疲惫之余心灵休憩的自在港湾。园林之于士人身心具有多重作用,或者是在宦海浮沉之后,将园林幻视为山野河源的移植,寄托着大隐隐于市的诉求;在隐逸之中寻求修身养性,涤荡俗世尘念;或者是在园林中化身农夫,在耕种、浇灌及收获作物中体验士、农两种身份自如切换的惬意,同时在现实层面,也可达至敬老养亲的夙愿;或者是在园林中结伴游观,赏鉴山石、竹林等景观,依凭共同兴趣点的维系,可实现与人沟通交际的目的。不论是向内的隐逸修身,还是向外的游观社交,抑或居于两者之间的耕作养亲,士人骨子里颇有建造并绘制、书写园林的癖性。在关涉园林的众多诗文书画中,颇可得见士人的心态变迁及社会的盛衰演进。概言之,一方园林空间,便是士人内心深处、纷繁大千世界的缩影。
对于园林的观照,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层面。首先便是聚焦于园林建筑的物质实体,包括亭台楼阁、山石溪水、奇花异草的设计,这是属于建筑学范畴的探讨。其次是对园林中所涉物体的描写、表现,包括园林文学、山水花鸟画等,这可归于交叉学科范畴下的考察。再次是超脱园林实体、园林文本,而是聚焦于造园的人,以及在园林中游赏流连者,这是能够发掘出更深内涵的解析层面。当然,以上三个层面彼此之间并非是完全剥离的,而是相互缠绕的错综关系。明末清初是社会遭逢大变动的时代,这种变动不仅体现为北方满清政权取代了汉人长达两百七十多年的朱明政权,更是在思想上发生了涉及各个层面的启蒙。于此时代背景下,园林更是成为了乱世中士人寻求全身远害的途径。竞相造园,以及书写、表现园林成为了一时风尚。明末清初各地的造园风潮中,尤以江南最盛,也最能代表私家园林特征。
一、梳理与表现:士人造园传统与江南园林风尚
士人造园传统由来已久,其轨迹的起点至少可以上溯至魏晋南北朝,彼时身在庙堂、心系山水成为士人普遍推崇的行为方式;而为实现这两者间的无缝对接,构筑园林成为了最好的选择。声名较著者如刘,《宋书》卷八十六载其“以世路纠纷,有怀止足……经始钟岭之南,以为栖息,聚石蓄水,仿佛丘中,朝士爱素者,多往游之”[1],在铺叙遭逢乱世的背景下,强调造园是士人安身立命的方式,更突显了园林实为士人交际的重要场合。再如名士纪瞻,《 晋书》卷六十八载其“厚自奉养,立宅于乌衣巷,馆宇崇丽,园池竹木,有足赏玩焉”[2],表现了纪瞻作为襄助司马睿建立东晋的重臣,享有在南京建造豪华园林的待遇。
唐朝时,士人造园在奔放昂扬世风的推动下更是走向了繁盛局面。我们所熟知的唐朝大诗人,往往多有营建私家园林的行为。如王维精心建造的辋川别业,能够因地制宜地将蓝田林泉风光融进花草树木中,更是连缀以《辋川闲居》《归辋川作》《别辋川别业》等诗,呈现那些令人瞩目的山水田园景致。再如白居易贬谪江州时,于庐山北麓香炉峰下倾心建造的草堂,并亲撰《草堂记》予以介绍造园缘起及追求旨趣:“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太原人白乐天见而爱之,若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为草堂。”[3]客居之地的景色与故乡别无二致,正是吸引白居易于异地另辟草堂的原动力。
两宋时,在重文轻武政策的导引下,士人的身份得以进一步提高,在处理政务之余,也多将闲暇时间投注到建造园林中去。《东京梦华录》卷六载“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4],足可见彼时造园之风的盛行之状。不仅作为富庶的国都如此,其余地方也不遑多让,如临近南宋都城临安的吴兴,造园也很盛行。周密《吴兴园林记》有载,“山水清远,升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其俊秀安僖王府第在焉,尤为盛观。麓中二溪横贯,此天下之所无,故好事者多园池之盛”[5],竞相造园,可见一斑。
到了明清两朝,特别是明末清初之时,造园之势风靡无比,单就江南地区而言,顾凯《明代江南园林研究》以方志等文献中所涉园林数据进行了一番统计,“园林营造遍布江南各地,而一些地区尤其突出。如在苏州,明代有记载的约二百六十处,其中府城内八十多处的园林,大部分为这一时期所建……在绍兴,祁彪佳《越中园亭记》,所记当时绍兴园林有一百七十六处之多”[6]。其中既有对明代江南造园整体情形的介绍,也关注了某地园林的高密度出现。
若进一步将园林建造的观照聚焦于明末清初的江南地区,则诚如童《江南园林志》所言:“吾国凡有富宦大贾文人之地,殆皆私家园林之所会萃,而其多半精华,实聚于江南一隅。”[7]具体而言,江南地区在明末清初造园风气盛行的表现约略有三端:其一,高质量园林建筑井喷式出现,如苏州一地便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环秀山庄、怡园、惠荫园、西园、瞿园、羡园等堪称精品代表的园林不断出现;其二,专擅造园的艺术家不断涌出,《江南园林志》特别提及了“明之朱三松、清初张南垣父子、释道济、王石谷、戈裕良等人,类皆丘壑在胸,借成众手,惜未笔于书耳”[8],这些艺术家在一方天地里叠山理水,将自然界里的无限风光搬演进园林之中;其三,总结性的理论著述不断出版,如林有麟《素园石谱》、周漫士《金陵琐事》、文震亨《长物志》、计成《园冶》等书的椠版,提出了构筑、赏鉴园林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如《园冶》卷一中的“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宜,愈非匠作可为,亦非主人所能自主者,须求得人,当要节用”[9],便提出了需妥善处理好工匠与主持造园者的关系。在此三端的推动下,提及江南,园林成为了不能忽略的重要标签之一。学界对江南园林的关注由来已久,此处拟另辟他途,以王锡爵、王衡、王时敏祖孙三代接续营建的南园、东园为中心,考察明末清初江南士人家族性的造园行为,以及时代风云际会影响下的园林诗文创作风格发生嬗递的具体表现。
二、接续与新造:王锡爵家族祖孙三代的造园行为
在江南地区的太仓州,历来有营建园林的风气,时人及后人对此多有关注。昆山人归庄在撰写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的《太仓顾氏宅记》中铺叙了在地构筑园林的盛行之状:“豪家大族,日事于园亭花石之娱,而竭资力为之不少恤。……今日吴风汰侈已甚,数里之城,园圃相望,膏腴之壤,变为丘壑,绣户雕甍,丛花茂树,恣一时游观之乐,不恤其他。”[10]在描绘了吴地士人争相建造园林之后,不忘忧心于奢靡之风对地方习俗的侵袭、破坏。童则在《江南园林志》中采择历时和共时共存的角度,描述了江南地区园林建造的演进过程,“南宋以来,园林之盛,首推四州,即湖、杭、苏、扬也。而以湖州、杭州为尤。明更有金陵、太仓”[11]。从中可见太仓造园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
在太仓州的众多园林景观中,当以王锡爵、王衡、王时敏祖孙三代接力营建的南园,以及王时敏新建的东园为翘楚。南园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内阁首辅王锡爵于此赏梅种菊、凿山引水,遂渐渐演化成一处园林胜景。王锡爵虽位极人臣,但在宦途凶险起伏中,常常流露出对隐居苑囿的无限憧憬。而其爱子王衡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因头疾早卒,晚年丧子的悲惨遭遇对其心境的冲击更为剧烈,更坚定了其退居园林的决心。在一系列的祭文中,王锡爵时常回忆起过往岁月里携子游赏南园时乐趣丛生的场景,如《王文肃公文草》卷十二《周年祭文》所记,“私念平生高兴,钟于各园花杲,理疾之暇,则以朝夕至各园,徜徉其间,而园中台榭,皆汝心经目营之地,触物成悲,期于破涕,而涕愈不禁”[12],南园美景依旧,但同游之子却已不在人世,在今昔场景对比中,愈发凸显其失子后的悲怆难抑之态。无怪乎,时隔不到两年,王锡爵也因沉浸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中黯然离世。
王锡爵之爱子王衡虽年少成名,却因其显赫门第而在科举上累受牵连。众多事件中最大的一次便是万历十七年(1589)礼部客司郎中高桂上疏的己丑科作弊案。《明神宗实录》记载:“今辅臣王锡爵之子素号多才,岂其不能致身青云之上,而人之疑信相半,亦乞并将榜首王衡与茅一桂等一同覆试,庶大臣之心迹亦明矣。”[13]王衡作为内阁首辅王锡爵的爱子,其一言一行自然逃脱不了政敌们的指摘、攻讦,虽然大多时候可能是欲加之罪。就己丑科而言,虽经复核证明了王衡的清白,但此次科场案对王衡心态造成了长久的负面影响。在考选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辛丑科榜眼不久之后,王衡便借机奉使江南之机,辞官回归故里,以逃避无处不在的官场构陷。在王衡的传世别集中,时常可见他对园居闲适生活的书写与向往,如《缑山先生集》卷一《春仲园居》:“无事此经月,细草衣垣墙。开门不见人,但闻花甑香。眷言对华滋,有怀托春阳。无弃管蒯资,生理各有当。”[14]在宦途百转千回之后,人生的豁达通透之悟,更显得弥足珍贵。

[明]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上海博物馆藏

[明]林有麟《素园石谱》,明万历四十一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明]王衡《缑山先生集》,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天津图书馆藏
经过王锡爵、王衡两代人的不断营建,南园景点更为丰富多样,传至第三代的王时敏手中时,更是多次修葺拓建,南园的景点分布状况也最终得以确立。除了继续拓建祖辈遗留下来的南园之外,王时敏还邀请了著名造园大师张南垣在芍药圃的基址上新造了东园,《奉常公年谱》中数条材料对此都有记述,胪列如下:
万历四十七年己未 是夏,将文肃公芍药圃稍拓,花畦隙地,插棘诛茅,作暂息尘鞅之计。适云间张南垣至,其巧艺直夺天工,怂为山甚力,遂不惜倾囊听之。[15]
万历四十八年庚申 是年经始东园。园本文肃公药圃,在东门外半里,向止老屋数间。公先以己意构造亭台,累山植木,名曰乐郊。以张南垣为累石妙手,延之过娄,遂尽废昔构,别出新裁,从来累石者惟以高架叠缀、危梯深洞为上,不解用土,南垣一变旧习,因形布置,土石相间,高阜平陂,独得真趣。[16]
崇祯七年甲戌 东园落成,园自庚申经始,中间改作者再四。磴道盘纡,广池澹滟,周遭竹树蓊郁,浑若天成,而凉堂邃阁,位置随宜,卉木窗轩,参差掩映,颇极林壑台榭之美。有藻野堂、揖山楼、凉心阁、期仙庐、扫花庵、香绿步、绾春桥、沁雪林、梅花廊、翦鉴亭、镜上舫、峭专壑、烟上霞外、纸窗竹屋、清听阁、远风阁、密圆阁、画就香霞槛、杂花林、真度庵并东岗之陂诸胜。十余年中,费以累万。乐郊之名,著海内矣。[17]
从年谱的记载可知,王时敏对东园的建造投注了长久的心力,重金延揽了张南垣这样的园林大家精心设计,历时十余载,让本是数间老屋的芍药圃焕然一新,诸多的景点经过改造或新建之后,成为了闻名遐迩的江南园林典范。
三、嬗递发生:从园居宴游之乐到隐居黍离之悲
作为家族接续营建园林的典型,王锡爵、王衡、王时敏祖孙三代皆在南园中留下了诸多印迹,王时敏更是在南园之外,新建了东园。南园、东园的一山一水、一花一木时常在三人的诗文中出现,但承载的情感却因所处时代氛围,以及个人境遇不同而表现出不尽一致的状貌。王锡爵多以回忆切入,对南园各处景色进行描绘;南园在其笔下扮演着勾连其子王衡的情感联系纽带,借此书写一己遭逢爱子中年病卒的创痛巨深。在王衡笔下,南园是躲避官场尔虞我诈的一方静寂之所;在对草木的品鉴中,冀望着在纷杂时世中寻求内心的宁静淡然。而到了王时敏笔下,南园、东园则成为了明遗民在新朝政治高压之下可以暂时躲避风险的夹缝;在此小小天地里,往还结交的前朝遗民凭依经营、游赏园林而消解亡国之悲,在诗歌唱和中,给予了彼此继续活下去的动力。下面结合明清之际易代局势、王时敏生平事迹,以及围绕南园、东园的交游诗歌,来细致探析园林空间之于士人活动的意义所在。
王时敏(1592—1680),初名赞虞,字逊之,有诸多别号,较常用者有烟客、懦斋、归村、偶谐道人、西庐老人等,世称西田先生,江南太仓(今江苏苏州)人。家世显赫,祖父为万历朝大学士、内阁首辅王锡爵,父亲为翰林编修王衡。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一对王时敏生平事迹有所记载,“以荫为尚宝丞,累官太常寺少卿。崇祯庚辰以病归。……易代后以父执事钱谦益,请业甚谨;时与吴伟业惆怅往还,皆东林也。累世富厚,而居乡颇言地方利弊兴革,为民请命。鼎革之际,独能保全其家,盖善以术自全者”[18],重点交代了王时敏在明清易鼎之际的自保行为。史料又载:“国朝顺治元年甲申,公抱病里居。四月杪得三月十九日确耗,五内摧裂,不自意生,哀恸欲绝者数次。会南都部院诸公拥立福藩,起太常寺正卿,公深惟知止之义,且见尔时朝政混浊,党论分争,自分无可报称,遂引疾疏辞。”[19]清廷定鼎之时,王时敏选择成为一名前朝遗民,居家不出,直至清康熙十九年(1680)以89岁高寿而卒。吴伟业《西田招隐诗·其二》“到此身世宽,息心事樵牧”[20]云云,便是对王时敏入清之后三十多年里生活状态的描写。王时敏的详细生平事迹可参见《娄东耆旧传》《清史稿》等书的记载,其传世著述甚多,主要有《偶谐旧草》《西庐诗草》《西庐诗馀》《西庐家书》《致清晖阁尺牍》《王奉常书画题跋》等诗词、家训、尺牍及书画论著十余卷。后世对王时敏的印象多是清初绘画名家,其在清初画坛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陈田《明诗纪事》辛卷二十七上所载可为证:“ 烟客续华亭之绪,开虞山之宗,太原、琅琊一时匹美。石谷、瓯香、渔山皆亲炙西田,得其指授;麓台之衍家传,又无论矣。”[21]除了画作闻名于世以外,王时敏也颇为擅长作诗,笔调横恣,蔚为大观。
明清鼎革的风云之际,严峻局势将士人推向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旧朝遗留下来的士人都不得不对政治形势做出判断,并在抗清殉国、苟安遗民、投降贰臣等多种身份中做一抉择。而一旦作出了选择,某种身份及其背后所象征的含义便会如影随形,成为时人舆论及后人评骘的重要参照。关于王时敏在易代之时的政治抉择,汪曾武《外家纪闻》记载甚详:
太常公遭明思宗之变,国祚已斩,宗社为屋,清军南征,将至太仓,郡人仓皇奔走。吴梅村与太常商议曰:“拒之百姓屠戮,迎之有负先帝之恩,终无万全之策。”太常筹画数昼夜,又与郡绅集议明伦堂,众以太原为明之旧臣,代有显贵,咸视太常为进退。太常知时势之不可回,涕泣语众曰:“余固知大臣之后,死已恨晚。嘉定屠城,前车之鉴。吾宁失一人之节,以救城百姓。”梅村相与大哭,声震数里,众亦咸泣。议遂定。而清军已至,遂与父老出城迎降。至今西门吊桥,颜公迎恩,可见当时太常之心良苦矣。[22]
江南士人知悉崇祯帝在煤山自缢殉国的消息之后,沉浸在悲痛之中尚不足一年,清军便已兵临南京城下,匆忙中建立的南明弘光朝不堪一击。在清军南征推进中,太仓州的前朝士人也在焦急地思忖着将至的命运。引文中的吴伟业在故明举业之途上春风得意,在官场上也先后任翰林院编修、东宫讲读官、南京国子监司业等职,可谓受惠于崇祯帝颇多。王时敏则因是万历朝重臣王锡爵的后代,并曾累官太常寺少卿,而成为地方上的名门望族。循常理来说,吴伟业、王时敏两人的身份特征更易导向的结果是杀身成仁。但有趣的是,在这段文字中,通过两人关于“迎降失节与保全城池”孰重孰轻的对话里,以慷慨大义来消解失节污点,从而为两人在亡国之时不殉国的行为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辩白。
对易代之际士人和园林的关系探讨,应析分成两个时段:一段是在故国,另一段则是在新朝。在故国时,园林往往是士人借以逃遁宦途尔虞我诈的心灵归隐之所;而在新朝,园林则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政治意涵。先看前者:
满径绿阴静,清和景最佳。微风归宿燕,细雨落轻花。老友不期至,清言何以加。酒酣馀逸兴,粉壁走龙蛇。(王时敏《思翁眉公过绣雪堂话雨留宿》)[23]
风物清和好,相将过竹林。骤寒知夜雨,繁响逗蛙吟。杂坐忘宾主,清言见古今。呼僮频剪烛,不觉已更深。(董其昌《丁卯四月七日同陈眉公过逊之山馆话雨留宿》)[24]
半载文园病,花前怅别深。何期今夕雨,重话十年心。池畔蛙声乱,楼头漏点沈。一尊更相劝,惜我鬓毛侵。(陈继儒《同思翁过逊之山馆话雨》)[25]
明天启七年(1627)四月一日,董其昌在娄江道中题跋了唐寅《梦筠图》之后,便在“七日,与陈继儒在娄东观王时敏藏黄公望《秋山图》,并赋诗唱和”[26],这便是上引三首诗的创作背景。《奉常公年谱》卷二对此次聚会的记载更为详细,“四月七日,华亭董思翁其昌、陈眉公继儒过南园绣雪堂,话雨留宿,思翁题‘话雨’二字于壁”[27]。董其昌、陈继儒两人在书画造诣上久负盛名,作为后辈的王时敏便邀约两人至南园绣雪堂赏鉴家藏的书画古迹,因遇雨留宿,便赋诗吟哦园林美景。从三首五律韵脚分布可知,董其昌、陈继儒两首应为作于同一时间的唱和诗,而王时敏的那首应是作于其后。董诗铺叙了春雨润泽中的绣雪堂景色,竹林掩映、蛙鸣阵阵,相知好友高谈阔论至深夜的情景跃然纸上。陈诗通过连缀落花、春雨、蛙声、酒樽等意象,书写雨后融汇了别离之悲和叹衰之愁的复杂情绪。王诗则具有主人口吻,在描绘绣雪堂雨后春景之后,感慨老友把酒重聚的欢愉情状。综观三首诗,更多书写的是向内的私人化情感。园林是士人相聚的重要场所,一年四季花草树木的荣枯便是士人心境悲喜的投射。在园林景物之前,士人恣意地表露着一己的内心隐秘世界。

[清]王时敏《隶书七言律诗轴》,国家博物馆藏

[清]王时敏《仙山楼阁图轴》,故宫博物院藏
当士人所心系的故国走向沦亡,无限悲怆便充斥在生活的每个时刻、每个角落,即使眼前的园林风光依旧引人入胜,但亡国之悲却常常被不自觉地糅合进遣词造句之中,乐景生悲情成为了此间诗词书写的共通模式。清顺治三年(1646),南园梅花绽放,王时敏、吴伟业等人在聆听白在湄、白彧如父子弹奏琵琶时,心有戚戚:“乃先帝十七年以来事,叙述乱离,豪嘈凄切……自河南寇乱,天颜常惨然不悦,无复有此乐矣。相与哽咽者久之。”[28]从以上引文截取的一个场景,便可知来自于故国的人事都会勾连起遗民对过往割舍不断的念想。背负着回忆在新朝挣扎前行,成为了明清易代之际这些两截人须臾摆脱不掉的宿命。
不扶自直疏还密,已折仍开瘦更妍。最爱萧斋临素壁,好因高烛耀华钿。坐来艳质同杯泛,老去孤根仅瓦全。苦向邻家怨移植,寄人篱下受人怜。(吴伟业《王烟客招往西田同黄二摄六王大子彦及家舅氏朱昭芑李尔公宾侯兄弟赏菊·其二》)[30]
东篱寂历抱幽香,误认柴桑是墨床。霜下染来僧衲素,风前翦去羽衣黄。自甘野逸惟宜冷,未必秋心不向阳。草色也同霜色落,更从何处觅花王。(释读彻《丁亥秋王奉常烟客西田赏菊和吴宫詹骏公韵》)[31]
上引三首诗作于清顺治四年(1647)秋天,彼时王时敏别业西庐农庆堂赏菊花盛开,“王遗民瑞国,吴梅村伟业,朱昭芑明镐,黄摄六翼圣,李尔公可卫,宾侯可汧,同过夜饮。月,苍雪法师亦至。西田看菊,梅村以诗贻公,公次韵答之”[32]。参加此次品赏园林秋菊活动的多是太仓州的前朝名流。不同于数年前未亡国时的聚会欢乐雅集,在物是人非的美景映照下,这些人常常情难自禁地流露出悲伤难耐。暗黑色系的意象点缀其间,寒灯成影、浊酒满杯、孤根伫立、素净僧衲,压抑已久的怆痛在字里行间满溢而出。“世事频年馀涕泪,秋光此日共徘徊”,苟活在新朝的故国士人,虽距易鼎已过去数载,但仍不免沉浸在涕泪横流中。秋日的美景更是徒增了无限伤悲。“苦向邻家怨移植,寄人篱下受人怜”,借物写人,菊花怨怼被从邻家故土中移植,仿若诗人幽影自怜身历两朝而无所凭依的无根之感。“自甘野逸惟宜冷,未必秋心不向阳”,则是方外人士释读彻的自相矛盾之语,遁入佛门理应对时事变幻淡然处之,但脑海中割舍不去的故国山河却仍羁绊着出家人未尽的六根。亡国之后,士人的雅集唱和不再有轻松愉悦,而是时常笼罩着悲怆凄厉的故国之思,诚如李联《西庐怀旧集序》“水残山,寄之豪素,伤心人别有怀抱”[33]所言。
除了在与同为故国士人的交游唱和诗中,可以读到王时敏园居生活下潜藏的万般忧愁之外,在他著名的七律组诗《西田感兴》三十首中,这种跨越到新朝的遗民心迹被更显豁地呈现出来,从中也颇可得见营建园林之于遗民的意义所在。
西田感兴 其一
栖迟何必叹途穷,寂寞荒江作隐翁。篷底斜侵花外雨,笛声远度陇头风。残生已分经霜柳,陈迹都如踏雪鸿。静爱小窗丛竹里,夜深禅诵佛灯红。[35]
《西田感兴》组诗作于清顺治八年(1651),彼时王时敏已经步入花甲之年,恰逢西田初竣及寿诞之喜,一众友人纷纷写诗填词恭贺,如陆世仪《西田八章章八句集葩经寿王烟客》、释通云《西田谣寿王太常烟客》、王昊《西田歌》等。但在王时敏自撰的《西田感兴》组诗里,却很少得见愉悦欣喜,更多的是满腔愁绪。在组诗小序里,王时敏不惮自述心声,诗人身逢易代乱世,只能依托于营建一方园林去全身远害,以困守在园林中的遗民身份求得政治上的安全,但即使如此,却依然无法获取心绪上的淡然。园林中的风物时常会触发王时敏掩藏不住的无限愁绪,只能在游赏园林之外,以作诗来排遣愁闷。循此可知,造园也并非故明遗民修身养性的良药。潘景郑《王烟客诗钞跋》载:“先生画名振千古,暮年困顿重敛,虽得薛凤荀龙,娱情田园,黍离宗周,意在言外。读其诗邈然清风,深得《小雅》,怨悱而不乱。”[36]诚可谓高山流水的知音之言。在组诗第一首中,愈发凸显王时敏的遗民身份和遁世心态,在纷杂尘世中,借助于园林生活,实现隐居夙愿,过往点滴只能在吟诵佛经中寻求慢慢消解。而在诗艺上,则正如陆元辅《王太常诗集序》所言,“有少陵之沈郁,兼香山之浏亮,而其深情逸韵,更能出入于眉山、剑南之间,彬彬乎质而能文,丽而有则,虽未尝与世别薰莸、辨泾渭,然已深砭俗学之膏肓,而投之药石矣”[37]。王时敏的诗被称誉为融汇了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诸位名家之长,而又能别具只眼,这应与其在明亡之后的诗风转变息息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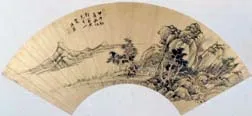
[清]吴伟业《山水扇》,故宫博物院藏
结语

《王文肃公年谱》,清乾隆三十八年王时敏刻本,天津图书馆藏
士人喜好营建园林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文化传统,而将观照点对准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士人群体,则愈发可见园林之于士人生命历程的重要意义。在山河板荡之前,士人往往沉醉于叠山理水之中,在游观品赏山石草木中实现远离宦海阿谀争斗的愿景;而乱世易鼎之后,园林则又成为士人在新朝消解敏感政治身份的自保场所。聚焦于这阶段特征明显的易代前后,关涉园林的诗歌创作也呈现出从园居宴游之乐到隐居黍离之悲的嬗递。虽为同一处空间,但因外在时局的风云变迁,以及士人心态的起伏不定,会呈现出不同状貌,不变之中萌生的变化情状,形成了非同一般的魅力。王锡爵、王衡、王时敏祖孙三代接力营建的太仓南园,以及王时敏新拓的东园,正好提供了一个可供剖析解读的精致案例。循此路径,明末清初的动荡时势,江南士人的造园风尚,乱离之下的心境起伏,以及园居里的诗歌创作现象,乃至于包孕在四者间的错综关系都可一一得以清晰揭示。
【注 释】
[1][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195-2196.
[2][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824.
[3]严杰编选.白居易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286.
[4][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邓之诚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176.
[5][宋]周密.吴兴园林记[M]//古今图书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96:366.
[6]顾凯.明代江南园林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124.
[7][8][11]童寯.江南园林志[M].北京:中国工业出版社,1963:3,7,28.
[9][明]计成原.园冶[M].陈植注释,杨超伯校订,陈从周校阅,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41.
[10][清]归庄.归庄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350.
[12][明]王锡爵.王文肃公文草[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447-448.
[13]明神宗实录[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3875.
[14][明]王衡.缑山先生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596.
[15][16][17][19][27][32][清]王宝仁.奉常公年谱[M]//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6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351,353,364-365,389,359,395.
[18]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M]//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学林类6).台北:明文书局,1985:72-73.
[20][清]吴伟业.吴梅村全集[M].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8.
[21]陈田辑.明诗纪事[M]//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学林类11).台北:明文书局,1991:980.
[22]汪曾武.外家纪闻[M].民国十七年(1928)无锡杨氏云在山房铅印本,国家图书馆藏.
[23][24][25][29][33][34][35][36][37][清]王时敏.王时敏集[M].毛小庆点校,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64,494,494,31,861,51,33,863-864,859.
[26]任道斌编著.董其昌系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242.
[28]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156.
[30][清]吴伟业.梅村家藏稿[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144.
[31]杨为星注.苍雪大师《南来堂诗集》诗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181-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