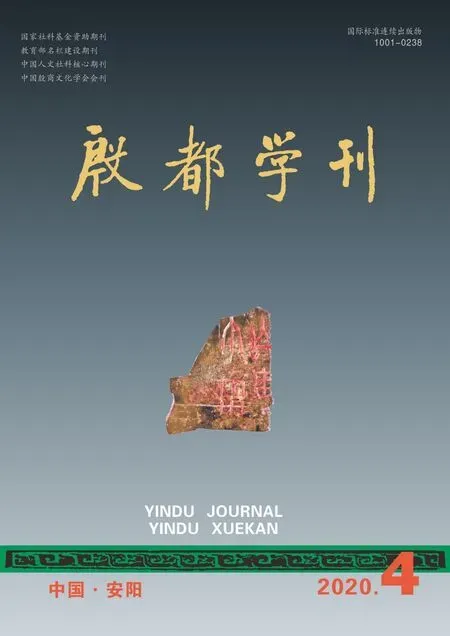焦循的通学观念及其诗经小学研究
2021-01-21康国章
康国章
(安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焦循(1763 —1820),字里堂,江苏甘泉(今扬州黄珏)人,嘉庆六年(1801)举人,《清史列传》卷六十九《儒林传下二·焦循》载其事迹云:“既壮,雅尚经术,与阮元齐名。元督学山东、浙江,俱招循往游。……经史、历算、声音、训诂,无所不精。”[1]一应礼部试不第,即闭门著书。葺其老屋,称之为“半九书塾”;复构“雕菰楼”,为读书之所。嘉庆庚辰七月而卒,年五十八。
焦循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世传《易》学,他曾与著名学者王引之讨论《易》学,引之以为凿破混沌。焦循在《易》学研究方面著有《易通释》20卷、《易图略》8卷、《易章句》12卷,合称《易学三书》,共40卷。《易》学之外,焦循最为看重《孟子》,著有《孟子正义》30卷,《清儒学案》卷一百二十《里堂学案》云:“里堂与阮文达同学,经学算学并有独得,百家无所不通,《易学三书》及《孟子正义》皆专家之业。”[2]焦循精心钻研古书注解之学,著成《周易王氏注补疏》2卷、《尚书孔氏传补疏》2卷、《毛诗郑氏笺补疏》5卷、《春秋左传杜氏集解补疏》5卷、《礼记郑氏补疏》3卷、《论语何氏集解补疏》2卷,合称《六经补疏》。个人文集方面,焦循“手订者,曰《雕菰楼集》二十四卷”[3];复有《里堂家训》2卷。焦循学问浩博,据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考述,“焦循一生著述,已刻、未刻之书,登录了五十九种”[4]。
一、焦循的通学观念
1.焦循通学观念的特质
扬州学派为学宏阔,具有圆通广大的气象,张舜徽《清儒学记》云:“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5]焦循世传学业,长年勤学深思,刻苦钻研,学术素养深厚。同时,他曾心怀敬意地向年辈稍长的钱大昕、程瑶田、段玉裁、王念孙等著名学者致信,虚心求教,且有幸与阮元、王引之、汪中、凌廷堪等学术名家保持交游关系。以上诸种人生际遇,加之个人因素,造就焦循一生既拥有卓越的学识,又具备宏阔的规模。阮元为焦循作传,径直称其为“通儒”,其《研经室二集·通儒扬州焦君传》云:“君善读书,博闻强记,识力精卓,于学无所不通。著书数百卷,尤邃于经。于经无所不治,而于《周易》《孟子》专勒成书。”[6]博学通识仅是焦循学术精神的一个层面,作为“通儒”,更重要的是他在治学上不偏蔽、不局隘,张舜徽先生说:“究竟他的所以够得上称为‘通儒’者何在?值得我们探索。一方面,固然由于他的学问很博通,知识范围很广泛;而更重要的,在于他的识见卓越,通方而不偏蔽;规模宏阔,汇纳而不局隘。在乾嘉学者中,不愧为杰出的第一流的人物。”[7]
2.焦循通学观念的学术渊源
焦循的通学观念,根源于他对孔子“一以贯之”的深入思考,其《一以贯之解》云:“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然则一贯者,忠恕也。忠恕者何?成己以及物也。孔子曰:‘舜其大知也矣。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舜于天下之善,无不从之,是其一以贯之。”[8](P132)他在《论语通释·释异端》中说:“惟圣人之道至大,其言曰‘一以贯之’,又曰‘焉不学,无常师’,又曰‘无可无不可’,又曰‘无意、无必、无固、无我’,异端反是。孟子以杨子‘为我’、墨子‘兼爱’、子莫‘执中’为执一而贼道。执一即为异端,贼道即斯害之谓。杨、墨执一,故为异端。孟子犹恐其不明也,而举一‘执中’之子莫。然则凡执一者皆能贼道,不必杨、墨也。圣人一贯,故其道大。异端执一,故其道小。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致远恐泥’,即恐其执一害道也。惟其异,至于执一,执一由于不忠恕。……执其一端为异端,执其两端为圣人。”[9]博学通识,一以贯之,执其两端,方能成为圣人;偏执其一,思想狭促,势必走向异端。异端偏执于一,而圣人忠恕,能够趋时,能够贯通“执中”“为我”“兼爱”为一,焦循在《攻乎异端解下》中说:“杨子惟知为我,而不知兼爱;墨子唯知兼爱,而不知为我;子莫但知执中,而不知有当为我、当兼爱之事。杨则冬夏皆葛也,墨则冬夏皆裘也,子莫则冬夏皆袷也。趋时者,裘、葛、袷皆藏之于箧,各依时而用之,即圣人一贯之道也。使杨思兼爱之说不可废,墨思为我之说不可废,则恕矣,则不执一矣。圣人之道,贯乎为我、兼爱、执中者也。”[8](P136)
3.焦循述圣眼界的宏阔
经学的本质在于述圣,在于贯通千家著述,从中参悟出立身经世之法,焦循在《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中说:“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阴阳、五行、六书、七音等为之辅。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训故,核其制度,明其道义,得圣贤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经世之法。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8](P213)经学有汉学、宋学之分,时人普遍存在着尊汉排宋倾向,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偏离述圣目标的,焦循在《述难四》中说:“‘吾述乎尔,吾学孔子乎尔’,然则所述奈何? 则曰:‘汉学也。’呜呼!汉之去孔子,几何岁矣?汉之去今,又几何岁矣? 学者,学孔子者也。学汉人之学者,以汉人能述孔子也。乃舍孔子而述汉儒!汉儒之学,果即孔子否邪……学者述孔子而持汉人之言,惟汉是求,而不求其是。于是拘于传注,往往扞格于经文,是所述者汉儒也,非孔子也。而究之汉人之言,亦晦而不能明,则亦第持其言而未通其义也,则亦未足为述也。且夫唐宋以后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汉学者,或屏之不使犯诸目,则唐宋人之述孔子,讵无一足征者乎? 学者或知其言之足征,而取之又必深讳其姓名,以其为唐宋以后之人,一若称其名,遂有碍乎其为汉学者也。噫,吾惑矣!”[8](P104-105)盲目尊汉排宋固不可取,简单转述汉人文辞而不深究其意就更为违舛了。
4.焦循解经的小学精神
欲洞察汉代人解经的真实面貌,进而窥知圣人之旨,须臾也离不开训诂的方法。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戴震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中说:“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10]焦循对于训诂之学的追求,亦在于通达,他在《复王侍郎书》中说:“向亦为六书训故之学,思有以贯通之,一涤俗学之拘执。用力未深,无所成就。阮阁学尝为循述石臞先生解‘终风且暴’为‘既风且暴’,与‘终窭且贫’之文法相为融贯。说经若此,顿使数千年淤塞一旦决为通渠。后又读尊作《释辞》,四通九达,迥非貌古学者可比。”[11]为此,焦循特别反对那些号称“考据”而执一害道的人,他在《里堂家训》中说:“近之学无端而立一考据之名,群起而趋之。所据者汉儒,而汉儒中所据者又唯郑康成、许叔重,执一害道,莫此为甚。许氏作《说文解字》,博采众家,兼收异说;郑氏宗《毛诗》,往往易《传》。注《三礼》列郑大夫、杜之春之说于前,而以玄谓按之于后;《易》辨爻辰,《书》采地说,未尝据一说也。且许氏撰《五经异义》,郑氏驳之语云‘君子和而不同’,两君有之。不谓近之学者,专执两君之言,以废众家,或比许郑而同之,自擅为考据之学,余深恶之也。”[12]
二、焦循《诗》学著作考述
在《诗》学研究方面,焦循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陆氏草木虫鱼疏疏》《毛诗地里释》《毛郑异同释》《毛诗补疏》(一名《毛诗郑氏笺补疏》)等著作。
1.《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
焦循六岁习读《毛诗》,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后开始创稿,至嘉庆四年(1799),前后历经19年,六易其稿,终成《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12卷,其《叙》云:“辛丑、壬寅间,始读《尔雅》,又见陆佃、罗愿之书,心不满之,思有所著述,以补两家之不足,创稿就而复易者三。丁未,馆于寿氏之寉立堂,复改订之。至辛亥,改订讫,为三十卷。壬子至乙卯,又改一次,未惬也。戊午春,更芟弃繁冗,合为十一卷;以考证《陆玑疏》一卷附于末,凡十二卷。盖自辛丑至己未,共十有九年,稿易六次。以今之所订,视诸草创之初,十不存一。”[13]
2.《陆氏草木虫鱼疏疏》
《陆氏草木虫鱼疏疏》原附于《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又单独成册,分上、下两卷。乾隆五十九年(1794),焦循在《陆氏草木虫鱼疏疏·卷上》记曰:“余以元恪之书既残阙不完,而后世为是学者复不能精析,因撰《草木鸟兽虫鱼释》。既成,又据毛晋所刻之本,参以诸书,凡两月而后定,附之卷后。有未备,阅者正焉。乾隆甲寅仲冬月,江都焦循记。”[14]
3.《毛诗地里释》
乾隆五十二年(1787),焦循在扬州寿家私塾授徒,有感于王应麟《诗地理考》琐杂难通,因而考之,成《毛诗地里释》,嘉庆八年(1803)自序云:“乾隆丁未,馆于寿氏之鹤立堂,偶阅王伯厚《诗地里考》,苦其琐杂,无所融贯,更为考之。迄今十七年,未及成书。今春家处,取旧稿删订其繁冗,录为一册。凡《正义》所已言者,不复胪列。又以杜征南撰《春秋集解》兼为土地名氏族谱,以相经纬,《隋书·经籍志》谱系次于地理,而《三辅故事》《陈留风俗传》与陆澄、任昉之书并列,岂非有地则有人,有人则有事!《小序》《毛传》中,有及时事者,亦考而说之,附诸卷末,共四卷。……嘉庆癸亥三月朔。”[8](P265-266)是故,该书名曰“地里释”,实则前三卷考释地理知识,第四卷考释“氏族”(即“人物”)。
4.《毛郑异同释》
在《毛诗补疏》成书之前,焦循还撰有《毛郑异同释》一书,他在《毛诗补疏序》中说:“余幼习《毛诗》,尝为《地理释》《草木鸟兽虫鱼释》《毛郑异同释》。”[15]有研究者根据收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焦循手批《十三经注疏·毛诗注疏》之“题记”,考证《毛郑异同释》始作于嘉庆三年(1798),该题记云:“省试被落,缘此可以潜居读书。《毛诗》久欲穷究之,因日间删订所撰《草木释》及《诗地释》两书,晚间灯下衡写毛、郑、孔之义。”[16-18]解《诗》须先通训诂,毛《传》在训诂上简约精当,最得诗旨,郑《笺》较之迂拙,不如毛《传》,“训诂之不明,则诗辞不可解。必通其辞,而诗人之旨可绎而思也。毛《传》精简,得《诗》意为多。郑生东汉,是时士大夫重气节,而温柔敦厚之教疏,故其《笺》多迂拙,不如毛氏。则《传》《笺》之异,不可不分也。”(《毛诗补疏序》)[2](P2153)对于孔颖达《毛诗正义》,焦循多有不满,他于《里堂家训》卷下云:“余尝究孔颖达之《毛诗正义》,其阐发《传》《笺》之同异,往往以同者为异,异者为同,而毛郑之本意未能各还其趣也。”[19]
5.《毛诗补疏》
嘉庆十九年(1814),焦循删录《地理释》《草木鸟兽虫鱼释》《毛郑异同释》,合为《毛诗补疏》5卷,其《叙》云:“《地理释》《草木鸟兽虫鱼释》《毛郑异同释》三书,共二十余卷。嘉庆甲戌莫春,删录合为一书。戊寅夏,又加增损为五卷,次诸《易》《尚书补疏》之后。”[20]《毛诗补疏》又名《毛诗郑氏笺补疏》,焦循在《群经补疏自序》中罗列有《毛诗郑氏笺》之篇,云:“西汉经师之学,惟《毛诗传》存,郑笺之,二刘疏之,孔颖达本而增损为《正义》,于诸经最为详善。然毛郑义有异同,往往混郑于毛,比毛于郑。”[8](P271)
三、焦循诗经小学特质分析
解经上的通达,要诀在于以己意裁定众说,王引之《经义述闻序》云:“大人又曰:‘说经者期于得经义而已。前人传注不皆合于经,则择其合者从之,其皆不合,则以己意逆经意,而参之他经,证以成训,虽别为之说,亦无不可。必欲专守一家,无少出入,则何邵公之《墨守》见伐于康成者矣。’故大人之治经也,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盖孰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者也。”[21]焦循解《诗》,既辨毛、郑之别,又详审孔《疏》之是非,兼下己意,于圆通宏阔中彰显出专精本色。兹主要以焦循的《毛诗补疏》(以下简称《补疏》)加以申明。
(一)比较毛郑异同
比较毛郑的异同,是焦循解《诗》的核心内容。以下主要按“郑《笺》申毛”“是毛非郑”“《笺》义为长”三个方面,举例而说明之。
1.郑《笺》申毛
(1)《召南·羔羊》云:“委蛇委蛇。”毛《传》:“委蛇,行可从迹也。”郑《笺》:“委蛇,委屈自得之貌。”《补疏》:“循按:‘君子偕老’,《传》云:‘委委者,行可委曲从迹也。’《笺》‘委曲’二字,正取毛彼《传》,以解此《传》‘从迹’二字。”
(2)《卫风·伯兮》云:“甘心首疾。”毛《传》:“甘,厌也。”郑《笺》:“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贪口味,不能绝也。”《补疏》:“循按:厌之训为饱为满。‘首疾’,人所不满也。思之至于首疾,而亦不以为苦,不以为悔,若如是思之而始满意者,此毛义也。甘心至首疾而不悔,则思之不能已可知。虽首疾而心亦甘,则其思之如贪口味可知。郑申毛,非易毛也。”

(4)《大雅·皇矣》云:“是伐是肆。”毛《传》:“肆,疾也。”郑《笺》:“肆,犯突也。《春秋传》曰:‘使勇而无刚者肆之。’”《补疏》:“循按:《大明》‘肆伐大商’,《传》亦以‘肆’为‘疾’,《笺》以《尔雅》‘肆、故,今也’易之。《正义》申毛,引《释言》‘窕,肆也’,又引《左传》‘轻者肆焉’,明肆为疾之义。此诗《笺》引《春秋传》,即《正义》所引。然则以‘突犯’训‘肆’,正是申毛,非易毛也。隐九年传‘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文十二年传‘若使轻者肆焉’,以‘肆’字代‘尝寇速去’,正是以‘速’明‘肆’,即毛以‘疾’训‘肆’之义。《正义》既以为异毛,又讥其引《左传》之谬。盖先儒互训之妙,至隋、唐已莫能知。《周礼·环人》疏引文十一年传注云:‘肆突,言使轻锐之兵,往驱突晋军。’此注不知何人,盖贾、服之遗。训肆为突,古有此义,故郑以为‘犯突’。”
(5)《大雅·民劳》云:“汔可小康。”毛《传》:“汔,危也。”郑《笺》:“汔,几也。王几可以小安之乎?”《补疏》:“循按:毛以‘危’训‘汔’。危可小康,犹云殆可以小康也。‘殆’训‘危’,亦训‘几’。郑训‘汔’为‘几’,正发明毛义也。”
2.是毛非郑
(1)《周南·螽斯》云:“螽斯羽,诜诜兮。”毛《传》:“诜诜,众多也。”郑《笺》:“凡物有阴阳情欲者,无不妒忌,维蚣蝑不耳。”《补疏》:“循按:《笺》本《序》耳,然审《序》文,‘言若螽斯’自为句,‘不妒忌则子孙众多’,申言子孙众多之所以然,非谓螽斯之虫不妒忌也。《传》但言众多,亦无螽斯不妒忌之说。”
(2)《召南·草虫》云:“亦既觏止。”毛《传》:“觏,遇。”郑《笺》:“既觏谓已昏也。《易》曰:‘男女觏精,万物化生。’”《补疏》:“循按:《易传》:‘姤,遇也。’‘姤’一作‘遘’,与‘觏’通。故得训‘觏’为‘遇’。《笺》以‘既见’为‘同牢而食’,以‘既觏’为‘觏精’,毛无此义也。”
(3)《邶风·柏舟》云:“我心匪鉴,不可以茹。”毛《传》:“鉴,所以察形也。茹,度也。”郑《笺》:“鉴之察形,但知方圆白黑,不能度其真伪。我心非如是鉴,我于众人之善恶外内,心度知之。”《补疏》:“循按:茹即谓察形。鉴可茹,我心非鉴,故不可茹。如可察形,则知兄弟之不可据,而不致‘逢彼之怒’矣。《笺》迂曲,非《传》义。”
(4)《邶风·谷风》云:“湜湜其沚。”毛《传》:“泾、渭相入而清浊异。”郑《笺》:“湜湜,持正貌。”《补疏》:“循按:《说文》:‘湜,水清见底。’《传》言‘清浊异’,以‘湜湜’为‘清’也,无‘持正’义。”
(5)《大雅·绵》云:“文王蹶厥生。”毛《传》:“蹶,动也。”郑《笺》:“文王动其绵绵民初生之道。”《补疏》:“循按:生即性也,谓感动虞、芮之性。毛详述争田、让田之事,申此义也。《笺》迂甚。”
3.《笺》义为长
(1)《召南·小星》云:“抱衾与裯。”毛《传》:“裯,襌被也。”郑《笺》:“裯,床帐也。”《补疏》:“循按:‘裯’,音通于‘帱’,字从‘周’。周为匝义。又‘裯’之为‘帐’,犹‘惆’之为‘怅’。《笺》易《传》为长。”
(2)《大雅·生民》云:“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毛《传》:“相,助也。”郑《笺》:“谓若神助之力也。”《补疏》:“循按:毛训‘相’为‘助’,未必如《笺》‘神助’之义。五谷生自天,必待人树艺之乃生。后稷教民稼穑,是代天以成其能,故云‘相’耳,非谓神助后稷也。”
除上述三种情况外,焦循有时仅对毛、郑之说各做客观描述,而不区分其间的优劣。如,《王风·黍离》云:“行迈靡靡。”毛《传》:“迈,行也。”郑《笺》:“行,道也。道行,犹行道也。”焦循《毛诗补疏》:“循按:‘行’字之训,或训‘往’,《释名》所谓‘两足进曰行’也;或训道路,《左传》‘斩行栗’,‘行栗’即道上之栗也。《传》训迈为行,即是训行为迈。既言行,又言迈,犹《古诗》言‘行行重行行’耳。《笺》以行字训道,盖以迈既为行,则行宜训道,又恐人误认,而申言‘道行,犹行道’,与毛义异也。”
(二)驳斥孔《疏》
焦循删合自己的前期《诗》学著作,名之曰“补疏”,暗含对孔《疏》(《正义》)的强烈不满。故而,在指摘孔《疏》失误时,焦循有时措辞甚为激烈。例如:
(1)《周南·兔罝》云:“公侯干城。”毛《传》:“干,扞也。”郑《笺》:“诸侯可任以国守,扞城其民。”《补疏》:“循按:此《笺》申明《传》义,殊无异同。《正义》言郑‘惟干城为异’非也。”又,《诗》云:“公侯腹心。”毛《传》:“可以制断公侯之腹心。”郑《笺》:“可用为策谋之臣,使之虑无。”《补疏》:“循按:‘制断公侯之腹心’,即是策谋虑无。《笺》申《传》,非易《传》也。《正义》强分别之。”
(2)《召南·采蘩》云:“于以采蘩,于沼于沚。”毛《传》:“蘩,皤蒿也。于,於。”郑《笺》:“于以,犹言往以也。执蘩菜者以豆荐蘩葅。”《补疏》:“循按:《传》训‘于’为‘於’,在训‘蘩’为‘播蒿’之下,明所训是‘于沼于沚’二‘于’字也。然则‘于以’之‘于’何训,故《笺》申言,‘于以,犹言往以’,训在‘蘩’字之上。《正义》云:‘经有三于,《传》训为於,不辨上下。’《传》明示‘于’在‘蘩’下,何为不辨乎?”
(3)《召南·行露》云:“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毛《传》:“不思物变而推其类,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郑《笺》:“变,异也。人皆谓雀之穿屋似有角。”《补疏》:“循按:以角穿屋,常也。无角而穿屋,变也。不思物之有变,第见穿屋而推之以寻常穿屋之事,则似雀有角矣。此《传》《笺》之义也。《正义》云:‘不思物有变,强暴之人,见屋之穿而推其类,谓雀有角。’经言‘谁谓’,无所指实之词,故《笺》云‘人皆谓’,则非指‘强暴之人’矣。”
(4)《邶风·燕燕》云:“差池其羽。”郑《笺》:“兴戴妫将归,顾视其衣服。”《补疏》:“循按:《左氏襄二十二年传》云:‘譬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杜预注云:‘差池,不齐一。’《左传》之‘差池’,即此诗之‘差池’。下章《传》云:‘飞而上曰颉,飞而下曰颃。’‘飞而上曰上音,飞而下曰下音。’即差池之不齐也。盖庄姜送归妾,一去一留,有似燕燕之差池上下者。《笺》言‘顾视衣服’,其说已迂,至解‘下上其音’,谓‘戴妫将归,言语感激,声有大小’,则益迂矣。《正义》绝无分别。”
(5)《邶风·日月》云:“胡能有定。”毛《传》:“胡,何;定,止也。”郑《笺》:“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补疏》:“循按:《正义》云:‘公于夫妇尚不得所,于众事,亦何能有所定乎?’《传》《笺》俱无‘众事’义。”
(6)《邶风·谷风》云:“行道迟迟,中心有违。”毛《传》:“迟迟,舒行貌。违,离也。”郑《笺》:“徘徊也。行于道路之人,至将离别,尚舒行,其心徘徊然。”《补疏》:“循按:‘徘徊’申明‘违离’之义。而所以说之者,非也。‘行道迟迟’,即孔子‘迟迟吾行’之义,不欲急行也。所以然者,以‘中心有违’,不欲行也。申为‘徘徊’,是矣。乃又以‘行道’为‘行于道路之人’,则非毛义。《正义》以徘徊为异,而以‘道路之人’云云羼入毛义中,两失之。”
(7)《卫风·伯兮》云:“焉得谖草。”毛《传》:“谖草,令人忘忧。”郑《笺》:“忧以生疾,恐将危身,欲忘之。”《补疏》:“循按:崔豹《古今注》引董仲舒云:‘欲忘人之忧,赠之以丹棘。’《说文》:‘藼,令人忘忧,草也。《诗》曰:焉得藼草。’重文作‘萱’。《文选》注引《诗》作‘焉得萱草’。以‘忘忧’得有‘谖’名,因‘谖’而转为‘藼’‘萱’。谓‘萱’取义于‘谖’,可也。谓谖草非草名,不可也。《正义》云:‘谖训为忘,非草名。故《传》本其意,谓欲得令人善忘忧之草,不谓谖为草名。’不知《传》言‘令人忘忧’,正指萱草言。若‘谖’仅训为‘忘’,则忘草为不辞。至于经义,正以忧之不能忘耳。《笺》言‘恐危身,欲忘之’,殊失风人之旨,非毛义也。而《正义》直以‘恐以危身’之说属诸毛《传》。”
(8)《周颂·闵予小子》云:“遭家不造。”毛《传》:“造,为。”郑《笺》:“造,犹成也。”《补疏》:“循按:《淮南子·天文训》‘介虫不为’,高诱注云:‘不成为介虫也。’是‘不为’即‘不成’。《笺》申毛义,而《正义》以为异,其解毛云‘家事无人为之’,于经义为不达矣。家不为,犹云‘鱼不为’‘禾不为’‘黍不为’也。”
(三)精心考证

(2)《邶风·北风》云:“其虚其邪,既亟只且。”毛《传》:“虚,虚也。”郑《笺》:“邪读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仪虚徐宽仁者,今皆以为急刻之行矣,所以当去以此也。”《补疏》:“循按:‘虚,虚也’,《释文》云:‘一本作虚,邪也。’此《正义》亦云:‘《传》质,训诂叠经文耳,非训虚为徐。’可知《正义》本作‘虚,徐也。’《传》以徐训虚,《笺》读邪为徐,‘其虚其邪’,犹云‘其徐其徐’。其徐其徐,犹云徐徐,徐徐犹舒舒,故《笺》以为‘威仪虚徐宽仁’也。《尔雅》作‘其虚其徐’。班固《幽通赋》:‘承灵训其虚徐兮。’‘其虚徐’,即用《诗》‘其虚其徐’,而‘邪’已作‘徐’,在郑前。毛直以‘徐’训‘虚’,谓不特‘邪’字是‘徐’,‘虚’字亦是‘徐’。郑氏则申明之,言‘邪读为徐’。‘邪’同‘斜’,《说文》斜读荼。《易》‘来徐徐’,子夏作‘荼荼’是也。马融解‘徐徐’为‘安行貌’,即此《笺》所谓‘宽仁’也。《淮南子·原道训》注云:‘原泉始出,虚徐流不止,以渐盈满。’此‘虚徐’正以‘徐徐’言也。《太玄·戾》:‘初一,虚既邪,心有倾。测曰:虚邪,心倾怀不正也。’王弼解‘徐邪’为‘疑惧’,曹大家解《幽通赋》为‘狐疑’,皆本此。在威仪容止则为宽舒,在心则为迟疑。‘虚徐’之为‘狐疑’,即‘徐徐’之为‘疑惧’。‘徐徐’之为‘安行’,即‘其虚其徐’之为‘宽仁’。于此知虚邪即徐徐,而毛以‘徐’训‘虚’,实为微妙。若以‘虚’训‘虚’,成何达诂?《易传》‘蒙者,蒙也’‘剥者,剥也’,上一字乃卦名,谓卦之名蒙、名剥,即取蒙剥之义,未可援以为训诂之常例。若谓上‘虚’是丘虚,下‘虚’是空虚,以‘空虚’之‘虚’解‘丘虚’之‘虚’,顾以虚训虚,曷以分其为丘虚为空虚?毛《传》宜依《正义》作‘虚,徐也’。《释文》本作‘虚,虚’,乃讹也。”焦循考证,毛《传》‘虚,虚也’乃‘虚,徐也’之讹误,“虚邪”为“徐徐”之义。
(3)《召南·草虫》云:“喓喓草虫。”毛《传》:“草虫,常羊也。”《补疏》:“循按:庶物之名,非以声音,即以形状。《淮南子·地形训》:‘东南为常羊之维。’高诱注云:‘常羊,不进不退之貌。’《俶真训》云:‘不若尚羊物之终始。’《汉书·礼乐志》载《郊祀歌》云:‘幡比翅回集,贰双飞常羊。’又云:‘周流常羊思所并。’颜师古皆训为‘逍遥’。盖‘常羊’犹言‘相羊’,‘相羊’者,‘逍遥’之转声也。草虫名常羊,犹荧火名熠燿耳。”焦循释毛《传》中的“常羊”为“逍遥”,完全突破了字形的局限,征引文献之精确、恰当,更是让人拍案叫绝,可谓得乾嘉考据学因声求义之精髓矣!
焦循为学通达,他在经学方面取得的成就自然是最为突出的,同时他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研究方面也颇有收获,陈居渊先生说:“十八世纪的学术界,朴学独盛。吴派、皖派和以扬州学者为主体的扬州学派以纯汉学形式的古文经学研究,笼罩学坛,考据著述如林,人才辈出。他们不仅经学研究有相当的造诣,而且对文学理论和诗文创作也有独到的见解。他们的学术修养、审美情趣,无不打上朴学的印记。然而丰硕的朴学成果,反将他们的艺术个性淹没不彰,其中最具代表的莫过于焦循所提出的‘扬花抑雅’的戏剧论和‘形意相合’的时文论的文学思想。”[22](P22-23)朴学的重点和核心固然在于考据,但其精神实质却在于探求古代文化的真相,所以说小学研究是过程探索而不是终极追求,推明故训的最终目的还是要理解儒家之道,洞察圣人之意。在先圣那里,道学和文学完全是统一的,所以经学研究也应该充满“性灵”,焦循在《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中论曰:“循谓仲尼之门,见诸行事者,曰德行,曰言语,曰政事;见诸著述者,曰文学。自周、秦以至于汉,均谓之学,或谓之经学。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训故,核其制度,明其道义,得圣贤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经世之法。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著书立言者之性灵,以精汲精,非天下之至精,孰克以与此?……盖惟经学可言性灵,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22](P313-314)
鉴于上述,在研究焦循诗经小学的过程中,也应该能够捕捉到有关“性灵”的说法。如,《周南·葛覃》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毛《传》:“兴也。覃,延也。葛所以为絺绤,女功之事烦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郑《笺》:“葛者,妇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兴焉。兴者,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体浸浸日长大也。”《补疏》:“循按:《传》训‘施’为‘移’,故王肃推之云:‘葛生于此,延蔓于彼,犹女子当外成也。’与《笺》较之,肃义为长。《正义》合郑于毛,云:‘下句黄鸟于飞,喻女当嫁,若此句亦喻外成,于文为重,毛意必不然。’窃谓此诗之兴,正在于重。‘葛之覃兮,施于中谷’,与‘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同兴女之嫁。葛移于中谷,其叶萋萋,兴女嫁于夫家而茂盛也。鸟集于灌木,其鸣喈喈,兴女嫁于夫家,而和声远闻也。盛由于和,其意似叠,而实变化。诵之气穆而神远。《笺》以‘中谷’为‘父母’家,以‘延蔓’为‘形体浸浸日长大’,迂矣。毛《传》言简而意长,耐人探索,非郑所能及。”《周南·葛覃》一诗极具审美意趣,郑《笺》擅长礼制考证,却在旨趣探求方面几无建树,所以在解《葛覃》之类的诗篇时常招人不满,“欧阳修所辨‘安有取喻女之长大哉’实是针对郑《笺》‘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体浸浸日长大也。叶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23]焦循结合文字训诂,发微《葛覃》一诗比兴之奥妙,直指该作“其意似叠,而实变化”的结构美学内涵,并以“气”“神”之类充满“性灵”色彩的词语揭示诗篇的美学价值,一扫汉代人解《诗》的迂腐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