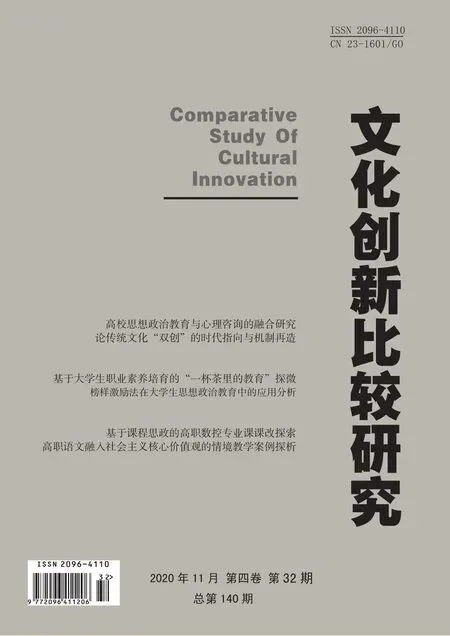四川阆中古城建筑装饰解析
2021-01-18田家赫陈恬恬张杰
田家赫,陈恬恬,张杰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四川乐山 614000)
几千年来,固有“阆苑仙境”之说的阆中古城无论是在历史建筑还是传统民居上,都营造了绚丽多彩的建筑装饰,建筑装饰已经成为彰显审美意识以及地域文化气息的象征,也承载着和谐之美所带来的精神共鸣。阆中古城独具特色的建筑装饰在明清时期发展到顶峰,随着近些年来阆中古城的开发,建筑装饰在色彩、图案、质感纹理上受影响较大,因此,如何进一步挖掘本土建筑装饰部位、题材和精神寓意等方面的特色和审美价值,并更好地延续其文化价值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该文以建筑装饰的表现形式为线索来研究其蕴含的地域特色和民俗文化内涵,促进地域文化和阆中古建装饰文化的传承。
1 建筑装饰部位
阆中古城鳞次栉比的传统民居不同建筑装饰部位述说着古城往昔的辉煌,残破的瓦当、朴素庄重的屋脊灰塑、形式多样的挑枋等明清独特装饰形成了古建筑青瓦粉墙的建筑风格。从建筑附属构件装饰到建筑匾额、家居陈设均各具特色,承载不同功能的建筑部位,其装饰形式也不尽相同。
1.1 建筑装饰
阆中古城建筑形式多为天井合院式建筑,以木材为主要建筑结构,建筑外墙一般不承重,素有“墙倒屋不塌”之说,主体围护结构如槛墙、山墙等多由空斗砖所砌,是阆中古城建筑装饰的特色组成部分。用空斗砖砌筑建筑下部槛墙,在功能上赋予建筑保暖、防火、隔热等多重作用,在建筑审美上,上部穿斗木结构的轻快牢固与槛墙平整厚实的体积感形成强烈的对比。山墙多呈梯状,高度8 m 左右,墙檐下部用砖砌筑,保持了材料的原真性,灰塑装饰、木色结构与青灰色砖瓦形成了阆中古城建筑整体典雅朴素的建筑风格。阆中古城的传统建筑虽然有着南北交融于一体的建筑风格,但其木质结构、主体围护结构等建筑装饰仍体现川东民居所秉承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崇高理想,巴人文化建筑风格彰显其中。
1.2 建筑附属构件装饰
(1)屋顶。
阆中古城不同功能的建筑其屋顶形式也有所区分,官式建筑及寺庙建筑屋顶多采用歇山顶,民居建筑屋顶基本形式则为悬山顶。悬山顶的结构简单,屋顶坡度平缓,青瓦斜侧砌筑的脊身与正脊中花灰塑装饰共同构成了古朴自然的民居建筑屋顶装饰一部分。阆中古城民居建筑屋顶瓦当为整体建筑装饰锦上添花,一般采用灰陶材质下垂尖形和如意状滴水与圆形或半圆形瓦当相结合的形制,不仅具有防止雨水回流的作用,同时刻画吉祥图案为古建筑增添了美好寓意。
(2)檐下。
阆中古城建筑大多沿街而建,为保护墙身、支承屋顶,出檐深远,多采用穿斗结构,穿过檐柱一头挑于檐下叫作“挑枋”,根据出檐长短可分为单挑、双挑和三挑,阆中古城建筑多见单挑,常在其下加以斜撑以增加结构稳固性。挑枋其本身就被赋予了修饰建筑外立面的作用,与撑拱、雀替等共同成为民居装饰构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装饰纹样简洁清新,常见卷云、象头等样式,保持了檐口的轻巧流线,成为巴蜀建筑装饰中极富特色的部位。
承受屋檐和挑枋之间的力的构件称为撑拱,是中国四川古建筑特有的穿斗结构构件,它使檐下的装饰千式百样,也使阆中民居建筑出檐更为深远。由于撑拱的装饰面积较大,且阆中古城民居建筑多为单层建筑,撑拱高度与人们视线高度相平,挑枋与柱之间通过撑拱的装饰过渡达到自然和谐的效果,使得撑拱成为匠人发挥精巧木雕技艺的重点。
坐墩是一种特殊的瓜柱,其用于挑枋与屋顶的檩木之间,支撑上层挑枋或挑檐檩,因其体形短小,所以称之为“坐墩”。由于阆中古城建筑屋顶不设天花,穿斗木结构展露无遗,故对坐墩做装饰处理。相比挑枋来说,坐墩表面雕刻花纹工艺略复杂,为木构件增添了艺术表现力。吊瓜是指穿过挑枋而垂下的柱头,也称“垂花柱”通常雕刻成瓜形,雕刻手法采用圆雕,样式有繁有简。
(3)石构装饰。
阆中古城所处地区湿热多雨,民居建筑中柱础则成为必不可少的石质构件,它能承受房屋柱结构的压力且保护木柱不受潮腐蚀。阆中古城建筑的柱础形式多变,以方形柱础和复式柱础为主,多用浅浮雕石刻装饰。门枕石位于大门两侧支承门框、门轴基石部分,简单加工使其呈方形或圆柱形,阆中古城建筑门枕石以方形为主,多设“抱鼓石”,装饰敦厚质朴。
(4)门窗。
夏商时期就有传统建筑门窗的史料记载,随着建筑规模的扩大,门窗的样式也越来越多,明清时期遗存了大量的建筑门窗,如板门、槛门、支摘窗、隔扇等。阆中古城的木雕门窗极具艺术性和观赏性,是古城建筑木雕装饰中的神来之笔。门窗花格造型繁多,排列图案各式各样,每个部件都饰以不同的纹样,在雕刻技法上也颇为复杂,结合高凸浮雕、线雕、镂空雕等技法,一窗一景,似隔非隔,既具有儒雅之风,又巧夺天工,给人穿梭于时光的视觉享受,体现了多姿多彩的木雕文化。
1.3 独立装饰(软装饰)
在阆中古城民居建筑装饰艺术中,神龛、楹联、匾额作为一种补充,对建筑整体的装饰作用也不可小觑。由于清朝时期“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阆中古城大多民居建筑仍注重堂屋设祭祀祖先的神龛,一般民居堂屋太师壁前放几案,几案上供奉装饰质朴的神龛,大户人家的神龛雕刻精致,加以彩绘以凸显家族的社会地位。楹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多刻画或悬挂于宅堂的楹柱之上,故作“楹联”。张飞庙垂挂着诗人流沙河所撰楹联,“园谢红桃,大哥玄德二哥羽;国留青史,三分鼎势八分书”,寥寥几笔,以对偶、修辞技法描绘了三国时期的背景,诠释了张飞文武兼备的形象,也彰显了楹联在装饰艺术中表达人们精神诉求的作用。匾额悬挂于门屏上以作装饰之用,反映建筑物相关属性,集文学、书法、雕刻、装饰艺术于一身。一般民居建筑匾额多黑底金字且四周简单包边不作装饰。
2 装饰部位与装饰题材关系
建筑装饰制度在宋朝时就已逐渐完备,早在建筑学文献《营造法式》中对建筑装饰部位与题材就有所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装饰尤其在题材方面独树一帜,不同建筑部位根据建筑功能、建筑形制的不同赋予其内容多样的装饰题材,表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也各具特色。
2.1 建筑主体装饰纹饰
阆中古城民居建筑外墙多采用空斗砖勾画十字缝,常见梯状、八字形砖墙,穿斗木结构与白墙、青瓦不施彩绘、雕刻等装饰,墙体上多开花窗,建筑主体墙面几乎不作装饰,少数点缀花草题材装饰,保持巴蜀传统建筑的质朴素雅,具有鲜明的地域风格。
2.2 建筑附属构件装饰题材
阆中古城建筑的附属构件装饰多分布于屋脊、瓦当、挑枋、撑拱、吊瓜、门窗、门枕石和柱础等部位,装饰题材多样,雕刻工艺精巧。建筑附属构件装饰题材涉及自然、文学、宗教、神话、生活等诸多内容,充分体现巴蜀传统建筑所蕴含的地域人文精神。阆中古城屋脊中花一般以“品”字型、“铜钱型”和“花瓣形”瓦片合叠的形式,少数屋顶正脊中花装饰采用灰塑,灰塑中花没有像岭南地区建筑装饰的各异样式,素面灰塑更加符合阆中古城整体敦实厚重的历史韵味,蝙蝠纹、寿字纹、回字纹等纹样是少数灰塑中花装饰主要形象,简洁又美观;在一般民居建筑瓦当、滴水上经常能找到莲花、菊花等吉祥植物的形象,蝙蝠、狮子等动物题材少量出现在祭祀性建筑和纪念性建筑上,寓意吉祥的动植物纹表达了宅院主人美好心理寄托[1]。
阆中古城建筑木雕装饰题材丰富多彩,卷云纹、动物纹、如意纹、花草纹、神话故事在木结构装饰中占有重要地位。阆中古城建筑檐下挑枋造型生动有趣,装饰题材以卷云纹、如意纹居多,少数象头、鳌鱼状等动物题材跃然出现在挑枋上; 民居建筑撑拱雕刻题材多为几何纹、曲纹、植物纹等,大户人家和纪念性建筑延续龙凤题材,并有狮子、博古架、文臣武将等题材出现;阆中古城建筑对门的装饰十分讲究,门簪、连槛横木都是装饰重点部位,题材常见四季花、团福寿、卷云、如意、蝙蝠纹样,纹样精细,寓意福寿安康[2]。
3 装饰解析
3.1 造型
阆中古城民居建筑正脊常用青瓦斜侧砌筑,脊尾呈上翅形态(见图1),灰塑没有镂空和雕花等复杂装饰,小青瓦在脊下叠置,与朴实的中花灰塑格调一致。屋脊、山墙、瓦当常见植物纹和动物纹样,植物纹多卷草纹、“岁寒三友”纹及“四君子”纹(见图2),造型丰富,运用渲染法,形态优美,雕刻线条细腻,整体气质清新脱俗,也体现了古时所崇尚涅而不缁的高尚品质。动物纹如蝙蝠、凤凰等多与“寿”字纹、牡丹纹结合,构图严谨,注重形态的灵动性,表达人们对福寿康宁的追求[3]。

图1 脊尾(来源:作者自摄)

图2 瓦当植物纹(来源:作者自摄)
阆中古城建筑木雕做工精细,常常雕而不漆,突出本质,在质朴中显示出工艺的精湛。阆中古城建筑挑枋上的浅浮雕多雕刻成象头、鳌鱼等瑞兽造型(见图3),一般下部附以辅助挑枋,饰以简化花鸟虫鱼图案,造型朴实,与主挑枋装饰纹样主次分明,赋予装饰节奏感。民居吊瓜形状以简单南瓜造型或灯笼状为主(见图4),坛庙建筑、标识性建筑的吊瓜多采用繁复的浮雕和透雕,镂空雕饰出花草、动物,附以卷云纹样,以装饰檐口,营造动态之美。
阆中古城建筑为明清时期遗留,其木雕门窗大部分保留清朝时期精美、繁复的装饰风格,木质隔扇长窗多用双面立体的透空雕、线雕、混雕等手法来雕刻民间传说、历史故事、虫草鸟兽、吉祥图案等纹样(见图5),手法精细,施以纹样优美的姿态及流动的线条,在注重整体图案和谐的同时注重细节的刻画。少部分窗格遵循对称排列、单独纹样排列及连续纹样组合的法则,保留明代简约、质朴的装饰风格,周围填充卷草纹、花卉纹等纹饰点缀,构图饱满,形式感较强,整个场景有虚有实,通透变化[4]。阆中传统雕花木窗在雕刻工艺的水平方面,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在窗扇的主要雕刻面精雕细刻,力求图案精美、线条生动,更是在细节处理方面也面面俱到,尽可能加以装饰。

图3 象头挑枋(来源:作者自摄)

图4 吊瓜装饰(来源:作者自摄)
民居建筑方形柱础多素面朴素装饰,少数采用复式柱础装饰精巧(见图6),柱座为刻有“万字纹”“回字纹”的方形基座,与八棱柱石墩相连,上部是饰以石钉的鼓形石板,整个柱础造型与柱形协调一致,富有厚重感和层次感。大型宅院的门枕石上多设“抱鼓石”,与石狮子相结合,用浅浮雕的手法在石鼓上饰以花草、瑞兽等图案,可见明清时期院落主人对宅门装饰的重视,须弥座下门枕石造型简洁质朴,与石鼓装饰疏密有致,独具匠心[5]。

图5 门窗木雕(来源:作者自摄)

图6 复式柱础(来源:作者自摄)
3.2 内涵
建筑装饰,是人们在共同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具有图案性质的符号,反映的不仅是某一系统的审美情趣,还包括这一系统在文化及信仰上的取向。植物纹样的出现是中华民族品位高雅的人文文化一种体现,阆中古城运用广泛的卷草纹一般单独图案连续排列,与卷云纹相似,婉转自如,用来饱满装饰纹样的同时寓意“吉祥之气”连绵不断;几乎遍布民居建筑装饰的“岁寒三友”题材和“四君子”题材在木构件上的应用,是对松、竹、梅等植物坚韧不拔的秉性延续,比拟古时文人墨客所崇仰的刚直与洁白自若的品格,来表达院落主人的追求。
“三阳开泰”“五福捧寿”“福禄平安”等是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祥瑞纹样,在阆中古城民居各处均有雕刻,饱含当地先民古老的自然崇拜。阆中古城享有“蜀之人物,惟阆为盛,科名之盛,甲于天下”的美誉,龙纹的大量运用体现出明清时期阆中先人尚文好学及入仕后对朝廷的巨大贡献。动物纹多采用谐音比拟的表达手法,如“富贵(桂)平(瓶)安、事事(狮狮)如意、喜(喜鹊)事(柿子)连(莲花)年等吉祥图案,阆中古城建筑“抱鼓石”上多雕刻两只石狮子(见图7),表达主人好客热情的同时赋予其“事事如意”的内涵。在创作时取事物的谐音或寓意和象征意义,有时把毫不相干的内容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具有美好寓意的图案。这些谐音比拟动物题材反映了古时先民对自然事物的崇拜遗风,追求装饰纹样和精神寄托的统一,成为阆中古城建筑装饰蕴含历史文化的写照[6]。
人物装饰题材多取自尊敬崇拜的神话故事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历史故事,如“福禄寿三星”“八仙庆寿”“渔樵耕读”等图案,先民通过对神灵的崇拜,秉承道家思想,期盼生活安康、延年益寿、驱灾免难。阆中古城门窗装饰和木构件装饰多选用人物场景题材,花窗窗芯多刻“八仙”“两老对弈”“麻姑献寿”等,大户人家大门撑拱上可见高浮雕“四大天王”“杨门忠烈”等形象(见图8),弘扬民间故事中蕴含的“礼”“义”“仁”“智”等美好德行,装饰纹样在彰显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展现了阆中古城建筑装饰巧夺天工的木雕技艺。

图7 抱鼓石装饰(来源:作者自摄)

图8 “四大天王”撑拱装饰(来源:作者自摄)
4 结语
建筑装饰是阆中古城生活情趣和审美修养的产物,是传统民居建筑装饰实用性和艺术性结合的典范。该文通过对阆中古城建筑装饰纹样考察发现,因装饰部位、装饰题材、寓意内涵等方面内容丰富,潜移默化影响着明清时期古城建筑装饰特点和建筑风格特征。阆中古城通过精粹考究的木雕、石雕等装饰手法,具有文化个性的装饰题材和内容使蕴含的生活理念和艺术追求显现,为现今多元文化融合的装饰艺术提供了借鉴。对阆中古城的建筑装饰的传承应发扬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秉承木雕装饰的匠心技艺和文化特质,提高对建筑装饰艺术的审美力和保护意识,以实现中华传统建筑文化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