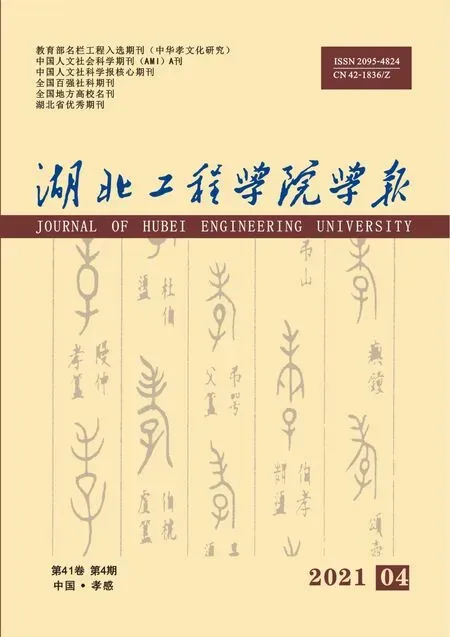隐私期待理论下手机搜查的比较分析及法律规制
2021-01-15孔丽君
孔丽君
(广西大学 法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国家公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最频繁的表现已经不是公权力对公民自由、财产等传统权利的侵犯,而是公权力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1]与传统的实物搜查不同,作为一个承载海量数据信息的虚拟空间,犯罪嫌疑人手机中不仅可能存在重要的犯罪证据和线索,通常其中涵盖的私密信息甚至比住宅中可搜查出的东西还要多,如果不加限制地允许侦查人员随意搜查,则会使本就脆弱的公民隐私权“一碰就碎”。那么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手机能否进行无证搜查?其搜查条件是什么?搜查界限又在哪里?本文将通过研究、借鉴西方国家相关判例和经验,在“隐私期待理论”下分析我国刑事侦查活动中手机搜查相关法律规范,以期我国手机搜查活动能在打击犯罪和保障公民权利之间达到一种动态平衡。
一、隐私期待理论下的“手机搜查”
隐私权最早被认为是“个人独处的权利”[2],即除非存在公益要求或其他合法依据,否则公民有权保持其隐私生活免受外界侵扰。相较于我国,西方国家更早关注也更加重视公民隐私权的保护,美国是其中的最典型代表。196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卡茨案中确立的“合理的隐私期待”(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标准,标志着《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以下简称《第四修正案》)适用与公民隐私权范围界定的里程碑式发展,其后为英国、新西兰、加拿大和欧洲人权法院吸收和借鉴,成为各国公民隐私权保护的法脉准绳。在手机搜查的法理分析中,“合理的隐私期待”标准的引入不可或缺。
1.美国“合理的隐私期待”标准的确立。在Katz v. United States案(1)Katz v. United States, 389 U.S.347, 361(1967).中,美国检方控诉卡茨通过公共电话传递赌博信息,其证据是联邦调查局探员通过窃听设备获取的通话内容,并且在获取该证据时未持有任何合法有效的搜查令状。卡茨对此提出异议,认为FBI窃听获得的电话录音证据违反了《第四修正案》的规定并侵犯了其个人隐私权益,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初审法院与上诉法院均支持该证据具有证明力,并对卡茨作出有罪判决。但最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决,其观点是《第四修正案》目的在于保护公民隐私免于部分类型的政府侵扰,当搜查行为冒犯了个人“合理的隐私期待”时,即构成非法搜查,并排除了该窃听录音证据,对卡茨作出了无罪判决。
卡茨案建立了一个双重检验标准,来确定第四修正案是否保护公民活动不受政府干预:(1)主观标准,即当事人是否存在对隐私权的实际期待;(2)客观标准,即社会是否认可这一期待具有合理性。由此标准我们可以审视一个具体的手机搜查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当公民对其手机中的数据信息持有“合理的隐私期待”时,那么该手机搜查行为就侵犯了该公民的隐私权,因此取得的证据也不具有合法性而应予以排除;反之,该手机搜查行为则合法,因此取得的证据也应予以采纳,即只要存在“合理的隐私期待”,政府利益必须让位于公民个人的隐私利益。
2.其他国家对隐私期待理论的吸收与借鉴。鉴于美国隐私期待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成功运用,英国、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也逐渐青睐这一理论,并加以吸收、借鉴来判断政府的搜查行为是否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利。
在2004年的Campbell v. MGN案中,英国法院首次适用“合理的隐私期待”标准来裁决隐私权案件。英国判断一项隐私是否给予保护也是主客观相结合的模式。英国在此模式下考虑手机搜查的合法性分为两步,第一步,分析当事人对手机中的数据信息是否具有“合理的隐私期待”,如果没有则不受保护,如果有则进行下一步讨论,即针对该案具体情况进行利益衡量与取舍。需要注意的是,二者是步步递进的关系,前者成立才继续后者的利益权衡。[3]
在加拿大R. v. Wong案(2)R. v. Wong (Ont CA),[1987 ]OJ No 267, 19 OAC 365, 34 CCC (3d) 51, 56 CR (3d) 352, 1 WCB (2d) 415.中,Wong被指控在一旅馆房间内开设赌场从事非法赌博活动,其证据是一份在旅馆管理部门的许可下安装的一个摄像机拍摄到的监视录像。Wong则以该录像证据侵入其生活“场所”侵犯了其宪法上的隐私权而主张予以排除。加方法官的观点是,警方合理地认为嫌犯存在犯罪行为且就在该房间,逮捕也系合法,因此其有权进行合法逮捕所附带的合理搜查,而搜查权包括搜查被逮捕者及其周围环境的权利,因此Wong不具有“合理的隐私期待”,当时获得的证据也应予以采纳。在冲突利益的权衡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加拿大更倾向于保护打击犯罪的国家利益。在手机搜查中,也是如此。
不同于英、美、加等国,德国对隐私权的保护是在一般人格权概念的基础上,创设出保护隐私权的“三阶层理论”。这种隐私权保护模式也极具合理性,它按隐秘程度将隐私权划分为不同等级,并在法律上给予不同程度的保护。在此理论的基础上判断政府的手机搜查行为是否合法,首先要确定手机信息属于哪一隐秘层级、法律给予何种程度的保护,然后才能对该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判断。
3.“合理的隐私期待”标准在手机搜查行为中的适用。在美国的United States v. Wurie案(3)United States v. Wurie, 612F.Supp.2d104, 109(D.Mass.2009).中,伍瑞因涉嫌贩毒被捕,并搜出两部手机。在到达警局后,警察通过手机锁屏发现一个多次来电的号码——“我家”,于是打开该手机搜查有关信息。警察在手机桌面发现了一张女人的照片,然后打开通讯录找到了那个名为“我家”的号码。通过这个号码地址警方找到了一栋带有伍瑞信箱的公寓大楼,并透过窗户在一房间内发现了与伍瑞手机背景屏幕上女子相像的那个女人。警方其后申请了搜查令并在该公寓搜到了枪支与毒品。据此伍瑞因涉嫌毒品犯罪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受到指控,但伍瑞对警察无证搜查其手机的行为提出异议,认为警方只获得了该公寓的搜查令,而未获得搜查其手机信息的授权,该手机搜查行为侵犯了他在宪法上的公民权利并主张排除警方因此在公寓中获得的相关证据。初审法院驳回了该异议,认为警方逮捕附带搜查其手机的行为合法并判伍瑞有罪;而上诉法院则撤销了初审法院对案中手机搜查获取证据合法性的裁定和伍瑞的有罪判决,认为即使已经逮捕,警方未经法院许可也无权搜查嫌犯手机;最高法院维持了该判决。
为保护公民隐私权,美国《第四修正案》规定搜查行为需获得授权令才得以进行,只有在一些特殊的例外情况下,如在本案中的“逮捕附带搜查”的情形中,“无证搜查”才是合法的。[4]伍瑞案的争议焦点就在于警察对手机的搜查行为是否属于第四修正案保护公民隐私权的例外,即警方“无证搜查”手机中数据信息的行为是否合法。针对此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14年6月25日对本案及Riley v. California案(4)Riley v. California, 573U.S. (2014).作出了联合判决。最高法院认为,与以往情形不同的是,手机中含有大量与生活隐私相关的信息,其中存储的数据也应受到《第四修正案》的隐私保护,即使是为打击犯罪也不能以入侵公民隐私为代价。因此,手机搜查不属于第四修正案保护公民隐私权的例外,警方若想搜查嫌犯手机,即使是正在执行逮捕也必须向法院另行申请搜查令状。
这份判决实际上是确认了手机所有人对手机中的数据信息具有“合理的隐私期待”,认为手机中包含了大量个人隐私信息,在主观上,确实存在对手机中数据信息的实际期待,客观上,社会公众也认可这种对手机中数据信息的期待是合理的,即使是为打击犯罪的国家利益也不足以撼动其中蕴含的庞大的公民隐私利益,因此,卡茨案中“无证”搜查的行为在手机搜查中更不被允许,必须坚持令状原则,先从法官处获得合法的搜查令状才能进行手机搜查。
二、手机搜查之“令状原则”的例外
从美国的司法实践来看,隐私期待理论并非“一刀切”地认定公民对某项事物是否享有隐私权并排除政府干预,而是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的。一般来说,手机搜查行为应坚持令状原则“持证搜查”,但我们无法保证这一原则能够周延到每一种具体情况,因此美国司法先例中也产生了诸多例外情形。
1.被搜查人同意下的手机搜查。如前所述,我们认为手机所有人对其手机中的信息数据有“合理的隐私期待”,对其中的隐私利益享有合法权利并排除政府干预,但既然是权利,就存在放弃的可能性。正如刑法领域中“被害人同意”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阻却犯罪,在刑事诉讼领域,如果相对人自愿同意搜查,执法人员就可以无需搜查令搜查一个地方或物品,即“同意无隐私”[5]。在法理上我们认可这种基于被搜查人同意而对其手机进行“无证搜查”的合法性,根据“利益放弃说”[6]的观点,其实质是被搜查人放弃了自己的隐私利益。
对隐私利益的放弃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但这种“同意”不是无条件的。首先,这种同意不能违背被搜查人的意愿,否则就成了变相的强制“无证搜查”,其违法性不言自明;其次,还需要考虑被搜查人的行为能力,综合其年龄、精神状态等因素,确定其是否具有“同意”能力;再次,其程序必须具有正当性,如搜查前告知相对人有权拒绝搜查等;最后,即使被搜查人同意,也应在其同意搜查的范围内进行。
在United States v. Blas案(5)United States v. Blas, 1990 WL 265 179,at*20(E.D.Wis.Dec.4,1990).中,布拉斯因合谋分发可卡因受到指控,但对侦查人员搜查其传呼机获得的证据有异议,他认为其同意警察查看他的传呼机仅限于查看该传呼机的外观而非查看其中的信息数据,要求排除在电子传呼机内存中发现的证据;警察认为被告同意“查看”传呼机就是同意启动传呼机并获取信息;法院认为,个人在寻呼机、计算机或其他电子数据存储和检索设备中的隐私预期与在封闭容器中的相同,同意“查看”该容器并不是同意查看容器内容。当警察问布拉斯“那是你的传呼机吗”或类似的问题然后要求查看时,布拉斯就可以合理地认为,警察只是想确认那是一个传呼机而不是武器。一旦警察完成查看传呼机外观的行为,布拉斯的同意即告终止,因此法官认定警察查看布拉斯传呼机中内容的行为超出了其同意范围,布拉斯对传呼机中的内容仍有“合理的隐私期待”并受到《第四修正案》的保护,最终排除了该项“非法搜查”获得的证据。与传呼机相比,智能手机能够储存更多信息;和计算机相比,智能手机储存的信息不一定更多但通常更加隐私,如果认定被搜查人对其同意范围之外的传呼机和计算机中的信息都有“合理的隐私期待”,那么智能手机的被搜查人就更应该对其中存储的信息享有隐私权。我们可以看出,犯罪嫌疑人同意的情况下,符合一定条件侦查人员就可以对其手机进行无证搜查,但不可以超过其同意搜查的范围。
2.紧急情况下的手机搜查。在一些美国司法判例中,法院认为“紧急情形下没有隐私”,紧急情况下侦查人员有合理根据也可以“无证”实施搜查、扣押行为。通常紧急情形包括:搜查目标对警员或他人人身、财产构成巨大威胁;证据可能被马上被销毁;犯罪嫌疑人可能马上逃脱等。其中证据保全目的在手机搜查中被援引最多,一方面手机不属于杀伤性武器,一般不会对警员或他人人身造成严重侵害,另一方面,手机中的数据具有脆弱性而容易被删除或销毁。但对于紧急情况下能否对手机进行“无证搜查”,法官们的观点并不一致。
在United States v. De La Paz案(6)United States v. De La Paz, 43 F.Supp.2d at 376(9th.Cir.2003).中,法院认可了警察无搜查证接听嫌犯手机的行为,认为警察有合理理由怀疑这通电话与涉案毒品交易有关,如果该情形下不接听这通电话则可能永远丧失接听这通电话可能获得的证据,从而导致无法查清其犯罪事实。在United States v. Young(7)United States v. Young, 2006 WL 1302667, at*13(N.D.W.Va May.9,2006).一案中,法院也支持了警察对涉案手机中数据信息的无证搜查,认为嫌犯对手机相关信息设置了一天后自动删除,如果不马上搜查会永久丧失该证据,因此属于可以无证搜查的紧急情形。
综合以上判例观点来看,某些紧急情况下警察可以对嫌犯手机进行无证搜查,但是需要有严格的条件限制。首先,只能在为了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证据保全、防止嫌犯逃脱等紧急情况下进行;其次,警察必须有嫌犯利用该手机进行犯罪的合理根据;最后,搜查范围仅限于一旦删除就无法恢复或恢复成本极高的电子数据以及接听电话、查看短信等简单搜查。一方面,被搜查人对与犯罪有关的通话记录、短信等隐私利益较小,不足以对抗打击犯罪的国家利益,紧急情况下可以进行无证搜查,一方面,其对手机中其他信息仍拥有“合理的隐私期待”,如需搜查必须向法官申请搜查令。
3.逮捕时附带手机搜查。逮捕附带搜查是指警察在实施合法逮捕时即使没有令状也可以搜查嫌犯人身或附近可以控制的物品、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所在处所等,由此获得的证据可以作为定罪依据。(8)Week v. United States, 232U.S.383, 392(1914).但逮捕附带搜查有着严格的适用条件:一是嫌犯被合法逮捕;二是搜查的范围仅限于嫌犯的身体或者是与其身体密切接触的物品;三是搜查必须在逮捕后的合理时间内进行。[7]
在美国,多数法院赞成逮捕时附带手机搜查。譬如,在United States v. Wurie(9)United States v. Wurie, 612F.Supp.2d104, 109(D.Mass.2009).与United States v. Gordon(10)United States v. Gordon, 895 F.Supp.2d 1011, 1024(D.Haw.2012).案中,法官分别将手机比作一个密闭的容器和嫌犯身上的钱包,均认为逮捕时无证也可以附带搜查手机。但也有少部分法院持相反意见。在United States v. Flores-Lopez案(11)United States v. Flores-Lopez, 670 F 3d 803, (7th.Cir.2012).中,法院对警察逮捕嫌犯并对其手机进行无证搜查所获证据效力并不认可。在其看来,手机与钱包或封闭的容器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作为一个可以存储海量信息虚拟空间,智能手机中的信息量即使是一个房间中存放的所有物品也不能及,况且其私密性也是封闭容器所无法比拟的。两种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于将手机视为个人要素还是个人占有物,导致逮捕附带搜查手机时对于时间要素和空间要素的组合和考量不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
大多数法院认为手机属于个人要素,并将其视为与嫌犯紧密相连的随身物品,因而将警察的搜查行为从逮捕时延长至逮捕后一段时间,这期间警察都可对嫌犯手机进行无证搜查,即搜查时间的设定比较宽松。在United States v. Finley案(12)United States v. Finley, 477 F.3d 250, 260 (5th Cir.2007).中,Finley因贩毒被捕,在被带回警局之后,警察才通过搜查其手机发现了其贩卖毒品的证据。法院认为,手机是在嫌犯身上发现的,因此将手机视为与嫌犯紧密相连的随身物品,属于个人要素,因此警察在将嫌犯带回警局后再搜查其手机的行为也是合法的。在The People v. Riley案(13)The People v. Riley, 2013 Cal.App.Unpub.LEXIS1033,1.中,上诉法院判决认为,只要手机被嫌犯随身携带,就被视为是与其紧密相连的个人要素,警察无证搜查该手机数据信息的行为就是第四修正案所允许的合法行为。
但还有少数法院认为手机是个人占有物而非个人要素[8],因为手机中通常存有海量隐私信息,其特性是口袋中的钱包、钥匙等传统实物无法比拟的[9],被搜查者在手机中庞大的隐私利益也不容忽视,因此将其解释为个人要素而赋予警察过于宽松的搜查时间是不合适的,从而对手机无证搜查的时间范围应做严格限制,甚至仅限于逮捕的同时。在State v. Novicky案(14)State v. Novicky, WL 1747805, at*4-5(Minn.Ct.App.Apr.15, 2008).中,法院因警方将嫌犯逮捕后的第二天才对其手机进行搜查而排除了据此获得的证据。在United States v. Lasalle案(15)United States v. Lasalle, Wl 1390820, at*7, (D.haw.May 9, 2007).中,警察在逮捕嫌犯3小时后搜查其手机获得的犯罪证据也被法院认为时间过长而排除。
对于逮捕附带搜查嫌犯手机的时间范围,我们比较认同后者的观点,即使是被逮捕嫌犯对其手机中庞大的隐私利益也仍具有合理的隐私期待,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虽然此时这种保护是有限的。因此,不能将逮捕附带搜查的时间设定过于宽松,最合理的是搜查时间应限于逮捕的同时或接下来的短时间内尽快搜查,如果逮捕嫌犯后长时间未搜查其手机就应当申请搜查令再实施搜查。
通过对域外手机搜查相关规则的探析,我们可以看出各国制度设计在平衡个人隐私权利与国家搜查权力中的审慎态度。实际上,各国对于手机搜查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即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充分尊重个人权利。尤其是美国,其警方在对手机进行搜查时必须持有法官令状,虽有无证搜查的例外,但均附以严格的适用条件。
三、我国手机搜查相关规范及其不足
1.我国手机搜查相关规范。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的健全与发展,我国法制建设越来越注重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我国宪法第40条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4条规定非法截获、篡改、删除他人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数据资料,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252条侵犯通信自由罪中规定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在当代信息社会,手机尤其是智能手机已经成为社会公众最重要通讯工具,其中蕴含的隐私保护至关重要。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通过以前,我国立法仅存在对一般物品与场所进行搜查的相关规定,2012年《刑事诉讼法》首次将电子数据规定为法定证据种类,但未规定该类证据搜查的特别程序;其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11月22日修订后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16)2019年12月30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最高检《诉讼规则》)重新修订施行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高检发释字〔2012〕2号)同时废止。、公安部于2012年12月13日修订后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17)2020年7月20日,《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公安部《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59号修正施行。、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0日修正后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18)2021年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发布并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2〕21号)同时废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6年9月9日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电子数据若干规定》),几个司法解释针对电子数据的相关术语、收集与提取、移送与展示以及审查与判断等方面进行了细化规定,一定程度上弥补了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不足,但尚未涉及电子数据的搜查问题;2019年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以下简称公安机关《取证规则》)增加了电子数据的检查和侦查实验、委托检验与鉴定等问题,但实质上仍然是对电子数据本身真实性判断的进一步细化,仍未触及电子数据包括手机中数据信息的搜查授权、搜查程序等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立法并未明确智能手机搜查的概念,并在实质上将其拆分为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检查等步骤。总之,手机数据信息地位在实践中被等同一般电子数据,手机搜查也无专门程序规范,即在我国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手机中电子数据的搜查无需特别程序的限制,通过自我授权即可对手机进行搜查,这对公民隐私权益的保护极为不利。
2.智能手机中的数字化信息对于现代侦查工作具有特殊意义和重要价值[10]。手机搜查的实质是对以其为载体存储的“数据信息”或称“电子数据”进行搜查。目前我国立法并未明确智能手机搜查的概念,并在实质上将其拆分为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检查等步骤。具体而言,因为缺少专门的程序规范指引,智能手机搜查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搜查无需特别授权。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规定,只要满足“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这一主观条件便具备启动搜查的理由,并无客观标准要求,使我国搜查条件在实质上并未受到限制。并且,根据最高检《诉讼规则》第203条以及公安部《程序规定》第222条规定,经县级以上侦查机关负责人批准便可实施搜查。然而,以上三条均规定搜查对象仅限于“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等有体物,即对手机中电子数据信息的搜查无须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如此一来,其实变相地赋予了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自行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手机进行搜查的权力,极大地损害了手机搜查对象的隐私权益。
其二,搜查程序不规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38条、最高检《诉讼规则》205条以及公安部《程序规定》223条规定,进行搜查须出示搜查证,但在执行逮捕、拘留时若遇紧急情况也可以进行“无证搜查”,虽然最高检与公安部对“紧急情况”予以具体说明和解释,但实质上仍未将智能手机等电子数据的搜查纳入其中。实际上,侦查人员在司法实践中对智能手机的搜查几乎也都处于“无证搜查”状态,这为个人隐私保护埋下巨大隐患。此外,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最高检《诉讼规则》203条以及公安部《程序规定》222条规定,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都可以进行搜查,不需要对搜查对象进行严格限制和具体描述,可见对传统实物的搜查范围弹性极大且具有极强的任意性,若不加限制、直接套用于对智能手机的搜查,其对相对人的财产权、隐私权的巨大危害性不言自明。
其三,缺乏事中监督与事后救济。随着立法者对信息保护的日益重视,《电子数据若干规定》以及公安机关《取证规则》对电子数据及其存储介质的收集、提取和扣押等程序需要有见证人在场监督,但其后的检查、侦查实验、委托检验与鉴定等步骤都不需要见证人的监督,以及见证人的担任条件也未有具体规定,这种随意性极易导致手机等电子数据的搜查因缺乏有效监督而“失真”。此外,若在此搜查过程中,手机搜查所获证据程序违法该如何补救?相对人的隐私权益受到损害又如何救济?目前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
总之,手机数据信息地位在实践中被等同一般电子数据,手机搜查也无专门程序规范,即在我国侦查人员通过自我授权即可对嫌疑人手机进行搜查,这对公民隐私保护极为不利。
四、我国手机搜查法律规制路径之探析
1.规制刑事侦查中手机搜查行为的必要性。首先,截至2020年3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8.97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3%,较2018年底提升0.7个百分点[11],手机搜查涉及权利主体数量庞大。
其次,手机搜查与传统搜查有着本质区别。手机在当代被视为传统文件的新的表现形式,是隐私信息的高级“容器”[12],区别于传统实物搜查,智能手机中海量数据信息蕴含的巨大隐私利益使手机所有人对此拥有“合理的隐私期待”,其隐私权的保护一定情况下甚至可以对抗打击犯罪的国家利益。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成为我国立法和司法亟待解决的问题。
再次,我国手机搜查相关规范准备不足。《宪法》第37条中规定了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40条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刑法》第245条规定的非法搜查罪对司法工作人员从重处罚。可见,宪法已经赋予我国公民隐私保护以及免受国家机关非法搜查的公民权利。但在我国,大众对于侦查人员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为侦破案件搜查犯罪嫌疑人手机的行为仿佛已司空见惯,被搜查人通常也不会对搜查其手机行为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在司法层面,我国仍适用《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中关于传统实物搜查的一般规定,这对于手机搜查显然不合时宜。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莱利等案件确定的手机搜查的令状原则以及无证搜查的例外规定和司法经验已经比较成熟,对此我们可以借鉴以促进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
2.我国手机搜查法律规制路径。手机之于当代多数人是最私密的领域,即使配偶、父母也不能随意翻看,相对于钱包、提包甚至住宅,搜查手机对私权的侵犯更大,因此在制度设计与实践操作上必须慎之又慎。
其一,确立特殊地位,明确搜查原则。智能手机中蕴含的巨大隐私利益使其不同于传统搜查对象,为保障公民隐私,在搜查活动中法律应赋予其特殊地位,并进行专门规定。对此,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确立令状原则,即在对手机进行搜查前,应先取得司法机关签发的令状,因此除非符合“无证搜查”之例外规定,否则,取得证据将具有效力瑕疵甚至被剥夺证明能力。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签发令状的机关,美国的经验是由完全处于中立审判地位的法官签发,防止无实质理由的处分及对警察无法理性判断的假设,以确保手机搜查的权力不被滥用。然而,基于我国当前国情,检察机关则更适合担任手机搜查的令状签发机关,尤其是监察改革后检察机关的侦查压力大大减小,并且其定位就是法律监督机关,相对侦察机关更为中立。因此,由检察机关签发手机搜查令状不仅更为经济,也更加公正。
此外,手机搜查还应遵循目的正当性原则、比例原则等,确保搜查手机是出于侦破案件、抓捕犯罪嫌疑人等正当目的,并且仅在确有搜查必要情况下实施,所采取的措施也必须有助于搜查目的的实现,使对权利侵扰的强弱与隐私期待的程度相称或合乎比例,力求将私权利损害降到最低。
其二,细化相关规则,做好例外规定。首先是搜查条件。手机搜查对个人隐私侵害极大,因此手机搜查的批准须符合严格的法定条件,在合理怀疑的基础上,侦查人员还应提供相关初步证据:一是要有证据证明该案犯罪事实;二是有证据证明拟搜查手机中数据信息与该案有关;三是只能适用于立案后确有必要进一步收集证据才能查清事实的刑事案件;四是不允许为调查轻微犯罪和其他轻微违法而搜查手机。只有满足以上条件,侦察机关的搜查申请才能得以批准。其次是搜查令内容。在司法实践中,搜查令内容通常比较简洁,为侦查人员留下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若不加限制任其膨胀,则会严重侵害相对人权利。为此,搜查令内容应当明确、具体,载明搜查理由、搜查对象、搜查范围以及权利救济等内容,搜查理由应客观、具体,不可笼统地“一言以蔽之”,并严格限制搜查范围,发现其他证据除遇紧急情况外最好另行申请,超出搜查范围获取证据则会招致效力瑕疵甚至被排除。最后是“无证搜查”特殊规定。虽然刑事诉讼法等规定侦查人员在执行逮捕、拘留的紧急情况下可以进行无证搜查,但失之于宽泛、规制不足,若在手机搜查中随意引用则会使相关法律形同于无。因此,侦查人员无证搜查的行为必须受到一些特殊限制,一是紧迫性条件,无证手机搜查必须满足紧急情况、逮捕或拘留附带搜查以及被搜查人同意等例外情形;二是相关性条件,手机中数据信息确系该案犯罪相关;三是范围限制,只能搜查那些与该案犯罪相关的手机信息;四是时间限制,侦查人员在获取犯罪嫌疑人手机后应在合理时间内尽快进行搜查、取证;五是补正要求,原则上手机搜查应遵循令状原则,即使在可以无证搜查的紧急情况下,事后也应向审批机关作出合理说明、补正程序。
其三,保障隐私权利,加强监督、救济。首先是搜查主体与监督。一方面需要两名以上侦查人员共同搜查、相互监督,防止搜查权力的滥用和扩张。并且侦查人员中至少有一名具备熟练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必要时可寻求技术人员或有关单位的协助。此外,还要加强侦查人员培训,提高办案人员法治意识和法治水平,保障手机搜查依法进行。另一方面需要符合法定条件的见证人进行外部监督。实际上,我国相关法将手机搜查拆分成了手机中数据信息的提取、收集、检查与鉴定等步骤,但仅明确要求电子数据的提取、收集与扣押须有见证人在场,使这种外部监督无法覆盖搜查全程,易产生法律漏洞。因此,可以通过两名侦查人员的内部监督与见证人的外部监督形成监督闭环,有效遏制手机搜查过程中侦查人员的权力滥用。其次是程序违法的救济。一方面是对违反搜查程序所获证据的补救。此处可以参考英美国家刑事证据的有限可采性原则[13],根据违反程序获取证据所侵害相对人隐私权益的程度,可以将相关证据分为“强制排除”和“自由裁量的排除”两种。对于严重违反手机搜查实质性规定所获取证据应当予以强制排除,如未获取搜查令状、超出搜查范围、数据内容真伪不明等情况;相应地,对于那些未违反手机搜查实质性规定的轻微违反程序所获证据应适用“自由裁量的排除”,即经过补正或合理解释仍可以采用,如缺少见证人签字但有录像等进行佐证可以证明其真实性的证据、对手机数据相关内容注明不清但事后予以补正的证据等均可以作为事实认定的依据。另一方面是对隐私权受到侵害相对人的救济。我们可以参考《欧盟数据保护通用条例》第17条关于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的相关规定,将非法获取相关数据予以删除[14],并根据实际情况对受害人予以经济及精神上的补偿和安慰。
五、结 语
在隐私期待理论下,无论是按主观标准还是按客观标准,我们都认为公民对其手机中的数据信息具有“合理的隐私期待”,政府的手机搜查行为都应坚持“令状原则”,即以持有合法的搜查令状为一般准则,同时又存在可以“无证搜查”的例外情形,但这种搜查并非没有边际,必须在一定限度内进行。因此,侦查人员应注意手机搜查的条件、范围、时间、监督与救济等,平衡好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利益与保护公民手机隐私之间的关系,严格把握搜查的界限,有限度地进行手机搜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