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归纳问题的一种现象学理解
2021-01-13买买提依明·吾布力
买买提依明·吾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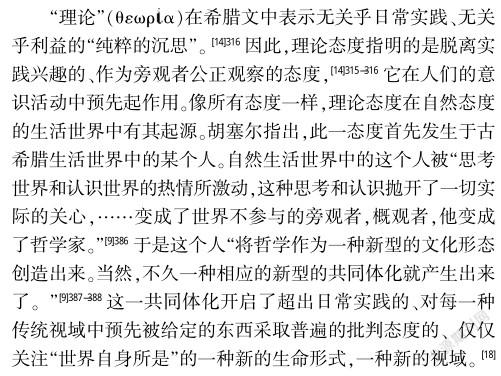
摘要:在现象学的思想道路上理解一事物,意味着由自行显现的原初意识现象而来,在绝然明见性中描述事物意义的本源性发生史。以此方式对归纳问题进行的理解表明,在意识现象的视域意向性中,归纳作为当下意识经验得以可能的条件自行发生。这种原始归纳是有限的、开放的,在生活世界的实践中不会构成一个问题。而发端于生活世界的理论态度则使归纳成一问题,因为此一态度要求认识行为通达理念的“真实世界”本身,而归纳无法通达此处。即便是在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实践中,承担起理论态度之认识任务的数学归纳,出于其本质上的有限性,仍无法胜任此任务。基于此,对归纳的怀疑和辩护的界限本身便获得了一种新的理解。
关键词:归纳问题;现象学;理解;自行发生
正统科学哲学基于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理解休谟所指明的归纳问题。在这一理解中,成问题的是依据多次出现的相同经验而达到的普遍性命题的有效性,而不是归纳推理中的单个经验本身。对于这种理解而言,单个经验是自明的,它直接把握着客观的外在世界或其表象。于是,这种理解一开始就忽略了经验本身所蕴含的一个认识论问题:意识的经验行为在何种意义上能够通达一个外在于经验的客观世界。这种客观性意义,在现象学的思想道路上得到了一种阐明。在阐明经验得以可能的先验条件之际,胡塞尔对归纳行为和归纳问题进行了现象学描述,这一描述构成了理解。
一、理解的前提:悬搁
胡塞尔的整个哲学都在“科学”领域内进行,[1]而这种科学乃是在古希腊哲学那里便已脱离“意见”(doxa)领域,进而追求普遍、必然、确定“知识”(episteme)的“严格科学”或普遍科学。胡塞尔指明,凭借于运思在此普遍科学之内,认识从一开始并在每一步都能够从自己的绝对洞见中为自己负责,[2]因为它合乎哲学的自我负责的彻底主义精神[2]9。胡塞尔之所以要在这种古典科学理念的彻底自负责性之内展开自己的思想,是因为在胡塞尔看来,“真正的人性和彻底自负责任的生存”是同一的,而“科学的自负责性与一般人类生存的全部责任”也是同一的,[3]胡塞尔期望认识能够自身负责。于是,对于胡塞尔来说,意识现象学成了这种自负责的“严格科学”。因为根据普遍科学,认识的基础及其展开的每一步必须在无前设的、绝对明见的、自身被给予的原初直观活动中显现出来。而现象学恰恰“是一门于其每一思考步骤里自身绝对自我证立的哲学。……是一种第一科学的观念,此门科学从一种坚持的和不可删除的、于此意义下为绝然的(apodiktisch)明见性出发,而且以相同的方式在此明见性的基础上建立、引申和证立每一接续的步骤。”[4]
基于这种科学理念,归纳在这种普遍科学中被理解之前需要被悬搁(epoché),这是因为:
(一)理解的严格性要求避免循环论证
归纳行为不是一种对象,而是一种认识方式。于是,在理解归纳以及归纳问题时存在一种循环论证的风险:以归纳理解归纳。因此,为了避免这种循环论证,在理解归纳之前需要悬置归纳。
(二)归纳的介入使得理解的绝然明见性变得不可能
19世纪下半叶开始流行的逻辑心理主义试图将普遍科学奠基于作为一门经验自然科学的心理学,进而把最具普遍性的可能思维之纯粹逻辑法则,即普遍科学置于心理學研究之内[1]25。胡塞尔对此进行的批判指出,经验心理学是归纳的,因而像所有经验科学一样,其认识无法摆脱或然性[5]。如果将普遍科学的原则建立在一门归纳性经验科学之上,那么我们不得不放弃认识可能性的普遍条件,我们的追寻终结于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5]108,而这就等于放弃了普遍科学的理念。基于此,胡塞尔区分了归纳的经验科学和作为普遍科学的现象学,前者唯在后者中才能得到理解。
(三)归纳推理基于其上的自然经验本身需要被悬搁,因而归纳推理也需被悬搁
归纳是对复多单个经验的归纳,因此归纳预设了单个经验之明见性,即在直观中对客观之物的直接把握。这种经验发生于胡塞尔所说的“自然态度”之中,此自然态度将世界视作预先被给定的、在时空中一直在此的现实存在的世界,并设定经验认识能够通达并认识这个世界[6]。胡塞尔指出了在此一自然态度中存在的“认识之谜”:作为一内在意识行为的认识活动,何以能够超越自身去通达、切中外在于它的客体?[7]换言之,作为意识行为的经验如何能够给出一个外在于意识的客观对象?[8]意识经验何以通达一个外在世界,只能由自行发生、自行显现的原初意识现象而来获得明见性理解。自然态度中的经验无法通达此一明见性,因为经验主义的归纳推理在将经验事物视作自明之际,并未分析使这种经验对象的现实性、客观性意义得以可能的内在意识行为本身。因此,归纳推理并没有从普遍科学的自明性根基起步,归纳推理的基础本身需要在现象学中得到理解。因此,在现象学的理解中,归纳推理需要被悬搁。
那么,悬搁归纳以后,现象学如何理解归纳?“如何”不仅关涉于将归纳理解为什么,而且首先关涉于以何种方式去理解归纳,后者通向前者。因此,这里首先需要指明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对理解的理解。这种理解与现象学本身是等深的。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将无前提、无先入之见的原初自明性,即自行显示的“事情本身”置于当下意识流之意向性,凭借于其立义活动,事物作为事物的意义得以发生。此乃原初自明的直观中自身被给予的纯粹现象,是所有认识的合法性源泉[6]84。此源泉使事物获得作为其所是的意义,因此认识和理解一事物意味着回溯其获得自身意义的原初明见性,由此原初明见性而来阐明其意义发生史。由于意义的意向性获取是先验的,因此意义赋予的历史发生为一先验的历史,胡塞尔将此先验历史视作真正的历史。基于此,胡塞尔指出,“真正的历史说明的问题,是与‘从认识论上进行的论证或澄清相一致的。”[9]这就是说,在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中,理解一事物意味着由自行显示的意识现象而来,在无成见、无前提的绝然明见性中描述此事物作为事物之意义的发生史。对归纳以及归纳问题的现象学理解,便发生在这一理解道路上。
二、归纳行为在意识现象中自行发生
从胡塞尔对理解的理解可以看出,现象学地理解归纳意味着由原初的当下意识流之意向性而来,描述归纳在意识现象中的发生史。对归纳的这种理解,应当包含归纳基于其上的经验的理解。而在胡塞尔的分析中,经验和归纳作为同一发生历程中的意识现象得到了理解,因为视域意向性由本源的意识现象而来,一并使得经验和归纳成为可能。
胡塞尔指明,最本源的纯粹意识现象发生为前对象的、前概念的、一直当下在场的、自行显现的内在时间意识流之意向性。它在绝然明见性中,即直观中自身被给予为“活的当下”。根据胡塞尔,原初的内时间意识并非是一个个点状时刻的意识,它具有“广延性”和“宽度”;而此一宽度并非由无数个点状时刻串联而成的宽度,它是一段连续同一的、永恒的“赫拉克利特之河流”。具有“广延性”的此一当下意识,即“现实性的高潮”,[10]被胡塞尔称为“原印象”。原印象总是带着一圈“晕”。原印象的晕延展至“刚刚过去”的原印象———“滞留”和“即将到来”的原印象———“前摄”。原印象、滞留和前摄连续地衔接为一段边缘模糊的原意识领域,它是非对象性地发生着作用的活的当下。当下意识经验总是在原印象的基底上向前延伸,凭借于前摄的期望和预示,在延伸的连续性中预期着当下意识流继续当下意识,进而朝向着与当下意识相似的意识。原印象的这种预期和朝向构造起了当下意识活动的未来边缘域,即未来视域。视域(Horizont)作为一地平线,指明着现象本身的边界或边缘域,它是有限的,却是不可逾越的,因为当意识朝着视域移动时,视域的边界随之而移动,如此移动的视域总是基于意识的当下位置、情况获得其可能性界域[11]。这就是说,未来视域乃是当下意识能够朝向的可能性范围,此可能性范围不是任意的,而是基于被当下化的先前经验之意义储备。
经验的意义作为意向相关项,在意识之意向性立义活动中获得其作为自身所是的意义。纯粹意识现象之意向性指明着意识在其所有行为中总是指向某物,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即意识是“意向的”。[12]意识的意向性活动乃是立义活动,此一活动总是构造着某物、指向某物,将某物意向为(intend……as)某物,[13]发生为“对象化行为”或“客体化行为”(objectifying act)[1]88。作为“对象化行为”的意向活动以及在当下意识流中前对象地被给予意识的“实项”内容,属于“真实的相即明见”内容;而意向对象,即在意向活動的对象化中被赋予某一固定意义的意向相关项,属于“意向的相即明见性”。[1]86-87当下意识流的真实明见性中的实项,总是在不同的视域背景下、从不同角度“侧显”出来的,如此显现的“实项”尚不是“某物”;而意识总是、而且只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此“某物”意味着在持续涌现着的当下意识流中被综合为“同一”的单个对象。于是,在当下意识流之“非课题的”相即明见性中,总是显现着超出当下内在意识的单一对象或事态,此单个对象或事态作为某物的意义“多于”相即明见性中的“实项”,被经验事物超出意识的内在性。这就是说,在意识现象的立义活动中,经验之物作为某物被构造起来,获得作为某物的意义,显现为超越于意识行为的经验物[14]。换言之,意识的意向性立义活动使经验事物的对象性和超越性获得其作为自身所是的意义,单一经验由此获得其外在性,即客观性意义,此客观性发生为内在意识的成就[15]。
在意识现象中如此获得其客观性意义的经验事物,超出意识流的侧显中前对象地、相即明见地被给予的实项内容,即超出了意识流的相即性本身。因此,在当下意识流中真实地显现之物,即实项内容,总是少于被意向之物的内容。因此,经验物的意义总留有“空缺”,它包含着“空乏意向”,它永远是未完成的。由于此空乏性,一个在其现实性中存在的经验之物,向着无限开放的充实可能性敞开着自己。充实作为一种意识行为,将一个空乏意向与当下发生着的直观活动带入一个综合性关联中,通过此一关联,一个空乏意向得到确认或受挫。超越之物的超出部分作为空乏意向性,期望着在连续不断地到来的当下意识中得到充实,而此一期望能够朝向的是由已被赋予意义的某一经验领域所开启的可能性范围,胡塞尔将此可能性范围指明为视域。对某物的经验,唯在视域中才是可能的,因为意识必须首先“知道”它使“超越之物”对自己显现出来的可能性范围,尔后才能够是关于某物的意识[12]18。在任何对象的显现过程中,对象的某些方面总是没有在当下直观中被给予,而是被期望着在将来的意识中得到充实。对象的那些非当下自身被给予的、在将来的意识活动中能够被给予的可能性方面,显现为视域意向性[15]162。视域意向乃是当下意识活动在已“看到”的东西的基础上向前“攫取”的意向[10]50。这是因为,凭借于当下意识的滞留作用,在“已看”的东西中保持着“意义的储备”,此一意义向外延伸,使得永恒当下的意识活动“带着意义的超验性。”[16]意义的此一超验性是关于对象物的一般经验得以可能的条件。也就是说,“任何本来意义上总是有所经验的经验,……都不言而喻地,必然地具有……对于此物的这样一种在经验尚未观看到它时即为它所固有的特性的某种知识和共识。这种前识在内容上未规定的或未完全规定的,但却不是完全空洞的,如果不同时承认这一点,那么一般经验就不会是有关一物和有关此物的经验了。”[16]47-48如此这般发生的“可确定的不确定性”,显现为视域。对一物的经验,即在意识活动中将一物显现为一物的意识行为,必然伴随着视域。
在当下意识的未来视域之中,感知之物的显现之所以是“依据相似性”的显现,其充实之所以总是期待着与当下已有的经验内容相似的内容,并在不断到来的当下意识中被充实,乃是因为,视域意向性自行发生于意识现象的被动发生领域,而被动发生的普遍原则是联想[2]109。而联想是“一种起源于活的意向性的意识成就”,在联想中“决定性的因素是相似性、对应性和相邻性。”[17]胡塞尔指明了两种联想形式:一种是,作为形成同一性的原则,即在当下意识流中的整合、构型的原则。此一整合的同一化基于相邻性、相似性得以完成,在意识中构造出单一对象或事态;另一种是,作为将某一对象作为特定意义的对象来经验的原则,此一经验基于联想活动激活先前经验,并基于此先前经验的意义储备,将此意义之相似性传递至当下意识的统觉行为中[1]184。基于联想的这种相似意义的传递作用,视域意向性总是依据相似性、相邻性去预测、期待与先前经验相似的经验。
基于联想的两种形式,任何当下经验都不仅有内在视域,即不仅是在对单个事物的构造性经验中依据已被赋予的意义去期望、预测相似的内容,“而且也拥有一个无限开放的具有共同客体(Mitobjekte)的外在视域”,此一外在视域使意识能够依据通过再回忆而被当下化的过去经验,去期望、预测与之相邻的、相似的单一经验。而内在视域和外在视域,都是在当下意识活动中有所期盼、有所预测的同一视域。作为当下经验之向前攫取的意向而发生的视域,意味着“在每个经验本身中、本质上属于每个经验并与之不可分割的诱导(induktion)。”[16]48Induktion通常被译为“归纳”,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这个词很有用,因为它预先指示着……作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归纳,并且预先指示着这种归纳在按其实际的理解进行解释时最终要归结到原初的和原始的预期上来。因此,一种真正的‘归纳理论……必须从这种预期出发才能建立起来。”[16]48-49这就是说,视域作为向前攫取的诱导,使得归纳得以发生。使得归纳得以发生的视域乃是外在视域。这是因为,内视域仅仅关涉于单一事物的构造性同一化经验,而外视域关涉于不同单一经验之间意义的相似性传递和预测。在当下进行着的单一经验活动中,外视域是“完全空乏的”,它“趋向于得到充实,并且在某个进展方向的过渡中以空乏前期望的方式去达到充实。”[10]52此处的“进展方向”,乃是依据先前的复多单一经验之相似性而自行开启的充实方向,在此方向上相似性意义过渡到当下单一经验期望中。凭借于此,外在视域的意向性能够依据相似性,使得先前的意义过渡到、继续到将来意识中,即能够依据至此为止已经发生的经验的类型,去预测与之相联系的新经验。而当下意识经验的这种预测,便是归纳。作为一视域意向,在意识现象中自行发生的这种归纳之预测是有限的。被预测的意义在有限的视域内被意向,并朝着无限开放的充实可能性敞开自己,在将来的当下意识中要么得到进一步加强,要么因失落而偏离早先视域,在新的可能性中继续期待着得到充实。
由于意识的所有意向性体验都是“客体化行为”,在意识行为之至此为止的活动中显现的所有经验事物,在意向性中被赋予作为超越于意识之外的对象性意义。基于此先前经验,当下意识总是期待着将经验物显现为外在于意识的对象。先前经验的这种意义储备,构造起了过去经验总的类型,使得当下意识活动的相似性联想被动地延续属于此类型的经验,进而构造起现时当下发生着的意识活动之总视域或“普全视域”。此一普全视域构造起这样一种信念和态度:“在一切認识活动之前,每次都先已存在有一个作为普遍基础的世界;而这首先表明它是无所不包的被动的存在信念的基础,任何单个认识行为已经作为前提的东西,都是存在于这个理所当然被视为存在着的世界的基础之上的东西。”[16]45-46此一态度乃是自然态度,在自然态度中被经验到的世界是生活世界[14]189。因此,胡塞尔又将“普全视域”指明为生活世界[10]41。由于归纳在视域意向性中自行发生,作为普全视域的生活世界充满着“普遍的归纳性”。[10]231在此世界中,“一切生活都依赖于预言,或依赖于归纳。在最原本的方式上,每一种素朴经验的存在确定性都曾经是归纳的。”[10]231换言之,生活世界中的任何经验,在归纳中,作为归纳而发生。随自然态度一并生成的这种素朴归纳,发生为对先于、外在于意识的经验对象所作的归纳。
三、理论态度使归纳成问题
生活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我们总是已经在生活着,并且它为一切认识作用和一切科学规定提供了基础。”[16]58这里的“基础”,乃是在活的当下意识之立义活动中作为有限归纳自行发生的素朴认识。发生于普全视域中的此一素朴认识,在一视域界限内展开活动,朝着无限开放的充实进程敞开自身,为未来的加固或失落保留着无限可能性。在此素朴认识的有限性中,归纳不但不成问题,而且是任何经验得以可能的先验条件。使归纳成一问题的,乃是一种新的态度———理论态度。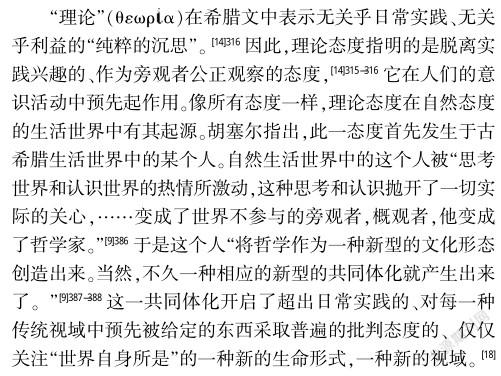
在这种生命形式中,作为一非实践的、“纯粹看”的态度,理论态度为自己提出了一种认识任务,此一任务要求认识活动超出基于历史的、文化的、传统的、信仰的视域而发生的素朴认识,即超出与生活实践的目的纠缠在一起自然认识,去认识“真实的世界本身”。随着理论态度的这种认识要求,产生了“世界表象与真实世界的区别,并且产生有关真理的新问题;……关于一种对所有的不再受传统蒙蔽的人而言是同一的普遍有效的真理,即自在真理的问题。”[9]387此“自在真理”关乎超出当下“主观”经验的“真实自在世界”。于是,在以理论态度进行着“纯粹观察”的哲学家之每一当下经验中,都有一个超出当下经验之特殊视域的、普遍的、完满的———作为理念的“真实之物”一同被预期,此一预期和信念在当下意识中自身被给予。理论态度所提出的认识任务便发生为对此“真实之物”的认识。而充满着生活世界的、发生于意识现象的一视域之界限内的素朴归纳,无法胜任理论态度的这种认识任务。于是,归纳行为在理论态度中的认识有效性成了一个问题。已经发生的这一归纳问题,在近代自然科学的数学化中显露无遗。
根据胡塞尔,理论态度的这种理念化,为每一当下经验赋予“一种理想,即理念上可以想象的,可以无限完善的,并且能够在被构想的无限性的过程中达到绝对完善的认识之理想。”[9]419-421此一认识理想,乃是向超越于诸文化、习俗、实践视域的“自在真理”无限逼近的普遍认识理想,即科学理想。这种科学理想所要认识的是真实的世界,即理念的世界。因此,唯基于对当下经验的理念化,科学认识才能够起步。胡塞尔指明,作为理念化的一个典范,首先发生的是几何学的理念化。在此理念化中,当下经验之形态(时空状态)方面的意义获得了时间流中不变的自我同一性,[14]233关于经验之形态方面的真理被确信为“对于不仅是历史上实际存在的,而且还有一般可能想象的所有的人,所有的时代,所有的民族,都是绝对普遍有效的。”[9]457此乃从生活世界上升的几何学理念化。胡塞尔在对自然科学发生史的描述中,指明另一方向的理念化,即运用几何学的理念化成就,从此一理念化下降到生活世界的理念化[19]。在下降的方向上,伽利略将当下经验之非形态的方面,即冷与热、粗糙与光滑、明亮与黑暗、酸与甜等“填充要素”归于当下经验的“形态要素”,借助形态要素在几何学中的“直接数学化”,对填充要素进行了“间接数学化”,[9]52进而完成了对自然的数学化、理念化。
伽利略的这种数学化,用数学中构建起来的理念世界替代唯一真实的世界,即在活的当下意识之普遍归纳性中绝然明见地显现出来的生活世界[18]96。由于在自然态度中,意识行为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对自然的数学化不仅发生为对经验对象的数学化,而且发生为对意识经验过程本身的数学化。因此,作为意识行为之普遍发生结构的连续性本身首先被数学化[9]407。这种数学化,使得人们能够对一切经验事物做出一种“全新类型的归纳的预测”,即对那些当下经验的有限视域永远达不到的事件做出“计算”。[10]224这种“计算的预测”使得自然的有限预见逐渐变成科学的“归纳”,使得科学归纳的向前攫取挣脱了所有在先被给予的视域限制,[10]39使科学归纳发生为能够通达数学理念之物的精确预测。这种归纳的能力,在伽利略的物理学中被提升到无限中去了[10]245。
然而,虽然精确的数学归纳之无限性看似克服了当下意识经验的素朴归纳之有限性,但由于前者起源于后者,又由于后者在原初意识现象中的普遍结构,数学化的科学归纳仍然是无限地不确定的和开放的[9]419。这就是说,根据胡塞尔,自然科学的数学归纳仍然朝着充实或失落的无限可能性敞开着自身。在自然科学的实践中,充实发生为“证实”或“确证”,失落发生为“证伪”或“反常”。换言之,即使在精确数学-物理的总观念中,也都包含着归纳性之永恒形式的“无穷尽的东西”,此“无穷尽性”使科学成为一个假说和证实的无限进步过程,一个越来越接近最终真实存在物、越来越好地去表象真实自然的认识过程[10]235。此一过程是数学化了的科学归纳不断失落、不断被调整的过程。科学归纳的这种失落使得在理论态度中隐秘地发生了的归纳问题显露出来:归纳在被数学化之际被赋予“科学认识”的任务,此一任务由科学认识的本质而来要求数学归纳能够一劳永逸地、准确无误地预测、通达“真实之物”;而由于归纳行为本身由其意识现象本源而来,为所有的归纳性预测的可错性、可修改性留有空间,归纳无法满足科学认识的“绝对真理性”要求。由此来说,“归纳问题”本身是在理论态度的科学理想从生活世界升起之际,在意识现象中自行发生的;休谟仅仅是“指明”之。
四、对归纳进行怀疑与辩护的合理性界限
在现象学的理解中,归纳行为在自身被给予的视域意向性中自行发生,它总是为将来的纠正留有空间。这种自发性表明,归纳不是人所创立的,意识中的所有经验只能是无休止地、连续不断地进行着归纳的经验。这种素朴归纳在生活世界中能够践行自己的使命,不构成任何问题。归纳成一个问题,始于理论态度。理论态度确立了普遍、必然、确定的认识任务,即科学的认识任务。虽然这是一个要求通达无限远处的认识任务,但此一认识活动只能在进行着有限归纳的意识行为中发生,因为我们只有这一意识。因此,自行发生的归纳无法通达“真实世界”的理念,即便在近代自然科学中素朴归纳被数学化为精确归纳,并以此冲破素朴归纳的有限性,但是数学归纳由于其本源植根于当下意识现象,仍然是不确定的、开放的。这就是说,理论态度造成的归纳问题,不会在源于理论态度的自然科学中消失。然而,自然科学的实践不可能因此而不再使用归纳法,因为任何意识经验行为,必然作为归纳而发生,没有归纳没有经验。
因此,对归纳的怀疑只有在理论态度中才具有合理性。理论态度追求绝对的知识,而归纳基于其有限性、相对性本质无法取得此一认识。与此同时,追求绝对知识的认识行为无法脱离这种归纳,因为这种归纳是真实的原始经验得以可能的条件。于是,无法被摆脱的此有限归纳,在追求着终极真理的哲学中合理地受到了怀疑。但是,这种怀疑的合理性仅限于理论态度中的认识,因为在生活世界的日常实践中,素朴归纳的预测范围,便是素朴认识的合理性范围,这里根本没有怀疑归纳的空间。而无论是在自然态度中还是在理论态度中,否定或放弃归纳是不可能的,因为归纳行为直接源出于原初自身被给予的意识现象中。因此,休谟式的怀疑无法触碰原初素朴归纳的自明性、现实性以及在有限范围内的可靠性。
与此同时,对于如此发生的素朴归纳而言,辩护是也无谓的、无意义的,因为在现象学的理解中,素朴归纳在有限范围的可靠性是无须辩护或论证的,它自行发生,并使得自然经验得以可能。驳斥休谟进而为归纳进行辩护的需要,唯在理论态度中才会出现,因为唯在理论态度中,归纳才成了一个问题。而虽然如此,理论态度的认识又只能发生在进行着归纳的意识行为中。于是,要使此认识合乎理论态度的认识理念,有必要为归纳的可靠性进行辩护。然而,只要这種辩护发生在理论态度中,只要这种辩护坚持归纳能够获得“普遍科学”的认识,那么此一辩护便是不可能的。
但这种不可能性无法阻碍科学活动仍然发生在归纳当中。科学归纳,由于其本源,总是开放的、可纠正的,其预测作为先前经验向未来的延伸,有一种“惯性”的“动能”,经验在向未来延伸的某个方向上动能越大,将来的经验事件扭转此延伸方向越困难。而由于意识现象之普遍发生结构的连续性本质,这种扭转只能以连续流动的方式逐步发生。基于此,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往往不符合实际科学史的原因得到了一种新的理解:单一的经验事件只可能使科学理论的预测得到加固或失落,而一次失落不足以使意识行为彻底放弃归纳的预测;在意向性意识流的历史长河中,任何一种预测都不会彻底被放弃,它只会在被转移的过程中逐渐暗淡下去。而如果所有意识成就连续地、无断层地发生着演变,那么科学史上的“科学革命”之“革命性”就成了值得再讨论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瑞士]贝尔奈特,肯恩,马尔巴赫.胡塞尔思想概论[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1.
[2] [德]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M].张廷国,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5.
[3] [德]胡塞尔.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4.
[4]倪梁康.面对事实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516- 517.
[5]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M].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52.
[6] [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93- 94.
[7] [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M].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30.
[8] [德]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M].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5.
[9]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现象学[M].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451.
[10] [德]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M].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1.
[11] Saulius Geniusas. The origins of the Horizon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M].Dordrecht,Heidelberg,New Yprk,London: Springer, 2012,1- 2.
[12] [德]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M].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8.
[13] [丹]丹·扎哈维.胡塞尔现象学[M].李忠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9.
[14] Dermot Moran, Joseph Cohen. The Husserl Dictionary[M].New York: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2:297- 298.
[15] Dermot Mor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M].London: Routledge,2000:60.
[16] [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M].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51.
[17]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修订版)[M].北京:生活·讀者·新知三联书店,2007,59.
[18] Dermot Moran. Husserls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ciences and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 introduction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65- 166.
[19] James W. Garrison. Husserl, Galileo, and the Process of Idealization[J].Synthese 66(1986):329- 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