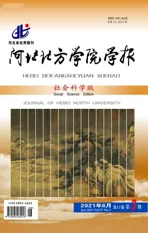试论元结《箧中集》中的讽谕思想
2021-01-12王贝贝
王 贝 贝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箧中集》是唐人元结编选的唐诗选集,辑录了王季友、沈千运、于逖、孟云卿、张彪、赵微明以及元季川等7位诗人的作品。这些诗歌大多诗风质朴,具有《诗经》和汉魏古诗的风韵,对当时局限于形式的诗风具有针砭作用。四库馆臣评论道:“七人所作见于他集者,亦不及此集之精善。盖汰取精华,百中存一”[1],足见此选集的文学价值。《诗大序》言:“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上以风刺上”[2]1,“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废兴也”[2]2。“风雅不兴,几及千岁,溺于时者,世无人哉?呜呼!有名位不显,年寿不将,独无知音,不见称显,死而已矣,谁云无之”[3]27,这正是元结《箧中集》的选诗标准。元结是《诗经》“雅正”传统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其《箧中集》中的讽谕思想是雅正传统的集中体现。
一、描写底层百姓的困苦
盛唐国力强盛,但百姓仍要受统治阶级的盘剥,加之安史之乱持续数年,兵荒马乱更是民不聊生。元结在《箧中集》序中写道:“吴兴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穷老不惑,五十余年……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3]27没有官爵禄位,久居贫贱下僚,这些诗人是盛世中的失意者。辛文房《唐才子传》论孟云卿:“云卿禀通济之才,沦吞噬之俗,栖栖南北,苦无所遇,何生之不辰也”[4]136;论王季友:“家贫卖履……白首短褐,崎岖士林,伤哉贫也。”[4]136孟云卿和王季友曾有一官半职,尚且穷困不得意,其余几人均为布衣,生活更加拮据潦倒。沈千运“天宝中,数应举不第,时年齿已迈,遨游襄、邓间,干谒名公”[4]135,但最终在感慨“如何巢与由,天子不得臣”[3]29后归隐山中;于逖虽是天宝年间的盛世诗人,也郁郁不得志;元季川悲叹“纵远当白发,岁月悲今时”[3]34;张彪于天宝末年和母亲一起躲避灾乱,狼狈潦倒;赵微明亦是生活困顿。综上可知,《箧中集》中的诗人都有困顿潦倒的经历,且大多是社会底层百姓,他们的诗更能反映出自己的困苦生活。如王季友《寄韦子春》:
出山秋云曙,山木已再春。
食我山中药,不忆山中人。
山中谁余密,白发惟相亲。
雀鼠昼夜无,知我厨廪贫。
依依北舍松,不厌我南邻。
有情尽弃捐,土石为同身[3]29。
鸟雀和老鼠知诗人家贫而不来厨房偷食,往日所谓情深义厚的朋友也尽都离去,诗人窘困至此,只能与土石同居。“白发”“贫”和“弃捐”等字眼,尽是悲怆之辞。这首诗揭露了势利之徒的丑恶嘴脸,表达诗人孤芳自赏的隐居意趣,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生活的困窘和隐居的无奈。又如于逖《忆舍弟》:
衰门少兄弟,兄弟唯两人。
饥寒各流浪,感念伤我神。
夏期秋未来,安知无他因。
不怨别天长,但愿见尔身。
茫茫天地间,万类各有亲。
安知汝与我,乖隔同胡秦。
何时对形影?愤懑当共陈[3]30。
这首诗直接点明诗人的现实境况,兄弟二人因饥寒而各自流浪,诗人思念兄弟之情愈深,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控诉就愈深。最后一句“何时对形影?愤懑当共陈”[3]30,诗人直接用“愤懑”两字来表达自己的怨怒之情。诗人有才情抱负,却连最基本的温饱生存都不能保证,济世救民的理想对他而言无疑是空想,整首诗充满了深深的无力感。再如孟云卿《悲哉行》亦是描写困顿人生:
孤儿去慈亲,远客丧主人。
莫吟辛苦曲,此曲难忍闻。
可闻不可见,去去无形迹。
行人念前程,不待参辰没。
朝亦常苦饥,暮亦常苦饥。
飘飘万余里,贫贱多是非。
少年莫远游,远游多不归[3]31。
诗人首先描写了“孤儿去慈亲,远客丧主人”的悲惨情景,寒门士子挣扎于底层的困窘跃然纸上。虽然日夜兼程,但前途并不明朗,仍是混沌黑暗的。这足以表明诗人在追求仕进的道路上处处受挫,生活更是捉襟见肘。末尾两句抒发了诗人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愤恨,劝诫世人不要去追求名利。困顿的个人遭际让诗人写出了与盛世繁荣不符的诗句,这不是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5]1780的傲气,亦不是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5]2265的悲壮。相比其他盛世诗人,《箧中集》中的诗人大多采用一种消极抵抗的方式,所写的是他们的切身感受,是来自于不公时代的悲苦命运,“身处江湖,心存魏阙……匹夫之志,亦可念矣”[4]136,处于庙堂为民请命固然值得颂赞,但身处江湖也可以心怀济世之志。诗人把这心愿诉诸于诗歌,使诗句具有了讽谕的寓意。
“在文学创作法则上真正褪尽浪漫的理想化光晕。作为由理想向写实转变的鲜明标志,只能以杜甫与元结以及《箧中集》诗人为代表。”[6]处在盛世转折点的诗人能褪尽理想浪漫的光晕,是因为他们诗中有讽谕思想的萌芽。诗人因为自身的经历而对底层人民更具悲悯之心,更能苦其所苦,乐其所乐。
二、讽刺统治阶级的黑暗
天宝十四年(755)爆发安史之乱,直至代宗李豫即位后安史之乱才彻底平息。经此一乱,大唐的国运由盛转衰,即使后来有唐宪宗李纯的元和中兴和唐武宗李炎开创的短暂中兴,也无力回天。处在动乱爆发前后的诗人们以一种冷静写实的笔调讥刺现实,讽刺统治阶级的黑暗统治。这些诗人和编者元结能于盛世犹在时写下如此令人痛心的诗篇,是王朝衰颓所带来的一种必然的文学走向。如《箧中集》中极具讽谕意味的《回军跛者》:
既老又不全,始得离边城。
一枝假枯木,步步向南行。
去时日一百,来时月一程。
常恐道路旁,掩弃孤兔茔。
所愿死乡里,到日不愿生。
闻此哀怨词,念念不忍听。
惜无异人术,倏忽具尔形[3]33。
该诗描写了一位老兵对家乡深深的思念、对自己人生遭遇的感慨以及对残酷战争的控诉。唐玄宗统治后期喜好边功,这不仅给王朝带来了动乱,更给百姓带来了祸患。战争无论以何种动机发起,无论胜负对百姓而言都是一种灾难。不同于充满豪情壮志的边塞诗,诗人从士兵的视角直接揭露战争的残酷。
《箧中集》中讽刺黑暗统治的诗歌具有一定的时代精神,因为这类诗歌真实反映了民生之苦与朝政之弊。诗人把浓烈的感情诉诸于诗歌,看似言事,实则饱含深情。此外,这些讽刺黑暗统治和揭露社会现实的诗歌沿袭了《诗经》的“风雅”传统,发挥了诗歌“怨刺”的功用。如沈千运《濮中言怀》:
圣朝优贤良,草泽无遗匿。
人生各有志,在余胡不激。
一生但区区,五十无寸禄。
衰退当弃捐,贫贱招毁讟。
栖栖去人世,迍踬日穷迫。
不如守田园,岁晏望丰熟。
壮年失宜尽,老大无筋力。
始觉前计非,将贻后生福。
童儿新学稼,少女未能织。
顾此烦知已,终日求衣食[3]28。
该诗以“圣朝优贤良,草泽无遗匿”开头,通过反话正说的方式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唐玄宗“天宝丁亥中,诏征天下士人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相国晋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也洩漏当时之机……已而布衣之士无有第者”[7]52。帝王征召贤士,但奸佞当道,从中作梗,致使布衣之士无人及第。当时杜甫与元结等诗人都参加过此次应征,最终受骗落第。沈千运在诗中揭露的正是玄宗宠信奸佞,致使有才有志之士报国无门的黑暗政治。诗中,李林甫用“草泽无遗匿”称颂皇帝政治清明,可诗人却“一生但区区,五十无寸禄”,只能“终日求衣食”,昔日情谊深厚的知己都忘却了,更不用讲兼济天下的理想,诗中的讽刺思想显露无遗。《箧中集》中充满了消极反抗的情绪,实是生存环境逼迫使然。《石洲诗话》评曰:“观《箧中集》所录,其意以枯淡为高,如以孟东野诗投之,想必惬意也。”[8]这枯淡的背后,是《箧中集》诗人最深切的哀伤和最深沉的用心。又如于逖《野外行》:
老病无乐事,岁秋悲更长。
穷郊日萧索,生意已苍黄。
小弟发亦白,两男俱不强。
有才且未达,况我非贤良。
幸以朽钝姿,野外老风霜。
寒鸦噪晚景,乔木思故乡。
魏人宅蓬池,结网伫鳣鲂。
水清鱼不来,岁暮空彷徨[3]29-30。
诗人漂泊异地,久经风霜,十分思念家乡。老来多病,却才志未达,给人以凄凉萧索之感。“水清鱼不来,岁暮空彷徨”表达了诗人不与世俗同流且不与黑暗合污的高洁心志。这种直书实录的方式使诗歌更具真实性,也更能体现诗人的情感。被元结收录至《箧中集》的诗人们一生都徘徊在士子的理想人生之外,他们中的许多人无法独善其身,兼济天下更是空想。因此,他们诗中的归隐之意也是一种对黑暗世界的无声反抗。
元结用《箧中集》来寄寓自己的诗学思想。正如刘熙载在《艺概》中写道:“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元次山以此序沈千运诗,亦以自寓也。”[9]元结推崇《箧中集》收录的诗人,最终目的是要复兴“风雅”的诗歌传统,以及由《诗经》发展而来的现实主义精神,并通过《箧中集》得到传承。换言之,风雅正声恰好是《箧中集》所追寻的,诗人们希望通过这些诗篇实现君主圣明和世道清明。
三、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懑
《文心雕龙·明诗》言:“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谋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性情。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10]《箧中集》中的诗歌除讥刺现实与讽谕时事以外,更多地是表达了诗人怀才不遇的苦闷和对实现人生理想的渴望。玄宗后期重用李林甫,但李林甫为人伪诈,最善蒙蔽圣听,排除异己。“宰相用事之盛,开元已来,未有其比……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且“自无学术,仅能秉笔,有才名于时者尤忌之……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寇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11]。因此,诸如《箧中集》诗人这一类士人几乎没有仕进的机会,选择归隐是他们反抗黑暗政局的方式。怀才不遇主题的诗歌在《箧中集》中的数量最多。如沈千运《山中作》:
栖隐非别事,所愿离风尘。
不辞城邑游,礼乐拘束人。
迩来归山林,庶事皆吾身。
何者为形骸,谁是智与仁。
寂寞了闲事,而后知天真。
咳唾矜崇华,迂俯相屈伸。
如何巢与由,天子不得臣[3]28-29。
此诗首句即表明诗人的归隐动机:“所愿离风尘。”诗人无法像溺于山水的谢灵运和放于田园的陶渊明那样,在山水田园中寻求人生真意和理趣。他归隐山中是迫于无奈,因为现实的黑暗令人心灰意冷。由此可见,诗人面对现实持逃避态度。但末句笔锋一转,“如何巢与由,天子不得臣”,诗人以巢父和许由之典表达自己仍渴望得到重用,归隐山林实属无奈之举。“不遇”和“归隐”是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主题,诗人以“归隐”来诠释“不遇”,看似向往山林,实则表达怀才不遇的怅惘。孟云卿30岁后才中进士,唐肃宗时期曾做过校书郎,但他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其《伤怀赠故人》写道:
稍稍晨鸟翔,淅淅草上霜。
人生早艰苦,寿命恐不长。
二十学已成,三十名不彰。
岂无同门友,贵贱易中肠。
驱马行万里,悠悠过帝乡。
幸因弦歌末,得上君子堂。
众乐互喧奏,独子备笙簧。
坐中无知音,安得神扬扬。
愿因高风起,上感白日光[3]31。
诗人德才兼备,却名不彰显,还被同门之友轻视。诗人把自己渴望“上感白日光”的心志袒露无遗,但又不愿攀附权贵与四处钻营,恐失了自己的君子之风。元结《贱士吟》“谄競实多路,苟邪皆共求。常闻古君子,指以为深羞”[7]19就道出了世道变离、谄媚之人上位与奸邪之人进爵的黑暗政治。收录至《箧中集》的诗人所追寻的是古代圣贤君子的品格,对这种蝇营狗苟的行径深感羞耻。这些诗人渴望进入仕途,兼济天下,但当时政局黑暗,清流之士没有机会实现理想,这更加深了他们诗中的讽谕色彩。“善道居贫贱,洁服蒙尘埃”[3]32,仁人志士居于贫贱,朝廷奸佞当道,在这种黑暗的环境下,被元结收录至《箧中集》中的诗人率先书写了大唐帝国的衰颓。此外,此类主题的诗歌还有沈千运《赠史修文》“岂曰无其才,命理应有时”[3]28,《濮中言怀》“一生但区区,五十无寸禄”[3]28;于逖《野外行》“有才且未达,况我非贤良”[3]29-30;孟云卿《悲哉行》“少年莫远游,远游多不归”[3]31;张彪《杂诗》“儒生未遇时,衣食不自如”[3]31-32;《北游还酬孟云卿》“善道居贫贱,洁服蒙尘埃”[3]32;元季川《登云中》“憀然歌采薇,曲尽心悠悠”[3]34。这些诗歌或表达诗人求取功名而不得的怅惘,或坦露诗人不遇良时的无奈。
被元结收录至《箧中集》的诗人以冷静的视角去描写所处的社会,并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去面对社会的黑暗,创作出具有讽谕思想的诗作,由此发出盛世之哀音。这些诗人不仅在诗书上有造诣,还和社会底层百姓共命运。因此,他们的讽谕诗歌更能引起社会底层百姓的共鸣。这些诗人也充满豪情壮志,但穷困潦倒的生活消解了他们的理想抱负,他们的诗歌大多反映生活的惨淡和人生的失意,少了些许积极和乐观,可以讲是中唐哀调的先声。元结的《化虎论》概括了他的人生理想:“化小人为君子,化谄媚为公正,化奸佞为忠信,化竞进为退让,化刑法为典礼。”[7]118天下不平,以风雅化之;政权黑暗,以风雅刺之。他辑录的《箧中集》承袭《诗经》的风雅传统,为穷而未达的人发声,用一种沉重的调子书写现实人生和黑暗社会。《箧中集》中的诗人的写作倾向和元结一样,也是“揭破人间诈伪,抨击腐败政治。暴露黑暗现实,反映人民疾苦”[7]10。他们把自己的悲惨遭际写入诗歌,表达对生活困顿的无奈;把统治阶级的黑暗写入诗歌,表达希望辅佐明君以使世道清明的政治愿望。
《四库全书总目》评论《箧中集》所选诗歌:“皆淳古淡泊,绝去雕饰”[1]1688,诗人们的苦难人生赋予《箧中集》文学上的敏感性,他们把人生遭际和政治理想化为古朴的文字,上承《诗经》的“雅正”传统,发挥诗歌的讽谕效用,观风补政;下启元白新乐府的写实诗风,是唐调转变的关键。因此,《箧中集》在诗歌发展演变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