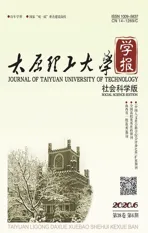20世纪前期晋商私家藏书流散研究
——以晋中商人为中心的考察
2021-01-10卢厚杰
卢厚杰
(山西财经大学 晋商研究院,山西 太原 030006)
藏书流散是历代藏书家都难以摆脱的宿命,因此成为传统藏书史研究的焦点课题之一。需要指出的是,既有研究聚焦于传统经典古籍藏品在不同藏书家之间的流转与传承等方面,但是对近代时局变革后私家藏书流散的新特点、新方式和新影响关注不足,未能充分揭示藏书流散与藏家群体、文教机构之间的多重关系。
作为明清民国时期藏书家群体中的一股新生力量,晋商藏书家积聚了数量庞大、版本精善的古籍文献[1]。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初期(1955),晋商私家藏书经历半个世纪的流散过程,为学界提供了分析近代私家藏书流散过程、方式、特点和影响的绝佳案例[2]。鉴乎此,笔者挖掘清末民国时期山西图书馆档案资料和方志等地方及民间文献,并以田野调查发现的手抄本《祁县人民文化馆收藏古书登记册》为基础,结合民国时期祁县晋商藏书家渠仁甫的个人日记资料,系统地揭示20世纪前期晋商私家藏书的流散过程,并重点探讨其流散特点和流散影响等历史问题。
一、晋商藏书流散过程
(一)清代末年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读书—科考”式的社会上升渠道被废弃,旧式教育场域的文化资本分配面临新的格局,包括山西商人在内的地方士绅开始投身新式教育的革新。在这一过程中,晋商私家藏书成为山西商人参与新式教育实践的文化资本。到20世纪前期,山西商人开始向新式中小学堂和图书馆等机构捐赠图书,晋商私家藏书开启了长达半世纪的流散之路。
榆次晋商常家累世注重藏书,时人称道:“魏榆素封之家,不一而足,而以读书为急务者,为常氏”[3]。20世纪初期,榆次常氏在当地开办新式学堂,并利用家中积聚的丰富藏书支持当地新式学堂教育资源的改善。在这一过程中,贡献最著者是晋商藏书家常赞春。光绪三十三年(1907),榆次县的凤鸣学堂“存书向时无几,除时文外,仅有瀛寰志略及方正学集二部,山西通志一部,清光绪丁未,移尊经阁藏书归之于是,闻藏书室仪器室于中院之东西二隅,诸书颇断烂失次”[4]。目睹凤鸣书院藏书稀缺之现状,常赞春将个人部分藏书捐给学堂图书馆,“出家藏之十三经、廿四史、廿二子、朱子全书、昭明文选,捐赠学堂”[4]。除此之外,光绪三十四年(1908),常赞春又将《四部丛书》及方志等二万余册藏书寄存于省图书馆[5]。
祁县晋商渠家的渠本翘、渠仁甫等人将私家藏书作为兴办祁县中学的助力。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清末教育新政影响下,渠本翘与祁县士绅集资2万两白银,将祁县昭馀书院改办为祁县中学堂,自任董事长兼总办,制定《祁县中学堂章程》35条,并把部分家藏古籍捐献给祁县中学堂的图书馆[6]。直至今日,祁县中学图书馆仍收藏有古籍一万余册[7],在全国的中学图书馆中可谓独树一帜。20世纪80年代,冀淑英、丁瑜等古籍版本学家在参观祁县中学所藏古籍后,给予“同类图书馆,南方没有,北方少有”的称赞[7]。2016年,据祁县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工作人员整理,祁县中学图书馆收藏古籍总数在万册以上,经、史、子、集、丛五部齐全,以史部与子部新学类数量较多,其中不乏明代汲古阁刻《十三经注疏》、北监本《二十一史》、清内府五色套印本《古文渊鉴》等名刻,以及《十通》《古今图书集成》《四部备要》等大部头古籍[7]。
(二)民国时期
1.渠仁甫与祁县私立竞新图书馆。民国十五年(1926),祁县晋商藏书家渠仁甫拿出一部分家藏典籍,辅以“购买新旧图书”[6],在县城创办私立竞新图书馆,成为渠氏私家藏书的一个流散方向。私立竞新图书馆“所藏新旧图书极丰。同时订有多种报刊杂志,对外开放,为省内县城中规模最大的图书馆”[8]。私立竞新图书馆“除供本校师生阅读参考外,还对社会人士开放,任何人都可以进去阅览。因藏书较多,在当时县城中无出其上者,故阅览之人终日不绝”[9]。1937年日军侵占祁县县城,渠仁甫南迁四川避难,私立竞新图书馆陷入停办状态[9]。建国初期,渠仁甫自四川返回山西。1951年,他将私立竞新图书馆捐给祁县中学[10]。私立竞新图书馆的藏书“经敌伪时期之损失,尚残存一少部分,也均于1954年全部捐献祁县文化馆”[9]。
2.日军入侵与晋商私家藏书流散。1937年11月9日,日军入侵祁县县城,祁县晋商私家藏书处境险厄,但大部分藏书幸运地被保存下来。如祁县晋商乔家南迁之前,将藏书运往祁县“永春原”药店二层仓库,采取较为妥当的安排,所藏古籍大多保存完好(1)访谈祁县乔超五曾孙乔新士,时间:2016年11月3日,地点:祁县晋商文化研究所。。“永春原”药店专营中药材,由渠仁甫和渠晋云等合资经营。祁县乔家之所以将藏书寄存在渠家的商号,原因在于渠晋云的妻子是来自晋商乔家的乔贞士。但是1948年后祁县晋商藏书家乔超五和乔致庸等所藏古籍开始散轶民间[11]。又如祁县晋商渠家大院位于祁县县城,日军将其作为战时司令部,并大肆劫掠渠仁甫精心收藏的名贵古籍书画。后来,祁县“长裕川茶庄”和“书业诚”两家商号的员工趁日兵外出之际,紧急抢运出大部分书籍,存放在“书业诚”的库房内,晋商渠家藏书虽有损失,但并不严重[9]。1953年,“书业诚”商号的员工将抢救下来的几十箱书籍、字画运至太原[6]。再如祁县晋商何氏“对蒙轩”藏书楼收藏丰富,抗战时期何家将藏书封存在祁县城南大街老宅院的幽僻之处,可惜的是藏书虽逃过兵焚之厄,却因“对蒙轩”藏书楼无人看管,所藏古籍文献大量遗失,甚至被城内卖熏肉的老人拿去包熟肉[12]。
(三)建国初期
建国初期,祁县等地的晋商藏书家将家藏典籍几乎全部捐给祁县图书馆及山西图书馆等机构。1955年12月,祁县人民文化馆对晋商藏书家捐献的古籍进行整理,编成抄本《祁县人民文化馆收藏古书登记册》(以下简称《登记册》)一册,每页分列编号、书名、套数、册数、卷数、纸别、版别、著作人、捐献人、备考等基本栏目,详细登记了晋商所捐古籍的信息,见证了晋中地区晋商私家藏书的最终归宿。
1954—1955年间,祁县晋商渠仁甫两次捐赠藏书。1954年,渠仁甫将四百七十七部一万一千四百余册珍藏书籍捐赠予祁县文化馆[6]。而早在1952年,渠仁甫参加山西省政协学习委员会之后,结识山西省文史馆馆长张兰亭,向其提出捐书一事。后因渠仁甫生病,直到1955年方才办理完捐书手续[9]。1955年3月27日,渠仁甫遣子渠川祜往访张兰亭,催其接收渠家捐献之书籍,并筹接收方法[13]。4月13日,太原市委统战部赵部长、张科长前来参观渠仁甫在“书业诚”的存书[13]。5月29日,渠仁甫与张兰亭约定暑假期间派人赴祁县接收所捐献之书籍。7月2日,张兰亭至祁县查看渠氏捐献之书籍,并准备接收装运方法[13]。7月30日,文史馆朱建中与渠仁甫商定接收书籍之期[13]。9月28日,渠仁甫移交文史馆书籍手续完成,共计捐书五百五十四部[13]。
20世纪50年代,祁县乔贞士的藏书通过出售和捐赠方式流出。一方面,乔贞士将部分藏书售与书店。1954年3月16日,乔贞士向北京几家书店提供藏书著录[13],供其甄选。3月23日,北京实学书店派人至祁县察看其所售之书,并协商售价[13]。4月5日,文汇书店又选购乔贞士藏书四十一种,作价一百七十八万元[13]。另一方面,乔贞士将剩余藏书捐献与祁县人民文化馆。1954年6月26日,古籍书帖整理完成,文化馆工作人员薛贵棻为乔贞士送来捐献志愿书一纸、收据一纸,以及书目一册[13]。乔贞士捐书共计有三百六十六种,包括经部一百○一种、史部七十二种、子部九十九种、集部八十种、类从部十一种[14]。
1950年,祁县晋商藏书家何绍庭后人何晓楼将“对蒙轩”藏书捐给政府。祁县人民文化馆派专人进行简单的编目整理,将“套书”存于文化馆后院正房楼下,“散本”则藏于临街楼上,共占用10间房屋[12]。据《登记册》统计,何氏捐赠古籍九百四十六种、二千六百六十二函、二万一千四百五十一部,包括经部一百一十三种、史部一百九十一种、子部一百四十七种、集部四百四十八种、类从部四十七种[14]。
太谷、榆次的晋商藏书家也多次将藏书捐赠给山西图书馆。如太谷晋商赵家累世注重藏书,“到(赵)铁山时,所收集之书更多更精,并喜求名人精校善本”[15]。1950年,太谷赵家“絅斋藏书室”的部分藏书捐赠给山西省图书博物馆[16]。1953年上半年,山西省图书博物馆图书部整理了太谷赵氏所捐赠的一百○五箱旧书,并分类登记,按号上列架,共计三万九千六百二十三册。据工作人员记载,赵家所捐书籍较为整齐,内有《太平御览》一部及《册府元龟》一部(不全),均属稀见罕物[5]。再如,建国初期榆次晋商藏书家常赞春的后人将其藏书分两次捐出。第一次是1951年,他们向山西省图书博物馆捐献书籍、书画等一百七十八件。第二次是1954年,常凤铭将其父常赞春寄存在榆次文庙的图书捐给原山西省图书博物馆[17]。

表1 1949—1951年接管、捐赠、购买、抢救书籍、字画统计表[5]
二、晋商藏书流散特点
(一)流散方式
20世纪前期,晋商私家藏书的主要流散方式是无偿捐公。从1905年常赞春、渠本翘等将藏书捐赠凤鸣学堂和祁县中学等新式中小学堂,到20年代渠仁甫藏书捐赠私立竞新图书馆,再到50年代祁县何家、渠家,以及太谷赵家等将私家藏书捐给山西省内各级图书馆,在近50年的晋商私家藏书流散过程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流散方式是无偿捐赠,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售卖。在这一过程中,大部分藏书被晋商藏书家通过无偿捐赠方式流向各级图书馆和中小学堂等文化教育机构。由此可见,晋商藏书家的私家藏书流散方式呈现出别具特色的一面。
作为私家藏书这一文化资本的拥有者,晋商将其无偿捐赠给各级中小学堂和图书馆,其行动逻辑自然值得推敲和思考。文章认为,晋商藏书家无偿捐赠藏书的背后既有社会公益心理的作用,也有财富实力的基础支持,更是一种理性的行动选择。布尔迪厄认为,在社会空间内部,文化资本、象征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等不同的资本形式之间可以互相转化[18]。在捐赠私家藏书的过程中,晋商藏书家的行动逻辑应是通过文化资本的让渡,获取其他形式的资本,比如,官方层面的认可、民众的交口称赞等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
(二)流散缘由
凭借雄厚的财富积累,晋商藏书家很少因经济问题而变卖私家藏书。虽然“自道、咸、同至清季以及今日,太谷商业被毁者十之八九”[10]。但是,从晋商藏书的流散历程来看,战乱时代和经济下滑之际并非晋商藏书流散的高峰期。同时,晋商私家藏书的流散极少是由于家庭内部出现纠纷或问题,以致子孙变卖祖业。我们认为,上述两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晋商在经济资本领域拥有较为深厚的财富积累。民国时期的晋商财富实力已不及清代晋商,但较之普通百姓和寒素士人,仍具有一定的财力优势,故而很少出现因经济因素而变卖藏书的事例。
私家藏书是晋商子弟接受文化教育的媒介,晋商藏家不会轻易变卖。民国时期落魄晋商子弟变卖家产者众,原因之一在于此类晋商家族私家藏书较少,不重视文化教育和家风、家训,致使家族子弟文化素养较低和文化资本较少,难以抵御商业兴衰和社会动荡。私家藏书较多的晋商家族,一般能形成较好的家风、家训,子弟都能获得较高的文化能力,即便遭遇商业失败,他们依然可以凭借文化资本跨越到不同的社会场域谋生。比如,祁县渠家、榆次常家等在家族商业衰退之后,子弟通过读书、求学等方式,积累一定的文化素养和取得相应的学历文凭,从而在民国时期的教育、科学和文化界站稳脚跟,拥有更加多元化的人生选择。
要之,20世纪前期,晋商私家藏书流散并非是由于家族人事、经济纠纷等传统因素,更多是基于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和崇尚,换言之是晋商藏书家主动选择的结果。作为传统中国文化领域的“弱势群体”,清代晋商及其子弟在藏书、读书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文化资本,为家族的兴盛和名声的提振打下了基础,他们知晓私家藏书作为稀缺的文化资源的重要意义,更愿意将文化资源转移到需要的行动之中,从而进一步发挥文化资本的历史作用。
(三)流散方向
近代以来,随着地域间和海内外学术文化交流的加强,许多私人藏家的藏书成为海外机构的囊中之物。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期,除了乔贞士卖到北京书店的部分藏书,晋商私家藏书主要是在山西省内文化机构之间流动。显然,与知名藏书楼的藏书流散相比,晋商私家藏书的流散方向单一、流散范围狭隘。
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较为特殊的历史原因。一方面,山西地处西北内陆,距离北京、上海及江南等文化重心城市甚远,山西的藏书活动、藏书人物长期远离中国古代藏书场域的中心舞台,致使山西藏书活动的影响力极为有限,晋商私家藏书在流散的过程中不易引起主流藏书界的关注。另一方面,传统藏书界注重的是珍稀版本古籍,商人出身的晋商藏书家在私家藏书选择方面更加务实,体现出偏重实用的藏书思想,其所收藏的珍稀善本难与知名藏书家的收藏相提并论,加之晋商藏书家的学术成就、藏书知识和社会影响难以与累世藏书的士人藏书家比较,故而在传统时代的藏书场域中处于相对边缘的社会位置。
要之,各种历史因素的叠加作用限制了晋商私家藏书的流散方向,使其更多是在山西省域范围内流转。值得庆幸的是,正是这一历史“局限”造就了近代山西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因为,对于文化图书资源相对稀缺的山西而言,晋商私家藏书流散至省内各级图书馆和学校,而非地域范围更广的外省或者外国,意味着避免了山西省内珍惜文化遗产的流失,从而将宝贵的文化财富遗产留在三晋大地。
三、晋商藏书流散影响
世人对私家藏书流散更多是从否定的视角予以评论,或以惋惜的态度予以同情,但是我们认为,20世纪前期晋商私家藏书的流散有着不同寻常的历史影响,它所形成的是文献典籍、私人藏家与新式文化机构三者共赢的局面。
(一)提振家族社会声望
20世纪前期,晋商私家藏书的流散并没有损害晋商的家族声誉和社会地位,反而成就了晋商在近代山西文化教育场域的重要位置。因此,私家藏书的流散过程也是晋商家族不断获益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晋商家族捐出了私家藏书,但同时收获了社会声誉。如常赞春向榆次县凤鸣学堂捐赠藏书,颇受时任地方官员的推崇,榆次知县沈继焱将此事禀报山西巡抚及提学使,巡抚恩寿和提学使锡暇分别题赠“士诵清芬”“分惠士林”的匾额[17]。官方的认可意味着榆次常氏在近代山西文化领域拥有较高的地位。民国时期,常赞春等在山西的政治、学术领域均有出色成绩,一方面是由于个人文化素养的不俗,另一方面也离不开社会声誉的积累,尽管他们“固非欲籍此而要誉于世也”[19]。
20世纪前期,晋商私家藏书实现“由私及公”的转换,由私家藏书变公共藏书,不再是仅供某位藏书家独自欣赏的文化典籍,而是成为学堂学生、图书馆读者等大众群体有机会接触的读物,有助于藏书的阅读使用和长期保藏。从这个意义上讲,晋商私家藏书的最终归宿实现了晋商藏书家“藏以致用”的初衷与理想。客观而言,晋商藏书家常赞春、渠仁甫、赵铁山等人的行动选择体现出相当的人生高度和开放精神。
(二)助力山西新式教育
清季以来,传统基础教育体系迎来破立之变,新式中小学教育进入摸索阶段。事实上,对于近代县域以下的基层学校而言,图书资料是较为稀缺的文化资源。作为重要的教育资源,藏书数量成为某一学校发展的约束性要素。同时,对于面向社会公众的新式图书馆而言,藏书的稀缺同样约束其社会教育职能的发挥。20世纪前期,数量庞大的晋商私家藏书主要流向各类学校和图书馆,可以最大化地发挥图书资源的教育价值。
20世纪前期,山西中小学流入大批来自晋商家族的藏书,如榆次凤鸣学堂、祁县中学及渠仁甫创办的祁县私立竞新小学校。晋商所捐藏书对于几所学校的教学质量提升和学生视野开拓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祁县私立竞新小学校和祁县中学成为民国时期享誉山西的知名学校,与晋商的大量捐书不无关系。关于捐赠图书的动机与出发点,榆次晋商藏书家常赞春言道:“今日道丧文弊,使读书种子不绝于人寰,亦云幸矣”[17]。可见晋商藏家捐赠藏书的初衷之一是推动文化教育的发展。
20世纪前期,晋商私家藏书流入省图书馆、省博物馆及县图书馆等机构,成为当地民众获取教育资源的重要媒介,推动了社会民众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图书阅读的普及。如二三十年代,山西地区最早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公益性图书馆——祁县私立竞新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便由祁县晋商藏书家渠仁甫一手促成。据祁县私立竞新小学校学生回忆,“学校附近的学生就去竞新图书馆,既乘凉避暑,又能阅览报纸书籍”[20]。可见,祁县竞新图书馆成为周边学生和读者从事借书、读书等教育活动的重要文化场所。
(三)丰富山西图书馆藏书
近代山西图书馆的发展离不开晋商藏书家捐书的支持。宣统元年(1909)四月,山西巡抚宝棻上《晋抚奏创设图书馆折》,云:“晋省创建图书馆,因筹款维艰,又僻居西北,搜罗难期完备,惟寻常书籍尚易购置,而鸿编巨册无从访求”[5]。对于僻居西北的山西而言,受制于购书经费不足和馆藏图书寡少,近代山西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坎坷前行。作为一种替代性制度,山西图书馆实行“藏家寄储书籍”,以增加馆藏图书资料。榆次晋商藏书家常赞春等人积极“将其所藏书籍碑帖寄储本馆。中有希世佳本,多为本馆所未备者,其增光禆美,至为鸿多。本馆实深感谢,除慎重保存外,并印行目录以资表彰”[5]。
作为县级图书馆,祁县图书馆藏古籍在数量、质量上远超省内外同级图书馆,是山西省内仅次于山西图书馆的古籍收藏重点单位,其所依托的主要是祁县晋商所捐古籍文献。据不完全统计,祁县图书馆馆藏善本和普通古籍数量为二千三百三十三种、四万八千七百零一部[14],而建国初期祁县晋商藏书家渠仁甫等向祁县人民文化馆捐献的藏书多达四千八百六十五函、三万八千九百零一部[12],占馆藏古籍总比重的81.3%.需要指出的是,晋商捐书内含大量古籍孤本、珍本,选送《中国古籍善本目录》的多达二百二十余种四千余册[14]。
四、结语
20世纪前期,祁县、榆次和太谷等地的晋商藏书家将私家藏书主动赠予各级中小学堂、图书馆、博物馆及文化馆,不但完成了“由私及公”的藏书流转,更是实现了从传统藏书楼到新式图书馆的转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晋商私家藏书不再是仅存于某一宅院偏隅的“死书”,而是成为中小学校和图书馆发挥教育职能的媒介,成为众人所阅读的“活书”,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古籍珍本的“文献生命”。对于晋商藏书家而言,曾被目为“逐利至上”的山西商人群体,在藏书流转和捐赠的过程中获得政府嘉赏、社会认可和士林尊重,改善了自身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要之,从这个角度而言,20世纪前期晋商私家藏书的流散,对文献古籍、新式文化机构和晋商藏书家族而言,是三方共赢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