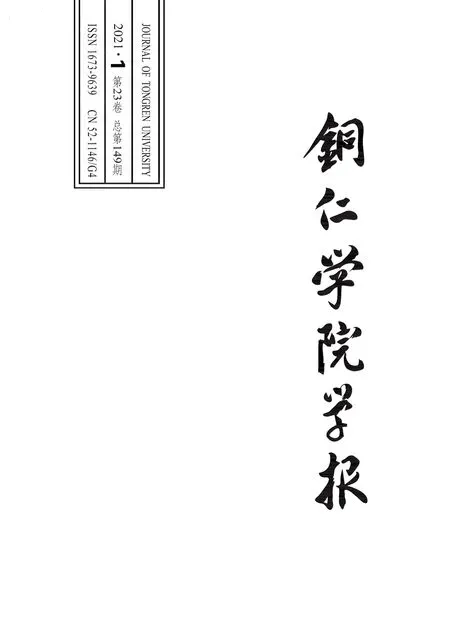朱熹论陶的历史传承与突破
2021-01-08郭院林
郭院林
(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
关于陶渊明其人其诗的阐释,从其去世不久后就开始了。颜延之的《靖节徵士诔》对陶渊明生平与气节作了全面的介绍,拉开了论陶的序幕。此后一千余年间,随着陶渊明认可度的提高,关于陶渊明的研究与日俱增。在朱熹之前,陶渊明是一个“高蹈独善”的“隐逸者”。颜延之追述陶渊明生平,称赞其“廉深简絜,贞夷粹温,和而能峻,博而不繁”[1]。此后钟嵘、萧统虽对陶赞誉程度不同,但总脱不了隐者的帽子。唐代文化价值多元化,一方面赞誉陶渊明淡泊自然的生活态度、洒脱恣意的诗酒人生,另一方面建功立业的想法成为时代的主题,他们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做法不能完全肯定,有时甚至颇有微词。①总的来说,唐代的陶渊明研究多从为人处世等外在方面来讨论陶的品性,但未能进一步追究陶渊明行为的根本原因,即内在思想与动力。
宋代是一个思想深刻的时代,因而论陶能够更加理性和成熟。钱钟书先生曾说:“渊明文名,至宋而极。”[2]陶渊明研究出现高峰,开始触及陶诗内核、奠定陶诗地位。宋朝文人们对陶的推崇达于极致,欧阳修、梅尧臣、苏轼等文学家都大力推许。梅尧臣在《送永叔归乾德》一诗中说:“渊明节本高,曾不为吏屈。斗酒从故人,篮舆傲华绂。”[3]23体现出他对陶渊明气节的认同,发掘出了陶渊明性格中的慷慨豪情。这些对朱熹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朱熹曾探寻陶渊明遗迹,赞其诗文,誉其为人。朱熹对陶渊明的阐发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建构了陶渊明形象,他对陶的肯定与评价也确立了陶渊明的文学地位并影响着后代学者的观念,而他的研究也为后世开辟了独特的解读角度。那么,朱熹是站在什么角度解读陶渊明的呢?他的施政思想与理学立场如何发明陶渊明?他理解的陶渊明有何特色呢?本文试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朱熹推动陶渊明研究,揭示朱熹对陶的阐释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陶渊明其人其诗的历史价值。
一、由隐士到贤人:朱熹对陶渊明形象的提升
因为为官经验与学者的身份,加上移风易俗的现实需要,导致朱熹对陶渊明的阐释,首先不是以文人的身份,而是作为纯粹民风的道德模范与政治伦理典型,彰显他的“贤”,挖掘与弘扬陶渊明内在的伦理文化资源,并为社会服务。南宋淳熙五年八月,朱熹 49岁,除知江西南康军(今庐山市),兼管内劝农事。第二年三月三十日到南康任。到任伊始,即颁发《知南康军榜文》《知南康军牒文》,问计于民,“宽民力,敦风俗,砥士风”②。从四月开始,他多次探访庐山南麓陶渊明遗迹上京、醉石与栗里。而对南村栗里渊明遗址,朱熹在《答吕伯恭书》中说:“陶公栗里只在归宗之西三四里,前日略到……”[4]“谷中有巨石,相传是陶公醉眠处。予常往游而悲之。”[5]“云”和“相传”等字眼表明,朱熹对陶渊明遗迹的真实性并未刻意追究,主要目的是肯定陶的品行,以此达到淳化地方风气的效果。淳熙八年,跋颜真卿《栗里诗》,刻于南康陶公醉石。颜氏所作诗,实名为《咏陶渊明》,全诗如下:“张良思报韩,龚胜耻事新。狙击不肯就,舍生悲缙绅。呜呼陶渊明,奕叶为晋臣。自以公相后,每怀宗国屯。题诗庚子岁,自谓羲皇人。手持山海经,头戴漉酒巾。兴逐孤云外,心随还鸟泯。”朱熹认为在前贤题咏栗里的作品中,颜真卿的诗最令人感慨。之所以如此,恰在于颜真卿以陶渊明不仕二姓,忠于晋室;淡泊名利,归于自然。这也是朱熹施政的指导思想,从此入手,他阐发陶渊明。以醉石为主题,他写有两首诗,成为醉石诗的里程碑。③朱熹作跋作诗,也是激活历史传统的举措。
为了利用传统文化陶冶民风,朱熹给陶渊明建祠立馆。他任职之初,便于《知南康军牒》中对陶渊明遗迹进行询究:“晋靖节征士陶公先生隐遁高风,可激贪懦,忠义大节,足厚彝伦。今按图经,先生始自柴桑徙居栗里,其地在本军近治三十里内。未委本处曾与不曾建立祠宇?”[6]后来,朱熹整顿军学,建五贤祠,“立得陶靖节、刘凝之父子、李公择、陈了翁祠,通榜曰‘五贤’。”[7]同时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学宫,以二程先生配。周祠在讲堂西,五贤祠在东。[8]建五贤祠与先贤濂溪祠同时并举,这也可以看出,在朱熹心目中,陶渊明不仅是诗人,更是贤人,他是可以和周敦颐、程颐、程颢这样的理学大家分庭抗礼的。淳熙六年九月,朱熹在栗里醉石旁建纪念亭,并取名为“归去来馆”。陶渊明的“隐遁高风”与“忠义大节”可以“激贪懦”与“厚彝伦”。在一定意义上讲,朱熹将陶渊明纳入了道学体系。
探访陶渊明遗迹并将其建设成为文化徽标,朱熹的考量恰在于陶渊明的“贤”。他在《陶公醉石归去来馆》诗中云:
予生千载后,尚友千载前。每寻《高士传》,独叹渊明贤。及此逢醉石,谓言公所眠。况复岩壑古,缥缈藏风烟。仰看乔木阴,俯听横飞泉。景物自清绝,优游可忘年。结庐倚苍峭,举觞酹潺湲。临风一长啸,乱以归来篇。[9]487
《高士传》实际收入自尧时到三国时期96个人物,大都是隐逸避世,不事王侯的。但这些人似乎过于脱离现实,与朱熹政治追求不一致。朱熹选择陶渊明作为自己的偶像,叹服与追慕的原因,是因为陶渊明是当时的贤人。
朱熹所定义陶渊明的“贤”,首先是以天理为乐,忘怀名利的人。他在《论语·雍也》“贤哉回也章”的注解中有详细说明:“颜子之贫如此,而泰然处之,不以害其乐。”[10]110此后在《朱子语类》中进一步阐释道:“颜子私欲克尽,故乐,却不是专乐个贫。须知他不干贫事,元自有个乐,始得。……这道理在天地间,须是真穷到底,至纤至悉,十分透彻,无有不尽,则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11]
陶渊明在《咏贫士》中说过:“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12]371朱熹说:“陶渊明说尽万千言语,说不要富贵,能忘贫贱,其实是大不能忘,它只是硬将这个抵拒将去。然使它做那世人之所为,它定不肯做,此其所以贤于人也”。“晋、宋间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渊明却真个能不要,此其所以高于晋、宋人也。”[13]在朱熹理解中,陶能区别名利“孰亲孰疏,孰轻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缓孰急。……久之须自见得合剖判处,则自然放得下矣。”[14]正如他自述:“岂无他好?乐是幽居。”[12]26陶渊明归隐的思想和行为中,蕴含着“孔颜之乐”的精神境界。他在《读山海经》(其一)中对幽居自得的隐居生活有细致地描绘:“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12]393在《拟挽歌辞三首》中表达对死亡的泰然与风流:“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12]425正是由于陶渊明能够放弃一些欲念,于心灵自由与名利得失中做出取舍,才成为朱熹选择的对象。
朱熹将陶渊明的隐逸与义利之辨建立联系,当然也有现实针对性。南宋自建立起,就处在金国铁蹄的威逼下,政弊横生。朱熹一直是以传道讲学、积极入世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虽十九岁即进士及第,但他的仕途生涯也几经坎坷,曾多次辞去官职,向权势抗争。朱熹幼年经历过国破家亡,而其父子都是主战派,自然不会忘记岳飞的话:“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15]这也是朱熹给现实开出的药方,所以尤其倡导陶渊明甘于平淡,辞官隐逸,这也是希望南宋朝廷能够风清气正。朱熹诗中多表达隐逸之心,有辞官务农的念头:“我愿辞世纷,兹焉老渔蓑。”(《落星寺》)[9]488这表现出朱熹淡泊名利,用舍行藏不是标准,而在于内心,也就是谢氏所说:“圣人于行藏之间,无意无必。其行非贪位,其藏非独善也。若有欲心,则不用而求行,舍之而求藏,是以惟颜子为可以与于此。”[10]121-122
如果说义利之辨仅是个人品行的话,那么君臣大义就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贤,朱熹理解的陶渊明是二者并具的。同是在知南康军期间,他写下《分韵得眠意二字赋醉石简寂各一篇呈同游诸兄》,诗云:
驱车何所适?往至秋云边。企彼涧中石,举觞酹飞泉。怀哉千载人,矫首辞世喧。凄凉义熙后,日醉向此眠。仰视但青冥,俯听惊潺湲。起坐三太息,涕泗如奔川。神驰北阙阴,思属东海壖。丹衷竟莫展,素节空复全。低徊万古情、恻怆颜公篇。为君结茅屋,岁暮当来还。[9]469
值得注意的是诗中“凄凉义熙后”一句,义熙是东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年号,后刘裕改革掌握大权,代晋自立。朱熹说陶在晋朝倾覆后的心情是“凄凉”,这种感觉不得不说是朱熹的体会与发明,可见他对“忠于一姓”这个说法是肯定的,并一直坚持着这种观点。
他又于《向芗林文集后序》中说:
陶元亮自以晋世宰辅子孙,耻复屈身后代,自刘裕篡夺势成,遂不肯仕。虽其功名事业不少概见,而其高情逸想,播于声诗者,后世能言之,士皆自以为莫能及也。盖古之君子其于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伦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后节概之高,语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16]
他认为陶渊明首先值得肯定的是气节,然后才是文学,君臣父子大伦大法的节概是文学高妙的根本。他一改《资治通鉴》不谈陶渊明不复仕宋的事,而是特别提出:“潜自以先世为晋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17]325《晋徵士陶潜卒考异》就提出“陶潜在晋乃太尉侃之孙,自其初年出处大致已有可观。至刘宋移国,耻复屈身,遂不出仕,卒能保全名节,故《纲目》特以晋处士书之,明其不失身于宋氏,独得为晋全人也……《纲目》取诸前史,以激千载之清风尔。”[17]325将陶渊明的隐逸行为与耻事二姓的君臣大义联系起来,应归于沈约的发明,他在《陶潜传》中称:“(陶渊明)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12]609他的理由有二:一、陶氏家族与晋朝关系;二、文章系年方式在“义熙”前后的变化。朱熹进一步讨论“处士”的春秋笔法:“书法有正例、有变例,正例则始终、兴废、灾祥、沿革及号令、征伐、杀生、除拜之类,义固可见;若其变例则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皆特笔书之,如张良在秦而书曰韩人,陶潜在宋而书曰晋处士……之类,是皆变文见意者也。”[18]朱熹认为,陶渊明不仅知道君臣大义,而且能够实行,这才是最为可贵的。在《跋洪刍所作靖节祠记》中,朱熹批评了言行不一的洪刍(驹父):“读洪刍所撰《靖节祠记》,其于君臣大义不可谓懵然无所知者。而靖康之祸,刍乃纵欲忘君,所谓悖逆秽恶有不可言者。送学榜示讲堂一日,使诸生知学之道非知之艰,而行之艰也。”[19]
纵观陶渊明接受史,“忠义”并非朱熹首创。但朱熹一再强调与彰显,将这一观点放大,后世之所以坚持认为陶渊明隐居是忠于晋代,朱熹起着不小的推动作用。这与朱熹的理学思想和南宋的政治文化风气不无关系,南宋王朝颇有些懦弱无能,投机者寡廉鲜耻,身为理学家的朱熹力图改变这种社会风气,因此他更关注推崇陶渊明背后的社会作用,用以激励百姓、教益俗世,陶渊明在他笔下由此成为了理义道德的化身。在他的描述中,陶渊明是一位“耻复屈身后代”的道德楷模,“忠于一姓”成为陶最显著的高尚品格,他于困厄中不改初衷,是君子固穷的坚定践行者,而陶的文章则是他道德品质的映射。这是朱熹赋予陶渊明的重要形象特点,是他加诸陶渊明的道德标准。朱熹将陶渊明的形象从隐士提升到贤人,突破了历代论陶的局限。
二、对抗与重建:朱熹对陶诗的文学史定位
南宋诗坛是江西诗派的天下,其末流掇拾陈言,过于重视推敲文字技巧。正如王运熙、顾易生所论述的那样:“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的影响尤为显著。然而在当时政治激变、国难严重的历史条件下,江西派片面崇尚形式的理论和创作,日益引起人们的不满。”[20]81对这种诗歌风格,朱熹甚是不喜。而与此相对抗的,朱熹认可的是古人的平淡,“夫古人之诗,本岂有意于平淡哉?但对今之狂怪雕锼神头鬼面,则见其平。”[21]他在《答杨宋卿》中说:“熹闻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辞之善否,今以魏晋以前诸贤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于其间者,而况于古诗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于此,故诗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22]朱熹反对刻意追求技巧,而倡导自然之诗。
理学开创者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提出“文以载道”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发展到程颐,则变本加厉,提出“作文害道”说,原因在于“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圣人只摅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23]朱熹有丰富的创作经验与极高的艺术鉴赏力,对诗歌的评价有其独到的标准和要求,“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24]一方面他认识到诗歌的情感因素,但他更强调诗教经过圣人加工,故而归之于正,以儒家修齐治平为标准,所以可以为教。对于诗坛玩弄技巧与道学家纯主道德,朱熹是不同意的,坚决反对文道脱离与对立,但如何做到文道合一?
北宋对陶诗的认识和接受还主要侧重诗歌形式上的“平淡”。北宋理学家杨时对陶诗有着这样的评价:“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于自然。若曾用力学,然后知渊明诗非著力之所能成也。”(《龟山语录》)[3]43杨时师从程颢、程颐,他对陶诗的理解注入了理学家的思维。“渊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诗家视渊明,犹孔门视伯夷也。”(蔡绦:《西清诗话》卷上)[3]53这就开启了朱熹论陶的新视角:陶诗自然平淡,其人不慕名利、德才兼备,可谓之“得道”,所以其诗为道德之言。朱熹评价历代诗文时,向来较为严格,但对于陶渊明的诗文,他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25]基于这样的看法,朱熹认为诗词不切自己的事,则是枉费工夫。这与儒家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篇》)相吻合的,“有德者,和顺积中,英华发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给而已。”[10]194而这也与二程主张一致。渊明之诗不加矫饰、发乎本心、自然成之,所以造就了其平淡又不失意趣的诗风。朱熹不以工拙论诗,故对于形式,强调质朴自然,陶诗的平淡风格也是朱熹欣赏与提倡的。
如果单是形式的平淡自然,没有内容的哲理性,陶诗也不会成为朱熹的选择,引起他的重视。白居易在深入体会陶诗的基础上,揭示陶诗具有玄思:“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白居易《题浔阳楼》)[3]20朱熹是将陶诗放在理学家的文学观念中看待的,“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所以朱熹一再说陶渊明与老庄的关联:“渊明所说者庄、老,然辞却简古;尧夫辞极卑,道理却密。”[26]“陶渊明亦只是老庄”[27]。陶诗文道家典故所在多有:如《劝农》中“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资待靡因”分别出自《老子》十九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和《老子》十八章中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12]36-37;陶渊明将其用于《劝农》,表达了自己对上古生民朴实自足生活与理想社会的赞叹之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的“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引用了《庄子·渔父》的“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12]184,这里的“真”,表现了陶渊明归隐的一种夙愿,希望保持内心的纯真;《杂诗十二首》(其七)中的“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引用《列子·仲尼》中的“处吾之家,如逆旅之舍”[12]353,表达出诗人对道家顺其自然的赞同,追求本真的愿望;《形影神(并序)》“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化用自《列子·天瑞》“吾又安知营营而求生非惑乎?”[12]61他将生死看作同类,毫无生死之忧。陶诗借此典故对为了留名而惜生的人们感到困惑,用过形、影的对话表明自己顺应自然的生死观。陶用道家典故41次之多,主要是为抒发自己安贫乐道的求真之心,感慨生命流逝之际,遵循自然之法。其实,与其说陶所说者为老庄,不如说陶诗对宇宙、人生、生死、祸福、历史等都有深刻的思考,作品及其人物形象都包含和表现出说理要素。作为理学家的朱熹,追和陶诗,作《寄题梅川溪堂》云:“静有山水乐,而无车马喧。”[28]又作《夏日二首》之一:“静有图史乐,寂无车马喧。”[29]之所以如此爱好,是因为陶诗意境冲淡,甚有理趣。陶诗有生活的思考,与儒家经典暗合,契合了理学家所倡导的文从道出,很容易为理学家接受与弘扬。
朱熹不仅继承前人肯定陶诗的“平淡”价值,而且将其作品纳入到“道”的产物,揭示其中的哲理,陶渊明其人其诗成为理学典范,从而朱熹重新抬升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钟嵘在《诗品》中,将陶诗列为“中品”,“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30]300此后论者如叶梦得、思锐、胡仔等对理论渊源以及隐逸定位多有不满,至王士祯才提出:“中品之陶潜,宜在上品。”[30]304而朱熹却重建文学谱系,将陶诗直接风骚:
尝间考诗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故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其不合者,则悉去之,不使其接于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则其为诗,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矣。[31]
且不论朱熹“三变”、“三等”的崇古理论是否存在问题,但他将陶渊明附骥于诗骚之后,并以为“诗之根本准则”,确乎在陶渊明研究史上振耳发聩了。在《楚辞后语》卷四中,朱熹认为陶渊明不俯仰时俗,《归去来辞》是“见志”之作。与其说这是对《归去来兮辞》的理解,不如说这是朱熹建构陶渊明人格的说明,不仕二姓,更是忠贞的体现。朱熹依据晁补之《续楚辞》《变离骚》而补定《楚辞后语》,“故今所欲取而使继之者,必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乃为得其余韵,而宏衍巨钜丽之观,欢愉快适之语,宜不得而与焉。……陶翁之词,晁氏以为中和之发……抑以其自谓晋臣耻事二姓而言,则其意亦不为不悲矣。”[32]9朱熹肯定了屈原忠君爱国,其作品出于至情,而陶渊明也正是接续这种精神的代表。
宋人与唐人重气韵不同,转而爱好平淡有味,而宋代陶渊明文学地位不断提升,“永叔推《归去来辞》为晋文独一;东坡和陶,称为曹、刘、鲍、谢、李、杜所不及”[33]。朱熹一方面有创作体验,能够涵咏作品;一方面继承理学,认为陶诗“自然”,是“道”的产物;最关键的是,陶的人品与作品是忠君爱国的,除“增夫三纲五典之重”[32]2外,还可以寄寓对现实斗争的积极态度。朱熹对陶的肯定与提升,不仅是对文坛不正之风的反驳,重建文坛的正宗谱系;也是对理学观念的倡导,以陶为楷模,证明文从道出的正确性;同时,以陶为典范,对当时投降派予以打击,纯粹民风的作用。
三、从平淡到豪放:朱熹对陶诗性情的揭示
陶渊明诗歌的平淡除了上述风格冲和之外,还有内在性情的特点。萧统在《陶渊明文集序》说:“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12]613-614这是最早将陶渊明“平淡”从其人其诗两方面来看待的,但他并没有看到人格的复杂性,而仅以单一的平淡看待陶渊明。唐人无论是孟浩然、李白还是杜甫、白居易,多谈陶渊明好酒,其实是设想陶渊明借酒麻醉自己,以应对现实,也就是:“爱酒不爱名,忧醒不忧贫。……归来五柳下,还以酒养真。人间荣与利,摆落如泥尘。”(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3]20需要麻醉,那么也就是说内在有矛盾冲突,可惜他们没有挑明。
倒是韩愈,诗文风格大多奇崛雄伟,看似与陶渊明诗风格格不入,却揭示陶诗的内在冲突。韩愈曾言:“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韩愈《答陈生书》)、“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韩愈《题哀词后》),韩愈主张的是“修其辞以明其道”(韩愈《争臣论》),即“文以明道”,在韩愈看来,文与道是可以统一的,“文以明道”与后世所言的“文以载道”是不同的,明,即彰显,而非承载。韩愈认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34],这也是陶渊明创作诗歌的内在推动力,“及读阮籍、陶潜诗,乃知彼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35]陶渊明的隐居在韩愈看来是排解内心不平的特殊方式,是对其所处时代的不满与反抗。
二程对韩愈的古文运动表示了轻蔑的态度:“退之晚来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④朱熹对韩愈的文道观也有不认同的地方,他在《论文上》中说:“这文皆是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36]4298“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36]4314由此可见,朱熹是有重道轻文的倾向性,但他也并非完全否认文学的价值,事实上,他于文道关系这一问题上是存在矛盾的,作为理学家,他更注重文章的工具性和其教化意义;但作为文学家,他也不否认文学的独立地位,对于文学的不同风格,他也能够接纳与欣赏,对于作诗也有着极大的兴趣。朱熹虽然也不赞同韩愈致力于古文创作,但他毕竟对韩文也着力颇深,曾编选《昌黎文粹》,并撰有《韩文考异》十卷。在这种情况下,朱熹继承韩愈的论陶观点并进一步发挥。
陶渊明确曾心怀大志:“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12]347而《咏荆轲》也确实令人血脉喷张,所以朱熹认为陶渊明并非生性冲淡之人,“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37]4323“陶却是有力,但语健而意闲。隐者多是带性负气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论文上》)[37]4325朱熹指出,渊明之隐,或为无奈之举,是于乱世中独善其身以固守本心。渊明之豪放,是“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12]371的安贫乐道,是“狡童之歌,凄矣其悲”(《读史述九章·箕子》)[12]514的怆然之叹,也是“君子死知己”(《咏荆轲》)[12]388的悲壮豪情。之所以说其豪放“得来不觉”,大抵是因为陶渊明淡泊洒脱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而他又惯于借古之贤士,来抒发内心慷慨,《咏贫士》和《读史述九章》等,除却表达对先贤的敬仰,也是阐明了自身在道德层面的追求。
平淡和豪放这两种性格交织,共同刻画出了一个立体、真实的陶渊明。朱熹“豪放”之论在陶渊明诗评中是比较新颖的观点,打破了固有思维和偏见,也能看出他对陶诗研究之深入。朱熹对陶渊明诗歌的看法大抵可以总结为:平淡而非寡淡,豪放中有旷达,这二者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朱熹之所以突出强调陶渊明的豪放,也是为了展现陶大义凛然、不畏生死的一面,为其教化民众的政治目的做铺垫。渊明并非遗忘世事,相反,他对时事亦有隐忧,但最后,他在矛盾中通透了,此种思虑被他放旷的情怀排解了,他所坚持的,是个性的释放,是“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辞三首》)的泰然与风流。朱熹最早挖掘出陶诗的豪放风格,在陶渊明接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苏轼与朱熹所处的年代相去不远,朱熹曾点评苏轼的和陶诗。苏轼对陶渊明经典化的推动起着难以磨灭的影响,苏轼揭示陶诗艺术上的内在含蓄性,他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与苏辙书》)[3]35,曾作和陶诗一百零九篇,掀起了文学史上和陶、评陶、拟陶的新风潮。朱熹曾将此二人作比:“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东坡乃篇篇句句依韵和之,虽其高才,似不费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38]朱熹认为苏轼拟陶之作模仿痕迹较为明显,苏轼的文字“驰骋,忒巧了”[36]4300、“华艳处多”[36]4308。“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揭示陶诗内在思想与外在形式的矛盾统一,启发后人进一步思考,使得陶诗的价值不断被发掘出来。而朱熹的豪放论却是强调人格中的多样性,苏轼强调作品,朱熹强调人品,主体不完全相同。
四、朱熹论陶的历史传承与突破
朱熹论陶既有家学渊源,也有发展过程。他的父亲朱松,就是一位理学家,推崇《诗经》,力贬唐诗。[20]119傅自得《韦斋集序》记录了朱熹父亲论诗的内容:“古之诗人,贵冲口直质,盖与彭泽‘把酒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同一关棙。”[39]7121岁时,朱熹在《与程允夫书》中说:“某闻先师屏翁及先大人解曰:作诗须从陶柳门庭中来,乃佳耳。若不如是,不足以发潇散冲淡之趣,不免于尘埃局促,无由到古人佳处也。”(《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九)[39]135年轻时朱熹就以陶为异代朋友:“平生尚友陶彭泽,未肯轻为折腰客。胸中合处不作难,霜下风姿自奇特。”(《题霜杰集》)[39]137赞誉陶渊明为人,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陶的欣赏:“佩萸笑长房,把菊追陶公。”[40]朱熹甚至效法陶渊明游斜川:“迥眺曾城皋,朗咏斜川流……但得长如此,吾生复何求。”[41]他对农事颇为热情:“久矣投装返旧墟,不将心事赋《闲居》。荷锄带月朝治秽,植杖临风夕挽蔬。三径犹寻陶令宅,万签聊借邺侯书。木瓜更得琼琚报,吟咏从今乐有馀。”(《再和》)[42]他还为隐居找到了好的去处:“已寻两峰间,结屋依阳冈……誓将尘土踪,暂寄云水乡。封章倘从愿,归哉澡沧浪”(《屡游庐阜欲赋一篇而不能就六月中休董役卧龙偶成此诗》)[43]。朱熹宛然渊明,忘怀得失,向往隐逸生活。朱熹的朋友也把他当作当世陶渊明看待,韩元吉在给朱熹送酒时就说:“平生爱酒陶元亮,曾绕东篱望白衣。”⑤吴芾也在《和陶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韵寄朱元晦》中说:“我爱朱夫子,处世无戚欣。渊明不可见,幸哉有斯人。”⑥朱熹已经和研究对象融合为一。
朱熹对陶渊明的认识,有浓郁的理学色彩。崇尚“中庸”之道,对风雅正统的追求使得南宋理学诗派的诗风偏向宁静平易,他们的文学主张多与道德修养、宇宙生命、真理真知有关。以理学家观之,诗本情性,陶渊明无志于世,深得理学宗旨。朱熹之所以将陶渊明的道德境界总结为忠义不屈、重大伦大法、固穷守节、不慕名利,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传道的需要,在朱熹心目中,勤学、修身、坚守道德情操与忘世是统一的,他去欲存理的理学思想,赋予了诗歌深厚的道德根基。朱熹称道、弘扬陶渊明的高洁品质,突出义利之辨,也是为了宣明教化、敦化风俗、教诫不良,他知南康军期间,也一直致力于推动当地民俗的淳化。他以陶渊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一诗劝诫士子:“但能参得此一诗透,则公今日所谓举业与夫他日所谓功名富贵者,皆不必经心可也”。[44]他不考察陶渊明当时的具体行程,而是对诗中的议论深为感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陶渊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人生旅途多险,更加风波阻挠,与其追求仕进,汲汲于名利,不如及时归隐。以此诗劝勉士子,要求他们守住本心、抵制诱惑,实为新颖。因此,朱熹对陶渊明的发明,有其身为理学家的考量,也是借陶诗中体现的一些道德精神来诠释自己的一些思想观念,将其作为载道、论道的工具。
朱熹对陶渊明的推崇,无论是从南宋社会背景、理学传道要求、还是朱熹个人经历来看,都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而他对陶渊明品格、诗文的评价,从陶渊明接受史来看,也是进步的,后人多引其“欲有为而不能”作为对陶渊明的评价。朱熹对陶渊明的认识在陶渊明接受史上是尤为重要的,宋朝时期的陶渊明批评研究已经大有突破,朱熹亦能在此基础上发表创新之见,其观点也一直影响着后世对陶渊明的研究。他将陶诗作为“诗之根本准则”,也影响了后世对陶的评价。可以说,朱熹为陶渊明经典化贡献了不可小觑的力量,赋予了新的研究价值。
注释:
① 如王维在《与魏居士书》中就提出既然陶渊明不肯屈腰见督邮,后贫而屡次乞食,“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陶是忘大守小。参见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页。
② 朱熹在南康军行事俱参阅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03-704页。
③ 李剑锋认为朱熹醉石题诗是醉石流变中里程碑,参见其《渊明醉石题咏流变考论》,《学术研究》2013年第7期。
④ 《二程遗书》卷十八,转引自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册第112页。
⑤ 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六《九日送酒与朱元晦》,转引自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第539页。
⑥ 吴芾《湖山集》卷一,转引自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第7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