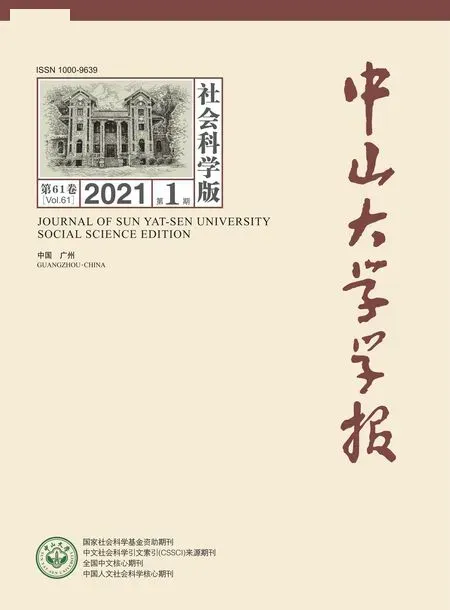胡塞尔论涵义与对象的区分*
——以弗雷格的语义学为参照
2021-01-03高松
高 松
一、涵义与对象指称的区分
1892 年,在《论涵义与指称》一文中,弗雷格以单称词为例明确区分了一个语言表达的涵义和指称①事实上弗雷格在1891 年1 月9 日在耶拿医学和自然科学学会会议上作的演讲中已经初步提出了这一区分。参见[德]弗雷格著,王路译:《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6页及以下。。这是现代语义学中的重要一步。在《逻辑研究》第一研究中,胡塞尔作出了类似的区分,所举的例子同样属于单称词②不同之处在于,在弗雷格的术语体系中,指称包括对象和函数,而胡塞尔则将一切指称视为对象。此外,二者所选择的表达方式也有所区别,弗雷格分别用Sinn 和Bedeutung 来表示涵义和指称;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则视二者为同义词,都表示涵义,而指称即是对象(Gegenstand)。由于涉及译名统一以及其他翻译问题,本文的部分译文可能在现有译本的基础上作了修改,以下不再一一说明。。研究者们争论的一个焦点在于:胡塞尔在这一点上是否受到了弗雷格的影响?例如德雷福斯断言:“胡塞尔只不过是接受并运用了弗雷格的区分……所做的唯一改变只是术语上的。”③Dreyfus,H.,“The Perceptual Noema:Gurwitsch's Crucial Contribution”,in Life-World and Consciousness:Essays for Aron Gurwitsch,ed.,Embree,Evanston,Il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2,p. 139-140.莫汉蒂则认为胡塞尔在1891 年对施罗德(E. Schröder)的“逻辑代数讲义”所作的评论中就已经独立区分了涵义和对象④Cf.,Mohanty,JN.,Husserl and Frege,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p. 2.。
无论在这一点上是否存在着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在各种语言表达中,弗雷格和胡塞尔都选择了单称词作为区分涵义和指称的典范。更仔细的考察揭示,它们属于单称词中的限定摹状词而非真正的专名。弗雷格的例子是,“晨星”和“暮星”这两个表达式虽然涵义不同,但都指称同一个星体①参见[德]弗雷格著,王路译:《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第96页。;胡塞尔的例子则是,“耶拿的胜利者”和“滑铁卢的失败者”虽然涵义不同,但都指称同一个人(下文简称“拿破仑例子”)②参见[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逻辑研究》修订版,第二卷第一部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55页。。无论是弗雷格还是胡塞尔都认为,涵义和指称的区别可以扩展至一切语言表达,但值得注意的是,二者的观点除了在限定摹状词上表现出某种一致外,在任何其他的表达类型上都判然有别。
弗雷格对涵义和指称的区分有着相对清晰的论述,相形之下,胡塞尔的区分原则却晦暗不清,并遭到一些学者的诟病。例如,弗雷格专家达米特曾如是评价胡塞尔的意义理论:
胡塞尔给我们留下一种只是模糊的有关对象指称的观点,以及一种只是模糊的有关涵义和对象指称如何联系的看法。③[英]达米特著,王路译:《分析哲学的起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57,57页。
如果说达米特的评价有可能出于对胡塞尔思想的不了解,那么深谙胡塞尔现象学的图根特哈特的相关评价便对胡塞尔更为不利:
胡塞尔大概不理解弗雷格所设想的形式关联,至少肯定认为弗雷格的结论在直觉上很不自然;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这一方案与摹状词的相关区分缺乏类比性。而他也没有对之进行进一步的扩展。④Tugendhat,E.,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Sprachanalytische Philosophie,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94,S. 154.
二位学者对胡塞尔的批评主要涉及他关于句子之指称的问题。众所周知,弗雷格将真值看作是断定句的指称,并对这个看似不自然的理论给出了明确的辩护。然而,在上述评论者看来,胡塞尔只是在涉及限定摹状词时接受了弗雷格的区分,却并不理解这一区分背后的原则,因此在涉及句子之指称问题时,他发现无法跟随弗雷格的脚步,于是便不得要领,不知如何抉择。例如二者都提到胡塞尔在将句子主词所对应的对象还是句子所描述的事况(Sachlage)看作句子的指称时犹豫不决。
那么胡塞尔到底有没有一套独立于弗雷格的涵义理论?本文认为,弗雷格和胡塞尔的语义学都与“真”密切相关。然而,对“真”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双方不同的语义学原则,前者从外延的角度理解“真”,因此其语义学以被理解为指称之对象的外延之真为原则,而后者则从内涵角度理解“真”,其语义学以被理解为意向之充实的内涵之真为原则。
对内涵之真的一般性解读倾向于将对象理解为带有涵义的意向对象,因此涵义与对象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平行关系。这一解读对“拿破仑例子”中所展示的涵义和对象的区分而言十分不利。然而,本文将梳理出《逻辑研究》的文字中所蕴涵的另外一种被忽视的解读可能性,在内涵之真的原则中维持涵义与对象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为胡塞尔对涵义和对象的区分作出一个合理的辩护。为此,我们先简述弗雷格的语义学原则。
二、弗雷格的外延之真
弗雷格区分涵义与指称的原则十分清晰,如达米特所说:
在判定应该把什么看作是一个表达式的指称的过程中,弗雷格有个明确的问题要问:它如何有助于决定任何含有该表达式出现的句子的真值?这里,这种帮助必然是它与在任何情况替代它真值都保持不变的一切表达式所共同具有的东西。⑤[英]达米特著,王路译:《分析哲学的起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57,57页。
这条原则即莱布尼茨早就表达过的保真替换原则(salvaveritate):“彼此可保真互换的东西是等同的。”①Lebniz,“Non inelegans specimen demonstrandi in abstractis”,Erdmann edn. Oper. Philos. I,p. 94.因此,两个涵义不同的表达式,只要互相替换后能保持句子的真值不变,我们就说它们具有相同的指称。弗雷格以一种十分直接的方式贯彻了这一原则:他直接将“真”和“假”这两个真值本身视为句子所指称的对象。但事实上,要想达到保真替换的目的,不一定非得如此。比如考虑三个句子:1)暮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2)晨星是一个被太阳照亮的物体;3)月亮是地球的卫星。这三个句子的共同点在于真值相同。然而前两个句子包含涵义不同但指称相同的专名“暮星”和“晨星”,它们之间的关系显然比它们与第三个句子之间的关系更密切。我们可以说,前两个句子不仅具有相同的真值,还指向同一个事实。并且一般地说,一切经过如此替换的句子都首先指向同一个事实。
将事实看作是句子的指称,不仅同样能遵循保真替换的原则,而且更符合从摹状词出发区分涵义与指称的自然理解。而将句子的指称规定为真值,似乎太过于宽泛也太违反常理了。但是弗雷格另有考虑,他希望在进入命题演算的阶段能直接按真值表计算出复合句的真值。为此,他需要且仅需要在达到句子层面时谈论真值,于是真值便先天地要成为句子的指称。而从句子下行至句子的组成部分,才又根据此原则将专名所标志的对象看作是专名的指称②弗雷格也曾试图从摹状词的涵义和指称的自然区分出发,利用“替换下保持不变”的原则论证句子的指称为真值。然而他真正遵循的其实是“保真替换”原则,因此整个论证都有窃题之嫌。参见[德]弗雷格著,王路译:《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第104页。。因此,在确定指称这件事上,弗雷格一开始就是以句子之真为鹄的的。
后来的逻辑学家将弗雷格所遵循的保真替换原则称为“外延论题”,并将弗雷格所创立的一阶逻辑称为外延逻辑③事实上弗雷格只在概念词这一层次上谈论外延,概念词的外延是落入该概念词所指称的概念之中的对象所构成的类。严格而论,在弗雷格那里专名和句子是不能谈论外延的。或许是因为罗素在其“On Denoting”中将弗雷格的Bedeutung 翻译为denotation,弗雷格的相关思想才在connotation(内涵)和denotation(外延)的模式中被转述。因此本文中所谈到的“外延”其实是弗雷格的“指称”(Bedeutung),而相应的“内涵”则相对于弗雷格的“涵义”(Sinn)。后世在广义上将弗雷格所创立的逻辑称为外延逻辑,然而弗雷格却是以第三者身份出现于外延逻辑与内涵逻辑之争中的。参见[德]弗雷格著,王路译:《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第125页及以下。。在这种逻辑中,语言表达的指称被视为外延因素,而涵义则被视为相应的内涵因素。虽然弗雷格一直强调真的外延性,并不遗余力地批判一切试图从内涵上理解真的企图,但是“真”并非只能从外延的角度被理解。
三、胡塞尔的内涵之真
对真的一种古老理解在于表象与事物之间的符合一致,在弗雷格看来,这是一种前逻辑学的真之理解,而逻辑学家应该关注的是真展开于逻辑真理中的那个层面④参见[德]弗雷格著,王路译:《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第130,131页。。显然,符合论所涉及的是以认识明见性为前提的内涵之真,而以逻辑真理为导向的真之观念则只关注真的外延特性。我们先来看看弗雷格对真之符合论的质疑:
要使一个表象与一个事物一致,仅当这个事物也是一个表象时才是可能的。而且,如果第一个表象与第二个表象是完全一致的,那么它们就是重合的。但这正是人们不乐见的,如果人们把真确定为一个表象与某个现实的东西的一致性。这里,现实的东西与表象不同,这恰恰是根本的。但是这样就没有完全的一致,没有完全的真。这样就会没有任何东西是真的。因为仅仅一半真的东西是不真的。真所传达的东西既不多也不少。⑤参见[德]弗雷格著,王路译:《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第130,131页。
这一批评对“符合一致”作了一种实在论的解释,照此观点,的确不存在真理意义上的符合。弗雷格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因为当时的确有一种观点将表象与事物间实在的相似性看作是对此处符合一致的解释①参见[德]胡塞尔著,高松译:《文章与书评(1890—1910)》,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84—385页。。胡塞尔反对这种实在论的符合论,但却没有像弗雷格那样全然抛弃对“真”的符合论理解,而是试图在全新的意向性理论中为之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关于“真”的符合事实上是涵义之间的符合。具体而言,是符号意指行为的意向涵义与直观行为的充实涵义之间的观念符合。
胡塞尔为符合论辩护的策略在于,将表象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两种行为之间的关系,表象被解释为对事物的“仅仅意向”的行为,纯粹的符号行为是其典型;事物则是在另一种行为中亲自被给予的,即直观充实行为,感知行为是其典型。经此转化之后,表象与事物的符合就被还原为两种行为因素之间的符合:意向行为和充实行为之质料(涵义)之间的观念同一。“我所意指的正是此刻被给予我的”,这就是真之符合论的现象学本质。
至此为止似乎一切顺利,但是仔细一点就会发现,使充实行为成为充实行为,将之与仅仅意向的行为区分开来的东西——充盈——在此理论中似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假如满足于此,那么弗雷格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便仍然有效:“如果第一个表象与第二个表象是完全一致的,那么它们就是重合的。但这正是人们不乐见的。”的确,若充实行为不带来新的因素,这种“重合”——哪怕是观念的重合——就是毫无意义的;但如这一新因素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颖之物,即一种超出重合的“多余”,那么它必定会导致重合的不完全。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对它的持守导致弗雷格不顾对真理的日常理解而拒斥一种符合论的真理观。而要为真之符合论进行辩护,就必须消解这一悖论。这就需要表明,充盈是某种既新又旧的东西。
胡塞尔关于直观的理论提供了走出困境的可能性。直观行为的充盈,即它的直观代现者,并不是与充实涵义完全无关的因素,虽然立义(涵义—解释)是一种主动行为,但在对直观代现者进行立义时,我们并不能真的随心所欲,而是感受到了一定的被动性。因为通常的充实行为属于符号和直观相混合的代现,尽管其中符号部分在充实涵义(质料)和代现者之间建立的是偶然的、外部的联系;但是在纯粹直观部分中,二者之间具有本质的、内部的联系②参见[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逻辑研究》修订版,第二卷第二部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96—97页。。因此,虽然在充实行为中我们对代现者所进行的立义有一定的解释空间,但并非完全自由。正如某个对象的未来充盈的可能性总是被此对象之涵义所勾勒出的内视域预先规定了,反之,我们也不可能对某个现时的代现者进行完全任意的涵义—解释③即便在诸如鸭兔图的情况下,我们对代现者的解释也并非任意的。例如我们很难对鸭兔图采取除了鸭和兔之外的立义。。
如果我们承认充实涵义在一定范围内由代现者所决定,便可以将胡塞尔的符合论看作意指涵义与直观代现者之间的符合,既意向与充盈之间的符合。所谓的充实涵义只是中介,它是直观代现者为了能够与意指涵义符合一致而采取的涵义形式。打个比方:意指涵义就是指定角色装扮的脚本,直观代现者或充盈是演员,而充实涵义则是演员的装扮。演员根据脚本来装扮,以符和角色的需要。在此,根据脚本选择演员以及某个特定的演员所能进行的装扮虽然有一定的自由空间,但显然不是任意的。
一旦直观代现者获得了涵义形式,它就成了自身被给予的对象,而这同一对象在意指行为中仅仅被空泛地意向着。因此,从对象的角度看,真之符合结合了两种行为之对象的同一性与此对象之直观充盈程度的差异性,以此方式,胡塞尔的符合论便避免了弗雷格对一般符合论的指责:要么不能真正达成一致,要么毫无建设性可言。
胡塞尔关于涵义和对象的理论正出现于现象学符合论真理观的语境之中。语言符号之所以可以指称一个对象,是因为激活此符号的涵义意向意指一个对象④因此,正如莫汉蒂所言,胡塞尔的涵义首先不是语言的涵义,而是意指行为的涵义(Cf.,Mohanty,JN.,Husserl and Frege,p. 62)。确切而言,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将涵义看作意指行为的种,虽然这个看法后来被抛弃了,但涵义始终首先与意指行为相关。。此对象首先是意向对象,即如其所意指(意向)的对象。只有这种对象才能在直观充实行为中如其所是地给出自身,满足意指行为的单纯意向(仅仅意向),使得认识主体获得明见性的体验,实现内涵意义上的真理。
四、意向对象的困境
斯多葛学派有一个著名的厄勒克特拉悖论:
厄勒克特拉知道自己有位哥哥叫奥列斯特,但她从来没见这位哥哥,哥哥有一天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于是:
(1)厄勒克特拉不知道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是哥哥,
(2)厄勒克特拉知道奥列斯特是哥哥,
(3)站在厄勒斯特拉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奥列斯特:
所以(4)厄列斯特拉既知道又不知道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是哥哥。
按照外延逻辑的保真替换原则,既然“站在厄勒克特拉面前的这个人”与“奥列斯特”的指称(外延)是等同的,那么(2)中的“奥列斯特”就可用“站在厄勒克特拉面前的这个人”来替换而不会影响句子的真值。可是,这样却导致出现了悖论(4)。因此,“站在面前的人”和“奥列斯特”虽然外延相同,但有一种因素却不同,正是这一因素导致二者的保真替换失效。这种东西被斯多噶学派称为“λεκτόν”,即“所意谓的东西”,实质上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内涵。
这个悖论很好地展示了胡塞尔的意向(内涵)对象与弗雷格的外延对象之间的区别。虽然弗雷格将涵义规定为指称对象的“被给予模式”①参见[德]弗雷格著,王路译:《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第96页。,但是对外延因素的偏爱使他从未认真考虑指称对象如何在涵义中被给予的问题,而只是满足于能够获得一个指称。而胡塞尔的意向对象则首先是如其被意向的对象,即以符合意指行为(涵义)的方式被给予的对象。
然而,著名的拿破仑例子却对意向对象的解读方向非常不利。因为能够充实“滑铁卢的失败者”这一涵义意向的对象只能是那个呈现为“滑铁卢的失败者”的拿破仑而非呈现为“耶拿的胜利者”的拿破仑。这两个意向对象是不同的。意向对象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意指的对象本身”②参见[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逻辑研究》修订版,第二卷第一部分,第58页。,而意指一个对象的各种方式无非就是隶属于此对象的各种涵义。因此,如果对象就是意向对象,那么涵义与对象之间即便不是完全不可分,也至少应该是《观念1》中能意(Noesis)和所意(Noema)的平行性所标示出的一一对应关系,而不可能是“多与一”或“一与多”的关系。然而胡塞尔却说,两个涵义不同的表达“滑铁卢的失败者”和“耶拿的胜利者”指向同一个对象。
有批评者已经指出了拿破仑例子与胡塞尔的基本立场之间的冲突,这无疑增加了胡塞尔在此例上抄袭弗雷格的嫌疑。如果胡塞尔知道上述两个涵义指向同一个对象,这是因为他利用了关于拿破仑生平的知识,在两个意向之外对二者进行了综合:
简言之,是知识而非对表达的单纯理解才使得人们能够区分涵义和对象。但是胡塞尔却坚持认为在对表达的单纯理解中人们就以指称的方式指向一个对象了。③Atwell,JE.,“Husserl on signification and object”,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6,1969,p. 316.
的确,由于胡塞尔将真之符合的双方看作两种行为,即意指行为和(狭义的)充实行为,而按定义,任何行为都必然同时具有其涵义和对象,因此单从意指行为单侧就已经有对象了,充实行为对于这一区分显得完全是多余的。胡塞尔所追求的内涵之真仿佛完全是分析而非综合的:作为符合之一方的涵义完全决定了另一方,即充实它的对象。弗雷格的批评如影随形。
但我们依然有为胡塞尔辩护的空间。单纯对表达式的理解恰恰无法使我们获得作为知识(认识)的真,哪怕是内涵之真。在《逻辑研究》第一研究中,胡塞尔在多处反复强调,与对象的关系在表达的符号作用或单纯的理解中是非本质性的,只有在表达的认识作用中,与对象的关系得到实现,对象才真正出场。如果单纯的理解已经决定了对象的一切,那么空乏的意向获得充实时,我们在认识方面获得了什么呢?如前所述,直观充盈的这个“多出”必然是建设性的,否则符合论真理观就谈不上认识以及“真”。
我们在第3节中曾建议将真之符合理解为意指行为的涵义意向和充实行为所给出的充盈之间的符合。这种理解在胡塞尔的文本中并非毫无依据,例如相对于充实涵义,他明确将意指涵义称为“不折不扣的涵义”(Bedeutungschlechthin)①参见[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逻辑研究》修订版,第二卷第一部分,第60,57页。,但就对象而言,“符号—涵义意向只是指向对象,直观意向则将对象在确切的意义上表象出来,它带来对象本身之充盈方面的东西”②参见[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逻辑研究》修订版,第二卷第二部分,第81页。。
如果从认识以及内涵之真的视角重构涵义和对象的区分,那么“真”就是意指涵义与充盈的符合。虽然胡塞尔在以“表达与涵义”为题的第一研究中已经引入了涵义和对象的区分,但只有进入第六研究“对认识的现象学阐释之要素”之后,才能更为深入地澄清这一区分。然而即便在第一研究中,紧接着在引入涵义—对象之区分的第12小节之后,胡塞尔在第13小节就对这一区分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他首先以一种几乎否定12 节的语气告诫我们不能过于认真地对待在每个表达上都可以区分涵义与对象这种说法,并进一步强调表达的本质仅仅在于它的涵义③参见[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逻辑研究》修订版,第二卷第一部分,第60,57页。。之后,他突然跳入第六研究的语境之中来说明多个涵义对应着一个对象的真实意思:
但同一个直观……能够为不同的表达提供充实,只要这个直观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被范畴地把握到并且可以与其他直观综合地联结在一起。我们将会听到,表达与它的涵义意向在思维和认识的语境中不仅使自己与直观(我指的是外感性和内感性的显现)相称,而且也使自己与各种理智形式相称,通过这些形式,那些单纯被直观到的客体才成为合乎知性地被规定的和彼此相互关联的客体。由此看来,当表达不具备认识作用时,它也仍然作为符号意向而指向在范畴上被赋形的统一。这样,不同的涵义可以属于同一个(但在范畴上受到不同把握的)直观,并因此也属于同一个对象。④[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逻辑研究》修订版,第二卷第一部分,第57页。这段引文几乎可以看作康德哲学的现象学注释,在此,胡塞尔似乎分享了某种曾经引导过康德的直觉。我们可以设想没有语言能力的动物也可以具有感性直观的能力,因而也至少可以和我们一样看到个体的感性对象,然而它们却无法在知性上用概念把握这些对象。
原来,胡塞尔在涵义—对象的区分中所谈的对象是一种剥离了范畴形式的“单纯被直观的客体”。于是产生了两个相关的问题:1)这种对象是否也剥离了涵义?2)涵义与范畴的关系如何?
五、“非意向”对象
我们先来思考第一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谈论剥离了涵义的对象无异于谈论木的铁、圆的方。因为从现象学的立场看,一切对象都是立义(涵义—解释)行为的构造成就,也正因为此,我们才会说胡塞尔的对象首先是意向对象,即“作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意指的对象本身”,也正是这一对象概念最后在《观念1》中变成了一个行为的所意涵义:“涵义就是这个所意(Noema)的‘在方式中的对象’。”⑤[德]胡塞尔著,李幼蒸译:《纯粹现象学通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2页。
然而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大概已经能确定,若要在胡塞尔那里维持涵义和对象的区分,最终必须找到某种在一定程度上剥离了涵义的对象,或曰“非意向”对象。这种对象当然不是纯粹理论上的虚构,甚至一种素朴的实在论直觉恰恰要求这种对象的存在。现象学无疑必须恰当地安置这种直觉。事实上,设想某个对象不变,但是它所具有的涵义发生变化完全是可能的。在胡塞尔的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非意向”对象的两个候选者。
第一个候选者是第五研究中相对于意向对象(Gegenstand,so wieerintendiertist)提出的绝然对象(Gegenstandschlechthin),后来在《观念1》中发展成作为涵义承载者的可规定的空x⑥参见[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逻辑研究》修订版,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66页;[德]胡塞尔著,李幼蒸译:《纯粹现象学通论》,第232页。。这个对象概念非常适于用来解释拿破仑例子,然而却似乎脱离了意向—充实的内涵之真语境。因为很难说这个x 是对它所承载的各种涵义的充盈,毋宁说,它表明互属的诸涵义意向不仅具有自身的特定内容,除此之外还总有一种超越自身内容向外汇聚到一个对象极的趋势。这个对象概念偏向于弗雷格的语义学①以弗勒斯达尔(D. Føllesdal)为首的一些学者正是以弗雷格的语义学来解释胡塞尔的涵义理论的。,至少在第一研究第13节的上述引文中,胡塞尔并未采取这一进路。
第二个候选者是本文一再强调的,即将真之符合论中充实的一方视为充盈本身,此充盈即为剥离了涵义的对象。这个选项的优点在于没有脱离意向—充实的语境,进而与第一研究第13节的上述引文相互兼容。“单纯被直观到的客体”很容易被解读为未经解释的充盈,因为胡塞尔此处用单纯直观确实意在描述一种尚未经任何立义或尚未起代现作用的纯粹感性显现。但相比绝然对象,这一选项却面临着一个更为严峻的挑战,因为胡塞尔明确说作为直观代现者的充盈本身不是对象②《逻辑研究》中的充盈有三种含义:1)作为被给予对象的直观代现者,2)作为行为的直观内容,3)作为以被意指的方式被给予的对象本身。胡塞尔在第六研究第22节中明确区分了前两种含义,又在第39节中引入了第三种含义。一个术语具有三种含义,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作者在术语使用上的混乱,这从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三种含义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三种含义中唯有第一种是剥离了涵义因素的,然而却也是唯一无法被解释为对象的。本处使用的正是这一含义。。
上述两种非意向对象的候选者各有缺点,如果能找到某种方式将二者结合起来,或许就能获得真正满足胡塞尔区分涵义—对象之意图的“非意向”对象。事实上,如果深入到意识最原始的综合行为中,就能获得一种初步的结合。
考虑到意识最原初的综合作用,根本就不存在纯粹的充盈,充盈与对它的“对象性立义”是一同被给出的,哪怕这种立义尚未携带任何语言涵义,不带有任何述谓的规定,只是空洞地给出一个对象。事实上,即便缺乏知性能力的动物也不会看到一个纯粹的充盈,它们总是看到一个对象,在空间中随视角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显现。它们也具有内时间意识,可以在每一个当下将以滞留的方式意识到的上一刻充盈、以原印象的方式意识到的此刻充盈以及以前摄的方式意识到的一下刻充盈综合统一起来。
绝然对象x 与充盈以此方式初步地结合了起来,前者因此而被带入了意向—充实的语境之中。然而这种结合多少是偏向前者的,所以由此获得的对象依然是对诸涵义无差别的。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在与具体充盈结合后,对象的一般性并不应该仍然是一种形式的一般性。对象应该具有某种随着进一步展开而变得越来越确定的前—涵义空间。
在《经验与判断》中,胡塞尔从前述谓经验和视域意向性的角度将这一非形式的一般性规定为类型化的视域:
一开始就对发达意识预先规定下来的不仅仅有作为“对象”、“可说明物一般”的一般性理解,而且已经有对一切对象的某种确定的类型化……从背景中发出剌激的东西以及在最初的主动的抓取中所把握到的东西,都是在某种远为丰富的涵义上被知悉到的,即它在背景中被动地被理解时,已经不单是作为“对象”、可经验的东西、可说明的东西的,而是作为物、作为人、作为人的作品,因而是在更进一步的特殊性中被理解的。因此它拥有自己的某种熟悉的陌生性之空视域。③[德]胡塞尔著,邓晓芒、张廷国译:《经验与判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55—56页。
在具体的意识生活中,对象总是在具体的、已经给定的视域中凸显出来的,因而即便还不具备明确的语言涵义,也已经带有了某种可能的前—涵义空间,胡塞尔将之称为类型。正是类型决定了对象,倾向于接受某些类型的涵义—解释,拒斥另一些。因此,第3 节中所说的充盈对涵义的限制,其实质正是作为视域而与对象如影随形的类型。
然而,为什么类型视域可以一般地先天与语言涵义相适应,达成直观与语言意向的符合?在回答这个终极问题之前,我们将试着解答上一节的第二个问题。
六、范畴与涵义
如果说第5 节是从对象出发接近涵义,那么本节我们试着从涵义出发接近对象。在第一研究第13节中,胡塞尔引入了一个本该出现于第六研究中的概念:范畴。涵义与对象之间一与多的关系被解释为以不同的范畴把握(fassen)同一个直观。胡塞尔明确将此处的直观理解为“外感性和内感性的显现”,即感性直观。接着他进一步明确了一个事实:“当表达不具备认识作用时,它也仍然作为符号意向而指向在范畴上被赋形的统一。”换言之,表达都是范畴性的。第六研究明确了范畴是一种被奠基的对象,甚至有自身的代现者。但在范畴上被赋形的对象显然只能是“在方式中的对象”,即与意指涵义一一对应的意向对象。例如,事态作为范畴对象与指向事态的陈述句的涵义之间就是一一对应的关系①在引入陈述句之对象的第一研究第12节中,胡塞尔在第一版中将陈述句的对象视为“陈述句所陈述的整个事态(Sachverhalt)”,而在第二版中则改为“隶属于陈述的整个事况(Sachlage)”。这一细微的差别对于本文的论述很重要。关于事态和事况的明确区分,参见[德]胡塞尔著,邓晓芒、张廷国译:《经验与判断》,第280页。。因此,如果我们意在寻求某种独立于涵义的对象,范畴对象显然并非合适的候选者。它们甚至应该被归为涵义一侧。问题是,是否一切涵义都是范畴性的,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感性直观的对象是否可以被视为剥离了涵义的对象?
纯粹的感性对象通常被理解为称谓行为(单束行为)的对象,正如作为范畴的事态是陈述行为的对象。然而这种对感性对象的理解显然过于宽泛了。在《逻辑研究》中,范畴并不限于陈述涵义,而是同样进入绝大部分的称谓涵义之中。不仅冠词作为大部分名称的构成要素表达着范畴形式,而且语词的名词形式、形容词形式以及单复数形式等等也在体现着范畴性,这其中甚至还包括语词的排列顺序②参见[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逻辑研究》修订版,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0,140,25页。。简言之,一切涉及语法的部分都是范畴性的。毫无疑问,像“滑铁卢的失败者”这样的摹状词自然充满着范畴,因此,在这一意指方式中的对象,即它的意向对象,便如“拿破仑是滑铁卢的失败者”所陈述的事态一样是范畴对象。
范畴具有如此的广度,这几乎要让我们得出结论:一切表达的涵义都是范畴性的,因此范畴与涵义之间是完全平行的。然而胡塞尔明确拒绝了这种解读的可能性:专名的涵义不是范畴性的③参见[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逻辑研究》修订版,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0,140,25页。。换言之,专名的意向对象是真正的感性对象,但并未剥离涵义。
至此,对第六研究的解读几乎已经否定了我们对第一研究第13节的解读。只剩下一种协调的可能性:专名的涵义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涵义,即在于一种“对此对象的直接意指”④参见[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逻辑研究》修订版,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0,140,25页。,因而在一切范畴性的涵义中都已经被预设了。专名的涵义(专有涵义)“以直接的方式”与对象相关,此时对象就在其直接性中被理解。但此处仍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解释。
七、专 名
专名很容易被认为是无涵义的,因为比如某个人被称为苏格拉底,或某个城市被称为科隆,严格而论是毫无理由可言的,因此似乎仅专名本身并不能带来任何理解。密尔说:
一个专名是一个无涵义的符号……如果我们陈述某一个事物的专名,如果我们指着一个男人说,这是米勒或迈耶,或者我们指着一座城市说,这是科隆,那么,仅仅如此,我们除了告知听者这是这些对象的名称以外,并没有告知他关于这些对象的任何知识。⑤参见[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逻辑研究》修订版,第二卷第一部分,第66页。
这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观点,然而胡塞尔却不接受。他的一个理由是:专名所指称的对象并不必须被认为是实存的,换言之,专名的对象也是意向对象,因此无需它同时也是一个真实对象,而这在无涵义的符号(指号)那里是做不到的①参见[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逻辑研究》修订版,第二卷第一部分,第66,67页。。
然而本文认为胡塞尔的这个理由是行不通的,因为他在后文中明确说,专名的正常使用要局限于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否则专名将失去它的直接性,具有了间接的意义“一个确定的,叫xxx 的人或东西”②参见[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逻辑研究》修订版,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50页。在后来的《逻辑研究增补》中,胡塞尔也否定了自己提出的这一理由。Cf.,Husserl,E.,Logische Untersuchungen. Ergänzungsband. Zweiter Teil. Texte für die Neufassung der VI. Untersuchung:Zur Phänomenologie des Ausdrucks und der Erkenntnis(1893/94—1921),2005,S. 362.。但这也并非表明专名就是一种指号。在笔者看来,胡塞尔在同一段落中的另外一番话倒是说出了真相:
【关键】在于向我们提出这个对象本身。这样,它才在陈述句中显现为被陈述的对象,在愿望句中显现为被愿望的对象,如此等等。只是因为这个功效的缘故,专名才能和其它名称一样,成为复合的和统一的表达的组成部分,成为陈述句、愿望句以及其它类型句子的组成部分。③参见[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逻辑研究》修订版,第二卷第一部分,第66,67页。
这段引文表明,专名之所以可以有涵义,是因为它可以出现于有涵义的复合表达(首先是句子)之中,专名的涵义在一种衍生的意义上同样源自其句法功能,即源自范畴!
这种说法不禁让我们想起弗雷格的语境原则,只不过语境原则以外延之真为鹄的,而胡塞尔的这一说法则仅仅承诺涵义来源于句法或范畴,或者来源于分环节(Geliedern)④参见[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逻辑研究》修订版,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41页。。这是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虽然涉及,但却未曾明确摆出的关于涵义的重要性质,在收入《全集》第20卷的《逻辑研究增补》中,胡塞尔才明确了这一点⑤Cf.,Husserl,E.,Logische Untersuchungen. Ergänzungsband. Zweiter Teil. Texte für die Neufassung der VI. Untersu⁃chung:Zur Phänomenologie des Ausdrucks und der Erkenntnis(1893/94—1921),S. 51ff.。可以被分环勾连,这正是语言作为有涵义的符号和其他符号的本质区别。非语言符号是整体性的,虽然不同的非语言符号也能传递不同的信息,但是它们无法被分环,并与其他符号重新勾连成为组合符号,以传达无限复杂的可能涵义,否则它们就已经是一种语言表达了。如果我们确定分环勾连是语言表达在结构上的本质特征,而涵义又是语言表达的本质规定,那么就可以获得一个弗雷格和胡塞尔(至少在《逻辑研究》中)都没有明确表述过,而海德格尔却在《存在与时间》中说过的命题:涵义是可以分环勾连(artikulieren)的东西⑥参见[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77页。。
获得这一命题之后,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弗雷格和胡塞尔都会选用限定摹状词来区分涵义和指称。因为一方面限定摹状词本身就是分环勾连的,因而具有涵义,另一方面它的目的又在于明白无误地指向一个对象,所以是区分涵义—指称的最佳例子,而真正的专名则更像一种无涵义的符号。然而,专名与无涵义的符号的本质不同在于,虽然专名在本质上无法被有意义的“分环”,但却可以作为一个可辨认的独立部分出现在不同的语词组合之中。因此,专名之为专名,也是以分环勾连为前提的,它是可以被“勾连”的符号,属于语言表达。
如果专名是有涵义的,那么在直观中可以充实专名意向的感性对象就必然也是有涵义的。然而,鉴于专名获得涵义的特别方式,专名之对象的涵义必然不同于摹状词对象的涵义。之前说过,专名意指其对象的方式是直接的。然而这一表述几乎是自相矛盾的。直接的意思是不借助于中介,而此处的中介就是涵义。我们理解了涵义,因而根据涵义给出的道路找到对象。但我们如何理解一个专名呢?
如果我们单独听到或看到一个之前从未接触过的专名,我们并不会获悉任何信息。如果未被告知这是一个专名,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属于语言符号。这本就是专名的应有之义⑦在一般情况下,比如我看见一张白纸上写着“张XX”,大概能知道它代表一个人名。但此时我已经利用了超出专名之外的知识,如“张”是一个常见的姓,而“张XX”大概是某一个姓张的人。换言之,“张XX”中的“张”(当然,“XX”也有可能被认出是人名的常用词)已经起到了摹状词的作用:姓张的某人。。因此,和其他语言表达不同,专名的这种出场方式无法使之成为一个表达,因为我们无法理解它。在胡塞尔看来,专名的正常使用要局限于我们所熟悉的人或物,以至于当我们说出或听到专名时,并不需要明确表象这个人或物的任何具体内容,却能直接将意向对准此人或此物,以便为随后可能会出现的述谓规定提供支点。然而,专名有可能如何被述谓,或者说可能进入怎样的一种分环勾连之中,这是由我们对此专名的熟悉所预先确定的。胡塞尔说:
在有意义地运用专名时,我们必须将专称之物,在这里是指“舒尔茨”这个确定的人,表象为这个确定的、带有某个内容的人。无论对这个人的表象是多么非直观,多么贫乏、模糊、不确定,这个表象内容不能完全没有。这种不确定性……永远不可能是完全无内容的。它自身在其本质中显然包含着进一步规定的可能性,而且这种规定不是在随意的方向上……而恰恰是就在这个同一的、在可能情况下被意指的“舒尔茨”的方向上。或者我们也可以与此相等值地说:在完全的具体性中的涵义意识凭借自身的本质建立了与某些群组而非其他群组的直观达到充实相合的可能性。由此可见,这种意识,即使它是完全非直观的意识,也必然会带有某些意向内涵,通过这些内涵,个体不是被表象为某个完全空泛的东西,而是被表象为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了的并且可以根据某些类型(作为物理事物、作为动物、作为人等等)来加以确定的东西,即便它尚未在这些涵义上被意指。①[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逻辑研究》修订版,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48页。
胡塞尔再次明确,专名虽然不具有像其他语言表达那样的明确涵义,但对它的使用也要建立在某种类型意义上的语境之上。《逻辑研究》中的这一说法与第5节末尾所引《经验与判断》的文字遥相呼应。
八、视域和语境
为了在胡塞尔的内涵之真的语境中替涵义与对象的区分作出辩护,我们一直在试图寻找一种与涵义若即若离的“非意向”对象。因为如果这种对象自身已经具备了确定的涵义,那么便无法维护这一区分,但如果它与涵义毫无关系,则又无法进入内涵之真的语境之中。通过对胡塞尔相关文字的解读,我们在第5节和第6、7节分别从直观和语言表达两个方面出发找到了通向这种“非意向”对象的道路。
从直观方面看,这种对象虽然尚不具备确定的语言涵义,却带有一个前—涵义的空间,先天地具备与语言涵义相适应的可能性。这一前—涵义的空间被称为类型视域。而在语言表达方面,与此“非意向”对象相对应的是专名。专名之“涵义”在于它可以进入某些特定的分环勾连之中,因而具有一种虽然尚未在涵义上确定,但却可以根据类型来确定的前—涵义空间,这一前—涵义空间可以被称为语境,此处所使用的是“语境”的字面意义。
从直观方面看,作为前—涵义空间的视域是意识权能性的游戏场,意识的目光在此空间中遵循一定的指涉规则自由活动。若不是已经潜在于此视域中,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被意识所关注,成为对象。因此,对象总要从某个视域中凸显出来,视域是对象的发生性基础。这一对象获得涵义的过程就是将潜在于其视域中的指涉规则以语言的方式明确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作为逻各斯的动物,本来就以相互交谈的方式生活在语言涵义之历史积淀所构成的生活世界之中,而生活世界正是一切视域的总视域。换言之,语言作为一种交互主体性的文化历史获得物是生活世界之指涉规则的构成要素,正是语言,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意义且有规则的世界之中。
然而,在这个深受语言影响的生活世界之中,有某类对象特别容易作为独立的统一体受到意识的关注,意识以最大的被动性,或者说按照最根深蒂固的习性接受它们从视域中的凸显。传统哲学称这类对象为殊相。殊相仿佛是世界的骨架,是对象的模板,是任何一份存在者列表上无可置疑的核心成员。殊相在语言中的对应物是专名,专名是语言中的原子,无法被进一步分环,却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进入勾连的语境之中。在很多语言中,真正的专名没有屈折变化,具有相对于各种语言的最大独立性。《逻辑研究》中对象之独立于涵义的素朴直觉即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