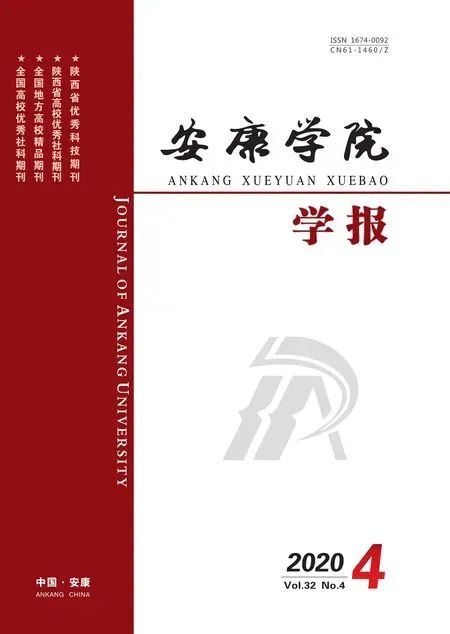翻译还是翻案?近现代“汉诗和译”的变异学考察
2020-12-27陈玉平
陈玉平
(安康学院 外国语学院/跨文化交际与翻译研究中心,陕西 安康 725000)
一、“汉诗和译”的历史演进
自古以来,凭借中日“同文异言”的特殊语言关系,日本人以“训读”的方式翻译和读解中国诗文。这种速成的翻译方法虽然弊病较多,但至今仍在沿用。同时,从《万叶集》开始,日本人就开始翻案、翻译中国诗歌,努力使其日本化,有力地推动了本国文学尤其是韵文学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在江户时代“国学运动”之前,日本人一直把汉诗文视为本国文学的一部分,并没有明确的国别意识。日本学者把汉字当作第二国文,或者把汉字当作辅助国字的重要文字,因此“日本人创作的汉诗文才能够声情并茂,构成郁郁葱葱的文学史”[1]。在此背景下,日本人对中国诗歌的学习、理解和应用自然就变得灵活而丰富了。
(一)古代日本丰富多样的汉诗“翻案”实践
自古以来,日本人消化和运用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翻案”。“‘翻案’一词,本来是中国诗歌创作论中的术语,所以最先接受的自然是汉诗人。在汉诗批评中,将对原诗加以改动以表达新的内容的方法,称之为‘翻案’。”[2]303“翻案”在日本有着广泛的认知度,但对其内涵的界定有着微妙的差别。木村毅认为,翻案是位于翻译与创作之间的文艺作品。即作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对原作进行大幅度的改写。如此一来,历史上对中国诗歌的许多处理方式都可以称之为翻案。
早在《万叶集》中,就有大伴家持等歌人根据中国诗歌的意境而吟唱的和歌,平安时代对白居易、张九龄等诗人的诗句做的“断句取义”等都已经改变了原诗的意境和艺术趣味。从对原作进行改写和重新表达的角度而言,奈良时代《和汉朗咏集》的朗咏(把汉诗与音乐、绘画相结合),平安时代《梁尘秘抄》与《唐诗选》的歌译、《句题和歌》的句译,中世纪的本歌取,江户时代松尾芭蕉及与谢芜村等俳人“断语取义”的俳译、三条西实隆的《和汉联句》等都可以归为“翻案”范畴。与现代意义上的翻译不同,这些“翻案”作品中,原诗与和歌同时出现。这种形式折射出译者具有并存共享的意识,不是用和歌去取代中国诗歌,而是让它们春兰秋菊,各擅其场[2]539。
(二)近代以来“汉诗和译”的多样化尝试
江户时代中后期的“国学运动”开启了日本人探寻本国文化的帷幕。明治维新以后,在西方价值取向的强势渗透下,日本人开始对中国文学戴上了外国文学的“帽子”。同时,在西方文艺理论的引导下,产生了“翻译”的概念,而在此之前,日本文学中只有“翻案”的概念。西方引入的“翻译”与日本原有的“翻案”截然不同。一般而言,“翻译”在内容和形式上必须忠实于原作,“翻案”则可以根据需要大幅度改写原作。因此,“日本近代文学中存在的诸多冠以‘译’的作品——如诗歌土歧善麻吕的《新译杜甫诗选》 (1955)、俵万智的《巧克力译〈乱发〉》 (1998)等,实际上却属于重新演绎古典诗歌或小说的‘翻案’之作”[3]439。
近代以来,受西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的影响,并顺应读者的需要,中国诗歌的现代日语翻译逐渐成为风气。译者为了克服传统训读“译诗语言陈旧、表达僵化、程式化不能贴近现代生活的弱点”[2]524,不断探索新的翻译方式,以“从看似陈旧的汉诗里获得新鲜感,找到现代性”[4]235。这些译作在译法上,有超译(豪杰译)、自由译、“印象”译、唱和等;在文体上,古典定型译和现代散文译并举;在语言上,有文语和口语,以及半文语。在书写方式上,除传统的和汉混淆文外,也有纯拉丁字母(如土歧善麻吕译的《春晓》)、纯片假名(如井伏鳟二译的《劝酒》)、纯平假名(如武部利男译的《中隐》)等多种书写方式,以给人呈现出不同的视觉效果。如此,近代“汉诗和译”在手段、语言、韵律、文体、书写方式等方面多样而灵活,自由而洒脱,一派异彩纷呈的景象。
二、翻案还是翻译?近现代“汉诗和译”的理论困境
按理说,近代以来日本学人受到了西方文学和翻译理论的强势影响,其翻译实践应该遵循现代翻译标准,但从既有翻译事实来看,大多数译诗并非如此,而是在抓住了中国古诗的神韵的基础上,进行了自由灵活的演绎。正如高兵兵所言:“按现代翻译标准来衡量,大部分的‘汉诗和译’作品均属于‘翻案’。”[3]440
由此,近现代“汉诗和译”究竟属不属于“翻译”?抑或是古已有之的“翻案”之法?长期受“信达雅”翻译传统影响的中国学者,以“庄重”的目光审视“汉诗和译”时,未免会产生困惑。这些困惑潜藏于学者们的行文当中,而且从日本诗歌汉译实践和效果中,我们也能窥见一端①如王晓平对近现代“汉诗和译”类型进行了梳理和考察,认为许多译法,如超译(豪杰译)、自由译、唱和、“印象”译等,都在韵律、修辞、典故、意境、情趣等方面与原作有所背离,游离于“翻译”与“翻案(改写)”之间。高兵兵梳理了近代“汉诗和译”纷繁复杂的诸多表现,认为按现代翻译标准来判断的话,这些译作大多属于“翻案”。她同时反观“和歌俳句汉译”现状,认为和歌、俳句在我国之所以热不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译者坚守“庄重”的翻译传统,怕发生误译和“创造性叛逆”等背离原作的情况,从而导致译作鲜有新意,缺乏活力,难以激起受众的阅读兴趣。。关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近代以来,中国学人承传统之风,尤其是翻译启蒙主义者严复基于只有“具有深厚传统的语言才能完成传达新思想的使命”[2]282而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思想,让中国学人走上了“庄重”的翻译研究路线。尽管有学者注意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学研究的两大转向(语言、文化转向),但传统经验式的思维痕迹仍难以消除,对于从事中日语言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此种倾向尤为明显。
其次,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翻译研究界出现了文化转向,此后不久,这一转向引入了比较文学领域,拓展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空间。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赋予了翻译研究更广阔的考察维度,更丰富的文学审美,并出现了“译介学”“接受美学”“变异学”等新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对于从事中日语言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可能对以上两大研究转向关注不足,从而出现了理论困惑。
再者,近代以来,中日文学翻译和批评一直是在西方翻译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而西方翻译理论是由西方国家“异文异言(不同国家的语言和文字不同)”的翻译实践而得来的。因此,当用西方理论对中日“同文异言(文字相同,语言不同)”状况下的文学翻译进行实践指导和批评时,就难免会出现对翻译特殊性揭示不足,甚至于出现偏误指导或掩盖差异等问题,而上文所述“翻译”或翻案的困惑也就随之产生了。
三、“汉诗和译”的变异学考察
那么,中日“同文异言”状况下翻译的特殊性究竟为何呢?笔者历时考察了日本人对中国文学典籍(尤其是诗歌)翻译和吸收的总体情况后,总结出了“和汉并存,同中求异,为我所用”的十二字方针。即,“在日本的汉译中,既有将原文照搬不动的训读,这是一种全方位的直译,是‘忠实’到不能再‘忠实’了”[2]523,也有把原文当作大袍大氅,由译家根据自己的需要翻案或改写为各类小衣小褂。前者是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继承,而后者则是对中国文化的过滤和重建,通过对中国诗歌的主题、意境、形象、情趣等进行日本化改造,以适应日本人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求,让中国文学在日本焕发出第二生命。很显然,“同中求异,为我所用”才是重点,也是翻译和接受的最终目的,这在近现代翻译中尤为明显。
一般而言,中国学者站在对外传播的角度去理解“汉诗和译”时,就容易产生究竟是翻案还是翻译的困惑,因为他们希望中国文学在日本尽量能够保持原汁原味。但若光看到中日文学的类同性和同源性,显然是不够的。中国诗歌之所以在日本经久不衰,丰富多彩,改造和变形是不可少的。故此,当我们站在文学接受者的立场来看待“汉诗和译”,把目光聚焦在中日文学关系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上时,就豁然开朗了。为了更好地考察中国诗歌在日本的接受和传播,进一步揭示中日文学交流的全貌,解除“汉诗和译”是翻案还是翻译的学理困惑,笔者拟以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理论视角,考察中国古典诗歌在日本翻译和接受的过程和规律。
(一)语言之旅
中国古典诗歌要进入日本,首先必须要打破语言壁垒。由于中日“同文异言”的特殊关系,最简便的办法就是用训读的方式最大限度地照搬汉文,但如此一来,译文的缺陷较多①黄珺亮(2004)认为训译汉诗存在“达意与传神的两难困境、押韵之美的缺席与退场、感情色彩的偏离与丢失、句法关系的变异与模糊”等缺陷。,汉诗的美感也大为缩水。当然,近现代“汉诗和译”主要是与“训译”相对应的“意译”,即现代语译。中日语言的异质性较大,若将汉诗翻译成日语,“总会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和口吻上违背或很不贴近原文”[5]。
佐藤春夫的《车尘集》突破了日本人靠训读和“返点”阅读中国古典诗歌的习惯,可以说是汉诗翻译的首创者。该译作都是女诗人的作品,其中许多为佚名诗歌,从选材上就体现出了明显的倾向性。他的译作,大体可分为忠实于原诗的翻译、对原诗进行改写和发挥的翻案和误译,且后者居多。翻案和误译首先体现在语言上的不忠实,如他译的《子夜歌》两首:
原作1:《子夜吴歌》侬作北斗星,千年无转移。欢行白日心,朝东暮还西。
译文1:『恋愛天文学』われは北斗の星にして 千年ゆるがぬものなるを 君がこころの天つ日や あしたは東暮れ西[6]374
佐藤氏以自己的感受和联想把题目改译为“恋爱天文学”,以新颖的视角让其与正文融为一体,有益于日本现代读者阅读和理解,但却与原题目毫不相干。《子夜吴歌》系六朝乐府中的吴声歌曲,相传是晋代一名叫子夜的女子创制,多写哀怨眷恋之情,分春、夏、秋、冬四季。故若将其翻译为“恋爱天文学”,则原诗中的以上背景和来源全然被抹去,也无法第一时间知晓诗的主人公为女性。此外,原诗中的“侬”带有鲜明的地域和性别特色,但译为“われ”之后也就立即变得模糊,甚至于走向了反面。
原作2:我念欢的的,子行由豫情。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
译文2:思ひ詰めては見えもする 君ゆきがてのうしろかげ おぼろめきつつ蓮さへ 花もわかぬ朝霧に[6]386
原作中,“的的”,明朗貌。“由豫”,迟疑貌。芙蓉即莲花。“见莲”谐音双关“见怜”(爱怜我,喜欢我)。女子很喜欢男子,但男子却显得比较犹豫,宛如朝雾笼罩的荷花,难以看清楚。用“见莲”双关“见怜”,把上下联衔接起来,构思巧妙,意趣横生。译文省略了主语,主人公性别没有得到明示。“思ひ詰める”偏向于理性的思考,而非感性的钟情,与原词不甚对应,词意发生了变异。最后两句只翻译出了原诗的表面意思,谐音双关无法再现,使得译诗的意境和情趣大打折扣。
从以上两个译例可以看出,由于语言的异质性,从汉语到日语,中国古典诗歌一路风尘颠簸,难免有所遗失和损伤,原诗的文化背景、情趣、意义等已经发生了削减、失真和走样。
(二)文化之旅
中国古典诗歌走进日本,带来的不仅仅是诗歌本身,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所承载的厚重的传统文化。汉诗在日本的跨文化、跨语际旅行,实质上是“两种甚至是多种文化的对抗、对话直至融合,堪称文化之旅途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这种最终的融合则往往是通过“他国化”(日本化)来实现的”[7]183。
在“汉诗和译”过程中,诗题、典故、情趣、意象等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却因读者难懂,或与日本文化相左,译者不得不进行替换、改写等“适应”处理,使其在日本读者群中产生“宾至如归”的效果。近代以来,中国诗歌在日本魅力大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训读对原诗亦步亦趋,语言和表达陈旧,不能贴近现代生活。为了克服这一缺陷,很多译者使用现代日语,大胆地进行“翻案”,也可以称之为“超译”或“豪杰译”,佐藤春夫和井伏鳟二就是其中的代表。
佐藤春夫经常将汉诗中以曲牌命名的题目,根据自己对诗歌意思的理解,进行大胆地改动,比如将上文所提到的《子夜吴歌》改为“爱情天文学”。另外,他把唐代杜秋娘的诗题《金缕衣》,改译为“ただ若き日を惜しめ”(须惜少年时)。再如,他将宋代朱淑真的诗题《愁怀二首》译为颇有日式情趣的题目“春ぞなかなかに悲しき”(春天啊,多么令人悲伤)。通过改写,虽然与原诗题目相距甚远,但“日本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原诗的主题与含义,更容易与原诗的作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8]。
除了改写题目之外,佐藤还经常改动原诗的地名、人名,使其具有日本风情。例如白居易的《洛中春感》:
原作3:莫悲金谷园中月,莫叹天津桥上春。若学多情寻往事,人间何处不伤神。
译文3:月をな泣きそ不忍に 春をな嘆きそ言問に あはれを知らば思ひ出の 何処とわかつ涙かは[9]
原诗中的金谷园、天津桥都是六朝时期洛阳的名胜,经常出现在怀古诗中,表达物是人非的慨叹。译者将其改为江户的名胜之地——泣月不忍(不忍池)、叹春言问(言问桥),便具有了日本化的文学意象。同时,他将“若学多情”意译为“若通物哀之情”,将日本人的“物哀”审美意识注入其中,原诗的感怀咏叹变成了与日本传统诗歌相同的意趣与情感。
井伏鳟二受《车尘集》的影响,创造性地翻译了中国古诗十七首,命名为《除厄诗集》。他将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都变为身边的事物,就像在吟咏身边的人和事。此外,他还把汉诗中有深厚意蕴的典故抹去,替换为自己生活中的事物。如高适的《田家春望》:
原作4:出门何所见,春色满平芜。可叹无知己,高阳一酒徒。
译文4:ウチヲデテリヤアテドモナイガ 正月キブンガドコニモミエタ トコロガ會トタイヒトモナク アサガヤアタリデオホザケノンダ[6]399
高适的诗语言质朴却气势磅礴,但井伏以片假名和汉字的书写形式,用轻巧明朗的现代语译出之后,立马变得轻松而飘逸了。“高阳酒徒”典出《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指称嗜酒而放荡不羁,但却胸怀大才,并非平庸无能的人。井伏把它换成了阿佐谷的酒亭,是他经常置酒畅谈的地方。如此一来,原诗具有深意的自喻便消失殆尽,只剩下春日出游的闲散和消遣意趣了。
(三)接受之变
文学在他国传播时,“接受者必然根据自身文化背景和时代精神的要求,对外来因素进行重新改造与重新解读和利用,一切外来文化都是被本土文化过滤后而发挥作用的”[10]。因接受者自身所携带的文化因素和审美需求,对他国文学的“过滤”和“误读”成为必要的翻译策略。
汉诗和译,既要尽量保持原诗的韵味,又要符合日本读者的口味,并且必须是“诗”,那么将其译为和歌等日本式诗歌是最为妥当的。实际上,自古以来的日本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歌译、俳译实践。他们按自己建设现代文化的需要,采来中国诗花,随心所欲地加工成和歌味、俳句味的新餐。[2]537但汉诗与和歌在信息容量、语言结构、审美情趣、表达技巧上的差异巨大,三十一音的短歌无法容纳汉诗的诸多意象、信息和内容,更无法再现汉诗韵律、对仗等美感。故译者们从汉诗中抽出最主要的情绪,省去意象和典故,译写为和歌。严格来说,这种抓住“诗心”(神韵)的做法并不属于真正的翻译,实际上是一种翻案之法,是对原诗的“过滤”和“误读”。例如,会津八一(号秋草道人)将自己阅读唐诗的独特感受,用和歌重新表达,这“既非翻译,又非创作,究竟为何物,予所欲问之也”[11]110,故暂将其题为《印象》。例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重写为和歌如下:
原作5: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译文5:うみにして なほながれゆく おほかはの かぎりもしらず くくるたかどの[12]
(大河入海流尽否,日暮高楼望无极。——高兵兵译)
显然,会津八一进行了过滤,只抽取了日暮时登楼远望,见大河入海的信息和情绪。“原诗表现的是积极向上的心态,而和歌则表现出了一种消极惆怅的心态”[3]440,可见这不仅是过滤,还是情感上的“误读”。
安藤孝行也认为唐诗翻译应该顺应日本诗歌简洁的特点,把注意力集中到原诗的趣向上,而不应该拘泥于细枝末节的词句,并用本国语的节律去取代原诗的韵律。他声援会津八一的“印象”译法,认为“翻译妙极臻于创作之域,凡是诗歌翻译,均不能不臻于此种境界”[13]17。他以唱和为主旨,将自己译为和歌的六百首作品题为《唐诗唱和集》,同秋草道人一样,不介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称其为创作或翻译皆可。如他把李白的《秋浦吟》二译为:
原作6: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译文6:いづくゆも 降っりる雪ぞ まそかがみ なげきかさねし ひとよおもほゆ[13]35
(不知是何时/下的这场雪好大/对镜连叹息/人啊这方才觉察——王晓平译)
显然,安藤只抽取了白发如雪纷纷落下的鲜明印象,用和歌捕捉形象的方式,进行了更为精炼地表达。“白发三千丈”是愁绪的极端夸张化表达,这种手法不适合于含蓄凝练、平缓叙述的和歌。译者用纷纷飘落的白雪来比喻白发,正是采用了和歌中常见的风花雪月的意象。见镜中白发那一瞬间的感觉,油然而生的惆怅,倒是和歌易于接纳的[2]566。
(四)规则之变
一国文学在他国发生最深刻的变异,便是“他国化”。即“一国文学在传播到他国后,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受之后产生的一种更为深层次的变异,这种变异主要体现在传播国文学本身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已经在根本上被他国所化,从而成为他国文学和文化的一部分”[7]193。
日本人对中国诗歌的继承和发扬,集中体现在各类灵活丰富的应用上,如根据中国诗歌意境吟唱、朗咏和歌等,其中以“断句取义”“断语取义”的方式进行歌译和俳译最为典型。他们切断原作的文脉,摘取短句或短语,吸取诗意转写为日本诗,这种做法不仅改变了汉诗的意境和情趣,更是改变了诗歌意义生成方式和文学话语表达规则,将原作彻底日本化了。
会津八一和安藤孝行都是近现代有名的歌人,他们的译诗在节奏和韵味上,都有浓厚的和歌味。会津八一对唐代李收的《幽情》译写如下:
原作7:幽人惜春暮,潭上折芳草。佳期何时还,欲寄千里道。
译文7:はるたけし きしべのをぐさ つみもちて すずろにおもふ わがとほつびと[11]109
(春意正浓时,摘取岸边的芳草。想起远方的那个人,有些许惘然。——笔者现代语译)
原诗首联描写在暮春时节折潭边芳草,引出尾联主人公对远方人的思念和盼归的情感。这是汉诗常见的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诗歌意义生成方式。由意象到意境,诗歌审美情趣逐步升华。秋草道人将其译写为31音的和歌,把暮春变成阳春,潭上改成了日本特有的望归之地——岸边,省略了主语“幽人”,后两句只说想起了远方的人,心绪略有起伏,没有具体告知所思所想的内容。如此一来,原诗明确的意义、因果关系和逻辑被消解,主人公的情感和主张变得捉摸不定,模糊不清。“简洁地叙述景物,通过各种复杂的修辞手法及深奥的语言结构,含蓄地表达作者对所遇到事物的意趣”[14],是和歌中常见的意义生成和文学话语表达方式,这种话语规则在本首译诗里得到了较为明确的体现。
安藤孝行既是歌人,也是画家,力求简洁地用和歌唱和唐诗。即便是具有浓厚哲理性的汉诗,他也会对其进行创造性翻译,只留下最具形象性、象征性的物象。如他对李白《庄周梦蝴蝶》唱和如下:
原作8: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一体更变易,万事良悠悠。乃知蓬莱水,复作清浅流。青门种瓜人,昔日东陵侯。富贵故如此,营营何以求。
译文8:周か夢 胡蝶かうつつ よしゑやしうつせみの世は 常なきものを[13]23
(不知是庄周/还是蝴蝶梦中翔/现实如蝉蜕/人世原本便无常——王晓平译)
歌人舍弃了“一体更变易,万事良悠悠”的议论和蓬莱水浅、东陵侯种瓜的典故,只取庄周梦蝶这一扑朔迷离、真幻相绞的富于动感的画面,在原歌中“蝉蜕”也可看作枕词,歌中那“是庄周呢还是蝴蝶呢”的自问似的语气,是极富日语特色的[2]568。这首极富人生哲理的诗,通过安藤的短歌化改造,尽力缩减意象之间的关系,短小凝练,但却内涵丰富,充满禅意。
除和歌外,以正冈子规为代表的近现代俳人,以“断句(语)取义”的方式吸取诗境,创作俳句,是改变汉诗文学话语规则的另一重要方式。子规的俳句中,出自唐诗名句的例子很多,尤以王维为甚。子规(1975)认为:汉诗中每句意完而具趣味者,王维之诗也……曰精微,曰有禅意,曰意在笔尖。要之,曰脱理窟。脱理窟,故每句趣味深远,故每句可译为俳句。如王维的《终南别业》中的两句译为:
原作9: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译文8:遡る夏川細く雲起きる[15]
(夏日,沿着小河逆流而上,白云起深处。——笔者现代语译)
子规将对仗的两句拆开,消除原诗“水”和“云”之间的逻辑关联,加上季语,变成了有些许禅意的俳句。再如他把王维《过香积寺》中的“古木无人径”抽取出来,译为“道細く人にも逢はず夏木立(小径不遇人,夏木郁葱葱——王晓平译)”,原句远山中古树参天,人迹罕至的苍茫深幽变成了近山林间里的清凉明快,通过截取和置换,从情趣和意义表达上都已经变为有季语、有对尘世生活纤细感受的俳句。
四、结语
汉诗曾长期受日本知识层的喜爱,但近代以来由于受西洋文化的冲击,昭和初期已面临严峻考验,五十年后的今天,已几近绝迹了。[4]210日本文人学士积累了大量的古代文学翻译经验,“然而很少有人对这些经验进行理论阐述,近代以来……,像冈田正三、森亮、加岛祥造等人的诗歌翻译业绩在业界也很少评价和研究,更不用说理论支持了,可以说,他们的摸索不免寂寥,也还很少看到后继者”[2]535。中国学者也对佐藤春夫、武部利男、会津八一等近现代日本学人“汉诗和译”的成绩作了评价和分析,但因站在对外传播的立场,故对文化层面上的翻译动因、翻译行为、翻译结果、翻译接受与影响等问题关注不足,对不忠实于原诗的“创造性叛逆”等行为和结果的总结和评价有失偏颇。汉诗和译究竟是“翻案”还是“翻译”的学理困惑就是该现状的集中体现。本论文参照比较文学变异学中的“他国化”思维,专题分析了近现代译者在语言、文化、接受和规则等方面对汉诗的继承和改造,旨在揭示文学接受的主体性、选择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挖掘和呈现近现代“汉诗和译”的内核。希望通过本研究,能为中国汉诗再次“走进”日本提供参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