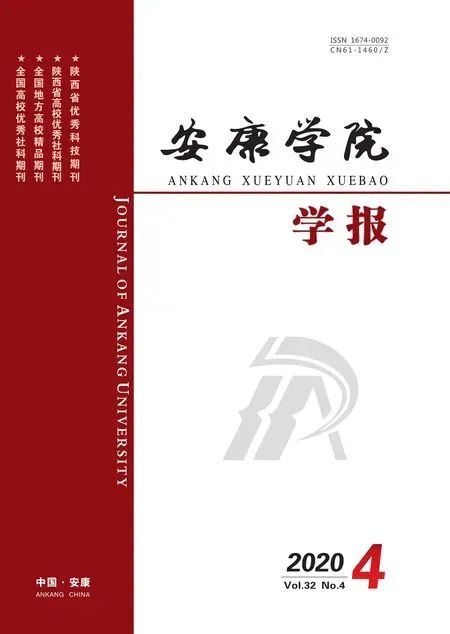梅里美中短篇小说的现代特点
——以《嘉尔曼》为例
2020-12-27邸玲
邸 玲
(安康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
《嘉尔曼》是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梅里美的中篇小说,讲述了吉卜赛女郎嘉尔曼与贵族青年唐·何塞的爱情悲剧,以震撼人心的力量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坛大家辈出,梅里美在这些作家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从创作量上来看,他并不是一位高产作家,他一生写下了二十多部中短篇小说,然而凭借着这些中短篇小说却使他跻身于法国一流作家之列。其中短篇小说兼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特点。又比同时代的作家更具有现代小说的特点。蒋承勇指出:“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处在新旧文化的交替阶段,他们即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深刻批判和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同时又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揭示人类深层的精神——心理内蕴。因此,他们的创作既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又具有文化批判的深刻性……酿就了二十世纪的现代文化基因”[1]。本文以《嘉尔曼》为研究对象,从小说的美学风格、主题内蕴及叙事技巧三个方面探讨梅里美小说所具有的现代特点。
一、美学风格:将恶纳入美学范畴
从古希腊开始,美即作为审美的标准,古希腊人的教育理想就是在美的体格中培育美的灵魂。十八世纪德国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中说:“美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2]因此,古希腊时期的绘画雕塑艺术都展现出了女性的体态之美和男性的力量之美,包括被蟒蛇缠绕的拉奥孔都极力避免表现他因痛苦而狰狞的面目。《荷马史诗》中美貌的海伦导致了特洛伊战争的爆发,特洛伊和希腊诸多著名的英雄在这场战争中丧命,但是因为海伦的美丽,特洛伊人和希腊人并没有指责她。而善是美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文学作品的美学范畴中,作家们极力颂扬和表现美与善,批判美善的对立面丑和恶。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3]的“美丑对照”原则,并在其作品《巴黎圣母院》中塑造了一位外表奇丑无比的卡西莫多,然而在他丑陋的外表之下却有着一颗至纯至善之心,因为在雨果笔下“丑”不是“美”的对立面,而是“美”的对照与衬托,因此雨果写“丑”最终也是为了颂扬美和善。
二十世纪的西方,由于非理性对理性的战胜,审丑和审恶进入了现代美学领域,成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之一。梅里美很早就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恶纳入美学范畴。他在《嘉尔曼》中为读者塑造了一位“恶之花”。嘉尔曼是一位吉卜赛女郎,在一家卷烟厂做女工,同时又充当走私集团的耳目。一次在与工厂女工发生冲突的过程中,嘉尔曼将对方打伤而被押送至监狱,押送途中她勾引了押送她的军官唐·何塞因而被放走,唐·何塞则遭受了军中严厉的处罚并被降级为普通士兵。嘉尔曼为了报答唐·何塞以身相许,唐·何塞疯狂爱上了嘉尔曼,因为嫉妒又杀死了情敌中尉,因此失去工作被迫加入了走私集团。在唐·何塞以为他可以永远得到嘉尔曼的爱情之时,他发现嘉尔曼原来有丈夫,而且她还在继续出卖色相,愤怒的唐·何塞杀了嘉尔曼的丈夫,要求嘉尔曼与他一起前往美洲,但被嘉尔曼拒绝,最终嘉尔曼死在了唐·何塞的刀下。
嘉尔曼的形象与以往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善与美的女性形象不同,她形骸放浪、杀人抢劫、走私卖淫……她的身上具有某些邪恶和残忍恐怖的特点,不受任何社会道德的约束。小说中这样描写嘉尔曼的外貌,“短的红裙子、破洞的丝袜,火红的绸带、腰肢扭动”“她的每一缺点总有一个优点作为陪衬,而这个优点在对照之下,变得格外显著”①本文所引原文均来自梅里美《嘉尔曼》,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由此可以看出嘉尔曼在作者眼中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美,“她的美是一种奇特的、野性的美”,是一种充满矛盾的个性的美。嘉尔曼的美正如波德莱尔所说:“无论人们如何喜爱由古典诗人和艺术家表达出来的普遍的美,也没有更多的理由忽视特殊的美、应时的美和风俗特色。”[4]优美和崇高的美学范式使人们将道德与审美直接联系起来,嘉尔曼身上却不具备道德因素,她轻浮放浪,唐·何塞说她“用拇指一弹,把花弹了过来,恰中了我的眉心”,利用自己的美色为走私集团充当耳目刺探消息是她惯用的手段;她残忍狡诈,设计一个又一个陷阱,夺人钱财甚至是性命,“一个女工四肢倒地,浑身是血,脸上是刀痕”。以至于对她疯狂迷恋的唐·何塞评价嘉尔曼:“如果世界上真有妖精的话,这个姑娘肯定是其中一个。”嘉尔曼尽管会让读者有不适感,但当嘉尔曼的这种恶与她对于自由的极致追求联系在一起时,带给了人们一种奇特的审美体验,即摆脱传统道德的束缚、追求个性的自由、尊崇个体的内心。
二、主题内蕴:文明与自由的对立
进入十九世纪,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社会道德成为人们生活的准则,人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渐渐丧失了精神自由。十九世纪的作家们在作品中通过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对于这种异化的担忧与反抗。在梅里美的作品中,他通过塑造个性独立、自由放浪的人物形象表达文明与自由的对立,发出反对工业文明的呼声。嘉尔曼身上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其对于自由的追求,她所追求的自由既包括精神上的自由也包括肉体上的自由。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为了“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5],要求女性必须要对男性忠贞,贞操观念成为女性道德评判的标准之一。然而嘉尔曼却无视这些道德规范,她有丈夫却依然用自己的肉体色相去引诱男人,她爱唐·何塞却不只忠于他一个人。当愤怒的唐·何塞逼迫嘉尔曼和他远走高飞时,嘉尔曼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声:“跟着你走向死亡,我愿意,但不愿意跟你一起生活”,“作为罗姆,你有权利杀死你的罗密。但嘉尔曼永远是自由的”,黑格尔说:“束缚在命运的枷锁上的人可以丧失他的生命,但是不能丧失他的自由。”[6]最终卡门死在了唐·何塞的刀下。
嘉尔曼与唐·何塞的关系就是文明与自由关系的隐喻,嘉尔曼是吉卜赛女郎,吉卜赛人大多靠卖艺、偷盗、占卜为生,长期过着流浪的生活,他们是生活在“文明”世界的边缘人,较少受到来自“文明”世界道德法律宗教的束缚,而梅里美正是通过对这些文明社会边缘人形象的塑造来表达对“文明”世界方式的反抗。嘉尔曼一再强调她是按照吉卜赛人的生活方式在生活,其实更确切地说她是按照自己的内心在生活,她说“自由就是一切,为了少坐一天牢,宁肯放火烧掉一座城市”,因而嘉尔曼被读者们称为“自由的精灵”。嘉尔曼偷盗抢劫杀人,这些行为极大地表现出对于文明世界社会法则的轻蔑,然而贵族出身的唐·何塞则是文明社会法则的遵守者与执行者,他不自觉地被嘉尔曼身上的野性神秘之美所吸引,为了嘉尔曼渎职杀人最终进入走私集团,然而唐·何塞是被迫卷入这种生活,而不像嘉尔曼那样认为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唐·何塞是一个被“文明”所浸染的“文明人”,他说“我从不相信漂亮姑娘不穿蓝裙子和没有两条小辫子挂在肩上的。”他为自己的行为而“悔恨”,所有这些充分说明文明世界的法律道德宗教观念支配着唐·何塞的思想,因此在他爱情观念中更多的是私有制社会中的强烈的占有欲,他把嘉尔曼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求嘉尔曼完全遵从他的意愿,剥夺嘉尔曼所珍视的自由,最终也彻底的失去了嘉尔曼的爱情。
嘉尔曼对待唐·何塞到底有没有爱情呢?嘉尔曼曾说:“我恨我爱过你”“你看我都没有收你的钱”,在嘉尔曼这里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决不能勉强自己的内心。最初嘉尔曼出于报答对唐·何塞以身相许,而后又被唐·何塞文雅、礼貌的风度吸引而爱上了他。唐·何塞与嘉尔曼的结合是两种异质文化的吸引,是文明与野蛮的结合。人类创造和追求文明、向往文明所带来的社会物质进步,然而文明的发展带来越来越多的束缚与限制,人的原始激情与自由在慢慢丧失。最终嘉尔曼爱上了年轻的斗牛士,年轻的斗牛士是原始生命力的象征,具有和卡门同质的生命的激情与活力,隐喻了现代人对文明的挣脱以及对淳朴自然人性回归的向往。
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社会弊病,巴尔扎克、雨果等作家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弊病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与批判,但他们的批判都是站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扎根于传统文化所发出的呼喊。十九世纪中后期,欧洲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恶性膨胀激化了社会矛盾,人类创造了文明,但文明在本质上与追求人性自由、追求自然的人相对立。作家们高举十八世纪法国作家卢梭“返回自然”的口号,从人性和自然法则出发,批判工业文明,歌颂人类的自然状态,对人的生存状态、人的本质问题进行探索。在这点上,梅里美虽然不是开创者,但却是最好的实践者,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了现代文化的特点。
三、叙事技巧:叙事聚焦视角的转换
西方文学从《荷马史诗》开始了流浪汉叙事的传统,在《嘉尔曼》中读者可以看到梅里美对于这一叙事传统的继承。小说讲述了“我”在远方异域与大盗唐·何塞萍水相逢的所见所闻,小说中有两个叙述者考古学家“我”和大盗唐·何塞,“我”虽然不是一个流浪汉,但是长期从事考古工作走南闯北,唐·何塞是大盗居无定所,因此两人的讲述呈现出流浪汉叙事的特点。然而梅里美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表现出现代小说的叙事特点。
十九世纪评论家勃兰兑斯认为梅里美圆熟的艺术表现使他高司汤达一头。和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的大多数作家一样,梅里美也喜欢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多采用叙事聚焦不断转换的现代手法。
《叙述词典》中称视角是“感知或认知的方位,被叙的情境与事件借此得以表现。被采用的视点可能是全知叙述者。其方位多变,有时无法确定,而且(总的来说)不受感性或理性的限制。或者说,视点可以位于故事事件中,或更为确切地说,寓于某一人物之中。”[7]叙事视角表示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种种复杂的关系,热内特在《叙述话语》中将小说的叙事视角分为非聚焦视角、内聚焦视角和外聚焦视角。非聚焦视角即零聚焦视角、上帝视角,叙述者可从任何角度来观察事件,甚至可以透视任何人物的内心活动;内聚焦视角指用故事中的人物的眼光进行讲述,叙述者仅说出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而外聚焦视角叙述者仅从外部客观观察人物的言行,不透视人物的内心,以冷漠的态度讲述故事,不解释不介入。而《嘉尔曼》则运用了内聚焦视角的转换的方法进行讲述。故事分为四个部分,第四部分为一篇关于吉卜赛人的研究报告,第二部分采用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由“我”讲述与大盗唐·何塞的相遇,“我”遇见了“粗壮”“阴沉”“傲慢”“拿了我的衬衫和《回忆录》”“健谈”的“对马很有研究”的唐·何塞,对他产生好奇心并被吸引;第二部分仍为“我”的叙述,讲述了“我”与波希米亚姑娘嘉尔曼的相遇,在自然状态的城镇,“我”被“头上插着一大束茉莉花”有着“醉人的清香”“皮肤光滑”“眼睛大而美”“头发粗、漆黑”的嘉尔曼偷了表,表找到了,唐·何塞入狱;第三部分叙事聚焦发生转换,“我”去狱中探望唐·何塞,由他讲述了与嘉尔曼之间的爱恨情仇的故事,这个部分讲述者变为唐·何塞,考古学家“我”由叙述者变为受述者,与读者一起倾听唐·何塞的讲述。
内聚焦视角的转换,形成了一个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内嵌式结构模式,这种结构模式源于古老的东方,而吉卜赛是“埃及”的音变,在西方人的眼中代表了神秘的东方,恰好与嘉尔曼的身份相吻合,增添了故事的悬念感,同时也增添了人物的神秘色彩。因为读者在阅读中直接面对的故事并不是作者所要讲述的故事,在表层故事中是由“我”考古学家讲述往事,而内核则是藏于故事中的故事,在双层故事网中作家给我们构建了一个厌倦工业文明,逃离工业文明、向往蛮荒的异国风情的考古学家偶遇江洋大盗和吉卜赛女郎的故事,而故事中真正震撼人心的则是为了追寻自由宁愿走向死亡的波希米亚女郎嘉尔曼的故事。这种内聚焦视角的转换构成了一个结构复杂的故事形态。
从创作的发生看,任何叙述的背后都是作者本人在叙述。第一人称的叙述中必然代表了作者的某种思想倾向、喜好态度以及个性特征。《嘉尔曼》中主讲述者“我”的身份是考古学家,也同样是梅里美多部作品中的讲述者,之所以安排这样一个人物作为作品的讲述者,首先与梅里美本人的身份相一致。梅里美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对待政治若即若离的态度形成了梅里美逃避现实的性格特点,而考古学家即是与古代残存遗迹打交道的人文科学家,与现实生活及政治相疏离,而对古代遗风及域外风情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长期的严密精确的研究工作造就了其严谨的态度,使“我”认为事实高于一切,《嘉尔曼》虽然讲述了一个浪漫而悲情的带有传奇性色彩爱情故事,但从整体上看来前三部分内容似乎都为了完成第四部分的研究报告,这样就增加了所讲述故事的真实性。同时因为“我”又是故事中的经历人,人物本身就被戏剧化了,突显了作品现实性与浪漫色彩的结合。
整个故事叙事的聚焦都在吉卜赛女郎嘉尔曼身上,嘉尔曼放荡不羁、抢劫偷盗,置文明社会的道德与法律于不顾。然而在考古学家“我”的讲述中呈现的是一个充满了“野性之美”的嘉尔曼,很明显由于“我”不自觉地被嘉尔曼所吸引,所以随她到了住处“心甘情愿”地被偷了表,而后来“我”到狱中探望唐·何塞也同时探听有关嘉尔曼消息。在第三部分唐·何塞的讲述中嘉尔曼是一个放荡的、邪恶的同时追求自由的吉卜赛女郎,唐·何塞在不知不觉中被嘉尔曼吸引,为了爱情放弃了一切。可见,无论是唐·何塞还是“我”其实都被嘉尔曼所吸引,在叙事视角的变换中不变的是嘉尔曼身上所散发的独特魅力,使“我”和唐·何塞为之着迷。正是通过这种视角的转移,避免了全知全能视角中不可避免的道德评价,也避免了外聚焦叙事的冷峻,读者在两位叙述者的讲述中随着讲述者一起在嘉尔曼的独特魅力之中沦陷,被她对自由追求的炽热所吸引。梅里美通过叙事聚焦视角的转换把一个“文明世界”的边缘人塑造得充满了魅力,颠覆了传统价值判断,丰富了世界文学画廊的人物形象。
二十世纪的小说创作在叙事技巧上进行了革新,在叙事视角等方面抛弃了传统小说的单一性,梅里美的小说大多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同时进行了叙事聚焦视角的转换,具有20世纪现代小说的特点。
苏联文艺评论家卢那察尔斯基曾评价:“梅里美是萧索时期一朵很典型同时又很独特的奇花。”[5]确实如此,梅里美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无论是在美学风格的开创方面、主题内蕴的开掘方面,还是在叙事技巧的革新方面,都具有二十世纪现代小说的部分特征,这是他能跻身于十九法国一流作家之列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