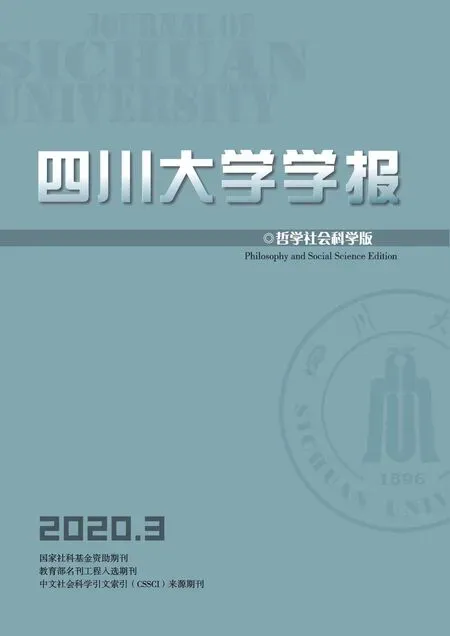国家权力、银行资本与民国时期农村合作社的异化
2020-12-26成功伟
成功伟
“建立一个合理化的、能对社会全体民众进行有效动员与监控的政府或政权体系”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目标。(1)Charles Tilly,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Foreword.20世纪上半叶,国民政府为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而进行“国家政权建设”,在整合乡村资源和重构乡村社会秩序的同时,国家权力也不断地向乡村扩张。“国家政权建设”是影响乡村社会变迁的基本动因,中国乡村社会呈现的种种特性也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后果。(2)张静:《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问题与回顾》,《开放时代》2001年第9期,第6页。学界时常以“国家-乡村”为视角来探析“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的各种乡村社会问题,其中不乏以农村合作运动为研究对象的优秀成果。(3)参见赵泉民:《合作运动与国家力量的扩张——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乡村合作运动中政府行为为中心》,《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第45-49页;魏本权:《20世纪上半叶的农村合作化——以民国江西农村合作运动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2005年第4期,第88-96页;赵泉民:《政府意志: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合作运动价值取向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90-99页;刘纪荣:《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近代农村合作运动——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为中心的历史考察》,《中国农村观察》2008年第2期,第28-39页;赵泉民:《“经纪”体制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绩效——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社会权力格局对合作社影响分析》,《江海学刊》2009年第2期,第151-158页;成功伟:《“国家权力—乡村社会”视野下的四川农村合作运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9期,第215-220页。然而,从这一视角去观察农村合作运动时却往往会忽视这场运动中的另一个关键因素——银行资本。正如罗正纲所言:“合作运动之萌芽、生长及发展,并未经自发的过程,全出于政治势力的孵育和金融资本的诱迫。”(4)罗正纲:《中国农村合作运动的自主路线》,《新中华杂志》1937年第5卷第13期,第87页。与政治因素相比,资本对于催生和催化这场“地方自治运动”所起到的作用同样十分重要。银行资本下乡不仅会改变乡村原有的权力格局和社会资源,也能使乡村村民自治虚化,甚至出现所谓“富人治村”的现象。(5)张晓欢:《资本下乡及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与对策》,《调查研究报告》2019年第48期,http:∥www.drc.gov.cn/n/20190729/1-224-2899069.htm,2020年4月22日。当近代新兴的金融业投资乡村后,其资金随即转化为农村合作社的农贷资金,从而对农村经济和乡村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面对农业金融枯竭、农村经济破产的衰败景象,国家、银行、农村合作社及农民在“重建农村”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并在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迁过程中留下深浅不一的历史印迹。农村合作社是国家、银行与农民的一个交集点,可以较好地反映出权力、资本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并能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民国时期的农村社会打开窗口。国家权力的渗透与银行资本的诱惑最终导致了民国时期农村合作社的“异化”,出现了合作社舍“质”逐“量”,管理者腐化及农民利益遭受侵蚀等现象。
一、国家权力与农村合作运动
国家的控制能力是国家权力的一种体现,包括国家机构和人员下沉、国家机构配置资源以实现特定目的和管理民众日常行为的能力,也包括国家制定的规则取代公众自己行为倾向或其他组织规定的社会行为的能力。(6)乔尔·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页。迈克尔·曼则认为,国家权力包括国家的专制权力和国家的基础权力。参见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9页。本文中的国家权力主要是指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即国家的控制能力。作为“地方自治运动”的农村合作运动正是国民政府行使国家权力而对乡村资源进行整合,以实现管理民众和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的一项运动。
五四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西方合作主义,并在上海等地创建了合作主义社团。随着中国农村问题的日渐尖锐化,合作主义者对中国社会的关注焦点逐渐从城市转向农村,并在河北定县、山东邹平等地建设了一批农村信用合作社。但是,中国的合作事业的发展并不像推行者最初所设想的那样,按照西方合作运动“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在中国形成“燎原之势”,而“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点缀品而已”。(7)陈岩松:《中华合作事业发展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57页。这种民间自发的合作事业常常被诟病为“城里人到乡下去替农民想办法”,“这般人跑到农村去,不会探寻到农村的真正问题,自然就说不上想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8)汪国舆:《乡村建设运动应该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建设周讯》1937年第1卷第3期,第10页。著名合作经济学家石德兰(C. F. Strickland)对中国农村合作事业进行考察后也有同感。他认为中国最热心的合作主义者都集中在上海等大城市,这是中国农村合作事业的一种危机。“这些城里人出于爱国的原因,可能会鼓励这场农村合作运动,但是他们却不会为了合作事业而进村”。(9)C. F. Strickland,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the Eas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1, No.6, 1932, p.816.可见,农村合作事业仅靠“门外汉”的一腔热忱难以成就一番事业。
1928年,国民政府开始推行农村合作运动,原本由“民间自发”的农村合作事业从此变成一项“国家运动”,甚至被认为是“实行地方自治的最重要方法之一”。(10)朱朴:《评合作运动》,华南丛书社,1931年,第62-66页。因不断的内战和自然灾害,中国农村人口锐减,“面对这种几乎无望的局面,农村合作运动不可能是自下而上的一种运动,而只能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政策来推行,……一个稳定和有效的政府可以通过推行一种农村合作的国家政策来帮助、教育和资助农民”。(11)H. D. Fong,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China,”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No.30, 1934, p.544.农村合作事业从“民办”转变为“官办”,一方面是因为合作制度在经济基础和社会服务方面可以为地方自治建设奠定较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合作主义”本身所呈现出的那种“符合中国的社会组织和人民的统治和生活理论的哲学”可能更加符合国民政府的需要。(12)J. B. Tayler, “Potentialities of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China,”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21, 1937, p.20.从“民间自发”变为“国家运动”后,农村合作事业被纳入国民政府“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体系内,成为“农村重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蒋介石看来,没有合作事业就没有现代的国家和现代的民族;合作事业不但可以解决民生问题,也可以造就健全的现代社会。(13)李敬民:《总裁之合作思想》,《中国合作》1941年第1卷第7期,第4-7页。可以说,农村合作运动兼具地方自治与农村重建等多重功能,是国家权力作用于乡村社会的一种体现。
在国共矛盾较为突出的时候,农村合作运动甚至成为国民党对抗共产党力量的一种工具。国民政府确定推行农村合作运动之时,正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而进行的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从某种程度上讲,民国政府正是以农村合作运动“复兴农村”之名行打击共产党力量之实。1930年底,国民党集中重兵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的同时,陆续颁行了《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合作预备社章程》和《剿匪区内各省合作社条例》,并开始在这些省份迅速组建农村合作社。这些行动表明,国民政府主要依靠合作社来进行收复地区的农村重建。(14)J. C. M., “Chinese Government Fosters Cooperatives,” Far Eastern Survey, Vol.5, No.11, 1936, p.113.在这种背景下,鄂豫皖赣等省的农村合作社数量急速增长,体现了国民政府在这些地方利用合作社进行“农村善后”的政治和军事意图。以安徽省为例,从1932到1933年,该省的农村合作社从16个增至1742个,举办合作社的县数也由5县增至24县。(15)骆耕漠:《信用合作事业与中国农村金融》,《中国农村》1934年第1卷第2期,第3页。弗雷德里克·费尔德(Frederick V. Field)指出,1931—1932年,国民政府意识到要打击共产党力量就需要解决农村经济崩溃的问题。也就是从那时起,国民政府对共产党阵地的攻击变成了政治、社会、经济和军事行动的结合,而不仅仅是军事行动。他认为“国民政府农村重建运动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对抗共产主义这一特殊问题决定的”。(16)Frederick V. Field, “The Call to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Far Eastern Survey, Vol.5, No.24, 1936, p.256.川政统一后,鄂豫皖赣诸省农村合作社的经验便推广至四川通江、南江、巴中等县,并以农村救济的名义组建了农村合作预备社1371个,社员共计109737人。(17)《民国二十六年度四川省合作金融年鉴》,四川省合作金库印行,1938年,第195页。但是,国民政府在这些地区所进行的农村合作社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农民的利益诉求,例如其在江西省农村合作运动中所执行的政策就与共产党“联合穷人来打倒富人”的政策直接相反。(18)G. E. Taylor, “Reconstruction after Revolution: Kiangsi Province and the Chinese Nation,” Pacific Affairs, Vol.8, No.3, 1935, p.309.
抗战时期,尽管沦陷区的农村合作事业基本停滞,但全国合作社的数量却持续增长。1936年全国合作社数量为37318个,1945年增至172053个。(19)《中国合作事业》,行政院新闻局印行,1948年,第26-27页。1940年8月,为了配合新县制的推行,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合作社组织大纲》。为了把县各级合作社建设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结构,国民政府开始对原有的农村合作社进行改组,试图建成由保合作社、乡(镇)合作社和县联合社组成的三级合作组织系统。(20)《现行合作法规汇编》,社会部合作事业管理局印行,1942年,第38-39页。到1948年10月,全国共建成县联合社3253个,乡镇合作社16523个,保合作社80511个。(21)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3辑,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85年,第469、473页。《县各级合作社组织大纲》的实施表明,国民政府开始将农村合作运动融入新县制政治治理体系,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合一”的具体表现。(22)熊在渭:《新县制与合作》,《中国合作》1940年第1卷第4期,第7页。在新县制下,各地为了实现“每保一社,每户一社员”的建设目标,农民加入合作社成为一种政府强制性的要求,社员也只有在合作社与他社合并、合作社破产或者政府强制性解散的情况下才能退社,(23)《现行合作法规汇编》,社会部合作事业管理局印行,1942年,第38-42页。完全违背了“自愿入社和退社自由”的合作社组织原则。吉登斯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基础就是国家对社会的全面监控,其目标是要造就一个边界明确、控制严密、国家行政力量全面渗透、大众文化取代传统的社会。(24)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46-147页。“每保一社,每户一社员”是国民政府强化对民众监管力度的一种体现,也是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下行趋势的一种反映。对国民政府而言,“用合作方式组织民众,比任何方式来得高明,来得永久”。(25)侯哲葊:《论中国之合作运动》,《合作与农村》1936年第1期,第2页。
国民政府加快推进新县制农村合作社建设的背后,一方面是抗战时期发展农村经济以保障军民基本供给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农村合作社既可以作为组织和监管民众的组织,同时也是国家权力下沉过程中控制地方势力的一种有效方式。休伯特·弗雷恩(Hubert Freyn)认为,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偏向性地向四川省提供农贷资金的措施实际上并非完全出于经济上的考量,而是一种政治上的策略。(26)Hubert Freyn, Free China's New Deal,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3, p.104.在新县制体系下,“国民党的代表们正在做有效的工作,确保已经组织好的县政府与执政党的计划一致”。(27)J. Stewart Burgess, “Reviewed Work: Free China's New Deal,”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3, No.3, 1944, p.278.通过合作社,国民政府控制乡村社会和整合乡村资源的力度越来越大,地方合作运动的自主性逐步丧失。国民政府在加强县级政府力量的同时,省级政府的势力则被削弱。因此,缓解农村贫困仅是合作运动的附带功能,其主要还是一个政治战略手段。(28)John Fitzgerald, “Warlords, Bullies, and State Building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Guangdong Cooperative Movement, 1932-1936,” Modern China, Vol.23, No.4, 1997, p.451.
二、银行资本与合作社农贷
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农村和城市的金融发展极不平衡。农村资金的极度匮乏与都市金融泡沫式的“繁荣”所形成的“虚像和倒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方面现金充斥,无正当生产用途,以至群鹜于投机事业,造成都市中虚有其表的繁荣;在另一方面,则现金极端缺乏,使农村一切经济流通,限于死滞的状态”。(29)碧笙:《典当公营与农村金融》,《西北春秋》1934年第11期,第8页。农村经济的崩溃几乎是举国共识。究其原因,“与其说是由于人口过剩或土壤质量差,不如说是由于缺乏农业资本”。(30)Leonard Shih-lien Hsu, “The Sociological Movement in China,” Pacific Affairs, Vol.4, No.4, 1931, pp.300-301.农村缺乏廉价和充足的信贷是限制中国农业生产和农村改善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导致了中国农村普遍的破产。(31)Kate Mitchell,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of the Nanking Government,” Far Eastern Survey, Vol.5, No.14, 1936, p.139.
面对困境,“资金归农”被认为是一剂既能化解城市资金泡沫又可以充实农村金融的双效良药,快速引起了银行业的积极响应,因为这些银行“都急于为因国家不稳定而闲置的资金在农村地区找到一个出口”。(32)Tayler, “Potentialities of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China,” p.9.时人就指出,“金融业既丧失过去的全部优厚利益的营业,在此日暮途穷的时候,也就不得不另找出路,而喊出‘资金归农’来了”。(33)姜筱宁:《农本局能救济农村吗?》,《生活知识》(上海)1936年第2卷第7期,第362-363页。可见,银行投资的方向从城市转向农村,既是资本利益驱动的结果,也是其日暮途穷时的一种必然选择。一方面,银行业普遍意识到中国农村经济即将解体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对“农村复兴”应该承担不可回避的责任。(34)Leonard T. K. Wu, “Merchant Capital and Usury Capital in Rural China,” Far Eastern Survey, Vol.5, No.7, 1936, p.63.毫无疑问,银行业对整个中国农村经济的控制力正在增强,资本下乡所带来的重要后果虽然尚未形成,但是可以预测。(35)George E. Taylor, “The Powers and the Unity of China,” Pacific Affairs, Vol.9, No.4, 1936, p.540.
作为“资金归农”的最佳媒介,农村信用合作社“能够有效地扭转资金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工业和贸易且再也不能回到农村的趋势”。(36)Y. S. Djang, “Credit Co-operatives in 1,000 Villages,”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15, 1931, p.163.推行农村合作事业也因此被认为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关键。“如果贷款能够扩展到合作信用社,由其所有成员共同承担若干责任,由其监督向个别成员发放和收取贷款,则管理成本可以保持低廉,借贷利率会大大降低。最终,这些信用社可以通过联合进行统一协调,整体则由中央银行控制。因此,最终可以形成一个国家的农业信用体系”。(37)Walter H. Mallory, “Rural Cooperative Credit in Chin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45, No.3, 1931, p.486.章元善则认为农村合作事业将带来农业与金融业的“双赢”,“商业银行通过合作社为农业提供资金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迹象,这一举动充满了可能性。它不仅使农业与工业、贸易处于同一个立足点,还满足了农业的长期需求,农业肯定会从中获益。农村合作事业还为中国的银行业开辟了一个巨大的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此外,政府当局对农村合作事业也越来越感兴趣,这是另一个好兆头,并带来了新的希望”。(38)Djang, “Credit Co-operatives in 1,000 Villages,” p.169.但是,并非所有人都看好中国正在兴起的这场农村运动。早在1931年,沃尔特·马洛里(Walter H. Mallory)就指出,尽管可以预计中国的农村合作运动将会得到更快的发展,各省政府也都对农村合作运动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状况,中国的农村合作运动几乎没有永久发展的指望”。(39)Walter H. Mallory, “Rural Cooperative Credit in China,” p.497.
要复兴农村,“必须迅速采取人为的方法使集中都市中的农村资金,复归农村不可”。(40)朱熹农:《十年来的中国农业》,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抗战十年前之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209页。这种“人为的方法”就必须依靠政府的推行。1934—1938年,国民政府陆续颁布了《储蓄银行法》《中中交农内地联合贴放办法》《各省市办理合作贷款要点》《战时合作农贷调整办法》《扩大农村贷款范围办法》等法令。这些法令成为银行资本下乡的助推器,在谋求农业资金流通的同时也起到了监督和规范农村合作贷款的作用。四联总处统计数据显示,1937年,全国合作贷款数额为2705余万元,到1947年6月已经增长至354亿元。在银行资金的刺激下,中国农村合作社数量和社员数量也急剧增加。据统计,1932年,中国仅有农村合作社3978个,到1947年,合作社数量已经增长至167387个;而合作社社员人数也从1937年的310余万人增长至1947年的2290余万人。(41)《中国合作事业》,第46-47、26-29页。合作社数量及社员人数的增加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银行贷款是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获取银行贷款可能是许多农民加入合作社的唯一动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民国时期的农村信用合作社通常又被称为“借贷社”。(42)Fong,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China,” p.542.
银行资本既为复兴农村带来了希望,同时也隐藏着危机。中国农村合作运动的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政府依赖农村合作社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弱点之一”。(43)Frederick V. Field, “Chinese Reconstruction in Practice,” Far Eastern Survey, Vol.5, No.25, 1936, p.268.由于国民政府的农村金融建设缺乏长期和系统规划,银行业在农村的自由投资最终演变为“农贷割据”。“银行漫无限制的自由放款,则于较富之农村必竞相割据,而于较贫之农村则又相率规避,其结果易使前者滥用贷款,而后者偏枯向隅,失其调协普遍之旨”。(44)李景汉:《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合作问题》,《东方杂志》1936年第33卷第7期,第18页。“国家银行→合作金库→合作社→社员”的合作农贷模式成为银行资本转化为农贷资金的主要途径。到1940年,全国已经建立省级合作金库6个,县级合作金库373个。(45)郑厚博:《中国合作金融之检讨》,《合作事业》1941年第3卷第1期,第104页。随着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合作金库所在县份自然成为各大金融机构的农贷区域。以四川为例,1940年,中国农民银行在川的农贷区域为53县,中国银行16县,交通银行10县,中央信托局5县,农本局37县。(46)成功伟:《从“农贷割据”到“农贷统一”——民国时期四川省农贷格局的演变(1935—1942)》,《四川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41页。四川省这种由于银行间无序竞争和摩擦所形成的农村合作贷款局面被认为是“合作金融防区制”。(47)伍玉璋:《贫血病的四川合作金融诊断书》,《新新新闻每旬增刊》1941年第3卷第19期,第5页。像中国这样由银行业参与的农村合作仅仅是一种“名义上的合作”,不但银行贷款会造成特定区域某种程度的垄断,而且银行之间的竞争也会造成合作社的组织紊乱,甚至导致财务危机。(48)Tayler, “Potentialities of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China,” p.9.为了资金安全和利润回报,银行的投资也总是倾向于相对富裕的农村。因此,银行业极有可能“最终将控制权扩张到合作社成员的最佳利益以外”。(49)M., “Chinese Government Fosters Cooperatives,” p.113.事实证明农村合作运动远远不能解决农村信贷的根本问题,“广大农民对经济援助的需求仍然非常普遍和迫切,需要比迄今为止更大更有效的组织”。(50)Cheng Ch'eng-K'un, “Regionalism in China's Post War Reconstruction,” Social Forces, Vol.22, No.1, 1943, pp.13-14.
三、合作社建设舍“质”逐“量”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然农村合作运动被纳入“地方自治”范围,但全国性的合作行政管理系统却迟迟未能建立,合作法规也尚待颁行,各地合作运动仍然无章可循,发展缓慢。1934年,中国22个省中只有2.6%的农村贷款由合作社提供,这对南京国民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许多人担心农村破产的速度会比合作运动的推行速度更快。(51)M., “Chinese Government Fosters Cooperatives,” p.113.这种赛跑式的思维促使国民政府以“更快速度”颁制了合作运动法令并建立了相关的管理机关。1934年3月的《合作社法》和1935年8月的《合作社法施行细则》不仅为农村合作社的组建和运行提供了法律依据,也表明国民政府正在着力加强对农村合作运动的监管力度。1935年5月,国民政府于实业部下设立合作司作为全国农村合作运动的行政管理机关,随后,各省(市)农村合作委员会和县合作指导室也相继成立。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合作行政机构的成立使农村合作政策在乡村迅速落实成为可能。“南京国民政府和一些省政府开始越来越多地将合作社视作解决当前严重的农村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几个主要省份中,合作社的数量和社员数量都在快速增长”。(52)M., “Chinese Government Fosters Cooperatives,” p.112.到1936年底,全国共建立农村合作社3.7万个,数量比上年增加50%;社员164.4万人,比上年增加60%。(53)Chih Meng, “Some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199, 1938, pp.236-237.
农村合作社数量及社员数量激增的背后是合作社“量”与“质”的失衡。各地在组建农村合作社的过程中大多未能兼顾效率与效益,往往片面追求数量与速度,而忽略了合作社质量。“合作社量的发展,已成为必然的趋势。如果是适应时代需要的量的发展,那么,质的健全,往往会跟着时代需要而推进的。我们尽管放心侧重量的发展来求质的健全吧”!(54)四川省农村合作委员会编:《工作周讯》,1936年第2期,第1页。上述四川省农村合作委员会“高速”建设合作社的口号,正是当时全国农村合作运动以“量”求“质”的一种反映。事实证明,以“量”求“质”只是合作主管机关的美好幻想而已,其结果最终只是舍“质”逐“量”而已。
由于舍“质”逐“量”,各地在推行合作运动过程中往往不会重视合作教育。而“如果没有健全的组织和充分的教育作为基础,合作运动就会处于过于狂热发展的危险之中”。(55)M. S. F., “China's Cooperative Movement Beset by Obstacles,” Far Eastern Survey, Vol.5, No.19, 1936, p.206.健全的农村合作社必须要通过合作教育培训出一批合格的合作指导人员,并使广大合作社社员具备一定程度的合作知识。正如秦亦文所言:“合作指导人员,必须具有合作信仰与各种指导技术,其信仰的陶冶与技术的养成,是靠合作教育的;……健全的社员,须具有合作信仰、组织能力及优良品性、合作道德,这种健全社员的培养,是靠教育的。”(56)秦亦文:《县各级教育与合作教育的配合》,《合作事业》1944年第6卷第3-4期,第14-15页。由于片面追求速度,各地政府并不是在合作社建立之前对合作社指导员或农民进行广泛而充分的合作教育,而是在农民尚未真正做好准备之前,就急于组建农村合作社了。“虽然这些组织者也接受过短期培训,但是由于教员自己往往也是经验不足,由此培训出来的人员也质量较差”。(57)Tayler, “Potentialities of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China,” p.9.江西省农村合作运动就出现合作指导人员缺乏训练、组织者经验明显不足的现象。(58)Taylor, “Reconstruction after Revolution,” p.308.由于缺乏教育,农村合作社社员对“合作”的认识也严重不足。尽管农村中“合作社”这个名称几乎“户知人晓”,但是大部分农民却只知道“借”字而不明了“合”字。(59)周耀平:《四川省合作金库视察报告》,《农本》1939年第30期,第19页。1935年浙江省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034个合作社中,只有10%的合作社社员懂得合作原则,其余社员对“合作”要么是误解或模糊地理解,要么是参与而不理解。而“只要农民自己不具备必要的知识,不能主动组织起来,这个运动一定是软弱无力的”。(60)M., “Chinese Government Fosters Cooperatives,” p.113.
合作指导人员不仅专业知识和指导技能欠缺,而且人数也较少。合作指导员的业务区域通常会涵盖100个农村合作社,农贷视察员的业务区域甚至多达1000个合作社。合作指导员或农贷视察员往往会因为区域范围广、合作社数量多而无法进行充分的监督和指导。石德兰把这种情况归结于合作社数量的快速发展以及合作管理机关对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价值的不重视。(61)C. F. Strickland, “The Co-operative Society as an Instru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No.37, 1938, pp.751-752.中国的农村合作运动舍“质”逐“量”的后果便是农村合作社弊端丛生,普遍存在挪用借款、土劣包办、借公营私、私派捐款、冒名顶替、社员吸食鸦片、信用缺失等问题。(62)《中国农民银行成都支行、四川省名山县合作金库关于信用社贷款、办法情形、催收代收款的函、代电》,第88全宗,第208卷,四川省档案馆藏。
四、银行资本对农民利益的侵蚀
1931年,时任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的章元善对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充满期待。他认为,如果中国成功推广农村信用合作社,其对农村传统高利贷的削弱将会立竿见影。(63)Djang, “Credit Co-operatives in 1,000 Villages,” p.162.然而,在银行资本催生下的农村合作社与章元善的预想并非一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6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6页。资金安全与投资收益是银行资本下乡考虑的首要因素,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将让步于其逐利性。民国时期的资本下乡是经济萧条时期银行业发展不得已的一种选择。银行对于投资利润的追求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会忽视农民的实际需求和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甚至侵蚀农民利益。1936年,中国半数以上的合作社是由政府组织,40%以上的合作社得到银行的资助,农村信用社占合作社总数的75.5%。通过这些信用合作社,农民极有可能惨遭剥削。(65)Field, “Chinese Reconstruction in Practice,” p.268.
一方面,合作农贷在抑制传统高利贷方面起到的作用有限。政府推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与农村传统的旧式高利贷争夺金融借贷市场,依靠新式的银行贷款来削弱传统乡村高利贷的势力。农村合作社甚至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护小农免受放款人和中间人剥削,并组织他们进行互助和集体行动的唯一方法”。(66)R. H. Tawney, 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32, p.85.然而,合作农贷对传统乡村高利贷的冲击作用实在有限。1934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对22省2268个村庄的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借款中来自高利贷和商业资本的部分占借款总额的95%,而来自现代金融机构的部分仅占5%。这份报告数据主要来自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最活跃的农村地区,就全国范围而言,银行贷款的比例可能更低。因此,“毫不夸张地说,高利贷和商业资本仍然是农村借贷的唯一来源”。与占主导地位的、根深蒂固的农村高利贷和商业资本相比,现代农村信贷的少数例子实则“相当不重要,而且数量也微不足道”。(67)Wu, “Merchant Capital and Usury Capital in Rural China,” pp.63-64.虽然政府早已启动“农村重建”工作,然而到1936年时,所谓“农村重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仅是一个“常用词”而已,而不是现实,农村信贷等问题仍然基本未被触及。(68)Mitchell,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of the Nanking Government,” p.139.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虽然加大了合作农贷的推行力度,但是乡村中的专业放债人、店主和地主仍然是小农的主要贷款来源。“农民作为一个整体是否能够因其作为债务人的地位而受益匪浅,值得怀疑”。(69)Guenther Stein and W. L. H., “China's Inflation Menace,” Far Eastern Survey, Vol.11, No.11, 1942, p.125.国民政府通过农村合作贷款来削弱传统乡村高利贷的努力在中国很多省份明显是失败的。
另一方面,原本肩负打击农村传统高利贷使命的银行资本一旦进入乡村成为合作农贷时,就极可能变异成为一种新型的“高利贷”。陈翰笙认为,在农村合作运动成为银行的投资领域后,外号叫作“收债会”的农村合作社只是一个“合伙高利贷机构”,其实质是“集体的高利贷代替了个人的高利贷”。(70)Chen Han-Seng, “Cooperatives as a Panacea for China's Ills,” Far Eastern Survey, Vol.6, No.7, 1937, p.76.虽然合作农贷的利率明显低于传统的乡村高利贷,(71)卜凯在《四川省农业调查》中指出,农民的借款主要来自合作社和乡村中的商人、地主及其他农民,其中来自合作社的借款利率最低,为月息12.1%,而其他借款利率最高则达到23.5%,是合作社利率的两倍。参见S. Van Valkenburg, “Reviewed Work: An Agricultural Survey of Szechwan Province, China,”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3, No.2, 1944, p.181.但是仍然远远高于农业的生产利润并超出了农民的还贷能力。1927年,中国农场借款的平均年利率为36%,而当年中国农场的平均投资收益率仅为9.4%。1933年,广西、河北和江苏三地农民的经济状况调查同样说明了农业投资与收益的不平衡与困境。(72)陈晖:《合作事业对于中国农村金融的影响》,《教育与民众》1936年第8卷第4期,第638-640页。陈翰笙指出:“就算合作社所负担的利率确实是月息1.0%~1.5%,即使是在中国,它肯定也仍然属于高利贷。这一利率折为年利率达到了10%,而农业投资普遍的收益率不足总收入的5%~6%,前者远远高于后者。”(73)Chen, “Cooperatives as a Panacea for China's Ills,” p.75.可见,从利率角度讲,借钱用于农业生产就意味着亏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农民宁愿继续遵循不良的耕作方式,也不愿借钱用于农业生产,这并非是因为农民缺乏相关知识和技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无法以合理的成本获得足够的信贷。(74)Paul C. Hsu, “Rural Credit in China,”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1930 Conference, August 18-29, 1930, Ithaca, New York, p.1007.长期致力于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的卜凯认为,“在中国,以合理的利率来为农民提供农业信贷的问题要比农业租佃问题显得更为紧迫,……只要有足够的信贷来满足农民的需求,利率就会下降”。(75)J. Lossing Buck, “Fact and Theory about China's Land,” Foreign Affairs, Vol.28, No.1, 1949, p.97.事实上,受到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尽管农贷数额增加,农贷利率也在大幅上涨。1940年合作农贷利率为月息1分2厘,1945年时已经涨到了月息3分9厘。(76)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349页;周春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3页。
正是在银行资本对投资利润的追逐下,合作农贷变异成为一种“集体的高利贷”,农民的利益遭受侵蚀。弗雷恩认为,尽管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农贷利息要比传统的私人借贷低得多,但是信用贷款并没有像政府所设想的那样履行其职能,贫困农民并没有从中受益。(77)Freyn, Free China's New Deal, p.106.李景汉也指出:“若各银行徒以营利为目标而忽于救济农村之旨趣,则与原来高利贷之性质相类,不过昔日受压迫于土劣盘剥者,移转于银行之下而已。此外巧立名目,滥行放款者,亦在所不免。”(78)李景汉:《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合作问题》,《东方杂志》1936年第33卷第7期,第18页。在实践中,并不是最需要农贷资金的人,而是那些最有资金安全保障的人获得了贷款。这种银行农贷制度,阻碍了农贷对于一部分农业人口的资金支持,则这部分农业人口在农业经济困难的时期必须去依靠昂贵的民间个人信贷。(79)Freyn, Free China's Dew Deal, p.105.
五、权力、资本与合作社管理者的“痞化”
从农村合作运动的角度看,国民政府“重建农村”在经济上的动因就是要调剂农村金融并打破传统放债人、商人和农村精英的垄断。因此,推广农村合作社便成了政府削弱传统乡村势力的一种尝试。甚至在农村合作运动的官方表述中,代表乡村势力的“地方恶霸和土豪劣绅”的危害要比农村贫困的危害还要大得多。(80)Fitzgerald, “Warlords, Bullies, and State Building in Nationalist China,” p.421.费尔德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缺乏“专业的放债人”,唯一能给农民提供资金的是那些代表传统势力的地主、商人、官员和士绅。然而,“这些地主、商人和官员在省政府,甚至在中央政府中都有很强的代表性,他们自然倾向于捍卫自己的利益”。(81)Field, “Chinese Reconstruction in Practice,” p.268.因此,国民政府最初在推行农村合作运动时遭到地方乡绅及传统放债人的抵制也就不足为奇了。(82)F., “China's Cooperative Movement Beset by Obstacles,” p.206.山西省的农村合作运动便是由于地方士绅和传统放债人的反对而失败。(83)Donald G. Gillin, “China's First Five-Year Plan: Industrialization under the Warlords as Reflected in the Policies of Yen Hsi-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30-1937,”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4, No.2,1965, p.257.如何应对这些传统的地方势力显然是农村合作运动必须要正视的问题。
近代以来,地方乡绅等传统势力虽然在激变中遭受重大冲击,但是并没有发生裂变或消逝,呈现出极强的柔韧性与延展性。国民政府与各大银行逐渐意识到,要消除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阻力,仅仅依靠下层民众依然是困难重重,还必须要笼络一批依然保持着声望、权威与地位的乡村领袖。四川新津县合作金库调查员许兆鹄在其报告中曾指出,要顺利推行合作农贷有赖于地方士绅的支持,“新邑地方情形,颇为复杂;地方士绅、旧有势力根深蒂固;或有政令所不能见效之势,经士绅一言,即可迎刃而解者”。1941年5月,新津县乡绅苟荣山、张新垣等集资创设的县银行开业时,该县合作金库受邀出席开业典礼并备礼前往庆贺,“以备将来追收各社贷款及治安方面或有借重两绅协助之处也”。(84)《新都、温江、绵阳等县及合作金库调查报告、表及农民银行成都支行的函》,第77全宗,第131卷,四川省档案馆藏。
面对传统地方势力,农村合作指导人员在推广农村合作事业时往往持妥协态度。地方势力逐渐由最初的被打击者转变为农村合作运动联合甚至依靠的对象。民国时期,由于合作指导人员少且薪酬低,他们往往不愿意驻乡对合作社进行实地指导,而是乐于将合作社事务交由保甲长来办理。因此,农村合作社“大多未脱离保甲之政治组织而独立”,“在农民之认识中,能分别保甲与合作社为二事者,恐反属例外”。(85)周耀平:《四川省合作金库视察报告》,《农本》1939年第30期,第19页。1940年,《县各级合作社组织大纲》促进了“旧”的保甲制度与“新”的农村合作社的进一步融合,保甲长成为控制农村合作社的不二人选。通过农村合作社,以保甲长为代表的乡村传统势力成为政府和银行在乡村中的代理人。保甲长不仅兼任合作社理事和监事,还操控着合作社的社务和业务。1940—1941年,一项对广东省和平县农村合作社的调查表明,要从合作社借款,必须以土地作为抵押,但是实际上需要借款的人基本都没有土地。保长依法成为合作社主席显得理所当然,合作社的控制权被牢牢掌握在地主手中。(86)Freyn, Free China's New Deal, p.181.正是通过这些乡村势力,国家权力逐渐渗透于农村合作社,达到其监督民众和管理乡村的目的。
乔治·泰勒(George E. Taylor)认为银行与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加大了合作社变异为剥削农民的金融中间人的危险。(87)Taylor, “The Powers and the Unity of China,” p.540.掌控合作社的保甲人员良莠不齐,在权力与资本共同作用下,保甲长呈现出“痞化”的特性。正如李宗黄所言:“一般公正人士多不愿意担任保甲长,一般不肖之徒多以保甲长有利可图,百般钻营。”(88)李宗黄:《现行保甲制度》,重庆:中华书局,1943年,第162页。这些保甲人员“很少优良份子,对合作意义既不明了,对贫农复缺乏同情心理,致社员入社退社,尽为彼辈操纵,贫农简直不能问津”。(89)陈礼泉:《贫农加入合作社问题》,《四川合作金融季刊》1941年第4-5期,第14页。丹尼斯·朗指出:“如果权力关系是必需的,也许会被描述为必需的邪恶。这种邪恶在于权力容易滥用,在于权力容易从合法领域扩大到其他领域。”(90)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1年,第292页。而农村合作运动中的财政援助“在没有宣传、组织、监督和教育的情况下极有可能会被滥用”。(91)Tawney, 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p.94.当权力、资金与农村合作社结合后,保甲人员实际上成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一种“赢利型经纪人”。(92)赵泉民:《“经纪”体制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绩效——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社会权力格局对合作社影响分析》,《江海学刊》2009年第2期,第151页。“这场运动对那些由于缺乏信用而不能从合作社获得信用贷款的贫困农民很难说是大有裨益的。其结果是这场运动主要还是掌握在乡绅、小地主或富农手中。这使这些农村势力集团极有可能利用从合作社获得的资金在贫困农民中发放高利贷”。(93)M., “Chinese Government Fosters Cooperatives,” p.113.
在农贷资金的诱惑下,民国时期的农村合作社俨然成为保甲人员的敛财工具。农民利益常常因为保甲人员挪用合作社贷款或还款而遭受侵蚀。四川省名山县合作指导员向静泉指出:“现在各种团体大多系由土劣把持,合作社监督较严,尚不免混迹其间,若经彼等主持,必反成为剥削工具。”(94)《中国农民银行成都支行、四川省名山县合作金库关于信用社贷款、办法情形、催收代收款的函、代电》,第88全宗,第208卷,四川省档案馆藏。社会舆论也时常批评农村合作社往往被土劣把持的现象。当合作社向银行借得贷款后,这些土劣随即以高利转贷给贫农,以致农民难获实惠。(95)《中国农行成都分行、四川省合作金库等关于农贷概况、营业报告及普遍放款等函件》,第71全宗,第491卷,四川省档案馆藏。1940年中国农民银行成都分行的农贷调查报告足以说明保甲人员对农村合作社的控制程度,兹摘录如下:
查四川推行农村合作以来,两年于兹,实际农民沾其实惠者颇占少数。查其推行之初,工作人员不深入民间,必期将款放出,图行上峰报告成绩,惟揽求联保办事处为之设法联保之。良者为敷衍场面计,遂约保长甲长各借数元以塞责,其不良者个人将款承借,以大利以其特贷乡农藉图自肥,甚有地方官吏伙同土劣将款截借自营商业者。此为最初病症。乃至去今两年,保甲见政府大量放款,各乡合作社之成立风起云涌,其社员姓名大半为联保捏造。一联保而成立十个以上合作社者触目皆是。虽成立之初派有指导员前往召集开会。此项人员每到乡镇即止于联保办公处,何人为社员原不认识,成立之日随凭保长邀十数人到场开会。成立所举监事理事鲜非保甲。贷款到手即由保甲瓜分,每一保长有借数百元千元不等,贷与农民者不及十分之一。(96)《农民银行成都支行、绵阳办事处关于合库紧缩放款业务原则、农贷计划、报告纲要、合作社推进办法、省农业金融促进委员会组织通则的函、代电》,第88全宗,第2360卷,四川省档案馆藏。
六、结 语
综上,民国时期农村合作社的发展是国民政府行使国家权力重构乡村社会秩序的结果,也是银行资本下乡的产物。政治因素和银行业的干预都影响了合作农贷主要功能的发挥。(97)Freyn, Free China's New Deal, p.106.国家权力下沉和银行资本下乡导致了农村合作社“舍质逐量”、合作社管理者的腐化以及农民利益遭受侵蚀等问题。合作社的建设偏离了自愿入社、民主管理和互助救济等原则,最终导致合作社的“异化”现象。
民国时期的农村合作社忽略了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组织方式完全违背了农民“自愿入社”的基本原则。农村合作运动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一项官方“地方自治运动”后,其本质已经不再是“农民自发的社会组织”。(98)陈晖:《合作事业对于中国农村金融的影响》,《教育与民众》1936年第8卷第4期,第630-641页。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方式随即也从自愿入社变为了被动入社,合作者的意愿被完全忽略。有评论者指出,合作者自己恐怕并不认为政府组建的合作社所带来的利大于弊。(99)“Cooperative as a World Movement,” Monthly Labor Review, Vol.24, No.6, 1927, p.38.在政府以“量”求“质”的合作社建设思维下,合作社不再是由农民自发成立的农村组织,而变成了合作指导人员甚至是县长的业绩考核内容。合作事业管理者和合作社的职员、社员的合作教育没有得到必要而充分的重视,最终导致合作社的“非正规化”。(100)M., “Chinese Government Fosters Cooperatives,” p.113.“这些合作社在没有真正了解合作意义的情况下走到了一起,只是为了获得廉价的信贷或其他利益”。(101)Tayler, “Potentialities of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China,” pp.9-10.在新县制体制下,各地为了实现“每保一社,每户一社员”的目标,“彻底消灭了自由组社而变成强制入社”,(102)徐旭:《合作与社会》,北京:中华书局,1949年,第164页。对农村合作运动的态度也由“放任”转变“强制”,(103)许昌龄:《新县制实施中合作事业的新动向》,《中国合作》1940年第1卷第4期,第11页。体现了国民政府利用合作社实现乡村社会治理的政治意图。这种牺牲农民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合作社建设是国家权力加强乡村控制的一种表现。以农村合作运动为代表的“农村重建”实际上是机会主义的,且是由“事件或政治必需品”所决定的。这些自上而下的“纸上谈兵”的“农村重建”完全忽略了人员、财务和技能等因素,“农民自己的主动性很少受到鼓励”。(104)Leonard S. Hsu,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Pacific Affairs, Vol.10, No.3, 1937, p.263.
“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意味着国家动用行政力量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和控制的加强,在这一整合过程中,国民政府在可供选择的社会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主要是借助保甲制的推行和官方任命的行政人员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控制”。(105)杜赞奇:《中国近代史上的国家与公民社会》,汪熙等编:《中国现代化问题——一个多方位的历史探索》,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68页。通过农村合作社来行使“乡村重建”的公共职权体现出国家权力的强制性、工具性、扩张性和腐蚀性等特点。在保甲长掌控下的农村合作社,“贫农小农屡遭拒绝入社”成为一种常态。(106)《四川省府、省合作金库、中国农民银行成都分行关于核放公用业务贷款、农贷通弊及整顿办法、加入合作金库的往来函及甜橙贷款实施计划》,第88全宗,第4425卷,四川省档案馆藏。民国时期的农村合作社忽视了农民的主体性,更谈不上社员的民主管理了。相反农村合作社社员主要由村里的士绅,而不是由贫农组成,贫民的利益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107)T. V. Soong Agnes Roman, “Reviewed Work: 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2, No.4, 1943, pp.404-405.政府推进和资本刺激下的合作社并没有成为一种农民互助救济的团体,权力和资本的合谋只是使其变为了“金融家和政府官僚的新型中间人”。(108)Hsu,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p.263.缺乏民主管理的农村合作社最易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合作社成为地方势力侵蚀农民利益的工具。“合作社构成分子,完全限于地主富农,与一般中农贫农毫无关系。中农贫农不仅得不到低利资金的润泽,一般地主富农反而运用银行对合作社的放款,转拿来高利剥削他们”。(109)李华飞:《战时经济问题研究》,战时文化社,1938年,第274页。信用贷款并没有像政府所设想的那样发挥其作用,即帮助中农和贫农。(110)Freyn, Free China's New Deal, p.106.在银行资本的逐利本能下,合作农贷没有成为打击传统民间高利贷的武器,“现代银行通过农村信用社实行集体担保的做法表明,那仅仅是用集体的高利贷取代了以前的个人高利贷而已”。(111)Roman, “Reviewed Work: 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 pp.404-405.
在农村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与银行资本在乡村社会形成利益联盟,共同构建了“权力-利益”网络,从而导致村庄公共性的丧失,其重构的乡村治理秩序也变成一种无正义的秩序。(112)卢青青:《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重构》,《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第128页。珀西·罗克斯比(Percy M. Roxby)指出:“中国的成功取决于农民在多大程度上能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和前途与国家事业的紧密关系。”(113)Percy M. Roxby,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Chinese Society,” Geography, Vol.26, No.2, 1941, p.60.农民主体性被忽视以及利益被侵蚀最终导致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以失败告终,凸显出保守改革方案在减轻农村系统性贫困方面的不足。(114)Fitzgerald, “Warlords, Bullies, and State Building in Nationalist China,” p.420.本文对民国时期农村合作社“异化”现象的探讨,并非意在全然否定这场运动在乡村借贷关系转型和农业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不过在权力下沉与资本下乡过程中,如何健全农村合作社、有效防止管理者的腐化以及保障农民利益等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