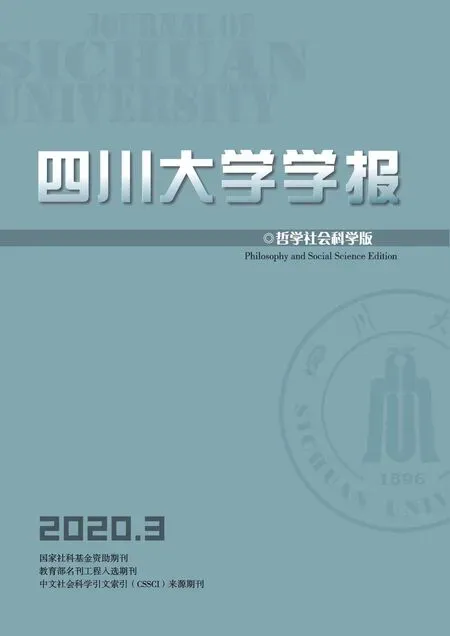美国的宗教信仰之谜:探析《圣洁百合》中的公民宗教
2020-12-26孙璐
孙 璐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宗教是构筑美国的基石。当19世纪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民主体制进行全面考察时,他曾感慨于宗教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好像从第一个在美国海岸登陆的清教徒身上就看到美国后来的整个命运”。(1)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23页。.然而,美国宪法不仅对“上帝”只字未提,更明确了永不建立国教的原则,这使宗教与美国政治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美国宪法虽然没有明文指示,但是“政教分离”已经成为公认的美国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不过,与政治划清界限非但没有弱化宗教信仰在美国的地位,反而成就了其无处不在的影响力。由此,宗教信仰之于美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成为学者和思想家争相论证的重要话题。
纵观美国文学史,宗教更可谓是贯穿始终、深入骨髓的母题。从记录早期清教徒新大陆见闻的叙事日志,到约翰·温斯罗普等神职人员的布道文,再到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等抒发个人情感的诗歌,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文学处处洋溢着清教理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清教思想直接的宣传工具。到了18世纪,无论是约翰·克里夫库尔的《一个美国农民的信札》对美利坚民族特性的探索,还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对美国梦的诠释,抑或是世纪之交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皮袜子故事集》中所塑造的典型个人主义的西部英雄,新教伦理与清教精神在美国人世俗日常中的阐释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内容。标志着“美国文艺复兴”的19世纪美国文学尽管弱化了清教色彩而更加关注“美国性”,但宗教依然是内化其中的隐性因子:伊甸园中的亚当形象成为拉尔夫·爱默生、沃尔特·惠特曼等人作品定义美国民族性的暗喻指涉,清教传统与弊病成为纳撒尼尔·霍桑创作的重要题材,加尔文教的“宿命论”思想和《圣经》预言成为赫尔曼·麦尔维尔小说的象征手法。如果说17世纪的美国文学记录着清教徒的虔诚,18世纪的美国文学书写着清教精神的世俗化身,19世纪的美国文学尽管充斥着反思与批判,但宗教的氤氲依然如影随形,那么20世纪的美国文学则弥漫着信仰的动摇与否定,讲述着“上帝已死”之后世界的混乱与生命的虚无。诸如威廉·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约翰·斯坦贝克的《伊甸园之东》、尤金·奥尼尔的《送冰的人来了》、托尼·莫里森的《宠儿》等作品,同样采用了圣经原型与隐喻的手法,却与原圣经故事形成了强烈反差,笼罩着信仰缺失、生存挣扎、救赎幻灭等挥之不去的阴霾。
在以现实主义白描手法演绎美国历史与社会变迁著称的约翰·厄普代克这里,正统基督教的衰微不再是隐性背景,而是成为显性素材。其中,20世纪美国中产阶级基督徒的信仰危机可谓是其大多数作品的核心关注,《圣洁百合》则是演绎这个话题的集大成者。这部1996年问世的小说沿用了厄普代克的惯常手法,以美国中产阶级一家四代为集合单位,围绕其中的四个代表人物讲述了其基督教信仰崩塌的第一代、投机拜金的第二代、成名成星的第三代以及丧命邪教的第四代的家族故事,折射出整个20世纪美国社会的风云变幻。绵长的时间轴和辽阔的辐射面所彰显的宏大气势,以及娓娓道来的细腻叙事,使《圣洁百合》“不仅是厄普代克先生时至今日最有野心的小说,还是表现最佳的一部”。(2)Michiko Kakutani, “Seeking Salvation on the Silver Screen: Review of 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by John Updike,” New York Times, Jan. 12, 1996, p.B1.然而,小说的包罗万象收获了评论界的溢美之词,也招致一些评论家的微词,如批评小说“缺乏中心人物”,(3)James A. Schiff, John Updike Revisited,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8, p.143.指责小说四个部分没有连贯性、没有中心主题,读起来更像是四个中篇小说。(4)James Gardner, “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Book Review,” National Review, Feb. 26, 1996, p.1.的确,小说四个部分笔墨均衡又各自独立,但实际四个代表人物的故事是一脉相承的,犹如一部交响乐的四个乐章,奏鸣曲、变奏曲、小步舞曲、回旋曲具有伯仲难分的同等重要性,而统摄全局、贯穿始终并对决定个人、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命运起关键作用的正是作品的核心主题——宗教信仰。
宗教在整部小说中充当的“主角”地位,单从小说的题目来看便可见一斑。“圣洁百合”源于美国内战时期被广为传唱的《共和国颂歌》中的一句歌词——“在海的那边,基督诞生在圣洁的百合中”,而按照厄普代克的自述,这句歌词“总结了我想述说的关于美国的故事,可作为整部美国史诗的题目,而我所有的作品,无论多少,不过是对这个大致呈矩形状、幅员辽阔的国家的点滴赞颂,大海横亘在她与基督之间”。(5)John Updike, Self-Consciousness: Memoir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9, p.103.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与基督隔海相望”的比喻性描述实际上诠释了厄普代克对正统基督教及美国人宗教信仰的深刻洞见:一方面,美国是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度,宗教为国家提供了合法性,为社会、历史、文化奠定了道德基石;另一方面,美国在20世纪出现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由此导致美国与基督教“相隔相望”的关系。不难想见,《圣洁百合》所着力呈现的正是宗教信仰之于20世纪美国的复杂面相。目前学界对《圣洁百合》的关注相对较少,对其中涉及的信仰问题多从宗教瓦解、道德沦落等角度探讨,如基督教如何被世俗实用主义所取代,大众文化如何腐蚀了信仰从而使人陷入精神的空洞等,(6)参见James Wood, “Among the Lilies: Updike's Sage of Lost Faith,” The Christian Century, Mar. 6, 1996, p.251; Carol Lakey Hess, “Fiction is Truth, and Sometimes Truth is Fiction,” Religious Education, Vol.103, 2008, pp.280-285;袁凤珠:《宗教+好莱坞=?——约翰·厄普代克近作〈圣洁百合〉》,《外国文学》2001年第1期,第92-94页;傅洁琳:《解读厄普代克小说〈圣洁百合〉的精神意蕴》,《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14-117页;金衡山:《百年嬗变:〈美丽百合〉中的历史迷幻》,《外国文学》2007年第5期,第43-53页。而本文围绕公民宗教这一概念,集中解析《圣洁百合》中所表现出的美国宗教信仰的演变轨迹,指出其独特之处正是“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并存,而美国宗教信仰在20世纪屡遭危机也是缘于“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失衡。
一、厄普代克的宗教观与美国的公民宗教
无论是“兔子四部曲”还是“《红字》三部曲”,厄普代克的大多数作品均表现出对宗教极大兴趣,对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做了不同程度地探析。厄普代克本人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但对宗教特别是上帝的存在却有着不同于正统基督徒的理解。厄普代克曾坦言,通过阅读索伦·克尔凯郭尔和卡尔·巴特等基督教神学家的作品,他确信上帝的存在,并因此收获了极大的慰藉,宽解了“内心因充分意识到我们生命的无足轻重、归于虚无和最终的消逝而产生的焦虑”。(7)John Updike, Odd Jobs: Essays and Critic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1, p.844.然而,正如厄普代克的研究专家詹姆斯·斯基夫所指出的:“厄普代克对神的信仰是双面的、充满悖论的”,因为他认为“上帝既隐匿又可见,既无处可寻又无处不在”。(8)James A. Schiff, “The Pocket Nothing Else Will Fill: Updike's Domestic God,” in James Yerkes and Grand Rapids, eds., John Updike and Religion: The Sense of the Sacred and the Motions of Grace,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p.51.具体而言,厄普代克一方面坚持巴特的神学立场,即上帝是人类无法触及的“绝对他者”,另一方面又相信上帝是“世间万物的终极存在”,同时存在于人的内心和现实生活中,(9)John Updike, Assorted Pros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5, p.275.而“宗教不仅体现在那些原始的、甚至有些残暴的正统宗教教义,同时也遁形于各种私人事务,无论是对猫王的崇拜抑或是对核武器的抵制,无论是对政治的狂热抑或是对大众文化的痴迷,宗教为人类个体的各种活动提供了一种超验的神圣意义”。(10)Updike, Self-Consciousness, p.226.需要指出的是,厄普代克这里言及的“宗教”特指美国的宗教信仰,在他看来,美国拥有一种多元、宽容而充满活力的信仰体系,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没有局限于严格意义的正统基督教,而是以泛化的形式内化于不同世俗事务,宗教因子弥漫在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
美国的宗教信仰体系源于却不同于正统基督教,这种特殊性与公民宗教概念有许多契合之处。尽管从起源来讲,公民宗教并非美国本土的产物,而是欧洲思想的美国实践。纵观近现代西方政治理论,其力图解答的一个基本问题是:面对一个个从城邦、村社、家族等原初社会共同体中分解出来的孤立个体,如何通过某种“契约”将其凝聚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共同体?对此,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明确表示,宗教信仰是建构国家、形成社会认同不可或缺的力量。这位以自由平等为理想社会之原则的启蒙大师认定,作为一种意义共契,公民群体的共同信仰是维持国家恒常、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一旦人们进入政治社会而生活时,他们就必须有一个宗教,把自己维系在其中。没有一个民族曾经是、或者将会是没有宗教却可以持续下去。假如它不曾被赋予一个宗教,它也会为自己制造出一个宗教来,否则它很快就会灭亡。”(11)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71页。然而,卢梭同样警惕宗教与国家完全粘连的危险,他提出的充当“社会契约”的宗教,既非依赖于信徒情感、拥有普世维度的“人的宗教”,也非直接写入国家典册、只为政治服务的“民族宗教”,而是集两者大成于一体的“公民宗教”,即同时保留对神的崇拜和对普世道义的笃信,以及对特定社会契约和法律的尊奉。在卢梭看来,“公民宗教”将有神论民众对神明发自内心的崇拜和公民对祖国及其法律的热爱融为一体,以普世性的教义支撑起某个特定的政治社会,从而拥有了道德教化与国家统治的双重价值。
或许是出于对天主教等建制性宗教的极端反感,卢梭只是强调了对于维系“主权在民”的自由社会秩序,培育公民对社会神圣性的认同感具有重要意义,而对“公民宗教”的具体形态、组织落实等建制要素语焉不详。不过,托克维尔在19世纪的美国社会生活中,为“公民宗教”的理论探究找到了现实依据。根据他的观察,宗教是美国民主政治的主要设施,而美国的政教分离正是宗教信仰对公民社会发挥和平统治作用的前提。具体而言,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对美国社会产生有益影响,依赖的是人们对基督教的自然情感而非国家或政党的强制力量,得益于基督教对民主体制的顺应而非对个人权益追求的一味压制,美国民众在政治层面充分享有自由平等权利和个人主体性的同时,在精神层面遵从宗教教义并主动承担起其提出的道德义务。(12)以上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338-342页。在托克维尔看来,在早期美国,宗教并未因为政教分离而退出公共的政治生活、沦为私人化的信仰,而是成为一种“公民化的自然宗教”,它消解了个人主义带来的离散倾向,为凝聚社会提供了核心价值,从而成就了美国自由与制约并行不悖的现代民主社会。
1967年,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再次复活了“公民宗教”的概念,一时间成为美国学界热议的焦点。在发表于《代达罗斯》(Daedalus)上题为《美国的公民宗教》一文中,贝拉开宗明义地声明:“在美国,存在着一种与各种基督教教会并肩相存而又明显不同的、精心炮制并充分建制化的公民宗教。”根据贝拉的阐释,尽管个人的宗教信仰是严格意义上的私人事务,并且美国由于政教分离而对多元宗教保持极大宽容,但大多数美国人共享了不同宗教取向中的共同元素,表现在一系列“信仰、象征和仪式之中”,为美国的国家体制和美国人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宗教维度。通过分析国父们的公开演讲、美国的国家庆典、总统的就职演说以及普通美国人对个人权利的诠释,贝拉指出,美国的公民宗教不仅作为宗教元素存在于政治领域,更广泛存在于非政治的、公共的、社会的领域,它弱化了神学定位而强化了道德教化和社会秩序维系功用,例如,上帝的概念就“与秩序、法律和权利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而非像正统基督教那样象征着救赎与仁爱”。(13)以上参见Robert N. Bellah, Beyond Belief: Essays on Religion in a Post-Traditional World,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70, pp.171,175.在贝拉看来,美国的公民宗教具有宗教性和社会性两种维度,前者表现在一套以新教为核心的象征化崇拜系统,使美国的政治权威与价值观标准拥有了宗教合法性,并由此建构起强有力的民族凝聚力和为达到国家目标而对个人深层动机的感召,后者表现在对公民共和美德的培育,使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在美国并行不悖,即美国人在充分享有个人自由权利的同时,保持自我克制和投身公共生活的积极性,这种宗教信仰作为一种道德节制,可以将赤裸裸的一己私利转化为具有公心且能够自我牺牲的利益追求。
公民宗教的两种维度使“神圣”与“世俗”在美国社会保持互相依存的关系,但两者并非能够始终保持相互制衡的理想状态。贝拉在文章的最后曾尖锐地指出:“尽管公民宗教帮助美国建构了一个契合上帝旨意的完美社会,它在过去曾被滥用,而今同样成为自私自利和丑恶欲望的托词。”(14)贝拉这里指的是越南战争,即主战派打着美国进行自由、民主“传教”和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的旗号掩盖意识形态博弈的真实动因。参见Bellah, Beyond Belief, p.186.而作为虔诚信徒的厄普代克,也见证了20世纪美国宗教信仰的变迁,根据他的回忆,在美国人生活中,不仅正统基督教越来越不重要,公民宗教同样遭遇“神圣性”与“世俗性”失衡的危机:“那种我从小耳濡目染的基督教,现如今已经没有人真正相信。”(15)Updike, Self-Consciousness, p.230.在一次访谈中,他坦言:“我觉得我们变得越来越唯我,越来越个人中心主义。”(16)Frank Gado, “Interview with John Updike,” in Frank Gado, ed., First Person: Conversations on Writers & Writing, Schenectady, N.Y.: Union College Press, 1973, p.89.当“神圣”退隐甚至完全让位于“世俗”,宗教信仰失去其应有的道德约束力,转而成为个人中心主义的托辞。这种变化成为包括“兔子四部曲”在内的厄普代克主要作品的核心关切,而《圣洁百合》则更集中地表现了20世纪美国宗教信仰的变化轨迹,包括正统基督教彻底沦陷以及公民宗教显现出的不同形态的问题。
二、正统基督教的腐化与衰微
《圣洁百合》开始于身为牧师的克莱伦斯基督教信仰的突然崩溃:正在教堂布道的他突然失声,感到“信仰的最后一个分子正在离他而去”。这件事情来得突然又令人困惑,对此厄普代克在小说的第一部分用不少笔墨剖析克莱伦斯基督教信仰崩溃的原因:或许是他深受无神论者罗伯特·英格索尔言论的影响,或许是达尔文的科学观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动摇了他,或许可以归咎于他个人性格的弱点,或许这原本就是上帝的旨意,就像克莱伦斯对妻子的坦白:“这不是我的决定。这个决定远远超出我的控制。是我的神决定弃我而去。”然而,这些个人因素充其量只解释了一部分原因,基督大厦的轰然倒塌实际上更多是缘于克莱伦斯对正统基督教内部腐化的绝望。在20世纪的美国,工业文明的迅速扩张使基督教失去了超验的神圣性,沦为唯利是图的资本家贪婪攫取的伪饰。克莱伦斯就在一次教堂基建委员会的会议上,强烈反对修建主日学校和扩建教堂的提议,因为在他看来这不仅毫无必要并且劳民伤财,不断涌现的大兴土木的提案不过是不同教区神职人员“急功近利、相互嫉妒”的结果,是对纯洁的宗教崇拜的亵渎,同时也是由于相关投资人“妄图接管第四长老会并为己所用”、用宗教“堵住穷人的嘴”,从而更加义正辞严地中饱私囊。(17)以上引文参见John Updike, 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London: Penguin Books, pp.5,64,37, 41.在目睹了神职人员逐渐背离正统基督教美德而深陷世俗功利的泥淖后,克莱伦斯发出“世间已无上帝”的感叹也就在所难免。
值得注意的是,克莱伦斯并非全盘否定正统基督教与世俗世界的关联,他同样认同加尔文主义将尘世的财富积累视为上帝荣耀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集神圣与世俗于一体的新教教义成就了美国宗教信仰的独特内涵。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详细论述了新教的“命定论”和“天职说”如何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即宣扬每个教徒只有通过尘世的辛勤劳动和勤俭克制荣耀上帝、确认自己上帝选民的身份,从而获得灵魂的拯救,正是这种拥有了宗教合法性的财富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斯基夫指出:“宗教(主要是加尔文教)在美国这个国家的工业和经济的发展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美国人提供了一种(被救赎的)希望,同时给予了他们一种生活中的道德准则。”(18)Schiff, John Updike Revisited, p.144.在一定意义上,新教自身兼具的“神圣性”和“世俗性”使之成为美国公民宗教的一种雏形:严格宗教意义上的“命定论”演化为以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个人主义信念,“天职说”世俗化为一种鼓励勤勉工作的伦理法则,而禁欲克制也成为一种普遍的美国生活方式。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的世俗演绎造就了以富兰克林为代表的一代美国实业家,美国经济也在其庇佑下得以快速发展。不仅如此,尽管新教坚持以个体的身份面对上帝,但绝非忽视群体的福祉与共同发展。在约翰·温斯罗普1630年发表的著名布道文《上帝慈悲的榜样》中,他不仅确立了在新世界建立“山巅之城”的目标,同时也勾勒了一种互帮互助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互相取悦,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一同欢喜,一同悲伤,一同劳作与接受考验,始终将我们的社区看作一个整体。”(19)John Winthrop, “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The Winthrop Society, 2015, https:∥www.winthropsociety.com/doc_charity.php, July 16, 2019.以自律自强的个人主义为基准,以共富共享的群体主义为导向,新教教义同样起到了社会黏合剂的作用,极大推动了美国初期的社会发展。
然而,19世纪美国的全面工业化造就了一大批野心勃勃的企业家,他们逐渐从伦理禁忌和道德约束中挣脱出来,个人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成为他们的唯一追求。当荣耀上帝的使命、友爱同胞的原则让位于个人世俗欲望的不断满足与愈发膨胀,宗教信仰的衰微也成为一种必然。小说中,克莱伦斯认定,为群体福祉做贡献才是真正基督徒的应有之义,正如他在探望一位垂死的教区居民时所说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对我们的同胞施以善举,相信上帝并享受他的恩赐。”然而,在克莱伦斯身边,不仅有贪得无厌的资本家,就连他所在教区的神职同事也被蛊惑收买,为获取物质财富而不惜牺牲教区居民的利益,使克莱伦斯不禁怀疑基督教的存在必要:“世界从未停止它的前进,换句话说,一如既往的浮夸和邪恶,不管有没有上帝。”基督信仰崩塌的克莱伦斯毅然辞去了牧师职位,随之而来的经济的困窘使他不得不干起了推销员的工作,走街串巷地兜售一部名为《大众百科全书》的流行读物。按照克莱伦斯的推销词,这部百科全书“清晰而直观地呈现了世界的所有事实”,可谓是“20世纪的《圣经》”。换句话来说,正统基督教“退场”之后,世俗世界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全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上帝已死”并不意味着“崇拜已死”,而是转化了对象,到了美国国家身上。比如,《大众百科全书》的卖点不仅在于它自诩的为《大英百科全书》的美国翻版——完全由美国人编纂,因此对涉及美国事实的讲述更胜一筹,更重要的是,它被认为是美国民主的结晶:不仅以更加低廉的价格服务于美国大众,就连书名中的“大众”一词也体现了美国“一切为民”的思想。(20)以上引文参见Updike, 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pp.45,23, 91-94.可以说,在正统基督教由于内部腐化而逐渐崩塌的20世纪美国,对国家的崇拜成为美国人新的信仰依托,它为人们的世俗生活冠以另一种“神圣性”,使这种国家崇拜更加鲜明地呈现出公民宗教的特点。
三、爱国主义宗教的力量与滥用
长久以来,美国独特的富有《圣经》隐喻的民族神话和发展历史,使民众对国家的情感与对上帝的崇拜结合起来,现世的爱国主义也由此具有超验的神圣性,成为美国公民宗教的一种形式。实际上,爱国主义与宗教的确存在某种微妙的关联,正如爱尔兰历史学家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所指出的,“启蒙运动削弱了个体的神,消解了王权统治,取而代之的是将某个特定领土的特定人群视为具有神性的民族”。(21)Conor Cruise O'Brien, God Land: Reflections on Religion and Nationalis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49.当国家本身成为公民膜拜的对象,爱国主义也表现出宗教崇拜的特征。不难想见,爱国主义式的宗教对以“上帝之国”自居的美国尤为适用。著名美国学者萨克文·伯克维奇曾指出,当清教徒视征服新世界为神谕时,“新大陆对他们而言已不再是隶属欧洲的荒僻之地,而是拥有了一种包含特殊目的论的神圣意义”。(22)Sacvan Bercovitch, The American Jeremiad,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p.81.换言之,从一开始,美利坚的民族身份就被认为具有“神性”。根据美国历史学家卡尔顿·海耶斯的论述,在美国,国家替代了宗教,国家的立国思想和政治体制犹如宗教教规和仪式一样,伴随每位公民的成长历程,使宗教崇拜与爱国主义没有本质区别。(23)Carton Hayes, Nationalism: A Religion,New York: MacMillan, 1960, p.12.美国研究学者安德鲁·德尔班科曾以美国人信仰的变化为标尺将美国文明划分为三个阶段:以上帝为信仰、以国家为信仰和以个人为信仰,美国人的“希望”也相应从寄托于“基督神话”演变成恪守“神圣联邦公民身份”的信念。(24)Andrew Delbanco, The Real American Dream: A Meditation on Hop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如果说公民宗教的独特性在于,既与上帝立约又关注尘世,那么爱国主义式的宗教以国家崇拜为核心,人们将荣耀国家视为荣耀上帝般的使命,则为个人不懈奋斗和不断自我实现提供了更高层次的动力。
在《圣洁百合》中,这种爱国主义宗教在克莱伦斯的儿子杰拉德和女儿伊斯特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父亲的辞职使全家陷入困窘之境,杰拉德却坚信美国“是一个不断自我创造的国家”,为每个美国人提供自我重生的机会。他带着一腔爱国热情投身一战,退伍后又把握住了战后经济繁荣的先机,赚了个盆满钵满。而伊斯特面对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虽有一时的消沉抱怨,但很快便开始努力工作,承担起支撑整个家庭的重任。在杰拉德和伊斯特看来,美国人的身份本身就包含着摆脱过往重负、重获新生的希望,这是国家对每个美国公民立下的犹如上帝与其子民盟约一般的许诺,而抓住机遇努力奋斗同样也需要像信仰上帝一样坚定奉行,正如克莱伦斯妻子所说,“置上帝赐予的机遇于不顾是最大的恶”。然而,对国家的崇拜并非永远向善,如同克莱伦斯目睹正统基督教沦为谋取私利的伪饰,爱国主义宗教同样也会被扭曲滥用。杰拉德不仅到处传教式地宣扬美国是“机遇的圣地”,每个美国人都应当抓住一切机会创造财富,“哪怕是摩门教徒现如今也能在华尔街赚钱”。而他在赚钱之后,则是放纵于纽约这座“遍地是表演、俱乐部和女郎”的享乐主义天堂。伊斯特也同样“游荡在美国欲望、快钱和爵士乐的海洋”,(25)以上引文参见Updike, 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pp.88,189,185,196.最终成为喧嚣的20年代以奇装异服博人青睐的轻佻女子。事实上,如同严苛的清教“坚决抵制不诚实和任性的贪婪”并要求每个人恪守自律的禁欲主义原则,(26)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by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Scribner, 1958, p.172.公民宗教的道德教化意义正在于其推行的自我约束原则。具体而言,对爱国主义宗教的信奉者来说,国家因全面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而成为崇拜的对象,但这种自由并非毫无节制,贪婪纵欲非但不能荣耀国家,还会使个体生命走入歧途甚至走向灭亡。小说中的杰拉德因贪欲而在投资和证券市场愈发疯狂以至于压上全部资产,而不久之后的美股崩盘和随之而来的大萧条使依靠投机发家致富的他一夜破产,直至身无分文。与正统基督教的内部腐化相似的是,在消费文化盛行、享乐主义至上的20世纪美国,爱国主义宗教同样打破了“神圣性”和“世俗性”应有的平衡。
颇有意味的是,在厄普代克笔下,当杰拉德和伊斯特以国家崇拜的名义放纵了自己的私欲,他们的弟弟泰德则以一种截然相反的方式诠释了何为真正的爱国主义。深受父亲克莱伦斯信仰崩塌的影响,泰德一直怀有一种“反宗教”态度,不仅从不去教堂礼拜,也不像杰拉德和伊斯特那样积极进取,而是一再推掉近在咫尺的各种工作,拒绝一切“自我实现”的机会,然而“他不愿去竞争,但竞争似乎是唯一可以表明你是一个美国人的方式”。泰德的“反基督教”和“非美国”特征使他成为整个家族的异类,但这两点恰恰击中了正统基督教与国家崇拜的软肋。泰德之所以对宗教没有好感,是因为他坚信父亲的抉择一定事出有因,而坚决站在父亲一边;他表现出的“不思进取”也非真正的懈怠懒惰,而是恪守最基本的道德规范、遵行脚踏实地的生活原则。在目睹了纽约纸醉金迷且不齿于同杰拉德等投机客同流合污之后,泰德回到家乡小镇做起了邮递员。在他看来,美国政府才是“最可靠的雇主”,他所从事的也是“最光荣的职业”,因为通过“投递邮件可以联结整个社会”,从而能够切实地“服务于国家”。(27)以上引文参见Updike, 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pp.139,204.在一定意义上,泰德所表现出的对欲望的克制、对生活的热爱、对善良和脚踏实地的坚守以及为国服务的信念,实现了公民宗教的真正价值,即每一个普通公民平凡的世俗活动都具有意义,他们对国家的信心与崇拜成为荣耀国家的力量源泉。
四、电影的宗教化崇拜与毁灭
如果说对上帝的信仰在克莱伦斯身上彻底垮塌,对国家的信仰在杰拉德和伊斯特身上遭到滥用,那么到了这个家族的第三代艾希这里,信仰再次找到了新的寄托之物。与祖父不同的是,艾希从小便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坚信上帝的无处不在:“上帝隐没在云中,他把基督送到人间,带来了圣诞节和复活节,上帝的爱从天堂撒进人间,充盈了她的整个身体,就像她浸泡在充满水的浴缸之中。……上帝的无处不在犹如血管中流淌的血液,甚至有时把耳朵放在枕头上都能感受到他。”(28)Updike, 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p.233.艾希对上帝的信念缘于家庭的宗教背景和一个孩童的想象,是上帝给予了她一种“个人被选择”的优越感,(29)Schiff, John Updike Revisited, p.149.而这成为她不断奋斗与自我实现、最终成为好莱坞影星的主要精神动力。然而,艾希的信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正统宗教,尤具讽刺意味的是,她脑海中的上帝形象不是别人,正是她那由于丧失信仰而最终在贫病中悲凉死去的祖父,而她所认为的天堂也不是此世以外的彼岸世界,而是现世中的电影。从童年开始,艾希就是电影院的常客,并且在电影中为自己建构了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在那里“她每一个梦想都能成真”,无需去面对“危险的峭壁和鸿沟的真实生活”。(30)Updike, 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pp.246, 247.沉浸于电影世界的艾希逐渐模糊了虚幻与真实的边界,以至于当她探访居住在纽约的表哥时,她一时竟分不清楚是踏入了表哥的家还是踏进了电影荧幕。对艾希而言,去电影院观影就像去教堂礼拜一样,电影中的人物取代圣经中的神成为她的崇拜对象,换句话说,电影才是艾希真正的信仰支撑。
事实上,宗教信仰与电影的复杂关系是小说贯穿始终的关注。在小说的最开始,厄普代克并未开门见山地叙说克莱伦斯信仰的崩塌,而是先描写了一部电影拍摄的场景,正当剧中女星突然从马背摔下,身在城市另一边的克莱伦斯涌起了对上帝的质疑。把两件看似不搭界的事件并置在同一时刻讲述,显然是厄普代克有意为之的隐喻,即20世纪初的美国正经历着正统基督教的没落,同时又见证了电影的兴起。小说接下来的故事,也在不断影射电影成为新的崇拜对象的可能,其中颇有意味的是,就连失去正统基督教信仰的克莱伦斯也转而投入电影的怀抱,甚至在他看来,“(电影院)就是一座教堂,散发着神秘的光亮,投射到充满期待的观众席上。……调动起观众整齐划一的情绪:愤怒、悲伤、焦虑,还有大团圆结局时的如释重负”。(31)Updike, 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p.105.就此而言,是电影接任正统基督教填补了克莱伦斯的精神空洞。作为20世纪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大众文化形式,电影已逐渐成为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电影院作为公共聚集场所,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代替教堂的功能,据厄普代克回忆,他青年时代所居住的小镇,两座核心建筑就是“几乎并肩而立”的电影院和教堂,它们“不仅一直争抢他的关注,有意思的是,它们变得愈发相像”。(32)转引自James A. Schiff, “Updike, Film, and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in Stacey Olst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hn Updik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41.而对于艾希来说,电影不仅是精神慰藉,帮助她摆脱现实的昏暗而进入“美好天堂”,更重要的是使她从崇拜者变成了被崇拜的对象,摄像机让她感受到“整个宇宙的注意力都聚焦在她的身上,就像在她小时候,上帝注视着她的每一步、记下她的每一次祈祷和渴望一样”。(33)Updike, 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p.335.从上帝的笃信者到成为被影迷奉为上帝一样的存在,艾希对电影“神性”的诠释可谓到了极致。
电影院被视作教堂而充当连接尘世与天堂的桥梁,与电影本身的特点不无关系。作为大众艺术,电影是“唯一一种展示出其‘原材料’的艺术,它将现实挖掘并复原出来”。(34)Siegfried Kracauer, Theory of Fil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303.当呈现于大众眼前的影像无限接近于真实世界,观影者在观看过程中就会感觉仿佛可以走进荧幕成为电影世界中的一员。德国文化批评家瓦尔特·本杰明在其著名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一文中曾指出,由机械复制生产出的电影改变了观众对艺术的感知:“人们不再像对待毕加索绘画那样战战兢兢,而是以一种进步的积极态度面对卓别林的电影,表现出专家一般的权威姿态,将所见与所感直接融为一体。”(35)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ed. by Hannah Arendt, trans. by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p.234.从这个角度来看,观影者与电影世界的“零距离”实际上消解了在传统高雅艺术中普遍存在的观者与艺术品之间的隔膜,换句话来说,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能够自由穿梭于电影内外,由此领略另一种世界的风采,甚至“亲身感受”另一种生活方式,也因此收获了现实世界无法企及的启示。厄普代克在回忆小时候的观影经历时就曾明确表示,自己在观看好莱坞影片的过程中收获了许多“教育和启迪”,他描述道:“电影院闪亮、富丽的装潢,一千零一夜般的玄幻和宫殿般的气派使美国城镇的男男女女从单调沉闷的日常生活中解放出来,走向一种超自然的状态。所有人都在一点一点尝试(电影中)明星的生活——穿着得体,行动果敢,爱得彻底。”(36)John Updike, More Matters: Essays and Critic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9, p.643.
电影抚慰了克莱伦斯的精神荒芜,引领艾希步入天堂般的美好世界并收获了上帝般的瞩目,但同样也是电影,它带给艾希的儿子克拉克的却是献祭般的毁灭。全身心投入明星事业的艾希遭遇了失败的婚姻,使克拉克从小便成长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缺乏父母之爱的他成了一个浪荡子,终日沉迷于电影和电视节目,唯一的梦想就是成为好莱坞大片中的英雄人物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与价值。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加入一个邪教组织并担任该组织的公关负责人,时常以发言人的身份接受媒体采访,满足了他成为“电视明星”的愿望。在政府对该邪教组织的一次围剿行动中,克拉克置身于枪林弹雨中满脑子想的却都是好莱坞大片的拍摄,并再次代表该组织接受直播采访,全然不觉这是性命攸关的时刻,反而是格外享受:“他并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的内容,只是喜欢对着这个小小的咖啡色的松下话筒讲话,感受着他的一字一句被如饥似渴的世界完全吸纳。”(37)Updike, 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p.451.最终,犹如好莱坞电影惯常的剧情反转,克拉克在最后关头“浪子回头、改邪归正”,挺身而出击毙了邪教组织头目,并舍命解救出了一些妇女和儿童,成了名副其实的“拯救者”。然而,克拉克的自我牺牲“看似是一种赎罪之举,实际上就像他的其他所作所为那样是深受电影影响的结果:指挥他最后行动的不是灵魂的醒悟,而是动作电影的套路,那就是迷途知返后的英雄总会通过杀死坏蛋和自我牺牲赢得我们的同情”。(38)Julian Barnes,“Grand Illusion:Review of 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by John Updike,” New York Times, Jan. 28, 1996, https:∥archive.nytimes.com/www.nytimes.com/books/97/04/06/lifetimes/updike-lilies.html?_r=1, July 20, 2019.当他的“英雄壮举”在电视中实况播出,却颇为反讽地呈现出一副娱乐真人秀的样子,而他的母亲艾希在通过收听广播得知儿子遇害的消息时,所关注的也只是自己的反应是不是符合一个女演员的标准。
克拉克的殒命,罪魁祸首不仅是邪教的毒害,同样也归咎于他对电影的狂热崇拜,此时,电影作为一种别样的公民宗教带来的不再是精神慰藉或是神一般的备受瞩目,而是盲目甚至偏执。厄普代克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圣洁百合》这部小说旨在“探讨美国电影如何成为一种(正统)宗教替代物”,因为电影不仅呈现了有别于现实的不同世界,并且犹如宗教教化一般启迪人们该如何生活,为人们提供了宗教一般的信仰归属。然而,紧接着,厄普代克同样直言不讳地指出当这种崇拜发展到极端之后的危害:“如今,我们时常看到人们的生活愈发电影化,以至于失去了与真实世界的联系。孩子们拿起枪相互射杀,认为第二天一切便可以重新来过。等到他们意识到扣动扳机的后果是死去的受害者无法再活过来时,已经太晚了。某种程度上,这些少年谋杀者难道不是电影宗教化崇拜的受害者吗?”(39)Charlie Reilly, “An Interview with John Updik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XLIII, 2002, p.239.在20世纪正统基督教式微、国家崇拜遭遇滥用的美国,电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特别的公民宗教,为人们提供了新的信仰寄托,但同时却潜藏走向狂热极端、甚至自我毁灭的危险。
厄普代克曾为这部小说撰写了《特别声明》,于中他直言道,“有关‘圣洁百合’这个题目我思考了很久,它透露出新教被流放的忧伤——‘基督诞生在圣洁的百合中,在海的那边’,而不是海的这边”,同时,厄普代克也解释道,他所讲述的一家四代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连贯的故事,而“上帝是其中真正的主角”。(40)Updike, More Matters, p.830.尽管政教分离的原则使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与美国社会和个人生活“若即若离”,但形式多样的公民宗教却为美国人提供了多元的信仰依托,使美国国家与个体的方方面面都兼具了“神圣性”与“世俗性”元素,尽管两者时常遭遇失衡、甚至毁灭性的后果。这正是《圣洁百合》着力探究的美国特点,也为读者打开了一扇洞悉美国的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