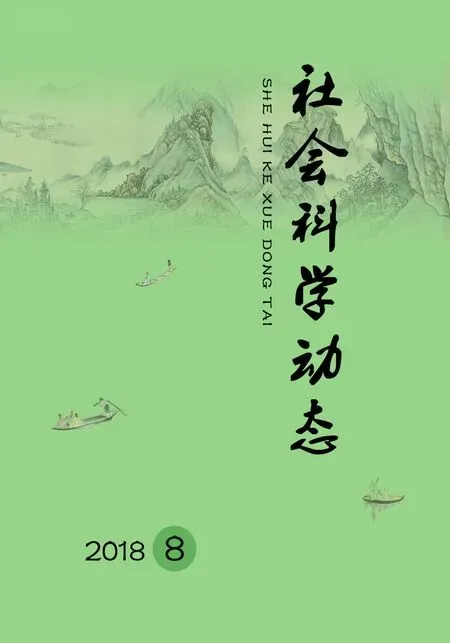基于农民视角的中国农民银行农贷政策检讨
——以湖北为个案(1935—1945)
2018-03-31陈明辉
陈明辉
一
1933年,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成立,设总部于湖北汉口。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将四省农民银行改名为中国农民银行 (以下简称 “农行”),并以之为发展农村经济的国有专业银行,代表国家意志重点办理全国农贷与土地金融业务,湖北亦因此成为农行最早举办农贷的省份之一。①随着农贷业务的发展,农行在湖北逐渐形成一个包括分支结构、合作社等在内的现代农业金融体系和包括农贷对象、利率、期限、类型等具有现代农业金融特征的农贷运作机制。农行在湖北的农贷运作对调剂农村金融,促进农业发展,减轻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等方面多有贡献,但也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制约了农贷效用的充分发挥。目前,学术界关于农行农贷政策的检讨主要是从政府、银行的视角进行剖析②,较少从农民的视角展开研究。笔者认为,衡量农贷政策的有效性,关键是看农贷政策能否满足农民的金融需求。并且,农民作为农贷的最终对象,切身体验着农贷的各项政策,了解农贷的运行状况和社会评价,对农贷绩效最具发言权。因此,本文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农民视角出发,检讨农行在湖北的农贷政策与措施,揭示农贷绩效不足的成因。
二
如何看待农户的生产行为,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总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两类:一类以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为代表,强调小农的理性动机。一类以美国经济学家J·斯科特为代表,强调小农的生存逻辑。毫无疑问,无论是舒尔茨的“理性小农”还是斯科特的 “道义小农”,对于农户的生产行为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为我们研究农村经济和农贷制度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有益的启示。但是,这两种观点亦存在一定的偏颇之处,即过于强调农户生产行为的某一面相,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特性。就经济领域而言,笔者认为农户是个复杂的、多元的经济体——既具有经济理性,亦具有盲目性,既具有生存理性,亦具有冒险冲动。农行农贷主要通过合作社进行贷放。以1940年为例,合作社放款占农行在湖北放款总量的86.02%。③因此,本文主要以农行的合作社农贷为考察中心。
1.农贷以数量有限的合作社为主要放贷对象,农民入社难
如前所述,合作社是联系农行与农民贷放款项的主要中介,是农民获得农贷的主要机构和途径。因此,湖北省合作社能否做到普遍设立,关系到农行农贷是否能够广泛覆盖和有效推广。
现有研究表明,1935年至1945年间,湖北省合作社数量和入社人数节节攀升。④值得注意的是,湖北省合作社数量的增加并不是农民自愿参与的结果,而是政府为实现社会控制和政治斗争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结果。换言之,湖北省合作社数量的增加是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产物,而非诱致性制度变迁下农民自主选择的结果。即便如此,这10年间,湖北省合作社数量最多时也只有12986个(1945年),最少时仅1900个 (1935年);湖北省平均入社人数仅占湖北省人口总数的23.34‰,最高年份亦不过54.69‰ (1945年),最低年份仅3.65‰(1935年)。⑤由此看来,湖北省合作社数量及入社人数仍然较少,在广大乡村社会中不具有普遍性,农民享受到农贷的机率自然也较低。
更确切地说,农行在湖北的农贷业务主要是通过合作社中的信用合作社进行运作的。1935年至1945年间,湖北信用合作社数平均占湖北合作社数的67.58﹪,最高年份达80.0﹪ (1938年),最低年份亦占48.1﹪ (1945年)。⑥但是,就绝对数量而言,信用合作社的数量和社员数量却仍然较为有限。以宜昌信用合作社为例,1934年,由农行宜昌办事处辅导并贷款支持组建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有20个,社员426人。1935年底,信用合作社增加到61个,社员达1356人。抗战军兴,这种增长态势很快就中断了。到1940年,宜昌半壁沦陷,各种信用合作社大都名存实亡。嗣后,政府一再推动,虽渐有发展,但仍较为有限。到1944年底,宜昌也只有专营信用合作社81个,社员2325人;兼营信用合作社3个,社员99人。⑦相对于数量众多的农民而言,这些信用合作社无法覆盖到多数农民,无异于杯水车薪。
综上可见,湖北省合作运动普及程度及范围极为有限,社员占总人口的比重亦较小,不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农行农贷自然也难以惠及广大需要农贷的农民。
2.农贷手续复杂,贷款成本高,农民贷款难
(1)农贷手续复杂。出于降低农贷成本和保障农贷安全考虑,农行制定了一套严密而又繁琐的合作社借款、还款程序。 《湖北省农村合作社借款还款程序》规定,合作社如有正当用途需要资金时,得向合作委员会或合作金库填具借款申请书,并由合作委员会考核贷款用途及数额,附注意见,函请农行核放;农行审核通过后,方填发合同及收据,交合作社查收签盖,向指定付款地点办理借款手续;借款到期前1个月,农行通知合作社准备筹款,并函知合作委员会;借款到期时,本利必须如数付清,不得稍有拖欠;如遇有特别事故不能如数、如时偿还时,必须在到期1个月前申述理由,请求展期。
对于农行来说,严密的农贷程序有利于保证农贷资金安全,降低农贷风险。但是,对于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且家庭贫困的农民而言,无疑增加了贷款难度:既要请人写申请书、求人作担保,又需等待评估、审核,甚至办理抵押等手续,辗转于合作社、合作委员会、银行等机构之间。
因此,湖北省 “各县农村合作社之借款……往往有申请已半年而款不能到手者”,手续过繁即是一重要原因。⑧尽管农行一再要求放款必须手续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 “手续既繁,费时亦久,难应农民急需。”⑨
(2)农贷成本高。由于农贷主要以合作社为放款对象,农民要想获得农贷,首先必须加入合作社。而加入合作社,必须缴纳入会金,一般在2元左右。然后,向合作社提交申请,并请乡绅、地主、富农等人作担保。在办理贷款的过程中,还会面临掌握合作社农贷人员的 “寻租”行为。例如,一农民 “借款十元,却需送二元给保长作为生日贺礼。”⑩枣阳县合作办事处主任刘道经每赴樊银行取款一次,借款各社均需缴送20元,以作路费之用。⑪
此外,农贷的交易履行、还款等环节亦是手续繁冗、消耗工时甚多,甚至还要支付抵押物的运输费用、保管费用等。
那么,湖北农民能不能负担得起这些费用呢?1936年,中央农业实验所通过对湖北黄安县成荘村的调查发现,该村自耕农兼雇农每年收入为97.5元,纯佃农的收入为74.75元。这与每户200元的“低标准”生活费用相较,相去甚远。⑫可见,湖北农村的贫困化已是一种常态了。根据全国土地委员会20世纪30年代对湖北11个县113547户农家的调查显示,负债户数为42578户,负债率高达37.5%,负债户中平均每户负债额为36.256元。⑬生活贫困、债台高筑的农民无疑是需要农贷资金的,但是成本甚高的农贷严重打击了贫困农民申请农贷的积极性,使得贫困农民有心无力、望而却步,抑制了农民的农贷需求,甚至葬送了贫困农民申请农贷的机会!
3.地方势力把持合作社,农民获利少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政权主要依靠 “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行政职能,形成了 “国家政权内卷化”,导致乡村社会为地主豪绅等地方势力所控制。在此背景下,为降低农贷成本和保障资金安全,农行直接指导农民组建的合作社,大都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与地方势力共同管理。在农行做基层农贷工作十余年的李秉枢指出, “一些农村的小地主、富农、保甲长和他们所豢养的亲信们组成了信用社的理监事会,银行农贷就是通过他们发放的,也就是受他们操纵的。银行也知道,要在农村站住脚,要取得贷款的安全,离开这些地头蛇是玩不起来的”。⑭
后来,政府收回合作社自办,尤其是1942年南京国民政府提出 “每保一社,每户一社员”的目标后,合作社要么掌控在合作指导员手中,要么掌握在地方势力手中。由于 “近代中国农村合作社多采取无限责任制,社员所负连带责任太重,必然考虑到偿还借款能力;合作指导员下乡的时候太少,与下层民众接洽更少,于是接触的多为土豪劣绅。”⑮所以,归根到底,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权最终落入乡镇保甲长、地主豪绅等地方势力之手。
湖北也不例外。例如,竹山县 “各级合作社理监主席多是乡长兼任,社内人事去留随其好恶,良莠不分,致引起一般人民的反感。都认为合作社是私人操纵的,俱不信仰。”⑯
宜昌信用合作社 “各社一般均设有理、监事……乡、保、甲长为各级信用社的理、监事,并会同当地豪绅共同组成理、监事会,统揽信用社大权。”⑰
在这种情况下,湖北 “大多数合作社徒具形式,有名无实,即或有其形式,乃为少数人操纵牟私之工具,享受免费、低息贷款,优惠价进货之权利,而另作私图。”⑱湖北 “信用合作社贷款,虽然形式上也有银行农贷员当场监放、检查,但只是一种骗人的手法,贷款上冒名顶替,或被保、甲长拐走的事时有发生,真正需要贷款的农民往往借不到钱。”⑲例如,通城县豪绅李树欷伪造名册,先行贷款2000元用于开设赌场,然后将伪造名册送办事处 “核查”了事;通城县政府官员任意将贷款挪作它用,甚至据为私蓄。⑳枣阳合作社王某理事长,“家本富豪,一时缺乏,完全用个人佃户三十余人领有(农贷——笔者注)600余元作己私用。”㉑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引发了民众的强烈抗议。1938年6月,枣阳县西北第一、二区两区25万人民代表联合呈控枣阳合作办事处主任刘道经 “串通一般土劣”包办合作社: “往来交游青年流痞,在四乡各镇组织合作社,每人确 (却)能入三、四次,希图多借渔利……”; “在枣经营放款多年,不知暗中勾结土劣若干,格外送人情,又不知若干。可怜农民苦向谁说。”㉒
凭借掌握地方政治、经济大权,保甲长、地主、豪绅等乡村势力把持合作社,还利用合作社名义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又把所贷款项以高额利息借给需要资金的农民,无孔不入地发挥高利贷的作用。枣阳合作办事处主任刘道经 “以利息甚轻之大宗款项,辗转借给农民,每年约三分至四分从中取利。”㉓宜昌 “各级信用社又均被当地保、甲长及豪绅把持。他们串通一气,伪造清册向农行取得低息(月息1—1.5分)贷款,转手以月息三至七分高利贷给农户,从中剥削。”㉔如此一来,农贷资金不仅未能流入生产领域,刺激生产经营,救济贫苦农民,反而为农村高利贷提供了资金来源,异化成“集团高利贷”的基金,变成剥削农民的新式工具。
综上可见,有限的农贷资金往往被地方势力占有,常常被他们用来投机于土地买卖、囤积居奇,或转手放高利贷,而农村金融资源的真正枯竭者——贫困农民却难以获得农贷资金。
4.农贷金额少、平均化、用途管制,与农民需求存在较大差距
一是农贷金额少,规模小,存在着金融抑制。现有研究表明,农行用于农贷的资金极其有限。㉕与此相对应,农行在湖北的农贷资金虽然不断增加,但亦是极其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农民对农贷资金的需求。㉖以郧县为例,该县1943年主要农作物生产成本包括:麦8万亩,成本2400万元;玉蜀黍10万亩,成本3300万元;甘薯5万亩,成本1460万元。但是,农行该年对包括郧西县在内的五个县的生产贷款总数仅17.29万元,所占农业生产总成本的比重几乎可以省略不计。次年,郧西县生产贷款数额虽增至35万元,与其所需的生产成本相比,亦是杯水车薪。㉗若再考虑到战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因素,则与农民的生产资金需求相差更远。可见,农行的农贷投放金额只是农民所需资金中极小的一部分。
1935至1945年间,湖北获得的农贷数量虽然渐有增加,但湖北在农行农贷系统中的地位却逐渐下降。武汉沦陷前,湖北一直是农行农贷的重点区域。据朱通九统计,截至1938年底,农行在湖北的合作社贷款共计7112679.13元,获得的贷款数额仅次于四川、安徽,位居全国第3。㉘武汉沦陷后,受战事影响,除鄂西、鄂北少数县份由农行老河口与恩施两办事处分别发放小额贷款外,其它地方的农贷业务基本停顿,湖北不复为农行农贷的重点对象,湖北获得的农业放款数额在农行农贷放款总量中的比例也不断下降:由最高时的11.92% (1938年)降至最低时的2.23% (1945年)。㉙由此可见,湖北农贷规模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全国中等甚至末等水平,农贷规模较小。
农贷数量少不仅体现在湖北获得的农贷总量方面,而且体现在湖北人均农贷数量方面。据农行宜昌办事处统计,1935年上半年,合作社社员人均获得农贷仅16.83元。即使是如此有限的农贷,也由于各地合作社财力微弱,经营不善,而难以支撑。㉚1940年,湖北合作社社员人均获得合作社放款金额为11.29元,排名全国第15位,远未达到21.47元的全国人均贷款水平。㉛与每户农民每年所需的255.22元现金的平均周转额相比,更是相去甚远。㉜
此外,农贷数量少还体现在农民获得的贷款少于申请的农贷金额。1935年6月,宜昌61所信用社共申请农贷款12990元,但实际只贷得10703元。㉝1944年,湖北向农行申请500万元农村副业贷款,但农行仅核准100万元。 “原定各种农贷额度,均经分配完毕,实际不敷甚巨”,各地 “纷请酌予增加”。㉞农行武昌办事处也声称 “农民需要多,而本行配贷额少”。㉟尽管农行一再强调要增加农贷数量,却始终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
可见,农行农贷供给严重不足,与农民的金融需求存在巨大的金融缺口和金融供需矛盾,存在明显的金融抑制。
二是农贷平均分配,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如前所述,湖北农贷数量相当有限。本该集中贷放重点需求区域,但由于各地普遍要求农贷,导致农贷分散,无法形成农贷资金的规模效应。汉口分行 “所配各种农贷每感不敷分配”,而各级政府 “复坚持普遍贷款,致使区域过于散漫,配额过于零星。”㊱尤其是在某一合作社内部,往往不顾社员间的需求差异而平均放贷。如武昌杨柳村莲藕稻谷生产合作社各户菜地在1—10亩之间不等,但每户所得农贷均为3万元;咸宁县马桥乡合作社各户耕地亩数在10—40亩之间不等,但每户所得农贷均为1万元。㊲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种做法明显脱离了农民的实际资金需求,也降低了农贷资金的利用效率。
三是农贷用途管制,难以满足农民需求。为增强农民的生产能力,发展农业经济,农行限定农贷必须用于农业生产及相关用途。农行在1935年条例的第7条中明确规定, “农业放款以供下列各项用途为限: (1)购买耕牛、种子、肥料、畜种及各种农业原料; (2)购办或修理农业应用器械;(3)农业品之保管、运输及制造; (4)修造农业应用房屋及场所; (5)其他与农民经济或农业改良有密切关系之事项。”㊳然而,这只是政府和银行的一厢情愿。由于湖北农民大都处于贫困化状态,对于他们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是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而农行农贷以生产用途为主的规定使得广大贫困农民对农贷望而却步。
因此,对于广大贫困农民来说,由于农行农贷不能提供给他们生存所需要的资金,即使有机会获得农贷,也不愿意申请,对农贷兴趣寥寥。当然,也有部分农民以发展生产的名义申请农贷,获得贷款之后再挪用于生活消费。咸宁县同德乡第七保合作社欲借农业生产贷款50万元,申请书上注明为购买农具肥料等,但在社员借款细数表上却写着“购米”!㊴揆诸史料,农贷被挪用、用途被转移的例子不在少数。这样一来,农贷难以达到供给农业资金,发展农业生产的预期目的,绩效十分有限。
三
出于加强社会控制和保障农贷资金安全,政府和银行以合作社为主要中介开展农贷,促进了资金、技术等现代性生产要素流入农村,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合作社数量少且多数为乡村中的 “赢利型”经纪所控制,农民入社难;农贷成本高,手续复杂,旷费时日,农民贷款难;农贷金额少、平均化及用途管制,农民贷款意愿弱。所以,真正需要资金的贫农不仅入社难、贷款难,而且即使是有机会获得贷款时,也未必愿意承贷。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农贷政策是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制度变迁,始终站在政府的立场,服从和服务于政府的统治目标和需求,过度强调农贷的生产用途,忽视了农民金融需求的多样性。近代湖北农民大都处于贫困状态,其首要的金融需求是生存性的消费需求,然后才是生产性需求。这就导致农行农贷提供的生产性金融服务与贫困农民这个消费性需求主体的金融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甚至于农民所需要的,政策不能够提供,而政策所提供的,却又难以满足农民的需求。可见,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农行农贷基本抛弃了农民的立场,几乎无视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的经济现状和生存性需求,并导致广大贫困农民在事实上被排斥在这一制度变迁活动的大门之外,难以得到农贷资金,违背了农贷的本意,制约了农贷绩效的充分发挥,在促进农业生产力提高和农村经济发展方面成效寥寥。
注释:
① 湖北曾为农行创办地和总行所在地,但关于农行在湖北农贷的研究却寥若晨星。论及农行在湖北农贷问题的代表性论文及著作有:姚顺东、唐湘雨: 《近代中国中部地区政府的农业投入——1937年湖北省为中心的考察》, 《农业考古》2011年第1期;李金铮: 《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
② 详见李金铮: 《绩效与不足: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与农村社会之关系》, 《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黄正林: 《农贷与甘肃农村经济的复苏 (1935—1945年)》, 《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等文。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 《财政经济 (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66页。
④⑤⑥王奎:《合作社组织与乡村社会变迁——以1931—1945年湖北省农村合作运动为个案》,华中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
⑦㉚ 湖北省宜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宜昌县志》,冶金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398、398页。
⑧ 程理锠: 《湖北之农村金融与地权变动之关系》,《申报年鉴》,申报年鉴社1936年版,第7页。
⑨⑪⑯⑱㉑㉒㉓㉞ 曾兆祥主编: 《湖北 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 (第3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5年刊行,第 342、345、346、347、345、345、345、342 页。
⑩ 章有义: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25页。
⑫ 李树青: 《中国农民的贫困程度》, 《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9号。
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 《财政经济 (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0页。
⑭㊳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 《中国农民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第152、331页。
⑮ 侯哲庵: 《如何使贫农加入合作社》, 《中农月刊》1940年第1卷第6期。
⑰㉔㉝ 宜昌市金融志编辑室: 《宜昌市金融志(1840—1985年)》,宜昌市金融志编辑室1985年刊行,第65、66、66页。
⑲ 湖北省志·金融志编纂委员会: 《湖北省金融志》(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⑳ 通城县志编纂委员会: 《通城县志》,通城县志编纂委员会1985年刊行,第362页。
㉕ 参见蒋国河: 《中国农民银行农贷业务评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等文章。
㉖㉙陈明辉、金东:《政府、银行与农户——中国农民银行在湖北的农贷 (1935—1949)》,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学刊》 (第1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3—156、143—156页。
㉗ 湖北省档案馆: 《中国农民银行武昌办事处民国廿二年度农贷分类统计表》,全宗号61,目录号3,案卷号38。
㉘ 朱通九: 《我国农业金融机关最近对于融通农业资金之鸟瞰》, 《中农月刊》1940年第1卷第1期。
㉛ 《廿九年度全国合作社放款金额与社员数比较表》,《中农月刊》1941年第2卷第4期。
㉜ 《建立合理的农贷制度》, 《新华日报》1942年6月12日社论。
㉟㊲㊴ 湖北省档案馆: 《中国农民银行武昌办事处武昌、大冶、通城、通山、咸宁、崇阳、嘉鱼、蒲圻、阳新等县农贷函表册》,全宗号61,目录号3,案卷号2。
㊱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农民银行汉口分行三十五年度农贷报告》 (1947年),全宗号399,卷号55080,转引自李金铮: 《绩效与不足: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与农村社会之关系》, 《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