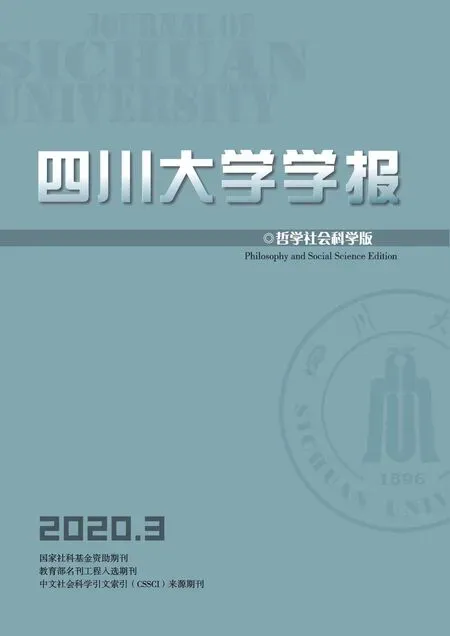生态女性主义的多元主体联盟:理论构建与现实挑战
2020-12-26张沥元
张沥元
近年来,发源于欧洲的“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周五为未来”(Friday for Future)等新社会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新一波绿色政治抗争浪潮。归纳起来,这些抗争活动有如下几个共同点:抗争主体明显以女性、青年、少数族裔民众为主,呈现出多元化身份交叉的特征;抗争议题不仅涉及环境保护,还包括全球正义、性别正义、种族正义等;抗争对象主要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其政治诉求超越了个体利益和道德伦理关切而主张对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深刻变革。总的来讲,这些新社会运动不仅呈现出多元化主体和多样化诉求交织的景象,还具有强烈的绿色左翼(1)郇庆治:《当代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4页。该书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进行了全面界定和阐释。从绿色变革的视角看,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绿色运动”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部分:以生态中心主义哲学观为核心的“深绿”运动,以经济技术手段革新为核心的“浅绿”运动,以及以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替代为核心的“红绿”运动——即绿色左翼运动。其中,绿色左翼主要包括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绿色工联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包容性民主理论、环境新社会运动理论等。政治意蕴。事实上,当今世界的绿色左翼政治运动也大都呈现出这种主体多元化的趋向,这在为运动本身带来强大活力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联盟主体之左翼属性的质疑。比如,欧洲左翼党内部最近争论的一个议题就是,多年来对女性群体或性别、环保议题的高度关注是否导致了对更广泛社会底层民众及其利益关切的忽视?甚至是否可以认为,对女性、自然、少数族群及其关切的过度强调使得整个左翼势力已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其阶级性本质,并忽略了与其他左翼政治力量的阶级团结?
针对这个疑问,笔者选取当代绿色左翼的重要理论分支——生态女性主义(2)“生态女性主义”一词由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西效·德·奥博尼(Francois d'Eaubonne)在1974年出版的《女性主义·毁灭》(Le Feminisme ou la Mort)一书中提出。她首次强调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将所有边缘群体(女性、有色人种、儿童、穷人)受到的压迫与自然界受到的压迫联系起来的政治理论。在她的影响下,以格里芬、麦茜特、米斯、萨勒等为代表的生态女性主义学者长期以来致力于从不同角度讨论这一联系,并据此阐述“女性-自然-原住民-少数族裔”等多元主体结成政治联盟的紧迫性和可行性。其中,作为其重要派别之一的“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由于明确承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地位,强调女性和自然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多重受压迫地位并主张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变革,因而属于绿色左翼政治的范畴。可以说,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对联盟主体的阐释深刻表达和体现了当下左翼理论关于多元主体联盟的思考和构建。为阅读方便,本文用“生态女性主义”代指“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对多元主体联盟的构建思路作为考察对象,试图探讨生态女性主义者们如何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来构建多元主体联盟,并据此回答这一构建过程是否确保了联盟的阶级性。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理论构想未必被现实政治所完全采纳和践行,但它对于绿色左翼运动当下的政治动员和未来的发展进路仍有着基础性作用,所以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具体地说,本文将依次从三个方面出发讨论生态女性主义对多元主体联盟的构建思路:基于重新界定的“再生产价值”的“女性-自然”联盟的政治经济学基础;资本主义体制背景下“女性-自然”联盟的政治哲学论证;“去欧洲中心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语境下联盟的区域和文化扩展。
一、“女性-自然”联盟的政治经济学论证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详尽考察了社会生产的总体运动过程,指出完整的社会生产过程包括“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再生产者的过程”,即人类物质生活资料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提出了“两种生产”的理论。依照马克思和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要想全面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就必须将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结合起来进行。
依此,生态女性主义认为,性别压迫或歧视和环境难题的成因就在于两种生产之间的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的根源就在于对人类“再生产劳动”及其价值的忽视。这里的“再生产劳动”,不仅包括女性的生殖劳动和养育劳动,还包括生产所有“生产资料”(包括自然生态环境)的劳动,涉及对所有人类和非人类动物、植物的生产与维护。(3)Terisa E. Turner and Leigh Brownhill, “Ecofeminism as Gendered, Ethnicized Class Struggle: A Rejoinder to Stuart Rosewarne,”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Vol.17, No.4, 2006, p.90.具体而言,这些学者从“再生产劳动”概念的阐释出发,首先批判性考察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域下对女性和环境价值的理解,然后构建了生态女性主义政治主体联盟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一)女性的“再生产劳动”
关于两性关系问题,马克思写道:“男人对妇女的关系是人对人最自然的关系。”批评者往往据此认为,这说明马克思习惯于运用抽象分析法将女性问题、两性关系问题“去社会化”,而没有正视女性的现实状况和真实需求。但生态女性主义强调指出,需要从女性所从事劳动的特点和现实社会实践等方面全面考察马克思对女性或女性议题的态度。因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女性的“再生产劳动”是极其复杂的,至少包括分娩、哺乳、抚养后代、教育、种植、烹饪、清扫房屋和处理垃圾等方面,而这可以大致划分为“生殖劳动”和“家务劳动”两个方面。
首先,生态女性主义者针对马克思的“生殖劳动”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虽然马克思认识到了“人类自身生产”的重要性、恩格斯也将“种的繁衍”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两者对生殖劳动的理解主要侧重于其为经济活动提供劳动主体和消费主体这一层面,这显然是不够全面或充分的。
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生殖劳动”并不是一个完全自愿的、性别中立的、无差别的既定“自然事实”或“社会事实”,而是被社会的、历史的、利益的和权力的关系所形塑的活动。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未能充分展现出来。比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人口增长之间关系的论述,就没有考虑到女性自身的生殖意愿。马克思关于人口论述的逻辑,建立在“生殖过程是一个纯粹生物学过程,可以随着经济发展而自行调节”这个基础之上,未能关注女性自身对生殖活动的反抗意愿,更没有将这种“反抗”纳入其阶级斗争理论中。而事实上,生殖活动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是被社会操控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否定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剥夺了女性生理和精神完整性的物质基础,将妊娠过程降级为一种被迫性的劳动。结果是,“女性经常被迫违反自身意愿进行生殖活动,经历了同她们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劳动、甚至是自己孩子的异化,这个异化过程比其他工人经历的异化还要深刻”。(4)Emily Martin, The Woman in the Body: A Cultural Analysis of Reproduction, Boston: Beacon, 1987, pp.19-21.
其次,生态女性主义通过马克思对劳动的阐述提出,在资本主义体制条件下,主要由女性承担的单调、重复、服务于家庭的家务工作一直以来都不被承认是“劳动”,尤其没有以获得薪酬的方式被承认。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力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可以看出,马克思所指的“劳动”,主要是工人工作时通过身体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去消费自然。而事实上,在照顾孩子、哺乳婴儿的过程中,女性也是通过自己的身体去消费自然,并将身体资源转化成为更高形式的存在。但是,工人对自然的消费能够获得资本主义薪酬制度的承认,而女性对自然的消费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薪酬。也就是说,单调、重复、服务于家庭的家务劳动虽然对国民生产总值具有基础性贡献,但一直以来都不被承认是“劳动”。
(二)自然的“再生产”活动
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自然的“再生产”活动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客观物质条件而开展的活动,二是自然生态环境的自我恢复和发展。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就已表达了对地下水污染、动植物保护等问题的关切,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这相对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来说是颇具前瞻性的。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关于自然的论述似乎也还存在另外一种不同的面相,而这种看似矛盾的立场往往会引起争议。
一方面,马克思承认,人与自然是共同进化的,人类在本质上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就说明,人类的生存依赖于自然,而自然也是人类的“直接的生活资料”。(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所以,人类作为自然存在物,必须通过劳动实现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以满足其生存和繁衍的需要。“劳动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4、102页。可见,马克思对物质变换过程的分析坚持了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基础性依赖关系。
但另一方面,马克思还说过,“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地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应的”。(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9页。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这里似乎把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视为人改造客观世界过程的一部分,即创造了一个“人类中心主义”性质的自然概念。(9)Pamela Odih, Watersheds in Marxist Ecofeminism,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4, p.li.
艾瑞尔·萨勒(Ariel Salleh)则认为,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或者说,这种倾向只是一种表象。她指出,马克思之所以会遭到这样的误解,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习惯性地从“生产”而不是“再生产”视角来理解自然的价值。“单纯的自然物质,只要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在其中,也就是说,只要它是不依赖人类劳动而存在的单纯物质,它就没有价值,因为价值只不过是物化劳动”。(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7页。可见,在马克思看来,没有人为因素参与的自然存在物是没有价值的。劳动作为可变资本被视为所有利润的来源,而自然资源作为永恒存在的资本,对于生产矩阵来说就没那么重要了。因而,“劳动价值论含蓄地将女性的再生产和恢复行为归为没有生产力的那一类”。(11)Ariel Salleh, Ecofeminism as Politics, London: Zed Books, 1997, p.74.
总的来说,生态女性主义者大都认为,她们对女性和自然价值的分析基于或遵循了马克思的劳动生产理论。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她们将“再生产”过程视为历史活动的起点,并专注于对女性和自然“再生产价值”的肯定性阐释。就此而言,生态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主要贡献就是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性别化或生态取向的阐释或“复位”。相应地,这种阐释也为其多元主体联盟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
二、“女性-自然”联盟的政治哲学论证
生态女性主义在批判性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发展出多元主义立场,逐步构建出一个反资本主义体制的、反社会压迫的和反父权制的多元主体联盟。这一联盟的核心成员是承担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被贬低和忽视的那些“再生产劳动”的社会主体,特别是处于双重被压迫地位的女性劳动者和其他相关劳动者。从政治哲学层面来看,生态女性主义对“阶级联盟”的重新阐释丰富和深化了绿色左翼联盟的主体构成。
(一)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和自然密切联系
作为一种立足于女性身体特点和具体劳动实践的理论,生态女性主义从来都不回避女性在生物学意义上同自然的天然联系。在它看来,由于身体器官特点和所承担的“生殖劳动”,女性确实拥有比男性更强的自然感知能力,从而形成了对自然的关爱品格。虽然这一对女性和自然联系看似“本质主义”的构建遭到了来自学界诸多方面的批评,但生态女性主义者们并没有放弃对这种生物学联系的强调。“女性和男性确实在存在主义意义上跟自然有着不同的联系,但承认这一点不是要说明女性在本体论意义上比男性离自然更近”,(12)Salleh, Ecofeminism as Politics, p.96.而是要立足于女性和自然之间的生物学联系,追溯女性被社会地“自然化”的过程,以及女性的“再生产劳动”是如何被历史地贬低和忽略的。
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就着重揭示了资本主义借由这一联系所发展出的对女性“再生产劳动”的历史性贬低。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与文化下,乳房和子宫作为生殖器官被视为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存在,不具有生产力;双手和大脑则恰恰相反。“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这种劳动的工具……是手和大脑,但从来不是女性的子宫或者乳房……因为人类身体本身被分解为真正的人类部分(手和大脑)和自然的动物部分”。(13)Maria Mies,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London: Zed Books, 1986, p.45.依此,通过乳房和子宫开展再生产劳动的女性代表了“自然性”,而擅长使用双手和大脑(理性)的男性则代表了人性和生产力。但实际情况是,女性在生殖活动过程中处在一个能够合理、理性利用自己能力的位置上,远非是被动的。而现实中对女性“自然性”的默认,看似合理地将女性的经济生产能力排除掉了。
(二)资本增值逻辑主宰下的女性和自然密切联系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女性和自然都被归结为被动的“他者”,归结为可以随时为资本增值提供服务的免费资源。结果是,主要由女性承担的“再生产劳动”就像空气、河流、森林和众多生物一样,成为无须报偿甚或考虑的外部性“生产条件”。
对此,詹姆斯·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做了较为深刻的分析,认为“资本耗尽生产条件”是资本主义的系统化趋势之一,其根源和表现就是资本不需要为再生产活动付出任何代价。(14)James O'Connor, “A Political Strategy for Ecology Movements,”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Vol.3, No.1, 1992, p.3.这一观点包括如下两个方面:首先,资本无须支付生殖劳动和家务劳动的费用,也不需要支付生态环境再生产的费用,而这意味着,生态环境必须由家务劳动和自然本身去再生产,否则自然将会走向衰败;其次,在经济危机期间,资本主义必定会进一步降低对再生产劳动的支付,同时还会加大对生殖劳动、家务劳动和生态资源的利用与盘剥。由此所导致的后果是:“自然资源将会持续走向枯竭;其他群体要代替资本去承担再生产代价,而从事再生产劳动的女性是这一群体的主要成员。”(15)Turner and Brownhill, “Ecofeminism as Gendered, Ethnicized Class Struggle,”p.91.就此而言,资本增值逻辑支配下的女性和自然之间存在着“双重联系”:自然为女性的生产和再生产劳动提供基础和条件;而资本对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侵占使自然和女性都受到剥削。
可以看出,奥康纳对“双重联系”的深入揭示,不仅确证了“女性-自然”政治联盟的必要性与合法性,还容纳了更为宽泛的联盟主体成员: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受剥削和压迫“他者”的代表,即女性与自然之外的其他受压迫或歧视群体。
三、“女性-自然”联盟的区域与文化拓展
生态女性主义清醒地认识到,女性和自然受压迫的根源在于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并且这种资本主义制度有着一种深度嵌入或欺骗性极强的意识形态根基。由于这一意识形态根基的标志性元素就是那个建立在贬低并压迫“他者”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欧洲中心主义文化,所以生态女性主义认为所有在欧洲文化、殖民文化下从事“再生产”劳动的“他者”们都属于被压迫的阶级,力图据此推动绿色左翼主体之间的区域联盟、文化联盟。
(一)否定“再生产”价值的欧洲文化传统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是二元对立的欧洲中心主义文化的必然现象,因而构建女性和自然的政治联盟关系必须从解构这种二元对立意识形态入手,尤其是阐明这种严重性别歧视性、社会非公正的文化理念及其社会经济模式是如何被建构出来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适性“逻辑”的。
欧洲中心主义文化的特征之一是只关注有效性或无效性。在这种思维逻辑下,男性的生产性劳动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女性和自然的再生产性劳动被认为是无价值的。女性和自然因此被归为“他者”,成为“次级”存在,而对“他者”的否定在本质上就是对“再生产力”的否定。由于男性缺少与“再生产活动”相关的意识和能力,所以只能回避“再生产”问题,并压制与“再生产”相关的主体,将其归类为“他者”。结果是,“他者”沦落为创造经济价值的工具,比如,女性、动物、自然资源都被当作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而男性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压制“他者”、重获“自我”所带来的愉悦,并将这种愉悦升华为以“生产力”为判断标准的“男性气质”。因而,男权和货币市场以“生产力”为搭扣,形成了一种以占有和支配“他者”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父权制面相。
(二)殖民文化支配下的多元受压迫群体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正是在欧洲中心主义文化的支撑和资本增值逻辑的催生下,欧洲资本开启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对全球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掠夺,发展出资本主义殖民文化,并催生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
具体来说,“殖民体系下的劳动力管理模式、出口导向的生产模式、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和国际劳动分工等,共同塑造了资本主义阶级关系”。(16)Silvia Federici, “The Devaluation of Women's Labour,” in Arial Salleh, ed., Eco-sufficiency and Global Justice, New York: Pluto Press, 2009, p.59.借助国际劳动分工,殖民体系把为欧洲提供“生活消费品”的奴隶劳动整合进了欧洲劳动力的“再生产”之中,削减了欧洲劳动力的必要成本。与此同时,处在这种劳动分工下的城市工人的工资,又促进了奴隶生产的产品走向市场。在这种系统化的奴隶制和工资体系的支持下,资本主义实现了规模上的巨大飞跃。对殖民地的原住民和奴隶来说,资本主义剥夺了他们的耕地和栖息地,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他们的劳动报酬;而对欧洲工人来说,他们的劳动中未能得到薪酬的那部分比重更大了,因为其工资水平和合法地位都受到了挑战。而由于这些剥削和压迫都是建立在忽视再生产劳动及其价值的基础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工人阶级、奴隶、原住民、女性和自然所受到压迫的逻辑内核是一致的。因而,第三世界原住民和少数族裔的劳动和生存现状以及政治抗争,已经成为思考资本主义环境危机深层原因及其社会政治解决路径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层面。
对此,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经典性的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分析。她认为,在印度,几个世纪以来女性都在亲自参与粮食种植和居住地维护,而正是在这种良性互动之下,社会与生态系统得以健康发展。然而,经济作物和现代种植技术的引入,破坏了传统的土地使用权,剥夺了男性劳动力以及女性对传统生产方式的掌控,打破了“自然-女性-劳动”良性关系链,造成了本土化的饥饿和生态退化问题。而所谓的各种环境修复政策,不过是打着环境友好的幌子,以科技、经济手段行资本主义牟利之实。“欧洲中心主义的科学和经济自负地绘制了一个线性的、还原论的、依赖管理的逻辑,来对抗自然的周期性变化,却无法达到其预期目的,而所谓的‘绿色变革’就是例证”。(17)Vandana Shiva, Staying Alive: Women,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Zed Books, 1989, p.45.因为,“绿色变革”所采用的经济和技术手段,不仅引发了更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还在本质上破坏了自然生产力。此外,这种生产力的衰败使男性遭受到巨大挫折,并将其面临的压力宣泄在妇女身上,演变成针对女性的社会流行暴力。依此,她强烈建议第三世界女性运用本土知识体系抗拒欧洲中心主义文化,从二元价值观走向多元价值观,构建一种基于环境、女性、原住民、少数族裔等有机联系的新的发展观。
综上所述,对于米斯、萨勒、席瓦等生态女性主义者来说,在全球化背景与语境下,女性问题、环境问题、种族歧视或非正义问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相应地,原住民、少数族裔等社会群体理应被纳入未来绿色变革的主体力量网络或联盟之中。也就是说,生态女性主义的“女性-自然”联盟是一个包括众多群体成员的复数或链条。
四、评 论
生态女性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从“再生产劳动”及其价值的重新阐释出发,系统揭示和彰显了女性和自然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中被忽视甚或贬低的客观现实,并希望依此构建一个类似“女性-自然-原住民-少数族裔”联盟的社会政治抗争主体集群。这些群体的共同之处是,她们长期以来都被排除在资本主义薪资以及保障体系之外,她们所担负的再生产性劳动大都不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承认,并因而受到资本主义体系的多重盘剥;相应地,她们的社会政治诉求(比如绿色环保、女性解放、全球正义等)恰好表达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社会关系、经济生产计量及其管理中亟待调整甚或重构的一些基础性方面,尤其是如何充分关注全球化时代社会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劳动者及其权益公正分配,从而创建一种更加和谐的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就此而言,这种多元主体联盟的理论构建与社会政治动员无疑拓宽了当代绿色左翼政治的时空想象,尤其是社会政治行动主体的视野,也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唯物史观。
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来看,这种多元主体联盟的理论构建及其社会政治动员也存在诸多先天性的缺陷,其核心则是对左翼阶级身份或政治团结的弱化:第一,它在理论上主要是基于对家庭活动、两性关系、边缘地带(群体)等在“再生产”过程中独特作用的探讨,而这或多或少造成了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重视程度不够、批判力度也有些欠缺的局面。第二,从政治联盟本身的实力来看,“女性-自然-原住民-少数族裔”的这个长链条联盟虽然看似人多势众,但严格来说并不具有实质性挑战或替代当前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和全球秩序的能力。可以说,它的一个重要结构性缺陷就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架构和领导群体,而这本来是传统的左翼政治或工人运动的优势。也就是说,弱化或失去了与工人运动密切联系的多元主体联盟,其实未必会变得更强大。第三,新社会运动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政治动员方式,虽然看似强化了这一政治主体联盟内部的民主质量和本土地方特色,但几乎肯定会带来政策共识达成和行动战略举措落实上的难题。而长期性的议而不决或多次性的无果而终,对于这一联盟的可持续发展乃至生存都将是一个严肃的挑战。
笔者认为,新社会运动强调新左翼政治的主体多元性和异质性固然重要,但基于“阶级性”或“阶级意识”的深度聚合对于主体联盟构建来说更为根本。“阶级具有一种其他压迫维度所不具备的战略或粘(黏)合功能。它可以把不同维度下的所有抗争群体联合起来,聚合成一种团结的力量,因为它们都受到当代社会中最为集中的权力——即资本——的胁迫”。(18)维克多·沃里斯:《交互性的粘合剂:阶级的政治优先性》,《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1期,第63页。在德国卢森堡基金会主办的马克思200周年纪念大会上,“新阶级政治”议题及其广泛讨论就充分体现了左翼政治内部对阶级斗争、社会经济结构性变革等传统主题的回归。许多与会者“要求切实重新走近广大的工人阶级或劳动者,聆听并反映、代表他们的利益关切与政治诉求,其中包括适当纠正左翼政治长期以来对女性主义和生态环境议题政治的偏爱”。(19)郇庆治:《政治·理论·社会主义:柏林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述评》,未发表。
总之,生态女性主义对于“女性-自然”等多元主体联盟的理论构建和实践努力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要想在社会现实中切实推进对女性、自然、原住民、少数族裔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重要群体的价值认可与社会承认,还必须更多考虑与主流性左翼政党和社会政治力量的基于阶级意识和团结的共同行动。而对于当下看似轰轰烈烈的新一波绿色政治抗争风潮的成效与前景,我们也可以大致做这样一种预估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