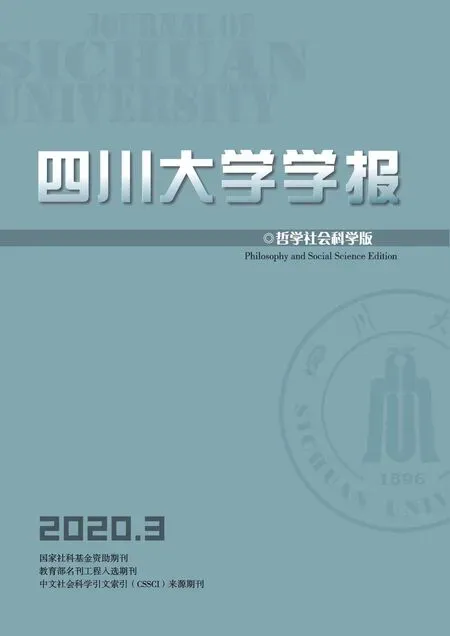“白莲教”质疑:无时不在抑或子虚乌有
2020-12-26刘平
刘 平
“白莲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响亮的名号,研究中国宗教史、秘密社会史与农民战争史的学者尤为关注,不仅经常使用,而且时加探究。100多年来,关于白莲教的创教源流、信仰体系、组织结构、发展演变等具体问题的研究,革命家与学者颇多论述,也存在诸多争论,但很少有人质疑“白莲教”之有无。
自“白莲教”一词出现以来,“白莲教”与“邪教”“异端”是划等号的。由于传统专制王朝的意识形态偏见,明教(转入地下的摩尼教)、白莲宗(净土宗异端)等教派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后,就开始了“被妖魔化”的历程,被贴上“吃菜事魔”“魔教”“白莲菜”“邪教”“反动会道门”等标签。新中国建立之初,一方面要摧毁“旧世界”的信仰遗产,故有取缔反动会道门等运动;另一方面,因为要确立农民为主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政权的合法性,特别抬高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多与宗教或宗教异端有关),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得以繁盛数十年。改革开放后,“农战史”日渐冷落,至20世纪90年代末,以镇压法轮功为主要内容的“反邪教运动”大规模兴起,所有带有“白莲教”“封建迷信”色彩的教派、气功团体、观念又被打回“邪教”原型。
在遥远的西方,一位荷兰学者独辟蹊径,专注于“白莲教”,对这一国人司空见惯的名词或概念提出质疑: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白莲教”这一教派吗?白莲教究竟是一个虚拟的通称,还是一个实在的个体,抑或只是一个施加迫害的标签?(1)Barend J. ter Haar, 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初版于E. J. Brill, 1992;再版于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该书书名直译为《中国宗教史上的白莲教》,中译本出版时,定名《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田海在该书导论部分提出了几个重要概念,成为我们理解其观点的基础:1.宗教“运动”——拥有共同的、独具特色的宗教信仰和活动内容的这类宗教团体,被称为宗教“运动”(movement)。2.宗教“传统”——本文立足于学术史发展脉络,将梳理以杨讷为代表的白莲教存在论、马西沙的白莲教阶段论与田海的白莲教否定论,并作出相应的评价。
一、以杨讷为代表的传统观点
许多宗教团体、甚或是单个的人,会拥有共同的宗教理想,虽然其表达方式不同,但是如果他们的共同理想足够明显,作者就会使用“传统”(tradition)一词。3.“教”——在宗教历史上,宗教导师总是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以书面或口头形式留下了一系列信仰和规矩(teachings)。田海想使“教”这个词语恢复其本来意义,即由传教者或其弟子留下来的经文教义。参见田海:《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第12-14页。中译本由刘平、王蕊翻译,列入刘平、(美)裴宜理主编的“中国秘密社会研究文丛”(商务印书馆2017年11月)。按,本文写作时,使用的是英文版及其页码;中译本标注英文版页码,可参考。
传统观点认定“白莲教”是一个统一的教派或一个通称,民国时期以陶成章、向达、陶希圣等为代表,1949年后以李世瑜、杨讷等为代表。(2)有关白莲教的研究论著,新中国建立前有陶成章:《教会源流考》(1908年),后收入《浙案纪略》,1910年(现据《陶成章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向觉明(向达):《明清之际之宝卷文学与白莲教》,《文学》1934年第2卷第6号;陶希圣:《元代弥勒白莲教会的暴动》《明代弥勒白莲教及其他“妖贼”》,分别载《食货》1935年第1卷第4期、第9期;陈觉玄:《白莲教抗元运动与大明王朝的建立》,《大学月刊》1945年第4卷第5-6期。新中国建立后主要有陈诗启、郑全备:《试论清代中叶白莲教大起义》,《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方庆瑛:《白莲教的源流及其和摩尼教的关系》,《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5期;李世瑜:《青帮、天地会、白莲教》,《文史哲》1963年第3期,以及《白莲教正义》,《历史教学》1987年第9期;夏家骏:《清代中叶的白莲教起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蒋维明:《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王兆祥:《白莲教探奥》,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杨讷:《元代白莲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港台地区主要有李守孔:《明代白莲教考略》,包遵彭编:《明代宗教》,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庄吉发:《清代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及其支派》,《台湾师大历史学报》1980年第8期;宋光宇:《中国秘密宗教研究情形的介绍(二)——白莲教》,《汉学研究通讯》1988年第7卷第2期;戴玄之:《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黄景添:《白莲教与明代建国》,香港:中华书局,2007年。在海外学者中,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韩书瑞(Susan Naquin)、吉冈义丰与野口铁郎等也基本持此论。(3)Daniel L. Overmyer, Folk Buddhist Religion: Dissenting Sect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中译本:欧大年:《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刘心勇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Susan Naquin, 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中译本:韩书瑞:《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陈仲丹译,杭州: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吉冈义丰:《现代中国之诸宗教——民众宗教之系谱》,东京:佼成出版社,1974年(台湾改名《中国民间宗教概说》,中国台北:华宇出版社,1985年);野口铁郎:《明代白莲教史之研究》,东京:雄山阁,1986年。关于白莲教的英文博士论文有:Yung-deh Richard Chu, An Introductory Study of the White Lotus Sect in Chinese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1967. Cecily Miriam McCaffrey, Living through Rebellion: A Local History of the White Lotus Uprising in Hubei,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2003. Wensheng Wang, White Lotus Rebels and South China Pirates: Social Crises and 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Qing Empire, 1796-1810,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2008.虽然这些学者在具体表述上存在诸多差异,但总体上认可中国宗教史上存在“白莲教(派)”或者“白莲教系统”。(4)国内主流辞典基本上认定白莲教是一个统一教派,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18页;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25-426页;郑天挺、吴泽、杨志玖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815页;《辞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修订本重排版,第2364页。
在诸多研究著作中,杨讷的《元代白莲教研究》可谓传统观点的代表,最具影响。总体上看,杨讷认为“白莲教”是事实上存在的宗教教派,“白莲宗”与“白莲教”并无本质上的不同,白莲宗就是白莲教,是一个新的佛教宗派。而“白莲教”与“白莲社”有联系也有区别。茅子元所创的白莲宗与之前的白莲社一样,崇奉阿弥陀佛,以往生净土为修行宗旨,强调“自信自行,自修自度”,(5)普度编:《庐山莲宗宝鉴》卷6,《修进功夫》,杨讷:《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1页。故白莲社与白莲宗-白莲教存在信仰上的共同关系,但两者之间没有组织关系。白莲教确立了较为严密的师徒关系和宗门关系,以“普觉妙道”四字为“定名之宗”,确立分散在各地的信徒之间的宗门关系。并说茅子元创建的“白莲教”可以称作“白莲社”,但在茅子元之前建立的“白莲社”却不能称作“白莲教”。(6)杨讷:《元代白莲教研究》,第24、115页。按,《元代白莲教研究》系杨氏相关研究之集成。实际上,杨氏很早以前就发表了颇有影响的《元代的白莲教》,载中国元史研究会主办的《元史论丛》第2辑,1983年,以及出版《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1985)、《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1989)等。他考虑了“白莲教”出现之前的情况,却没有分析“白莲教”出现之后,依然有诸多并未遭到朝廷迫害的“白莲净土”信仰者存在于明清社会之中(田海称之为“白莲传统”)。近年有学者称,“明末无异元来、紫柏弟子钱士升还对《庐山莲宗宝鉴》赞叹有加,宣德四年更将之编入藏经等等资料显示,(茅)子元所创的白莲宗,应有为教界其他人士所肯定的面相未被学者挖掘出来”。(7)释印谦:《白莲宗析论》1,《圆光佛学学报》2000年第5期,第47页。
明清官府与佛教正统以及后来研究白莲教的学者把元朝及其后来出现的各种以“白莲”为名号的结社均视为白莲教,杨讷归纳说:“元代白莲教(白莲宗)情况很复杂,其称谓也不仅是莲宗和莲教,还称白莲社(《元史》记至大元年‘禁白莲社’)、白莲会(杜万一‘指白莲会为名作乱’),指的都是以白莲为名的宗教社会。我们还在《大明律》中看到,明初仍称白莲教为白莲社。白莲教(宗)的派别、信仰,并不以称宗称教或称社称会标志出来”; “‘白莲教’和‘白莲宗’都是历史上的称谓,其内涵是那时已经确定了的,不能根据我们今天的需要另作规定”。(8)杨讷:《元代白莲教研究》,第188、187页。尽管如此,我们从杨讷的论述及相关史料中,看到的是白莲宗有“莲教”之自称,并无“白莲教”之自称;自称“莲教”自然没有贬义,后来指称的“白莲教”则等同于“邪教”。两者不是一回事。
承继杨讷的元代白莲教研究,喻松青对明清时期的白莲教进行了探讨。喻松青认为明清时期的“白莲教”既是一个单独的教派,也不断融合其他教派,是一个通称。她认为,“明代的‘邪教’,除白莲教外,还有其他教派,尤其是万历以后,教派林立,名目繁多”,但是,“各个教派的渊源和思想,有所不同。有的是从元末明初直接传下来的白莲教,有的是白莲教的支派或和白莲教有关的(如滦州王森的闻香教);有的和白莲教本来不同,有所区别,自成系统,但逐渐白莲化了的(如山东即墨罗静的罗教);有的则已不可考。不过总的说来,各教派的信仰、组织等情况是大同小异的,原来差异较大的,也逐渐趋归一致,互相混同。所以我认为这些所谓的‘邪教’可以用白莲教总其名”。(9)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第11-12页。凡为“教”或“教派”者,必有创教源流、教主、教义等基本要素,喻氏语焉不详,一蹴而就于“白莲教”,乃习惯使然,与前述杨讷的“白莲教(宗)的派别、信仰,并不以称宗称教或称社称会标志出来”观点一致。
而且,她在行文过程中对“白莲教”“白莲菜”“白莲社”“白莲会”等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是不加区别的,如“教徒有妻子,半僧半俗。他们谨戒杀生,严避荤酒,茹素念佛,男女一起集会,忏悔修行,号白莲菜”;“后来朝廷将茅子元问了妖妄惑众的罪,流放江州(江西九江),白莲菜被取缔。元代的白莲教,除仁宗时一度受到朝廷的承认和护持,曾公开传教外,仍属严禁之列”;“洪武十九年(1386年),新淦彭玉琳,‘自号弥勒佛祖师,烧香聚众,作白莲会,……谋为乱’”。(10)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第3-5页。这些是自称还是他称?标签还是实质性结社?含混不清。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因袭“朝廷”思维,对于诸多史料未加以仔细辨别。
与杨讷和喻松青不同,连立昌认为南宋时期茅子元建立的是“白莲宗”。白莲宗在元代中期发生分化,下层白莲道人因不满社会现实,在教义中引进了弥勒救世思想。在元末,这种变化了的白莲宗(会)与元以前的佛教异端弥勒会(含香会)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白莲教,属于“元末衰世的产物”。白莲教形成之后的发展情况如何呢?连立昌的表述似有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他指出明初不断有白莲教起义,如彭玉琳、唐赛儿等;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在明初高压政策下,民间秘密教门中人忌讳白莲教这一称呼,没有人自称为白莲教。这其中既有本身就不是白莲教的唐赛儿,也有本身就是白莲教的张普祥。所以明代的“白莲教”仅仅是一个泛称,实际上已经没有一个以此命名的教门了。进而,连氏将新出现的众多教名进行了分类,认为除了避讳之外,部分新的教名在教义上有了新发展,其实就是出现了新的教派。除了白莲教色彩浓厚的教派外,还有佛教禅宗倾向和道家倾向以及取义不明的一些教派。这些教派采取“三宗五派”“九杆十八枝”等细胞分列式的组织形式也是元代白莲教所不曾有的。(11)连立昌、秦宝琦:《元明教门》,谭松林主编:《中国秘密社会》第2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80-85、119-121、378页。
关于清代的情况,1981年出版的《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因循传统说法,将这次大规模农民起义认定为白莲教起义。(12)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室、资料室编:《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1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编例”第1页。按,清廷称呼此次起事者为“教匪”“邪匪”。学界也多沿袭这一说法,将这次起义称为“川楚白莲教起义”。20世纪90年代,从马西沙开始,由“白莲教”发动这场起义的说法遭到质疑,后来有学者进一步展开研究,认为起义系清代新兴教派所发动,如秦宝琦认为是“混元教与收元教所发动”,(13)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第1卷《清前期秘密社会》,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年,第210页。曹新宇则认为由收元教发动,与白莲教无关。(14)曹新宇等:《清代教门》,谭松林主编:《中国秘密社会》第3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5页。他们没有从宏观上否定白莲教,只是在具体个案上展开研究,这也是近年来民间宗教研究的一种趋势。
二、马西沙的修正
马西沙在其与韩秉方合著的《中国民间宗教史》(1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初版1册,2004年修订版上下册。第二章“弥勒救世思想的历史渊流”中对白莲教、元末农民起义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梳理,稍后他对以杨讷为代表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批评,其观点主要体现在《白莲教辩证》一文:1.白莲教是弥陀净土宗与天台宗混合的世俗化教派;2.元末农民起义应该称为香会起义(或香军起义);3.明清民间宗教不应统称为白莲教。我们可以把马西沙的观点归纳为“白莲教”阶段论,也就是说,历史上确有名为白莲教的教派(弥陀净土宗与天台宗混合的世俗化教派),主要存在于元代前中期,一般认为的元末白莲教起义实为香会起义,要分清白莲教与其他民间宗教的界限。(16)马西沙:《白莲教辩证》,《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第1-13页。
关于白莲教,马西沙认为:“茅子元创白莲菜的时代,尚不完全具备‘邪教’特点和组织体系,仅为一异端的净业结社组织。只是到了元代,才形成分化,一部分白莲道人发展了茅子元宗教理论中的异端成分,并把组织体系完全独立化,逐渐形成了白莲教。”(17)马西沙:《白莲教辩证》,《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第1页。进入明清时代,“白莲教”已不复存在。换言之,真正的白莲教只存在于元代。这一观点与连立昌很接近,区别在于连立昌提出白莲教形成于元末。
马西沙与杨讷的主要分歧在于对白莲教与弥勒净土信仰关系的认识,由这一认识上的差异又引出两人关于元末农民起义是白莲教起义还是香会起义的争论。
在分析白莲教与弥勒净土信仰关系时,杨讷指出,“在元代渗入白莲教并且终于使它大为改观的是弥勒净土信仰;更准确地说,是‘弥勒下生’故事”。他认为,“弥勒和弥陀毕竟是有不解之缘的,弥勒的名字在主要的弥陀经典中屡屡出现,阿弥陀佛的许多神异就是通过释迦与弥勒的对话介绍出来的”;“白莲教渊源于弥陀净土,弥勒在白莲教徒的信仰中自然也占一席之地”;“由于弥勒、弥陀难分难解的亲缘关系,一部分白莲教徒可以毫不费力地接过‘弥勒下生’传说来为己用。‘弥勒下生’只是宗教幻想,没有确定的社会内容,它可以被利用于不同目的”。(18)杨讷:《元代白莲教研究》,第128、131-133、134页。从逻辑上来说,杨讷之论可以成立,但从元末实际情况而言,崇奉弥陀净土的白莲教为何以弥勒净土的“弥勒下生”、摩尼教(明教)的“明王出世”为号召,必须以证据说明,否则属于想当然。
至于马西沙所说元末农民起义是香会主导的观点,我们从佛教史、净土宗演变的实际情况来看,弥勒和弥陀是两种不同的信仰,不能随便改“宗”;所谓元末“白莲教起义”并没有以“白莲宗”的弥陀为号召,而是以明王、弥勒为号召;弥勒如何渗入弥陀,让元末“白莲宗”忽然改观,至今仍然是一个谜。马西沙无法解开这个谜,只好从所谓的“香会”寻求突破,不幸的是,“作者证‘白莲教’与其他民间宗教之异同,其基本依据还是在白莲教的规定性上”;“作者所以要否认白莲教曾受到其他民间宗教特别是摩尼教、弥勒信仰的影响,是因为一旦承认,那么元明清时代打着‘弥勒下生’旗号、烧香聚众者就不能在弥勒信仰与白莲教中被区分开了,作者也就无从提出创见(即马西沙氏提出‘香会’‘香军起义’用以取代‘白莲教’‘红巾军起义’的观点。笔者注)”。(19)张传勇:《白莲教的名实之辨——读〈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70页。
正是从弥勒和弥陀不能随便改“宗”的立场出发,马西沙认为,弥陀净土信仰是白莲教的根本信仰,凡是信仰弥勒而不是弥陀的教派均不能视为白莲教:“明中叶仍有‘白莲教’活动,但这些‘白莲教’并不信仰弥陀净土思想,大都以弥勒下生为号召,这种‘白莲教’仅有白莲教之名,而无白莲教之实了。本质是弥勒教的信仰了。”他列举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李福达“白莲教案”,“这种‘白莲教’不但与宋茅子元所倡白莲教迥然不同,与元代普度的白莲教也没有任何内在联系了。明代诸多所谓‘白莲教’大抵应作如是观”。明代成化、正德年间创立的罗教,“其教义既不同于向往西方极乐世界的白莲教,也不同于倡弥勒下生的弥勒教”,罗教所开创的信仰世界是“白莲教”所难以包容的。不仅如此,“明、清时代,多类民间教派还受到道教内丹道的启迪与滋养,众多的教派都以内丹道作为修持的根本,这种特点更与白莲教迥异”。除了弥勒信仰之外,马西沙还提出“无生老母”和“三世应劫”观念也不能算到白莲教体系;林兆恩的“三一教”、刘沅的“刘门教”与张积中的“黄崖教”是由知识分子的学术团社转化而成的民间教派,更不能视作白莲教。(20)马西沙:《白莲教辩证》,《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第8页。
关于白莲教的最终归宿,马西沙认为白莲教在明清时代已经消失,“人们再也找不到一支真正以弥陀西方净土为信仰,以家庭寺院为组织,以普、觉、妙、道为道号的白莲教了。宋、元时代的白莲教,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已经融进了波澜壮阔的民间宗教运动的大潮之中,已不具备主宰的地位了”。当然,部分民间教派也受到了白莲教的影响,比如以“普”为号。(21)马西沙:《白莲教辩证》,《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第9页。那么,《明史》与《明实录》等官书记载的明前期出现的大量白莲教起义及其以后出现的无时不在的白莲教案件又该如何对待呢?官府、文人与百姓可不管你是弥勒还是弥陀的啊!
至于元末农民起义是否为白莲教起义,杨讷依据《元史》指出,“栾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颍上之寇,始结白莲”,这两条记载无论是“白莲会”还是“白莲”,指的都是白莲教。(22)杨讷:《元代白莲教研究》,第158-159页。而马西沙认为元末农民起义是香军起义。虽然元末有一大批白莲教徒参加了起义,甚至成为骨干成员,但是白莲教并非起义的主力和倡导者。白莲教的弥陀信仰在这次起义中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这次起义的首倡民间教派是香会,即弥勒教会和摩尼教的混合教派。所谓“弥勒教”,按百度百科词条云:弥勒教最早于梁武帝时期创立,创始人傅大士,其后数百年间,不断吸收佛教、道教、摩尼教诸教部分思想,最后形成白莲教。笔者认为,这是一个笼统而无意义的解释,傅大士是佛教本土化的一个关键人物,颇多创见,不限于解释弥勒;佛经中早有《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但说傅大士创建弥勒教则毫无依据;有些人还把北魏法庆之乱、北宋王则之乱直至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指为弥勒教发展的线索,更是附会之言——把历史上弥勒信仰的一些现象想象成一个实体性的“弥勒教”了。
除了元末起义,马西沙还否定了明清时期诸多重大民间宗教教派的起义是白莲教起义。如明末徐鸿儒起义是闻香教起义,清中期川陕楚等五省农民起义是混元教和收元教起义,嘉庆十八年的起义是八卦教起义。(23)马西沙:《白莲教辩证》,《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第9页。这种以个案实证研究来推翻笼统而模糊不清的成见具有积极意义,但正如笔者在上面提到的,他没有解释为何会出现这种白莲教无时不在的现象。
故而,马西沙的观点,对于辨明传统所说的元代白莲教、他本人使用的香会或香军,与明清民间教派的区别是有帮助的,但他没有说明明前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白莲教”起义与案件,即使是在明中期至清代依然如故。
三、田海的观点
(一)“白莲教”的概念史研究
1992年,当时任教于荷兰莱顿大学的田海教授(24)田海现任德国汉堡大学教授,他1984年于荷兰莱顿大学毕业后,即留校任教。1990年,他在许理和(Erik Zürcher,以及韩书瑞)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2008年至2018年,他先后任德国海德堡大学中国社会与经济史C3教授、莱顿大学中国历史教授、牛津大学邵逸夫中文讲座教授等职。田海对文化史与宗教史有浓厚兴趣,此外,还广泛研究种族认同、暴力与恐慌、社会组织等问题。他认为宗教维度是中国传统生活的中心,而传统文化与文化模式至今仍然发挥着影响。田海目前较重要的研究著作有三部:第一部为199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第二部是《中国三合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The 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 Creating an Identity,Leiden:E. J. Brill,1998);第三部是《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代罪》(Telling Stories: Witchcraft and Scapegoating in Chinese History,Leiden:E. J. Brill,2006)。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一书。与中国学者研究断代或专题之类的视角相比,该书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将以往零碎的有关白莲教概念的辨析集中起来,将白莲教的语义分析置于从两宋至清末这一长时段的历史语境之中,对白莲教进行了概念史的重构。(25)田海的研究代表了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史学研究开始关注一些重要概念的语义变迁,逐渐形成概念史。李宏图认为,“概念”在“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时间性和多重性日益受到思想史家们的重视,由此逐渐开辟出了概念史研究,并成为具有独特理论和方法支撑的专门领域。其主要内容是通过研究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接受、转移和扩散来揭示概念是如何成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核心,讨论影响和形成概念的要素是什么,概念的含义和这一含义的变化,以及新的概念如何取代旧的概念。实际上,重点是要研究在不同的时期,概念的定义是如何发生变化,一种占据主导性定义的概念是如何形成,概念又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被再定义和再概念化。同时,又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概念的转换,甚至消失,最终会被新的概念所取代”。参见李宏图:《概念史:历史研究的新进展》,《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1月7日,第3版。田海借鉴了西方学界有关种族歧视研究所使用的“标签”(label)与“成见”(stereotype)两个术语,指出宋元时期存在“白莲传统”及“白莲运动”,这一传统原本具有积极的意义并被作为“本名”使用,后来逐渐变为模式化的邪教与叛乱意义的标签——“白莲教”。所谓“白莲教”是官方与文人逐步建构的概念,事实上并不存在,只是一个“假名”。另一方面,宋元时期的白莲运动被继承下来。无为教继承了“旧式的非精英大众层面的白莲运动”,“明末僧人祩宏、憨山德清、紫柏真可(达观)所领导的精英民间佛教运动,则继承了文人学士层面的白莲社”。而“民间佛教徒使用道人或道民的名号,领导或发动公共福利建设(比如建桥)”(26)田海:《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第218、219页。则是第三类继承,即比较分散的继承。
借用“标签”和“成见”的概念对白莲教历史进行分析,与传统的研究有很大不同。以“夜聚明散”和“吃菜事魔”为例,传统观点的代表者杨讷侧重于解释原因与考证史实。关于“夜聚明散”,他指出,“因为教徒中有许多是劳动群众,他们白天需要干活谋生,故而夜间参加宗教活动”,“但是,由于聚的多半是下层人民,又是在夜间,官府难以督查,因而也给各种性质不同的反官府力量提供了活动机会,成为他们组织群众、酝酿闹事的场所,而闹事的顶点就是造反。这在官府看来自然是邪道,但我们不应这样看,因为这同密传生死、乱说灾祥之类是不同性质的事”。关于“吃菜事魔”,杨讷批驳了吴晗关于宋元之际明教与白莲教已经混合的论断,指出:“明教本就含有佛教成分。但白莲教与明教除了源头上有点关系,可说是互不相涉。”(27)杨讷:《元代白莲教研究》,第76、114页。而在田海看来,“夜聚晓散”“男女混杂”“吃菜事魔”这三个词就是一种“成见”,“被用来贬损这类宗教现象,而非描述。因而,这些词语传达的信息只是使用者的态度问题,而无助于我们对宗教现象本身的理解”。(28)田海:《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第13页。田海的分析很有道理,杨讷所谓劳动群众“夜间参加宗教活动”,当然最有可能参加的是政府认可的佛道之类宗教活动,怎么会变成贬义而且违法的“吃菜事魔”呢?
除了借用概念外,田海还建构了一些重要概念。如“许多宗教团体、甚或是单个的人,会拥有共同的宗教理想,但他们对于理想的表达方式,无论是宗教的还是社会的,可能会千头万绪。如果他们的共同理想足够明显,我就会使用‘传统’(tradition)一词”。作者用“白莲传统”(White Lotus tradition)或“文人理想”(literati ideal)来指代文人类型的团社,而平民类型的集会具有大量鲜明的特征,被冠以“白莲运动”(White Lotus movement)。(29)田海:《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第11、49页。
田海强调,“我们不仅要关注宗教现象本身的变化,还要关注名称使用的变化。对于白莲教名号的研究将产生一个解释性结果——不仅要解释其中所包含的不同内容(这方面已经被很多学者关注),还要研究人们使用这一名号时所处的历史及社会背景”。在对宋元时期白莲运动的历史与社会背景的分析中,田海批评了以往学者的做法:“如果史料的可靠性极高的话,后来的史料可被用于稍前的时代,可把它们看成是同一时代的史料,这种史实要么发生在稍早的时代,要么同处于大的宗教背景之下。同样道理,不同地域的史料,也可相互结合起来使用。”通过分析,田海认为,“宋元时期,念诵佛号、咒语与佛经是世俗佛教居士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希望,这样做可以使他们在现世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并且坚信这种抽象的虔诚也能带给他们长远的好处”。与此相关的是元代僧人普度卫教的问题,“由于白莲传统所拥有的诸多内容类似当时的世俗佛教,那么普度所批评的那些信仰与实践,并不是白莲运动所特有的”。(30)田海:《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第9-10、5、45、72页。
(二)“白莲教”——建构的概念
与传统观点“元末白莲教大起义”以及马西沙的白莲教徒融入元末“香军起义”不同,田海指出,“旧式的白莲运动,以及滋养它的白莲传统,在元末起义时期依然十分活跃。当时之人从未把它与元末起义相联系”;“白莲教与韩山童所引发的元末红巾军起义之间有确切联系,是在很晚以后的事情。到明末时,红巾已成为数不胜数的宗教起义的一个显著标志,但是没有人直接把它与白莲教相联系”;“据我所知,最早提到白莲教与元末起义之间存在明确关联的,是在描述1796—1804年的‘白莲教’起义之时,它把白莲教的根源追溯到元末的红巾军起义”。也就是说,所谓“白莲教”的历史是后人逐步建构完成的,“(清中叶‘川楚白莲教起义’时)刘之协与其他人的供词记录十分关键地证实了人们既存的‘理解’:白莲教是‘隐藏于其后’的。在供词记录的誊抄和总结的过程中,后来的作者省去了教派的本名,而代之以白莲教这一名号。在总结性的供词中,大量的重要信徒都把白莲教这一名号作为本名,这种有选择性的抄写行为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种印象:白莲教就是本名”。(31)田海:《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第88、89、194页。
在田海看来,白莲教这一名号在明代中期开始成为一个贬损含义的“标签”,“无论这个被贴上标签的现象与之前旧式白莲运动或白莲传统有多少相似之处,它都已经与这一名号被使用的内涵毫不相干了”;“白莲教这一名号不断地被与叛乱、低级的幻术、危险的‘末劫观’(不只是弥勒教)甚至还有业镜等现象联系在一起……。在1525年之后,白莲教这一名号用于‘解释’大量互相之间并无关系的各种宗教与幻术团体所带来的威胁”。(32)田海:《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第127、128页。那么,“白莲教”是如何成为一个贬损含义的“标签”呢?
田海考察了“白莲教”名号传播中的人际网络,“对白莲教及异端观念的形成起重要作用的,不是受到这一被标签化的现象本身的影响,而是这些作者特殊的个人及官职背景”,“这些作者之间确实存在着非常多的私人关系。而且,他们通常都有居士的身份,在他们生平的某些阶段,也曾担任维护思想正统的官职”。(33)田海:《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第181页。确实,明清时期,攻击宗教异端与“邪教”最力的不一定是官府,而是自诩为正统的宗教界人士或是居士,居士中若有曾经受过儒家正统教育的官员,则攻击最力。
田海还根据后世官员在解决具有相同特征的问题时查阅相关记载与案例的经历,来说明“白莲教”名号的建构。比如有关1557年集体恐慌的史料,“不断地为理解和描述后来发生的事件以及理解某一行为的进程提供范例”。这一思路在1622年的白莲起义中被再次强化,“1622年起义以及对这些事件的不同处理(史实上的与小说中的)所导致的后果便是,在文人学士精英看来,白莲教、叛乱、宗教教义、巫术之间存在关系,而且这种观念也越来越根深蒂固”。此后,“任何宗教团体都可被归于白莲教,因而任何团体都有煽动叛乱的嫌疑。这一观念开启了永无止境的迫害之门,而设定迫害界限的除了主管官员的个人观念及偏向以外,别无其他”。(34)田海:《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第145、175、166页。
至于这一现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田海这样分析道,晚明时期,“科举体系已经开始非常成功地维护着极端狭隘的正统思想:朱熹的理学成为标准,任何事情都必须以此为准绳。而且,宗族世系的理想不断发展,其强度与影响已然不可小觑,而宗族理想与民间佛教行为是直接抵触的。明朝的文人学士通常依靠宗族的财力支持以完成学业、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如果加入反对宗族理想的宗教,必然会使自己疏远自己的宗族,无法完成自身学业”。到晚明时,“精英阶层与非精英阶层的民间佛教徒之间的分歧不断扩大,使得宋元时期大规模存在的集体活动以及宗教、哲学之共同繁荣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35)田海:《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第182页。这种观点与我们正统史学中的明清时期是“封建专制集权达到鼎盛”的观点颇为一致。
四、比较性评价
我们知道,南宋高宗绍兴初年茅子元创立的白莲宗崇奉阿弥陀佛,后来的所谓白莲教则崇奉弥勒佛;白莲宗是净土宗异端,白莲教则被所有正统宗教排斥。对白莲教这一概念不加辨析的使用是否是一种群体无意识或下意识?其实杨讷、戴玄之(36)戴玄之:《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第103页。等学者对白莲教、白莲会、白莲社等概念都做出过分析,因为针对的目标是一时一事的,故最终结论遂归于白莲教之真实存在。田海系统地分析了长时段历史背景下“白莲教”这一概念的语义变迁,认为“宗教团体具有潜在的反叛性特征基本上是模式化观念的产物,正如它们被认定缺乏改进,或者是背离了已经确立的佛教、道教、儒学传统。我期望我的研究可以使宗教团体最终脱离模式化观念与历史神话的束缚。尽管思想意识的迫害史与这些团体的社会宗教史是紧密纠缠在一起的课题,学者在对它们进行分析的时候还是应当有所区分”。他评价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宗教的研究“还没有突破纯粹的描述阶段”。(37)田海:《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第227、221页。实则不尽然,中国学者以考证见长,国外学者以理论见长,各有特色。但在白莲教本身之模糊不清与相关史料有限的情况下,视角的转换无疑是研究的重要突破点。欧大年评价道:“这部书反对了一些学者的观点,包括我自己,曾经使用这一术语来指代一种类型或类别的大众宗教教派。……这部著作结合了细致的文本研究与严谨的分析,是一个重要的新贡献。”(38)Barend J. Ter Haar,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review by Daniel L. Overmyer,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1, No.4 (Nov.1992), pp.908-909.韩森(Valerie Hansen)认为:“田海的《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一书坦率地说是一部杰作。宽广的视野,横跨宋到清数朝,指出白莲这个词开始作为一种自我参照,或者本名,在16世纪退化成为一种贬损的标签。”(39)Barend J. Ter Haar,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review by Valerie Hansen,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79, Fasc.4/5 (1993), pp.367-374.德国莱比锡大学的苏为德(Hubert Seiwert)认为:“田海的书是一部内容充实且令人兴奋的作品,值得认真审视。也是一项充分纪录历史信息,充满鼓舞人心的解释的研究。”(40)Barend J. ter Haar,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Sinica Leidensia 26, review by Hubert Seiwert, Monumenta Serica, Vol.42(1994), pp.521-529.加州州立大学的石汉椿(Richard Shek)称赞此书“是一项关于中国民间宗教历史上白莲传统/运动的发人深省的具有修正意义的研究。它挑战了长期存在而且至今仍旧被采用的(历史上)存在着一个连续的白莲传统的观点”。(41)Barend J. Ter Haar,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review by Richard Shek,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Vol.3, No.1, Spring 1996, pp.274-277.
当然,质疑之声也随之而来,田海博士论文导师之一的韩书瑞教授就认为该书“追述了白莲教教义的早期历史,并争论说,‘白莲’是由明清教派的敌人用来称呼它们的名字,是教外者所贴的‘标签’,所以严谨的学者应该避免使用这一术语。尽管我同意他的逻辑,但在他对这一熟悉的名称的怀疑上,我感到很遗憾。这个名词强调了这一宗教内部的联系,我相信它拥有足够的标识性和内聚力,可以成为自己的名字。由于缺乏这样一个单独的名称,我们被限制在各种模糊的替代名称上,但它们并不能够充分强调这种共享的历史和信仰。这些替代名称包括:民间宗教运动(popular religious movements)、异端教派(heterodox sects)、异议教派(dissenting sects)、中国教派主义(Chinese sectarianism)、中国教派宗教(Chinese sectarian religion)、民间教派主义(folk sectarianism)、大众教派主义(popular sectarianism)、秘密宗教、民间宗教、民间秘密教派。所以,称为‘白莲教’会更简单些”。(42)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刘平、唐雁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中文版“序”,第2-3页。笔者也曾经提出,“白莲教虽然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形成,但它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宗教或组织,只是成为后世种种教门、秘密宗教的代名词或曰一种历史现象而已”。(43)刘平:《中国秘密宗教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4页。
那么白莲教这个概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备宗教迫害的含义呢?嘉庆帝关于“川楚五省白莲教大起义”的评论表明,政府往往不是出于宗教因素的考虑而是镇压反叛的需要,“至于白莲教之始,则为骗钱惑众,假烧香治病为名,窃佛经仙箓之语,衣服与齐民无异,又无寺宇住持,所聚之人皆失业无赖之辈,所以必流为盗贼,是又僧道之不若矣。然天下之大,何所不有?苟能安静奉法,即烧香治病,原有恻怛之仁心,在朝政之所不禁,若藉此聚众弄兵,渐成叛逆之大案”;“夫官军所诛者,叛逆也,未习教而抗拒者杀无赦!习教而在家持诵者原无罪也。……故白莲教与叛逆不同,乃显而易见之理。设若贼营中有一二僧道,岂尽行沙汰二氏乎?有一二生员,岂遂废科举之典乎?然则白莲教之为逆者,法在必诛;其未谋逆之白莲教,岂忍尽行剿洗耶?白莲教与叛逆不同之理既明,则五年以来所办理者,一叛逆大案也。非欲除邪教也。然聚众敛钱,终流为不靖,是在良有司实心训导”。(44)清仁宗:《邪教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室、资料室编:《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5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5-166页。苏为德也指出,“官员已经学习的历史经验教给他们:在动乱的时期,这种结构(跨省的教派网络)很容易转变成叛乱的核心。对中国官员而言,其最重要的职责是阻止社会动乱,而动乱的原因主要是宗教的还是经济的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具备一个超地方性的通信网络的宗教团体参与到了其中。更重要的是宗教教义经常通过提供必要的煽动民众的宣传证明其能力”。(45)Barend J. Ter Haar,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Sinica Leidensia 26, review by Hubert Seiwert, Monumenta Serica, Vol.42(1994), pp.521-529.可以说,很久以来,宗教或秘密宗教之聚众-造反功能是皇帝及其官员最为关注的。
传统观点认为,“白莲教是一个历史性的、(或)社会性的宗教团体”。(46)田海:《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第220页。似乎从茅子元开始,白莲教就逐步形成、发展,一脉相承,直至明清时代。后来的观点认为白莲教只存在于元代(马西沙)或形成于元末(连立昌),白莲教在明清时代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众多的新兴教派。田海认为历史上的“白莲教”只是政府和文人制造的概念,而事实上存在着一条从茅子元到无为教(包括僧人祩宏、憨山德清等)的绵延不断的白莲传统的线索。其实无论是杨讷,还是田海,都在追寻一条宗教传统延续的线索。换言之,即寻找断裂之外的继承性。就田海而言,他论述的重点在于质疑“白莲教”的概念,对这种继承性的论证尚有欠缺,比如从白莲宗到白莲教、从崇奉弥陀到崇奉弥勒的转化,以及类似教派为何被贴上“白莲教”的标签等问题。在史料并不充分的情况下,民间教派的发展存在着多源并存式发展的可能,即并不仅仅只是茅子元继承了慧远的莲社遗风,众多自称白莲的教派可能是与茅子元、普度并存的白莲信仰者。
故而,窃以为,如果说历史上确有白莲教的话,那是专指南宋茅子元创立的白莲宗,属于佛教净土系统,因白莲宗并未以此自称,故属于外人指称;后世意义上的“白莲教”,乃明清王朝对于各种主要含有弥勒救世思想的民间教派的攻讦之词,或曰标签性用语;同时认为,由于传统惯性的原因,用“白莲教”指称那些具有融合白莲宗、摩尼教与弥勒信仰等宗教教义,后来又糅合佛、道、巫术(如扶乩)的民间教派未尝不可,但要注意区分“标签”与“史实”、宏观与个案之间的差距。
明清时期的教派与白莲教的联系主要是在组织形式(推动正统宗教世俗化)方面。以茅子元创立的白莲宗为代表的民间教派组织,打破了正统佛教及其背后的皇权束缚,深入民众之中,促使教义、修行方式、组织形式都尽量符合民众的实际需要,成为佛教世俗化的重要力量。明清时期民间教派的发展繁荣与佛教在这一时期的衰落蜕变(民国时期人间佛教的兴起),显示出中国宗教的发展趋势。